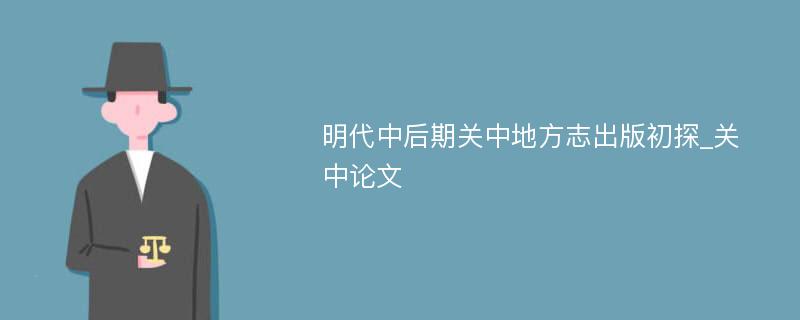
明代中后期关中方志出版探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中论文,明代论文,后期论文,探微论文,方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图书编辑与出版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具有独特面貌。在版本学中,编辑与出版分别对应纂修与刊刻。特定时代与特定地域方志出版研究,实有裨益于编辑与出版学科之完善与深化。据《明史》卷四二《地理志》,[1]关中主要包括西安府大部分和凤翔府全部。其中,西安府领华州、商州、同州、耀州、乾州、彬州六州三十一县,除商州不在关中外,余皆属焉;凤翔府含陇州一州七县。明代正德以前关中方志编辑与出版甚为寥落,正德至崇祯年间则大为兴盛,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本文以正德至崇祯年间为明代中后期,[2]重点观照正德至万历四朝,对明代中后期关中方志编辑与出版进行考述,并就正于方家。 一、地域与时代分布格局 明代中后期关中士人在康海《武功县志》和韩邦靖《朝邑县志》等典范之作的影响下,编辑出版了大批质量上乘的方志类书籍,掀起蔚为壮观的方志出版热潮。 1.质量上乘提升出版影响 质量是出版的生命线,明代中后期关中方志类书籍可堪称道者比比皆是。中华民国《潼关县新志》冯光愚序称“明代名志多出于秦”,并指出“脍人口者约十种”。是书肖万康序引清代山东学者王士祯语云“关中名志甲天下”,[3]高度评价明代关中方志。王士祯《蚕尾集》卷二《新城县新志序》又云:“以予所闻见前明郡邑之志,不啻充栋,而文简事核,训词尔雅,无如康对山之武功,其他若王渼陂志鄠、吕泾野志高陵、韩五泉志朝邑、乔三石志耀、胡可泉志秦、赵浚谷志平凉、孙立亭志富平、汪来志北地、刘九经志眉、张光孝志华。其地率秦地,其人率秦人也。故予尝谓前明郡县之志,无愈秦者,以其犹有《黄图》、《决录》之遗焉。”[4]王士祯所列方志大部分修于正德至万历年间,作者多为关中人,纂修之地亦多在关中,显示出明代中后期关中方志兴盛程度。其中,康海《武功县志》、王九思《户县志》、吕楠《高陵县志》、韩邦靖《朝邑县志》、乔世宁《耀州志》、孙丕扬《富平县志》、刘九经《眉县志》和张光孝《华州志》,更是被后世称为“关中八志”。清嘉靖《咸宁县志》高廷法序称“关中称名志者七”。《四库全书》收入县志凡三部,其中属于关中此间的有《武功县志》和《朝邑县志》二部,明代中后期关中方志质量与影响可见一斑。 2.数量众多推动出版“集团化” 据王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5]和《陕西省志·著述志》,[6]明代中后期关中方志在正德、嘉靖、隆庆至万历三朝出现纂修与刊刻高潮。其中,府、州、县志数量最多,质量最佳,为明代中后期关中方志之主体。此外还出现了具有开创性的卫所志书。《明史》卷九七《艺文志》载:“孟秋《潼关卫志》,十卷。”[7]西安府关中部分辖华州、同州、耀州、乾州和彬州五州,凤翔府仅辖陇州。除陇州无州志外,西安府五州均有州志。西安府直领十四县,除分治府城西东的长安和咸宁二县倚郭和兴平一县无方志出现,余皆有志。凤翔府直领八县,除凤翔、麟游和千阳三县外,余县皆有志。如此密集的方志编辑与出版,推动方志“集团化”出版热。 3.屡次续修促成出版持续性 有些方志有明一代不止一次纂修。嘉靖六年(1527)张琏纂修《耀州志》二卷,并于嘉靖二十年(1541)重刊;嘉靖三十六年(1557)李廷宝修、乔世宁纂《耀州志》十一卷,附录一卷。正德四年(1509)池鳞纂修《彬州志》,仅存康海、池鳞序文二篇;嘉靖年间姚本修、阎奉恩纂《彬州志》四卷;万历二十七年(1599)杨廷裕重刊,增序一篇,二者均已亡佚。嘉靖二十年(1541)南大吉纂修《渭南县志》十八卷;万历十八年(1590)南轩续修南大吉原本《渭南县志》十二卷;天启元年(1612)南师仲增订南大吉原本《渭南县志》十六卷。嘉靖王九思纂《户县志》;万历四十六年(1618)刘璞修、赵崡纂《户县志》十一卷。正德四十年(1612)王道修、韩邦靖纂《朝邑县志》二卷;万历十二年(1584)郭实修、王学谟纂《续朝邑县志》八卷,为《韩玉泉集》附刻本。万历八年(1580)杨光溥纂修《同官县志》;万历四十六年(1618)刘泽远修、寇慎纂《同官县志》十卷;崇祯十年(1637)孙尚标增补万历四十六年(1618)抄本成《同官县志》十卷。方志续修或再版,显示出方志出版极强的生命力,促使方志出版常态化。 二、内外部因素共同营造良好出版环境 明代中后期关中方志繁荣离不开社会环境、出版资源与印刷技术优势的共同作用。 1.社会环境宽松催生繁荣 明代中后期关中方志出版形成井喷之势得益于明代社会风气。明代中央王朝出于军事和政治等考虑,高度重视舆地资料的整理与编纂,并屡次诏修志书,特别是科举、书院、理学、教育等的日渐发达,为方志写作与编辑、出版及再版提供了土壤,以至于出现了“天下郡县莫不有志”的现象。 方志社会功能深得统治者喜爱。明永乐《蒲城县志》云:“邑不可无志也,乃博采群议,搜辑旧闻,爰取关于风化,足永劝惩,涉于沿革,以备观览者若干。”方志除记录乡邦地理、文化与历史等功能,还具有净化风气与教化民众之功效。这些作用为统治者所需,故朝廷多次要求各地修志。 2.出版资源丰富创作条件 出版资源是与出版产品直接相关的各种要素之集合。其中,选题资源作为核心资源,包括历史资源、文化资源、作者资源等。关中方志异彩独放得益于特殊的地域文化。一者,关中历史悠久,人才辈出,浓厚的人文氛围和丰富密集的文化遗存、遗迹为方志类书籍写作提供素材,韩邦靖《朝邑县志》王道跋云:“(王)道始至蒲,临河而西望朝邑,即状其山河之美比八境,左唐关,右隋宫,尽揽其古迹之盛比八廓,闾里辉联,后先掩映,则又叹其人物之秀且盛,果非他邑比也。”一者,关中方志写作与编辑传统源远流长。关中人司马迁所著《史记》和班固所著《汉书》,为史书编写提供准例。从两汉至南北朝,关中地志以《西京杂记》和《三辅黄图》最为人所称道。唐凌准《彬志》为关中乃至陕西残存最早州志之一。北宋宋敏求纂修《长安志》二十卷,是关中现存最早的成型方志,也是全国现存第一部完善的方志。南宋程大昌《雍录》、元李好文的《长安图志》、骆天骧纂《类编长安志》均有可观者。明代中后期关中方志正好与此优良传统一脉相承。 作者与编者资源在出版资源中具有主体地位。方志写作与编辑在古代以纂与修之方式呈现。修者是书籍编辑,主要以当地官员主持,并向当地乡贤约稿。韩邦靖《朝邑县志》王道序云:“川塬改革,此其大者而弗著,后之人何考焉?他可知矣。县尹陵川王君曰:‘是志且不传,然乌可以但已邪?’乃以五泉韩子,韩子于是乎编焉。”[8]王道向韩邦靖约稿编写县志,于是在署名问题上就出现了王道修、韩邦靖纂的情况。韩邦靖《朝邑县志》康海序云:“朝令、邑陵川王君莅县之明年,以五泉韩子汝庆所撰《朝邑志》刻成,谓予宜序诸首。”可见第二年县志即已刊刻,康海还为之作序。 作者队伍主要是学者和作家,其中一部分由关中学派的学者充任。张载为关中学派肇端。张载理学思想蕴涵了两个思想维度,“为往圣继绝学”是对历史传统之守护,“为万世开太平”是经世致用之宣扬。明代关中学派承张载、吕大临、李复、杨奂等理学大家,并在王恕、薛敬之、吕楠、冯从吾、王征等人努力下继续发展并不断传播。其或著书立说,或创建书院,或四处游学,从而以书院为中心聚集了大批人才,为方志写作与编辑提供了作者群体和编者队伍。尊古与尚实是关中学派的旗帜,“资军国,益劝戒”之方志无疑与此合拍。正是在此种风尚之下,学者积极投入方志写作与编辑之中,现存明代中后期《陕西通志》二种均为关中学派学者所编纂,一为嘉靖二十一年(1542)赵廷瑞修、马理和吕楠等合纂《陕西通志》四十卷,一为万历三十九年(1611)汪道亨修、周宇和冯从吾等合纂《陕西通志》三十五卷首一卷。 明代中后期方志作者也包括一批以文章名世的作家,如武功县康海和户县王九思等人,均在方志纂修方面具有重要示范作用。康海和王九思甚至位列“前七子”,是明代关中著名作家,才华与学识均造极一时,在地方德高望重,具备纂修方志之能力。特别是关中士人因政治失意,纷纷回归乡梓,归隐赋闲,从而有相对充裕的时间整理乡邦文献,发展当地文化事业,从而引领关中文学风气。此外,作为土生土长的关中人,他们于当地地理、历史、文学、民俗、乡贤等相对熟悉,无疑,关中士人之回流,恰好为方志编纂提供了“人和”。此外,有些士人在方志编辑方面经验丰富,如南大吉在知绍兴府时,于嘉靖元年(1522)纂修《绍兴府志》十二卷。退居关中后,于嘉靖二十年(1541)再编《渭南县志》,可谓得心应手。 康海和韩邦靖是关中方志写作领袖。康海《水仙子·甲午元日》云:“今春喜值六旬年,花甲虽周愧子先,登科误上麒麟殿。被人呼司马迁,又何曾记史题玄。名姓随他唤,风流且自怜,肯空过罨画山川。”[9]词作于嘉靖十三年(1534),是时康海六十岁。词中提及自己被人称为司马迁,虽为过誉,其在关中方志界之地位可见一斑。 在编辑过程中作者广泛交流并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群体。王九思评吕楠《高陵县志》云:“其言约而尽,其事赅而彰,其议允而确,太史氏笔也!”方志作者以序跋与评语等辅文形式,共同提升书籍品位,亦可以看出在撰写方志过程中,他们互相切磋,书序做跋,共同将明代中后期关中方志推向高潮。 3.印刷技术高超提供基础 明代中后期关中方志类图书出版得益于明代关中得天独厚的书籍刊刻条件。唐代以长安为都,故而在长安图书刊刻十分兴盛。唐亡以后,图书事业随之衰落,直至明代因靠近刻书中心山西平水,才稍有起色。以有明一代全国书籍出版业而论,关中刊刻技术高超。“仅就方志而言,嘉靖一朝所刻印者即有近四十种,堪称明代陕西雕版印刷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10]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卷四:“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近世甚希。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不若三方之盛。”此处之秦乃是指明代陕西布政使司,因春秋战国时期此地属秦国而得名。明代刻书兴盛以吴、越、闽三地为代表,秦地虽不如此三地,然有可观者。 三、再版中读者接受、传播与再创作 关中方志出版后消费旺盛并不断重印再版。这首先得益于关中方志在编辑上以精简为主,便于读者阅读;另外,一些方志系出名家,故而深受士人追捧,市场上供不应求,得之者视为珍宝。如明万历四十五年《武功县志》卷四云:“词林之士,冀得一帙,兢获自惊。惟是刷印无虚日,而磨勒竟至模糊,检阅之际,令人饮恨。”[11]康海《武功康志》冯玮正德初刻本刊行之后,因是名人名志,慕名者尤其是当地官员与社会名流竞相刷印,以之馈赠亲友上宪,视为礼货。频繁刷印致使板片受损,竟致版刻字迹模糊,历经补板递修,初刻初印本已极为罕见,后印本存世甚少。 关中方志成为后世方志模仿之典范,并形成了续修传统。清康熙元年(1622)李绍韩修、张文熙纂《武功县续志》三卷刊刻;雍正十一年(1733)沈华修,崔昭、孙景烈等四十余人纂《武功县后志》四卷刊刻;清嘉庆十九年(1814)张树勋修,王森文、党行义等十八人纂《续武功县志》四卷刊刻;清光绪十四年(1888),张世英修、巨国桂等四十四人纂《武功县续志》一册;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高锡华修、张尚谦纂《武功县乡土志》二十大目。 后人以序跋、书评、钤印、典藏、眉批、校勘、句读等方式对这些方志进行再创作。康海《武功县志》卷首有吕楠书序、何景明撰并书序、赵崡重刻撰序、玛星阿新刊书序、孙景烈新刊书序、张洲书序、董教增《续武功县志》撰序,卷末有冯韶书跋、杨武跋、崔昭《武功县后志》跋、张树勋《续武功县志》跋,并有胡瓒宗、王士祯、陈宏谋、宋荦诸家评语,张筠、桂殿盈、孙燮和魏大作校字。仅就乾隆二十六年(1761)康海《武功县志》重刊而言,就有孙景烈评注,玛星阿参订,耿性直、王应槐、孙景熙、何瑞等校勘。此间关中另一部名志韩邦靖《朝邑县志》卷首有康海序、韩邦靖序、吕楠序,卷末有王道跋。诚可谓之“热闹非凡”,此种现象确乎罕见。不惟当时,关中方志创造了古代出版史上一个奇迹。仅以乾隆二十六年重刊本《武功县志》眉批而论,孙景烈或是点评,如“叙述千年沿革,简净详明,笔笔有法,极为疏古”,“结语精,笔亦有力”,“文简劲可式”,“笔墨轻清可爱”等;或是校勘,如“他本‘七’作‘士’,误”,“‘懼’当作‘瞿’”;或是指陈康海之失,如“夏秋赋与总数不合”。将评注引入方志使得志书再版时质量不断完善,其地位与影响也相应扩大。由此可见这种方志在当时出版后影响之巨。 明代中后期关中方志类书籍是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与图书资源,因此我们有必要将现存馆藏方志整理与开发,做好校勘、笺注、标点、今译、影印、排印、汇编等工作,统一字体为通用字体,利用多媒体技术实现数字出版,以便传承与传播,让更多读者和学者阅读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