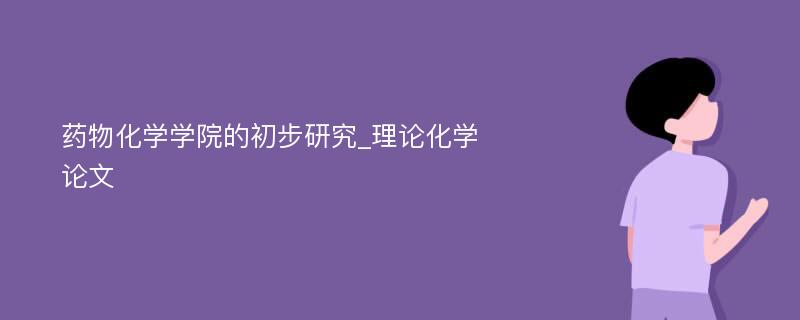
医药化学学派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派论文,化学论文,医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法分类号 O6—09
化学与医学的关系源远流长,密不可分。在化学这门科学产生、演化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几乎到处都可以找到医药学家或药剂师们辛勤耕耘的足迹。当化学还处于原始的萌芽时期,它就与医学和药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古代炼金术被视为化学的原始形式,无论是中国的炼丹家,如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还是阿拉伯的炼金家,如札比尔、拉泽等,几乎都是医学高手,并且为化学的演进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由于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的差异,欧洲中世纪的炼金术几乎与医学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但文艺复兴以后,随着炼金术的日趋没落,一批有识之士终于冲破了荒诞虚幻的炼金术的束缚,开始转向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医药化学,形成了一个阵容强大、影响深远的医药化学学派。正是由于16—17世纪的医药学家们以勇于同旧传统决裂的革命气概,以及注重实际、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使化学逐渐走出炼金术的困境,向着健康的道路迈进。一大批医药学家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不仅为近代化学的建立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实验资料,而且初步形成了近代化学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成为古代化学向近代化学过渡的桥梁。也正是由于医药学派的影响,直到19世纪末,化学的每一个进步几乎都与医学有关,许许多多医学出身的化学家的足迹几乎遍及整个化学领域,为化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试图通过对医药化学学派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特点的历史考察,阐明其对化学的建立和发展所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以揭示化学学科发展的规律性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内部矛盾运动。
1 医药学派的兴起
15世纪以来,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工场手工业和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从而加速了封建社会的解体和人们意识形态的转变;新航路的开辟不仅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积累了雄厚的资金,开辟了广阔的市场和建立了殖民地,而且大大开阔了欧洲人的眼界,促进了科学冒险精神的觉醒及天文学、航海、力学、地理学等诸多学科的勃兴。始于意大利并波及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是新兴资产阶级为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内取代封建统治阶级而发起的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化大革命,是自然科学与宗教神学的一场生死大博斗。文艺复兴的后果不仅直接促进了欧洲文学艺术的高度繁荣,而且赢来了自然科学独立发展的地位。从此,自然科学终于挣脱了宗教神学的桎梏,开始以迅猛的速度腾飞。医生出身的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动摇了宗教神学的基础;德国天文学家开卜勒则进一步发展了哥白尼的“日心说”,提出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医学系毕业的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的《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不仅捍卫了“日心说”,而且奠定了近代实验物理学的基础;比利时医生维萨里的人体解剖学说和西班牙塞尔维特及英国哈维提出的血液循环学说猛烈抨击了教会宣扬的上帝造人的神话,对传统医学和世俗偏见提出了挑战……。医学家们在科学革命的洪流中奋勇向前,成为许多领域的开拓者和殉道者。正是这些名垂千古的英雄人物吹响了近代科学精神的号角,成为科学新时代到来的鲜明标志。科学革命的急风暴雨荡涤着旧世界的各个角落,使人们的自然观、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都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变革。当时仍处于幼年时期的化学也毫无例外地经受了这场科学革命的洗礼。在欧洲,持续了几百年的炼金术遭到人们普遍的嘲笑和批判;日趋严重的神秘主义和一些江湖骗子的欺骗行为使炼金术在官方眼里再次变得声名狼藉,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就曾颁布过取缔炼金术的敕令[1];诗人但丁则把炼金术打入地狱;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乔叟在《卡农·耶奥门的故事》中对炼金家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鞭挞。然而,由于化学变化的复杂性和隐蔽性,化学的进步并不象天文学或物理学那样迅猛。尽管如此,它仍以显而易见的方式在演进。新科学精神的感召促使化学去寻找自己的出路。
16世纪以来,欧洲化学是沿着炼金术、工艺化学和医药化学这三个方向发展的。尽管屡试屡败的炼金术日益遭到人们的指责甚至官方的禁止,但长期流行的炼金术思想和传统依然根深蒂固,人们仍然难以从理论上证明其虚幻和荒谬,仍有一批炼金术士在惨淡经营,继续做着点石成金的黄金梦。每况愈下的炼金术显然已是苟延残喘,在新的历史时期成了化学发展的最大障碍;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刺激下,一些注重实际的工艺化学家在已往积累了相当可观的经验知识的基础上,致力于采矿、冶金、酿造、染色、制酸等实际化学生产的考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以后化学和化学工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坚实的基础。但这批讲求实用的化学家对自己的研究常常缺乏理论分析,因而不为当时崇尚思辨的哲学家所重视。面对炼金术所处的穷途末路的困境,越来越多的炼金术士有所觉悟,开始比较注重实际。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城市扩大,人口相对集中,各种疾病和瘟疫的流行,给人们的生活和生命造成极大威胁,一些炼金家开始改弦更张,纷纷把化学知识应用于寻求治疗各种疾病的药物。于是从16至17世纪的100多年间,在欧洲形成了一个对化学发展至关重要的医药学派。一大批医药学家勇敢地冲破了古代思辨哲学和炼金术的束缚,力图创建新的化学和医学理论。他们以强烈的革新意识和科学求实精神制备和提纯了许多化学物质,并研究它们的性质和药理作用。这不仅大大促进了医学的发展,而且给化学领域吹来一阵清新的凉风,扭转了化学发展的方向。医药化学成为这一时期化学发展的主流。
医药学派的创始者和杰出代表人物当推瑞士医生帕拉塞斯(P.A.Parracelsus,1493—1541)。他在矿区长大并学习过医学, 良好的冶金学和医学知识使他在科学革命中得以大显身手。他首先把炼金术和医药化学结合起来,认为人体本身的生理活动就是一个炼金过程,各种疾病的产生是由于人体内硫、汞、盐三种要素的比例失调所致,并提倡用化学药物加以治疗,从而开创了“化学医术”的新医学。帕拉塞斯虽然也相信炼金术,但却认为炼金术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炼制金银,而是为了制造药物[2]。他给炼金术下了一个更加广泛而实用的定义, 认为“凡是把天然原料转变成对人类有益产品的过程”[3]都可称为炼金术。金属冶炼、药物制造、食品加工等任何对人类有益产品的化学过程和生物过程都属于炼金术研究的范畴。帕拉塞斯运用化学的方法制取药品,并广泛用于治疗各种疾病,大大修正了以往的医学理论。为了制取各种药物,他用许多金属进行了一系列反应,制得了各种金属的盐溶液,并归纳出了一些化学反应的一般特征[4]。 他的学说从根本上改变了医学和化学发展的道路。帕拉塞斯的追随者、德国医药学家李巴乌 (A.Libavius,1540—1616)把当时分散在炼金术、制药学、冶金学中的化学知识加以综合,编写了著名的《炼金术》一书,确立了17世纪德国化学教科书的传统,教育了几代化学家。他还进一步指出:“炼金术是通过从混合物中离析出实体的方法来制造特效药物和提炼纯净精华的一门技术。”[5]炼金术目标的重大转变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实际上是对炼金术的一个有力批判。炼金术含义的扩大,大大拓宽了化学研究的范围,而各种化学物质的分离、分解和提纯又为近代化学元素概念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实验方法。德国医生兼冶金家阿格里克拉(G.Agricola,1494—1555)通过在矿区多年的实地考察,写出了著名的《论金属》十二卷,详细记叙了金、银、铜、铁、锡、铅、汞、锑、铋等金属的冶炼、提纯、分离等工艺过程,成为16世纪最高的工程师。德国的格劳贝尔(J.R.Glauber,1604—1668)受过良好的医学教育,也从属于医药学派。他不仅出售各种药剂,而且试图用化学亲合力来解释一些金属或金属氧化物的反应[6],努力总结化学反应的某些规律性,并成为研究和制备酸、碱、盐方面享誉欧洲的专家。
比利时医学家海尔蒙特(J.B.van Helmont,1579—1644)继承和发展了帕拉塞斯的学说,成为医药学派的又一位杰出的代表人物。他反对空想和思辨,提倡独立思考和科学实验,为以后化学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因在气体化学方面的成就卓著而被誉为“气体化学之父”[7],成为18世纪气体化学研究的先躯。是他首先区分了气体和蒸汽,初步揭示了气体及其变化的物质性,制备出了二氧化碳、二氧化硫、二氧化氮、氢气等多种气体,并制取了许多化学药物。他还提出了酵素的概念,尽管相当简单粗糙,但在不少方面与近代酶学说相似[8]。
作为化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化学借助于医学步履蹒跚地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终于在17世纪末才确定了自己研究的对象,以独立学科的面目迈向近代化学的新征程。
2 医药学派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上的特点
医药化学的兴起受到科学革命的熏陶,适应了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医药化学学派不仅为古代化学向近代化学的过渡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而且在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上具有许多不同于古代化学的特点。
首先,医药学派的化学家不迷信传统学说,富有强烈的怀疑批判意识和锐意创新的精神。他们反对教皇统治和不合理的等级制度,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独立自由和平等的,反对盲从,提倡独立思考。他们之中的大多数虽然仍然相信炼金术,但却能根据社会需要,大胆冲破炼金术传统的桎梏,把炼金术推广到更加广泛和实用的领域,呼吁医生们把化学知识应用于医疗实践,唤起更多的炼金家抛弃寻找哲人石和点石成金的梦想,走出苦心经营了几百年的死胡同,给化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生命力。医药学家们藐视古代思辨哲学和各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勇于创立新的化学观和医学理论。1527年,帕拉塞斯在巴塞尔大学讲授医学时,就象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烧毁罗马教皇的圣谕一样,当众焚烧了一直被人们奉为经典的古罗马医生盖伦和中世纪阿拉伯医生阿维森纳的著作,以表示与权威教条决裂的决心,充分体现了一位化学改革家的气魄和批判精神,被誉为“化学中的路德”。帕拉塞斯还大胆摈弃了自亚里斯多德以来的“四原性说”,提出了著名的硫汞、盐“三要素说”。不仅用于解释世界万物的组成,而且作为自己新医学的理论基础。盖伦的四大体液说认为,人生病的原因在于体内四种体液不平衡,主张用动物和植物汁液来恢复体液的平衡;帕拉塞斯则认为疾病的产生是由于人体内的三种要素比例失调,主张用无机药物来改善三要素的比例,就可以去病强体。帕拉塞斯及其信徒们还比四原性说更进一步,强调用火可以把物质分解成元素。虽然这种方法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正确,但却促使人们去思考、寻找分解物质组成元素的新方法。海尔蒙特曾系统阅读了古希腊医学著作后感慨地说:“我十分惊叹地发现,我付出的辛勤劳动和花费多年的光阴几乎全都浪费了。”[9] 因此他对因袭守旧的医学和古代自然哲学进行了严苛的批评,并指出了科学研究的方向:“摧毁古人的全部自然哲学,并创立自然哲学学派的新学说。”[10]这正是16—17世纪医药化学家破除迷信、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的真实写照。海尔蒙特抛弃了亚里斯多德以来的四元素说,也不苟同于帕拉塞斯的三要素说,提出了水是世界万物本原的一元论的元素观。批判和创新是科学发展的灵魂,以后的化学家正是继承和发扬了医药学派的这种叛逆精神,才不断在化学发展的道路上开拓进取。
其次,医药学派继承和发扬了古希腊人热爱自然、崇尚真理的科学精神,注意探求隐藏在自然现象背后的规律性。在中世纪的欧洲,封建迷信盛行,基督教会漠视个人主张,宣扬不学无术才是最虔诚的母亲,把希望和幸福寄托于虚无飘渺的来世。古希腊科学精神和学术传统已荡然无存。医药学家们虽然仍信仰宗教,但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却采取了世俗的态度,放弃了各种超自然的观念,不计个人名利地位,潜心从事自然科学研究。海尔蒙特出身名门贵族,却不愿过豪华的宫廷生活,甘愿在充满油烟的实验室里从事默默无闻的科学研究工作,把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和为人类治病当作自己最大的快乐。正是这种崇尚自然和热爱真理的科学精神,逐渐形成了一种科学合理性的社会新环境,培育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不计清贫,乐于此道。正如亨利·奥尔登伯格所说:“杰出的先生们,打消惊扰我们时代庸人的一切疑惧,为无知和愚昧而作出牺牲的时间已经够长了;让我们扬起真知之帆,比所有前人都更加深入地探索大自然的真谛。”[11]科学精神的形成和发扬是医药学家在化学领域中做出的重要贡献,近代化学的重要奠基者波义耳就曾把海尔蒙特等医药学家作为自己的榜样处处加以效仿,把这种科学精神加以发扬光大,并带动更多的化学家积极投身到当时还不是正式职业的化学研究中去。
另外,重视实地考察和科学实验是医药学派研究方法上的显著特点。帕拉塞斯及其信徒们竭力反对经院哲学的繁琐考证和空谈,主张进行广泛的实地考察和科学实验。他们认为单纯利用逻辑推理是不可信赖的,因为它缺乏实验依据。“人们靠内心默想绝不会知道万物的本性。眼所见的,手所接触到的才是他的老师。”[12]许多医药学家都曾漫游欧洲各地,到矿山、工厂、作坊广泛进行实际考察,获得了大量感性材料。帕拉塞斯和他的弟子们通过对各种矿物药剂的性质和临床治疗的研究,完成了大量化学物质的制备、分离和提纯工作,并根据它们的性质进行了分类。海尔蒙特是一个对实验着了迷的科学家,他扎着围裙,终日满身油烟地忙碌在自己的实验里,并自称是“火术哲学家”。他制备了许多有效药物,发现了一些当时鲜为人知的气体。他还十分重视定量研究,在实验中广泛使用天平。他所做的一些实验已经蕴含了物质不灭的思想。他的研究方法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更加接近现代化学。定量分析方法在以后经波义耳、拉瓦锡等化学家加以弘扬和发展,成为化学研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海尔蒙特还特别注意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力图通过实验证明自己提出的理论。他为了证明水是世界万物的本原及水可变土的观点,曾设计了化学史上著名的“柳树实验”和长时间蒸馏水的实验,堪称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尽管他从中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但却体现了一个真正科学家的作风。
尽管医药学家的工作已经触及到现代科学思想和研究方法,然而在总体上仍未能摆脱宗教神学和炼金术的藩篱,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还都是一些神秘主义者,在其著作中既有一些先进的观点,同时也充斥着荒诞不经的说教。帕拉塞斯仍然相信任何事物都受命于上帝,相信哲人石和灵魂的存在。他的三要素说也是受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宗教思想的启示,在炼金家提倡的硫汞基础上又加上了一种要素盐。硫代表易燃的元素或灵魂,汞是液体或精神,盐则成了固态的实体。如当木柴燃烧时,“燃烧的是硫,蒸发的是汞,变成灰烬的是盐”[13]。医药学家的元素论实际上同古希腊的四元素说都是属于一种原性说,因此也并不比以往的元素说高明多少;从总体上看,医药学派把化学的任务仅局限于制造药物,也不符合化学的本来面目,因此对化学的长远发展又有其不利的一面。医药化学从中世纪的废墟中崛起,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社会的痕迹,但化学毕竟借医学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对近代化学的建立和发展的贡献不可低估。医药学派的优良传统在17世纪以后得以发扬光大,其局限性也逐渐得以纠正。
3 医药化学的余绪
医药学家在轰轰烈烈的科学革命的感召下,藐视经院哲学的权威和各种传统观念,继承和发扬了古希腊人的科学求实精神,把宗教信仰与科学知识区分开来,以批判和创新的精神去认识自然,以探索自然界的奥秘和造福人类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努力使科学合理性得到社会公众的承认,力求建立新的科学社会环境。近代化学家们正是继承了医药学派宝贵的精神遗产,使化学研究日益走向健康和独立发展的道路。正是医学家们冲破了炼金术和古代自然哲学设置的陷井,开辟了化学研究的广阔天地。他们在自己的药房或实验室里制备了各种各样具有实用价值的化学物质,详细研究了它们的理化性质,总结了许多物质的分离鉴定方法,研究了呼吸、燃烧等化学现象,为近代化学的建立积累了大量宝贵的资料。医药化学家们把科学实验对科学发展的作用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身体力行,成为名符其实的实验家。近代化学的奠基者波义耳正是继承了医药学派的科学求实精神,把科学实验的方法引进化学。在批判了医药学派局限性的同时,明确了化学研究的方向,终于把化学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医药化学对化学的影响还远非如此。到17世纪末,医药学派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逐渐被新的化学观所代替,但这个学派对化学的影响却并没有了结。直到19世纪末的二百多年间,欧洲许多药房的实验室仍然是化学研究的中心,成为近代化学确立和发展的一支必不可少的重要力量。许许多多的化学家都受过良好的医学教育,或是药剂师和药房学徒出身,却在化学的各个领域做出了非凡的贡献。要一一介绍与医学有关的近代化学家的名字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里我们只简单列举其中的一小部分就足以说明医药学派对化学发展的深远影响。
德国医药学教授贝歇尔(Becher,1635—1682)和斯塔尔(Stahl,1660—1734)提出了在化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燃素说; 药房学徒出身的瑞典化学家舍勒(Scheele,1742—1786)在暂短的一生中发现了氧、氯、氟、锰等多种元素,制取和分离了多种有机酸,被誉为“药房里的化学家”,成为近代化学的奠基者之一;法国当过公爵御医的贝托雷(Bertlolet,1748—1822)、受过医学教育的孚克劳(Fourcrog,1755 —1809)、药房学徒出身的沃克兰(Vauguelin,1763—1829)都是拉瓦锡氧学说的积极拥护者和宣传者,为法国化学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德国药剂师出身的化学家克拉普罗特(Klaproth,1747—1811)发现了铀、锆、碲、铈等多种元素;药店学徒巴拉德(Balard,1802—1876)发现了溴; 医学系毕业的英国化学家武拉斯顿(Wollaston,1766—1828)打开了铂系元素的百宝箱;当过药房学徒的英国天才化学家戴维(Davy,1778—1829 )发现和制备了多种碱金属和碱土金属,并奠定了电化学的基础;也是药店学徒出身的法国化学家莫瓦桑(Moissan,1852—1907)首次制得了单质氟;获得医学硕士学位的莫桑德尔(Mos-ander,1787—1858)发现了镧、铽、铒等多种稀土元素;当过医药学徒的伏累森纽斯(Fresennius,1818—1897 )创立了金属元素定性分析法,成为近代分析化学的奠基者;曾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瑞典化学家贝采里乌斯(Ber-zelius,1779—1848)在无机、分析、有机化学等许多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关于原子量的测定和提出的电化二元论,使他成为19世纪初国际化学界的权威,被誉为近代化学的组织者和建设者;近代有机化学的奠基者和有机合成的开拓者维勒(Wolher,1800—1882)曾做过药房里的学徒, 是他首先用人工方法合成了尿素,开辟了有机化学的新天地;医学系毕业的法国化学家贝特罗(Berthlot,1827—1907)紧随其后,合成了甲烷、乙炔、苯、乙醇、乙酸等一系列有机物;当过药房助手的李比希(Liechig,1803—1872)被誉为“德国化学之父”,他在有机化学、农业化学和大学化学教育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开创性贡献;药剂师出身的德国化学家肖莱马(Schorelemmer,1834—1892)奠定了有机化学的理论基础; 英国医生普劳特(Prout,1785—1850)提出了具有革命意义的氢母质假说;医生出身的德国矿物学家米希尔里希(Mits-cherlich,1794—1863 )发现了对于测定原子量具有重要意义的同晶型定律;医学系毕业的意大利化学家斯达(Stas,1813—1891)确定了O=16原子量测定的新标准,为原子量的精确测定做出了杰出贡献;医学博士盖斯(Hess,1802—1850 )在热化学中提出了著名的盖斯定律;德国医生迈耶尔(J.R.Mayer,1814 —1878)第一个阐明了能量守恒定律;法国医生杜隆(Dulong,1785 —1838)提出了修正原子量的原子热容定律;医学博士、当过开业医生的亥姆霍兹(J.L.Helmholtz,1821—1890)成为热力学一、二定律的创立者之一;医学博士迈尔(Meyer,1830—1895)几乎与门捷列夫同时发现了元素周期律;当过药剂师助手的英国化学家弗兰克兰(Frakland,1825—1899)首次提出了原子价学说;药物合成大师、 德国医生艾里希(Ehrich,1854—1915 )合成了治疗梅毒的特效药物“六○六”和“九一四”;德国药物学家多马克(Domagk,1895—1964 )制得了第一个抗菌磺胺药物百浪多息……。
由于健康和治疗疾病的需要,医术很早就引起人们的重视,并最先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当物理学和化学还隶属在自然哲学的麾下时,医学在中世纪的大学里就已经作为一门主要课程。一些名医成为宫延御医或贵族的私人医生,倍受社会的尊重。但由于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医学在本质上仍然是一门治疗疾病的实用技术,在理论和方法上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占星术、魔法和巫术十分流行。加上教会的控制,使医学理论充斥着封建迷信和神秘主义,各种各样的药方都缺乏理论根据和临床经验。胆汁、血液、鸡冠、羽毛、毛发、唾液、蝎子、蛇皮、蜘蛛、地鳖等稀奇古怪的物质被广泛用于治疗各种疾病。根据盖伦的四大体液说所采用的放血法几乎成为每病必用的方法。身患疾病的人往往变得轻信,因而常常被江湖庸医甚至根本不懂医术的人所欺骗。在医药化学时期,虽然出了不少名医,也发现了不少有效的治疗药物,但医药学家的医学理论仍然十分落后。帕拉塞斯虽然也谴责占星术与医学的结合,宣称星宿与人体无涉,但他却臆想出精灵或灵气支配着人的命运。看来医学要想在诊断、治疗、理论和医药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还有赖其他学科的发展。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使医生和药物学家受到鼓舞,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虽然受到的是医学教育,但却对医学理论感到无所适从,纷纷把注意力转向非医学领域,如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矿物学等新兴学科,并成为这些学科的先躯。由于医药化学时期化学为医学提供了大量治疗疾病的有效药物,促使更多的医药学家涌向化学这片正待大力开发的绿洲沃土,这就造成在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众多的医学家或药剂师成为著名的化学家。所以在近代化学的发展中,医药学家确实为化学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与此同时,化学也给医学以丰厚的回报。化学的帮助不仅为医学提供了更多诊治疾病的医疗手段,而且发现和合成了许许多多的治疗各种疾病的特效药物,如解热镇痛药、降压药、磺胺药、抗菌素、防腐剂、消毒剂、麻醉剂等,并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医学理论。可以说,在化学孕育、确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医药学家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而化学的进步又反过来为医学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理论基础。这种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至今仍是如此。20世纪以来,一大批化学家又纷纷涌向医学领域,与医学家携手合作,为生理医学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辉煌的贡献。不少化学家荣幸地成为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开辟了维生素和激素的合成、药物化学、酶化学、蛋白质化学、细胞化学、遗传基因工程等许多新领域。同时化学也成为医学家们的必修课程,从事医学和药物学研究的人员如果不懂化学,就根本无法在医学领域站住脚。在新的历史时期,医学和化学的亲缘关系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更加亲密。自然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以自然界各个侧面作为研究对象的各门自然科学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它们相互依存、交互作用,严格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运行,并协调一致地向前发展,充分体现了人类认识上的规律性和科学发展的内部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