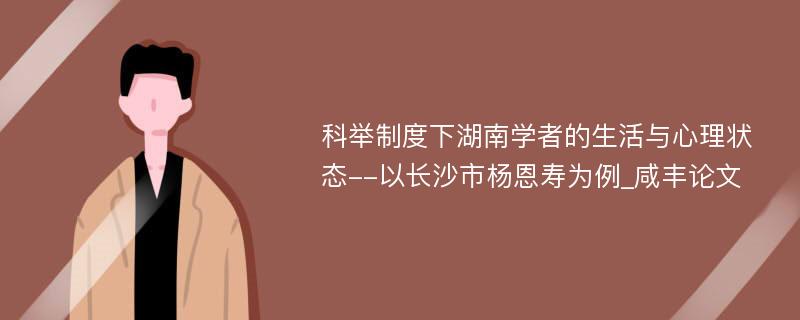
科举制下湖南士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以长沙杨恩寿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人论文,科举论文,长沙论文,湖南论文,为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G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6)05—0032—16
长沙士人杨恩寿(1835—1891,字鹤俦,号鹏海)系典型的科举士人,他17岁始应童试,21岁得秀才,25岁得优贡,经过6次乡试37岁中举,41岁第一次参加会试失败,从此放弃科举,以作幕宾和著述渡过余生。杨恩寿一生著述颇富,有《坦园丛书》14种问世,多为戏曲、传奇。另外,他还有10册未刊的《坦园日记》留下来,日记始自同治元年(1862),止于同治九年(1870)①,记录了作者此期的科举生活及其相关方面,内容十分丰富。恩寿与湖南著名士人郭嵩焘、王先谦、王闿运等人均交往数十年,与湘军人物曾国荃、李元度等人亦有不疏的交往,因此日记在反映同治年间长沙士人的生活和精神状况方面,以及反映该期湖南地方社会状况方面,有极高的社会史、文化史的史料价值。
通过对日记提供的南方内地城市士人生活样本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建立以下观点:第一、举国一体的科举体制是超越地域文化、学术传统及民风的现实存在,它对士人生活和精神状态的影响力居于绝对优势地位;第二、科举制度建构了政权与士人之间控制——依赖的关系,广大士人通过科举被纳入现政权体制内知识分子队伍,而科举制度对士人的控制效率与其为士人提供的成功几率为正比,士人对科举成功的期望则与科举制度提供的成功机遇之间张力的适度维持,是双方控制——依赖关系得以延续的基础;第三、传统社会予“士为四民之首”的崇位,并寄以“士志于道”的期许,而“志道”被社会期许的理想性与“入仕”个人目标的现实性之间的固有紧张关系的调适,也取决于士人对科举成功的期望与科举制度提供的成功机遇之间的张力。近代之前,中国长期存在人口增长背景下科举队伍基数扩大导致成功机率的持续下降,形成科举对士人的控制效率和士人道德自律水平同步下降的社会政治危机。进入近代后,这种危机非但未找到解决的办法,它还在有新的非传统性的因素介入下继续发展演变。《坦园日记》作为一份同治年间士子科举生活的实录,在反映危机的传统性、深刻性方面颇具价值。
本文的研究将主要依据《坦园日记》而展开②。
一、恩寿的家世和父兄
《坦园日记》仅是杨恩寿28岁至36岁的日记,且以记录个人文事和社会活动为主,关于作者早年(道光、咸丰年间)的生活情况,只能凭借日记中追忆往事的文字为线索加以整理。而对作者家世和家庭状况的了解,更只能依据日记中涉及家族生活的文字与县志、省志中的记载。因为家世背景对于士子的科举生活至关重要,这里必须首先对其家世展开研究。
杨氏家族祖居地在长沙城东60里左右名“山市”的地方,至早在恩寿曾祖杨正启一辈就迁居长沙城内③。有两条资料表明杨氏家族居长沙以经商为本业,且在同光年间甚发达④。其一,同治六年(1867)六月二十九日,恩寿日记载:“吾家契买西长街铺面房屋两栋”,“是日兑价”⑤。同治年中期湘军官员衣锦还乡,纷纷在长沙营建私宅,致长沙地价骤长⑥。在如此背景下一举购得市内铺面房屋两栋,既可见其时杨氏家族的财力,也可见其由经验而致的商业魄力。其二,光绪七年(1881)八月初四日,郭嵩焘日记载:“画眉冲杨氏祖茔,则杨鹏海家发冢也,气局更较大”⑦。光绪五年郭嵩焘自英法公使任提前引退,归国后隐居长沙。因其长期耿耿于同治年以来包括丧子在内的公私两方面的多难遭际,受转运愿望驱动,再度陷入寻求家族营葬吉地的迷津⑧。他在地师、友好的陪同下频频赴长沙周边地方看山脉地势,因此日记中留下上述关于杨氏家族先祖营葬地的文字。无论是郭嵩焘本人的观感或是地师的评说,“杨鹏海家发冢也,气局更较大”一说,必有杨氏家族当时在长沙的发展引人瞩目的现实背景。而长沙社会关于杨氏家族的成功印象应该主要得自其商业经营领域,而非科举仕途的领域。因为在科举仕途领域,该家族并无特别炫世的成功。
恩寿系杨氏家族在科举仕途领域成绩最著者,在光绪年间是拥有“运同衔湖北知府”衔的举人⑨。恩寿六兄彤寿(1823—1877,字麓生),在咸丰年间湘军的活动中“历尽戎行”,于同治年“保举文职”,先后任广西阳朔、北流、宣化等县知县,并“为父母亲请得二品封典,并貤赠曾祖父母”⑩。从恩寿父杨白元(?——1878)晚年因子而得封典的事实看,他本人在科举或仕途方面似无可观的成绩。恩寿所谓“家君任校官,垂三十年”一说,则是关于其父受聘于知县、知府等地方官员为塾师,并兼及县学、府学襄校试卷事务的游幕经历(11)。道光年晚期,杨白元的幕主系“师事姚鼐,受古文法,称高第弟子”的湖南衡州府通判何彤文,并任其子弟的塾师(12)。此亦足以说明杨白元的学识水准。恩寿“自幼侍亲秉铎宦游”,直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前后自衡州“归家”。因此恩寿早期习儒包括从事科举的前期训练,均得其父的亲手调教(13)。
二、咸丰年间恩寿的科举生活
恩寿离衡州时曾作“何年重到此,今日且归家”的豪言,显示此度“归家”意义的非同寻常。另外他自述早期科举生活的长诗,开端之句谓:“道光纪元岁庚戌,我生匆匆年十七;城南老屋方读书,半堵土墙支陋室。”可以理解其“归家”之际的豪情是因“始应童试”而发(14)。恩寿的科举生活开始两年,长沙遭逢太平军战乱的冲击。咸丰二年(1852)六月,太平军突破清军湘桂河防席卷湘南,并于七月下旬兵临长沙城下,因久攻长沙不下,于十一月弃长沙而北上。湖南全省的战乱自然致该年壬子科乡试无法举办,影响也波及咸丰五年乙卯科乡试不能举办。对于像恩寿这样已经参与科举又尚无任何功名的年轻人而言,短暂的围城动乱以及科举考试暂时的中断是不足以扰动其既定人生行程的。而咸丰四年长沙有新建求忠书院的动议,并付诸筹建。可见战乱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社会对科举及教育的政治功能的期望。长沙除乡试外的各级考试及时恢复,咸丰四年恩寿获得科举最初的突破——获秀才进县学(15)。
仅凭《坦园日记》的文字,要了解恩寿早年习儒及咸丰年间的科举生活显然有所不足。恩寿后来关系密切的友人王先谦的年谱有谱主本人和兄长的习儒及科举经历的大事纪要,这里借用补充作恩寿相关经历的背景资料:王先谦(1842——1918,字益吾)长沙人,年少恩寿7岁。先谦之父业儒,并以授徒维持家计。先谦年四岁“始入家塾”,从长兄先和(1829——1853)习儒,长兄去世后又从二兄杨先惠(?——1857,字敬吾)学。咸丰四年,先谦年十三“始应童试”,而先惠则“以府试冠军入县学”。五年,先谦“从县学生林子静先生树荣学”;六年,先谦“从黄翰仙先生锡涛学”,而先惠则于此年“补廪膳生”。七年,先谦“应县、府试皆前列”,“院试入县学第十二名”,该年湖南补壬子、乙卯科乡试,先谦、先惠同赴乡试,先谦“荐未售”,列名副榜贡生;先惠“闱前染疾,出闱九日而卒”。八年,先谦应戊午科乡试“未售”,受父命在家授读其弟杨先恭(字礼吾)。九年,先谦岁试一等第五名,补廪膳生。十年,先谦科试一等第八名。十一年,先谦父亡,先谦因“家徒壁立……糊口无资,不得已于六月赴湖北”,入湘军水师“司书记”(16)。
一般而言,家庭外的因素对于士子科举生活的干扰是较小的,子弟是否从事科举,主要取决于家庭对自身承担科举全过程成本的能力的评价,以及对子弟科举能否成功的潜能的评价。因此,尽管咸丰年间全国包括湖南地方不断的政局动乱,王先谦直至其兄、父相继去世,他必须担当起维持家计的责任时才游幕军营,而科举也才暂时退居他生活的次要位置。其时王先谦年届二十,并早在三年前已娶妻成家。士子科举生活受家庭变故的干扰,这乃传统社会中常见事例。另外,王先谦的经历也说明咸丰年间湘军的兴起固然令湖南士子多了一条投笔从戎的入仕捷径,但军营、战场毕竟为畏途,非迫于生计士子难作此种选择。恩寿的另一名年长三岁的友人王闿运(1832—1916,字壬秋)湘潭人,年十八肄业长沙城南书院,年十九得秀才入学——时在道光三十年(1850)。后曾国藩创办湘军,闿运性之所至跃跃欲试,所谓“是时曾侍郎年四十四,余年二十三,初入学,上谒論事,辄自专”(17)。尽管此后闿运仍屡有投笔从戎的冲动,但终均未见结果,后于咸丰七年乡试中举,咸丰九年赴京会试。其谋取仕途的期待仍然落实在常态化的科举考试之中(18)。
恩寿的家境自然优于王先谦,而其科举成功的潜力当也不逊于王先谦、王闿运二氏。何况咸丰年间恩寿家已有“从戎曾橐笔,捧檄为娱亲”的六兄彤寿了(19)。家庭环境和个人性情、身体条件均令恩寿安心从事科举,且自入学后“微名自兹起,声价增十倍”的学习状态也激起他更强的成功欲望和自信(20)。
关于咸丰年间的科举生活,恩寿日后的记忆充溢着温馨而欢乐的主调,这与他在各类考试中出类拔萃有关。其中最令他得意者是咸丰六、七两年间的经验。咸丰五年(1855)八月,浙江人张金镛(道光二十一年榜眼)出任湖南学政,他的莅任为湖南地方科举的全面恢复注入了动力,长沙各级科举考试得以正常举办。因张金镛督学湖南“待士甚宽”,士绅社会口碑极佳。郭嵩焘好友朱克敬籍甘肃,咸丰年间任官湖南龙山县,解任后长期留寓长沙,在湖南士绅界甚有影响,他作为旁观者评说张金镛督学湖南事迹:
张金镛督学湖南,奖诱后辈特勤,才思稍异,即召至后堂,赐酒食笔墨,劝之勤学。放黜者有佳句,辄标举之。一时才俊争愤于学。至今儒生谈海门先生故事,辄欷歔感叹。(21)
曾得提携的士子本人更津津乐道,如王闿运就曾称“平湖张侍讲提学湖南,弘奖知名之士十数人,有武陵蔡子纯、溆浦严咸、湘潭蔡毓春”(22)。恩寿则是在咸丰六年岁试后应邀出席试院“怀清堂”诗会,以诗才得张金镛赏识。张氏“称王(闿运)、杨(恩寿)、嵇(月生)、蔡(毓春)为‘四子’,比作初唐诗坛四杰(23)。得学政如此的推举,对提高社会知名度的意义非同寻常,咸丰年间恩寿在全省高才士子之列当属无疑。
壬子、乙卯连续两届乡试中止后,咸丰六、七年岁、科两试的举办带动湖南省内士子热烈的交往活动,张金镛在其中的组织、推介作用甚为重要。见《坦园日记》所载情节:
丁巳(咸丰七年,1857)之秋,张海门学使师招致怀清堂,时甫按试常澧归,盛夸安福黄生道让、武陵蔡君子纯之才,并出试卷见示,遂识二君之名,久未得晤。(24)
科举士子们通过这种交往活动相互缔结起学缘关系。这种关系其价值的重要性,在同治六年(1867)恩寿借重当年“同是受知”于张金镛的学缘步入长沙上层政界及士绅界之际有集中的体现。也正是在那样的情势下,恩寿格外有“回首师门感最长”的感想(25)。得张金镛推举的士子包括恩寿在内,均系同光年间湖南的有名士绅,其中王闿运、严咸、黄道让(字岐农)、蔡子纯(字吉六)诸人在咸丰七年补行的壬子、乙卯科乡试中举。恩寿虽没有这般幸运,但他参与乡试的早期经验还是堪可告慰,并令他对科举前程充满希望。他于“丁已年(咸丰七年,1857)初次观光,即鼎荐”;而戊午科(咸丰八年,1858)则以“贡优行第一”得优贡(26)。就恩寿早期的科举经历而言:年十七(1850)“始应童试”,二十一(1854)得秀才入县学,二十四(1857)首度入乡试,二十五(1858)二度入乡试获优贡,这般经历不但在同期从事科举的学友中堪称顺畅,即便与王闿运、王先谦等成功者相比亦无太多逊色。同治年初,恩寿关于咸丰年间科举生活的记忆均不乏成功者的心态。如有关此期考场经历,他有诗回忆:“曾记城南选胜场,冰纨借得箧中藏。桃花扇底春如许,摇向风前影亦香。”(27) 对考试有如此温馨美好之记忆,实是恩寿对科举寄予更大成功的反映。
三、咸同年间恩寿的游幕生活和精神状态
以咸丰八年乡试获优贡为标志,恩寿在长沙城南书院的书院士子生活告结束,其时恩寿年二十五(28)。就如此的科举成绩及年龄言,只要当事人有搏取更高科名的意愿,家庭通常是予以支持的。但因科举生涯就此延长难以预料终期,成年士子或兼作塾师,或外出游幕,是一般家庭兼顾子弟前程全面考虑的普遍而务实的安排。生活在商人家庭的恩寿于咸丰十年(1860)开始外出游幕亦是此理。
恩寿的第一位幕主魏式曾(1809?—?),字镜余、镜如余、镜如,直隶临榆人,道光二十年(1840,庚子)举人,“由幕入官”,咸丰十年二月任湖南武陵知县,十二月任长沙知县,同治元年二月任郴州直隶州知州(29)。恩寿在魏氏幕始于咸丰十年初魏氏赴武陵知县任之际,止于同治三年四月魏氏离郴州知州职时(30)。恩寿在魏幕除担任两位公子习儒及从事科举的业师外(31),魏氏作为知县(或知州)主持当地考课及校阅课卷等公务,也由他代劳,另外还兼及“司记室”、“草禀启稿”等。恩寿游幕所事乃与其父杨白元当年游幕衡州府通判何彤文所事基本一致。
恩寿开始游幕正在中国政局内外危机交迫、渐趋崩溃边缘之际。在太平军对东南数省的军事威胁持续加剧的同时,由广州绅民反英国人入城运动所引发的中英冲突不断升级,终于导致了一场以政治中心津京地区为主战场的中外战争。在内外两种不同性质及内容的危局中,湖南均地处冲突漩涡之外,因此其境内各级科举考试始终在进行。甚至咸丰十年(1860)八月英法联军入北京城,皇帝等人出逃承德,以及其后于九月相继签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等一系列重大变故,长沙府试及选拔来年乡试的科试还是在十月间照常举办,只是因受时局影响,该年新入学的生员名单迟至十二月中才得张布。其时在北方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在南方太平军几乎据有全国赋税重镇江浙两省全境的政局恶化的最新发展,亦未干扰长沙士绅们相互祝贺子弟入学,以及为子弟聘请来年业师的心情和气氛(32)。不过,咸丰十一年湖南士绅对北京政局的关注则不能不有所上升,咸丰皇帝滞留承德不归以及清廷政权运作的持续瘫痪令预期中的本年辛酉科(1861)乡试蒙上阴影。在期待时局恢复正常和乡试如期举办的长时间焦灼不安的气氛中,七月间长沙士绅“悉衡州之驱逐夷人,及省城会议不准夷人入城,以为士气”(33)。这是以东南口岸城市及北方京津地区为舞台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影响,终于波及内地城市长沙的标志。同治元年,湖南巡抚毛鸿宾查复教案文关于前年事陈述:
去年履任时,适有法国传教士自湘潭来长沙。其时士民激于义愤,相率至明伦堂集议,不期而会者竟至数千人。当经谆饬两县会同学官反覆开导,并将洋人护解出省,幸而无事。嗣闻有刊刻檄文到处张贴。(34)
此是咸丰十一年(1861)外国传教士恃有北京条约保护进入湖南活动,衡阳、湘潭等地民教冲突发生,而引发长沙“省城会议,不准夷人入城”的事件。长沙、善化“两县会同学官反覆开导”,表明士子系“省城会议”的中坚力量。不过,对于象恩寿这样对进一步的科名抱有势在必得决心的士子,即便有反教情绪,也是能谨慎言行的。事实上,咸丰十一年夏因传教事引发的长沙社会动荡,因为传教士的暂时离境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另外,更重要的新的政治信息转移了士子对传教事的关注。因为咸丰皇帝于七月十一日逝世承德的消息于八月初已经传抵长沙,随后受到士子广泛关注的消息则是清廷就包括湖南在内的各省新学政的任命。该年十月同治皇帝继位,次年——同治元年——是士子们的“大比之年”,亦理所当然的在清廷的设计和地方士绅社会的预期之中(35)。“庚申之变”后长期弥漫于清廷的政局迷雾终于尘埃落定,地方士绅更关注于清廷在内政方面的举措,其心思则多为科举恢复所牵动。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因魏式曾得郴州直隶州知州的新任命,恩寿随魏氏远赴郴州。
同治元年二月二十四日,恩寿由长沙赴郴州,作为《坦园日记》的第一部分“郴游日记”由此开始。日记使同治年后恩寿的生活有更丰富细致的展现,因而探求他面对具体事件的立场,甚至心理和精神状态都成为可能。作为对科举功名期待甚切的士子,恩寿从事游幕的心态在赴郴途中表现得尤见深刻。赴郴前恩寿有当年六月由郴州返长沙准备乡试的明确安排,因此自始就全身心地沉浸于对该年乡试的期待中。动身之日恰逢书院甄别考试,当晚恩寿“篷窗秉烛”,遥想“书院此时,考棚烛影吟声,其光景宛然可绘”,徒增其“客况凄凉”之感(36)。当途中感受船舱暑热难耐之际,恩寿自然虑及数月后赴乡试的归程境况。而途经衡州刻意寻访旧读之地,重温当年归长沙赴童试作“何年重到此,今日且归家”的壮志豪情,更是寄托了他对“大比之年”成功的期望。有此心态,恩寿在赴郴途中频作不甘于游幕生活的怨言愤语(37),其中固然不乏功名心太过的矫情,但该年的乡试也确实于恩寿有特殊意义。自1850年首应童试以来至1862年,是恩寿的科举生活“弹指年华又一周”的开端之年。寄于该届乡试的特殊期待,令恩寿心里有更多的紧张不安,他本人也有“三分病态七分愁”的自嘲(38)。在此背景下,恩寿不但于赴郴途经衡州逗留两天期间,未留下任何有关上年当地“驱逐夷人”事件的文字,而且他在郴期间对四月初三日士子“乘考聚众,焚毁该堂,拆毁教民房屋,人逾数万,势甚汹汹,几至酿成巨祸”的衡阳教案事件(39),也未留下任何感想。此期恩寿的郴州生活,日记最细的是他的观剧感受(40)。
四、同治元年乡试后恩寿有关湘军的感想
同治元年(1862)春赴郴,恩寿在郴州只呆了三个月,六月中匆匆校阅完州学士子的课卷,他就按预定计划回长沙准备乡试。恩寿在日记中就该届乡试的经历有以下记录:
自甫返家门,即移静室。自六月二十七日始,每日作诗文一首,杜门却扫,仅于黄昏时归家一定省焉。至八月初五,袱被回家,初八日即入矮屋矣。十六日场事既毕,始出应酬。闰秋六日揭晓,名落孙山,废然自失。及见落卷,始知为恩小农荣所黜。小农与余旧好也。入闱之前,或以奔竞劝者,余自以得失有定,而气节不可不矜,谢而勿往。今果被放,战之罪欤?嘻,命也!(41)
日记道出科举考试秩序破坏加剧的真相。该届乡试系恩科,并补行咸丰九年已未科乡试,中举名额加倍,而在如此有利的局面下沦为考试不公的牺牲品,落第的打击也就更大(42)。恩寿自述“甫经落第,又作远游,烦恼填胸,莫可名状”(43)。重返郴州后仍然生活在落第阴影中的恩寿,不再有往日观剧的嗜好,日记也因此开始出现较有政治思想色彩的文字,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动向是恩寿的言论对湘军问题的涉及。士子的身份以及对平定内乱的愿望,决定恩寿对曾国藩及湘军在南方士绅抗衡太平军的自救运动中崛起持赞赏立场。不过,对平定内乱的期望,并不能决定恩寿与湘军有共命运的感情,况且在湖南基本摆脱了太平军战乱威胁的背景下,恩寿更关注于个人的科举命运,因此1862年恩寿对湘军有以下感想应该与其乡试落第遭遇相联系。至好张恩准(字绳生)“千里从军,到营四十日而病殁”,恩寿闻讯作七律四首悼念亡友。其中之二、三如下:
平生福慧竟双修,君所居,署曰福慧堂。静对莲花品最幽。百炼吟诗何碍苦,四时得气独先秋。自饶古趣寻碑帙,尚有豪情寄酒筹。架拥藏书仓拥粟,问君底事觅封侯?
赫赫将军幕府开,翩翩名士渡江来。六朝落日金陵冷,一曲秋风玉笛哀。未了功名归梦幻,遥传生死费疑猜。于今记室知谁是,可有飞书草檄才?(44)
1862年初冬,湘、淮军于东南数省与太平军的搏杀继续在惨烈地进行,而恩寿此际悼念亡友的诗文却表白他与湘军陌路人的感情。另外,他于数日后游郴州学宫及楚怀王“义帝陵”的感想,则又进一步曲折隐讳地表达其作为湘军事业陌路人的理由。见游览当日记:
出西门谒孔庙。发贼之乱,竟毁其半,颓垣断瓦,睹之令人愤懑。醵资重修,亦良有司之所急也。旋谒义帝陵。昔项羽弑帝于江中,遂葬于此……余辈徘徊太息,废然而返……灯下作《谒义帝陵》诗云:碧树阴森惨四围,墓门惟见暮鸦飞。牧羊旧阜怀潜邸,逐鹿中原起杀机。痛哭重瞳余血泪,江山千古对斜晖(45)。楚人寸土原乌有,刘沛于今事亦非。”末句推及之,帝在九原,亦当干笑。(46)
郴州学宫在1852年毁于太平军的占领,曾国藩曾将之作为太平军毁灭中国文化及传统的最典型案例载入著名的《讨粤匪檄》,所谓“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并由此将湘军与太平军的斗争定性为事关中国文化及传统生死存亡,事关中国与西方、正义与邪恶的神圣事业(47)。恩寿游学宫自然不可能不联想到曾氏的《讨粤匪檄》。再说,1862年在处理衡阳教案过程中地方士绅对抗清廷政治动向的公开化,也应构成恩寿联想《讨粤匪檄》的因素。就此而言,恩寿在义帝陵前对楚汉相争历史故事的感想,是不能仅限在兴亡之叹层面理解的。关于楚汉之争的历史故事,历代文人于败者项羽多有惋惜之意,并赞其英雄气概;而于胜者刘邦则多有鄙弃其虚伪的感想。恩寿《谒义帝陵》也不无这样的倾向,然他以“末句推及之,帝在九原,亦当干笑”一语,着意点明“楚人寸土原乌有,刘沛于今事亦非”之句有深意存焉,表明该诗在借古讽今。
游览次日,意犹未尽的恩寿再著诗纪游,将借古讽今的用心进一步阐发。纪游诗所谓“昔年逐鹿雄,惟馀数弓地。重瞳信凶暴,行此非常事。沛公为发丧,其意亦虚伪”。该诗对于项羽的立场作重大调整,拉大了他与常态见解的距离,完全否定楚汉之争中对立双方是非、正邪价值区分的存在,并由此突出牧羊人出身的楚怀王成为争斗双方的工具,而终至沦为牺牲品的悲剧命运(48)。恩寿对楚汉之争的感想与曾国藩《讨粤匪檄》中就湘军与太平军之间斗争是非、正邪对立的强调形成对比,这在湘军与太平军残酷搏杀并经历了“庚申之变”的1862年的中国,不可能是无所寓意的。尽管曾国藩赋予湘军抗击太平军的行动以“卫护名教”的名义,但民间对此却只有乱世群雄逐鹿中原的感想。曾国藩在“庚申之变”之际拥兵自重,坐视北京失陷的事实,强化了一般士绅对民间观感的认同(49)。以此看恩寿的“沛公为发丧,其意亦虚伪”诗句,是不难读出其中嘲讽《讨粤匪檄》的喻意;至于“昔年逐鹿雄,惟余数弓地”,则更不难读出关于清廷权势全失的寓意。湘军的崛起导致旧有地方权力结构及秩序破坏的加剧,恩寿非议湘军似当与湘军势力操纵该届乡试致其落第有关,这与1862年春湖南地方各级科举考试中士子以反教为由闹事的原因同出一理(50)。
嘉道以来日益庞大的士子队伍导致科举成功的几率持续下降,而积累下巨大的社会压力。咸丰以来在太平军的战乱中湖南政权虽得惨淡维持,但清廷中央——地方政府——地方士绅——三权制衡的地方权力结构形态却已发生变异。科举成功机率下降与地方权力结构变异之间的矛盾和争斗相结合,极大地弱化了旧有权力结构对士子队伍的控御能力,士子群体性地发泄不满情绪成为可能,任何自圆其说的主张均足以成为他们闹事的理由。1862年恩寿的思想动向与士子群体性的公开反教活动,有共性的背景因素。
当代学者的研究认为:“通过科举这个竞技场,知识分子只能成为最高统治者的手脚,成为体制内知识分子。”而“体制内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的核心——道德论——包含着分裂的契机。其理论自身就必然地制造出反体制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常常以理想的正统理念作为基准对现今王朝进行批判”(51)。恩寿虽然自觉于体制的约束,而科举的连连失意,尤其对考试不公正的感受激起的怨怒情绪,还是导致他在“士志于道”所赋予士者言论载道的使命感的鼓舞下产生了评说湘军的冲动。这是与同期湖南士子以“夷夏之辨”这一“理想的正统理念作为基准对现今王朝进行批判”,并恣意发起反教运动是同一性质的社会现象(52)。恩寿的批判对象虽仅达于体制内的一个强势集团——湘军,但也已不乏叛逆动向。因为在“忠”于清廷的层面上否定曾国藩及湘军的同时,恩寿也在“夷夏之辨”的观念上否定将清廷作为当然效“忠”对象的地位。《谒义帝陵》的“楚人寸土原乌有,刘沛于今事亦非”诗句,就隐喻了外族身份的清朝最高统治者对于中原“寸土原乌有”的历史故事。显然,恩寿对清廷在新一轮群雄逐鹿中原的争斗中无奈的地位完全缺乏同情,他评判湘军的言论已含有反体制的倾向。
五、同治三年乡试与恩寿对湘军克复金陵的立场
1862年,恩寿与科举之间的束缚——依赖关系出现的裂痕远未达到破裂的程度。乡试三度落第的恩寿难以作出毅然放弃科举仕途的决断,也就不能不有意识地控制思想波澜中的叛逆的倾向。日记中所谓“能守书香即奇福,不招人忌是庸才。功名自有前因在,阅历都从末路来”等消弭怨怒情绪诗句的出现,乃恩寿调整心态所为。当年冬孤身在郴度岁的恩寿作新年寄语:“明年定开庆榜,志切观光,桂林一枝,势在必得!”(53) 表明他主意已定继续从事科举。不过,同治二年(1863)新年伊始,恩寿日记就长期中断的事实,则又表明情况似乎并不乐观。
同治二年秋,恩寿“草草还家祗六旬”,日记恢复于回到长沙一个月后。据恩寿的新年寄语,他返家当与参加选拔来年乡试资格的科试相关(54),但日记又始终未言及科试。从恩寿十月重返郴州途中极为恶劣的心情看,或科试失利,或因故未能参试,致其无望或无意参加来年乡试。见日记题名《感怀》诗:
十年博得旧儒巾,压住眉头两不伸。哆口莫谈天下事,称心谁是意中人?流分清浊原难合,语带周旋便不真。纵觏奇穷何用悔,须知龙性未能驯。(55)
诗的前四句恩寿表白了对体制约束的自觉,而后四句则跃动着他摆脱束缚的冲动。尽管不清楚恩寿如此激愤的直接原因,然缘于来年乡试无望则无疑问,因为此间恩寿不断流露出不再从事科举的意向,并因此陷于极度的思想危机。这一点首先表现在他对清廷出台有关优贡的科举新政策消息的反应上。以前“优贡朝考,向不列等”,即不能入仕,因此恩寿并不看重自己已有的优贡功名。而同治四年将予实施的新政策,优贡朝考“照拔贡复试例,以知县、教谕用”。恩寿甚为这一入仕途径吸引,一时有“径欲先期便束装”早早北上入京的念头。但此念来得迅疾去亦无踪,优贡新政策无助于解脱恩寿在来年乡试问题上听任失去参试机会还是再作力争之间选择的困境。此后恩寿笔下连连出现“岂学昏昏名利人,终日摩挲守阿堵?君不见纱帽场,大腹贾!”“莫学硁硁章句小儒徒自苦,身虽未腐神先腐。君不见亡是公,可怜虫!”等鄙弃科举仕途的文字(56)。这是他在为选择放弃而坚定意志。然激愤之余恩寿则不能不正视现实,自身知识的、精神的状态,以及地方社会可提供的生存空间,都决定他难在科举仕途外找到更佳的人生位置。恩寿寄希望侄辈们振兴家族科举命运时的淳淳言辞,透露的乃是他的心声。所谓“既不屑为农工商,舍却读书将安往?”对其侄辈是一现实,对其本人又何尝不为现实呢(57)!因此同治二年秋虽有如此激烈的情绪发泄,次年初春当恩寿回长沙度岁重返郴州之际,诸如“乘风买棹归来日,领取天香折一枝”的诗句再现日记中,表明参加当年秋天的乡试又稳稳地在他的计划中了(58)。
同治三年六月底,日记再度中断,此乃恩寿全力投入乡试准备的标志(59)。然第四次乡试恩寿仍系落第结局,日记亦迟迟未恢复。直至次年二月,恩寿“登舟游粤西,省麓兄于阳朔”,日记才又重新开始(60)。在题名《舟行有感》的诗作中,恩寿一方面有“最怕旁人誇早慧,模糊往事不堪提”的诗句,表明四度乡试落第令他不堪回首早年科举成功下的豪情壮志;另一方面则有“一事抚膺聊自慰,从无书札到豪门”的诗句,表明他继续坚持内心的高傲和倔强(61)。不过总体而言,恩寿以平和的心态接受了落第的结局,更多的感慨是发自对科举自信的丧失。而下届乡试远在三年之后,恩寿也就暂无对个人科举仕途前程作抉择的压力,因此在赴广西省兄的漫长行旅中,恩寿有较多的心情感受世态社情。
同治三年(甲子科)乡试前后,是中国政坛出现重大转机的时期。六月十六日湘军攻克金陵,持续十数年席卷南方的太平军运动终告结束,一个赋予传统重建机遇的新时期“同治中兴”开始了。在这历史性的时刻,恩寿却以特殊的方式再度明确自己对于同治中兴的中流砥柱湘军陌路人的立场。该年终止于六月二十九日的恩寿日记,未见有关湘军收复金陵大获全胜的任何信息(62)。同治四年春,恩寿赴桂途经湘南时所作《邻舟行》诗,以实录社会对湘军衣锦还乡景观的反响表达了自己的感想和立场。诗谓:
邻舟有客声讻讻,自言凯撤从江东,桅杆簇簇连艨艟,前列五色纛,后列八宝驄;左拥二八姬,右拥十五童;船头低压雪白镪,船尾饱载赤廑铜,敷腴意气何豪雄!旁有小弁誇是翁:是翁福命郭令公,生平从未习战攻。习战攻,必终凶,何如高垒坚壁死不出,待贼自遁尾贼踪。岂知贼势亦疲癃,久据孤城城已空,饥餐树皮食人肉,猛兽落阱鱼釜中,一时涣散如沙虫;大军乃得振旆入,捷书飞奏红旗红。吁嗟乎,杀运终,贼技穷,将军静坐成奇功!奇功成亦何从容,十年方博茅土封。(63)
民间对湘军克复金陵大获全胜的非英雄主义的理解,是湖南地方社会对湘军的事业缺乏基于正义性和神圣性的认同立场的集中反映。恩寿长期对湘军陌路人的立场也不乏同样的思想背景。尽管如此,湘军衣锦还乡解甲归田作为社会政治问题还是引起他的关注,他以传统的思维及士者应有的立场作了更深一层的冷眼旁观之论。这就是在作前诗后二日途经祁阳所作《蘭华寺》一诗。蘭华寺原系雍乾两朝重臣陈大受、陈辉祖父子故宅。陈大受祁阳人,雍正年进士,历任皖、苏、闽巡抚,直隶、两广总督,兴水利、缉盗贼、赈灾荒,朝廷倚为重臣,累官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衔。陈辉祖以荫生官至闽浙总督,于乾隆四十年遭革职,旋被杀。陈氏故宅则“籍没入官,遂废为寺”。恩寿游蘭华寺引发的历史幽思,显然缘于他对湘军获胜现实问题的关注。如诗中有意点明陈大受出身,所谓“中丞家世殊寒陋,赫赫原来宰相胄”,实是恩寿对包括曾国藩在内的湘军将领出身的感想。在诗结尾一段,恩寿直言道明该诗的讽喻旨意:
我来太息肠先断,凡事须知戒盛满;一枕黄梁好梦长,三秋白草春光短。功名近日推南州,一时风气何轻浮;新贵书衔续貂尾,通侯妙技烂羊头。足谷多牛生计好,菟裘预筑谋娱老,倚天台阁结千层,平地楼台装八宝……但觉青春多岁月,须防白日走雷霆……不信繁华转眼空,请到兰华寺前去!(64)
恩寿在“士志于道”的立场上有心以历史的经验警戒功成名就的湘军集团,然也充分地暴露了他作为言论者缺乏对现实洞察力的弱点。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军战乱的重创,清廷的政治权威大为削弱,尽管它仍不乏废黜惩处南方政要的威慑力,但乾隆朝“天威震怒雷声高,铁锁银铛付法曹”处置封疆大吏陈辉祖的故事,在湘军高层将领及其后辈身上重演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况且自身腐败的严重性,也已极大地削弱了清廷惩处各级地方政府腐败的能力和用心。因恩寿缺乏正确估价中国政局发展,尤其清廷统治权威得以重建的可能程度,他的警戒只能成为毫无历史回声的空洞说教。
值得强调,科举失意消解了恩寿自觉接受体制约束的意识,导致他时有肆意表达其对湘军集团的冷眼旁观者立场的冲动。然在个人科举成败外的利害关系方面,他与湘军集团并无重大冲突,因此在作《邻舟行》、《蘭华寺》的同时,恩寿在《渡黄沙河》诗中对曾国藩及其湘军的功业表达了由衷的敬意。所谓:“吾楚伸义愤,乡兵成劲旅,曾侯信奇杰,朝廷寄心膂,百战功乃成,迭更数寒暑,余党渐殄灭,论者比伊吕”(65)。这构成恩寿思想和精神状态复杂性的另一面,也是他的体制内士人身份始终得以保持的思想和精神的基础。
以同治三年六月湘军克复金陵为标志,清政权开始所谓“同治中兴”的复兴时期。恩寿此间围绕湘军胜利问题所思所感的意义,在于它深刻地反映了“同治中兴”在湘军的故乡湖南地方,实有与作为“中兴”实践的中心地区,即深受太平军政权蹂躏的江浙地方有完全不同的社会政治意义。在江浙地区是士绅对旧有制度、传统规复的期待,但在湖南则更多一层关于湘军胜利后势力扩张构成对地方社会秩序新威胁的忧虑。
六、同治六年后进入长沙上层社交界与恩寿中举
同治四年春暮至次年冬初,恩寿在兄彤寿广西北流县知县任上担当“刑席”,并兼校课县学的幕僚。在为时不足两年的广西生活期间,恩寿内心始终在进行自我反省和检讨。这种现象最初的记录出现于同治四年春他在赴桂途中而北京举行会试之日。该日恩寿赋诗寄怀王先谦等赴京会试诸友,在以“远程期万里,慎勿自菲薄”鼓励祝愿友人的同时,他以平和的心态反观自己的落伍:“岂不欲奋飞,所嗟羽毛弱”,并对自己失利的原因进行分析以及作出解决对策,所谓“翳余本微材,辄被浮名缚,鹦鹉工语言,转以招矰缴,誓当自断尾,径向风尘落,仙凫影翩然,或可踏双脚”(66)。恩寿反省的重点显然不在考试,而在由科举制度体现的对体制束缚的适应问题上。对于自己得不到权势者青睐的境遇,他完全放弃同治二年秋“龙性未能驯”的愤世对抗立场,而表明“誓当自断尾”,“或可踏双脚”的转变立场。此后,友人王先谦在科举仕途上的不断成功成为恩寿自我反省不断深化的动力,他的悔悟自责甚至及于自己的天性气质,所谓:“余自幼即解笔墨,矜奇斗捷,盛气凌人,且好使笔锋,嬉笑怒骂,不无大伤忠厚之处。频年行事乖舛,科名蹭蹬,未尝不由于此”(72)。
同治五年初冬,恩寿再度回到长沙,一为来年丁卯科乡试作准备,二为谋求可以定居长沙的称心幕职。因此回长沙后恩寿的社交活动显现出扩展上层社会关系网的新动向,而并非仅限于为乡试成功的目的(68)。扩大上层社会关系网,对于作为长沙高才士子,并兼有富商家庭背景的恩寿而言并非难事,只要他用心于此。此期为恩寿进入长沙上层社交界提供帮助者,如朱宇恬(名昌琳)、朱岳舲兄弟和张自牧都是身份地位特殊的湘籍人士。据郭嵩焘记:朱宇恬(?—1912)“少业儒,通学籍为名诸生。道咸之间,江湖岁潦,民困于食。禹田转百货居积为贾”,“久之,利大雠,辄分其羡以散友朋亲族及道路之穷饿者。如是数年,人高其义”。曾国藩督两江期间改革盐政,“分楚岸行引,专立湘岸,禹田力任其难”(69)。同治十一年曾氏去世后长沙建祠,地方财势人物群相推脱承担之责而朱氏兄弟力任其事。郭嵩焘有“禹田所为,利乐其乡人而维持人心风俗于不敝”的评价。王闿运在朱宇恬去世后挽联谓:“喜卅年平揖公卿,豪情吐尽书生气”,“看诸子满床簪笏,里社仍祠积善翁”(70)。尽见朱氏兄弟及其家族在长沙社会地位之显赫。早在同治二年秋恩寿的交往录中,就有朱氏兄弟(包括张自牧)之名(71)。尽管恩寿从未言及与朱氏兄弟关系的渊源,但杨氏作为长沙有地位的商人家庭,不难想象在朱氏主持的厘捐事务和包括慈善在内的地方社会公务活动方面均有所参与。同治五年后恩寿与朱氏兄弟的密切交往,想必有借助其力量进入长沙上层社交界的意图。
张自牧字力臣,湘阴人。张氏家族“先世以行贾,寄籍宛平”,自牧父张学尹(字少衡)“既举进士,奉父丧归葬,复为湘阴人”。学尹以知县官福建,因事罢官,“归而著书讲学三十年”。自牧虽仅为诸生,而以才名震动长沙学界,咸丰年间他亦是得学政张金镛欣赏的高才士子。湘军之兴,“自牧积劳至道员”,同治六年更“以筹办黔捐,洊保藩司衔,并戴花翎”,恩寿称其为“吾半生来贫贱交中之得意者”(72)。同治年间张自牧凭借家世、财势及才学,确立其在长沙上层社会的显赫地位(73)。恩寿与自牧的关系有“同是受知”张金镛的学缘背景,而自牧的多重身份也决定他能够帮助恩寿进入长沙上层社交界。恩寿进入长沙上层社交界的首度活动,就是同治六年初春出席张自牧的一次招宴。在宴席上他结识了有湘军上层关系的前辈、道光二十七年进士黄彭年(74),以及当年得张金镛提携的同辈、进士黄道让。恩寿出色的诗才成为他攀结这些名流,并使双方关系得以延续发展的重要媒介(75)。至当年初夏,在黄道让的招宴上恩寿又结识了“由曾侯幕府平江南而成功者也,现领防勇守省城”的黄润昌(字少鲲)。润昌湘潭人,与恩寿为“同案入泮者”,且咸丰六、七年“同应岁科试,曾相识”,虽然现今地位悬殊,但二氏以诗文为媒迅速发展起密切关系(76)。
与此同时,同治六年的丁卯科乡试也在渐渐逼近。对比社交的活跃,恩寿的备考状况显然不足。最初他的表现似乎还有信心,曾于四月、五月两次“应校经堂课”,作备考的恢复性训练(77)。但七月初“始理旧业”进入全面备考状态后,恩寿却不断有“文思甚滞”、“文思颇钝”等缺乏自信的慨叹(78)。直至乡试现场,恩寿的自我感觉更是欠佳,所谓:“余自丁巳(咸丰七年)观场,经、策均极用心;今年因文不惬心,故均草草”(79)。总之,该年乡试再度落第的结局不应大出恩寿本人的意外,因此他对参与上层社交活动的热情丝毫未受落第打击的影响。
得落第信仅一月,恩寿就同王先谦拜访了临时回湘的曾纪泽,“并读其诗稿”,对贵公子作“高蹈不仕,好学之士也”的誉词。次年初春,旧日同学陈杏生招陪曾国荃,恩寿作《赠威毅侯曾沅甫少保》。诗不但以“世俗但惊天宠渥,岂知艰苦历临冲”表达对社会非议曾氏兄弟舆论的不以为然,并还以“敢因门户存私见,奚恤钟彝杂谤书”句,表达他对曾国荃种种越轨的政治行为的赞赏,其中应包括曾国荃在湖北巡抚任上参劾湖广总督官文激起政坛轩然大波一事(80)。在湘军上层人士面前作这样有违自己此前社会批判立场的言论,对于恩寿并非初次。前湖南巡抚张亮基因黔乱于去年秋在署贵州巡抚任上遭革后侨寓长沙,该年二月恩寿呈诗张氏,不但以“房杜同时善断谋,谓公及骆花县师相。烽烟楚戎昔年收”诗句高度评价其在湖南巡抚任上的功业,并对其遭革事与自己的科举不第作同病相怜之感,诗有“敢说文章例功业,定评得失待千秋”之句(81)。新任湖北提督郭松林(字子美)于同治八年春回湘省亲,恩寿四月“晤郭子美、黄子寿于力臣座上”。郭氏长期滞留不赴淮军平捻前线,并在长沙营建起“规模宏敞,为省垣住房之冠”的豪宅。对此,恩寿仍在其贺郭氏“新第落成”的对联中作“我幸结邻分夏庇”,“公应释甲展春晖”的谀词(82)。恩寿如此积极自觉地进行言论立场的转变,显现他对广泛的上层关系的渴求,背后自然是为谋取个人发展的动因。
同治六年乃恩寿乡试五度落第,事后他不能不有个人前程的重新规划。最初他曾有捐纳入仕之念:“余拟于明年,俟捐妥部曹后,即入都供职”。然至次年春此念已淡去(83)。虽然关于下届乡试,恩寿的态度尚欠明朗,但他似乎更坚定了在长沙谋求理想幕职的决心。他力拒魏式曾欲其赴澧州幕的邀请,居家辅导三侄考课为事,静待机遇(84)。此期恩寿积累下的广泛的长沙上层人事关系,开始显现助成他实现包括下届乡试成功等多种目标的迹象。在此有必要强调恩寿与外省籍湖南地方官员发展关系的线索。同治七年春经黄润昌推荐,恩寿为湖南布政使李榕代笔,撰写湖广总督李翰章母的祝寿骈文,骈文撰写的成功导致“由工部援例来南”候补的江苏进士裴荫森(1823—1895)慕名登门拜访。恩寿与裴氏的关系很快就步入“至好”的佳境。由此恩寿遇事疏通于政府的人事关系亦更为直接、全面(85)。
同治七年秋,恩寿尚“因谋一枝栖未得,而私逋毕集,夜思之不寐”(86)。入冬后湖南政府设局编纂《湖南通志》,志局以郭嵩焘、曾国荃为总纂,张自牧、黄彭年列名提调,其中张自牧因掌管资金而地位尤重(87)。湖南士绅谋职志局趋之如鹜,恩寿则在首批“派司襄纂”之列,并有“承修人物列传,乃大文章”的殊荣(88)。其间各种人事关系的助力自在不言中。入志局后,恩寿频频出入有郭嵩焘、曾国荃、李元度等前显宦出席的地方上层绅士聚会,他在政、学两界的社交圈进一步扩大,包括结识“久负诗名,心折已久”的文坛名宿吴敏树(89)。同治八年春,恩寿终于如愿以偿地入新任署长沙府知府杜瑞联幕“习书记”。其中“裴樾岑观察为之先容”的作用功不可没(90)。进入长沙知府幕,恩寿与地方政府主持科举考试的中枢机关的人事联系就更为直接了,因此当年其三侄参加府试,致恩寿在考试期间二十余日“未入署,遵廽避例也”(91)。至此,就人事关系而言,恩寿在同治九年乡试中的成功已有水到渠成之势。
同治九年庚午科乡试,恩寿以第二十一名中举,这样的结局在考前对于恩寿本人而言,已并无太大的悬念(92)。不过当年恩寿母亲去世,他为“守制”失去次年赴京会试的机会(93)。同治十三年春,恩寿首度赴京会试,而这只是一次失望之旅。当恩寿于当年夏南归时,王先谦曾赠别诗,以“期子盛功名,簪毫图紫光”鼓励他再赴会试。恩寿的科举生涯似以此次会试为终结,因无任何有助说明他曾再度赴京会试的资料。光绪年后恩寿长期游幕云南(94),大约在光绪七年开始定居长沙从幕职(95)。光绪十五年,在湖南“在省诸巨绅公祝”巡抚王文韶升迁宴上,恩寿与郭嵩焘、王先谦等并列在座(96)。这颇反映恩寿作为地方士绅最终所达到的社会政治地位。
七、结语
恩寿未取得科举最高一级的进士功名,这无疑给他留下终身的遗憾,但举人的身份以及富裕的家庭背景,最终仍使他跻身于长沙地方最有影响力的绅士之列。而他为这样的人生成功付出的是延续至41岁的科举生活,并终以牺牲自我独立意识为代价完成了走向体制化的改造。恩寿在历次乡试落第后的心路历程,显现出这一改造过程非但痛苦和激烈,而且还具有非道德性。他在其改造过程中有两方面的思想动向:一是张扬个性,以摆脱现存体制的束缚及以此为背景的社会批判;一是泯灭个性,以适应现存体制的束缚及以此为背景的自我反思。前者不乏“士志于道”的道德正当性的自信,后者则自始就包含对个性自我扭曲的非道德成分。恩寿个人的选择联系了他个体生命实践的价值取向,强烈的科举成功欲望和不能摆脱在现存体制内谋发展的生存状态,决定他在对立的两种思想动向中不断强化自我反思的趋向,并终至消解其对社会的批判立场。同治七年恩寿作《远嫁行》一诗,可谓他完成走向体制化改造的标志。全诗如下:
胡姬十五颜如花,巧梳云髻双盘鸦;娇歌宛转解人意,能将新曲翻琵琶。芳年如许犹待字,无主玉容难自弃;少年游侠多黄金,策马经过不留意。贾胡好色与众殊,解繻立赠双明珠;毡车即是贮娇屋,风尘从此长驰驱。驰驱不怨风尘苦,为感深恩泪如雨;翻悔平时心志高,信口讥评大腹贾。(97)
恩寿坦然地承认自己以牺牲自我独立意识,实现走向体制化改造乃至于自甘道德沉沦的心路历程。
晚清科举队伍的扩大联系着考试规模的扩大,如同光年间湖南历届乡试的规模就均过万人。考试规模的扩大,引发从考场管理到阅卷评判等诸多环节上难以克服的技术困难,科举取士的效能由此而低下。同治初年,南方改革思想家冯桂芬曾言及科举取士效能渐趋低下的现实,“嘉、道以降,渐不如前。至近二三十年遂若探筹然,极工不必得,极拙不必失,缪种流传”。在竞争加剧和效能低下的双重压力下,科举制度设计中的固有缺陷暴露无遗,其败坏士人道德方面的作用则更趋明显,明末清初关于科举制度“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等激烈化的批判言论,再现于晚清社会(98)。在传统的历史演变进程中,科举制度于晚清已步入危机时期。恩寿于同治年间科举生活的日记的价值,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份评价这种危机的性质和程度的实录。
科举是形成现政权体制内知识分子队伍的制度基石,而科举制度的运作过程却不能避免制度自身的异化,除庞大的失败者队伍中酝酿出现政权的批判者甚至叛逆者外,更普遍的弊端则是连续的失败打击将坚持在现存体制内谋发展的士子推至精神上的绝境,直至他们背弃从属于该体制的“意识形态的核心——道德论”,即背弃“士志于道”的社会期许和自我道德完善的追求,在精神上自我放逐。同治六年前后恩寿的思想、精神动态正是这样的案例。科举考试就这样造就了专制政制体制内知识分子。科举对士子的人格和精神的塑造过程,不但是士子个人的自我异化——丧失普遍的社会道德,也是体制的自我异化——培植出一批对体制缺乏忠诚感的体制内人。因此呈现于晚清历史画卷上的庞大的科举队伍,包括不同等级的科举成功者,在清政权逐渐衰亡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保持了所谓清醒的“智者”的选择立场,鲜见为该政权的生存作出卓绝努力并直至献身的志士仁人。更有甚者,他们成为地方社会动荡的重要制造者。如清政权的最终崩溃,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南方科举知识分子整体的背叛。
收稿日期:2006—01—18
注释:
① 关于杨恩寿的生卒年份、他的著述及日记的情况,参见《坦园日记》“出版说明”。另外,杨恩寿生于道光十四年十二月初九,即公历1835年1月7日。本文所涉恩寿年岁系以阴历计算,与《坦园日记》一致。《坦园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② 根据对中国期刊网的检索,自2000年以来有三篇关于杨恩寿研究的论文,其内容集中于他的戏曲及戏曲理论方面,未涉及他的科举生活及相关方面。
③ 《坦园日记》,第57、299、334、338页;《长沙县志》卷22,同治十年刊本,第36页。
④ 同治四年,恩寿“自制《族谱》一序”,应与其时家族事业发达而致家族有编族谱的动议相关。参见《坦园日记》,第136页。
⑤ 恩寿六兄彤寿任广西北流县知县,三兄作为幕吏主持该县厘捐税关事务,并曾赴梧州“办粤产”,显示其有经营才干。参见《坦园日记》,第137、224页。
⑥ 同治九年,郭嵩焘在长沙置房产而有感于地价几涨十倍,叹谓“省城近年房屋之贵,有不可思议者”(《郭嵩焘日记》(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86页)。同治年间恩寿家“居藩署围后”,与湘军人物黄彭年“同街而居”,与郭松林新建豪宅“结邻”。从中也可见恩寿家在长沙的社会地位。参见《坦园日记》,第207、273、361页。
⑦ 《郭嵩焘日记》(四),第206页。
⑧ 同治六年,郭嵩焘从广东巡抚任上隐退归乡后惨遭丧子之痛,导致他“为先人求地三四年,苦累万状”,“所购得十余所,无一当意者”,但仍矢志不悔。所谓:“凡族姓为一乡之望者,其祖坟必居一乡之胜。谚云:天道无凭,地道有凭。其理有不能易者。”《郭嵩焘日记》(二),第741页。
⑨ 《湖南通志》,光绪十一年重修,商务印书馆影印本,第2860页。
⑩ 参见《坦园日记》,第62、249、262、295页。长沙县志在“例仕”卷“保举文职”目下,记“杨彤寿,花翎,阳朔县知县,补用同知直隶州”。恩寿曾祖杨正启、祖杨荣、父杨白元分别得“荣禄大夫”褒封。参见《长沙县志》卷22,第36、64页。
(11)(13) 《坦园日记》,第273、3、94、97、101、241、248页。
(12) 恩寿于同治年间与何彤文子何子莲、何晃生仍交往(见《坦园日记》,第3—4、75、212、227页)。何彤文,字芰亭,安徽南陵人,乡试副榜,道光二十六年任衡州府通判,二十九年任岳州府通判。同治元年,恩寿称通判衙署系“十五年前钓弋处”,及其道光三十年“归家”,均与何氏任职衡州时间相符。这有助于说明恩寿父受聘何氏的长期性,包括在衡州以外的任职地。参见《湖南通志》,第2531页;《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188页。
(14) 同诗“太岁在寅月建子,芹菜一枝搴泮水”一句,表明恩寿于咸丰四年(甲寅)进学。参见《坦园日记》,第3、57页。
(15) 咸丰元年九月至四年七月,任湖南学政的是云南人刘崐,后又于同治六年至十年任湖南巡抚。咸丰五年乙卯科乡试在湖南未能如期举行,原因并不限于本省环境条件,因为江西、湖北、江南数省均未如期举办该届乡试。
(16) 《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84—686页。同治元年,恩寿忆士子“芳辰选胜青同踏”旧事,提及的同游人有陈小斋、王先谦、陈杏生、罗寄云、杨商农等,均系恩寿同治年间友人圈中的主要人物。参见《坦园日记》,第46页。
(17)(22) 《湘绮楼诗文集》,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427、1271页。
(18) 恩寿关于王闿运有所谓“与吾为文字交”之说。光绪三年,王闿运作《杨蓬海诗集序》于两人关系有“闿运与交几廿年”一说。参见《坦园日记》,第60、321页;《湘绮楼诗文集》,第379页。
(19) 恩寿曾以体弱解释于咸丰年间不能投笔从戎的原因,同治八年又曾以“家有老亲”婉拒友人聘其随军从幕的邀请,并同时以“衣短后而跃马,乃素愿也”以示遗憾之意。但恩寿关于士人投笔从戎一事的真实想法,体现于同治元年他就“至好”死于军幕而作“闲云出岫太无因”,“架拥藏书仓拥粟,问君底事觅封侯”的感想中。参见《坦园日记》,第38、53、102、293页。
(20) 恩寿日记载“丙辰(咸丰六年)应书院课,承首拔者三次”。 这是恩寿在城南书院考课的成绩记录。参见《坦园日记》,第81、84、160页。
(21) 朱克敬:《瞑庵杂识、瞑庵二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4、115—116页。张金镛(1805—1860)字韵笙,号海门,浙江平湖人。
(23) 恩寿述“怀清堂”诗会:“当年试院徹文光,佳句曾传贮锦囊”,参见《坦园日记》,第207、235页。蔡毓春(字与循,后改名枚功)和嵇月生均见于咸丰十一年郭嵩焘日记。见《郭嵩焘日记》(一),第440、465、467页。
(24) 黄道让后为进士;蔡子纯后改名元燮,官云南知县。参见《湖南通志》,第2853页。
(25)(30) 参见《坦园日记》,第206、235;161、294页。
(26) 《坦园日记》,第366页;《长沙县志》卷22,第6页;《杨蓬海诗集序》,《湘绮楼诗文集》,第380页。
(27) 《坦园日记》,第322页。“城南选胜场”当指长沙城南书院的考课活动。
(28) 同治八年夏,恩寿偶入城南书院,有“不登此堂已十年矣”之说,参见《坦园日记》,第322页。
(29) 同治元年,恩寿为魏式曾抵郴州知府任撰“观风示稿”,其中“昔日陈经,庚子之微名倖捷”;“本州曾探桂宇,屡任花封”等说,表明魏氏乃举人身份,曾多次赴京会试。后魏氏于同治四年任澧州知州,八年任永顺知府。参见《坦园日记》,第11、250页;《武陵县志》同治二年刊本,卷29,第16页; 《长沙县志》卷17,第18页;《湖南省志》,第2525、2536页。
(31) 同治元年三月,恩寿抵达郴州,“见东门,有衣冠揖于道左,门下士仲仪、叔云也”,可见恩寿教读魏氏二位公子仲仪、叔云由来已久。参见《坦园日记》,第13页。
(32) 此况参见《郭嵩焘日记》(一),第403、413、421页。
(33) 《郭嵩焘日记》(一),第469页。同治元年衡阳教案中士人起草的文告,述咸丰十、十一年间士绅社会的气氛:“我衡湘士民,自闻逆夷震逼京师,凡在血气之伦,已莫不茹痛含酸,卧薪尝胆,又值圆明园被毁,先皇帝北狩木兰,道路讹传不一,而教门势更枭张,语言无状,实有若辈口得而言,吾民耳不忍得而闻者。”参见《瞑庵杂识、瞑庵二识》,第92页。
(34) 《教务教案档》第1辑,台北1974年版,第1055—1125页。
(35) 同治元年三月始抵郴州,恩寿为魏式曾撰“观风示稿”有“今秋逢大比之年”一说。参见《坦园日记》,第11页。
(36) 《坦园日记》,第1、5页。
(37) 所谓“挟瑟三年惭下客”,“出山小草非初志”;“祗为饥驱出,频年悔浪游”;“为此蝇头小利,竟作千里之游,当年蓬矢桑弧,岂为依人作嫁衣而设!”等等(见《坦园日记》,第2、3、6、7页)。其实,从魏氏的器重,以及恩寿长期从幕魏氏的事实而言,他的游幕聘金想是可观的。
(38)(43) 《坦园日记》,第7、32页。
(39) 此记载见《瞑庵杂识、瞑庵二识》,第87页。同治元年,王先谦无参加当年乡试计划,二月他由安庆湘军幕辞归,五月赴湘南永州,有《至永州》诗谓:“伊余冒锋镝,时势正仳离。黄尘蒙翠盖,岛夷在王畿。北望负深痛,南图竟何为!家绵诗书泽,身有文采施。生为中天民,帝力岂忘之?斑竹泣风雨,丛生湘江涯。攀髯苦莫逮,恸哭对九疑”(《葵园四种》,第367页)。王先谦由长沙赴永州府署所在地零陵县,湘潭、衡阳乃必经之地,该诗关于“庚申之变”的联想,必乃衡阳教案所致。
(40) 对于频频得见来往广州的人员,恩寿也只有“粤中风土”“奇闻”的记载。总之,在科举事外不见任何令恩寿感受忧虑不安的时局的信息。另外,恩寿嗜好戏剧,不但喜好观剧,自己亦创作剧本。
(41) 恩寿日记记“恩小农明府,余旧好也,余卷为伊所斥”,并称“公论人都惜,遭逢事太奇”。见《坦园日记》,第32、33—34页。
(42) 王闿运:《杨鹏海诗集序》中有所谓“几四十而后昏”之说(《湘绮楼诗文集》第380页),因此同治元年年届二十七的恩寿尚无婚史,虽与其体貌不佳有关,可能更是他自许“狂狷”一面的原因。但在落第的背景下,恩寿应允一门预定来年迎娶的亲事,但该婚约当年即因对方病故告终。同治六年春,恩寿娶王先谦族人王氏是其第一次婚姻。参见《坦园日记》,第41、212页。
(44) 另,恩寿对王闿运等于同治二年冬赴广东巡抚郭嵩焘幕,作“南禺开幕府,重为整纶巾”,“见说汪洋处,鱼龙赴壑忙”(《坦园日记》,第38、60页)的感想,也少见羡慕之意。
(45) 此句后有眉批:“垓下歌声余血泪,关中王气冷斜晖”。
(46)(48) 《坦园日记》,第39—40页。
(47) 转引自《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湖南省志》第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页。
(49) “庚申之变”时隐居湖南的郭嵩焘认为:“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勤王之师理势兼谕,不可无此一枢纽”。对曾国藩、胡林翼等此间的举措深表不满。参见《郭嵩焘日记》(一),第401—402页
(50) 1862年冬,恩寿评论长沙政局“始则小人引小人,继则小人攻小人,一弹指顷而变态百出,嘻,可畏哉!”参见《坦园日记》,第63页。
(51) [日]三石善吉:《传统中国内发性发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页。
(52) 《传统中国内发性发展》,第132页。
(53)(56) 《坦园日记》,第32、47、48、55页。
(54) 八月中旬末恩寿抵长沙,九月二十一日恢复日记,十月初六日“府试长、善二县头场”,日记无恩寿参加同期举办的科试的迹象。参见《坦园日记》,第49、51、52、74页。
(55) 相似的文字还有:“有时豪气吐长虹,一洗闲愁万古空。……拍案揽衣长啸起,昂头天外看神龙。”参见《坦园日记》,第53、54页。
(57)(61) 《坦园日记》,第56;56、57、59;33、95页。
(58) 另有“料想相逢应不远,秋香吹上桂花时”,也表明恩寿计划该年回长沙乡试。恩寿在乡试事上情绪和主意的转变,与他落实了入选乡试的途径相关。日记关于同治六年、九年两届乡试的记录,恩寿均是通过参加乡试前由学政主持的“录科”考试获得乡试资格。据此可以判断同治三年他也是以“录科”为途径进入乡试的。参见《坦园日记》,第73、76、226、361页。
(59) 魏式曾“因蜚言撤任”,同治三年四月恩寿即已返回长沙,六月初得友人“毋作闲游,为秋香得意计”的忠告,他有“药石向贻,良深铭佩”的感想。参见《坦园日记》,第77、90、91页。
(60) 同治三年五月,杨彤寿由长沙赴广西阳朔知县任。参见《坦园日记》,第94页。
(62) 对湘军攻克金陵这样重大事件毫无反响,并不能以恩寿当时心系乡试为解释,更不能以其对时事冷漠为解释。因为当次年春恩寿由长沙南下赴广西途中,他最多的感想是回顾当年太平军由桂入湘北上的旧事。如此冷眼旁观的立场缘于士绅社会关于太平军战乱兴起时的观感,即政府在军事方面的儿戏导致了太平军最初的胜利及其日后的发展。而恩寿日记“上游有勇赴援鄂中,沿途掳船,其势张甚”;“省城有勇开行,掳船甚猛”等文字,则明显有他对湘军扰乱社会民生的不满。参见《坦园日记》,第32、62、72页。
(63) 《坦园日记》,第98页。
(64) 《坦园日记》,第98—100页。
(65) 该诗以“我生苦孱弱,身若囊中处,未与鞬役,徒结烟霞侣”,表达对当年未投身湘军事业的遗憾之意。另外同治五年夏,恩寿赞誉左宗棠、郭嵩焘“二公皆为今之正人,洵疆吏中不数觏者”,并对二氏交恶事件甚感痛惜,反映了他对湘军集团保持政治影响力的善意期待。同治六年冬虽经乡试失利,但面对民间非议湘军衣锦还乡之事,恩寿还是表明了维护曾国藩声誉的立场。参见《坦园日记》,第102、177、244—245页。
(66) 《坦园日记》,第103页。
(67) 王先谦始终是恩寿自我反省的榜样。 如同治五年秋恩寿《寄怀王益吾》诗谓:“众谤频年集一身,王郎无事不惊人;如何自向天门跃,似觉神龙性渐驯”。参见《坦园日记》,第112、130、181、323—324页。
(68) 当时恩寿“得友人书,所谋未谐,殊败人意”,他不得已作接受时澧州知州魏式曾聘入幕府的打算,同时又谓“吾始意原决然不再作依人计,今既一无所遇,潦倒飘零,舍此别无生路,终不免作下车冯妇耳”。该说不无矫情,因当时恩寿既不具备任官资格,其“所谋”之事就不可能出作幕客的范围。恩寿当时不能如愿者,当不能在长沙谋事而已。参见《坦园日记》,第174、175页。
(69) 《郭嵩焘诗文集》第299—300页。另外,咸同年间湖南办湘军饷务的其他重要人物如黄冕(?—1871,号南坡)以及李仲云(1824—1881)、李桓(号黼堂)(1827—1891)兄弟,也在同治六年后的恩寿社交圈内。
(70) 《郭嵩焘诗文集》,第300页;《湘绮楼诗文集》,第2008、2024页。
(71) 恩寿以“兄”称宇恬、岳舲,并曾分别请宇恬为自己及母亲看病。参见《坦园日记》,第218、257页。
(72)《郭嵩焘诗文集》,第404—406页;《坦园日记》,第206、211—212页。
(73) 张自牧去世,王闿运挽其:“壮岁相逢意气欢,尔时才识无双,官职声名俱入手;三致千金隐沦晚,独恨经纶未展,鼓角歌钟两寂寥”(《湘绮楼诗文集》,第2020页)。光绪初年,张自牧以主张“西学中源”说的《瀛海篇》名扬洋务学界。同时,他又投资“盐引”获利。郭嵩焘称:“笠臣于经营事理,均能洞悉原委,精微透辟,委曲周至,于时罕见其比。”参见《郭嵩焘日记》(四),第162页。
(74) 《坦园日记》,第174、205页。黄彭年(1823—1891)字子寿,贵州贵筑人(原籍湖南醴陵),同治十二年受李鸿章邀赴保定主持编纂《畿辅通志》,光绪朝中期历官江苏、湖北布政使。参见《郭嵩焘日记》(二),第468—479页。
(75) 恩寿在广西北流期间精心删订誊录完成的个人诗稿,在同治六年后的长沙上层社交宴席上递呈于名流之间。参见《坦园日记》,第174、205页。
(76)(77)(79)(80) 《坦园日记》,第221、235;215;228;240、260、262页。
(78) 恩寿称:“余自甲子年(同治三年)后,屏弃笔墨,不事帖括者几三年矣。兹复从事于此,不独所读之经书强半遗忘,即时墨烂套,亦不记忆”。参见《坦园日记》,第224、225、226页。
(81) 张亮基,字石卿,江苏铜山人, 咸丰二年在湖南巡抚任上对长沙城避免太平军侵扰有贡献。见《坦园日记》,第263页;《王文韶日记》,中华书局1989 年版,第201页。
(82) 郭松林,湘潭人,原湘军曾国荃部属,后为李鸿章创淮军骨干。 同治九年李鸿章率淮军赴陕平捻,郭松林滞留湖南不归营,次年春清廷“以省亲不先请旨饬部议处”。参见《坦园日记》,第313、361页;《王文韶日记》,第136、254页。
(83) 同治七年春,王先谦赴京,催恩寿尽早“入都”,但恩寿显然已无此愿。参见《坦园日记》,第242、272页。
(84) 时澧州知州魏式曾力邀恩寿“主讲澧阳书院”,并辅导其二子仲仪、叔云从事科举。同治二年恩寿子侄中有绍曾、绍弓两位习儒。同治七年则仅三侄绍曾一位继续从事科举,并于八年入学。据光绪十一年王闿运函言及绍曾当时在四川谋官情况。参见《坦园日记》,第263—264、265、295页; 《湘绮楼诗文集》,第989—990页。
(85) 《坦园日记》,第257、264页。裴荫森,字樾岑,江苏阜宁人,同治二年进士。其在湖南政界高层的地位,与同期在湖南候补的陈宝箴相仿,二氏同在《湖南通志》“监修提调”之列。光绪九年裴氏由辰沅永靖道迁福建按察使。
(86) 同治七年闰四月,恩寿曾“奉札委襄办常德厘金”,九月黄润昌率军援黔聘其“同去办文案”,他均以“家有老亲”婉拒。参见《坦园日记》,第275、293页。
(87) 湖南士人竞相请托入志局而不能,令郭嵩焘承受很大的舆论压力,他称其间言者“直谓志局用费由张力臣经营,曾沅甫承认一切,而我(郭嵩焘)一力把持,阻寒士生计”。参见《郭嵩焘日记》(二),第506、511、566、538、541、542、553页。
(88) 同治九年夏,张自牧总办援黔捐输局,恩寿受命办文案,“因捐务较忙,不能兼办”而“辞志局差使”。参见《坦园日记》,第300、316、328、360页。
(89) 《坦园日记》,第300、301页。
(90) 杜瑞联,字棣云、聚五,号鹤田。山西太谷人,恩寿日记载:“壬子(咸丰二年)翰林,戊午(咸丰八年)典试湖南,前年出守宝庆,现调署长沙,今午来拜,得见,订余习书记”(参见《坦园日记》,第308页)。光绪元年, 杜瑞联以湖南辰沅永靖道迁四川按察时,光绪二年秋迁云南布政使。
(91) 恩寿的三侄在该次府试中“取进府学第六名”,获秀才功名。参见《坦园日记》,第28页。
(92) 七月下旬,恩寿以参加所谓“现任教职及京外职官”的“录科”考试,入选当年乡试(参见《坦园日记》,第361、366页)。时王文韶以湖南布政使主持该届乡试组织事务,他于乡试前四日因“学院录送至今尚未截数”致其不能“造册”,而对湖南“录科”泛滥甚有烦言。谓“求录之风亦复相延成习,百出其奇,实为各省所未见”,并称“本日函托跪求者尚纷纷不绝,真恶习也”(参见《王文韶日记》,第214—215页)。可见,此年湖南的“录科”试似有隐情。另外,同治九年乡试前后恰是天津教案事发及曾国藩在天津艰难地处理教案之时,湖南上层士绅于此虽均甚表关心,但《坦园日记》中毫无涉及。
(93) 同治九年十二月,郭嵩焘曾“交杨朋海带投合肥相国一信”,表明恩寿本有次年赴京会试打算。恩寿母亲去世,张自牧及时函告郭嵩焘,后湖南巡抚王文韶亲赴杨宅致吊。这是杨氏家庭在长沙社会地位的体现,不应单纯作恩寿中举所致理解。参见《郭嵩焘日记》(二),第641、649页;《王文韶日记》,第245页。
(94) 王先谦赞恩寿的从幕能力:“调停不枘鑿,信子夙所长”。另据同诗知,同治十三年,时云贵总督刘嶽昭(字荩臣,湖南湘乡人)有意招恩寿入幕,而王先谦劝恩寿赴云南(《虚受堂诗存》卷9,第5—6页)。 不过恩寿是否曾入刘嶽昭幕待考,因刘氏当时不在任所,且光绪元年即遭革。恩寿居云南似当与其前幕主杜瑞联相关。光绪元年杜氏迁四川按察使,又二年迁云南按察使任,并直至云南巡抚。据光绪二年李榕函可知,恩寿不在杜氏任川臬幕;据王闿运光绪六年函可知,时仍在云南的恩寿有意往湖北候补官职,但王氏劝其打消此念。参见《李申夫(榕)先生全集》卷5,第5页;《湘绮楼诗文集》,第988页。
(95) 《郭嵩焘日记》(四),第389页。
(96) 《王文韶日记》,第774、775页。
(97) 当年冬,恩寿作咏梅诗:“花好原宜冷处看,萧萧风雪晓凭阑。三春桃李誇繁艳,谁抱冰心耐岁寒”。该诗以“高处不胜寒,我欲乘风归去”的意境,表达其自甘沉沦的思想。参见《坦园日记》,第267、299页。
(98) 《校邠庐抗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页。称士子参试“若探筹”,表明冯桂芬认为取士效能的下降成为科举队伍恶性膨胀重要原因,因此他主张加大考试难度作为控制考试规模的措施。
标签:咸丰论文; 太平军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长沙发展论文; 历史论文; 同治论文; 王先谦论文; 科举制度论文; 湖南发展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太平天国论文; 汉书论文; 后汉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