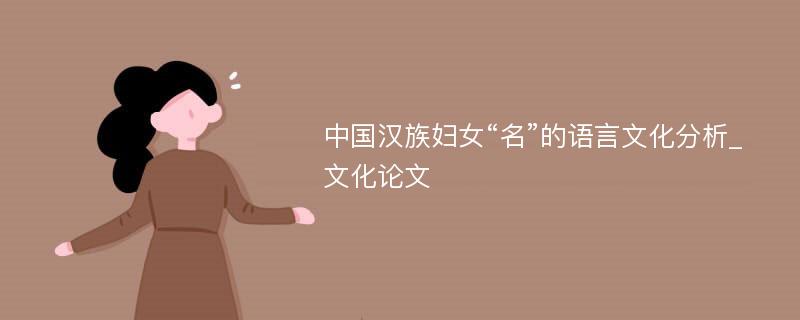
中国汉族女性“名”的语言文化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族论文,中国论文,语言论文,女性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姓名,是一种特殊的符号,它以文字的形式代表了一种语言现象,又因其蕴涵了人的指称 而 代表了一种文化现象。姓名由“姓”和“名”组成,“姓”是家族的徽号,象征着血缘承传 ,“名”则是用来区分彼此的识别标志。本文以中国汉族女性的“名”为核心,以期通过对 其形式和内容的描述分析,来揭示其中包含的语言文化信息和与之相关的人文道德精神。
一、“名”的概说
“名”由“夕”和“口”组成,《说文解字》解释说:“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 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由此可见,人名产生于人与人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它的最 本质的作用,就是在社会交往的所有场合都可以区别人的个体。
“名”的产生早于“姓”,最早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史前时代,因为从那时起的原始人就在 彼此生活交往中开始有了区别个体的单名。[1](P3)人类进入封建时代以后,姓与名合而为 一,成为具有社会象征意义的符号系统。
这一符号系统除具有对人群中个体的指代意义这一基本属性外,还有其他的特性,王大良 先生将之归纳为简明性、审美性、稳定性和地域性。[2](P87)简明性是指其作为一种语言现 象表现出的口头语音和书面文字两个指标上的简洁、短促。后三者则是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而派生的特征,审美性指代“名”在字形、字义上对人的感觉的愉悦性;稳定性指代其作为 某一个体专有符号的长期性和有效性;地域性则包含了不同地方文化对“名”的意义的理解 和认识。
“名”与“姓”不同,“姓”作为家族的象征具有传承性和统一性,一个家族中的个体, 在“姓”的同一前提下,而“名”则具有随意性和多样性。“名”除了作为某一个体的指称 符号外,还具有其他功能。譬如包含了父母的期望,表达了该个体在家族中的行辈,隐含了 与该个体有关的阴阳五行、命相运气等。
二、中国女性“名”的显性意义
一般而言,男性之名与女性之名具有明辨性的差异。汉族传统上的男女人名在外在形式和 内 在意义上有区别。“在历代的取名实践中,男性的取名重视刚劲、响亮,女性取名则充满柔 顺、甜美。这些习惯作为历史的积淀,反映了人们对审美观的追求。在这种习惯下,男性的 名字与其将要扮演的角色是和谐的,女性的名字与其性别特征也是和谐的。只有如此,才能 反映出名与实的统一。”[3](P124)
(一)女性“名”的字形、音、义选择
女性作为与男性相对比的群体,其体质、性格、社会角色、文化期望等方面的特征使其定 格于一种阴柔的文化氛围中。女性的“名”因而也选用与阴柔有关的字。女名用字通常有以 下八类:
①女性字:娘、女、姐、姑、姬、娥、婷、娜
②花鸟字:花、华、英、梅、桃、莲、凤、燕
③粉艳字:美、丽、倩、素、青、翠
④闺物字:秀、阁、钗、钏、纨、香、黛
⑤柔景字:月、湄、波、云、雪、雯、春、夏
⑥珍宝字:玉、琼、瑶、珊、瑛
⑦柔情字:爱、惠、喜、怡
⑧女德字:淑、娴、静、巧、慧
女性的名在字形的选择上,除具有与男性相同的规则,即名为姓的省文,名为姓的增文, 名为姓的分文外,①还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选用以“女”字为偏旁的字,如上述的娘、 媛、姬、娥等。选用这些字,能直接表明该个体的性别身份。我国有“女娲补天”的故事, “女娲”这一名字被认为是最早使用女性字的例子。其实,这些以“女”为偏旁的字中有很 大一部分是从姓演化而来的。《说文解字》中解释“姓”曰:“人所生也,从女从生。姓的 本义就是妇女所生,如姬、姜、嬴、妫、姒、姞、婤、姶之类是也。”[1](P35)古代女 子无名,以姓为名,又以字系姓为称,如伯姬、仲子、季姜之类,后世不明其理,误以为 “姬”、“姜”之类字为名,从而导致了他们由姓到名的演变,女名中如“虞姬”、“孟姜 ”、“窦娥”等便是如此。
女名在字音的选择上,也隐含了性别身份。一般情况下,汉语音韵十三辙中的一七、姑苏 等音色细弱,而阴平声调听觉清脆,为女名常用,如“玉”、“媛”、“芬”、“娇”、“ 花”、“云”、“娴”、“晶”等。[5](P165)另外,女名也常利用同音字假借之法来选取 ,如“娣”音同“弟”,许多未生育儿子的夫妇都喜选用此字作为其女的名,前冠以“ 招”、“引”、“领”、“盼”等字,以表达他们期望下胎为儿子的愿望。除此以外,女名 在字音的选择上,还喜用叠音,这种情况在近二三十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历史上如北宋的 李师师、明代的陈圆圆,当前的如范冰冰、李媛媛等。这种叠音名读来朗朗上口,听来婉转 入耳,用于女性身上,还能让人体会出娇美和乖巧的意味来。
女名在字义的选择上,更突出地强调了女性的性别角色。自古以来,以花鸟字、闺物字、 粉艳字、柔景字、珍宝字、女德字命名的女性占据女性总数的绝大部分,这涉及到人们的文 化心理和审美观的问题。女性阴柔娇美的性格和体态特征使人们总是将之与花鸟相联系,以 花鸟字为名,意寓女子容貌秀丽、性格温婉。闺中之物和珍宝饰品是女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装饰物与用品,他们与女性息息相关,装点、修饰了女性,因之成为女性的又一象征。以闺 物字和珍宝字为女名,一方面具有审美观上的熨贴、恰当之感,另一方面寄托了父母希望女 儿性格柔和、生活富贵美满的心愿。粉艳字和柔景字是又一组携带了女性气息的符号体系, 微波流云、早春晚夏、彩霞柔月,这些字眼体现出“阴柔之美”,与人们传统心理中女性之 美合而为一。选用粉艳字和柔景字为女名,符合大众的审美情趣,亦有“人如其名”的含义 。从女名用字的意义选择上可以看出,其字义多表达了性格上的温婉柔和与容貌上的娇美秀 丽,在女名中很少能体会到男名中包含的高远志气,这可能与中国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 ”、“郎才女貌”等观念有关。
(二)女性名的变迁
据王国维的《殷商制度论》所述,殷商时代的男女“皆以日名”,按殷人以天干表日,即 殷人以天干命名,而未见姓氏制度,从而提出了殷代女子无称姓,周代才建立“男子称氏, 女子称姓”制度的结论。[1](P24)据此论,商周以前,女子是有名而无姓的。
商周时代,女子无名,以姓为名。这是因为女子要嫁到他族去,明其姓是为了“同姓不婚 ”。顾炎武《日知录》曰:“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氏一再传而可变,姓千万年不变”。[4 ](P56)如前所述,女子在姓前以字系姓为称,如伯姬、仲子、孟姜等。
人类进入封建时代以后,逐渐形成了“姓+氏+名(包括字、号等)”的姓名结构,后来姓氏 合而为一,又形成“姓+名(字、号)”的姓名结构。但封建时代的女性处于男性的从属地位 ,女性的名字只在出嫁之前使用。出嫁以后,因为变成了某男子的夫人,其名字也变成“夫 姓+ 己姓+氏”的固定格式。《颜氏家训·风操篇》载,南北朝时期,妇女已嫁,则以夫家姓氏 称之。[1](P70)《后汉书·烈女传》中,已婚女子皆称某人妻,如“渤海鲍宣妻”、“太原 王霸妻”等。如果其子成名,则以儿子姓名为称,如“陶侃母湛氏”、“虞谭母孙氏”。[1 ](P70)随着时代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女性逐渐抛弃了“夫姓+己姓+氏”的姓名形式,特别 是新中国成立后,女子的姓名也同男子一样,采用“己姓+名”的格式。且在用字的表意上 ,突破了花鸟、珍宝、柔景、粉艳等字类的范围,有的名字具有男性化的趋势。
三、中国汉族女性“名”的隐性意义
姓名首先是社会交际中用于识别个体的符号体系,以语言文字的形式表现在口头或书面上 。但这一语言符号体系形式和结构的背后则反映出一定的文化内涵,如信仰、习俗、道德观 、价值观、美学观、文化心理等。
(一)封建时代女“名”反映的社会道德规范
不同人名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可折射出不同的文化内涵。“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在人名的表层 会有什么样的投影。如汉族人名系统受汉民族文化的礼教、等级观念的影响和限定,人名现 象中便有明显的礼教色彩。”[5](P203-204)
中国封建时代盛行“男尊女卑”的道德规范。“阴为地处下而卑”,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庸 而存在。男尊女卑的观念渗透于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名也不例外。封建时代的女名 很好地体现了“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道德训诫。女孩出嫁前之名因其嫁于某 男 子而不再使用,出嫁后采用“夫姓+父姓+氏”之格式,而当丈夫死去后又被称为“某某之母 ”。①有些女子终其一生都没有专属于自己的名字,对他们的称谓无不折射出男本位的观念 。
“男尊女卑”观念对人名影响的另一方面表现在男名的正式、庄重复杂,女名的随意、简 单上。东汉以后,名字越变越复杂,有的官僚、贵族子弟,始生就有名、有字,且名与字的 含义须相一致。除名与字外,古代的男子还有许多代替名字使用的其他称号,如别号、室号 ,以官爵故里代替名字之称呼,对前代皇帝称庙号,对已故人物称谥号等。如明代的王守仁 ,他又叫王伯安(字)、王余姚(籍贯)、王新建(爵封新建伯)、王文成(谥)、王阳明(号)。女 子之名则不讲究上述规则。女子之名只在出嫁前使用,就算是在出嫁前,一般的女子也很少 有正式的名字,大多依行第称大女、二女、三女或大姐、二姐、三姐。少数女性有自己固定 的名或字号,他们大都是出身较好或受过才学熏陶的女性。
中国封建时代对女性之德行设立了一套严格的规范,“三从四德”、“三纲六纪”被视为 约束妇女行为和品格的正统为妇之道。贤淑敏惠、忠贞守节、灵心慧质、恭承曲顺等是古代 妇道的具体规定,因而,在女名中,“贞”、“淑”、“瑞”、“娴”、“静”、“慧”、 “巧”等妇德字占有很大比例。另外,中国古代采取弱化女性才之标准的倾向,认为习得、 精通“女红”便是女子之才,因而,女名中也大量采用“纨”、“织”、“绢”、“绣”等 与织做有关的字。以妇德字和“女红”字为女名,不但寄托了父母期望女儿忠于妇道、熟于 妇道的心愿,亦符合了传统道德对女性的规范和顺应了社会风气。
(二)建国后女性“名”的变迁
作为一种特有的语言文化现象,人名也随时代的推移而变异,不同时代的文化总是带有该 时代的烙印,从人名的变迁亦可以证实这一点。
新中国建立后,女性的姓名逐渐摆脱了“夫姓+己姓+氏”的传统模式,采用与男子相同的 “己姓+名”的格式。这一改变使女性之名在语言的层面上具有了较大的可选性;在文化的 层面上具有了广博的隐寓性;而在社会运动的层面上,则具有了一定程度的记忆性和时代性 。
建国初,人人歌唱新中国,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这一时期,“华”、 “英”等字是女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据统计,在1949年10月至1966年5月间,“华”、 “英”二字在使用率占前6位的人名中位居第一和第二,②人们选用这些字,一方面表达了 对新中国的热爱之情;一方面使其名字具有纪念意义。建国初出生的女性中,名如“建英” 、“振华”、“国华”之类的十分多见。
文革期间,全国山河一片红,人名作为时代缩影的见证之一,也体现了那个时代特有的事 物,如“跃进”、“卫东”、“文革”等。“红”作为传统女名用字之一,成为文革期间最 受青睐的字眼。据统计,1966年6月至1976年10月之间,“红”字的使用率居全国首位,诸 如“继红”、“永红”、“卫红”、“志红”等名字屡见不鲜。这时的名字,超越了符号体 系的文化含义,而具有了政治色彩。
文革后,社会逐渐摆脱了畸形发展的轨道,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行动自由获得了空前的 保障。这种相对的自由体现在名字上,突出反映在选字范围的广博、意义的多源和审美性的 加强等方面。从现时的人名中已很难寻觅到高度的政治性,父母为儿女取名,一是寄托自己 对儿女的期望,二是力求使名字新颖独特,不落俗套,上口易记。女名也具有这些特点。由 女名的演变可直接映射的一种观念变迁是由“男尊女卑”向“男女平等”的转化,这主要 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女性的姓名不再隐喻女性是男性的附庸这一含义,尽管目前社会上也 存 在“夫姓+太太”之类的称呼,但这仅是一种对女性的敬称,而不是作为其固有的姓名所用 ,女性的姓名与男性姓名一样采用“己姓+名”的格式;二是女名的选字不再一味强调选用 可标示女性性别身份的字,许多女性拥有男性化的名字,如物理学家吴健雄,邮票设计家卢 天骄,外交家丁雪松,机械师梁军等,[2](P267)从一些女性的名字中亦可以看出高远的志 向和理想,这类名字不再为男性所独有;三是近些年在取名时出现了“父姓+母姓+名”的形 式,采用这种取名法一方面是为了避免重名,另一方面似也隐喻了母亲姓的被重视。
观念变迁的另一表现,在于姓名的血缘宗法功能逐渐淡化,人们取名不再像过去一样重视 姓名的血缘意义,而将姓名作为单纯的人际间彼此识别的符号。过去,许多人名以家族行辈 为依据,同一家族的同辈人,均采用属于他那辈人专有的派字。如今,这种现象有不断减少 的趋势,人们更愿意在名字中表达愿望、喜好或理想。女名在过去一般不按辈分取,现在更 加脱离这一传统规范。近来女名中出现了一些新兴的用字,如“婧”字,因表达了“女子有 才能”的意义而被众多望女成凤的父母所钟意;又如“书”字,因其含有“知书达礼”的意 义而被广泛采用。女名的另一流行趋势在于英文名谐音的采用,如丽娜、琳达、玛丽、海伦 等。这些现象都表明人们为姓名赋予的血缘宗法意味的减弱,名字在音、形、义、文化蕴意 等维度拥有越来越自由的选择空间。
四、结 语
“姓名使用的语言材料及其组合构成姓名形式。姓名形式是有限的,而来自社会的姓名意 义却是无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