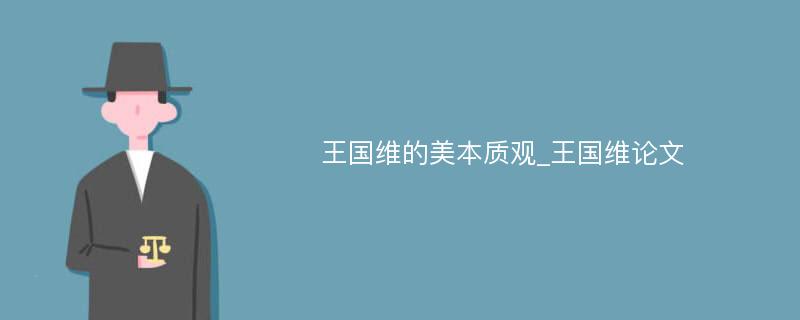
王国维美的本质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质论文,王国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194(2001)04-0418-05
研究王国维美学思想者,无不重视他与叔本华的关系。但长期以来,叔本华对王国维的影响被不自觉地夸大了。一谈到王国维,人们想到的不是近代中国的社会特点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特性,而是悲观阴郁的叔本华哲学。事实上,由于传统文化和近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制约,王国维美学思想经历了一个由信仰叔本华到怀疑、扬弃,再到融合德国古典美学和儒家美学而思考美学问题的发展变化过程。本文拟从美的本质切入,重新审视王国维与叔本华的关系。
无论多么对立的美学理论,对“美”的界定都建立在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上。抽象地说,美与人的本质是一种显现和象征关系。在王国维哲学思想中,人的本质即“人性”。长期以来,人们把王国维的人性论局限于叔本华哲学的影响,忽视了王氏人性论的其它丰富内容,从而造成了对王氏人学思想理解的片面性。这种片面的理解表面看来并不缺乏依据,王氏在《红楼梦评论》中说:“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此即宇宙永远的正义也”,“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1]据此,人们断言,王氏完全接受了叔本华的人性论:人生即欲望和痛苦。但《红楼梦评论》是王氏前期思想中极不成熟的作品,其中对叔氏哲学思想的运用明显带有削足适履的痕迹。并且《红楼梦评论》中的人论思想只是王氏整体人性论的一部分,当王氏从哲学高度独立思考人的本质时,则认为性善性恶均不能成为形而上的命题,人的本质是不可知的:
今《孟子》之言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曰:“人之性恶”。二者皆互相反对之说也,然皆持之而有故,言之而成理,然则吾人之于人性固有不可知者在欤?孔子之所以罕言性与命者,固非无故欤?且于人性论中,不但得容反对之说而已,于一人之说中,亦不得不自相矛盾。《孟子》曰:“人之性善,在求其放心而已”。然使之放其心者谁欤?《荀子》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然所以能伪者何故欤?汗德曰:“道德之于人心,无上之命令也”。何以未几而又有根恶之说欤?叔本华曰:“吾人之根本,生活之欲也”。然所谓拒绝生活之欲者,又何自来欤?……今论人性者之反对矛盾如此,则性之为物,固不能不视为超乎人之知识外也。
王氏在人的本质问题上的游移态度和不可知论倾向,实际上从逻辑上否定了人的本质是“生活之欲”这一命题。这一点对理解王国维的美学思想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无论是康德、席勒,还是叔本华、王国维,都把美作为对人的本质的直观或显现。人的本质决定着美的本质。如果像叔本华所说,人的本质是生命意志,人生是罪恶和痛苦,那么美和艺术就会合乎逻辑地成为对痛苦的直观和逃避;但如果人性有善的一面,人生是合理的,那么美和艺术就应该是道德的象征和理想人生的显现。王国维美的本质观正是沿着这两条道路而发展、分裂乃至矛盾的。
人的本质和世界的本质在叔本华哲学中是一个盲目的意志冲动。意志是世界的本体,它表现于主体就是求生的意志和无尽的欲望。主体的合目的合规律的实践活动完全被盲目的意志吞没了。“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一切欲求的基地却是需要、缺陷,也就是痛苦;所以人生来就是痛苦的……如果相反,人因为他易于获得的满足随即消除了他的可欲之物而缺少了欲求的对象,那么,可怕的空虚和无聊就会袭击他,所以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着。”[2](P427)那么,如何摆脱这种痛苦和无聊呢?叔本华开出的药方就是审美和禁欲。就审美而言,是主体产生一种神秘的变化,上升为不带意志的纯粹主体。这种纯粹主体超越了根据律的束缚,从而直观到的不再是具体的对象而是与自身无利害关系的对象的理念。此时,对象与主体就形成了审美关系,而对象则成为审美对象。由此可见,叔本华一方面否定了主体感性欲望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夸大了这种感性欲望的必然性。前者使他把审美看成是与感性相对立的东西,后者又使审美活动的产生与他的意志本体论自相矛盾。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和《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中全面接受了叔氏关于美的本质的理论。王氏确信,人生、欲望和痛苦是三者而一的。主体的一切活动无不为生命意志所驱使,从而陷入永无休止的痛苦,因为主体与对象的关系是一种现实的利害关系。而美的对象不是具体的“特别之物”而是对象的理念,审美主体也不再是为欲望所驱使的“特别之我”,而是“纯粹无欲之我”。但任何接受过程都同时是一个阐释的过程。在叔本华那里,审美对象的不关利害有赖于主体上升为纯粹主体,而王氏似乎没有觉察到叔氏的良苦用心,总是要在审美主体之前预设一个已经存在了的审美对象。“唯美之为物,不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而吾人观美时,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尽管王氏同意叔氏关于审美本质的理论,但究竟是审美主体将特别之物转化为审美对象呢?还是审美对象将特别之我转化为审美主体呢?如果说在这里王氏尚未自觉到叔氏的矛盾,那么对“拒绝意志”的怀疑则开始了反思和突破。
对“拒绝意志”的怀疑从两个方面拓宽了王氏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从而使自己的美的本质论走出了叔本华美学的阴影。一、如果拒绝意志是可能的,那么人的本质(生命意志)里就内蕴着否定自身的因素,即人有“生活之欲”,同时又有“拒绝生活之欲”之欲。这样,人的本质是“生活之欲”的命题就破产了。二、如果拒绝意志是不可能的,而现象界又存在着善与恶的对立,则意志作为本体,表现于现象界既能为善又能为恶。无论如何,人的本质是“生活之欲”都无法自圆其说。因此,王氏一面说人的本质是“生活之欲”,一面又说:“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岂不以其有纯粹之知识与微妙之感情哉?”(《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然人之所以为人者,岂徒饮食男女,芸芸以生,厌厌以死云尔哉?饮食男女,人与禽兽之所同,其所以异于禽兽者,则岂不以理性乎哉?”[3]在王氏看来,人不仅有饮食男女等基本需求,更有理性,情感等高层次的需求,并且只有后者才是人的本质特征。其实叔本华尽管把人的本质与万物的本质都视为“意志”,但当他说人能够直观理念并自觉拒绝意志时,实际上是以一种歪曲的方式指出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因为动物是直接属于自然,为本能所支配,既不能直观自身也不能拒绝意志。只有人才能超越自身的自然性,改造自然同时也改造自身。但由于叔氏对理性的仇视,人对自然的超越性成了非理性的直观,并且反过来与主体的感性存在相对立。按叔氏的逻辑,人的本质应当是对理念的直观和对物欲的超越。王氏引用叔氏的话说人是“形而上的动物”,就是指这一点而言。但叔氏恰恰是把生命意志作为人的本质,于是直观与意志就成了势不两立的东西,无法统一在人的本质之中。
王氏意识到了叔氏在此问题上的矛盾,他借助席勒的“游戏说”提出所谓的“势力之欲”:
人类之于生活,既竞争而得胜矣,于是此根本之欲复变而为势力之欲,而务使其物质上精神上之生活超于他人生活之上。此势力之欲,即谓之生活之欲之苗裔,无不可也。人之一生,唯由此二欲以策其知力及体力,而使之活动。其直接为生活故而活动时,谓之曰工作,或其势力有余,而唯为活动故而活动时,谓之曰嗜好。(《人间嗜好之研究》)
王氏企图区分主体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不同,前者“直接为生活故而活动”,后者则“唯为活动故而活动”。但他最终没能把二者从本质上区别开来。因为“势力之欲”在本质上也是寻求一种感性的满足,并非精神对物质的自由超越。它是主体的基本生理需求满足之后,进而要求在“物质上精神上之生活超于他人生活之上”的争强好胜的欲望。就文学艺术而言,则是势力之欲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而在虚构的境界中得以发泄。而真正伟大的艺术,则具有普遍性,因为它发泄的是人类整体的势力。我们知道,主体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实现自身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从而直观到实践结果是对其自由自觉的本质的肯定与确证而感到喜悦和愉快。而主体的美感一旦产生则不仅会对自然的合目的的形式感到愉悦,而且要求主动创造新的艺术形式来满足自身的审美需求。王氏未能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来解释这一问题,因而使用了“势力之欲”解释人类的审美需要。但由于“势力之欲”在根本上和“生活之欲”并无本质区别,这就使得作为满足“势力之欲”的手段的审美和艺术缺乏应有的超越性和自由性。王氏试图通过席勒的“游戏说”实现感官快感向审美快感的过渡。但他理解的“游戏说”是一种社会生物学的观点,“势力之欲”与席勒的“游戏冲动”并不是一回事。王国维认为文学艺术是“势力之欲”的发表,是“剩余势力”的产物。但这种“剩余势力”仍然是一种感性欲望,它无法说明美和艺术的理性内涵。虽然“势力之欲”的提出不能科学地解决美的本质问题,但它毕竟突破了叔氏的审美本质论。在王氏看来,审美已经不是与感性欲求相对立的东西,而是满足“势力之欲”的手段。
王国维的美的本质观的发展变化,还与康德美学有关。叔本华“审美无利害”的观点源于康德,但又与康德有本质的不同。康德的“审美无利害”建立在他的合目的性概念的基础上,即自然向道德的、文化的人的生成。审美活动是无目的而又合目的的,无目的的形式自由地符合着主体的认识功能和终极目的。而叔氏的“审美无利害”却有一个具体的目的,即摆脱感性欲望引起的痛苦和空虚。王国维声称自己是由叔本华上窥康德的,而实际上却是借助康德而摆脱叔本华的。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中,王氏采用了康德关于“美”的定义,并根据自己的理解结合中国的艺术实践经验作了发挥。“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也。”“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在这里,王氏仍坚信美是无利害的形式,但这时的无利害不是为了避开现实利害所造成的痛苦,而是为了纯粹的不带欲念的爱玩,这种“爱玩”与王氏对人的本质的扩充相适应,是主体的一种内在需求;这里的“形式”也不是叔氏所谓的无意志的主体所直观到的对象的理念,而是一种有意味的、能够表现主体某种感情的形式。“就美之自身而言,则一切优美皆存于形式之变化及调和。至于宏壮之对象,汗德虽谓之无形式,然以此种无形式之形式能唤起宏壮之情,故谓之形式这一种无不可也。”“故吾人之感情外,凡属于美之对象者,皆形式而非材质也。”前文曾提出,叔氏的逻辑是主体上升为纯粹主体,然后审美对象才得以产生。而王氏则预设一对象,对象使主体升华为“无欲之我”。在王氏看来,美是一个既在的对象,是能够唤起主体某种感情的形式。经由康德,王氏扩展了他对美和艺术的本质的理解,不再局限于叔本华美学。审美对象不再是主体摆脱意志的工具或无欲之我直观到的理念,而是带有欲望的主体的情感的表现形式,是主体精神、人格的外在表现。当王氏脱离对美的本质的抽象思辩,尤其是当他面对活生生的艺术创作和特殊的中国艺术客体时,就得出了一系列准确的结论。“诗歌者,感情的产物也。”“诗歌者,……描写自然及人生。”“诗歌之题目皆以描写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主。其写景物也,亦必以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始得于特别之境遇中,用特别之眼观之”(《屈子文学之精神》)。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特别之眼”和“特别之境遇”。本来,王氏介绍叔本华美学时说:“一、被观之对象,非特别之物,而此物之种类之形式;二、观者之意识,非特别之我,而纯粹无欲之我。”[4]而在这里,王氏认为诗歌创作却必须在“特别之境遇”中以“特别之眼”观之。这不仅不同于叔氏而且简直与叔氏对立了。“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也……激烈之感情亦得为直观之对象、文学之材料,而观物与其描写之也,有无限之快乐伴之。要之,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文学小言》四)情感是主客矛盾冲突在主体方面的反映,叔氏所描述的审美过程中主体对理念的静观,实际是以虚幻的方式回避主客矛盾,而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是通过对主体情感的否定而实现的。王氏要求艺术表现情感,则是对主体情感的高扬与肯定。这是对中国古典艺术抒情本质的准确把握。“夫绘画之可贵者,非以其所绘之物也。必有我焉以寄于物之中。故自其外而观之,则山水、云树、竹石、花草,无往而非物也;自其内而观之,则子久也,仲圭也,元镇也,叔明也……画之高下视其我之高下,一人之画之高下又视其一时之我之高下。”(《二田画庼记》)必须指出,王氏在这里所说的艺术要表现“我”,已不是叔氏的“无欲之我”。在叔氏那里,审美对象也不是纯粹主体的表现,而是在无利害观审中主客体的同一。王氏在这里所说的“我”,恰恰是充满生命活力,情感激荡的创作主体。就自然美而言,王氏认为:“古之君子,其为道也盖不同,而其所以同者,则在超世之致与不可屈之节而已。其观物也,见夫类是者而乐焉;其创物也,达夫如是而后慊焉。如屈子之于香草,渊明之于菊,王子猷之于竹,玩赏之不足而咏叹之,咏叹之不足而斯物遂若为斯人之所专有。是岂徒有托而然哉?其于此数者必有以相契于意言之表也。”(《此君轩记》)自然事物之所以美,在于它象征了主体的精神、人格和情操。
在《红楼梦评论》中,为了突出说明美的不关利害的性质,王国维还使用了叔本华美学中“眩惑”这一概念(《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译本译作“媚美”),它指不但不能使人远离生活之欲,反而激发感性欲望的对象。他列举的例子中有《西厢记》的《酬柬》和《牡丹亭》的《惊梦》。但在《人间词话》中,他却肯定了主体的情欲和感性追求。王氏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又在《宋元戏曲考》中说:“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就是说境界(美)的本质在于真感情的感性显现。但是要追问什么是真感情,就涉及到了人的本质问题。真感情,无非就是理想的本质的人应该具有的感情。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久(守)贫贱,轗轲长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非无淫词,读之者但觉其亲切动人。非无鄙词,但觉其精力弥满。
以“亲切动人”和“精力弥满”衡,王国维恐怕要推翻自己原来的结论。佛雏先生认为,真感情就是叔氏所谓的罪恶的生活意志。[5](P16)笔者认为这恰恰颠倒了真感情与境界的关系,因为在《人间词话》中,境界(美)是对真感情的肯定和高扬。
由上述可见,王氏关于美和艺术的本质除了在起点上搬用了叔本华的一些观点外,他对美和艺术的理解与叔氏是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所以,不能简单地用叔本华美学来套王氏的一系列符合中国古典艺术实践的理论观点。但是王氏虽然试图从哲学的高度探索美和艺术的本质,但远远没有达到康德和席勒的高度。康德关于自然向人生成和席勒关于“游戏冲动”的观念是“自然的人化”和“人的对象化”思想的萌芽,但王氏显然没有理解康德、席勒的这一思想。所以他看到了美是对感性欲望的超越但又并不否定感性生命(这是他与叔氏的根本分歧),却不明白美为什么不关利害而最终又肯定了主体的生命意志。这实际上仍是感性和理性如何统一的问题。王国维美学思想是在中国知识分子为解决民族危机而对传统和现实进行反思的背景下形成的。这一方面造成了王氏在对西方美学思想接受过程中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使王氏没有成为西方美学思想的奴隶,他对西方美学的接受无不与中国的传统和现实有关。而这正是王国维哲学美学思想的意义所在。所以,要真正把握王氏美学思想的本质,必须同时考虑到它与西方美学、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近代的社会现状三个方面的关系。
[收稿日期]2001-03-30
标签:王国维论文; 康德论文; 叔本华论文; 美学论文; 理性与感性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哲学家论文; 王姓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