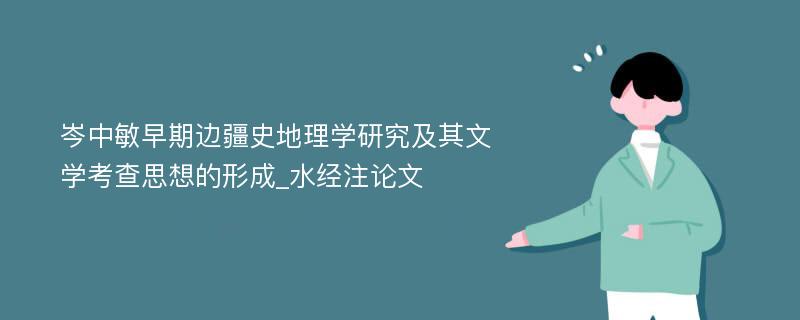
岑仲勉早年边疆史地研究与其文献考掘思路之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疆论文,早年论文,文献论文,思路论文,岑仲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岑仲勉(1886—1961),名铭恕,字仲勉,原名汝懋,以字行,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先生一生精研乙部之学,不仅于先秦史、隋唐史、中外交通史、少数民族史(尤其是突厥史)、史地学、金石学、文献学等研究领域均有不朽建树,尤对所治领域史料有大量校雠辑佚,征引广博,考订精审,为20世纪文史研究、特别是唐研究提供了一份坚实的文献基础,沾溉后人良多。上世纪50年代,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刘节教授即将岑仲勉与陈寅恪二先生并称为“中古史的两位大师”①,此后不少学人也一再提到岑仲勉先生在中古文史文献考据方面的贡献②。考察其学术历程可以看到,岑仲勉致力于文史文献考据这一学术进路的形成,与其早年边疆史地研究紧密相关。作为自学名家的学者,岑仲勉早年学术研究主要围绕乙部史地考订之学展开。他那些篇幅长短不一、征引史料繁复、考订雠校严密的史地学论文,虽然文献涉及面与后期相比并不算宽,但其中所透显出的“史源”追考意识,无疑成为岑仲勉此后治学偏重文献考据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一、史地考订中的“史源”追查
岑仲勉自1912年底毕业于北京高等专门税务学校后,先后进入沪、粤两地政府机关供职,长达二十年之久。工余之暇,博览群书,尤关注实科及乙部之学,撰有大量读书笔记。30年代之前,除《对于植物学名词的管见》(1923年《科学》8卷11期)、《楮构说》(1924年《科学》9卷1期)、《遵路杂缀》(1928年《津浦之声》3—4期)等少数几篇文章外,其研究所得多未发表。直至1931年任教广州圣心中学后,岑仲勉始借编辑校刊《圣心》,逐渐将其早年学术成果公诸于众③。从这当中,恰可见其早年学术思路。
依陈达超教授所整理之《岑仲勉先生著述要目》④,岑氏在《圣心》杂志共发表论文31篇,其中一期14篇,二期17篇,今收入《中外史地考证》一书者26篇⑤。这26篇论文均为史地考订类,篇制不一,长者数万言,短者百十字。就内容而言,大体可划分为八类:
(一)重要古地的证订。如《唐代阇婆与爪哇》、《阇婆婆达》。
(二)古代地理交通考证。如《南海昆仑与昆仑山之最初译名及其附近诸国》、《掘伦与昆仑》、《明代广东倭寇记》。
(三)建置及区域考证。如《〈拉施特史〉十二省之研究》、《唐代大食七属国考证——耶路撒冷在中国史上最古之译名》、《〈诸蕃志〉占城属国考》、《广府》。
(四)往日为人所忽略的边远史地考订。如《柳衢国 致物国 不述国 文单国 拘萎蜜国》、《阿軬荼国》、《奇沙国》、《末罗国》、《憩野》。
(五)汉籍记外国地理之误会辩证。如《〈水经注〉卷一笺校》。
(六)外语所译我国地名之原名考释。如《暮门》、《zaiǜun非“刺桐”》、《Quinsai乃杭州音译》、《波凌》、《亚俱罗》。
(七)唐以前地理佚书考辑。如《晋宋间外国地理佚书辑略》、《〈翻梵语〉中之〈外国传〉》、《王玄策〈中天竺国行纪〉》、《西域记》。
(八)不经见之外地名称的考释。如《苫国》、《朱禄国与末禄国》⑥。
就上述诸文之考订方法而言,岑仲勉在上世纪60年代重编《中外史地考证》的“前言”中曾予略述:
抑既寝馈于斯二三十年,虽乏寸长,要思献曝,今试略言之:
要注重材料来源之价值。如一等、二等……之类是也。文字一经转录,字句小差,便生别解⑦。
可见,“注重材料之来源”——亦即今人所常言之“史源”追考,正是岑仲勉数十年史地考订、甚且可谓其整体学术研究方法上的重要小结。
应该说,岑仲勉“注意材料之来源”的思路,受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特别是“三通”之研究思路影响颇多。
中国古代史学研究素有“原始察终”(《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的学术传统,故司马迁“通古今之变”说(《报任安书》)堪谓后世治史通则。这一点,在“三通”之中尤有体现。刘知几《史通·自叙》即指出,“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道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⑧;此后郑樵《通志·总序》也明揭“学术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⑨ 的治史轨则;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更倡言,要研讨古来典章经制“变通张弛之故”,“非融会错综,原始要终而推寻之,固未易言也”⑩。此三者所述“指归体统”之辨察、“学术源流”之检讨、“典章变通”之推寻,可谓均含有一种“商榷千载”(《史通·六家》)的眼光和胸怀,力求就古来史学之发展流变“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杜预《春秋左氏传序》)。故后世断代史书的首出之作《汉书》,尽管有班固“综其行事”、“上下洽通”的修撰声明(《汉书》卷一百《叙传》),但仍不免为《通志》、《文献通考》所诋(11),可见此一传统之影响。循此线索来看,岑仲勉少年时即自修乙部之学,尤好读其父所遗留之“三通”(12),自然不会不受到上述史学传统之影响。
然中国史学凸显“会通”精神的背后,实不仅指涉对史实本身之条理安排,同时亦蕴有对史料本身予以考察之意涵。毕竟,追寻史实之迁变离不开对史料传录之考究,故考订析理史料之来源,正是史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刘知几在《史通·采撰第十五》中即指出,史书之撰著一方面要“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但另一方面,“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13)。当然,这种对“异辞疑事”的考察,尚非30年代以后陈垣所开创的“史源学”研究——后者更强调通过史料出处、主次源流之根寻(14) 来考察史料之信值,而岑仲勉真正受陈垣影响而明确标举“史源”这一概念也要迟至30年代中期以后(15)。但是,源于上述类似考察“异辞疑事”而形成的追查“材料来源”的研究思路,实早已潜藏于其早年的学术研究之中。这从《圣心》所刊诸文可见。
《唐代大食七属国考证——耶路撒冷(Jerusa-lem)在中国史上最古之译名》一文,在《圣心》所刊论文中篇幅较长,也是其中极见其治学特点的一篇。大食,即七世纪兴起于西亚地区的阿拉伯帝国,是当日世界堪与唐王朝并驾齐驱的强盛之国。有唐一代,双方多有往来,但中国古代史料中有关大食的记载却很少。晚清学者洪钧(1839—1893)《元史译文证补》曾指出,“《唐书》所纪都盘六国,方向程途,殊难考合”;现代著名史学家张星烺(1889—1951)《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对此亦曾有专门研究,然在岑仲勉看来仍存在一些“甲是则乙非”的问题(16)。故岑文由此入手,试图弄清大食属国相互间纠结难辨的方位关系。
文章先追考一般讨论此一问题的原始史料——即宋初王溥所编《唐会要》卷一百。其中记载,唐天宝二年(743),鸿胪卿王忠嗣答玄宗问“诸蕃诸国远近”时曾引及《西域图》。岑仲勉指出,史载永徽二年(651)大食始来朝,然许敬宗等奉敕纂修《西域图志》实在显庆三年(658)至乾封元年(666)(17),而大食此时实力尚未发展至中亚,故与王忠嗣所言情势显然龃龉难合。岑氏据此推定,王忠嗣所引述之《西域图》,并非许敬宗等所修之书,而只可能是玄宗时汤嘉惠所撰之《西域记》。岑文所提之汤嘉惠系玄宗时人,开元年间曾任安西副大都护(18),其书早佚。因而,要从许敬宗等所修之书与汤氏此佚亡之书追讨大食属国史料记载更早之史源,显然均已不可能。由此,岑文转换思路进一步指出:
惟《元龟》及《新唐书》传、志之史料,似无疑同出一源,其间小有异同者则缮写或剞劂之讹也。余频年习史地,每及此节,即作种种臆测,冀得一当,然或先入为主,或辄疑舛误,究不能自完其说,作而辍者屡矣。近则抛弃旧说,别开新途,先于宋人著述所记位置,某也符合,某也抵牾,作一剖解清表,次乃就其最不可解者构思之,始得一线之光明焉,虽不敢自谓必完全无误,然舍此解法,似更无以合乎旧籍各说(19)。
所谓“同出一源”之“源”,实即“史源”。亦即是说,从史源学角度来看,宋人王钦若、杨亿等所编之《册府元龟》,以及宋祁所修之《新唐书·大食传》、欧阳修所修之《新唐书·地理志》,与《唐会要》实为具“父子关系”或“兄弟关系”的史料,其价值具同一等次。因而,在无法追讨更早且更可信史源的情况下,惟有通过对同一等次信值的史料作相互比勘,以发现记载歧异最多的问题,由此入手方有进一步深入研讨的可能。岑文后部,正是通过列表比较,发现“除少数差点,如日程、方向等外,其书说中最不相容者,厥为岐兰之位置”(20)。然后以岐兰为观测点,根据各国间相互位置及距离日程,逐一考订陀拔思单、罗利支、都盘、渤达、河没、沙兰(今耶路撒冷)、怛满等大食七属国之具体方位。
很显然,岑文最终对问题的解决并未依托更早史源之追考而完成,但指出当时条件下所能追考到之史料相互间的源流关系,却无疑出于一种“史源学”的思路。稍阅《唐会要》与《新唐书》相关文字,即可印证岑氏“小有异同”之说——《新唐书·地理志》与《唐会要》文字几乎全同;《新唐书·大食传》稍有变化,但所载各国相互位置及距离日程也大多一致。由此可见,追讨史源正是此文核心思路所在。不仅如此,岑仲勉还提出在面对史源相近或具同等信值史料的情况下,如何开拓此类史料深层价值的可能。
又如《南海昆仑与昆仑山之最初译名及其附近诸国》一文。该文主旨在考订唐代“南航必经之途”(21) 的“金邻大湾”,及其旁之金邻国——亦即“南海昆仑”之实际方位。早在岑文之前,法人伯希和即撰有《交广印度两道考》(1904),费琅也撰有《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1919,岑文称《昆仑考》),已就中国南海和印度洋地区的海路交通作了开拓性研究(22)。然而岑文指出,伯、费二文并未注意到“南海‘昆仑’(非西域昆仑),在我国实为再出之译音,非最初之译音也”,因而未能发见此“最初译音”,“故昆仑族之来源,尚不能阐发净尽”。缘此,岑仲勉利用“对音”方法指出,“昆仑”系“金邻”之音转,而“金邻之称,有史记载,可上溯至三国时代,且起自南洋,洎后本我国地理上之通俗语,遂蜕化为昆仑,久之,人因其肤黑,凡皮色相近者又均以昆仑呼之,南海昆仑一语之历史,大概如是”(23)。此一结论及其“对音”方法运用之是非先不论,关键是如何考证“昆仑族”之真正起源,以及“金邻”之真实所在呢?岑氏于此恰另有一番“史源”追考的功夫和眼力。
关于史书中涉及“金邻国”之记载,岑文先引证《梁书》五四《诸夷列传·扶南传》,其中有扶南王范蔓欲伐金邻国事。文章指出,《梁书》此段故实“今各书所载《扶南传》残文无之”,因而以为“大约取材于康泰《扶南传》”,并推断“金邻国”之名,三国吴时即已有,且与扶南相邻(24)。由《梁书》所载故实,岑仲勉进而又追讨到三条史料:一是刘逵(渊林)《吴都赋注》所引《异物志》,文称金邻国去扶南二千里;二是《太平御览》卷七九○所引《异物志》所载“金邻一名金陈,去扶南可二千余里”;三是《水经注》卷一引竺枝《扶南记》所载“林杨国去金陈国,步道二千里”。由此断定:“金邻之名,确可上溯至吴,或且至后汉中叶;且知金邻一名金陈,去扶南及林杨各约二千里。”
然而,金邻四置若何仍未可知。岑仲勉又追考到《太平御览》卷七八八所引《隋书·南蛮传》(笔者按:今本《隋书》无此记载,《御览》所载应出自另一版本),以及《通典》卷一八八《边防典·南蛮下》,二书都记载由扶南渡金邻大湾,南行三千里,有边斗(一作班斗)、都昆(一作都雅或都军)、拘利(一作九雅或九离)、比嵩四国,“其农作与金邻同,其人多白色”。由此得出结论,金邻不仅是国名,且为湾名,金邻国即濒临此湾。又以扶南即今之柬埔寨,推定金邻大湾应即暹罗湾。同时,岑文更由上述四国及与之有关之顿逊、林阳(即林杨)、盘盘三国之地理考辑,最终考定“古金邻国之疆域,应为今暹罗西部迤西至下缅甸一带”(25)。
反观岑氏此文可见,倘要考察金邻国其地所在及其四至,《梁书·扶南传》及《隋书》(《御览》所引)、《通典》之记载似已可满足需要。那么,他何以又要追考刘逵《吴都赋注》、《太平御览》所引《异物志》,以及《水经注》所引竺枝《扶南记》?由文章的论证思路可以看出:
其一,成书于贞观十年(636)的姚思廉所纂修之《梁书》、魏征等所修之《隋书》,以及成书于贞元十七年(801)的杜佑之《通典》,三书在史源上来说不可避免有其“血缘关系”,难以互作引证;
其二,三书中以《梁书》为早(笔者案:姚思廉父察曾仕隋,本有初稿),但其《扶南传》一节又不见于他书残文,适为孤证。因此,岑仲勉实际是从史源追讨的角度,考及刘逵、李昉等书所引之《异物志》以及竺枝《扶南记》。刘逵系晋人,竺枝系刘宋时人,故所著皆较上三书为早。而刘、李之书所引《异物志》虽系简称,亦未见作者名,但岑氏以为其书或为东汉杨孚之《异物志》,但也不排除或为三国吴人万震之《南州异物志》、抑或吴人朱膺之《扶南异物志》等书的可能,总之至少可作为三国时期之史料来看。正由这三则史料,岑仲勉才断定“金邻之名,确可上溯至吴,或且至后汉中叶;且知金邻一名金陈,去扶南及林杨各约二千里”,从而为下文引证姚思廉等人之三书作史源上之证明。由此可见岑氏在追讨史源上所用的工夫及眼光。
实际上,岑仲勉在此文开头谈及“昆仑”系后出转变之译音时,已在“注释”中指出:“昆仑二字,虽见《南州异物志》及竺枝《扶南记》,然不过左右大臣及国王之名号,非国称也。据余所见,以昆仑为南洋国族之称者,实始于林邑记(《水经注》卷三十六)之‘昆仑单舸’。”(26) 其言下之意,即如果仅仅从“昆仑”这一专有名称的使用来考察,其实较容易找到问题答案,刘宋时佚名(托名东方朔)所撰《林邑记》早有记载。然而若想要详细考订其实际方位、作为国族之称得名原始,则史料表层之“史实”实不能满足要求。质言之,考察史地之名,如果仅仅凭据一二材料上偶合之记载,而不深入问题作详细的史源追讨,所得只能是一种表面之史实。这一点,对于今天日益发达的电子古籍检索手段而言,显然具有其现实针对性。
二、从追考“史源”到文献考据
以上二例中的学术思路,在《圣心》所刊诸文中比比皆是,可见岑仲勉早年史地考订中所培养成的“史源学”眼光。然而岑仲勉的研究又并不局限于此,而是在此基础上,更将学术目光拓展到“史源”追考所涉及的文献之考订上。即在史地考订中,他逐渐发现不少史料虽广为学人所知,也多有使用,但这些史料本身往往问题多多,缺乏细致、详尽的整理考订,严重影响学术研究之拓展。因而在其早年史地研究追讨史源的过程中,他往往会“顺带”做些校勘、辑佚、辨伪之类的文献考据工作。尽管目的或许尚不在文献考据本身,然而其“顺带”作这些文献考据工作的同时,也就逐渐形成了一种将追讨史源与文献考据紧密联系的学术思路。
1933年《圣心》二期所刊《〈水经注〉卷一笺校》一文,堪称20世纪《水经注》研究史上一篇名文,曾深得陈垣、陈寅恪、胡适等赞誉(27)。岑仲勉在上世纪60年代回顾此文时曾提到,他之所以致力于《水经注》卷一之笺校,起因在明人周婴《卮林》批评《水经注》“蹑法显之行踪,想恒流之洄洑”,“我为求指出其误会所起,才作《〈水经注〉卷一笺校》,同时因郦注此卷引用《佛游天竺记》文很多,且有不少异同,故就此等异同地方,顺带作校勘记多条,并非试图校勘郦注”(28)。然而从文章实际来看,其所作又似并不完全合乎其“顺带”的初衷。譬如文章对《水经注》卷一“释氏《西域志》曰:恒曲中次东有僧伽扇柰揭城”一句的校释,先指出“僧伽扇”(SamKasya)即《法显传》“僧伽施”之异译,然后考订曰:
明周婴《卮林》谓郦氏蹑法显之行踪,想恒流之洄洑,水陆未辨,道里难明,历举多事,俱与传大致相违,所言颇中其失矣。然周氏徒指郦注之误,未抉其致误之因也。……考注于拘夷那竭国之前……盖道元未履异域,惟采旧闻,安、显二书,一炉而冶,无怪乎东西互易,间有差违矣。若以今图诊之,则……此本注所引法显行经各国之方望大较也(29)。
此处“若以今图诊之”之后,有一段较长的具体考订文字。从这一大段地理考订可见,虽然岑氏说目的不在校勘郦注,而只为纠正郦注因“未履异域,徒采旧闻”导致的诸多讹误,但就其“顺带”所作的这些工作来看,实即按“他校法”,以《法显传》及后世舆图来校订郦注。文章中此类例子不一而足,适可见其文献校订的学术“趣味”与考据工夫。
其实,岑文文首小序已明言其当日实际思路所在:
原夫道元之书,朱郁仪首启蓝缕,合全、赵、戴为明清四大家,后儒踵起,三百年来涤污荡秽,宜若廓霾雾而见青天矣。然试一展卷,则焉鸟亥豕,独有承伪,即许脉水功深,犹是考古力弱(此两句翻套杨氏语),因综平日手记较多之卷一,排比为数十条,书而出之,井蛙之见,敢云驾轶前人,正谓整理古籍,需功尚巨,读书者慎毋曰珠玉当前,遂退藏自馁耳(30)。
所谓“试一展卷,则焉鸟亥豕,独有承伪”云云,完全是一种文献校勘之眼光,故而紧接之后才会提到“正谓整理古籍,需功尚巨,读书者慎毋曰珠玉当前,遂退藏自馁耳”。可见,固然岑仲勉本意在郦注所涉史地之考订,然而潜意识中似乎又自然而然的关注到对文献予以考据异同。而这一治学“习惯”,在同时期完成的不少文章中都有同样体现,1934年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成名作《〈佛游天竺记(31)〉考释》一书,表现得尤为明显。
岑仲勉原已撰有《法显西行年谱》及《法显西行年谱订补》各一篇(后者刊《圣心》二期)。《考释·序》称原二文对其书所涉“今地之考证,仍弗备也”,故“去岁获毗氏翻本,亟取可采者录之,再于法显历程,通盘剖析,无意中乃发觉向来中外考据家一大错误”。这一错误,即后来学者过于轻信清代官修之《西域图志》,而此书实存在“计里未周,指方或昧,不克按图索骥”等诸多问题(32)。所以,为纠正《西域图志》以来后人对西域史地认识中的讹误,岑书不仅就《佛游天竺记》一书中有关地名的“今地”予以详考,更就全书内容予以周密笺注,以求为后人了解“显师辛苦跋涉之游踪”(33) 提供一全面可靠的史料。可见,如果说《水经注》卷一之笺校仍属一种“顺带”的工作,则《考释》一书已显然是有意而为的专书文献考据。
再如岑仲勉1935年9月所发表之《〈括地志(34) 序略〉新诠》(刊1935年中山大学《史学专刊》1卷1期)一文。从文末所述“稿成阅岁”,可知此文大约写成于1934年。其出发点本为纠孙星衍辑本之偏——“不疑遗文之残错,即信《旧书》为疏略”以致“两者冤同不白”。然而岑仲勉以《序略》残文与《旧唐书·地理志》所载之地理沿革相参证,“择其各州之志无专条者,名有更易者,易生疑问者,谅系舛讹者,一一条解”(35),则显然正是以《旧志》来雠校《序略》。在该文中,岑仲勉更明确指出:
读古书而不得厥解,疑之诚是也,顾吾人未致其疑,先须求其所可是,求之不得,方伸我见,庶不至妄抵前人。盖旧籍中常有似误而未必定误者……尝见夫有清学者,好征斯志,大有非唐以前书不读之概,然征之者多,治之者少,学术所以不振也。辑本虽寥寥数卷,订批正缪,要非易事;人有良田,草莱不治,人有金沙,泥砾弗除,则亦何贵乎良田金沙者;整理之责,诚有望于爱读是书者矣。稿成阅岁,旅中多暇,爰写而存之。一九三五年秋九月,顺德岑仲勉。(旅中未得取各本《初学记》互勘,所校《旧唐志》,又未克与甘泉宗贤刻本封照,俟他日再为之。)(36)
由文中所述来看,岑氏对其时学界之疑古风气显然并不认同。他强调对古籍本身应予深入考辨,而不可轻易断为伪造了之;同时认为,对古籍的利用不能不辨良莠随便征引,而应充分注意对史料本身作详细整理,且认为史料整理不够,适成学术发展进步之瓶颈。清儒曾指出,治书之学非仅人受益,并书亦受益——亦即通过整理考订来开拓文献史料的实际应用价值。岑仲勉此处所述,正是这一思路的流衍。所说“整理之责,诚有望于爱读是书者矣”一语,已隐然透出其此后以整理古书为重要为学内容——亦即为现代学术之进步而致力于学术资料之考订整理——的学术思路。正出于这一强调对文献予以“整理”的精神,其由追讨史源到侧意于文献考据的学术研究进路,最终得以形成。
注释:
① 蔡鸿生《康乐园“二老”》,《学境》,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21。
② 如周勋初教授在上世纪90年代谈及唐代文学研究现状和前景时曾指出:“我国本有文史不分的传统。陈寅恪、岑仲勉等前辈学者更把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陈寅恪采用以诗证史的方法,在研究元白诗等问题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岑仲勉在唐代史和唐代文学作品的文献整理方面作出了贡献,他对《元和姓纂》等史料典籍的整理,大量运用碑志等材料,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周勋初《中国大陆唐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1995),林徐典编《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文学语言卷)》(上),中华书局,1995年,页164。荣新江研究员在为中华书局2004年新版“岑仲勉著作集”所撰书评中也提到:“陈寅恪和岑仲勉两位先生是无可置疑的‘中古史两位大师’,对隋唐史贡献尤多。两位大师的性格不同,治学方法和取向也不一样。陈寅恪先生为后人理解隋唐史,提出了许多今人尚无法逾越的解释框架;岑仲勉先生则为后人研究隋唐史,整理了几乎所有相关的隋唐史资料,同时也开启了隋唐文献研究的许多领域。”荣新江:《〈岑仲勉著作集〉书评》(2004),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584。
③ 有关岑氏生平,参见姜伯勤《岑仲勉》,陈清泉、苏双碧主等编《中国史学家评传》下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页1299—1325;姜伯勤《岑仲勉先生学记》,向群、万毅编《岑仲勉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1-6;陈达超《岑仲勉先生传略》,《岑仲勉史学论文集》,中华书局,1990年,页1-10;邢玉林《潜精治史著作等身的大家岑仲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4期;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岑仲勉》第四册,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页133—136。
④ 陈达超整理《岑仲勉先生著述要目》,见岑仲勉《隋唐史》(二十世纪史学名著)“附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页670-689。
⑤ 《麴氏高昌补记》、《黎轩语原商榷》、《义静法师年谱》、《法显西行年谱订补》、《再说大食七属国》等5篇,未见于中华书局版“岑仲勉著作集”(共15种17册)。
⑥ 以上八类名称系撮述岑仲勉先生所言而成。笔者按其所述略作分类,或未尽准确。详见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前言》,中华书局,2004年,页1-7。
⑦ 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前言》,页7。
⑧ [唐]刘知几《史通》,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页87。
⑨ [宋]郑樵著、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总序”,中华书局,2000年,页8。
⑩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中华书局,1986年,页3。
(11) 《通志·总序》曰:“自班固以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总序”,页3。《文献通考·自序》亦提到:然则考制度,审宪章,博闻而强识之,固通儒事也。《诗》、《书》、《春秋》之后,惟太史公号称良史……然自班孟坚而后,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马端临《文献通考》,页3。
(12)岑仲勉《〈杜佑年谱〉补正》(1948)回忆道:“先君留心经世之学,旧政书如《三通》等,皆丹黄并下。小子志学之岁,文义稍通,窃尝摩挲手泽而未有得也。”《岑仲勉史学论文集》,中华书局,1990年,页306。复旦大学傅杰教授曾提示笔者,既然岑氏自言“未有得”,则所谓其深受“三通”影响是否还能如本文此处所言是“一定”的。笔者揣摩岑氏此处所说,有推重其尊人学术之意,加之系回忆少年时之问学状况,故用语歉抑。从其此后很多著述来看,岑氏对“三通”是非常重视的,也是深受其影响的。
(13) [唐]刘知几《史通》,页34、36。
(14) 参见李瑚《励耘书屋受业偶记》,陈智超编《励耘书屋问学记》(增订版),三联书店,2006年,页221。
(15) 此一问题,笔者另有《〈元和姓纂〉校雠与岑仲勉的唐诗文献考据》一文予以讨论,此处不赘述。
(16)《唐代大食七属国考证》,《中外史地考证》(上),页324。
(17) 岑仲勉对唐高宗时许敬宗等奉敕纂修《西域图志》另有考述,详见《中外史地考证·西域记》(上),页297-298。
(18) 据《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开元五年”(717)条载:安西副大都护汤嘉惠奏突骑施引大食、吐蕃,谋取四镇,围钵换及大石城,已发三姓葛逻禄兵与阿史那献击之。
(19) 《唐代大食七属国考证》,《中外史地考证》(上),页324-325。
(20)《唐代大食七属国考证》,《中外史地考证》(上),页327。
(21) 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订·前言》(上),页3。
(22) 参见胡戟、张弓、李斌城、葛承雍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与南海诸国的关系”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页285。
(23) 《南海昆仑与昆仑山之最初译名及其附近诸国》,《中外史地考证》(上),页115、133-134。
(24)笔者案:据《晋书》卷九七《四夷列传·南蛮传》,《南齐书》卷五八《东南夷列传》,《梁书》卷五四《诸夷列传》,可知扶南王范蔓为三国吴时人。
(25)《南海昆仑与昆仑山之最初译名及其附近诸国》,《中外史地考证》(上),页116-117、133。
(26) 《南海昆仑与昆仑山之最初译名及其附近诸国》,《中外史地考证》(上),页149。
(27) 1933年12月初,载有长文《〈水经注〉卷一笺校》的《圣心》二期出版后,岑仲勉即将杂志邮寄给陈垣。陈垣不仅于12月20日致函岑仲勉,对其奖誉有加,且赠送其佐成论证的有关研究资料,更将杂志分致陈寅恪、胡适等学者,均获赞誉。岑仲勉1934年1月22日回函陈垣称:“奉十二月二十日惠书,夹陈君寅恪手缄,奖誉备至,惭汗交并。……惠于文襄手迹乙册,已拜领并谢。内有涉《水经注》者二条,似足证实东原之攘窃公案也。”陈智超编《陈垣往来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页568。姜伯勤《岑仲勉先生学记》也提到:“陈垣先生奖誉仲勉先生的信今已不见。但当年读过这些信的圣心中学同事马国维先生,后来曾在香港出版物中回忆道:陈垣先生‘遂亲笔致书于岑,其大意则云:寄来圣心校刊……得见尊著……考证明确而精审,珠江流域有此出类拔萃之学人,真可为吾乡扬眉吐气。’”向群、万毅编《岑仲勉文集》,页2。另胡适1944年2月13日复王重民函也提到:“岑仲勉的《〈水经注〉卷一笺校》,当然远胜一切旧校。其附录五件,尤为有用。但其中亦有未尽满人意处。他对戴氏先存成见,故往往作过甚之贬辞……岑校本误信‘全校本’为真,与杨守敬同。”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156。
(28) 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前言》(上),页5。
(29) 岑仲勉《〈水经注〉卷一笺校》,《中外史地考证》(上),页229-230。
(30) 岑仲勉《〈水经注〉卷一笺校》,《中外史地考证》(上),页209。
(31) 《佛游天竺记》,一称《历游天竺记传》,《佛国记》,《高僧法显传》,抑或简称《法显传》。系东晋释法显(约337—约422)记述其西行求法十四年间所见所闻而成,广泛涉及西土地理物候、民风人情、文化历史,为我国现存最早有关南亚及南洋地区的确切记录,是历来研究西土地理和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史料。清人丁谦曾作《佛国记地理考证》,日本足立喜六作《法显传考证》,贺昌群也撰有《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等书。详见关枫总主编,王兆明、傅朗云主编《中华古文献大辞典·地理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页172-173。
(32) 清代乾隆年间由军机大臣傅恒主持纂修的《西域图志》,虽采辑前人不少实测资料而成,但却较少关注到地理因素的准确度。郭丽萍在《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一书中指出:“书中《西域全图》等地图,既无经纬坐标,也不讲比例尺,更不像《内府舆图》采取经纬相交的标识法,图中的山川城池只是被置于大约的相对位置上。这样的舆图也只是个示意图。”三联书店,2007年,页31—32。
(33) 岑仲勉《〈佛游天竺记〉考释》,《中外史地考证》(下),页741-742。
(34) 《括地志》,又名《魏王泰坤元录》、《贞观地记》、《贞观地志》、《魏王地记》、《括地象》等,系一部唐及唐以前的地理总志。唐魏王李泰主修,萧德言等撰,正文550卷,序略5卷。始纂于贞观十二年(638),十五年(一说十六年)成书。《序略》部分,概述历代政区地理,本于《贞双十三年大簿》所规定都督府区划和州县建置,博采经传地志、故老旧闻,于正文详载各政区建置沿革,兼记山川河渠、风俗物产、人物古迹等故实,对《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诸书编纂有较大影响。原书于南宋后散佚,清人先后有九种辑本,而以孙星衍《括地志辑本》八卷较为通行,收入《岱南阁丛书》、《正觉楼丛书》、《槐庐丛书》。今人贺次君在孙氏辑本基础上撰成《括地志辑校》,中华书局,1980年。见关枫总主编,王兆明、傅朗云主编《中华古文献大辞典·地理卷》,页248。
(35) 岑仲勉《〈括地志序略〉新诠》,《岑仲勉史学论文集》,页519、521。
(36) 岑仲勉《〈括地志序略〉新诠》,《岑仲勉史学论文集》,页5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