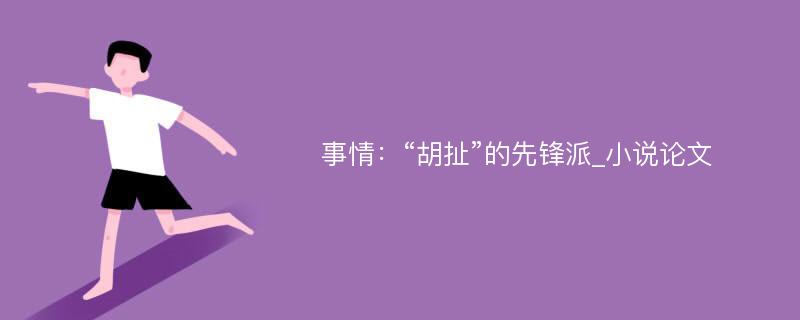
东西:“东扯西拉”的先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扯西拉论文,先锋论文,东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必须承认,阅读东西的小说,足以构成对批评家审美判断力和智慧文化的考验。这一事实本身,就充分证明了东西的地位和意义。东西是十足的先锋作家,他同苏童、余华、格非、北村、孙甘露、吴滨等一样,也有呈示其独具的先锋之刃的巧智和巧技。
按照一种古老的设问:东西是现实主义作家吗?回答是肯定的。但是,如果有人反问:你不是说他很先锋吗?回答也同样是肯定的。这样,似乎就出现了矛盾,尽管现实主义并非完全与先锋无涉。实际上,东西就是矛盾的统一体。东西不仅是现实主义同现代主义的矛盾体,还是现代主义同后现代主义的矛盾体。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拆解,构成了这种矛盾性,甚至这是一个青年写作人群体的集体特性。但正是“东扯西拉”构成了东西的先锋性。福柯在论述新历史主义问题时,提出discursiveqraeictis,即“东扯西拉”或“推论”的实践,研究者用“东扯西拉”这一译词来描述其特点,东西用小说证明自己擅长对三大主义进行“东扯西拉”或“推论”的实践。
在我所知道的东西已发表的包括《没有语言的生活》、《慢慢成长》、《迈出时间的门槛》、《商品》、《抒情时代》、《睡觉》、《溺》等在内的十多个中篇小说、十多个短篇小说以及十多篇散文中,除个别散文外,其余全部发表在90年代。所以华艺出版社把东西的中篇小说集归入晚生代作家丛书,海天出版社新出版的新生代作家丛书中有他的中短篇小说集《抒情时代》,或许是理由充分的。当然,东西一定是80年代就加入写作之旅的。这样的写作年期提示我们:当时的先锋派或反传统的文学流派,已经为人们所普遍接受,为社会所容忍,所承认,或为流行的审美趣味所包容,虽然它自身已经“涅槃”了,在这个时刻,它已丧失了它的独立性和批判性,已经开始为社会所吞并或消化,并开始成为传统和现有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这可以部分地覆盖或遮蔽我们的阅读感受:何以东西小说总体上并没有太强的社会批判力量和太大的艺术创造原动力。本文开头关于三种主义的那种笼统的概括还包涵着另一意思:叙述文体中同时存在着写实和虚构两种倾向。由此出发,我们能够找到何以东西的小说可读性强的原因。现代小说的叙述文体可以视为两种对立的叙述类型的有机统一,即以趋于真实的叙述取代趋于神话的叙述的经验同以趋于理想的叙述取代趋于神话的叙述的虚构型二者的合一。由于创作年期外部社会文化大气候的影响和作家本人的偏爱和选择,东西的小说总体上看,显然是经验型倾向大于虚构型倾向,经验型倾向中,表现出历史型压倒摹仿型的倾向;在虚构型倾向中,表现出浪漫型压倒训诲型的倾向。
作为经验型强势小说,东西的作品所具备的生活印象整合性是在其他先锋小说那里不多见的。它们不属于以意识流和时空跨越等见长的心理现实主义,但同心理现实主义依然有所关联。亨利·詹姆斯在《小说的艺术》一书中说:“小说之所以存在,其唯一理由就是它致力于再现生活,”而他又认为:“现实是很难用固定的标准衡量的。”“一部小说,就其最宽泛的定义而言,乃是作者个人对于生活的直接印象。”东西的小说中充满现实性,但它是以客观存在的载体的生活印象,或者说是生活印象所产生的小说现实。这种生活印象或生活经验,由东西的秉赋构成,它们包括从已知猜出未知,追寻事物的启示,以及按既定的范式,即完全按感受生活那样对事物的整体作出判断,因而东西的小说能给人以现实感,让读者产生来自作者的具体陈述的可靠性。这样看来,东西的小说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记录生活,而是创造生活;他的小说中的现实不是实而是一种建构。作家的小说艺术观基本上属于展示式,而非报道式。东西似乎走着同多数先锋作家很不相同的先锋之路。在东西的小说中,很难见到意识流、时空跨越等,甚至连心理独白都不常用。但是,他显然更加远离那种曲解“典型性”的书写,那种把作品人物只看作是社会势力的化身,把“典型人物”看作是阶级的象征,而活生生的历史被撇在一边,独特的历史精神也无影无踪的书写方式。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典型性,比如《慢慢成长》中的小硬汉马雄,也只能被看作是具备那个历史时刻本身的典型性。马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但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那种显得十分渺小的、可悲的、无可奈何的,或处于被动的地位的“反英雄”,虽然他也不无渺小的、可悲的、可笑的、无奈的、被动的处境或性格、心理。他似乎生活在被剥夺了可靠感、价值观念甚或意义的环境之中。但他毕竟通过自己的“坚持”或坚忍、不屈不挠的英雄或硬汉精神换回了特定时刻的尊严和社会的让步。这样的硬汉在当代文学史上并不多见。无论是追捕、求职、求爱,或是工作本身,他都处于最为卑下的位置,但以反英雄的处境赢得英雄的待遇,不能不令人反思精神的力量、内在的价值和“耐心”的意义。向即将驶入受灾路段的火车示警,堪称典型的英雄壮举;让灾民吃上肉的事迹,属于乡村办事员式狡智的产物,也使他成为传奇人物。但没有多久,就在苦日子快要熬到头的时候,他已经会到下面“拿钱”,“烟酒有人送”了,5个月搞了1万块,连根据诺言可以换来李寒姑娘的金属拐杖,也是交警大队报销。他还会倚仗县长虎威,胁迫不买帐的基层干部。真可谓“此时的马雄已不是彼时的马雄了。”这是一个集英雄、反英雄和蜕变英雄于一身的小硬汉。
在东西的小说中,有复杂的个人关系以及知觉的视角,有人际冲突、寻求自我,以及个人选择等问题,但不太重视个人与历史、主观愿望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内在联系。它们的现实是人对经验世界的一种主观体验。正因此,小说内部在叙述倾向上,从写实向虚构摆动的位移时有透露。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而非意识流等方法),我们可以把东西小说中的现实主义看成为形式现实主义。伊安·沃特在《小说的兴起》一书中说:“小说这种详尽地观照生活的叙述方法可以称之为形式现实主义;其所以是形式的,乃是因为现实主义这个术语在这里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文学教义或目的,它只不过是一套叙述程序而已,它们往往见诸于小说,而在其他文学体裁中则非常罕见,因此,它们可以被视为这一形式本身的典型特征。”东西在使用小说这一形式本身的所谓“现实主义”的典型特征方面,在利用“现实主义”的“叙述程序”方面,是相当得心应手的。这样的策略,显然在俘获读者方面,取得完全成功。这表明,东西对于中短篇小说形式方法的理解,是相当成熟的。这类小说占大部分,例如《一个不劳动的下午》、《睡觉》、《离开》、《雨天的粮食》、《美丽的窒息》、《没有语言的生活》、《慢慢成长》、《溺》等,虽然其中《雨天的粮食》范建国疯了的结局和小说的结尾,《睡觉》的静旗历尽劫难、苦苦找“我”的结尾,《一个不劳动的下午》队长和冬妹烧死的结果,属于“虚构”和“浪漫”,也是一种主观体验的外化。
“虚构”压倒“写实”的情形,在东西的小说中也有:《我们的父亲》、《商品》、《抒情时代》、《我们的感情》、《跟踪高动》等。但除《跟踪高动》外,上述小说就其虚构主体而言,还是一种写实化虚构或虚构的写实。东西没有像国内或国外某些作家那样采用摹仿通俗文体,强调人物的单面性、情节的扁平性,没有突出文本的捉摸不定,不可信赖,没有故意采用强调故事真实性的手法,设置一个主导叙述者,让这个叙述人突然消失,突然出面,还会自打耳光,承认刚才全是虚构杜撰,让读者不知所以。东西也很少采用剪贴、拼接等手法,以达到模糊性格、社会和政治的界限,除了《商品》等个别例外。东西之所以如此,是他没有像那些作家那样陷入认识论方面的危机。东西对于社会和世界有自觉地、深沉地揭示悲剧性和无意义的一面,但并未完全放逐灵魂,游走自我。东西看起来较为封闭和固守的小说艺术观念,其实依然保持了后现代的先锋性。他的写实化的或生活化的虚构接通了这样一种观念形态。当代文化思潮的转变,导致一项新的发现,即一切关于我们的经验的表述,一切关于“现实”的谈论,其本质都是虚构。换言之,生活等同于虚构。我们说他“接通”,而非“等同”。他是运用后现代的发现,运用虚构与生活的近似一致的关系,来同构一种被他观念化的生活。
小说文本的互文互参性,在东西也不例外。东西作品的文本,就像任何作品的文本,并非独立存在,并非独创的结果,而是从其他的文本中编织出来的。如鲁迅的《狂人日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语态和句式的来源往往是不自觉的:“今夜我从窗口看到天上挂着的一轮月亮,它像一盏灯照亮我的床前。我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我想姚昌凡失眠了,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是好消息为什么卫功达不让我看信?他为什么把信撕烂?其中必定有诈,卫功达再次欺骗了我。(《睡觉》)“狂人”印记一目了然。至于马尔克斯式的跨越时态、生死、往返现实与梦幻的段落章节,在《迈出时间的门槛》中俯拾皆是:
“我死后两年的秋日傍晚,母亲和姐夫一家人在堂屋吃晚饭。”
“我还在世的时候,母亲常带着儿子钻到小巷里捕捉飞动的虫子。”“这样,我能安静地面对稿纸和笔,思绪穿越茂盛和嘈杂,我看见我在深秋里溘然长逝,我没能挨到冬天,我没能看到那些蝶蛾似的飞雪扑落在我窗外的树上。”“我和所有的人一样最终被投进火炉。火化的日子,算得上亲朋好友的均已到场,但是母亲没有去,母亲不能接受一个事实:她生下来的一块肉体变成灰烬。母亲望着那只药碗发呆,那只药碗是我留给母亲的问候,药碗将伴随母亲度过暮年。”“我从生之地出发,穿越时间日夜兼程地往死之地行进。”(《迈出时间的门槛》)东西小说同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还有其他联系:(例如)叙述不动声色。《一个不劳动的下午》、《跟踪高动》、《没有语言的生活》、《溺》和《慢慢成长》等,几乎都是这样。因为作者已把绝望的爱情、死亡和悲哀,以及残缺的生活、非人性的存在都当作现实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作者为了不使被叙述者感到孤独,有意使自己通过冷静、不动声色的叙述,成为被叙述的一部分。语气平缓,如谈家常,削弱主观色彩和对读者的强加性影响。
在东西的小说中,可以看到通过对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双重的保留来表现对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双重的拆解。他基本保留了叙述的连续性,放弃了规范的人物表现方法,同时违反叙述语言的传统句法和一致性。从语言效果看,他的所有小说都是采用抒情和叙述兼并的书写方式,由此可以确认东西同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等人在语言方式上的一致性。艾略特对乔伊斯的《尤利西思》这样评论:“传统的文学作品那种假定一个相对有条理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布局方式不符合‘当代历史所呈现的总的绝望和无政府主义状态’。”如乔伊斯和庞德那样,艾略特在他的作品中试图用新的形式、新的文体来表现当今社会的混乱,并经常把这种混乱与那种失去了的、建立在过去文化历史的宗教和神话之上的秩序形成对照。在《荒原》中,艾略特用支离破碎的语言代替富有诗意的、规范流畅的语言,用零乱的层次结构代替传统的诗歌结构的连贯性,使得读者不得不去寻找或虚构各隔膜部分之间的联系。东西不属于这种典型的现代主义形式观念。他的语言之流是相当整饬的、舒缓的、流畅的、诗意的,文体也并不混乱破碎,反而相当有条理、相当稳定有序。这使得读者容易对东西的小说产生信赖感、安全感。即使读到最后,也不会因故事结局沉痛或人物下场的可悲而遭受过分的震撼、打击或如丧考妣的心理创痛。这倒是一种揉合了传统文学的规范性特征来冲击现代主义的写作行为,是以一种传统拆解另一种传统的写作策略。它达到了某种具有后现代主义意味的效果:以观念化的现实生存经验和生活印象,推翻我们业已接受了的思想方式及其经验的基础,以展示生存的无意义(《商品》)、非理性(《没有语言的生活》)、悲剧性(《慢慢成长》),以及那潜在的“深渊”(《睡觉》)、《迈出时间的门槛》)、或者“空洞”(《抒情时代》)或者“虚无”(《我们的感情》、《跟踪高动》)。
艾略特曾在他的《玄学派诗人》一文中引入“感觉分离”的短语。东西也“拥有一种能吞食任何经验的‘感觉作用过程’”,能表现出“一种对思想直接地、感官上地领悟”,“如同闻到玫瑰花香一样迅速地‘感觉’他们的思想”。对东西来说,一个思想就是一种经历,它增强了他的感觉力;反过来,一种经历也是一种思想,它增强了他的思想力。许多先锋作家可以归入这样的行列:要么想到什么,要么感觉什么。但东西是既想到什么,又感觉什么,二者达成一致的感觉行为,即小说。《商品》就是依照一种发展的现代化观点,把世界看作剥掉了人类价值观念和感情外衣的物质世界,在小说中,物质世界也可以是商品化的包裹在爱情之躯上的外衣;而爱情也可以被当作外衣,如同作家以爱情作为原料,以汉字作为工具来生产小说。自称二郎者以痴情的大郎的爱情故事打动或勾引了薇冬,就是一个以爱情作为外衣、工具、原料的例证。怀抱爱情结晶的薇冬,后来对爱情也产生了怀疑担忧,因为大郎二郎各自拥有不同的爱情,而薇冬是如何地理解爱情故事,也成为问题。始乱终弃的古老幽灵,在现代人的爱情树上徘徊。《睡觉》哲理化地证明:我们想象的安全感就是靠似乎既定的思想方式及其经验的基础来维持的,而这种维持本身就是不安全的,充满阴谋、侵犯和恐怖氛围的。“我的失眠是纯精神的;”睡眠中,什么都会发生,因而无法入眠;世界一片混乱;强盗在利用别人睡眠作案;而健康人被强行送到康复疗养院;那里强制“病人”“睡觉”,并且充斥着不能让人入眠的怪人怪事。“睡觉”是一个类同萨特等人所谓“恶心”的存在主义范畴,它绝对是东西本人的创造,这个创造在所有先锋作家那里都没有出现。有人曾利用小说提出“奔丧”的范畴,但如此日常化而又如此哲理化的“睡觉”;从社会批判到人文关怀到心理安全的范畴,实在是属于很高境界上的发现和表现。《离开》中的“离开”也有多重含义,无论是对于家乡、农村,还是家庭关系、姐妹情谊和歌星,以及百无聊赖的受到操持皮肉生涯的孪生姐保护的生活和租住的房屋,当然还有伦理道德和贞节状态,以及那只白哈巴狗。这正是城市化潮流或商业化浪潮中的相当普遍的“离开”:在离开中新旧交替。离开中的阵痛属于中国的农村乃至整个中国。如果就姐姐“有时她仿佛觉得妹妹就在自己的身边,就躲在自己身体的某个部位”,那么这种感觉也是土地或乡村对于自己的儿女的感觉。当然,还可以从“离开”的一般意义上理解,假如我们指出“离开”即一切都离开的物理变动状态或社会运动本质,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这个残酷的判断和严肃的事实。《我们的父亲》中,“我们的父亲”失踪,又据称摔死土葬,尸体却在移葬时再次失踪。有没有失踪,有没有入葬,都是问题。二度失踪的,也许一直在失踪之中的“我们的父亲”,在任何处所都无法存在。这当然已经不仅是一个“我的”如何对待“我们的父亲”的问题了。“我们”在结尾似乎被死了的“我们的父亲”的失踪惊呆、迷惑:“我们的双腿突然软下来,一个一个地坐在新翻的泥土上。四双眼睛盯住那个土坑,谁也不想说话。我们似乎都在想同一个问题,我们的父亲到哪里了呢?”至少,“我们的父亲”似乎是不断逃避“我们”(也许是被“我们”所驱赶),或许是以逃避的方式在对“我们”进行消极还是积极反抗?“我们的父亲”被一般化了,姐夫说了句实话:“不就死了一个人吗?在医生们的眼里,死岳父和死一个陌生人是一回事。”小说充满着陌生化的人物、情节和叙述。这也是以陌生化造成的“间离效果”和案例效应来发人深省。“我们的父亲”似乎也以失踪的经过构成了以存在的迷宫出现的“时间的迷宫”(在与不在,寻找与躲避,生与死等)。作者几乎不留痕迹地让我们看到了博尔赫斯式的对于现实与梦幻、世界与迷宫、文学与游戏、存在与虚无、亲情与陌生等形而上的思考与概括。他以写实代替梦幻,但依然使读者产生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若即若离、飘忽不定的象征性幻象。此外,情境的变异,对于一个人的命运意味着什么?《雨天的粮食》举了一个粮所所长范建国从英俊潇洒到发疯的例子。现实与梦幻合二为一的情形还出现在《我们的感情》之中。感情是游戏的结果,还是感觉的结果,还是脱离语言(语词)中心的结果,抑或反过来?尤其是所谓爱情。这都不甚了了。在迷途之中的游戏、挑逗,有时又是真实人性的表露,但依然会有恐惧地挣扎或欺骗麻痹性的反应。出了迷途但又入了歧途。现实与梦幻、梦幻与文学、文学与现实、语言与梦幻、语言与现实、爱情与无爱、情爱与性爱难分难解,只不过梦幻以性爱为中心事件,使得小说带有爱情、性爱思考的色彩。同时,也解构了梦幻中的、性爱中的、爱情中的语言中心或语言外壳。《溺》中的关思德要为儿子溺水身亡找到“凶手”来报仇。绝望使人悲哀愤怒,非理性地举起斧头,时间终于又葬送一切。“突然”与“必然”的岁月长河、非理性与理性构成的冲突终于被埋没。这个冲突从一开始就缺乏力度,因为关思德的所谓报仇是徒劳无成的。人的脆弱、荒唐和可怜于此可见一斑。队长为情欲所葬送,同时也毁灭了情欲的对象。这就是《一个不劳动的下午》。最初“烧火”的动机如何不可遏制地变成了可以乘乱“猎获冬妹的最好时机”,而终于在误作“英雄壮举”的灭火过程中丧生。人物有性爱、权力欲望,它能够催生催死,而生与死也相互转化。但是,一争都会化作:“看着满山遍岭的青草,社员们都说那个下午好玩。”一念之差,生死互换。偶然必然,难分难解。正是非理性的玩火者,证明了人的灭顶之灾会随时降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