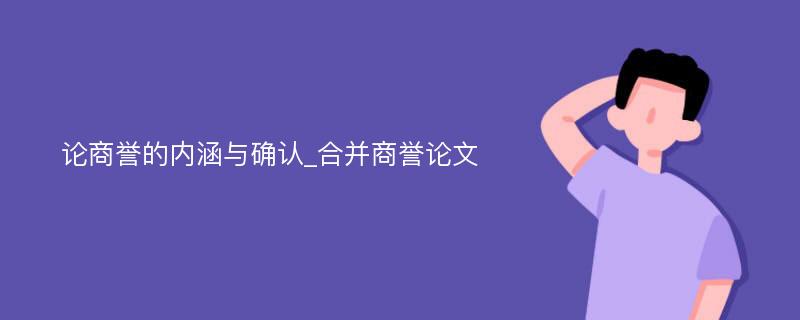
商誉的内涵及其确认问题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誉论文,内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商誉是什么?这是一个具有持续魅力的研究论题。对商誉内涵的争议,直接导致了商誉确认和计量方面的争议。因为,按照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层次,要素的定义先于要素的确认与计量,而非要素的确认和计量支配着要素的定义。若仅将商誉限定为狭义的“外购商誉”,那么商誉问题存在的争议在于:商誉是否摊销?按照什么方式和什么年限进行摊销?抑或不予摊销,而只是定期减值测试、计提减值准备。但若将商誉的范畴扩大,包括外购商誉与自创商誉,那么问题将进一步复杂化,譬如自创商誉是否、何时可以入账(确认和计量)?如何进行后续计量?可见,如何正确界定商誉的内涵问题,有赖于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范畴内,进行系统的规范研究、借以加深理解。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在对商誉的构成进行分解与重新界定的基础上探讨商誉的内涵,并进一步深入分析商誉的确认(包括初始确认与后续确认)问题。本文的贡献可能在于:第一,对商誉的组成进行了分解与经济学的分析,指出商誉仅应该包括“合并商誉”和被并购企业的自创商誉,借以确保商誉的“干净化”;第二,针对商誉的不同组成,本文认为应采纳不同的后续确认方法。
本文余下部分的篇章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本文尝试对商誉进行分解、透析商誉的合理组成部分;第三部分主要探讨商誉是否满足资产的定义,是否可以被初始确认、如何进行后续确认等;最后是本文的结论与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二、从商誉的分解透析商誉的构成
(一)目前商誉的计量模式
关于商誉的定义(内涵),存在如下典型观点(葛家澍、杜兴强,2007):(1)商誉是可以为企业带来超额盈利的一切有利的要素和情形;(2)商誉是预期未来超额盈利(能力)的贴现值;(3)商誉是企业总体价值与单个可辨认净资产价值的差额。其中,“商誉是可以为企业带来超额盈利的一切有利的要素和情形”这一定义,属于描述性的。“商誉是预期未来超额盈利(能力)的贴现值”的定义方式,属于直接定义商誉的方式,但由于涉及参数估计,所以直接计量却往往会给商誉的会计计量、甚至估价带来一系列的偏误和不可操作性。“商誉是企业总体价值与单个可辨认净资产价值的差额”这一定义方式,则和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层次性存在一定的不协调性——因为是商誉的定义决定商誉的计量,而非商誉的计量结果决定商誉的定义。尽管如此,“商誉是预期未来超额盈利(能力)的贴现值”和“商誉是企业总体价值与单个可辨认净资产价值的差额”这两种商誉的定义方式,还是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很大程度上的接受。要全盘摒弃,不太现实。为此,本文尝试融合上述两种商誉的定义方式,探讨商誉的相关问题。
根据“商誉是预期未来超额盈利(能力)的贴现值”和目前广为接受的“差额观”——“商誉是企业总体价值与单个可辨认净资产价值的差额”,本文形成如下的模型(1),来解释商誉的计量原理(假定购买企业通过并购拥有了被购买企业100%的净资产,下同):
PG=PP-(FVA-FVL)=PP-FVA+FVL(1)
其中,PG代表外购商誉(purchased goodwill);PP代表购买价格(purchased price);FVA代表资产的公允价值;FVL代表负债的公允价值。
(二)商誉的分解与内涵的界定
1.商誉的分解
模型(1)中,外购商誉PG,目前俨然已经成为了一个容纳各种原因导致的“计价差额”的“容器”。凡属于收购价格超过“购买企业在被购买企业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中拥有份额”的部分,一律被计量为“外购商誉”,而完全忽视了商誉的经济性质或商誉的内涵。实际上,作为价差部分,相当一部分根本就不是商誉,根本不可能给企业带来超额的盈利能力。为了更为清楚地说明模型(1)中外购商誉PG构成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探究商誉的内涵,本文对商誉进行分解,重新探讨商誉的合理组成部分。
(1)由于受到现行财务会计与报告模式的制约,相当一部分资产和负债可能由于无法满足严格的确认标准(即符合要素定义、可计量性、相关性与可靠性等四条标准),从而并未在财务报表中进行确认。那么,未确认资产的存在,意味着FVA被低估,从而导致最终计量的PG将被高估(参考模型(1)的计算)。同理,未确认负债的存在,使得FVL被低估,外购商誉PG将由此被低估。
换言之,一旦此前未确认的资产或负债得以在财务报表中进行确认,那么商誉的计量结果亦会相应发生较大的变化。
(2)外购商誉源自于并购。并购价格的确定,必然涉及估价,而估价过程必然需要对各种参数进行假设,这极有可能导致计价错误,甚至并购时机选择也有可能使估价陷入尴尬。下面一则例子迫使我们对并购过程中的估价与商誉的计量进行反思:
1989年8月8日,联合航空公司股票价格为$164.50,实施并购企业的CEO马文·戴维斯提出了每股$240、共计54亿美元的收购报价。9月1日,飞行员工会和联合航空公司的管理层则给出了每股$300、总计67.5亿美元的报价。10月13日开始,由于受美国股市下跌的影响,联合航空公司的股价由285美元跌到223美元,为此10月23日,工会与管理层报价也随之跌至每股225-240美元。但到了1990年3月20日,工会与管理层的报价进一步下调至41亿美元。不久,并购谈判终止了①。
从上面的例子中可以清晰看出,在前后持续大约8个月的谈判期间内,联合航空公司财务报表上可辨认的净资产的市场价格实际上变动很小,但股票价格却因整个证券市场的原因,波动很大,从而导致市值下降。联合航空公司的商誉在8个月的时间内却变化更大,从最高的67.5亿美元跌至41亿美元(问题是41亿美元实施并购的一方还无法接受)。商誉真的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吗(26.5亿美元)?商誉究竟是什么?超额盈利能力会受到股票价格的影响吗?毫无疑问,8个月的并购谈判过程中,商誉受到了谈判双方的主观因素、对未来的预期,以及估价偏差的影响。
(3)Jensen and Meckling(1976)指出,企业本质上是一系列契约的结合(a nexus for a set of contracting relationships)。更具体的,现代企业是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组成的特殊合约(周其仁,1996)。由于公司高管往往并不向企业投入100%的财务资本,所以代理问题普遍存在。在股权相对分散为主要特征的上市公司中②,公司高管以牺牲委托方的利益为代价来追求个人私利的行为屡见不鲜(Jensen and Meckling,1976)。问题是,在股权分散的情况下,众多小股东往往无法低成本地监督公司高管,那么高管的行为将失去控制、任意驰骋!须知,高管的自利行为不仅包括在职消费、更多的闲暇,甚至包括经理帝国的构筑——包括在雄性荷尔蒙(male hormone)③的刺激下,为了满足个人野心而进行的并购行为。
鉴于上述逻辑,公司高管往往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或雄心,对一些并不成熟的并购势在必得,因此在估价被购买企业的过程中往往出现过度乐观、自负的倾向,从而导致并购价格非理性的节节攀升。过度乐观、自负的并购行为导致的副产品就是并购过程中出现了巨额的、过度高估的“商誉”——有些公司的商誉因此高达并购对价的90%以上。但问题是,高估的商誉,相当一部分根本就不是商誉,无法给企业带来持续、超额的盈利,甚至导致企业在并购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为此“买单”——业绩持续的恶化。为此,本文认为,代理问题的存在,往往造成了商誉被高估。下面举例来进行阐述④:
2000年1月10日,世界最大的传媒集团之一—美国时代华纳公司和世界上最大的ISP公司—美国在线(AOL)公司对外宣称,两者将以换股的方式进行合并。时代华纳股东将以1∶1.5的比率兑换股票,美国在线股东将以1∶1的比率兑换股票。当时,美国在线的股票市值大约有1640亿美元,时代华纳公司的市值约为970亿美元。并购完成后,按照FASB的SFAS No.141《企业合并》准则的要求,合并成本为1470亿美元,但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商誉却高达1300亿美元!商誉居然占到合并成本的88.44%!
但是,超乎理性的并购行为很快受到了市场的惩罚!颇具讽刺意味的是,2002年根据SFAS No.142《商誉及其他无形资产》的规定,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选择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为此在2002年的第一季度和第四季度分别计提了542亿美元和447亿美元的商誉减值准备,减值金额合计989亿美元,几乎冲销了原合并商誉的76.08%,也导致2002年的亏损总额达到创纪录的986.96亿美元。
这里虽然不排除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利用商誉减值“洗大澡”(take a big bath)的嫌疑,但须知美国的GAAP规定,长期资产的减值不得转回!因此合理的推断是,最初合并过程中形成的商誉被严重高估!巨额商誉减值计提是对之前过度乐观行为的矫正(getting the behavior right)!
(4)“并购别人说明了并购方有实力、被别人并购则往往说明被并购方有价值”。某个企业被并购,往往说明该企业相对于别的企业具有异质性,或者其价值严重被低估。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被并购的企业可能往往已经存在一定超额盈利能力,但赚取超额盈利能力的潜力被严重低估。具体到商誉问题,被并购企业可能已经拥有了一定的自创商誉,只是由于受到会计准则或会计制度中关于确认标准的制约,往往无法在财务报表中对商誉进行确认、无法使之在财务报表上进行列报,甚至无法披露。并购行为与并购的完成,犹如“显像剂”,使这一“潜伏”在被并购企业内部的自创商誉得以“彰显”。
(5)本文上述列举的各种情况,无一不在揭示:外购商誉的计量存在偏差!外购商誉必须在剔除上述各项计价偏误后,才比较接近于商誉的本质。换言之,购买企业和被购买企业的资产进行整合之后(纵向一体化、横向联合抑或兼而有之),将产生协同效应(即AB>A+B)。
基于上述,参考Johnson and Pertrone(1998),本文定义合并商誉(combination goodwill)为:
CPG=PP-(FVA-FVL)-(NRA-NRL)-ERRORS-AGENCY-IG(2)
模型(2)中,CPG代表合并商誉;ERRORS代表估价错误;AGENCY代表高管出于过度自负和乐观因素,以及个人自利的目的,而导致收购价格的偏高部分;IG(inherent goodwill)是被购买企业自身通过经营而积累的自创商誉(假设被购买企业之前未购买第三方企业);NRA、NRL分别为未确认的资产、负债。
2.商誉的内涵界定
上文对商誉的构成进行了分解。下文将进一步探讨与并购行为相关的商誉,究竟包括什么内容?
借鉴Johnson and Pertrone(1998)的思路,本文将模型(2)稍作变形,那么最终应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加以确认的商誉(recognized goodwill,RG),包括合并商誉CPG和被购买企业因并购行为而逐渐“显性化”的自创商誉(IG):
RG=CPG+IG=PP-(FVA-FVL)-(NRA-NRL)-ERRORS-AGENCY
=PG-(NRA-NRL)-ERRORS-AGENCY(3)
乍一看,以上的思路好似要确认自创商誉。其实不然!商誉的形成、存在,必须满足财务会计确认的基本标准。其实,无论是FASB、IASB还是我国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无一不承认自创商誉的确能够为企业带来未来的经济利益,为此符合资产的定义。但符合资产定义是一个项目在财务报表中被确认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自创商誉尽管已然形成,但若未借助于并购行为等使之显性化、取得可验证的证据,那么暂时依然不能够予以确认。换言之,自创商誉要在该企业被其他企业收购或兼并时才会实现,从而才能予以确认。而RG(包括其组成部分CPG、IG)正是通过并购过程得以显现,并基本上满足了确认的标准。
最后,本文总结上述各个关于商誉的模型(1)-(3),得出“外购商誉PG、合并商誉CPG、被并购企业自创商誉IG及其他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的基本关系:
PG=RG+NRG=(CPG+IG)+[(NRA-NRL)+ERRORS+AGENCY](4)
RG=CPG+IG (5)
NRG=(NRA-NRL)+ERRORS+AGENCY (6)
从上述模型(4)、(5)、(6)可以看出,目前在企业财务报表上加以确认和报告的是外购商誉PG,其范围最为广泛;而上文分析的应确认的商誉RG,则仅包含合并商誉CPG与被并购企业因并购行为而得以显性化的自创商誉IG。外购商誉PG中除了应确认的商誉RG之外,部分NRG不能够确认为商誉的组成部分。下文将详细讨论。
三、商誉的确认
(一)初始确认
以下本文结合商誉的不同组成部分,来分析上文研究结果即RG为何应该被确认为一项资产。
1.符合资产要素的定义
要想确认为财务报表上的一项资产,首先必须满足资产的定义,包括能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为企业所拥有或控制以及源自于过去的交易或事项。未来经济利益的概念过于抽象,但普遍认为,只要能够独立或协同具有创造现金流的能力、可以用来进行交换或偿还债务,那么就认为一个项目往往具有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能力。
RG的确无法单独带来现金流、亦不能用来直接进行交换或清偿债务,但这只能够说明与RG有关的未来经济利益相对于一般的实物资产而言,辨认的难度更大,但并不意味着其不能够带来未来的经济利益。实际上,RG可以通过与其他资产结合的方式,为企业带来现金流,甚至是超预期的现金流。为此,RG具有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能力,因此符合资产的定义。
RG能否被企业拥有或控制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实际上RG被企业控制是一个或有状态。先来探讨RG的组成之一的CPG。对于并购形成的合并商誉(CPG),相对而言企业具有较强的控制性。因为并购作为产权交易的一种,相对而言具备法律或契约的约束力(但对并购中,由被并购企业创造的那部分自创商誉,可控制性的程度相对较低)。但是须知,具有控制权,并不意味着未来的超额盈利能力是确定的。IG是被并购企业内形成,但是由于并购行为的发生、而使之显性化的商誉。那么,IG能否为企业、特别是并购后整合的企业所控制?显然,IG被合并后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能力较差,从而使得IG相关的未来超额盈利能力具有不稳定性。即便如此,在一个整合良好的企业集团内部,可以很好地消除并购过程中产生的负面因素,再辅以良好的企业文化和公司治理,若股东、债权人、公司高管、各级管理人员和员工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监督和激励相容、剩余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匹配的机制(张维迎,1999;杜兴强,2002),就可认为IG创造未来超额盈利的能力相对稳定,且可以控制。
此外,RG往往是伴随着并购行为而产生的,并购作为一项资本交换的交易,符合“过去的交易或事项”这一要求。
2.商誉的可计量性
首先必须明确,难以计量并不等于无法计量。况且在剔除了估价偏差(ERRORS)、管理层过度自负导致的偏误(AGENCY)等因素后,RG的“干净”程度大大提高,至少具备了货币可计量性的要求,且有现实的交易作为基础。
3.相关性与可靠性
RG相关的信息披露,毋庸置疑是满足相关性标准的,因为RG比模型(1)的PG可以提供更加透明和增量的信息。但是否满足可靠性,则因为看问题的视角不一而存在差异。若过于强调、乃至指责RG计量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不可避免的主观性,显然就认为RG不满足可靠性的标准;但是,若以存在现实的交易作为判断可验证与否的标志,那么显然就会同意RG的计量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实际上,任何会计计量及信息披露的可靠性并非绝对的黑与白般的泾渭分明,而只存在可靠程度的差异。所以,我们认为基本上是满足相关性与可靠性标准的。
综合上述,本文认为RG满足资产确认的四条标准,理应在财务报表上确认为一项资产。
(二)商誉后续确认的层次性
上文指出,应在合并财务报表上确认的商誉(RG)应包括合并商誉(CPG)和被购买企业因并购行为而逐渐“显性化”的自创商誉(IG)。接下来的问题是,RG如何进行后续确认?
1.商誉后续确认的典型观点
商誉如何进行后续确认,长期以来主要存在四种不同的典型观点:直接冲销法、系统摊销法、永久保留法和定期计提减值准备。直接冲销法不赞同在财务报表上单独反映商誉,主张将商誉与购买企业或合并报表中的资本公积等直接对冲。永久保留法强调外购商誉应单独确认为无形资产,且永久保留,除非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超额盈利能力不复存在。系统摊销法虽然建议将外购商誉单独确认为一项无形资产,但同时认为,商誉应该在一个合理的期限内予以摊销。
目前,国际会计准则与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均认为,商誉本质上属于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既然承认商誉的经济寿命不确定,那么无论永久保留、立即冲销还是定期摊销,均含有主观武断性。为此系统摊销商誉并不能反映经济实质,也不能提供有用的信息。因此,对商誉应至少每年进行一次减值测试,一旦发现商誉的可回收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就应计提减值准备。
2.商誉的后续确认:分层次的思路
目前准则规范下的商誉是PG,而非RG。那么,首先让我们审视一下按照会计准则确认的商誉PG(模型(1))和模型(3)确定的商誉RG之间的区别。
毋庸置疑,PG>RG。
照此,若按目前准则确认的PG(商誉),显然可能存在被过度高估的情况。高估的部分无法整体上体现资产的定义—未来的经济利益,也无法体现商誉的性质——未来的超额盈利。至少PG中存在特定的部分如ERROR和AGENCY,难以带来未来的经济利益,更何谈超额盈利?为此,本文认为,RG比PG更符合资产的定义与商誉的性质。
但是,理论因其前瞻性,往往和会计实务存在一定的差距(GAP)。由于目前在财务报表确认的外购商誉(PG),为此我们既应重新审视RG与PG之间的差异,进一步思考会计计量及与此相关的估价问题,同时对不同的商誉组成部分,采纳不同的是后续确认思路。
(1)对于RG,包括CPG和IG,因为并购行为的存在,已经获得了显性的、可验证的经验证据。其中,CPG是由于存在并购交易的明确证据,因此符合确认的条件而应该在财务报表的表内被确认;IG则同样是因为并购行为,而间接被证明存在性,至少并购双方认可!为此,对于CPG和IG,既然在财务报表上经过初始确认(属于再确认环节)作为一项商誉,那么其后续确认就应该按照逐年减值测试、计提减值准备。
(2)对于PG-RG的差额部分,包括未确认的资产与负债之差(NRA-NRL)、估价谝误(ERRORS)和公司高管代理问题产生的成本AGENCY等,则要区别对待:
①对于未确认的资产与负债之差(NRA-NRL),如果情况允许且可以计量,则力争不确认为商誉的一部分,而应该在财务报表的附注中进行披露;
②对于估价偏差(ERRORS)和代理问题产生的偏误(AGENCY),则不应该确认为商誉的一部分,应直接冲销资本公积。
3.商誉后续确认:定期计提减值准备抑或定期摊销
上述仅是从理论上阐述了为何商誉的不同组成部分应该按照不同的思路进行后续确认。但是,会计准则具有一定的经济后果(economic consequences),由此导致了关于商誉后续确认上的争议。譬如IASB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规定商誉应该进行减值测试,但是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中小企业部分却倾向于采取逐期摊销的思路。这一看似矛盾的思路,其实仅是“佯谬”(paradox),因为背后隐藏着利益集团围绕会计准则的游说(lobby for or against)和博弈。最初APB Opinions No.16规定企业可以从“权益联营法”、“购买法”两种方法中选择其一,引起了商誉后续确认的争议(指直接冲销、永久保留或逐期摊销);此后,由于跨国公司等利益集团的游说,加上众所周知的“安然”公司等一系列财务丑闻引起的“原则导向”与“规则导向”的争议,最终在SFAS No.141“企业合并”中,FASB将商誉的后续确认由“逐期摊销”改为“定期进行减值测试、计提减值准备”。尽管如此,学术界迄今仍未就商誉“定期减值测试”或“逐期摊销”的理论基础达成一致,且认为减值测试并不比逐期摊销理论上更合理。
由于FASB对商誉的后续计量由逐期摊销转向定期减值测试,考虑到FASB和IASB的趋同(convergence),出于战略方面的考虑,IASB对商誉的会计处理采纳了和FASB的SFAC No.141一致的规定。但是,IASB并非从根本上认同定期减值测试的方法,所以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中小企业部分,按照自己的研究结论与一贯主张,规定商誉可以逐期摊销。原因是中小企业并未像大企业那样游说支持减值测试,而且逐期摊销的技术相对减值测试较为简单,更适用于小企业,更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所以,本文认为商誉的后续确认,淋漓尽致地体现着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并凸显着除了技术性之外的、会计准则(会计信息)具有的经济后果性、公共选择性等性质。毫无疑问,商誉后续确认、计量的讨论,还将持续处于争议之中,并依赖于财务会计基本理论的发展来逐渐消除争议、获得共识。当然,商誉的后续计量,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是,会计准则具有经济后果性等其他特征。
四、结论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本文立足于既有文献关于商誉问题的论述,在对商誉的构成进行分解的基础上,对商誉的内涵及确认进行拓展性的分析。首先,本文对商誉进行了分解与重新组合,指出商誉的构成应更“干净化”,应该只包括“合并商誉”和被并购企业的自创商誉。前者的确认是因为存在客观的证据,而后者是因并购行为而得以显性化。进一步,本文详细探讨了商誉是否应该在财务报表上确认为一项资产、如何进行初始确认与后续确认等问题。
本文的研究对于理解商誉的内涵及其确认的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此外,本文的研究,可以促使有关监管与准则制定机构思考商誉的初始确认与后续确认问题,借以在时机成熟时对我国的会计准则进行必要的修订,提高会计准则的质量,确保会计信息披露的透明度。
但是,本文仍存在如下不足:(1)限于篇幅和逻辑架构,本文未结合《企业会计准则》颁布后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上列报的商誉项目与权益价值的相关性,探讨商誉相对于其他资产在权益计价方面具有的相对“超额”性。(2)本文虽然通过研究指出“商誉应该仅包括合并商誉和被购买企业通过并购行为得以显性化的自创商誉”,但是因为篇幅的限制,并未对相关的计量、估价问题进行细致的探讨。这将是本文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注释:
①引自Michael Davis.1992.Goodwill Accounting:Time for an Overhaul.Journal of Accountancy,6:75-83.
②当然LLSV揭示了全球范围内存在着股权集中度较高和大股东资金占用的问题。这与本文的讨论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本文讨论的是高管和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而LLSV讨论的则是大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
③有人戏谑到:“(外购)商誉”是上市公司高管雄性荷尔蒙作怪的产物。的确在一次次的合并、并购浪潮中,我们看到很多缺乏效率的并购,并购后的公司业绩并未出现期望的“协同效应”,反倒是出现了下滑。这使得本文重新思考外购商誉的经济性质是否可以被界定为“超额盈利能力”,抑或只是一个“合并价差”?(参考了Ferrini等,1998)
④转自:杜兴强、桑士俊,《中级财务会计》,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
标签:合并商誉论文; 商誉减值论文; 资产减值测试论文; 商誉论文; 企业合并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测试模型论文; 企业资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