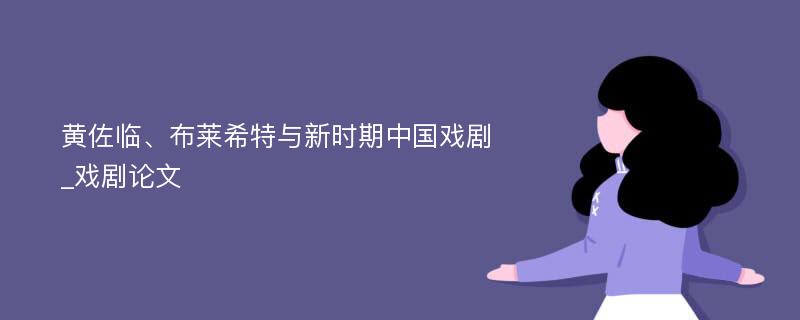
黄佐临、布莱希特与“新时期”中国戏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布莱论文,中国戏剧论文,黄佐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黄佐临先生是向中国“引进”布莱希特的第一人。我在这里说的“第一”,不仅是指时间之早——早在中国大陆仍然闭关锁国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而且是指影响之大——黄佐临先生创造了“戏剧观”一词,从戏剧发展的全局观念上解说了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可谓高屋建瓴;尤其是他通过《胆大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伽利略传》和《中国梦》三次重要的艺术实践,促进了人们对于布莱希特戏剧理论的理解,使布莱希特成为中国戏剧界一位无人不晓的西方人物。如果我们说,布莱希特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齐名,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最具影响的两位外国剧场艺术家,这是符合实际的。我们也许可以说:中国戏剧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选择,首先是接受了国际国内政治、文化大环境的引导,戏剧家个人在这种选择中的作用甚至并不是主要的,而中国戏剧对布莱希特的选择,却首先是接受了黄佐临先生的引导。如果没有黄佐临先生在中国戏剧界的声望,如果没有黄佐临先生作为一位剧场的实践家直觉性地把握了布莱希特繁杂理论的精髓和他的言简意赅的阐说,如果没有黄佐临先生对于布莱希特理论三次重要的剧场实验,仅凭翻译界和学术界对于布莱希特的介绍,这位欧洲戏剧家在中国如此崇高的声望也许至今还不能建立起来。
布莱希特对于中国当代戏剧是非常重要的。在“新时期”之初,国门微启,教条主义仍然盛行,甚至包括了荒诞派戏剧在内的众多西方戏剧现象、作家、作品、流派和理论都被我们看作腐朽的资本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的布莱希特就成了我们再次与西方戏剧建立联系、实现沟通的最初的桥梁。黄佐临先生是通过布莱希特的《中国戏剧艺术的陌生化效果》一文认识这位德国戏剧家的,布莱希特从他所陌生的中国戏曲中看到了熟知戏曲的中国人所没有看到的东西,他在全部西方戏剧实践和理论背景之下对于中国戏曲的解读,反过来激励中国的戏剧家在融合本土戏剧与外来戏剧方面,更加乐观而积极地进行探索。在黄佐临先生把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描述为三个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表演体系之前,我们对中西戏剧的对立性、不可渗透性是看得更绝对化一些的,对这两种不同戏剧的交融比现在也更少一点信心。最重要的,当然还是布莱希特的理论本身突然地大大拓展了我们的戏剧边界,大大丰富了我们的戏剧手法,大大改变了我们戏剧创作的面貌。“新时期”话剧创作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桑树坪纪事》,便是传统的戏剧性戏剧与布莱希特叙述体戏剧兼容、结合的佳作,而黄佐临先生的《中国梦》则另有尝试布莱希特与中国戏曲兼容、结合的意义。
南京大学的董健先生始终站在五四启蒙主义的立场上,坚持戏剧在中国的启蒙使命。中国戏曲学院的傅谨教授很不赞成董先生戏剧观中的启蒙主义,他认为董健先生的那个启蒙主义不就是政治实用主义。傅谨教授既有道理,也没有道理。因为一方面启蒙主义和政治实用主义有着质的差异,而另一方面在启蒙主义中就蕴藏着走向政治实用主义的危机。在中国话剧一百年历史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这个危机并不仅仅是一种可能,而是一个令人厌恶的事实。同样的情况是,在“布莱希特”中也蕴含着一种危机,“新时期”终结之后,这种危机业已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事实。
布莱希特自身含有一个矛盾。他孜孜以求的目的是戏剧对于社会的理性批判,是戏剧的教育作用,他被黄佐临先生抓住了的最具价值的戏剧思想“‘破除生活幻觉的效果’或即‘间离效果’”①(Verfremdung seffekte)不过是他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但是事实上,在他的目的和手段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破坏幻觉”的戏剧并不必然地比“制造幻觉”的戏剧具有更多的理性和更大的教育的功能。他对亚里士多德式的戏剧的批评,主要停留在“制造幻觉”这一点上,他认为幻觉激动了观众的情感,这是不好的,他要“激动”观众的理性。这个观点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根本就是缺乏根据的信口开河。所以,他自己的创作实践往往是他的理论的反证。他的最好的作品,例如《伽利略传》,恰恰是感人至深的作品。黄佐临先生注意到,“他总结《伽利略传》写作过程时讲:他发现这个戏在编剧技巧上是极大倒退。‘倒退’就是说不是按照布莱希特戏剧理论去编剧……”②非常有意思的是,黄佐临先生实践“布莱希特”的经历,和布莱希特本人的实践一样,也是他的理论的反证。黄佐临先生自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他的《胆大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一剧,是我导演八十八个戏中最大的失败,我归罪于‘间离效果’,把观众都间离到剧场外面去了。”③黄佐临先生在他第二次排演布莱希特戏剧的时候,吸取了教训,反反复复地强调:布莱希特“在表演上跟我们认识的表演距离不是那么大,甚至他早年的作品《母亲》尽管有些不成熟……观众看后,认为与斯坦尼的表演没有什么区别。到后期成熟了,在排练中也不大提间离效果了,区别越来越小”;“我们不用那些被歪曲了布莱希特的要求,而用我们习惯的表情方法,斯坦尼方法”;“斯、布没有区别”;“我们的原则是布、斯结合,现在看来,布的少了。这我们不怕”。④看得出来,黄佐临先生的追求就是要激动观众的情感,感动观众。他说:“其实布莱希特照样要感情,要感人。”⑤黄佐临先生的《伽利略传》获得了巨大成功,“两个小时内,半个月的票已经一抢而空……一千座位,场场爆满”。⑥黄佐临先生和布莱希特自己的剧场实践与布莱希特理论之间的矛盾,其实是不难解释的。任何戏剧,把教育作为最重要的目标总是要失败的;缺乏理性深度而感人的戏剧固然不好,但好戏却必须感人;所谓激动理性就是通过理性之路激动了情感,通过情感之路达到了理性的高度,理性与情感浑然一体,不可辨认;把“间离”作为阻断情感活动的手段,在剧场是注定要失败的。黄佐临先生在他更多地了解了布莱希特之后,介绍了波兰戏剧家格洛托夫斯基对布莱希特的看法:“他认为布莱希特不是个体系,而是个美学观点”,⑦他似乎赞同格洛托夫斯基的这一看法。他说:“我们在排《伽利略传》时,有人说‘这不是布莱希特’,恐怕就在于这些人不够了解布氏学说的性质,把尚是一种美学愿望当作是具体的演剧方法来理解了……布氏的学说只是提出了美学要求,而不是教人怎么做的方法。”⑧出席1988年“国际布莱希特学会第七届研讨会”后,黄佐临先生介绍了加拿大女教授Josette Feral的一个说法:“1979年布莱希特的多年同事班诺·卡逊(Benno Bessen)写道:‘我与布莱希特一起工作多年,从1949年起至1956年。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有一次听见布莱希特提起过间离效果。‘间离效果’这个理论是布莱希特在30年代提出的,但自从那时起从来没有再使用过它。’”⑨
布莱希特不仅在中国享有崇高的声望,他在全世界戏剧界的影响也是广泛的。这样一个理论上并不成熟,自身充满矛盾的戏剧革新家为什么能够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呢?一种学说在历史上的地位,往往并不是由这个学说自身完满的程度决定,而是由世界对这个学说需要的程度决定的。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文学艺术出现了转向内心,表现心灵真实的趋势:达利、毕加索的绘画不再描绘客观世界的真实细节,转而描绘人的心灵感受;小说也出现了内心独白的反省方法,出现了亨利·詹姆斯这样的主观叙述者;在戏剧中,易卜生对象征的使用、斯特林堡的梦幻剧、契诃夫使用表层对白指向藏在后面未说出的内在涵义真实、魏德金德求助于怪异漫画化人物和情景的强化现实主义则是这个趋势的最初表现。当情节和冲突作为戏剧主体的时候,戏剧的行动是可以根据生活细节的真实在舞台上模仿的,剧场的任务就是制造生活的幻觉,剧场的审美资源主要由情节的张力和人物可视可听的外部动作所展示的性格来提供。这个时候,亚里士多德可以说,“戏景”是最不重要的,即使不看表演,光听情节,也可以激起恐惧与怜悯,斯坦尼也可以要求演员消失于角色之中,使观众忘记表演,产生逼真的幻觉。但是,当戏剧描写淡化了外部冲突,走向心灵的时候,模仿生活细节的表演就不够用了;心灵是无法被遵守生活细节规则的表演所模仿的。恰恰在这个时候,布莱希特强调的剧场的叙事因素的彰显,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为了唤起理性,布莱希特要求阻断模仿,在剧场加入或加强叙述。这个叙述的因素不是别的,就是包括表演、布景、灯光、舞美、有时还有影像在内的全部剧场的因素。Theater和Drama是戏剧的两极。中国戏曲从一开始就是抒情诗,它的情节艺术从来没有发育得像欧洲戏剧那样成熟,但是适应于心灵表现的要求,它以表演为核心的剧场艺术(Theater)得到了完美的发展;欧洲戏剧的情节艺术(Drama)所要征服的剧场,主要是剧场的时空,或者说,是剧场时空相对于戏剧情节的极端有限性,从一开始它就把以表演为核心的剧场艺术(Theater)当作自己的奴仆,它的剧场艺术处于模仿情节的奴仆地位,随生随灭,始终不能形成积累。但是,欧洲戏剧内容心灵化的趋势迫切地要求剧场艺术从“模仿”走向“表现”,从Drama的笼罩之下走出来。实际上,不单是布莱希特,法国戏剧家安托南·阿尔托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所有呼唤剧场艺术的声音在这个时代都得到了热烈的掌声。恰如黄佐临先生所说:“内心世界不能装在‘口袋’里,他们必须外部化,所以我们同时又借用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效果’……”⑩“陌生化”不是别的,就是表演这从人物和情节中走出来,用公然地强调剧场艺术的方式“叙述”人物和情节,特别是“叙述”无法通过模仿生活的外部细节来表达的人的内心世界。
总之,“叙述体戏剧”也好,“间离效果”也好,布莱希特的意义,并不像他自觉追求的那样,在剧场以理性成功地取代了情感,从而提高了戏剧的教育作用。布莱希特的意义,是发现了在所谓“亚里士多德式的戏剧”中被长久压抑的剧场因素,唤起了它的觉醒。而剧场因素所以能够觉醒,并且这觉醒所以如此之重要,是因为它适应了戏剧内容心灵化的转向,为表现这个新的戏剧精神内容,拓展了戏剧的边界,打开了一间丰富的武库,提供了新方法、新原则、新手段。
但是,自“新时期”以来,中国戏剧界给予布莱希特极其崇高的地位,却并没有意识到布莱希特唤醒戏剧之剧场因素与现代主义戏剧心灵化内容的关系,甚至以为剧场艺术应该也能够充分地独立于戏剧文学,剧场艺术就是戏剧的全部。我们一遍遍地重复着彼得·布鲁克名言:“我们可以选取任何一个空间……一个人在别人的注视之下走过这个空间,这就足以构成一幕戏剧了”;(11)我们一遍遍地重复格洛托夫斯基的论证:“演员的个人表演技术是戏剧艺术的核心”,(12)但是我们却不去追问:是什么把非戏剧的表演上升为戏剧的表演呢?例如高行健先生,在追求纯粹的剧场艺术的戏剧的时候,甚至看不上创造了极高成就的西方荒诞派戏剧,他的理由就是它们“反戏剧的种种努力还是落进语言游戏的巢穴里去了,同戏剧艺术的关系较小,更多是文学上的事情”(13)。
“新时期”结束后,中国的主流戏剧在精神上日益走向启蒙主义的反面,深陷于庸俗的实用主义泥潭,猥琐不堪,而在其剧场艺术方面却日趋奢华精进,“一流的舞美,二流的表导演,三流甚至不入流的剧本”成为普遍的现象;艺术家民间制作的非主流戏剧也往往忽略文学性、精神性的追求,日趋沦为空洞的剧场匠艺的把玩。最近林兆华工作室上演的《建筑大师》也许多少反映了中国戏剧的这种精神面貌。易卜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受困扰的痛苦而疯狂的心灵,但是主创人员的心思似乎并不在表现这颗高傲、衰老、抑郁、沉思、狂躁、热烈、梦幻、冲动……的心灵上。该剧以林兆华、濮存昕、马艳丽这些著名艺术家和陶红这位明星相号召,在人们熟知的汉语译名上加了一个“大”字,在宣传上把易卜生的这出于写作时间并非最后,于艺术成就并非最高的作品称为“终极巨著”,在舞台上挖了一个深及一人的“坑”,搭了一个高及屋顶的梯,但是,硬是没有取出易卜生这枚坚果的果肉来。对《建筑师》这枚坚果来说,林兆华先生成了一只橡皮榔头。十多年来,我们记住了林兆华先生在舞台上建过水池、在水池上搭起亭子,记住了他让提线木偶与演员同台表演,记住了他用一把老式剃头椅子做国王的宝座、把电风扇降到距离地板不足一公尺的高度……但是我不记得他再造过一个像狗儿爷那样的灵魂。像启蒙主义在中国戏剧中的尴尬处境一样,“布莱希特”在中国也失去了创造的元气,一天天走向自己的反面。
当代中国戏剧为自己失魂落魄的病态辩解,经常使用两条理由,一条是近两百年来民族戏剧脱离文学成为玩物的“传统”,一条是近一百年来西方戏剧摆脱文学的呼声和实验。人类最常犯的错误之一,就是把自己地域的风尚当作人性普遍的特征,把自己时代的风尚当作人性永久的特征。西方戏剧两千多年来,中国戏剧八百多年来,真正值得我们肃然起敬的,是那些伟大戏剧家的对于人类的精神拷问,而不是匠艺的把玩。
我们纪念黄佐临先生的百年诞辰,不妨再回忆一下1978年《伽利略传》的演出吧:这部戏所描写的对真理的追求和这种追求所遭受的压制之间的冲突,对于处在思想解放运动前夜的中国产生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最近南京大学戏剧研究所为纪念易卜生逝世一百周年做了—个戏,《〈人民公敌〉事件》,重提易卜生、布莱希特和黄佐临先生追求真理的话题,一个在当代中国扮演斯多克芒的大学生,却遭遇到了一百年前斯多克芒在挪威遭遇的同样困境,他用易卜生写下的台词责问他的同学,也是责问观众:“让我们想一想,我们习惯于听谎话,说谎话有多长时间了?”傅谨教授在他的剧评中写道:“我们在舞台上有多久没有看到这样真实得让人无法喘息的戏剧了?”(14)即使将来有一天,已经不再有专制的力量逼迫人们说谎,布莱希特所描写的伽利略在伟大使命和个体生存之间所作的卑微抉择,这一抉择中所含的“人”的意义,它所表达的人类困境,仍然会震撼我们的心灵。黄佐临先生在为《伽利略传》首次在中国上演而作的两篇文章中,四次引用了“布莱希特为伽利略写的一句漂亮台词‘思考是人类最大的快乐’”,(15)他说:“德国民族的一大特征是思考,作为德国杰出的戏剧家布莱希特的作品具有和他民族同样的特点——思考。我们认为思考不能成为德国民族的专利……让我们通过《伽利略传》的演出,了解布莱希特的思考,享受思考的快乐吧!”(16)他还说:“戏剧,布莱希特认为是给人以娱乐的,而最高的娱乐莫过于思考。”(17)非常令人痛心的是,当今中国戏剧恰恰丢弃了思考的品质。撇开当代戏剧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不谈,中国戏剧自身放弃思考的理由,居然也是“布莱希特”!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注释:
①黄佐临:《德国戏剧艺术家布莱希特——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排演〈胆大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前的讲话》,《我与写意戏剧观》,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第167页。
②④⑤黄佐临:《在〈伽利略传〉排练厅的讲话》,《我与写意戏剧观》,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第201页,第175-195页,第200页。
③黄佐临:《回顾·借鉴·展望》,《我与写意戏剧观》,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第420页。
⑥(17)黄佐临:《伽利略在北京》,《我与写意戏剧观》,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第220页,第223页。
⑦黄佐临:《格洛托夫斯基的“穷干戏剧”》,《我与写意戏剧观》,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第515页。
⑧黄佐临:《人气·仙气·志气——关于话剧提高的发言》,《我与写意戏剧观》,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第487-488页。
⑨黄佐临:《国际布莱希特学会第七届研讨会的感受》,《我与写意戏剧观》,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第256页。
⑩黄佐临:《〈中国梦〉——东西文化交流之成果》,《我与写意戏剧观》,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第541页。
(11)彼得·布鲁克:《空的空间》,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12)格洛托夫斯基:《迈向质朴戏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13)高行健:《对一种现代戏剧的追求》,《对一种现代戏剧的追求》,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83页。
(14)傅谨:《中国为何没有易卜生?——由〈人民公敌事件〉想到的》,《北京日报》2006年9月12日。
(15)(16)黄佐临:《追求科学需要特殊的勇敢——为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首次在中国上演而作》,《我与写意戏剧观》,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第210页,第2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