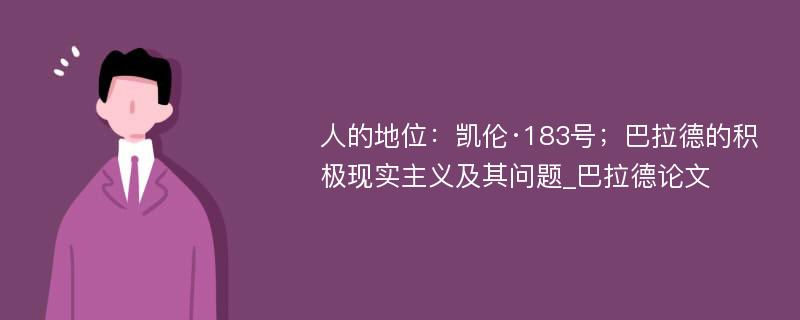
人的地位:凯伦#183;巴拉德的“主动实在论”及其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在论论文,巴拉论文,主动论文,地位论文,凯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2)04-0083-06
量子力学在20世纪初的出现,无疑对物理学以及整个人类认知图景带来了深刻的挑战与影响。它对于人类观察和实验行为的强调,引发了当今许多重要的哲学讨论。其中尤为关键的一个,就是对“人的主动性在描述实在的过程中具有何种地位”这个问题的讨论。正是在这一讨论中,凯伦·巴拉德(Karen Barad)提出了她的“主动实在论”(agential realism)。在本文中,笔者就将对这一理论的形成背景(量子力学的相应讨论)、内涵和存在的问题做出分析与讨论,借此对作为这一讨论主线的关于“人的地位”的问题,做出相应的评论与思考。
一 量子力学与观察行为
尼耳斯·玻尔(Niels Bohr)认为量子力学所引发的变革是在20世纪的第一年,“由普朗克关于普遍作用量子(universal quantum of action)的发现所肇始的。”①作用量子揭示了原子过程、同时也是我们整个自然描述中一种“本质性的非连续性(discontinuity)或称个体性(individuality),而这对传统理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②我们传统的自然图景以牛顿的连续时空观为基础,具体地:如果给定了作用于物体(粒子)的各种力,那么只要我们掌握它在任一瞬间的位置(position)和动量(momentum),也就掌握了它在整个时空中的连续轨迹。换句话说,它的整个过去和未来是被决定了的。③整个传统的图景也正是以因果性和连续性,以及决定论和机械论观念为特征的。
量子理论的变革首先在于,揭示出自然的描述奠定于由作用量子及普朗克常量(h)所规定的一系列不连续(离散)量的基础上。玻尔进而认为:“原子态的每一改变都应该看成一种不能描述得更加细致的个体过程;通过这种过程,原子将从一个所谓的定态(stationary states)进入另一个定态。”④定态概念旨在指出原子状态的改变并非连续性的渐变过程,而是“跳跃性的”。实验发现“只有当被传递的能量恰好等于由谱项算得的定态能量差时,从电子到原子的一次能量传递才有可能发生。”⑤在相邻的两个定态间并不存在一些中间状态,也没有一些累积性的渐变过程,它们之间是非此即彼的跳跃关系:要么满足了固定的能量而完成一次跃迁(表现出一些可观察的现象,例如光的辐射),要么维持原样什么也不发生。除此之外,不可能对跃迁的过程做出更加“根本的”描述与解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其的描述不可能像传统理论一样成为因果性和决定论的,而“只能应用几率考虑来预言个体过程的发生”。⑥同时,这些特征不仅局限在微观层面,而且存在于整个自然的描述中。传统理论因果决定论式的描述,其可行性乃是依赖于这一事实:“和我们在通常的现象中所涉及的作用量比较起来,作用量子是非常小的。”⑦所以,巴拉德认为“严格说来,牛顿力学是一个有缺陷的(flawed)理论”。⑧
传统图景的连续性和因果决定论特征,在很大程度上被另一个密切相关的假定所巩固。即人类的观察测量行为相对于描述对象的独立性。在对自然的描述中,人的地位是一个超然的旁观者,其观察行为是对描述对象做如实的反映,而不会干扰到对象的自在状态(即便干扰存在,也可以降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不会影响到对象过去和未来的连续“轨迹”。而量子理论则意味着,对微观对象以及整个自然观察测量的可能性,根本上来源于其态势的改变(无论这种改变是自发的还是由人所导致的),其中不存在一种基于传统连续性和因果性的“预测”。尤其在“不可见”的微观层面,我们通常是经由主动的观察行为和实验装置,来获得对对象的认识。构成观察可能性的那些现象,与作为观察对象的现象之间是不可分割的。与传统图景截然不同,此时“显然已不再可能在一个物理对象的自在存在,和它与其他作为测量工具的物体间不可避免的相互作用之间做出区别”。⑨对象的性质无法在人类对其观察行为和实验装置之外得到确定,“自在对象”的概念从而变得空洞。人的地位不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对象性质描述的一个主动的参与者甚至构建者。
二 “测不准”与“互补性”
量子理论对观察对象与人类观察行为之间相互作用的强调,在哥本哈根阐释中表现为著名的“测不准定律”,⑩由沃纳·海森堡于1927年提出。玻尔很赞赏海森堡的贡献,并将“测不准”所刻画的情形简要地描述为:“以在空间和时间中排比基本粒子为目的的任何测量,都要求我们放弃对于粒子和用来作为参照系的测量尺杆及时钟之间的能量交换及动量交换进行严格说明。同样,粒子能量和动量的任何测定,都要求我们放弃粒子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精确标示。”(11)“位置”和“动量”这对在传统理论中用于预测物体整个轨迹的量,此时在具体的测量手段和装置下,被表明是不可兼得的。
对此,巴拉德给出了一个形象的“思想实验”(gedanken experiment)来说明。假设我们在暗室中通过发射一个光子(photon)和一个粒子碰撞来测量其位置和动量。为此我们需要一个感光的胶片底板来记录碰撞后的光子的情况。为了准确记录其位置(借以确定那个粒子的位置),需要将底板固定,否则影像会模糊而位置信息也就丧失了,但是由于固定的底板吸收了光子的动量,所以动量信息就消失了。此时无法通过排除作为测量工具的光子的影响,而根据动量守恒定律计算出该粒子的动量,即使我们事先知道了光子的初始动量。因为这一计算还需要测量光子碰撞后的动量,而这显然需要一个可移动的而非固定的底板。为了获得动量信息,必须将底板安置在一个可移动的支架上来记录其移动的量,然而此时,正如我们所说的,其位置信息又被模糊掉了。(12)这个思想实验表明:我们唯有通过观察工具和对象之间不可避免的相互作用来描述对象,其中人的主动地位不容忽视。同时,为了测量位置和动量这两个性质,我们需要根本上相互排斥的不同观察装置。
值得重视的是,虽然“测不准定律”标志出了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阐释的关键点,然而对于它所刻画的情形,特别是其认识论意义,玻尔和海森堡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阐释。海森堡认为测不准性来源于实验干预所造成的影响,当我们试图,比如用一种γ射线显微镜,来测定电子的位置时,测定本身会造成光子从电子中散射,因而“在测定位置的瞬间(从而也是光子被电子散射的瞬间),该电子经历着一种不连续的动量改变。当所用光的波长越小时(从而对位置的测定越精确时),这种改变则越大。”(13)测量所难以避免的不连续的动量改变影响了我们同时对动量进行精确测定。巴拉德指出,海森堡的“这一分析建立在干扰(disturbance)概念的基础上,这个分析促使海森堡得出结论:测不准关系是一个认知原则,它表明了我们所能认识的东西的界限。换句话说,一个该电子动量的确定值,被设定为独立于测量而存在,只是我们无法知道它;因为测量的相互作用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干扰,我们对它的值仍然保持不确定(uncertain)。”(14)可见在海森堡的分析中,一个传统的独立于人类观察行为的“自在性质”观念仍旧保留了下来;一种试图将位置与动量概念整合进一个完整图景的直觉依然存在。
但对于玻尔而言,测不准性并不构成一种干扰或界限,相反正是解决传统认识论和实在论自身问题的契机——“尽管将这对概念整合到一个由事件的因果链条构成的单一图景中的企图,是经典力学的本质所在;然而,那些超出了这种描述理解范围的规律,却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才能得到把握,即对于互补性的现象的研究需要相互排斥的实验装置。”(15)与海森堡的“不确定性”解释不同,玻尔用“互补性”(complementarity)(16)概念来阐释测不准现象,并将其作为一种有别于传统的新的认识论的标识:不存在自在的对象和自在的“客观”性质,也不存在一种绝对排除人类观察行为的“整全”描述。人类对实在与客观性的描述本身就包含了人类实践的因素,不同的实践方式展现出不同的客观性方面。确定的实践方式与对象共同构成一种“现象”(phenomenon),而它正是客观性存在的条件。(17)
正是这一来自哥本哈根阐释内部的争论,特别是玻尔的互补性观点,最终促使哲学家巴拉德发展出了“主动实在论”。而在她立论的过程中,又包含了对玻尔没有彻底推进其观点的批判,这一批判构成了她主动实在论的特色,同时也暴露出了问题。本文将陆续讨论这些内容。
巴拉德认为“玻尔的哲学-物理学所构成的根本挑战,不仅针对牛顿物理学,同时也针对笛卡尔认识论,及其关于语词、认知者和事物三者的表象主义结构。”(18)关于表象主义,我们可以看一下笛卡尔方法论原则的第一条:“在我没有关于其如是存在的明证知识之前,绝不承认任何东西为真;也即,小心避免仓促和成见,只将那些清楚和明白地将自身呈现给我的心灵(presented itself to my mind)以至于我无法怀疑的东西,纳入我的判断。”(19)关键之处在于:将认知对象“呈现在心灵前”,而人作为认知者所处的地位,是一个超然的、与对象对立的旁观者和反映者。如海德格尔所说:“在表象中,我们把某物摆在我们面前,使得它作为如此这般被摆置的东西(即被设定的东西)与我们相对,作为对象而站立。”(20)采取这样一种观点的后果,首先就是认为认知对象的性质,是独立于人的认识而自在和先在(preexisting)地存在的,人的认知行为不会也不应影响这种存在,而更像是镜面似的反映。同时也正因为如此,对象乃至整个自然在根本上被认为是经由一种“上帝之目的眼光”(God's-eye view)(21)一览无余地呈现给人类;因而人的认识应当是全景式的,对对象的描述也必须是整全的。
玻尔的互补性观点则揭示出,人作为认知者的主动地位,以及认知行为与对象的互动作用(interaction),恰恰是知识和真理的必要条件。人与实在不是分离和对立的,而是在相互作用中共同构成种种“现象”,而这正是客观性的条件。这种观点构成了巴拉德“主动实在论”的基本(但不是全部)内涵:她将玻尔的“现象”作为实在展现的方式,认为“现象是互动中(intra-acting)的主动者(agencies)之间本体论上的不可分割/相互交缠(inseparability/entanglement)。”(22)这里她没有用通常的“interaction”,而是构造出“intra-action”一词,旨在强调这种互动不是事先存在的不同实体间的交往,相反一切事物恰恰是经由相互作用、相互构造的方式而得以存在和展现的。而这正是“实在”与客观性的意义所在。威廉·詹姆士的一段话可以作为目前这一观点的绝好诠释——“认知者的地位不像一面四处飘浮、无所驻依的镜子那么简单,他并不是针对他遇见并发现存在的秩序做出被动的反映。认知者一方面是真理的一个参与者和协同者,另一方面他也对自己帮助创造的真理予以认可。”(23)
三 主动实在论的“后人本主义”
然而,我们刚才所阐述的内容,在巴拉德看来仅仅构成了其主动实在论的部分内涵。人的主动地位及其对实在的协同作用,诚然是她的主动实在论所认可的,但在她看来这些并不构成其本质特征。具体地,她不赞同将“主动性”的地位仅仅归赋给人和人的实践。从而,她认为不应在世界的相互作用、相互构造的过程中,单单给人留出一个特定的(即便已经不是统治性的)地位。鉴于我们在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之后,根本上将人类实践理解成语言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认为人类实践可以不是言语的(linguistic),但本质上是语言的和处在意义空间中的;巴拉德进一步认为实在的客观性与意义本质上并不是由人类的语言实践所决定的。
她对主动实在论这一本质特征的阐发,是从对玻尔的批判开始的。她指出玻尔虽然在其“互补性”理论中给予了主动性和互动性充分的关注,但他的理解仍然以人和人的(科学)实践为立足点:“坚持只有那些在(实践的)实质安排中作为一个部分而具体地展现、并因此而得到定义的概念,才是有意义的;而那些实质安排则包括了标识出特定性质的值、并使其可以被一个人类观察者所识别的(实验)装置。”(24)玻尔将实在的意义定位于人类实践,特别是语言实践当中,并且将科学的实验安排作为其特定展现的观点,在她看来是一种犹豫和不彻底,因为他的“互补性”理论已经包含了更具革命性的信息,而他并未接受。无论是出于一个科学家的经验,还是一个哲学家和人本主义者的谨慎,巴拉德认为玻尔的这种保守是值得批判的。“关于主体以及体现在玻尔理论性的装置概念中的那种理所当然的静态和限定性的装置,所抱持的自由人本主义观念,阻碍了玻尔的努力,使他无法得出一种更深刻的关于科学实践本性的理解,最终也使他错失了自己观点深刻的本体论含义。”(25)因此,巴拉德认为她的主动实在论的根本特征,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对玻尔观点的一种挽救,将其革命性的信息从他的人本主义、从关于实在的“拟人论”(anthropomorphic)(26)观点中挽救出来。为此,她认为“所需要的是一种关于语言实践的后人本主义(posthumanist)理解”(27),而这正是她的主动实在论的本质形式。
语言学转向后的“人本主义者”,将实在理解为处于实践中,而将实践理解为人的语言实践。人的视角、语言以及概念框架,是实在和意义的展现过程中不应摆脱、也无法摆脱的条件。而巴拉德的“后人本主义”则批判这种观点将语言实践理解成了“以人为基础”(human-based)的实践,并且在“人”与“非人”(nonhuman)之间设立了一个界线。相比,她的“主动实在论关于语言实践的后人本主义阐释,并不在分析之前在人与非人之间设立界线,而是允许在一种关于人的物质-语言(material-discursive)呈现的谱系学分析的可能中考虑此界线。……人不是纯粹的原因或结果,而是世界的无限生成过程中的一部分。”(28)在此,主动不是人的主动,语言也不是人的语言,一切都来自“世界正在进行中的主动地互动”。最后,她给出了其主动实在论的关键表述:“语言实践是世界的特定物质(重)构造行为,通过它一切界线、性质和意义的确定性才被有区别地规定。”(29)
然而此时,巴拉德理论的问题也就出现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她对玻尔观点的“挽救”是否合理,更确切的是,她对于“人的地位”的理解是否合理。
四 意义问题与人的地位
我们看到,巴拉德的主动实在论,特别是她的“关键表述”,包含了很多新的信息。她从中表达了一种她称之为“后人本主义的语言实践阐释”,试图从对语言意义的规定过程中,根本地排除“人的地位”的影响。她不认为人有一个先定的地位,同时也不认为要给人保留任何一种哪怕已经不是启蒙主义意义上的地位。然而问题在于,没有了任何意义上的人的地位作为根本的观点,我们该如何去理解语言的意义呢?如何去理解一种不是人的主动的“主动”、不是人的语言的“语言”呢?特别地,对于她的这个关键表述:“语言实践是世界的特定物质(重)构造行为,通过它一切界线、性质和意义的确定性才被有区别地规定”,我们该如何理解其意义呢?
关于语言(语词)的意义,我们有三种基本的可能观点:(1)形而上学实在论(metaphysical realism)或柏拉图主义,认为“有一个被永恒确定的形式(Form)、共相或者‘性质’的整体,而一个语词的每一个可能的意义都对应于这些形式、共相或性质中的一个。”(30)也就是说,意义是由形而上学的实在而非人类实践决定的,并且是永恒的和在先的。(2)心灵主义(mentalism),认为语词的意义在于它作为符号所要表达的心灵观念,或者它所激起的内在经验和过程。也就是说,语词本质上是符号(symbol),而意义在心灵(头脑)中。(3)语用学(pragmatics)或“生活形式”意义上,认为“语词的意义在于它在语言中的使用”。(31)这种使用是处在人类实践中的,但并不意味着意义是由人所任意决定的;它必须经由规范,通过语词在生活实践中所占据的地位而得到确定。
在此,我们就要考察巴拉德的关键表述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具有意义。对于观点(1),首先它存在着自身的困难:那些被永恒和先在地确定的实在或“形式”,是以何种方式决定我们的现实实践呢?是如何让我们的语言有意义呢?这个困难可以表达为:“如果在我们用语言说的东西与那个实在的任何方面之间,不存在任何证明性的(justificatory)联系,那么任何语句都不能关于一个外在实在而成为真的或假的”,(32)也可以说就是无意义的。缺乏语义联系而使得我们语言的意义呈现方式沦为“神秘主义的”,显然这一困难,反对表象主义的巴拉德也是清楚的。同时主张世界的“进行中的主动地互动”的她,也不会承认有一种永恒固定的意义决定方式。而对于观点(2),它的另一个称呼也正是表象主义。当然,对于反对启蒙意义上的人本主义的巴拉德来说,心灵不是一面镜子,意义也不在人的头脑里,而语词即便是符号(能指)也绝非“标签”意义上的。因而这一观点也应排除。看来唯一可信的只能是观点(3)了,但问题是,虽然我们还不能确定巴拉德究竟认为意义来源于何处,也即此时所考察的这个句子的确切内容,但是我们知道她反对什么;她反对的不仅是启蒙意义上的人本主义,而且是任何意义上的以人类语言实践为基本观点的意义解释,而这恰是观点(3)的要点,所以它也被排除了。眼下我们似乎没有什么办法来理解巴拉德的关键表述了。
然而,即便如此,似乎也还有一种方式来解释巴拉德那个表述的“意义”,那就是将它作为一种“元语言”(meta-language),认为它是规定和解释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包括科学语言)如何具有意义的语言。它的“意义”不是“对象语言”(object language)层次上的意义,确切地说,不是“我们的语言”所说的意义,因而是“后人本主义的”。元语言在语义解释的层级(hierarchy)中处在对象语言的上端,因而我们之前对其意义的讨论因为混淆了层级而变得无效了。这一思路似乎解决了巴拉德所面临的问题,然而,我们即将看到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
即便处在语义解释的上层,元语言自身的意义仍是问题。因为显然不可能从“下端”(对象语言)得到解释,所以只有两种可能方式:从“上端”或者从它自身得到解释。从上端解释意味着在它这个“元语言”之上,还有一个更原初的语言“meta-meta-language”来规定和解释它的意义。但无论我们怎么定义这个“meta”,这种语义解释的上溯都会导致无限循环;并且我们在这一思路中也找不到什么特定的“基点”,来终止这种无限的上溯和搁置。(33)因此只能从它的自身解释。然而,这意味着在这里出现了两套语义解释方式:一种是通过上端的元语言来解释对象语言,一种是通过元语言本身来解释其自身意义。但是,在一种“语言分级”的语义解释理论中,为何要允许一种自我解释的方式呢?并且,解释出的“意义”既然在我们使用的语言之外,又要怎样理解或至少是“谈论”它呢?不同的元语言理论只是提供了不同的元语言候选者,断言它们是语义上优先和自我解释的,却并未认真考虑这种处在我们语言之外的“意义”有何意义?
为了看清这一点,不妨列举一下元语言的三个候选者,看看巴拉德主动实在论的“元语言表述”属于其中哪一种:(1)形式化的语义学“定理体系”,正如塔斯基的“Convention T”所表示的,它们规定了日常语言意义解释的“形式规则”。(34)(2)实证意义上的“现象语言”,比如最简单的知觉“观察报告”。(3)形而上学实在论的“语言”。很明显,她的关键表述不是形式定理,也不涉及观察报告;另外,其实也只有从我们的语言出发才能理解这两种“元语言”。而唯一的可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元语言。但之前讨论到,她实际上也不会同意形而上学的意义决定方式。只是在这里,这种形而上学的“元语言”(“世界的特定物质(重)构造行为”),似乎具有了一种特权,根本不再以人的理解为条件。但是,正如普特南所说:“这种认为有一种不能被‘言说’的语言性思想的观点,就是我说的那种我无法理解的形式主义把戏。”(35)也就是说,巴拉德的表述若想有“意义”,若想成为一个被人理解的表述,根本上必须以我们的语言实践为基础。“一个语言游戏中的语词的用法,不可能不运用到这一游戏中的词汇而得到描述。”(36)因为人的语言实践(游戏)构成了我们无法摆脱的“地位”,对我们具有“强制性”(imperativeness),在它之外将不再有任何对错、认识和意义可言。因而在我们的语言之外,不可能、也不需要有一种“元语言”。因此,元语言的思路同样无法解决巴拉德表述的“意义问题”。
我们可以理解巴拉德主动实在论所坚持的“后人本主义”,是为了让我们彻底摆脱“拟人论”的神话,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迷信。但这并不要求抛弃整个“人的地位”,即便我们并不承认一种启蒙意义上的先在“人性”。人对于自身及其实践的认识是不断更新和发展的,但这一切并未脱离人类实践的轨道,并未脱离人类语言实践的范围。维特根斯坦强调“让我们作为人”(37),在人的地位中思考和实践,并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迷信”和以人类生活图景为基本观点的(也是玻尔所执着的)“人本主义”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诚然,我们可以将一幅牢固地植根于我们心中的图画,看成一种迷信;然而同样正确的是,我们最后总要达到某种坚实的基础,它或者是一幅图画,或者是其他什么,因此一幅处在我们所有思想的根基的图画,应当被尊敬,而不应被当成迷信。”(38)这些应当受到尊敬的图画,构成了我们作为人的地位,而这个地位是我们一切实在和实践得以展现的条件。
注释:
①②(14)(15)J.A.Wheeler and W.H.Zurek ed.,Quantum Theory and Measuremen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3,p.9,p.88,p.64,p.19.
③⑧(12)(13)(17)(18)(22)(24)(25)(26)(27)(28)(29)K.M.Barad,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Quantum Physics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Matter and Meaning,Durham &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7,p.107,p.423,pp.110-113,p.116,p.120,p.138,p.139,p.143,p.145,p.149,p.148,pp.149-150,p.148.
④⑤⑥⑦(11)N.玻尔:《尼耳斯·玻尔哲学文选》,戈革译,商务印书馆,1999,第86-87页;第29页;第87页;第92页;第91页。
⑨(16)N.Bohr,"Causality and Complementarity",Philosophy of Science,Vol.4,No.3,1937,p.290,p.291.
⑩“测不准定理”在英文中一般翻译为“uncertainty principle”和“indeterminacy principle”,即“不确定性定理”。关于其翻译和辨析请参见:M.雅默:《量子力学的哲学》,秦克诚译,商务印书馆,1989,第73-74页。
(19)R.Descartes,Philosophical Writings,Elizabeth Anscombe and Peter Geach,trans.& ed.,Upper Saddle River:Prentice Hall,1971,p.20.
(20)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第532页。
(21)(33)(35)H.Putnam,Realism with a Human Fa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p.5,pp.13-14,p.15.
(23)W.James,Writings 1878-1899,Literary Classics of United States Inc,1992,p.908.
(30)H.Putnam,The Threefold Cord:Mind,Body and World,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p.6.
(31)L.Wittgenstein,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G.E.M.Anscombe trans.,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58,§43.
(32)H.Putnam,Pragmatism:An Open Question,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95,p.65.
(34)(36)H.Putnam,Words and Lif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p.319,p.283.
(37)(38)L.Wittgenstein,Culture and Value,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80,p.30,p.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