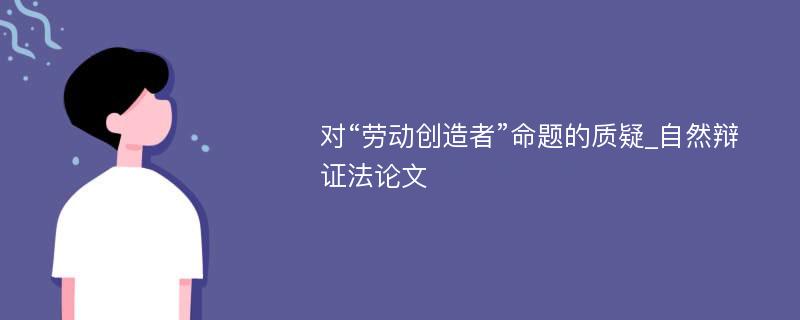
对《关于“劳动创造人”的命题》的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命题论文,创造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人类的起源,国内理论界历来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是依据于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人的学说,将人类产生的基本原因归结为“劳动”,本文称其为“劳动说”;另一种则依据现代达尔文主义强调生物进化的决定因素在于突变、选择、隔离等遗传学机制的论点,将人类起源归结为进化生物学问题,本文称其为“遗传说”。龚缨晏先生的《关于“劳动创造人”的命题》属于后者(论文刊载于《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并分别为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1994年第9期和《新华文摘》1994年第9期全文转载。本文简称为“《命题》”。以下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引自《命题》)。
《命题》的新颖之处,在于作者将人类起源归结为一种纯粹的“内在生物学机制”,完全否定了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人”学说的科学性,从而把“遗传说”的论点推到了极致。鉴于唯物史观同“劳动创造人”学说之间的内在关联,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提出反论,以就教于龚缨晏先生。
一
恩格斯在《劳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以下简称“《劳动》”)中,对“劳动”的界说,有两个前后衔接、相互连系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从“猿手”到“人手”之间的使用天然工具的“几十万年的劳动”①;第二阶段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真正的劳动”②。根据现有的材料,前者是指迄今四百万年前至二三百万年前这一百多万年间的南方古猿,即“正在形成中的人”的使用天然工具的劳动③;后者是指自二三百万年前早期猿人即能人的出现,直到十几万年前智人的出现,即“完全形成的人”的制造并使用工具的劳动④。由于《命题》明确表示“工具的制造标志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故其同《劳动》之间的分歧,集中在对第一阶段的劳动于人类起源是否有意义这一焦点上。《命题》强调人类起源是受“内在生物学机制决定”的“新物种如何形成的问题”,而南方古猿使用天然工具的劳动“之类的外部活动并不能导致遗传基因和遗传信息的变化,不能导致物种的形成”,所以“如果用‘劳动或其它非自然因素来解释人类的产生过程,如果认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的人类的起源是受超自然规律的支配,那么,就会产生一种新的特创论,实际上否定了现代科学’。”
《劳动》则强调“正在形成中的人”使用天然工具的劳动在人类起源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进化生物学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文化社会学问题,因此这一阶段的劳动具有文化——生物学的双重含义,人类起源是文化——生物学双重机制的整合过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⑤。《劳动》对第一阶段的劳动赋予了以下几项内容:
1.“渐渐直立行走。这就完成了从猿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⑥。
2.“手变得自由了,能够不断地获得新的技巧,而这样获得的较大的灵活性便遗传下来,一代一代地增加着”⑦。
3.劳动过程中的共同协作使“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的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⑧。
4.由于“劳动”和“语言”的双重推动,“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了人的脑髓”⑨。
近70年来的南方古猿化石的大量发现和研究表明,上述四项内容都可以在化石中得到有力的证明。这些在化石中明显存在的人科特征,究竟同“使用天然工具之类的外部活动”有无关系,是否真的像《命题》所说:“直立行走、手的灵活性、器官性状的变化,……都是由遗传基因的变化而造成的,并不是经常使用的结果”,“所有的这些活动都是由内在生物学机制所决定的”,因而“人类的起源不能由双脚行走开始的劳动来说明”?
现代遗传学强调,突变的“利”或“害”“与特定的环境有关”,突变的适应作用如何取决于生物体生活的特定环境”⑩,对生物进化具有甄别和导向作用的“自然选择是由环境施行的,是由环境施行的选择”(11)。动物对环境的适应性活动和行为,则是连系环境与突变的中介。
美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学术界公认的进化生物学权威,综合进化论的积极创导者之一E.迈尔认为,环境的变化引起的“行为转变”,直接构成了对突变的新的选择压力,从而使表现型的功能或结构,在遗传型的“高度复杂的系统”所许可的范围内,逐渐发生改变,“由行为改变引起的新的选择压力导致形态变化以利于占有新生境或新适应区”(12)。迈尔论证道:
原始的啄木鸟由于行为转变到在树干和树枝上爬行,虽然仍然基本具有其祖先的足部结构,但是这新的习性对几种不同的啄木鸟产生了新的选择压力,使其足部和尾部高度特化以适应更有效的攀援活动。在进化进程中很多(如果不是绝大多数)新获得的结构都能归之于新获得行为所施加的选择压力。因此,行为在进化演变中扮有重要的带头人的角色。大多数适应辐射显然是由行为转变所引起的(13)。
迈尔的论断显然也适合于解释何以在南方古猿身上同时既保留了若干由人猿超科祖先的主干继承下来的原始特征,即“共同遗传的特征”(Charactersof common inheritance),又出现了新的人科特征,即“独立获得的特征”(Characters of independent acquisition)这一现象,其直接原因正是在于被《命题》所拒斥的“使用天然工具之类的外部活动”的行为转变,引起了新的选择压力而导致的表现型的功能和结构的变化。因此我们认为,就人类起源而言,南方古猿使用天然工具的劳动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关键环节。离开被《命题》所拒斥的这一重要环节,所谓的“内在生物学机制”就成了不受环境制约和自然选择支配的绝对物,这样的生物学机制是根本不存在的。
不错,《命题》确实说了自然选择对突变的甄别和定向作用的话:“生物进化的基本过程就是自然选择”,“自然选择的法则支配着人类的起源”,“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有利的突变得到保存并遗传给下一代,有害的变异被淘汰灭绝。这样,在下一代群体中,有利的基因就会以较高的频率出现。这就是适者生存。”并且还用“适合度”和“最适合者”这两个概念来论证这个问题。但既然是在生物进化、物种形成的范围内讲变异和遗传,与“适合度”相辅相成的“选择压力”,与“突变”不可分割的“环境条件”,却又只字不提。而缺失这两个至关重要的环节,适应环境的行为转变就无从谈起,遗传变异同自然选择之间就失去了现实的连系,生物进化就无从实现。
为了突出遗传变异的自在自决性,《命题》还例举了“中心法则”和“中性学说”来加以论证:“中心法则表明,遗传信息是由核酸传递给蛋白质,而不能由蛋白质传递给内部的核酸。中性学说更进一步说明,基因的突变有它自身的规律,而不是由生物体外部行为所决定的。因此,使用天然工具之类的外部活动并不能导致遗传基因和遗传信息的变化,不能导致群体基因频率的变化,不能导致物种的形式”。
但是,“按体内环境的选择标准对功能蛋白质进行分类”的研究表明,作为遗传变异机制赖以进行的体内环境的蛋白质,对突变基因具有“第一次整理”的作用,即“剔除了致死突变,使许多中性基因,有利基因,中性偏好或偏坏的基因,以及不利基因的表型个体得到保存,为体外环境选择提供了原料”(14)。在生物进化范围内,只强调“遗传信息由核酸传递给蛋白质”,而不提蛋白质对基因突变的“第一次整理”的作用,突变基因何以附着?遗传信息何以传递?
“中性学说”证明了基因突变作为分子水平上的进化,本身确实“不是由生物体外部行为所决定的”。但《命题》似乎忘记了,自己论证的问题既然是生物进化,因而就必须在表现型水平的进化层次上引入自然选择这一支配机制。正如“中性学说”的创始人木村资生所说的:“中性说是始终以分子水平结构来提问题的。至于表现型水平,我没有说过什么。这只能用达尔文自然选择说来解释吧!因为只有自然选择说能够很好地说明这种适应现象”(15)。在讨论生物进化时只涉及分子水平的进化,回避表现型水平的进化,其结果必然是否定自然选择。而承认自然选择,就意味着必须承认“环境条件”、“选择压力”,与“突变”、“适合度”之间是互相依存的范畴,意味着必须强调“使用工具之类的外部活动”等“行为转变”在生物进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迈尔引入“关键性状”这一概念来论证这一问题,认为由行为转变引起的新的选择压力,致使表现型结构或功能发生变化的过程,即是所谓“关键性状”的逐步获得过程。他指出:“就人类进化而言,从树栖的类人猿阶段过渡到现代人阶段就涉及一系列关键性状。直立姿势,灵活的手,制造工具,捕捉大型有蹄类动物,以语言为基础的信息交流系统等等,就是这样一类相连续的关键性状”,“现在已弄清楚大多数进化实际上只限于关键性状以及少数与之有关的性状”(16)。作为遗传变异与自然选择的对立统一关系的体现,“关键性状”是在生物进化过程中基因型与表现型、核酸与蛋白质、适合度与选择压力、突变与环境条件等多层次相互依存的自然关系的矛盾过程的产物。动物的适应性活动和行为绝不仅仅是受制于“遗传基因的变化”这种“内在生物学机制”的单向受动过程。
尽管我们认为把人类进化局限于物种的“关键性状”的获得,即在进化生物学范围内讨论这个问题,仍然是一种十分偏颇的观点,但这至少能促使我们对第一阶段的劳动在人类起源过程中是否具有意义这一争论焦点,得出两点启示:
1.迈尔的“行为转变”和“关键性状”的论点及其论述,为恩格斯提出的第一阶段的“劳动”的四项内容,提供了现代达尔文主义的坚实的理论基础。
2.正因为《命题》割断遗传变异与自然选择之间发生联系的现实中介,故而其完全否认“使用天然工具之类的外部活动”在人类起源中的决定作用这一论断的证据不能成立,所以说《命题》所得出的“‘劳动创造人’的命题是不符合生物学研究成果的,是缺乏生物学基础的”结论,也是一个站不住脚的结论。
我们认为,“劳动创造人”学说中的“劳动”,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生物学范畴,由其开创的从文化—生物学的双重机制来阐释人类起源问题的逻辑起点,迄今仍具有巨大的理论生命力。
二
《命题》否定恩格斯“劳动创造人”学说的基本论据有二,一是上文已提到过的不受外部活动影响的“内在生物学机制”,二是“劳动创造人”学说使用了“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来论证自己的论点,“这种观点正是拉马克学说的基本内容。但是,现代生物学已经否定了拉马克学说,因此,‘劳动创造人’的命题也就失去了其生物学依据。”
作为直到19世纪末还广泛流行的生物进化论观点,“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一直为达尔文所接受,直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这种观点才逐渐受到普遍怀疑而被多数生物学家所否认。即使如此,国内外不少生物学家仍持有不同看法。例如我国著名生物学家方宗熙在其60年代出版的《生命的进化》一书中就鲜明地指出“获得性状可以为遗传性的发展开辟道路”,并提出了自己的实验依据。(17)我们无意也无力对“获得性遗传”是否成立这一生物学问题进行探讨,只是想指出,抓住《劳动》使用了一个迄今尚有争议的学术观点这一点,是远远不足以断然否定成书于1876年的“劳动创造人”学说的。
我们认为,与其说因为《劳动》将“获得性遗传”作为其“生物学基础”而应当加以否定,不如说因为这一学说赋予“劳动”以生物进化和文化发展的双重含义而容易引起误解。查《劳动》使用“获得性遗传”的地方共有两处,引述如下:
1.手变得自由了,能够不断地获得新的技巧,而这样获得的较大的灵活性便遗传下来,一代一代地增加着(18)。
2.所以,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只是由于劳动,由于和日新月异的动作相适应,由于这样所引起的肌肉、韧带以及在更长时间内引起的骨骼的特别发展遗传下来,而且由于这些遗传下来的灵巧性以愈来愈新的方式运用于新的愈来愈复杂的动作,人的手才达到这样高度的完善,在这个基础上它才能仿佛凭着魔力似地产生了拉斐尔的绘画、拉尔瓦德森的雕刻以及帕格尼尼的音乐(19)。
恩格斯实际上谈了两种遗传性,一种是手的灵活性即文化学意义上的遗传,一种是手的解剖学特征即生物进化意义上的遗传。当代进化生物学以无可辩驳的科学事实,证明了“手的灵活性”,作为后天习得的功能,尤其是人类所特有的文化性的劳动技能,是不可能通过生物进化途径得以“遗传”的;而手的解剖学特征,作表现型结构和功能的改变,则是可能逐代地加以遗传的。可是问题在于,这两种不同性质的“遗传”恰恰都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谁也不会为人类所逐代取得的巨大文化成果和人类进化各阶段的大量化石证据而困惑不解。这一事实说明:不能把人类起源问题仅仅归结为进化生物学问题,它既不是“由内在生物学机制所决定的”,也不仅仅是“关键性状”的获得,而是一个横跨进化生物学和文化社会学的跨学科的综合性理论问题。
《劳动》对其“劳动”范畴的文化学描述,几乎囊括了当代文化学研究的各个层面:从使用工具的生产活动到社会交往活动,以及作为这两种活动中介的语言符号活动。
首先是工具的发展。从使用天然工具到制造工具,既伴随着从“猿手”到“人手”的表现型结构和功能的转变,也伴随着从“正在形成中的人”的劳动到“完全形成的人”的劳动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手的专门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20)。牢牢地把握住从动物式的本能劳动走向有目的的对象化劳动这一中心线索,是在人类进化领域内走出“遗传说”误区,克服“劳动说”弊端的关键。
其次是社会性交往和语言活动的出现。“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一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21)。其间伴随着“猿类不发达的喉头”,到人的能说话的“口部器官”,以及猿脑到人脑的表现型结构和功能的改变过程(22)。
第三是“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而产生了新的因素——社会”,一方面有力地推动着工具—交往—语言符号活动这一崭新的超生物学的文化机制“大踏步地前进”,另一方面又为其把定着脱离动物界、向人类社会提升的“更确定的方向”(23)。区别于动物习性的“人性”在回归人类社会的“狼孩”身上的某种程度的失而复得,说明这一新机制与生物进化规律之间既有先天的联系,更有本质的区别。
美国人类学家怀特指出,人类行为是“机体要素”和“文化要素”的“复合物”,人类的语言符号能力使文化因素“成为严格意义上的超生物学的或超躯体的存在”,“文化通过社会继承机制而流传,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是超生物学的”(24),工具—交往—语言符号活动是文化“遗传”得以形成的社会学内在机制。在“劳动创造人”学说中,这种机制以胚芽的形式存在于使用天然工具的“正在形成中的人”的劳动中。“手的灵活性”之类的文化“遗传”,正是在人的“关键性状”获得的劳动过程中逐渐萌芽和发育起来的。这是“正在形成中的人”使用天然工具的劳动同其他生物物种适应性“行为转变”的本质区别所在,也是我们不能同意《命题》所谓“从古猿发展到人,实际是一种新物种如何形成的问题”,“人和猿的差异,本质上是由基因及染色体的若干差异所决定”的论断的依据所在。
我们把以“正在形成中的人”使用天然工具的劳动和“完全形成的人”制造并使用工具的劳动为中心线索的人类起源过程,视为两个交互作用的变量的函数,它们分别是:以“行为转变”和“关键性状”的逐步获得为内在机制的进化生物学变量,和以工具—交往—语言符号活动的逐渐发展为内在机制的文化社会学变量。
文化社会学变量萌芽于400万年前开始的南方古猿使用天然工具的劳动之中,随着人的“关键性状”的逐渐获得而孕育生长。到了迄今二三百万年前的早期猿人即能人出现时,孕育于进化生物学机制内的文化社会学机制,终于脱离其母体而成为人类起源函数中的一个独立变量,开始了两个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的变量共同作用于人类进化过程的崭新阶段。这些从南方古猿中分化出来的“完全形成的人”,通过制造并使用工具的“真正的劳动”,完成了人猿相揖别即“人最终同猿分离”这一人类起源过程中最为关键的环节(25)。其生存方式已经迈开了由受动型生物性的适应方式向创造型文化性的劳动方式的最初的然而又是决定性的一步,由动物的感知反映的信号世界迈向人类的价值意义的符号世界,由本能的行为转变走向自觉的目的活动。《劳动》根据19世纪的生物胚胎发育的重演学说,提出了从“孩童的精神发展是我们的动物祖先,至少是比较近的动物祖先的智力发展的一个缩影”(26),这一探讨人类进化机制的思路。当代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这条思路在探讨人类起源的双重机制的发生发展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文化社会学机制一经产生,它就随着石器的不断改进、语言的出现、火的使用、社会性交往等等文化创造的不断涌现和累积迅速地成为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主要变量,而进化生物学变量则从原先的主导地位而降至次要地位。这两个变量的一升一降,突出地表现在当人类进化至十几万年前的智人(现代人)阶段时,人脑及其相关中枢神经系统的容量、结构和功能,已经在得到飞速进化之后而基本趋于停止,以至出现了人类同黑猩猩在分子特性和染色体结构上非常相似,而在脑和相关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上又高度分化这一典型的“镶嵌进化”现象。怀特指出,动物意识的变化“是机体结构变化的函数”,而人类意识的变化则“是文化传统变化的函数”(27),相对于支配人类社会发展的文化社会学机制而言,体现生物进化最高成果的人类“机体的心身因素可以看成一个恒量”(28)。曾经一度支配人类起源过程的进化生物学机制成为人类认识并加以利用的自然规律。然而,亿万年的自然—文化历史进程赋予人的潜能素质都不断地以胚芽的形式积淀并孕育在人脑中,成为乔姆斯基所谓的作为语言能力的“天赋宫能”,即外在于人类躯体的文化社会学机制赖以累积和发展的生物学出发点。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进化生物学机制在人类机体上并未完全失去作用,只是这种机制的动力源,已经由昔日的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的没有意识的自然界,转移到工具—交往—语言符号活动的社会领域之中。正是在劳动使文化社会学机制从进化生物学机制中孕育产生并得以发展这一综合性的文化—生物学意义上,恩格斯强调劳动才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29)。
因此,人类的起源和进化,不仅要接受自然选择的严峻考验,更要面临文化创造的严格筛选,人是自然选择和文化创造的共同产物。那些未能经受住自然选择考验的南方古猿的特化类型,在大约100万年前灭绝了;经受住这类考验的南方古猿的进步类型(非洲种或阿尔法种),则在面临进一步的文化创造筛选时发生了进一步的分化:只有那些能够在直立行走、使用天然工具劳动等“行为转变”和“关键性状”获得的进化生物学机制内及时萌发出工具—交往—语言符号活动的文化社会学机制的种群,才能迈上从使用天然工具的劳动到制造并使用工具的“真正的劳动”这一条人类进化的崎岖之途,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转变。而大多数进步类型的种群,则因为种种原因,或未能及时萌发出文化社会学机制,或即使有所萌芽——如大猩猩的未能符号化的简单推理能力——却又不可能得以积累和传递,故始终受进化生物学机制的支配,或者灭绝,或者演变成现今的与人类亲缘关系颇近的猿类。所以,举出“那些已经直立行走、使用天然工具的南方古猿及它为什么会灭绝”这一事实,恰恰不能作为否定“劳动创造人”学说的论据,而只能是这一学说的有力佐证。
三
对待前人的学说,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结论性命题,应当把视野放在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中,看其相对于前人而言,提出了哪些有意义的新见解,然后才有可能讨论这类见解在当代有什么新的意义和不足之处。这样,我们才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一步地向上攀登。《命题》则舍弃这个前提,直接用当代遗传学的尺度来抽象地衡量“劳动创造人”学说,比如说:“现代生物学已经否定了拉马克学说,因此,‘劳动创造人’的命题也就失去了其生物学根据”;再比如《命题》用只能建立在现代生物学基础上的个体遗传与群体遗传的概念,指责道:“‘劳动创造人’的命题的致命弱点之一,就在于不能将个体遗传与群体遗传区分开来”,等等。这种指责前人的学说因为没有能够说出现代科学的结论而否定其理论意义的反驳方式,是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态度的。
成书于1876年的《劳动》及其“劳动创造人”学说,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这个学说赖以建立的进化生物学理论亟待现代生物学理论成果的补充。而把“获得性遗传”和“用进废退”直接作为人类起源的文化社会学机制的铺垫的描述方式,又很容易使人们忽视其中的进化生物学机制,这也许是我国理论界中的“劳动说”或多或少产生“在左倾思想影响下过份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过份夸大主观意识的作用”的理论偏颇的原因之一。在这一点上,我们所要加以纠正的,恰恰是我们的思维模式,而不是“劳动创造人”学说本身。
综上所述,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人”学说的强大理论生命力,就是在人类起源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上,在进化生物学机制内引入了文化社会学机制,从而把人类进化过程看成为这两个变量的函数。这是我们深入探讨人类起源问题的唯一正确的逻辑起点。如果像《命题》那样,一方面否认使用天然工具的劳动之类的外部活动在人类起源过程中的意义,另一方面又肯定“工具的制造标志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那么就等于在南方古猿和人之间划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一方面是完全受制于内在生物学机制的南方古猿阿尔法种永远不得人类进化之门而入,另一方面是突如其来的制造工具的“完全形成的人”的降临。这实际上已经“产生了一种新的特创论,实际上否定了现实科学”。
注释: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0页。
②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4页。
③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2页。
④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3页。
⑤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49页。
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0页。
⑦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2页。
⑧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3页。
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页。
⑩[美]弗·乔阿耶拉等著:《现代遗传学》,湖南科技出版社1987年版,第657页。
(11)[美]E·迈尔著:《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713页。
(12)[美]E·迈尔:《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699页。
(13)[美]E·迈尔:《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699页。
(14)李难主编:《生物进化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167-168页。
(15)转引自李难主编:《生物进化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373页。
(16)[美]E·迈尔:《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701页。
(17)李难主编:《生物进化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149页。
(18)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0页。
(19)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0-151页。
(20)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9页。
(2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2页。
(2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2-153页。
(2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3页。
(24)[美]怀特:《文化科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9、117页。
(25)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3页。
(26)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8页。
(27)[美]怀特:《文化科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1页。
(28)[美]怀特:《文化科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1页。
(29)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8页。
标签:自然辩证法论文; 现代生物进化理论论文; 突变理论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生物技术论文; 生物进化论文; 自然选择论文; 进化论论文; 南方古猿论文; 恩格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