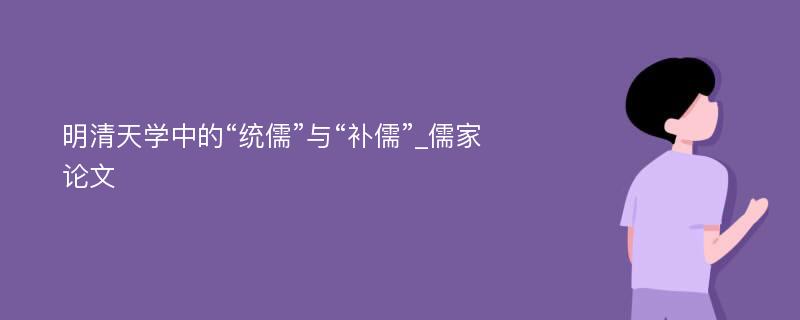
论明清间天学的“合儒”与“补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清论文,间天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学东渐”源于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来华。“中国正式接触到所谓‘西学’,应以明末因基督教传入而带来的学术为其端倪。(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册,第1189页)
耶稣会士来华以后中西宗教和哲学开始接触,中西文化的交流进入了思想观念的会通与融合、碰撞与磨擦的阶段。
本文旨在对来华耶稣会士针对儒家思想所制定的对策给以简单的剖析,不足之处请学界同仁给予指正。
一、耶稣会士的“合儒”政策
利玛窦作为一个传教士,对他来说,“最重要和最中悦天主的事,是教友能日渐增加”,他的所有工作都是“希望这个伟大的计划能早日实现”(《利玛窦通信集》,台湾光启出版社,1986年版,第42页)。
但利玛窦所到达的不是非洲和美洲,而是一个在西方文化之外,完全自主、独立发展起来的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国,“是唯一的一种保留了精确的哲学反思之重要证据和未曾使用一种印欧语言的文明即中国文明”(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第347页)。利玛窦初到中国时完全被中国的这种高度发展的文明和悠久的文化所震憾。在他初到肇庆后写回西方的第一封信中,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中国的赞美,中国有广阔的国土,“它整个看起来就像一座大花园,并有无可形容的宁静与安详, ”(《利玛窦通信集》台湾光启出版社,1986年版,第47页)中国人勤劳,智慧,创造了辉煌的文化成就,而这些都是在完全没有同西欧人交往的情况下“完全有自己的经验获得如此的成就”,中国有良好的秩序,有效的管理,无穷的财富。
面对着这样一个完全成熟的、异质的文化,如果采取天主教以往那种直接面向下层群众的布教方法显然不行。必须从文化入手,从上层入手。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1538—1606 )所规定的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策略直到利玛窦时才逐步变成了现实。
利玛窦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有一个从浅到深的过程,这从他由着僧服改为着儒服就可以充分表现出来。通过他的学习与观察,他认识到儒家文化在整个中国文化中的主导地位,他说:“儒教是中国古代原有的宗教,故此古代和现在,这些人一直握有政权,也是最盛行,最受重视,经典最多的宗教”。(利玛窦《中国传教史》,台湾光启出版社,1986年版,第83页)“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是孔子”(同上,第24—25页)孔子在中国具有极高的地位,因为“虽然不能说在中国哲学家就是国王,但可以说国王是受哲学家牵制。”(同上,第21页)。
利玛窦已经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的政治文化特点是政教合一,皇帝就是天的代表,而只有“皇帝给上帝奉献祭祀,若有别的人妄想行此仪式,则认为是侵犯皇帝之权利,而加以惩罚。”(同上,第385页), 这自然与西方的政权和教权机构相分的体制不同。
面对着这样一个神权与政权完全融为一体的社会结构,天主教要想进入中国,利玛窦要想完成其肩负的使命,几乎可以说没有其它的选择,他只能与当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学结合,即走“合儒”的路线。当然这个方法对于天主教的传统传教方法来说也是很危险的,有些叛经离道的感觉,这也是造成后来耶稣会与其它后进入中国的天主教修会,如方济各会、多明我会、遣使会、奥斯丁会等发生分歧,并引起内部不同意的根本原因之一,所谓的“礼仪之争”是从这时就埋下了导火索。
但若从中西文化交流史来看,从西方思想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来看,利玛窦毕竟迈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正是这一步西方文明开始了与东方文明的真正相逢,因为西方文明的核心——哲学与宗教开始同东方哲学和宗教展开一种实质性的对话与比较这是以前所从未做的。与马可·波罗那种威尼斯商人的眼光相比,利玛窦看的要深刻的多。一场对中西文化日后的发展都起到重要作用的哲学、宗教对话由利玛窦开始拉开了序幕。
研究利玛窦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解释,分析他的“合儒”“补儒”尝试的得失不仅可以使我们理清明清思想上的一段公案,对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的这种历史性努力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给一个公正结论,而且从中可以加深我们对中西文化各自价值特点的认识和反思,尤其是在今天当中西双方重新平等地坐在一起时,文化问题凸现出来,中西双方都又回到了这个原点上来;中西文化如何会通?这成为我们今天必须重新思考的问题。利玛窦研究的价值正在于此。
我们从对利玛窦思想的研究入手,重新分析一下四百年前中西哲学与宗教的冲突与融合。
当利玛窦在瞿太素的劝告下,脱下僧服披上儒装时,他就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即采取了与中国主流文化——儒家文化亲合的办法。来华耶稣会士“会儒”工作大体是从三个方面入手的。
首先,突出原儒文化的宗教性质。中国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期间殷周时期是个关键,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形成了它的基本特点。如果同西方文化的“轴心期”的文化转型相比,中国文化的特点不是像西方那样超越自身把终极的关怀寄托于神那里,而是从诸神转向人间,把精神的超越寄托于人世间的伦理活动中。
利玛窦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敏锐地察觉到儒家文化的这种伦理性和一神教的天主教的宗教性的差别,于是他采取了将儒家一分为二的方法,对于原儒他肯定其宗教性的一面。以表示他对当下儒家理论的不满,对于新儒家,他采取批评态度,从而达到“以耶补儒”的目的。关于他对新儒家的批判下面我们还要具体展开,这里暂且不议,而他所谓的“合儒”实际上又是为他批宋儒所做的一种理论准备。我们只有首先弄清其“合儒”的内涵,才能理解他批儒的实质。
对于原儒的宗教性的肯定他主要是通过文献考据学方法来完成的,通过考证证明中国古代存在上帝,说明儒耶本为一家。
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说“吾天主,即华言上帝”。于是他做了一系列的引证来证明这一观点。
孔子在《中庸》中说的:“郊社之礼以事上帝也。”
《周颂》曰:“执兢武王,无兢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
又曰:“于皇来年,将受厥明,明昭上帝。”
《商颂》云:“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只。”
《雅》云:“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易》曰:“帝出乎震。”
《礼》云:“五者备当,上帝其餐。”
又云:“天子亲耕,粢盛柜鬯,以事上帝。”
《汤誓》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又曰:“唯皇上帝,降哀于下民,若有恒时,克绥厥犹,唯后。”
所以,结论是“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和持异以名也”。利玛窦这个思路为大多数来华传教士所承袭。 方济各会的利安当(Antonila Sancta Maria Caballera)在《天儒印》中采取的就是利玛窦的这种方法。他分别列举出儒家经典的部分论述,尔后从天主教方面加以解释,以证实天儒本为一家。如对《大学》中的“明明在德”的解释为“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人之灵明不能自有而为天主所界也”(《天儒印》)在白晋(Joachim Borvet,1656—1730)的《古今敬天鉴》中,在孟儒望(Jean Monteiao,1603—1648)的《天学略义》中, 在中士严保禄的《天帝考》中,所采用的论证方法,大体都是如此。
利氏的这种文献学的方法对于言必称三代的儒家知识分子来说有很大的说服力,他们一方面感到这些传教士学府五车,满腹经伦,与自己是同道人。另外,以古人之言为证,使后人十分信服。利玛窦所开创的这种“文献解释学”的方法是成功的。
就理论本身来说,中国文化在殷周时期的确经历了一个从自然宗教信仰到人文伦理信仰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自然保存着自然宗教的痕迹。我们的小标题用“原儒”仍不太准确,因在殷周时代尚没有儒家,或许用“前儒”更合适。但中心是要说明在殷周之转变中,自然宗教的痕迹仍大量存在。
作为自然宗教中崇拜的“上帝”和已经成熟的基督教的一神论中的“上帝”二者之间有着原则性的差别。利玛窦混淆了这种差别而只突出其一致性的方面,应该说利玛窦的方法是很高明的。
一方面是他采取策略的高明,更重要的在于他早已认识到中国文化本身的这种形态的转变。四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在讨论这个问题,从“巫”到“士”再到“教”(儒教,姑且称之)每个阶段所表现的特点是不同的。作为一个外来的传教士能敏锐察觉到这一点,不能不令人敬佩。
其次,强调耶儒在伦理上的一致性。“孔子贵仁”(《吕氏春秋·不二》)“仁爱”是儒家伦理的根本特征,这种“仁爱”的原则既有基于宗法血缘关系的“爱亲”的含义,如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论语·学而》)但同时也包含有泛爱的含义,如“楚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八佾》)这种泛爱实际是对人道德的提升,标明人的伦理之进化,以别于动物。
基督教伦理学也强调爱,“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彼此相爱吧,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凡是实行爱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子,来自上帝。任何人如不实行爱,就不会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约翰书》第四章)基督教的爱这里有二层含义:一是“爱上帝”,二是“爱人如己”。显然,耶稣教与儒家既有共同性,也有差别性。但来华传教士在“合儒”中只强调其共同性一面,或者把基督教的爱的伦理套用到儒家的“仁”的伦理上。如利玛窦说:“天德之品众矣,不能具论,吾会为子惟揭其纲,则仁是焉。得其纲,则馀者随之,故易之:‘元者,善之长;君子体仁,足以长人。’”然后他概括说儒家的仁学主要有二条:“‘爱天主,为天主无以尚;而为天在主者,爱人如己也’,行斯二者,自行全备矣。”(《天主实义》第八编)利玛窦对这二层含义与儒家“仁”的对应并未做区分。
利类思在《天儒印》中解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时,也说“吾主圣训有是语,此即爱人如己之大旨也”。他认为“天主既为天地大君,不爱天主,可谓忠乎?欲爱天主而不爱天所爱之人,可谓恕乎”?利类思的思路略有变动,因为从逻辑上讲爱天主和爱人是不能互证的,爱天主是没有逻辑前提的,它是信仰在伦理上的体显。所以当利类思提出“爱主爱人如南北东西权不容阙一,不爱主断不能爱人,不爱人称不上爱主”(《六儒印》)时,已经向儒家思想做了一定的妥协和让步。
最后,对儒家礼仪的宽容性。
利玛窦对于中国传统的祭祖和祭孔采取了一种宽容态度,樊国梁在《燕京开教略》中说“溯自利玛窦开教中华,中国之仪之节礼,不免有碍圣教正道之条,新奉教者遽难一一断绝。传教士等初尚一、二,以为此等仪礼,不尽涉于异谓,……。”(樊国梁《燕京开教略》),中篇,第44—46页)如果利玛窦要想得到儒家的支持,非如此不可,这种做法显然赢得了大多数教中儒士们的支持。尽管这种做法为以后的礼仪之争埋下种子,耶稣会内部也发生了分歧。但利玛窦所确定的这个路线为当时为天主教在中国站稳脚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艾儒略在《大西利先生行迹》中说:“大西利子,奉天主真教,航海东来,其言多与孔、孟合。”但“合儒”对来华耶稣会来说主要是策略性的,当然也有被中华悠久文明所打动的部分,把利氏等人的做法完全归为策略也不妥。利玛窦在促进文化的融合上,在对基督教理论的普世性理解上都有着开创性的建树,把他称为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是当之无愧的。
对传教士们来说,传教是宗旨,但如果耶儒完全相同,那何苦要引进天主教呢?因而他们必然要同中国文化划出界线,以彰明天主教来华之必要。
二、耶稣会士的“补儒”政策
宋明理学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是经东汉经学、魏晋玄学之后,中国哲学思想向其理性化发展的最高表现。它以儒家伦理为核心,以道家的宇宙论为基础,在大量吸收佛教思辨特点的情况下,将儒家的思想向本体的方向提升,使其抽象化、理性化。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的“理气论之大成者是朱晦庵(熹)。朱子根据伊川之学说,加以扩大、充实,予以丰富的内容,形成中国哲学中最缜密、最有条理的本根论系统”。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8页)张先生所说的本根论即理性化的本体论。
理性化的儒家哲学体系同天主教一神论的分歧是十分明显的。正因此,来华耶稣会士对宋明理学展开了多次的批判。
第一,理不具有本体功能。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首次展开对理学的批判,其入手之处就是哲学本体论上的判定。宋明理学以《易学》作为其宇宙论的框架,周敦颐《太极图》中最早提出了一种宇宙生成发展的图式,他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金、木、土,五气,四时行焉”。(《周子全书》卷一)
利玛窦说:“呜呼!他物之体态不归于理,可得将理以归正义;若理之本体定,而不以其理,又将何以理之哉?吾将先判物之宗品,以置理于本品,然后明其太极之说不能为万物本原也。”(《天主实义》第二篇)这里他首先提出了一个原则:万物分为二类,一类是自立者,一类是依赖者,只有自立者才能成为本体。他说:“夫物之宗品有二:有自立者,有依赖者。物之不特别体为物,而自能成立,如天、地、鬼、神、人、鸟、兽、草、木、金石,四行斯属自是也,立之品者。物之不能立,而托他体以为其物,如五常、五色、五音、五味、七情等是也,斯属依赖之品者。”
由这个原则来看理,那么“若太极者,止解之所谓理,则不能为天地万物之原矣。盖理亦依赖之类,自不能立,曷立他物哉?”由于理不是自立者,它无法成万物之本原。
艾儒略在《万物真原》中也遵循着利玛窦这一思路,以“自立者”和“倚赖者”区别为其依据,来判定“理”的性质。他说“凡物共有两种,有自立者,有倚赖者。自立者,又有二种:有有形者,如天地金石人物之类;有无形者,如天神人魂之类。倚赖者,亦有二种;有有形而赖无形者,如冷热燥湿、刚柔方圆、五色五味、五音之类;有无形而赖无形者,如五德七情类。夫此自立与倚赖两种,虽相配而行,然必先有自立者,而后有依赖者。设无其物,则无其理,是理犹物之依赖者也。无有形之体质,则冷热燥湿、刚柔方圆、五色五味是五俱无所着。无无形之灵,则五德七情亦俱泯于空虚,而谓理能物乎?即云天地之理,理神鬼有神鬼之理,亦从有生之后,推其然;若无天地人物神鬼,理尚无从依附,又何能生生物乎?”(转引自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3页)
理不是实体,其虚空,所以结论必然是“或曰,气不能自分天地万物,固已;然气中有理,理能分气,造天地万物之功,理之功也。曰,不然此乃非理之说也。理也,道也,皆虚字耳,何以能生物乎?”(同上,第142页)
第二,理不具有灵觉功能。如果上面是正面论述,这一条是反证。理既然是虚空无灵觉,它怎能派生出有灵觉万物呢?利玛窦说:“理者灵觉否?明义否?如果灵觉明义,则属鬼神之类,曷谓太极,谓之理也。如否,则上帝鬼神夫人之灵觉由谁得之乎?使理者以己之所无,不得施之于物以为之有也;理无灵无觉,则不能生灵生觉。谓子察乾坤之内,惟是灵者生灵,觉者生觉。自灵觉而出不灵觉者,则有之矣;未闻有自不灵觉而生有灵觉者也。”(《天主实义》第二篇)
龙华民在《灵道体说》中引出宋明理学的“道体”同基督教的神学本体的十大区别,其中第七条的区别在于:“道体”,即理无明悟,而灵魂是有明悟的,他说:“道体冥冥,块然物耳,无有明悟,不能通达。灵魂则有明悟,而能通达天下之理,追究吾人自何处来,向何处去,并能识我性命根本之根本。”(《转引自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1页)
在做这一批判时他把原儒与宋儒区别开来,因为在孔子那里“太极”并不是他的根本性概念,而在宋儒那里,太极是本体的,太极生两仪,二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由此推演万物产生。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就提出这样的问题,他说来华多年,读遍经书,只听到过先君子敬恭于天地之上帝,未闻有尊奉太极者。如太极为上帝万物之祖,古圣何隐其说乎?孙璋(Alexandre de la charme,1695—1767)也说“孔子何不之知太极?……孟子曰:‘存心善性’,何不云以所以事太极?”(《性理真注》)
太极为何不受传教士们喜欢呢?太极无灵性?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理不具有人格功能。龙华民认为:“道体无意无为,听其使然而然,又不得不然,是谓有受造之能,而无创造之能。灵魂者自有主张,行止由己,不受强制于物。”这点明了理是被动的,而灵魂是主动的,另外,“道体本为自如,无德无恩,亦无功罪。灵魂能行德恩,亦负反功罪”。这说明理是无德性的,德性是人格的表现。最后“道体自无福,自无祸,不赏不罚。灵魂则能行善恶,能受赏罚”。(《灵魂道体论》)宋儒中的理是一种哲学的抽象,朱熹把其规定称为是“无形迹”、“无情意”的精神本体。这样和具有人格特点的上帝是完全不同的,就此,龙华民的批评也是对的。
龙华民等人心中的本体是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体,是一个人格神,它具有创世之功能,有行善恶性之德心。正如利玛窦所说:“如尔曰:理合万物之灵,化生物,此乃天主也,何独谓之理,谓之太极?”(《天主实义》第二编)
三、中西哲学之比较
今天我们来重新反思这场中西哲学之争,可以看出,尽管来华耶稣会士广交儒友,读遍经书,但对宋明理学的理解仍有很大的距离。一方面,他们的确看出了中西哲学之不同,差别之大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他们的许多批评是隔靴抓痒,文不对题。从前者来说,他们强调“理”不具有人格神的特点是十分准确的。基督教作为一神教,其重要特点在于神通过耶稣这个人的形象来显示出来,这就是所谓的“道成肉身”,上帝以基督的肉体显示了自己。正因为这样,人格神是基督教的根本原则。耶稣是“起初就与天主同在的圣言”,“圣言就是天主”;耶稣也是“不可见的天主的肖像”,是“天主光荣的反映,是天主本体的真象”这样耶稣是一个有其生活历程的可感受的形象。上帝这种本体被人格化了,神被人格化了。
凡是读过《新约》的人,便能感知到基督的精神。他一降于世界就受苦,直到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以自己的精神感召人们。正因这样,人格神是基督教的根本所在。
在基督教与希腊哲学相融合以后,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上帝的存在通过理性化的论证而更显示出它的哲学色彩,但人格神的特点始终是基督教的根本特征。
中国文化自春秋以后已摆脱了原始宗教色彩,经过汉代经学、魏晋玄学的一系列演化后,到宋明理学时已发展到它的最高阶段,到朱熹那里,他在二程的基础上,把儒家的道德伦理,心性之学与道家的本体论和佛家的思辨结构已经融为一体,他创造了儒家思想发展史上的最完备的哲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理成为天地万物的最高实体,“宇宙间,一理而已”。(《朱子文集卷十七》)宋学与汉学之别就在于把汉学那种粗糙的神学目的论进一步向理性化推进。
在董仲舒那里,天人感应,“天是人之祖父”(《春秋繁露》)。他还说“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阴阳位》)这表明“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阴阳义》)董仲舒采取了阴阳家的思想,从天与人的关系中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提供了一套理论的说明。
他的学说一方面是原儒学说的发展,使儒家向宇宙论方向推进,尤其是奠基了儒家作为国家学说的地位。但同时,他的学说不精致,天人关系仍未讲透, 天仍有人格神的一面。 天究竟是“主宰之天”的天(Heaver),还是“自然之天”的天(nature),在他这里还讲得不太清楚。冯友兰先生曾引用过金岳霖的一段话,十分精彩。“我们若将‘天’既解为自然之天,又解为主宰自然的上帝之天,时而强调这个解释,时而强调另一个解释,这样我们也许就接近了这个中国名词的几分真谛。”(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1996年版,第166 页)理学在一定意义上是汉学的改造,理是一种精神的实体,世界万物存在的根据。理的根本特点是其抽象性,“理无形也,故假象以显义”(《二程集》,第695页)朱熹说“若理则只是个净洁空阔的世界,无形迹, 他却不会造作。”(《朱子语类》卷一)所以,在宋学中人格神的因素已经完全被排除了。
利玛窦等人在中国几十年,熟读经书,但一讲到哲学,讲到形而上学,仍是用西方的概念来理解,可见文化理解决非易事。中国文化的这种“伦理本体论”从利玛窦开始直到黑格尔都无法理解,黑格尔干脆认为中国无哲学。而不理解中国哲学这一特点,便无法抓住其本质。这是中西哲学之重大差异,如何对待这个差异,在中西哲学交流史上可总结的经验教训不少。
因此,利玛窦等人认为理不具有人格神的特点,是正确的,在这种批判中,表现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非宗教特征的认识。
作为后者,传教士批评的不足可以从二方面表现出来,其一,不理解理的理性本体论特征。在对“理”的这一类批评中,他们所使用的所谓“自立者”和“依赖者”的理论,实际上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唯名论的观点。中世纪的“唯实论”和“唯名论”之争是从柏拉图的理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学说中引申出来的,“唯实论”赞同柏拉图的观点,认为一般概念先于事物的存在,理念在先,存在在后;而“唯名论”,认为一般概念仅仅是个别事物的名称,它不先于事物,也不在事物之中,而是在事物之后。
当传教士们认为理不是“自立者”,而只是“依赖者”时,他们完全没有认识到“理”在抽象形态上是和他们所赞同的亚里士多德理论中的“质料”与“形式”二基本要素中的“形式”是十分近似的。既然“目的因”可以作为最终的原因,既然“灵魂”可以作精神实体,为什么“理”为万物之本不行呢?
“理”在中国哲学中就是“自立者”,“要之,理之一字,不可以有无论,未有天地之时,便已如此了也。”(《答杨志仁》,《文集》卷五十八)因而,传教士们用“自立者”和“依赖者”的理论来批“理”,有些文不对题。所以,他们仍未真正理解“理学”。
其二,忽略了“理”的伦理功能。传教士认为天主具有扬善惩恶之功能,而理不具有,它只是“虚”。这很明显地暴露了传教士并未根本上理解宋明理学。“理学”本是封建伦理思想的本体论化,把中国的传统儒家伦理思想提高到宇宙论的高度,如朱熹所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而为性。其张之如三纲;其纪之如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子文集·读大纪》)
由此可见,中国哲学作为有别于印欧语言文化系统的理论思考,有着它的独特特点,如何认识中国哲学的这一特点,始终是西方人的一个难点,利玛窦等来华传教士对这个问题虽有所察觉,却还未能真正理解,但他们毕竟迈出了第一步,这是历史性的一步。这一步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思考和总结。
标签:儒家论文; 利玛窦论文; 传教士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太极中国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明清论文; 读书论文; 太极论文; 国学论文; 基督教论文; 耶稣会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