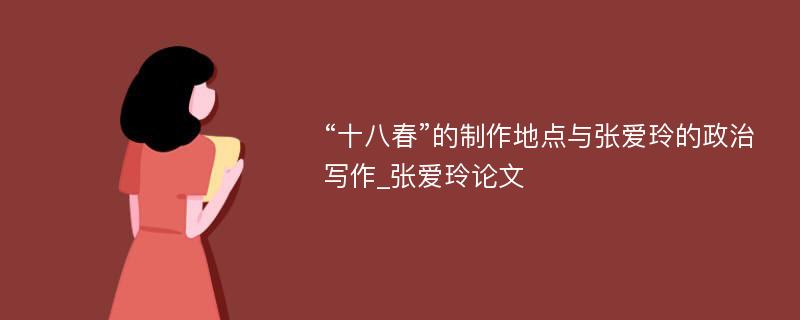
《十八春》的生产现场与张爱玲的政治化写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场论文,政治论文,十八春论文,张爱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十八春》到《半生缘》:漫漫十八春 作家艺术生命中的“第一次”,往往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性意义,如处女作、第一部别集之类,往往都是最能够激发研究者热情的对象,一如《狂人日记》《尝试集》等,文学史叙述一般不会轻易放过,并且浓墨重彩详加论述者居多。然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认真谈论《十八春》的却不多,尽管它是张爱玲的第一部长篇创作。后来张爱玲在美国根据《十八春》改写的《半生缘》,反而为研究者所重视。① 究其原因,一方面,张爱玲本人对《十八春》的态度十分暧昧;另一方面,这是她继《传奇》之后,在大陆完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但作品人物的身世命运、生活环境与作品的思想基调、风格等却与此前的《传奇》大相径庭,故不被研究界认为能够作为张爱玲“风气”②、趣味和水准的代表。 其实,张爱玲心底里非常看重《十八春》,正像和张爱玲交谊甚笃的夏志清所言,“她对这部作品极为心爱”③。《十八春》最初在《亦报》连载,如今已是文学史的常识,无须赘言。但从《十八春》到《半生缘》一路走来,过程却十分绵长,历经了漫漫18春。是张爱玲有意为之抑或巧合,没有确切证据之前,笔者不予置评。简单回溯《十八春》到《半生缘》的曲折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段。一、以“梁京”为笔名,在上海《亦报》边写边发表的时期。始于1950年3月25日,终于1951年2月11日,《十八春》共分317次连载完毕。二、完成初版本的修改与出版(1951年2—11月)。《十八春》连载完毕后,作者自补“漏洞”④。1951年11月,《十八春》单行本与读者见面,出版者、发行者同为“亦报社”,著作者署名“梁京”,印数2500册。⑤三、定居美国后,再次全面改写、修订,先在《皇冠》月刊连载,后以《半生缘》为最后定名,在台湾出版、行世。 现代文学史与出版史上,像这样耗时费力,谨慎修订、反复改写一部20来万字旧作的个案,除此之外,或许很难再找出第二个例子。作者若不是特别珍视,根本就不会如此煞费苦心。 然而,《十八春》实在又是作者难以释怀的一块“心病”。1961年秋,访问台湾时,张爱玲便向接待她的台湾作家王祯和透露打算修改《十八春》的想法。⑥在张爱玲与友人夏志清的通信中,读者还可以清楚看到其心头的矛盾和纠结。1966年10月2日她在给夏的信中说:“在大陆曾写potboiler《十八春》,在小报上连载后出过单行本,过天行李到后,等我拿出来看看,如有可能性,当寄来给你看。”⑦(potboiler,英语,为糊口而写的意思)很显然,是她首先向夏志清提起《十八春》,并许诺寄给他看。或许她想获得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学者认可并寻求知音。但过了十来天,张爱玲的主意又变了,她很委婉地给夏做了一些解释,说“长篇大论,婆婆妈妈的”,“末尾需加整理,一时不能寄来”。⑧作者丝毫不掩饰自己对《十八春》的“不满”。但为了藏拙,不得不为自己寻找借口,避免陷于难堪,故在写给夏的信中又说:“《十八春》原稿跳来跳去,不自己校更会脱落整段。倘来不及,宁可且慢登。”⑨此信写于1967年11月25日,距离上次说寄《十八春》给夏志清,已经过去一年多。张爱玲心里的如意算盘可能是倚重夏志清的学者名望,推升其作品的社会影响力,以便她在海外的中文刊物上发表作品,赢得读者。既是为了解决生计,也有展示个人实力的考虑,同时为她在文学市场站稳脚跟积累深厚的资本——她本来就是在文学市场里成长起来的职业作家。然而,到了1969年,夏志清依然还是没有看到《十八春》。倒是看到这年1月3日张爱玲给他的信中这样表示:“《十八春》我那本拆散了,插入改稿连载,不然寄给你看。”⑩事实是,《十八春》在台北《皇冠》月刊早连载过了,起止时间是1968年2—7月,不过张爱玲没有再用《十八春》的题名,而是改作《惘然记》。换言之,张爱玲已经将《十八春》更名为《惘然记》在《皇冠》月刊连载结束半年后,她才向夏志清说出实情,而且,看起来还挺难为情似的——“不然寄给你看”。其实,这只是搪塞夏志清罢了,并借此掩饰自己不想让夏看到《十八春》“真容”的内情。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夏志清用了超过鲁迅的篇幅来讨论张爱玲,真心欣赏其早熟的文学成就。可是,只怕他没有想到一代才女忽悠人的圆熟技巧也同样卓绝超群。张爱玲蓄意护短、虚与委蛇的“精明”做派昭然可见。令人不禁想起她的名言:“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倘若认为在张爱玲“也许是不甚健康的”夫子自道中,颇有几分自知之明,蕴藏着自省意识和自我批判精神,那就误会了。接着一句“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11)恰好又表露出其丝毫不掩饰生为上海人的自鸣得意与自我陶醉。 回到正题。改写、修订后的《十八春》作为张爱玲作品系列第六种,1969年3月,由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取名为《半生缘》。经历漫漫十八年,最初在《亦报》化名“梁京”发表的小说《十八春》,才最后定稿、定名,真正画上了句号。 二 “三角恋”故事穿上“翻身文学”的外套 张爱玲不满《十八春》,却还是喜欢、珍爱,且毫不掩饰,常常溢于言表,在与夏志清的通信中不时直接吐露与坦承。如一边说“写得perfunctory,没精打采的”(12),一边又有些小得意,称“《十八春》的戏剧性强”适合改编成电影,“可由一人兼饰姐妹俩正反二角”(13),承认虽然整体上有明显缺陷,但“部分地有两处我也还喜欢”(14)。自我炒作之嫌,不言而喻。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十八春》宛如张爱玲的一个孩子,因为长得不很理想,当妈的一方面视为心肝宝贝,疼爱有加;另一方面,又抹不下脸面,不愿给外人一睹孩子的真实面貌,羞于将她领到世人的面前。所以,张爱玲在信上反复说要寄书给夏志清,最终不了了之,私底下却在精心修改。经过一年多改头换面的装扮,就成了坊间流传的《半生缘》,原著《十八春》反而不为读者所知。 笔者认为,设若研究者和后世读者都忘掉《十八春》,缄口不再提起,仿佛张爱玲从未写过这小说,这样,反而恰好是作者想要的结果。进一步说,张爱玲求之不得的美事,最好是研究界和偏爱她的读者,都以为《半生缘》是一部新作。按常理说来,承诺给看,却又始终不践约寄《十八春》给夏志清,喜欢却不愿其直接面世,藏拙之外,一定还有不愿被触碰,害怕被人揭破的秘密。 刚出道时,张爱玲所写主要是上海弄堂殖民文化环境下小市民的日常生活和清末遗老的家族故事,热衷且擅长演绎小儿女的三角、多角恋爱戏,同时声称“我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15)。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新的政治转型面前,张爱玲抛开轻车熟路的情爱叙事,以《十八春》和《小艾》(《亦报》连载,署名“梁京”)为转型,融入国家意识形态主流话语,给工农兵画像、立传,借文学手段诠释新政权的合法性,紧跟新的执政者,参与建构新的国家认同,终结了其“写文章不涉及政治”的历史,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敏锐的政治嗅觉。貌似孤傲不群、清高自持的才女,一旦投入政治的怀抱,也有不俗的表现。 拿《十八春》为例,小说以1949年中共接管上海为时间界碑,叙述主人公顾曼桢在“新”、“旧”社会两种不同的人生际遇。1949年以前,旧的无能的统治集团,害苦了善良、淳朴的顾曼桢,使她生活在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饱受熬煎。共产党来了,才带她逃离苦海,重见光明,焕发新生,走出个人狭小的生活圈子,成为了“革命的大家庭里的一员”。人物命运的前后比照,可以这样认为,小说文本的意义指向,显然在于礼赞新中国,诅咒旧政权,服务新的执政当局,以文学的手段证明,中国共产党取代国民党执政是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就这个意义维度而言,《十八春》堪称“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典范”之作。小说主线和叙事动力,是顾曼桢、石翠芝与许叔惠、沈世均的多角恋故事。叙事的框架和结构,人物的身世、命运与终局,都没有超越《白毛女》的文本模式——大光明、大团圆的收尾。夸张一点说,《十八春》其实就是上海版的《白毛女》。文学史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情呼唤的“政治正确”的“代表”,大抵不过如此。 再看,继《十八春》之后,在《亦报》连载的《小艾》——张爱玲在大陆期间创作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16)小说以官宦之家的婢女小艾从童年到青年的人生际遇为叙述框架,意在建构新政权认同的文本意蕴,清楚了然。六七岁就被卖入席家做婢女的小艾,正值豆蔻年华惨遭主人奸污,落下妇科顽疾后,丧失了生育的能力。上海解放后,共产党掌管的“为人民服务”的医院,终于治好了小艾的沉疴。解除病痛获得新生的她很快成了幸福的“准妈妈”。小艾和丈夫冯金槐在欢呼“他们已经完了,现在是我们的世界了”的喜庆氛围中,小说画上了句号。无疑,这是典型的国家意识形态叙述话语,即草根阶层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以上可知,《十八春》及随后在《亦报》连载的《小艾》,开启了五十年代张爱玲有意味的政治化写作旅程,成为1950年代初期当代中国文坛“翻身文学”、“服务文学”的新样板。桑弧的提醒,值得关注。他说:“我读梁京新近所写的《十八春》,仿佛觉得他是在变了。……在思想感情上,他也显出比从前沉着而安稳,这是他的可喜的进步。”同时,他还说:“我虔诚地向《亦报》读者推荐《十八春》,并且为梁京庆贺他的创作生活的再出发。”(17)就《亦报》连载的《十八春》和《小艾》而言,给三角恋爱故事穿上“翻身文学”、“工农兵文学”的外套,大概便是张爱玲“在思想感情上”的“可喜的进步”。“创作生活的再出发”,意味着从写饮食男女向“为政治服务”转型。 三 读者参与生产的文本 生长在洋场社会,没有任何底层生活经验的张爱玲,志愿服务工农兵,为工农兵画像、立传,如何成为可能?《亦报》里高度政治意识形态化了的连载小说,与写《传奇》《流言》的张爱玲,怎么会是同一个人?我认为,《亦报》里以“梁京”名义发表的小说,不同于张爱玲个人的独立著述,而是读者和作者并置在同一话语空间,读者群体深度介入,共同参与完成的文本。返回《十八春》的生产现场,便可了然。五十年代初,文学生产被强制纳入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生产的轨道,框定在计划经济的套子里,卖文为生的张爱玲,倏忽之间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自由的文学市场。“服务工农兵”政治话语成为统领文艺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教条。新形势下,张爱玲改变个人偏好,给体制外仍旧按市场化模式运作、由民间资本经营的《亦报》写连载小说。按张爱玲的说法,当时是“在报上一边登,一边写,写到后来,明明发现前面有了漏洞,而无法修补,心上老是有个疙瘩”(18)。 问题正在这里。“一边登,一边写”的文本制作过程,即是文学的生产与消费并置在同一个话语空间的生产机制下,文学生产者的思想空间、情感空间不再完全独立,自主性和整一性受到破坏。易言之,文学消费与文学生产并置在同一话语空间时,文学消费者实际上也参与了文本生产。尽管无法准确量化《十八春》生产过程的读者参与度,但说《十八春》的故事由《亦报》读者和张爱玲(梁京)共同完成,大体能够成立。 《十八春》刊发前后及连载期间,《亦报》读者频繁发表阅读感受,并按自己的意愿和偏好安排小说人物命运走向和故事结局。笔者收集到不少于21篇,点评《十八春》和张爱玲/梁京的长短不一的文章(19),其中有文坛耆宿周作人分别用笔名“十山”和“持光”发表的文章两篇(20);张的恋人,其时在演艺界已经小有名气的电影导演桑弧用笔名“叔红”发表的文章两篇。此外,还有《亦报》主编唐大郎的捧场,《亦报》专栏作家齐甘的品评。 桑弧与张爱玲,一个导演,一个编剧,曾有过很默契、愉快的成功合作,1949年之前的出品有《不了情》《哀乐中年》和《太太万岁》等影片。《十八春》刊出前一天,桑弧用“叔红”的笔名在《亦报》发表《推荐梁京的小说》。1950年,桑弧编导的《太平春》公开上映,张爱玲撰写影评《年画风格的〈太平春〉》发表在《亦报》,对影片给予高度好评。(21)既然如此,不妨先看看《十八春》在《亦报》连载约半年之时写的《与梁京谈〈十八春〉》。桑弧说: 自从曼璐设计让祝鸿才污辱了曼桢以后,无数《十八春》的读者都义愤填膺,一方面为曼桢掬同情之泪,一方面对曼璐和祝鸿才发出最黑最黑的诅咒。有很多读者写信给梁京,认为非把这一双狗男女枪毙不可,同时也吁请作者“笔下超生”,让曼桢的悲剧中止发展下去。 我昨天去看梁京,她指着桌上的一些读者的来信对我说,她没有想到读者竟这样关心她小说里的人物的遭遇。这使她高兴,但也使她惶恐,因为她担忧人们对她有一种误解,以为她故意把曼桢陷入最悲惨的境遇,用廉价的手法骗取好心肠的读者的眼泪。 我说,“一般读者似乎对曼璐更比对祝鸿才来得憎恨,因为鸿才的卑鄙无耻原在意中,然而人们对于曼璐的陷害同胞的曼桢,总觉得毒辣过分,不知你自己以为如何?”(22) 一方面,读者纷纷写信给“梁京”,另一方面,桑弧直接探访作者,都直截了当向作者表明《十八春》的读者所乐意看到的顾曼桢的命运结局。何况还有“不但读者希望她(指顾曼桢——本文作者注)坚强地活下去,作者也没有权利使一个纯良的女性在十八年后的今天的新社会里继续受难”(23)的坦诚相告。与其说这是桑弧贡献给张爱玲的善意建议,倒不如说是桑弧代表读者明确替《十八春》设计好了人物的命运及其结局。前文已经说过,《十八春》还未和读者见面,桑弧就为“梁京”“在思想感情上”“可喜的进步”公开贺喜。这等于既给张爱玲洗脑,也为她的新作预先“定调”。 另一读者的文章,一点不含糊地指出:“我也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梁京笔下的曼桢,最后应该是健康的、愉快的,让那些哀愁、怅惘、惋惜掷给那个不彻底的、妥协的、爱面子的、世均去享受吧?”(24) 《亦报》专栏作者齐甘讲述了发生在身边的一个小故事。他说,有位邻居是30多岁的胖太太,隔几天就要到他家借读《亦报》。某日,这位胖太太送还前几天借过去的《亦报》,平素和气的她,表现令人意外: 忽然神色很有异,把报纸扔在桌上腾的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竟叫了起来:“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我们面面相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又把报纸恨恨地打开,指指恰巧登到第163天的《十八春》,对我吼着说,她恨不得两个耳刮子打到梁京脸上去! 我明白了,她是因为《十八春》写到鸿才强占了曼桢,不胜其愤慨了。(25) 诸如此类的小文章,频频见诸《亦报》。可见,读者并非完全被动地接受张爱玲单方面给定的人物与故事。受市场法则支配,曾以文学市场维持生计的职业作家张爱玲,大概没有理由对读者的接受反应与消费诉求爱理不理、我行我素。“再出发”的宣告业已在前,那么,投读者所好,正是人情之常。而且,时机恰好又在风云际会的社会政治转型之际,只有求得“政治正确”,文学存在和公开生长才成为可能。同时,这阶段也是作者渴望新变,寻求突破的敏感时期,诸如此类的读者反应,必定作用于文本生产。尤其是熟悉作者,且如桑弧这样的文学内行,三言两语的品评,无疑都将改变作家的运思和叙述路向等。就《十八春》言之,《亦报》读者从个人的接受期待出发,根据自身的文学经验、生活阅历,以书信、谈话和公开发表阅读感受、短小评论等多种方式深度参与了《十八春》的文本生产。换句话说,《亦报》读者与张爱玲共同完成了小说《十八春》。因此,这是有众多读者参与生产的一个文本,不可和张爱玲的独立撰述等量齐观。 四 张爱玲政治化写作的投机性与报复性 不仅如此,上海新的执政当局也深度介入了《十八春》的生产过程。 自尊敏感、名利意识重是张爱玲的个性特质,20多岁就发表《必也正名乎》(26),嚷着“出名要趁早”(27),其富有强烈的现代权利意识可见一斑。或许这是受了殖民地文化濡染、浸淫的结果。曾经,政坛局势不管怎样动荡不安,政治气候无论如何晦暗不明,她从不害怕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公众视域。上海沦陷时期,给日本人扶植的刊物写稿,追随胡兰成,与之同居又分道扬镳。这些,在众人看来,都是丢人现眼,很不名誉的事情,然而张爱玲并不隐瞒——事实上也瞒不住。尽管胡兰成受追捕时,张爱玲也曾过了一段风声鹤唳的日子,但她始终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依然以“张爱玲”的大名发表新作。重印旧著,编写的电影剧本《太太万岁》,照样顺利搬上银幕。(28)一句话,“张爱玲”三个字没有影响她作为公众人物一直活跃在大众视域里。 日本人投降,国民党政府垮台,应该是张爱玲驰骋文学天赋的大好时机。然而,事实恰好出乎人们的预料。共产党接管上海后,文化/新闻/出版/印刷等,全部实行军事管制,文化/图书市场重新洗牌。原来的报纸、期刊、书店,不论官办、私营一律关停,经新政府审查后获准重新登记注册者才能出版、发行、营业。靠市场为生的张爱玲,眼看几乎要断了生路。当时的《文汇报》《新民报》与由《申报》改组后的《解放日报》等,审稿、用稿都十分严苛,有很多禁忌,自然来稿一般很难被采用,报纸上也极少发表文艺创作,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章或讲话,经常在报纸上唱主角。所幸,此时有两家小报——《大报》和《亦报》获准创刊,这是共产党接管上海后,半体制化的两家民营报纸。而且,其选稿、用稿尺度宽松得多,办报主体大多是那些未被体制正式收编的报人、自由撰稿人。 棘手的问题是,《传奇》《流言》出版之后,张爱玲已是声名显赫的当红作家。1947年《太太万岁》上映时,叫好又叫座,票房十分红火,却遭遇猝不及防的挞伐(29),张爱玲的声名更高了,但同时却成了一个不宜公开露面的敏感人物,她的名字显然成了禁忌。“梁京”因此悄然问世,并带着耀眼的光环——《亦报》专栏著名作家,广受读者追捧的小说家,上海第一次文代会代表。(30)总之,“梁京”取代“张爱玲”频频出现在彼时上海的公共文化生活。 《亦报》虽然只是一家民营小报,但背靠新政权支撑是明摆着的事实。资料显示,主《亦报》笔政的龚之方、唐大郎,由当时上海军管会文化委员会头号人物夏衍圈定,《亦报》的出版用纸,由军管会特别批准。 知情人士回忆,张爱玲以其年轻、卓尔超凡的文学才华,深得识才、惜才、爱才的上海文化宣传教育界的主事者、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部长夏衍欣赏。“当年没有一个革命作家敢承认张爱玲”的时候,夏衍便率尔坦承“她是写短篇小说的能手”,不仅他自己喜欢张爱玲的小说,还介绍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去读她的作品。(31)为了挽留张爱玲,并使其抛弃顾虑,尽力为国家服务,1950年代初,夏衍曾在上海市军管会文化委员会的重要人物姚溱、陈虞孙两人亲自陪同下,以朋友间家庭聚会的名义,秘密约见过张爱玲,地点在沪上某富裕人家的私人厨房。受邀前来聚谈的沈毓刚还清楚地记得,那天的“菜很精致”,饭却“吃得有点尴尬,谁也没有说多少话”。据策划操办的龚之方、唐大郎两人后来的“说法”,安排此次餐叙是因为“有点事请示领导,同时,夏衍同志想见见张爱玲,并托他们两人劝劝张爱玲不要去香港”(32)。 餐桌上都说了什么,沈毓刚没有述及。但张爱玲深得夏衍及其幕僚、友人的暗中呵护,却是不争的事实。由此推知,离沪赴港前,张爱玲化名“梁京”写连载小说在《亦报》刊发,应邀出席上海市第一次文代会,大概都与此次餐叙有某些关联性。龚之方个人的回忆,虽然没有明确述说夏衍与张爱玲晤面的经过和情形,但直接确证了张爱玲出席上海第一次文代会是夏衍画了圈圈的事实,“1950年夏天,上海举行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代表中赫然有张爱玲的大名,这显然是夏衍为她安排的。”(33)编发过张爱玲作品的柯灵,和她有过一些交往。据柯灵说:“抗战结束,夏衍从重庆回到上海,就听说沦陷期间出了个张爱玲,读了她的作品。解放后,他正好是上海文艺界第一号的领导人物。这就是张爱玲出现在‘文代会’上的来龙去脉。”(34) 上海第一次文代会代表的名字都登在《解放日报》上,“梁京”的名字也在其中。(35)可见,“梁京”是化名,并非只在写作、发表文章时才使用的笔名,是直接取代“张爱玲”公开使用的名字。会上,柯灵、龚之方等都注意到了,她不穿“延安装”(在《十八春》里叫做“列宁装”),而是“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坐在会场的最后一排座位。(36)严肃的政治场合,行止异于多数人的“梁京”,必定格外引人注目。 为应对朝代更替的政局世情,委曲求全换姓更名,对于重名、爱名,且又名噪一时的张爱玲,想必十分排斥。埋葬了沾染历史烟尘的“张爱玲”,实际上等于向世人昭示一个事实,曾经洛阳纸贵的著名女作家张爱玲已经“死”了,而此时,张氏刚踏上30岁,正好是艺术创造力最强大、最旺盛的年龄阶段,本来应该如旭日高升光照四野。就此偃旗息鼓隐姓埋名,无论怎么说,对她都是惨重的命运打击——才起了个头,她都还没红够呢!所以,1196期《亦报》里(主要在1950-1951年间),“张爱玲”的本名见诸报端至少在3次以上(37),此外,《亦报》还有文章故意称“梁京”已有《流言》等书销行于世。(38)这类“此地无银”的小伎俩等于明确昭示读者,“梁京”者,张爱玲也。笔者以为,这是用心呵护张爱玲的各方人士,精心谋划用来测度读者反应的手段和技巧。 至此不难明了,《十八春》的问世和张爱玲化名参加上海第一次文代会,全在政治权力操控下按部就班地进行。 《十八春》后,张爱玲仍旧以“梁京”之名在《亦报》上连载中篇小说《小艾》。可是,直至1952年女作家离境出港,“张爱玲”三个字再没有在《亦报》上出现过。张爱玲再有才华,“政治正确”的《十八春》《小艾》写得无论如何精彩,新的执政当局,都没有准备接纳她的意思。有柯灵的回忆为证。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成立时,夏衍拟邀张爱玲当编剧,就有人直接反对(39),夏衍也改变不了张爱玲的命运。偌大的上海已无她的栖身之地,政局的发展显然令生存空间本来逼仄的张爱玲越发艰难与惶恐。压抑自我,放弃个人立场,甚至完全听命于新的政权,然而,个人处境并不因此向好。她后来义无反顾地出走,与此不无关系。 如前所述,张爱玲在给夏志清的信中辩称,写《十八春》出于糊口。关于《小艾》,也可作如是观。她曾说:“我非常不喜欢《小艾》。”(40)事实上,不满自己的创作,并不是她要表达的全部意思。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对那些从尘封的故纸堆里翻出她的旧作,不经本人同意擅自重印的好事者表示愤慨。在笔者看来,《小艾》的“遵命”和“御用”气息更浓烈,“为糊口而写”的谄媚投机意味远在《十八春》之上,前面已经说过,在此不赘。张爱玲不喜欢《小艾》最主要的原因,大概在此。前面所述,《十八春》登完后,回头再看“心上老是有个疙瘩”也有同样的意味,只是没有明说罢了。 假如说,时易世变之际,《亦报》里张爱玲的政治化写作,是个人的一次误判,因年少轻狂不小心上了政治的当。那么,离沪赴港后创作的《秧歌》却与《十八春》《小艾》唱起反调,完全颠覆与改写了执政党与新国家的形象,完全否定共产党所领导和发动的“土地改革”。继而,坦然欣然接受来自国际、国内反共势力的资助,听任中共敌对势力的摆布,按他人预先拟定的大纲,完成《赤地之恋》。(41)对此,又当如何解释呢? 我以为,张爱玲急功近利、沽名钓誉的投机心理,实在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怪不得势利无情的政治。譬如《十八春》,她有自己的一套说法: 如果读者读到曼桢被辱的一章而有一种突兀或不近人情的感觉,那是她写作技术上的失败。但是她仍要说,曼桢这一典型,并不是她凭空虚构的鬼话。与其说曼璐居心可诛,毋宁说她也是一个旧社会的牺牲者。她自己不懂得劳动,她在风尘流转中捡上了祝鸿才而企图托以终身。一旦色衰爱弛,求生的本能逼使她不择手段地牺牲了曼桢,希望借此拴住鸿才的心。当然,曼璐为了慕瑾,对曼桢也有一些误会和负气的成分,但曼璐的陷害曼桢,最主要的理由还是应该从社会的或经济的根源去探索的。这并不是说曼璐的行径是可以宽恕的,但旧社会既然蕴藏着产生曼璐这样人物的条件,因此最应该诅咒的还是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42) 只看这番话,一个“跟跟派”的形象呼之欲出。这和写《倾城之恋》《金锁记》的张爱玲,判若两人。可见,她并不是糊里糊涂“上了政治的当”,而是心甘情愿被政治所用。当然,她同时也在利用政治,投靠政治,因而,张爱玲的政治化写作和她本人的政治立场或信念没有直接的关联,而实质是趋炎附势的政治投机行为。 其次,有资料披露,张爱玲到香港后,曾被怀疑“可能是共产党特务”(43),加之赴港前“忠而见疑”的不平际遇,驱使其政治投机心理或有变本加厉的可能,并朝着相反的路向运动,即投靠与共产党为敌的政治势力并获得庇护。此时,张爱玲的政治化写作除了继续投机之外,还混杂着多种成分。一是想自证清白,封堵指控她“可能是共产党特务”的别有用心之徒的嘴;二是为了泄愤,报复/反击对她存有芥蒂的执政当局。总起来说,相较于《亦报》里的连载小说《十八春》《小艾》,《秧歌》和《赤地之恋》除了具有相似的政治投机性和“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特征外,更多了一重报复性和攻击性。尽管各自服务的对象不同——前者为刚刚夺取政权的共产党“御用”,后者反转枪口,服务于反共、反华的政治集团,然而,“服务文学”的性质相同。 正是因为张爱玲歌颂新政权,礼赞共产党并非源自真心诚意,而是出于强烈的功利目的和投机性,所以,《十八春》里去了延安的许叔惠,到了《半生缘》就改成赴美国了。两部小说的结尾也迥然有别。前者,许叔惠从延安回到解放后的上海,顾曼桢、沈世均和石翠芝等人,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奔赴沈阳,豪情满怀地加入了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建设大军。后者的故事止于抗战结束。许叔惠从美国回到上海,亲朋故旧久别重聚,无限感慨,在“我们回不去了”的怅惘中,半生情缘戛然而止。 收入近年出版的《张爱玲全集》的《小艾》(44)和《亦报》连载的初刊本相比较,也有指向性相类似的删削和修改。前者叙述止于小艾的丈夫冯金槐抗战结束后回到上海,小夫妻得以团聚。后者则装有一条光明的尾巴——上海解放后,小艾一家过上了安定幸福的日子,永远告别了为人所驱遣,忍辱受气的非人生活。 五 结论 由上所述,可以认为,张爱玲以“梁京”之名在《亦报》发表的小说《十八春》《小艾》,是《亦报》编者和读者及彼时共产党主政上海的文化官员,共同参与生产的文本,是五十年代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生产新机制下,集体智慧合力“孵化”的“翻身文学”、“服务文学”的仿制品。此为张爱玲由市民趣味向政治化写作转型的“拐点”。然而,张爱玲的政治化写作,不过是给“三角恋”故事、鸳鸯蝴蝶小说披上“工农兵文学”的外套而已。此时,张爱玲的文本意图在于以文学为材质,参与完成建构新的国家认同的政治使命。 吊诡的是,张爱玲的热情与积极,并没有得到执政当局的接纳和赏识。赴香港后,转身“向右”,倒戈逆袭,写作《秧歌》和《赤地之恋》,改写执政党和新政府形象的同时,也颠覆了《亦报》期间,故意装扮成听话的“党的女儿”的公众形象。既想撇清与中共的瓜葛,也暗含宣泄愤懑,以小说报复/反击新政权的意思。整体上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张爱玲的政治化写作,无关政治立场和政治信念,也不能代表其真实的文学趣味和艺术观念。其意在于全身避祸,牟取名利。所以,她答应寄《十八春》给夏志清看,结果却食言,反复修改后,定名《半生缘》,几乎等于亲手埋藏《十八春》,洗刷污秽的意图自不待言。尤其在国共对峙,中美“冷战”格局中,设若《十八春》和《秧歌》同时置于夏志清和公众面前,人们将会怎样评说张爱玲的人品和文品?缘于此,死守自己曾经不光彩的国共两党“通吃”的秘密,掩盖个人的投机行为,尤为紧要。这既是维护个人尊严和体面的需要,也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 综观而言,缺少政治操守和个人立场的张爱玲,在国际、国内不同政治集团之间首鼠两端,关系暧昧又紧张,明知政治投机需要付出成本与代价,却来者不拒,失掉的不只是尊严和人格,实在不足为训。置身纷纷攘攘变动不居的时代大潮,把定自我人生路向,实属不易,然而无比重要。 ①由止庵主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张爱玲全集》,只收入《半生缘》而不收《十八春》。 ②李君维(即东方蝃蝀):《张爱玲的风气》,《人书俱老》,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67页。 ③⑦⑧⑨⑩(12)(13)(14)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52、50、53、84、114、115,60、53页。 ④高唐:《访梁京》,《亦报》1951年2月15日第3版。 ⑤据1951年11月亦报社出版发行的《十八春》版权页查证。 ⑥陈子善:《〈半生缘〉编后记》,《张爱玲集·半生缘》,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11)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张爱玲全集·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15)张爱玲:《有几句话同读者说》,《张爱玲全集·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63页。 (16)《小艾》载《亦报》始于1951年11月4日,终于1952年1月24日,共计81期。 (17)叔红:《推荐梁京的小说》,《亦报》1950年3月24日第3版。 (18)高唐(唐大郎):《访梁京》,《亦报》1951年2月15日第3版。 (19)陈子善在《〈亦报〉载评论张爱玲文章辑录》和《〈亦报〉载有关张爱玲文章补遗》两文中梳理出9篇和《十八春》及张爱玲有关的文字。参见陈子善《说不尽的张爱玲》,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37~149页。 (20)参见巫小黎《周作人与张爱玲:〈亦报〉空间的“互动”》,《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6期。 (21)(35)巫小黎:《张爱玲〈亦报〉佚文与电影〈太平春〉的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6期。 (22)(23)(42)叔红:《与梁京谈〈十八春〉》,《亦报》1950年9月17日第3版。 (24)明朗:《也谈〈十八春〉》,《亦报》1950年9月30日第3版。 (25)齐甘:《〈十八春〉事件》,《亦报》1950年9月11日第3版。 (26)张爱玲:《必也正名乎》,《张爱玲全集·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27)张爱玲:《传奇再版的活》,《张爱玲全集·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页。 (28)(29)巫小黎:《“战后”上海文坛:以〈太太万岁〉的批判为个案》,《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5期。 (30)张爱玲在《亦报》发表过至少2篇文章,2部小说。即《十八春》(长篇小说)、《小艾》(中篇小说)、《亦报的好文章》(散文,署名张爱玲)和《年画风格的太平春》(电影评论)。最后一篇未编入任何一种文集,详见拙作《张爱玲〈亦报〉佚文与电影〈太平春〉的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6期)。 (31)夏衍、李子云:《文艺漫谈》,《人民文学》1988年第5期。 (32)其佩:《也说张爱玲》,《新民晚报》1988年6月4日第6版。其佩即沈毓刚(1920-1999),笔名还有方晓蓝等。曾任《亦报》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1952年11月20日《亦报》终刊并入《新民报》(即《新民晚报》的前身)后,沈毓刚的关系也转入《新民报》,并曾先后担任过编辑主任、编委办公室副主任、副总编辑等职务。 (33)龚之方:《离沪之前》,《金锁沉香张爱玲》,关鸿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页。 (34)(39)柯灵:《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她》,《金锁沉香张爱玲》,关鸿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页。 (36)柯灵:《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她》,龚之方:《离沪之前》,《金锁沉香张爱玲》,关鸿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37)传奇:《梁京何人?》,《亦报》1950年4月6日第3版;高唐:《街头杂写》,《亦报》1950年9月15日第3版;《亦报的好文章》。见本文第16条注释。 (38)高唐:《街头杂写》,《亦报》1950年9月15日第3版。 (40)张爱玲:《关于小艾》,《张爱玲全集·重访边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页。 (41)(43)张惠苑:《张爱玲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2页。 (44)《小艾》经过删削后,收入《余韵》,但张爱玲未有任何说明和解释。本文参考了止庵编的《张爱玲全集·怨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