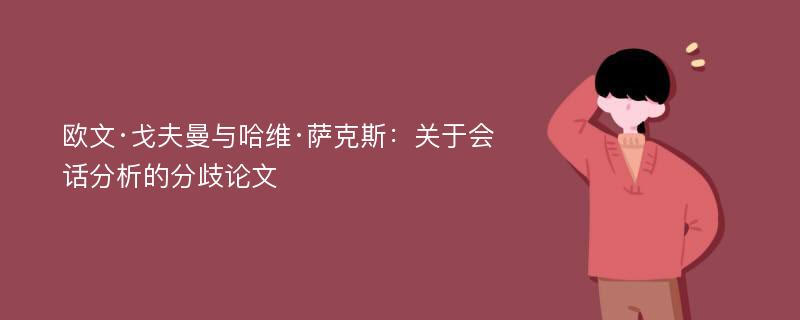
欧文·戈夫曼与哈维·萨克斯:关于会话分析的分歧
王晴锋
摘要: 哈维·萨克斯与欧文·戈夫曼在会话分析的问题上存在细微而重要的差别。哈维·萨克斯强调以原始录像或录音等方式收集数据,话轮转换、相邻对、序列性和补救是会话分析的基本构成。哈维·萨克斯等人还提出话轮转换的最简模型,即以两个要素和一套规则来描述话轮转换系统。而欧文·戈夫曼分析谈话的要素包括话步、情境和仪式等,他视谈话为焦点式互动,批评会话分析的相邻对概念,将会话分析中“提问—回答”的相邻对序列替换成“陈述—回应”模式,并采用“生产格式—参与”框架来探讨谈话互动。欧文·戈夫曼与哈维·萨克斯之间的关键差别在于:仪式是欧文·戈夫曼社会学的核心,互动的组织化是为了确保个体的仪式需要。事实上,哈维·萨克斯对语言的理解更接近于欧文·戈夫曼早期对互动的理解,而不是后期他关于语言的阐释。
关键词: 欧文·戈夫曼;哈维·萨克斯;会话分析;框架分析
哈维·萨克斯(Harvey Sacks) 是会话分析的主要创立者,可惜他英年早逝。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欧文·戈夫曼的互动秩序观念与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的影响之下,哈维·萨克斯和他的亲密合作者伊曼纽尔·谢格洛夫(简称谢格洛夫)、盖尔·杰弗逊(简称杰弗逊)等人创立了会话分析学。该学派主张通过录像或录音等方式收集原始数据,主要研究口头的对话,而不是结构完整、经过转换的书面语。会话分析与系统功能语法、篇章语言学、言语行为理论、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等都属于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的范畴。
欧文·戈夫曼与哈维·萨克斯之间的关系颇有些类似于弗洛伊德与荣格,后者曾是前者的得意门生,后又分道扬镳、自立门户。哈维·萨克斯的会话分析学与欧文·戈夫曼关于谈话的分析之间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并且第一代会话分析学的核心人物曾经是欧文·戈夫曼的学生。然而,欧文·戈夫曼对会话分析学的批评甚为尖刻。两者之间的过节与交恶要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的哈维·萨克斯还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生。1966年,欧文·戈夫曼拒绝参加哈维·萨克斯博士论文的综合考试,因为他认为哈维·萨克斯的论文中关于“成员资格类型”(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 的分析犯了“循环论证”的谬误以及过于学究式行文风格。①欧文·戈夫曼的这种态度对后来成为会话分析旗手的哈维·萨克斯造成很大的心理伤害。本文主要探讨哈维·萨克斯与欧文·戈夫曼在社会语言学领域所存在的重要分歧。与语言学家不同,二者同为社会学家,但又都对人际间的语言互动具有浓厚的兴趣,因此两者之间的比较也更具有典型意义。
一、哈维·萨克斯的会话分析结构
20世纪60年代,哈维·萨克斯和欧文·戈夫曼、加芬克尔等微观社会学家有过重要交集,尤其是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为哈维·萨克斯创立会话分析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因此,会话分析甚至被认为属于常人方法学。这一时期,录音器材的普及与运用也为研究会话提供了物质和技术基础。1963年,哈维·萨克斯在加芬克尔的帮助下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同时在洛杉矶自杀科学研究中心兼职。哈维·萨克斯对自杀预防中心的电话录音材料进行了研究,揭示了会话的相邻对和会话序列,从而逐渐发展出会话分析学。在哈维·萨克斯短暂的一生里,他没有公开发表系统性的研究专著,其思想主要通过三个方面得以保留、传播:一是他生前发表的若干论文,尤其是《会话中话轮转换组织的最简系统》;二是1964年至1974年间其所讲授的《会话序列的规则》这一课程的内容;三是在他去世之后,由其先前的合作者继承的一些观点。
哈维·萨克斯等人认为,话轮转换、相邻对、序列性和补救是会话的一般性特征,也是会话分析的四大基本构成要素。哈维·萨克斯虽然提出了话轮的概念,但是他并未对其下过明确的定义。话轮既可指成为说话者的机会,也可指说话者在下一个说话者开始说话之前所说的所有内容。相邻对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事物构成,它们包括:
(1) 两个话语段。
(2)话语要素的并置。
(3)不同说话者产生的每一段话语。相互关联序列的话语构成一种已然实现的相关性,它可以在相邻的话语之间获得,同时也部分的是说话者按次序生成的类型学之产物。在具体运作时,这种类型学将话语类型划分成“始发语”和“应答语”,将一个始发语与一个应答语合并成一个“配对类型”。“提问—回答”、“问候—问候”和“提供—接受/拒绝”是配对类型的典型例子。一个既定的序列由一位说话者产生的作为始发语的一句话和直接伴随着另一位说话者产生的话语——它是由一个应答语和来自作为构成该序列第一句话的同一配对类型构成。由此,相邻对序列进一步显示出其他的特征。
(4)各部分之间的相对次序,即始发语先于应答语。
通过前期建模时数据整理发现,优质窖泥的pH值多集中在6.0~7.5范围内,而质量一般窖泥的pH值多集中在5.0~6.0或7.5~8.0,当窖泥pH<4.5时,窖泥质量明显下降。pH值可引起细胞膜电荷的变化,从而影响了微生物对营养物质的吸收;也可影响生化反应过程中酶的活性[12]。3年窖泥的pH值较10年、30年的窖泥低,pH值缓冲能力较弱。随着窖泥年份增加,pH值逐渐稳定在5.0~6.0。
开初外祖母不肯,到后来,她说若是不让她读书,她是不出嫁的。外祖母知道她的心情,而且想起了很多可怕的事情……
(5)可鉴别关系,即配对类型的始发语与应答语的部分要素是相关联的。②
会话分析的关注点与欧文·戈夫曼非常相似,但仔细分析之下他们之间存在重要的分歧。在语言风格和资料来源上,哈维·萨克斯等会话分析学者使用真实会话的材料,他们强调严格的经验技术,主要使用互动事件或片段的录音或录像资料,而欧文·戈夫曼则广泛采用各种或虚或实的事例。哈维·萨克斯关注前后相继的序列分析,欧文·戈夫曼关注仪式秩序、印象管理或框架。欧文·戈夫曼认为,必须区分互动的仪式要求与系统要求,指责会话分析对非言语互动缺乏考量,而哈维·萨克斯则认为没有必要区分系统限制与仪式限制。哈维·萨克斯研究言语秩序的在地生成,强调话语的序列组织对意义的作用,指出只有在序列性的语境中才能减少话语与行动的不明确性,而这种意义的含糊性在理论上是无法彻底根除的。哈维·萨克斯关于会话组织的关联性序列秩序之承诺与共同投入的思想与欧文·戈夫曼早期关于自我的论述甚为契合,但欧文·戈夫曼对谈话的分析偏离了他早期的互动研究范式。在关于谈话分析的立场上,欧文·戈夫曼更像是传统的社会学家,而哈维·萨克斯则更像现代语言学家。
(1)对任何话轮而言,初始的话轮构成单位就是初始的转换关联位置:第一,如果话轮的构成采取“当前说话者选择下一个说话者”的方法,那么被选择为说话者的一方有权并有义务接下一个话轮而说话,而其他人则没有这种权利或义务,话轮转换发生在该位置,这种规则简称a。第二,如果话轮构成不采取“当前说话者选择下一个说话者”的方法,那么便会启动自选下一个说话者,但这不是必须的,最先开启者获得话轮权,话轮转换发生在该位置,这种规则简称b。第三,如果话轮的构成不采取“当前说话者选择下一个说话者”的方法,那么当前的说话者可以说话、但不是必须继续说,除非其他人自选为说话者,这种规则简称c。
(2)如果在初始话轮构成单位的初始转换关联位置,规则a和b都没有运作,而是运用了规则c,也即当前的说话者继续说话,那么在下一个转换关联位置将再次运用a至c的规则丛,并且在每一个接下去的转换关联位置反复循环,直到发生话轮转换为止。③
·以目标读者为中心的原则。即在品牌定位之前,充分考虑目标读者的特征,通过科学的市场调查了解读者需求,以求其定位与读者的需求吻合,并通过一系列的推广活动向读者传达这一定位信息,让读者感觉到这一品牌就是他们所需要的。
在欧文·戈夫曼看来,一切表意性行为都发生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他之所以反对会话分析,是因为会话分析认为谈话具有自主属性,谈话与情境适当性地被割裂。欧文·戈夫曼认为,“确实,前一个话轮很可能会根据当前的话语阐释提供一些背景……但是,前一个话轮永远不会是要求当前的说话者作为一种指涉框架来使用的唯一条件”⑭。对话中的某一句话与前一个轮次“必须在决定论的支持下进行研究,这就像任何即将开始谈话的人可获得的所有自由度能够用某种方法进行操作化处理、掌握、控制,并通过分析产生类型化的模式”⑮。谈话并不是信息表达的主要方式,“话步/行动步骤的变动”的概念使其他表意行为与谈话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欧文·戈夫曼并不认为存在统一的、结构化的情境。例如,演讲场景本身仅仅是一种临时建构,一旦演讲结束,演说者和听众马上回归到他们不同目的的情境之中。欧文·戈夫曼用他早年提出的框架分析理论来批评会话分析,他首先将矛头直指会话分析的基本分析概念——相邻对:假如一位言说者需要知道他的信息是否已经被接收,如果已经被接收的话,那么它是否被理解得当,而且假如一位接收者需要表明他已经接收到信息并且理解正确——假如这些都是作为沟通系统的谈话之基本要求——我们便有了使相邻对存在的最基本理由,即谈话促使双方间的相互交换。⑯
二、欧文·戈夫曼的谈话分析框架
欧文·戈夫曼试图创立一整套关于面对面互动的规则体系,他认为谈话的思想与会话分析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尽管欧文·戈夫曼早期的研究对会话分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他后期对日常生活中谈话组织的分析却受哈维·萨克斯和谢格洛夫等人的影响。欧文·戈夫曼对哈维·萨克斯的会话分析不乏欣赏之意,尽管他在著述中避免使用“会话分析”而采用“谈话互动”这样的表述。早在出版于1961年的《交遇:关于互动社会学的两项研究》一书中,欧文·戈夫曼已经提及哈维·萨克斯。⑤而在《公共场所的关系:关于公共秩序的微观研究》里,欧文·戈夫曼也很关注哈维·萨克斯的研究工作。⑥哈维·萨克斯等人的《会话中话轮转换组织的最简系统》与欧文·戈夫曼的《框架分析》都发表、出版于1974年,欧文·戈夫曼在此提出了关于谈话的基本理念,尤其是关于“参与框架”的思想。
注释:
在欧文·戈夫曼的社会学里,move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在分析一般意义上的面对面互动时,可以理解为“行为步骤的变动”,它是个体在面临着选择的重要时刻和机会时决定采取的行动。⑦他认为,语言和非语言的面对面互动都由行为举措的变动构成。它不是任何停留在行动者脑海里的观念、决定或表达,而是会对外部世界产生真实的有形后果(即导致生活情境发生具体改变)的行动步骤。⑧他将move定义为“行动者在采取行动的转折点上传达出来的一切”⑨,它包含了行动信息、仪式性尊重、面子工夫、沟通性约束以及框架指令等,所有这些都受“言辞适切的条件”⑩限制。另一种含义的move出现在分析语言时,它可以理解为话步,指任何谈话或其替代形式的充分延展,对个体参与其中的某些情境设置——诸如沟通系统、仪式限制、经济谈判和角色竞争等产生影响。⑪在欧文·戈夫曼那里,话轮是指在会话过程中控制发言的机会,而不是指在控制发言时所说的内容⑫,这一点与哈维·萨克斯有所不同。话轮是谈话发生的“槽缝”(slot),话步有时可能与句子或话轮重合,但是话步并不总是等同于话轮转换,同一个话轮可能包含多个话步,一次话轮转换可能发生多次话步。话轮转换使个体与他们的谈话相一致,而话步则使情境与谈话相一致。⑬欧文·戈夫曼认为谈话具有对话性,并不断延展串连成互动链,但是句子并不是分析性关联的实体,因为回应者在单个的互动关联性事件中可能采用重复句。此外,虽然两个不同话轮之间的谈话可能发挥着作为基本互动单元的功能,而且序列关联单元的边界与言语的边界通常重合,但是在分析时必须将它们分离,并将话轮组织本身与互动序列区别开来。欧文·戈夫曼以话步作为谈话分析的着力点,将纯粹语言学的分析转向关于互动的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综合考虑研究区域的实地调研数据与视域分析结果,结合空间句法的理论,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对中山路教堂广场区域的改造更新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话轮分配并非在会话一开始就已确定,而是通过在转换关联位置不断地进行协商而确定的。话轮转换系统起着话轮转换生成器和推动器的作用,它使会话顺畅地进行而不致于出现中断。哈维·萨克斯认为,对提问的回答只能在它们的序列位置中才能得到理解,在序列性上居于提问之后的任何话语都可能被看作是一种回答。会话分析的基本机制具有“语境无涉性”,因为它可被运用于一切谈话情境。但它又具有一定的“语境敏感性”,在实际的具体会话中,其复杂性和意义可以不断延展。例如,通过在始发语前加置一个初级序列或在始发语与应答语之间插入其他谈话等方式,相邻对可以衍生出更宏大的序列。对哈维·萨克斯而言,谈话互动中的人们之所以能够彼此理解,并不是基于动机关联性、文化关联性或制度关联性,而是言语中跨越不同制度设置的序列关联性。这种序列关联性“不是通过说明获得的,个体也不是根据它们对行动进行说明”④。哈维·萨克斯在共享的正当性语境中区分了可说明性框架(具有规范的正当性条件)和无法正当解释的序列。在哈维·萨克斯看来,会话的序列秩序不同于社会结构和制度秩序,它对共同在场的他人是否理解谈话甚为敏感,同时又对意义的实现产生制约作用。
欧文·戈夫曼将谈话视为一种聚焦式互动,认为话步的概念有助于理解非言语行为,譬如话轮间的沉默。对此,他先是将会话分析中的“提问—回答”相邻对序列替换成“陈述—回复”模式,进而扩展至“陈述—回复”语序列。他重新定义了陈述与回复:陈述是以引出某种问题为导向的话步,而回复则是作为前述事件之回答的话步。⑰因此,陈述与回复指的是话步,而不是句子或言语。谈话通过不同言说者之间的话轮转换得以链接和运转,由此,谈话也成为互动的典型形式。谈话的不断推进和持续是由序列性的话轮转换完成的,当这种序列中的应答语句无法与回复的观念相一致时,欧文·戈夫曼又用“回应”取代“回复”,以此弥补相邻对的缺陷。在他看来,“正如交换能够将非语言行为共同纳入到关涉这些行为的口头语言之中,那么交换也能够结合过去的行为作为对当下的行为进行褒贬的理由,从而将回应置于更广泛的情境中——或先或后于这些情境的话语指涉,并将它们带入交换”⑱。
换言之,欧文·戈夫曼用“提问”、“陈述”和“指涉”取代“相邻对前轮”,用“回答”、“回复”、“回应”等取代“相邻对后轮”。通过这种方式,他试图削弱会话分析的相邻对概念,从而提炼出更抽象和形式化的语言分析模型。这种类型化的阐述为他在一般意义上探讨面对面互动提供了理论基础。欧文·戈夫曼认为,会话分析忽略了互动秩序中仪式维度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会话分析所注重的对行动(交谈)序列性的考量相当于他所说的系统要求,但忽略了仪式要求。在交谈过程中,参与者也是道德行动者,他们对他人的即时感受具有移情能力,并会适时作出反应。互动参与者遵从文明得体的行为规范、彼此尊重,谈话互动深受这种“社会接受性”的影响。欧文·戈夫曼指出,关于行动构成的探讨是一个哲学问题,它在谈话中具体的落实与施行是语言学问题,而关于它的表达规范与礼仪则是社会学应关注的问题。因此,“这里很清楚,哲学和语言学必须让道于社会学”⑲。
欧文·戈夫曼表达了对会话分析的忧虑,认为会话分析的决定论立场使它对谈话的开放性与机动性缺乏充分考量。在实际会话过程中,同一个人经常同时扮演着多个不同说话者的角色,说话者的身份与他们所说的话语之间会出现分离现象。因此,他区分了说话者的不同类型,如发声者、作者和责任者等。⑳具体而言,发声者是言说的实体,是发出声音的“音盒”;责任者居于由言说者确立的位置,是对具有特定言说意义的位置或立场承担责任的一方;而作者则是责任者所处位置的创造者。欧文·戈夫曼将这些不同类型的说话者统称为面对面互动的“生产格式”。㉑他试图以此阐明说话者与其谈话间的松散联系。在日常谈话过程中,参与者可能是被正式认可的接受者,也可能是未被正式认可的接受者,他们是偷听者或旁观者,这些具有不同参与合法性地位的听话者共同构成了“参与框架”。㉒此外,他还探讨了框架破裂、反思性评论、话头以及饶舌、打哈欠、走神等,尤其是以唱片骑师(DJ)为实例,探讨了即兴谈话过程中不同的纠正措施,从直接忽略口误到尴尬地坦承错误等,从而通过具体的语境分析个体经验的基本结构。
三、会话分析学者对欧文·戈夫曼的回应
大体而言,会话分析学者对欧文·戈夫曼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资料收集方法。会话分析认为,会话研究应是一门观察性的经验科学,因此对会话的科学研究应采取具象的观察而非抽象的推理,应将现实的观察而非虚构的想象作为理论化的基础。虚构的、想象性的会话资料已经过合理化的转换,并预设了分析者与会话对象之间所共享的文化定义。因此,会话分析学者通常采用现代的录音、录像技术,精确地分析具体对话,比较常见的例子如医生与会诊病人之间的情境互动。这些数据都是在自然的情况下发生并获得的,会话分析学者不一定非得要在现场,也不一定需要他们亲自参与交谈,从而最大限度地排除了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干扰行为。第二,会话分析认为,仪式要求对于日常生活的实际谈话通常是一些修饰性的“旁枝侧叶”,而非主干。会话分析学者研究具体的行动序列和相邻对关系,关注日常的行为与社会行动的情境性和序列性的组织,因此,会话分析不需要仪式。㉟类似地,同样是研究尴尬问题,会话分析学者认为,根据自我和身份认同或印象管理的思想很难设想一段关于尴尬的影像片段里的行为。如果使用根据自我和印象管理将行为概念化的情境模型而不是真实的数据,会忽视尴尬所发生的特定情境中的行动的复杂性,从而掩盖参与者的真实行为,导致真实的互动消失。因此,“此类分析仅停留在现象的边界上,而对那些在社会生活中瞬间发生的人们的真实行为仍有待解释”。㊱需指出的是,会话分析并不完全排斥形式化的理论,如谢格洛夫认为,谈话互动可以跨越社会和互动的情境以及参与者的特征。㊲
我当时还是一位受古典训练的研究生,痴迷于
社会理论、关于知识和文化的社会学以及越轨
行为,正是从他(欧文·戈夫曼)那里,我第一
如果说是消费品互联网在很成熟的情况下,产业互联网的难题和挑战是巨大的,消费品互联网具有锐度,产业互联网绝对是厚度,消费互联网是长跑,产业互联网是中长跑。在目前产业互联网包括生鲜产业互联网已经到了高原地带,不仅仅是工业互联网,冷链产业也属于产业互联网范畴,因为涵盖了一二三产业。目前的困惑是产业的不融合,供应链不协同,区域的不平衡,以及平台的不支撑,还有我们高端市场要素的不积聚,未来还需要做相应的调整,但是冷链产业的前景非常好,虽然还存在些许问题,但是终究运用现代科技与手段都将迎刃而解。
次认识到研究他所专注的领域中各种事件的可
行性。从这种意义上而言,他至少可以部分地
被看作是我所从事的研究的前辈。㉓
值得注意的是,谢格洛夫在讨论欧文·戈夫曼的研究时,他用的是“关于会话的分析”(the analysis of conversation)这样的表述,以示区别于他所归属的“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这一流派。谢格洛夫指出,哈维·萨克斯和他本人的努力在某些方面都是建立在欧文·戈夫曼研究的基础上,而非对立的立场,因此,会话分析学者并没有“弑父”的动机。相反,谢格洛夫借用他昔日好友哈维·萨克斯的话说,这个在如今被看作是弑父故事的俄狄浦斯传说,它却起源于一起故意谋划的“弑婴”事件。谢格洛夫在这里试图表明的是,早在《回复与回应》中,欧文·戈夫曼就对哈维·萨克斯等人的会话分析进行了批评与攻击,一直到他去世之后所发表的《言辞适切的条件》。而反观会话分析这一边,他们对欧文·戈夫曼的批评却相当克制。1986年,两位会话分析学者保罗·德鲁和安东尼·伍顿还召集了第一届探讨欧文·戈夫曼对社会学贡献的国际会议,会议成果被汇编成书出版。㉔
哈维·萨克斯、谢格洛夫和杰弗逊在会话分析的经典论文《会话中话轮转换组织的最简系统》中指出,会话的话轮转换组织和序列性是松散的,被话轮转换结构化的会话可以通过相邻对和话轮序列进行分析。㉕谢格洛夫认为,从最早的关于人际互动的研究中,欧文·戈夫曼对谈话与行为类型的研究都与仪式、面子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拒绝行为“句法”(syntax)的世俗化。㉖欧文·戈夫曼既用仪式、面子来解释行为,也将它们视为互动仪式组织的促发性基础,谈话本身具有的自我复位和补救性特征(也即仪式要求)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因此,欧文·戈夫曼与哈维·萨克斯之间的关键性差别在于:仪式是欧文·戈夫曼的互动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互动的组织化是为了确保个体的仪式需要。㉗可以说,欧文·戈夫曼赋予会话分析以意义和价值,而哈维·萨克斯关注谈话的序列组织。
在谢格洛夫看来,欧文·戈夫曼过于强调仪式以及回避对真实发生的事件细节进行分析,这严重损害了欧文·戈夫曼关注“各种时刻,而不是人”(the moments,not the men) ㉘的机会。正是由于对仪式、面子等的持续关注,最终使欧文·戈夫曼未能摆脱个体及其心理,从而阻止他对“交往”的充分研究。这种倾向在《回复与回应》一文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欧文·戈夫曼抨击会话分析以行动组织本身作为正式分析单元的努力。谢格洛夫认为,这种对仪式的强调高于对序列性的考量是对互动句法的社会学研究向自我的心理学研究的一种倒退。正因如此,欧文·戈夫曼对个体的兴趣始终高于对互动结构及其句法的关照。欧文·戈夫曼之所以无法解决行为之间的句法关系,其最大的障碍是由于他自身“对‘仪式’的承诺以及不情愿将这种‘句法单元’与一种对仪式组织和保全面子的功能性的具体承诺相分离”㉙。只有在《框架分析》中,欧文·戈夫曼才真正关注到行为之间的句法关系。
谢格洛夫指出,如果存在与沟通系统有关的“统一的工程学要求”,即欧文·戈夫曼所提出的八项系统要求,那么原则上应该存在满足它们的各种方式,而不仅仅只是仪式而已。会话分析没有像欧文·戈夫曼那样强调仪式的维度,它认为会话中的仪式关注是偶然的,并具有语境性的迭合特征(context-specific lamination)。会话互动过程中更重要的是各种“言语交换系统”,它在处理对话实践时采用以下方式:第一,话轮转换组织,它分配、限制参与机会的大小,这种设置是为了考虑到具有不同特征的参与者,如唠叨啰嗦和沉默寡言。第二,相邻对组织,即轮流交替的次序及其特征。第三,修复组织,它规定了特定类型的行为机会,也就是应对会话中出现的故障。㉚这些特征在原则上独立于行动者以及他们的表意性行为,它们共同构成了会话互动中的基础组织,并强调社会行动的构成与合作。
混凝-加核絮凝组合工艺首先利用无机网捕作用,使废水中难以自然沉淀的胶体状污染物和一部分细小悬浮物经过脱稳、凝聚、架桥等反应过程,形成具有一定大小的絮凝体,直接进入加核絮凝单元,由于加入了较重的沸石,不仅使已经形成的矾花能够加速沉淀,并在加入高分子有机聚合物CTMAB的情况下将未去除的部分大分子有机物、悬浮物进一步絮凝沉淀。猜测制浆造纸废水中应该存在某种难以用混凝-加核絮凝组合工艺去除的物质,下面采用GC-MS法对组合工艺处理后废水进行分析。
①Gregory W.H.Smith,Ethnomethodological Readings of Goffman,in Javier Trevino ed.,Goffman’s Legacy,New York: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3,p.256.
会话分析学者与欧文·戈夫曼之间的争论似乎隐含着一种难以摆脱的俄狄浦斯情结。如前所述,会话分析学最重要的人物,如哈维·萨克斯和谢格洛夫等人,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时都是欧文·戈夫曼的学生。当欧文·戈夫曼发表《回复与回应》一文时,哈维·萨克斯已不幸因车祸去世;而作为哈维·萨克斯生前亲密搭档的谢格洛夫对欧文·戈夫曼进行反驳时,欧文·戈夫曼也已去世。谢格洛夫坦承,欧文·戈夫曼是他最重要的老师之一:
四、安妮·罗尔斯对欧文·戈夫曼和哈维·萨克斯的评价
安妮·罗尔斯认为,哈维·萨克斯对语言的理解事实上更接近于欧文·戈夫曼对互动的理解,而不是他对语言的理解。二者都探讨了共同在场的面对面互动如何实现社会秩序,他们之间的区别不在于自我观和互动秩序,而在于欧文·戈夫曼缺乏研究会话场景的构成性要素和谈话的序列规则所必需的详尽数据资料。在安妮·罗尔斯看来,欧文·戈夫曼关于谈话的观点是传统的结构主义视角。欧文·戈夫曼的语言观之所以缺乏洞见,是因为他将语言视为制度和文化的产物,而不是“互动式达成”,从而偏离了他早期关于自我研究的立场。而哈维·萨克斯追随着加芬克尔,“在谈话和实践行动的层次上论证了本土性生成的秩序”㊳,因此,哈维·萨克斯关于语言的论述与本土性生成的互动秩序和欧文·戈夫曼对自我需求的观点相一致。㊴
在欧文·戈夫曼那里,语言不是一种构成性秩序。欧文·戈夫曼虽然强调构成性的自我,但关于语言的论述却转向结构性特征,并使之具有文化和制度的本源性。这是很多人批判欧文·戈夫曼语言观的根本原因。哈维·萨克斯认为,意义不是通过语法的一致性而达成的,也不是由制度化的规则所定义,会话“在本质上是互动性的,它是根据会话需要而不是语法需要、真理标准或制度秩序进行组织化”㊵。社会秩序“不是制度约束的产物,而是通过交互链进行运作的产物”㊶。行动者并非为了实现意义而遵循规则,而是以特有的感知性,通过一系列如哈维·萨克斯所说的偏好来建构会话,这种偏好或期待不是在文化或制度的层面上进行运作的。意义通过序列关联性而建构的观点是哈维·萨克斯对语言哲学最重要的贡献。
会话分析学者认为,个人特性(如身份地位)与社会结构等因素会自然地进入会话,但它们对会话本身不起决定性作用。会话秩序首先确保的是参与者的共同投入(如说话者、听话者、旁观者等的责任与义务),而不是身份的再生产。由于欧文·戈夫曼未能明确区分互动秩序与制度秩序,因此他无法处理将语言作为一种构成性秩序的问题,而哈维·萨克斯则将会话偏好与道德、制度化的价值进行了区分。欧文·戈夫曼无法解释尽管存在大量不符合语法规则、索引性表达以及逻辑混乱的现象,但是在日常生活中,谈话参与者之间仍然能够相互理解。也就是说,某些组织化的、有意义的行动和言语并不具有社会预先规定的正当性条件。而哈维·萨克斯以会话的构成性为基础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就话轮转换和序列关联性而言,会话参与者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不相关的。“虽然通过框架化和可说明性的原因可能引入诸多不同的社会秩序或制度关联性,对会话产生影响,但是会话行动产生的序列秩序本身的组织化独立于并先在于这种关联性,而且它为避免这些社会关联性的影响提供了各种策略。”㊷
谈话互动的参与者可能通过“合成性策略”限制和减弱意义表达与序列秩序之间的关联性,或者通过“构造性策略”使索引性最大化,从而实现对会话的策略性操控。与之相对应,言语既可以是合成性的,也可以是构造性的。在谈话互动中,这两种言语在不同的程度上都存在。通过构造性策略可以颠倒可说明性序列,迫使对方进入说话者重新设置的话轮转换。在这种情况下,先前提供话语意义的框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序列关联性。在该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的是序列关联性,而不是外部的文化、制度和结构等要素。概言之,哈维·萨克斯充分阐明了会话及其意义的互动式达成,以及本土性生成的秩序是如何在谈话互动中不断地发生改变和再形成的。
王屋镇古树名木资源较为丰富,有15种,分别是国槐、皂荚、黄连木、侧柏、龙柏、栓皮栎、橿子栎、白皮松、大叶朴、核桃、红豆杉、槲栎、七叶树、桑树、银杏,其中国槐所占比例35.1%,皂荚所占比例为17.0%,黄连木所占比例为13.8%,侧柏所占比例为12.7%,龙柏所占比例为6.3%,这5个树种共80株,所占古树名木比例达84.9%,为王屋镇的优势树种。
合成性策略具有一系列预先准备好的意义与关联性,它将说话者和受话者置于一种先在的、制度化的关系之中。它通过表演者与序列关联性及其必须履行的承诺或投入之间的疏离产生意义的不明确性。说话者越是试图避免序列性达成的意义,就越会引起不明确性。序列秩序包括生成性与约束性两个维度,约束性指确保会话序列的责任担当与义务约束,因此在微观层面上的序列秩序也具有道德意涵,序列关联性也获得了道德关联性。说话者越是脱离序列性,他们之间越是更加疏离,对交换秩序的投入程度也越小,谈话互动也越有可能被操控。序列秩序的道德性和非工具性是它的构成性与制约性之表现,哈维·萨克斯这种思想与欧文·戈夫曼的自我观相契合。从这种意义上而言,哈维·萨克斯的序列秩序是欧文·戈夫曼的互动秩序在语言学领域的充分运用,而欧文·戈夫曼本人却在对语言的分析中放弃了他最初的分析思路。在哈维·萨克斯看来,由于意义是由序列秩序决定的,因此,“字词的意义越是预先被带入情境的各种关联性所框架化,那么在其使用过程中便会产生更多的不明确性与随意性。词意越是没有被预先框架化,那么互动参与者就越是必须依靠序列关联性来决定意义,从而实际产生的不明确性与随意性也较少。就这个角度而言,意义衍生自使用过程中的序列意涵”㊸。
译者是翻译的主体,翻译就是跨越语际的障碍,达成交流的一种文化活动。,在翻译实践中,只要是能顺畅地交流思想或情感,译者就无须过于恪守原文的形式,企图形式上的完全对等。只要能让翻译的目的得以达成,那么,以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为指导,通过适当地采用多样的翻译方法来达到翻译效果的动态对等是便一种更加实际有效的翻译准绳。总之,译者应自由,译法无限制,只要是尊重原文的思想和内容的前提下,译者就可以并且应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灵活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促使翻译活动的顺利达成。
“合成性”与“构造性”是一种实践性的区分。合成性言语可以通过共享的文化或“动机词汇”(vocabulary of motives)获得其意义,与之相对的是构造性言语,其意义只有通过对序列秩序的持续性投入才能获得。某一言语所具有的合成性或构造性的特征取决于它是被用作索引性的和构成性的行动还是其意义已经被阐释框架所明确规定。在构成性的视角下,自我、意义、语言和互动本身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既是制约性的又是构成性的,意义在本质上不受秩序的约束。
哈维·萨克斯关于意义的理论填补了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游戏的逻辑缝隙,并且解释了通常所谓的社会行为的非理性事实上具有明显的秩序性。㊹在安妮·罗尔斯看来,当个体进入某个特定的情境时,他首先要解决的是第一句话该说什么或者第一个动作该怎么做,而不是先寻找或确定某个阐释性的情境框架,然后再采取某种行动。因此,实践是原生性的、第一性的,框架是次生性的、第二性的,即当个体无法成功地将实践定位于某种框架或类型时,却能够用实践来确定框架。㊺对安妮·罗尔斯而言,作为行动者的个体脑海里是否充斥着应对现实情境的各种框架是一个伪问题,因为他们首先需要的并不是这些框架。个体不断地从实践经验中学习,使他有足够丰富的知识去有效地理解新的实践丛,以至于他们好像是通过将框架或类型运用于新的情境才完成的。社会秩序处于不断再生产的情境实践中,而不是在辨识它们的观念性类型中。安妮·罗尔斯认为,与其他社会学家一样,欧文·戈夫曼犯了混淆观念与实践的错误。互动本身的脆弱性需要道德承诺来维系,这使欧文·戈夫曼的互动论带有明显的道德论色彩,而正是欧文·戈夫曼以观念代替实践来理解互动导致了这种脆弱性。
五、结语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欧文·戈夫曼受到来自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和哈维·萨克斯的会话分析的挑战。事实上,欧文·戈夫曼持久地关注着语言互动的微观研究,哈维·萨克斯及其会话分析是他的重要关注对象。在其三十余年的学术生涯里,可能没有一位学者使欧文·戈夫曼如此长时间地投以关注、对话或批评。终其一生,欧文·戈夫曼极少回应或反驳关于他的学术批评,除了他对结构主义标签的公开反驳。但人们通常忽略的是,他的《谈话形式》一书其实是对哈维·萨克斯的会话分析所进行的系统性回应。就谈话分析而言,欧文·戈夫曼没有提出一种规范性的、科学的方法,也即可供复制和追随的研究范式,在这种意义上,他是一位思想家或哲学家。与之相比,哈维·萨克斯所留下的作品虽然并不多,但却明确提出了一套规范性的会话分析概念与体系,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在会话分析学界、甚至在整个语言学界,欧文·戈夫曼的影响不如哈维·萨克斯的原因。
1974年,哈维·萨克斯、谢格洛夫和杰弗逊在《会话中话轮转换组织的最简系统》一文中提出了话轮转换的简易模型,他们用话轮构成要素、话轮分配要素和一套话轮转换规则来描述话轮转换系统:
采用SPSS 17.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会话分析学者认为,欧文·戈夫曼讨论的不是相邻对,而是更弱、更一般化的组织特征,即“毗邻关系”。㉛一个人所说的话轮是否被听到以及如何被理解,这是下一个话轮建构的副产品,下一个话轮表明对前一个话轮的理解。也就是说,毗邻关系的运作是向后的,下一个话轮才可实现说话者对前一话轮的理解。而相邻对的运作是朝向未来的,始发语对接下去相关联的应答语的作用非常有限。相邻对关系是话轮的进一步组织化,作为一种序列关系,相邻性是一种对话性的、互动的和社会性的事实。相邻对为这些不同的层次增加了未来导向的、多重话轮的和复合进程的行为。谢格洛夫认为,由于欧文·戈夫曼混淆了会话中连续变化的相邻关系与作为序列组织单元的相邻对,进而也无法区分话轮交替组织与序列组织。因此,欧文·戈夫曼仍然需要决定哪一种关注是主要的,“是话轮组织本身还是互动序列”㉜。而在会话分析学者看来,这种决定是多余的,因为“一方面是话轮与话轮交替组织,另一方面是序列,两者都是互动式谈话的一般性组织。它们都同时出现。谈话可以通过两者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进行组织”。㉝此外,谢格洛夫等认为,处于会话秩序之中的谈话参与者会受到规范的制约,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具有一定的选择自由和能动性。而由于欧文·戈夫曼对抽象性与普遍化的追求,他未能阐明在自然情境中构成参与者行为的生产与认可的基础组织。对信息交换和情境定义的研究都无助于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它们是抽离了真实行为的形式化分析。因此,欧文·戈夫曼没有对参与者行为的互动结构提供清晰的阐释,他研究的并非真实的互动秩序。概言之,欧文·戈夫曼关于会话的分析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哀婉”和“过早断言的虚无主义”。㉞
②Emanuel A.Schegloff,Harvey Sacks,Opening Up Closings,Semiotica,1973,8(4),pp.295-296.
③Harvey Sacks,Emanuel A.Schegloff and Gail Jefferson,A Simplest Systematics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urn-Taking for Conversation,Language,1974,5(4),pp.702-705.
④㊳㊴㊵㊶㊷㊸㊹Anne Warfield Rawls,Language,Self and Social Order:A Reformulation of Goffman and Sacks,Human Studies,1989,12(1),p.160,p.153,p.160,p.160,p.165,p.163,p.164,p.166.
⑤Erving Goffman,Encounters:Two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Interaction,Indianapolis:Bobbs-Merrill,1961,p.68.
⑥Erving Goffman,Relations in Public:Microstudies of the Public Order,New York:Basic Books,1971,p.149.
3. Mr. Shakabpa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said mission have no authority to enter into direct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but the Chinese Embassy will be glad to facilitate the purpose of their visit, which is understood to be in the interest of trade.
⑦⑧ Erving Goffman,Strategic Interaction,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69,pp.89-90,p.90.
⑨Erving Goffman,Interaction Ritual:Essays on Faceto-Face Behavior,New York:Pantheon,1967,p.20.
⑩⑭⑲ Erving Goffman,Felicity’s Condition,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3,89(1),pp.1-53,pp.49-50,p.32.
⑪⑫ ⑮ ⑯⑰⑱㉑ ㉒㉜ Erving Goffman,Forms of Talk,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1,p.24,p.23,p.72,p.12,p.24,p.58,p.145,p.137,p.24.
国内外学者都在商务合同的研究上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他们的研究重点有所不同。海外学者专注于研究商务合同的特征,而中国学者则更加关注商务合同的风格特征及其翻译。整体而言,我国的商务英语翻译研究起步较晚。商务合同兼具商务英语和法律英语的特点,因此使得商务合同翻译的难度加大。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学者近年来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明显增多和加强。在商务英语合同翻译的文本特征、翻译标准和翻译方法等方面均有涉猎。
⑬Robin Williams,Goffman’s Sociology of Talk,in Jason Ditton eds.,The View from Goffman,London:Macmillan,1980,p.218.
⑳Erving Goffman,Frame Analysis: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4,pp.517-523.
㉓㉖㉗㉙㉚㉛㉝㉞Emanuel A.Schegloff,Goffman and the Analysis of Conversation,in Paul Drew,Anthony Wootton eds.,Erving Goffman: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Order,Cambridge:Polity,1988,p.91,p.94,p.97,p.95,p.94,p.113,p.115,p.117.
㉔ Paul Drew,Anthony Wootton,Erving Goffman: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Order,Cambridge:Polity,1988.
㉕Harvey Sacks,Emanuel A.Schegloff,Gail Jefferson,A Simplest Systematics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urn-Taking for Conversation,Language,1974,50(4),pp.696-735.
㉘Erving Goffman,Interaction Ritual:Essays on Faceto-Face Behavior,New York:Pantheon,1967,p.3.
重大活动保障作业业务流程分为作业指挥和作业实施两部分,启动重大活动保障服务时,市级人影部门根据服务主体的需求,在区级人影部门的指导下,根据预案成立指挥中心,并设立专家技术组、作业指挥组、飞机作业中心和地面作业中心。市级负责作业预案、方案、计划的制定,决 策服务产品的制作及联合作业的指挥等,旗县级负责地面作业的具体实施。
㉟Philip Manning,Ritual Talk,Sociology,1989,23(3),p.374.
(一)最急性型 突然发病,个别病猪未出现任何临床症状突然死亡,病猪体温达到41.5℃,倦怠、厌食,并可能出现短期腹泻或呕吐,早期无明显的呼吸症状,只是脉搏增加,后期则出现心衰和循环障碍,鼻、耳、眼及后躯皮肤发绀。晚期出现严重的呼吸困难和体温下降,临死前血性泡沫从嘴、鼻孔流出,病猪于临床症状出现后24~36 h内死亡。
㊱Christian Heath,Embarrassment and Interactional Order,in Paul Drew,Anthony Wootton eds.,Erving Goffman: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Order,Cambridge:Polity,1988,p.154.
㊲Emanuel A.Schegloff,Confirming Allusions:Toward an Empirical Account of Action,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6,102(1),pp.161-216.
㊺Anne Warfield Rawls,Orders of Interaction and Intelligibility:Intersections between Goffman and Garfinkel by Way of Durkheim,in Javier Trevino ed.,Goffman’s Legacy,New York: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3,p.235.
中图分类号: C9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5982(2019) 04-0035-08
作者简介: 王晴锋,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北京,100081。
(责任编辑 陈 艾)
标签:欧文·戈夫曼论文; 哈维·萨克斯论文; 会话分析论文; 框架分析论文;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论文; 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