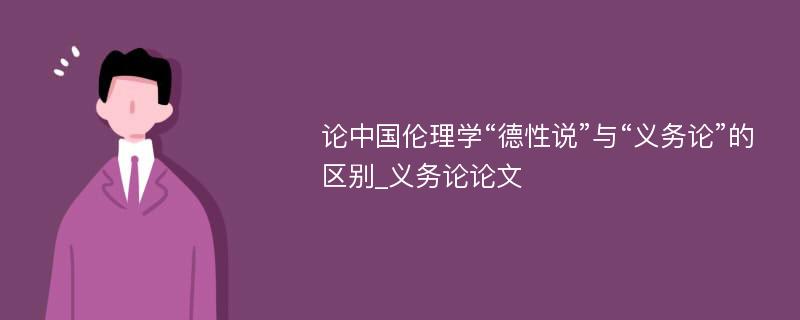
论中国伦理的“德性论”与“义务论”之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野论文,德性论文,中国论文,伦理论文,义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看,中国传统伦理学说有“道义论”和“功利论”两大流派。其中道义论内部又有“德性论”和“义务论”两大支派。我国学术界对传统的“道义论”与“功利论”的关系已有阐释,但对道义论内部“德性论”与“义务论”的分野却极少论及。考辨此问题,不仅有利于深化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认识,而且对于评价和构建当代中国伦理学,也具有价值论和方法论上的借鉴意义。
一、德性论的伦理学说
德性论又叫品德论或美德论。它所讨论的主要问题是:道德上完美的人是什么样子,人如何实现道德完美的理想。它的理论出发点是人性、人格或人的本质。
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上,孔子是第一个从德性论角度构建伦理学说的思想家。他抓住当时已经出现的“仁”的观念,把它提升为具有人本主义和德性主义思想内涵的伦理原则和理想,并以此为核心建立了自己的伦理学说体系。孔子的“仁”虽有多重涵义,但最基本的意思则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许慎说:“仁,亲也。”(《说文解字》第八篇上)毛泽东也说“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①(P182)以仁为核心,孔子提出了孝悌、忠信、智勇、中庸、礼义、温、良、恭、俭、让、宽、敏、惠、刚、毅等反映人的品德状况的伦理范畴(即“德目”)。他还把具备了较完美德性的人称为“仁人”或“君子”,把与此相反的人称为“小人”。这就为人们建立了一种人格理想和人生价值观。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致思方向。他说:“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又说:“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孟子·尽心上》)这是说,只有具备仁德的人,才有贵于天地的人生价值,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也正是从肯定人的道德价值和理想出发,孟子才把人性理解为“善”的。在孟子看来,只有天赋的德性才能把人与禽兽区别开来,并使人获得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而且性善论还内涵着人对人的信任、尊重、激励和理想等丰富内涵。孟子还认为,作为社会道德规范的仁、义、礼、智,来源于人的天赋心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所以,人人都有“不虑而知”的“良知”和“不学而能”的“良能”。良知、良能合起来就是良心。孟子认为,源于人心的仁义礼智信,可以应用于调整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等“五伦”关系。孟子还强调独立人格,提倡“威武不屈”的大丈夫精神。这些都表明,孟子是彻底的德性论者,而不是义务论或规范论者。
由孔、孟开其端的德性论伦理学说,继其后者不乏其人。大约成书于秦汉之际的儒家经典《礼记·大学》,提出了儒家政治伦理学说的纲要,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三纲领”,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这也是德性主义的代表作。到了唐代,韩愈在学术思想上“柄任儒术崇丘轲”(《石鼓歌》),以继承发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道统”自命,“抵排异端,攘斥佛老”(《进学解》)。他把人的德性状况分为上、中、下“三品”:“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己矣。”(《韩昌黎集·原性》)这是注目于人的品性的明证。他在著名的《师说》一文中,提出了“传道、授业、解惑”的师德观和重视品德教育的思想。作为韩愈学生和挚友的李翱,在伦理思想方面突出发挥了《中庸》的“性命之道”。他认为,“性命之道”是儒学的精华,它由孔子经子思和孟子而传之公孙丑、万章之徒,至“秦灭书”而废缺。为使这“缺绝废弃不扬之道几可以传于时”,李翱著《复性书》,认为“性善情恶”。他说:“人之所以为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因此,他提出了“灭情复性”的成圣之道,也就是“教人忘嗜欲而归性命之道”。李翱的“性命”之说,体现了儒佛合流的特点,遵循了德性主义的伦理路线,对宋明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北宋周敦颐以“诚”为道德之本。这个“诚”就是指人的道德品性和道德信念。他说:“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通书·诚下》)他还把善恶区分为刚善、柔善,刚恶、柔恶四种品行,认为这些都有偏颇,唯有“中正仁义”的“圣人之道”,才是做人的最高理想。他继承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的修身观,吸取老、庄道家的主张,提出了“无欲”、“主静”的道德修养论。这些表明,周敦颐是位“德性论”者。南宋陆九渊提出“心即理”的道德本源论。他认为“圣贤之所以为圣贤”,就是因为有“此心此理”。在道德修养方面,他提出了“自存本心”的“易简”修身法。在著名的“鹅湖之会”(在鹅湖寺进行学术讨论)上,陆九渊兄弟二人同朱熹展开辩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陆九渊赋诗说:“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②(P409)后来黄宗羲在评述朱陆之争时,依据《中庸》中“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一语,指出:陆九渊之学“以尊德性为宗”,而朱熹之学“则以道问学为主”(《宋元学案·象山学案案语》)。这就一语道破了陆九渊的德性主义伦理路线。
明朝中期,王守仁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伦理思想,提出了以“正心”为出发点的“致良知”说。他认为《大学》中提出的“修身”、“诚意”、“格物”,都是为了“正心”。而“正心”又是“致良知”的同义语。他说:“吾生平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寄正宪男手墨二卷》)所谓致良知,就是要通过人的认识和修养,克去私欲对“良知”的障蔽,以复明吾心之“天理”。他强调向内用功,捉心中贼,同时又用“知行合一”的观念强调“行”的重要性,要人把省察克治和在事上磨练作为致良知的主要方法。这显然也是重心性、尊德性的伦理学说。
作为现代新儒家代表的熊十力、贺麟等人,也都遵循了德性论的方向。熊十力从他“体用不二”的本体论出发,引伸出“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贺麟是站在陆王心学的立场上学习、研究和吸取新黑格尔主义的,试图寻找陆王心学与新黑格尔主义的共同点,以便把二者结合起来,创立新说。贺麟在创造他的“新心学”之前,还对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等人的“新儒学”一一作了评论,总结了“新儒家”哲学思潮的发展情况和经验教训。他认为:“新文化运动以来,倡导陆王之学最有力量的人,当然要推梁漱溟先生。”③(P213—214 )他还认为冯友兰是程朱理学的继承者,尽管也多少受英美新实在论的影响。他说:“讲程、朱而不能发展到陆王,必失之支离。讲陆、王而不能回复到程、朱,必失之狂禅。”③(P215)
德性论的伦理学说在中国源远流长、盛而不衰。它对中国20世纪所有伦理学家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时至今日,它倡导的思想品德的教育和修养,仍然是受到普遍重视的问题。
二、义务论的伦理学说
义务论的伦理学说侧重于社会道德规范的建构,把道德规范的实质理解为个人对社会(包括他人)应尽的义务。它的理论出发点是社会关系或社会实践。
中国的义务论伦理学说可以上溯到西周时期。当时的宗法等级制度成为人们道德义务的社会基础。但是,当时的伦理思想家周公,却没有直接依据宗法等级制度论证道德义务的来源,而是利用人们的天命观念来解释道德义务的由来。在他看来,宗教——道德——政治联为一体,道德来源于宗教信仰,应用于政治实践。他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政治伦理思想,认为统治者担负着“保民”的道德义务。同时,出于维护宗法等级秩序的需要,他又提出了“孝”和“忠”的道德义务要求,这就把上对下的道德义务转化为下对上的道德义务。在等级森严的社会关系中,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之间,虽有名义上的相互道德义务,但实际上却只有下对上的道德义务。周人把宗法等级制度称为“礼”。礼既是道德规范的基础,又是由道德规范来规定和表现的。到了春秋时期,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的观点,表明他认识到了道德与宗法等级制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是,他所强调的“仁”仍属于人的内在品德,而非外来义务。
战国后期的荀子提出以“礼”为根据和原则的义务论伦理学说。他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这是用社会的原因论证道德规范和道德义务的根源,同以往的天命论和先验论有很大不同,有比较接近现实的一面。荀子认识到人类生活的根本特点是“能群”。这个“群”,也就是指社会。他认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道德义务(礼),就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反过来说,履行道德义务的意义不仅是为了个人“能群”,而且是为了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他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荀子认为“礼”对社会有极端重要性,所以,提倡“隆礼”,并且提出了以“礼”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而这个体系的职能就是表达人的道德义务。
西汉董仲舒的伦理学说亦属义务论。“三纲五常”是董仲舒义务论伦理学说的基本内容。“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规定了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的道德义务。“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在先秦儒家那里主要是作为品德范畴来使用的,但在董仲舒那里,则是作为从“三纲”派生出来的基本道德规范,即个人对社会的道德义务来论述和使用的。他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春秋繁露·仁义法》)他还从神学宇宙论的高度论述了道德义务的根源。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对策》)又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他认为,道德是天意的体现,天意又是通过阴阳、五行来呈现的。“天意难见也,其道难理。是故明阴阳入出、实虚之处,所以观天之意。辨五行本末、顺逆、大小、广狭,所以观天道也。”(《天地阴阳》)“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基义》)这是把从封建社会关系中产生的道德抽出来而赋予天、地、阴、阳、五行之义,将自然的天神学化和伦理化,然后又用“天人合类”、“天人交感”的理论,把人的道德义务置于“天”的神威之下。“天”不仅是道德命令的发布者,还是人们执行道德命令的监督者。这就强化了道德的社会调节功能,使人不得不以“敬神”的态度“敬德”。
宋代二程、朱熹以“天理”为万物的本原和本体,进而认为人们的道德义务或道德行为规范来源于天理。二程认为,万理本于一理或归于一理,因此君臣、父子、长幼、夫妇、朋友等伦常之理均出于或归于天理。朱熹说:“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朱子文集》卷五十九)又说:“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有父子之理。”(《朱子语类》卷九十五)这就是说,天理在先,“三纲五常”等道德原则、规范生于后。这与董仲舒“道之大原出于天”的说法并无二致,所不同的,只是采取了更加思辩的形式而已。二程、朱熹还认为,人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百行万善的根源,气质之性则是为不善的根源。朱熹说:“人之所以有善有不善,只缘气质之禀各有清浊。”(《语类》卷四)又说:“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同上)这实际是说,人的内在道德意识是外在天理的内化,而“人欲”,则是本来就有的。因此,他们认为道德修养的实质是“存理去欲”、“存善去恶”。朱熹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学者要于此体认省察之。”(《语类》卷十三)总而言之,在二程、朱熹看来,道德义务源于人之外的天理,而不是源于人性的内在要求。
近代以来,人们多从社会发展、国家兴亡的视角理解道德的本质,也就是把道德视为从社会整体利益中引伸出来的行为规范,对个人来说,意味着对社会的义务或责任。加之某些政治(政策)的、法律的规范也转化为道德规范。这就是许多人经常不加思索地称道德为行为规范。我国现行伦理学教科书也以建立社会道德规范体系为己任,被称为规范伦理学。这些都表明义务论伦理学说仍有很强的生命力。
三、中国伦理的“德性论”与“义务论”之关系
从价值论上看,“德性论”和“义务论”都属于传统“道义论”一派,而不属于“功利论”一派。大体说来,在中国古代,道义论居主导地位,近现代以来,功利论日盛,并有压倒道义论之势。但从社会全面发展的要求看,道义论与功利论的融合(即“义利兼顾”)将是未来的必然走向。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对中国传统“道义论”的价值取向应持肯定态度。
从方法论上看,道义论内部的两大支派——德性论的伦理学说和义务论的伦理学说,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而又互补的伦理思维方法,这可以从它们二者的理论特点看出。
“德性论”的理论特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1.以个人为道德的主体和载体,把道德与有道德的人等同起来,伦理认识的对象集中于独立个人的品德。重视人的道德主体性,强调自由、自律和负责精神。在解释个人品德的来源上,有天赋说、养成说和神授说等不同观点。2.把品德价值视为人的价值的一个方面。它不仅把品德好坏作为区分人与非人的界线,而且还作为衡量人的价值的重要标准。它把人的美德作为价值追求的目的,而不是作为达到其他目的之手段。3.在伦理认识中,重视个体道德心理分析。认为道德表现于人的言谈举止,深藏于人的品性之中。因此,重视知、情、意等理性和非理性因素对行为选择的影响,以心理学为伦理学之基础。4.重视品德范畴(又叫“德目”)的体系建构和实际应用。有一套反映品德现象的特殊语言系统,并与其他的知识性语言系统相对区别。相对于研究社群道德的宏观伦理学而言,它是注目于个体道德研究的微观伦理学。5.它局限于个体人的道德完善,忽视社群环境对个体道德的制约性,没有把作为道德主体的人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不利于实现个体道德建设与社群道德建设的平衡发展。
与德性论不同,“义务论”的理论特点是:1.以维护社群整体利益为出发点,提出对个体的道德规范要求。重视社会道德规范体系的建构,并把这些道德规范是否被遵守作为评价个体行为正当性的依据。2.从个体方面来说,把履行社群提出的道德规范作为一种不可推御的道德义务,也把学习和实践道德规范作为个体获得社群成员资格认可的必要条件。3.在对道德规范(或道德义务)正当性的论述中,不仅从社群生活的伦理关系出发,还从自然规律或超自然的信仰对象中寻找依据。4.在道德认识上,把“实然”与“应然”、求“真”与求“善”结合起来。在道德价值上,强调社群利益高于或先于个人利益,坚持重群体轻个体或先群体后个体的价值导向。在道德实践上,重视道德教育和道德评价的他律作用。5.由道德规范所体现出来的道德义务,既可以是个体的,又可以是群体的。并且使道德规范与其他的社会规范相交织。
“德性论”与“义务论”的分野,有深刻的理论和社会根源。从理论上看,德性论的基础是人性善论;而义务论的基础是社会善论。这里的“人”,主要指人民群众。因此,从历史上看,德性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统治者对群众力量的信任和依赖,具有民本倾向;而义务论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统治者对群众力量的利用和防范,具有君本倾向。
“德性论”和“义务论”的分野,既是价值论的,又是方法论的。同时,它们二者的优势又是互补的。其中,德性论突出了道德的自律性和人类学意义;义务论突出了道德的他律性和社会学意义。这两个方面,是任何一个社会的伦理学体系都不可或缺的。因此,我们在讲到传统“德性论”和“义务论”的区别时,不要忘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在讲到二者的联系时,又不能忽视它们之间的区别。可以说,中国传统道义论的两大支派——“德性论”和“义务论”,都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容丰富的价值体系。它们共同为中国古代社会关系和人的发展提供了价值导向和精神动力。深入总结传统伦理思想的有益经验,对于构建当代中国伦理学,促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有重要借鉴意义的。
标签:义务论论文; 儒家论文; 德性论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孟子·尽心上论文; 国学论文; 伦理学论文; 读书论文; 孟子论文; 道德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