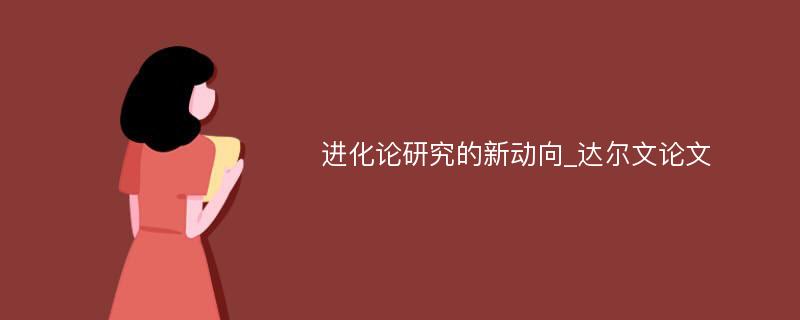
进化论研究的新动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化论论文,新动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无须神意设计,物种起源仅与自然选择有关
达尔文进化论强调,自然选择好比是无形之手,引导物种的起源。其对立面就是自然神学中的设计论,强调上帝以有形之手操纵物种的起源。但是,进入20世纪之后,设计论又有了新版本。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张志林教授的论文《进化论与设计论证》即分析比较了三个典型的设计论版本,并以最新的斯温伯恩版本为据,认为进化论与设计论证不仅互不冲突,而且相互补充。在张志林看来,斯温伯恩的设计论证不同于传统自然神学的做法,因为他不再局限于钟表—工匠、目标—设计者之类的简单类比,而采用自然规律—人为规律和人类—上帝式的类比。也就是说,由人所确立的科学规律常常能够得到自然现象中的有序关系的验证。至于人与上帝的相似性则表现在,两者都具有理性、美德、智慧特性等,而差异则表现在这种特性在人类身上是有限的,而在上帝身上则是无限的。由此得出类比结论:无限的规律必定由上帝建立。但细加深究,我们就会发现,斯温伯恩的版本好比是“新瓶装旧酒”,并未论证出什么新意。科学解释与哲学解释或神学解释的区分就在于,前者仅对现象给出机制性的说明,亦即过程是“如何”展开的,而不可能涉及现象背后的“为什么”。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宇宙是这样,这是科学问题;宇宙为何是这样,这是宗教追问。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因为父母受精卵的形成,这是科学解释;至于说到为何是“我”来到这个世界,我来到世上的意义何在,这就是一种宗教或形而上学的追问了。说到宇宙居然是“有”,而不是“无”,这也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惊奇罢了,而科学的使命仅在于解释这种“有”的展开机制。当然,由这种惊奇进而推出神意的存在,对于一个宗教徒来说无可非议,因为那是信仰,其实信仰本来就无须理由。但若要说这是一种严格的逻辑论证,由此推出上帝存在这一必然结论,则是一种越界或犯规。同样道理,说到科学规律背后的那个最高公设,斯温伯恩强调的空间秩序的“同时并存规律”以及时间秩序的“前后相续规律”,那也只是一种信念。若一定要追问其来源,或许可以这样来理解,现代科学观念从表面看来似乎极其抽象,但用来构造它们的基本概念却令人惊讶地简单,这是因为根据达尔文理论,智力的出现本来就是为了对付生存所需,于是判定空间秩序的同时并存及其时间秩序的前后相续就是一种最原始的需要。对于这种根本性的信念,理性无能为力,它本也不需要理由。由此推出神意,无关逻辑论证,只是一种宗教信仰罢了。因为它经不起这样的追问,神背后又是什么?若设因果链终止于神,依据何在?这就回到了当初休谟的质疑,但它针对斯温伯恩的论证依然有效。
但即便由此推出神意,这个世界上也存在各种“神”,但为何推出的是那个惟一的位格化的神,其实也就是圣经中的那个神,斯温伯恩引用的理由居然是奥卡姆剃刀:简单性原则。这把剃刀虽然锋利,但也不是随时可用。当用于评判各种不相上下的科学解释时,作为一种最后定夺的标准,它是有效的;但当用于评判相互平等的宗教信仰时,它却是用错了地方。我们甚至可以这样来用,根据简单性原理,剃掉所有的终极原因,回归无神论,岂不最为简单?
事实上,古希腊以泰勒斯为首的爱奥尼亚学派持的就是这一观点,中国人的宇宙观也与此相近,即宇宙恒古存在,无始无终。只是自柏拉图起,才引入设计观念,以此解释宇宙的有序,至中世纪的自然神学,更是将设计论推向顶峰。其实设计论有两层含义:神分别设计了众多物种,神设计了自然规律,具体的物种依据自然规律而产生。达尔文理论摧毁的恰是第一种含义上的设计论,物种经由自然选择而产生,从而无须神的干预。至于第二种含义,如上所述,本已不属于自然科学范畴。
当时英国有一位牧师金斯利曾这样写信给达尔文:“现在有两种信念:第一,相信上帝创造了原始类型,它们能够自我发展为当时和当地所需要的一切类型;第二,相信上帝有过另一次的干预行动以便补足‘他自己’所创造的那些空隙。我已逐渐认识到,前一信念和后一信念同样都是神的崇高概念。我怀疑的是,前者是不是一种更崇高的思想。”①这位牧师就是在第一种含义上认同达尔文理论,但把上帝看作是自然选择理论的始作俑者。
在文章中,张志林还引用了达尔文的原话,“无论如何,我也不愿将这个美妙的宇宙,尤其是我们人类的本性,甚而将万事万物都视为野蛮的非理性的力量的产物。我倾向于把一切事物都看成是由设计好的规律所产生的结果,而细节无论是好是坏,都可用我们称之为偶然的东西来说明。”②张志林由此认为,达尔文是认同设计论证的。其实达尔文还有后话,“然而这一概念还不能使我完全满意。我深切感到,就人类的智力来说,整个问题是太深奥了。……我也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可以表明所有这些法则都是由一个全知的、预见了每一未来事物及其结果的创造者特为某种目的而设计出来的。”引文至此,关于达尔文对于设计论的看法,相信读者自己就能做出判断。
综上所述,张志林的结论,进化论与设计论证不仅不存在冲突,甚至是相互补充之说,或许难以成立。其一,就神设计了自然规律而言,所有的科学理论与宗教都不冲突,因为这本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其二,就是否要引入神意而言,这是一个神学问题,事关信仰,与逻辑论证无关,但人们之所以要执着于信仰或终极原因,乃在于人性有此要求,人生在世,最大的不安全感即是由不确定带来的恐慌,而信仰给出的最终解释则有助于消解这种恐慌;其三,达尔文理论的意义恰在于,无须神意设计,物种的起源仅与自然选择有关。
二、自然选择理论的科学地位问题
杰瑞·佛笃基于哲学的立场对自然选择理论进行了批判。首先,为什么说自然选择理论是伪装的神学?佛笃以青蛙为例予以说明,青蛙有一套特殊的捕食系统,尤其是它的复眼,专门用于锁定运动中的飞虫。青蛙的捕食系统乃是出于捕食飞虫的目的而被选择出来的。但事实上,自然选择的作用机制与这种内涵对象无关。具体说来,凡是嗡嗡叫的小黑点在移动,青蛙的捕食系统都会对之起反应,而无论它是否是飞虫。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凡是嗡嗡叫的小黑点,大多都是小飞虫,因而这套系统是行之有效的。但由此却带来一个问题:自然选择所要达到的效果,究竟是针对飞虫,还是嗡嗡叫的小黑点?不得不承认,自然选择机制确实没有能力对此做出区分。若是如此,自然选择理论就不是一种正宗的科学理论。
但有两种方式可以捍卫自然选择理论。第一种是,假设在自然选择机制背后存在一个幕后操纵者,它能区分飞虫和小黑点之间不同的内涵。我们不妨称其为“大自然母亲”。若是如此,它就成了“上帝的代名词”,自然选择理论即沦落为“伪装的神学”。这当然是致命的一击。对此,徐英瑾的回应是,青蛙吃了飞虫后得以生存下去,但吃了小黑点之后却会死掉,自然选择就是以这种机制来区分飞虫和小黑点的,哪里还需要引入什么“大自然母亲”?
但佛笃的回应却是,那就再举更为恰当的例子。如鹿角,向来被当作是自卫的武器,但现在却被认为是雄性向雌性炫耀的工具。也就是说,针对同一种表型(鹿角),却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于是,佛笃引入了数学函数中的自变量与应变量关系。对于特定的自变量来说,只有一个确定的应变量与其对应。但在自然选择理论中,对于一个特定的环境自变量(大多数移动黑点是飞虫)来说,却可以得到不止一个表型应变量(针对黑点以及针对飞虫的捕食系统)。同理,面对捕猎者和配偶对象(环境自变量),得到的却是两种都有可能成立的应变量:自卫和炫耀,且难以区分。这就打破了数学函数本该存在的关系,因此自然选择理论不是一个合格的科学理论。
但在笔者看来,佛笃在此混淆了问题。对于青蛙的捕食系统来说,它面对的确实是“等外延且异内涵”的对象。在青蛙眼里,只有小黑点,飞虫的表现形式恰巧与小黑点同构,亦即它们等外延;但却异内涵,因为飞虫可作为食物,而小黑点却不是。因此,吞食小黑点的青蛙会饿死,这就是自然选择的淘汰机制,可见不需要引用大自然母亲,自然选择本身就可对这种异内涵做出区分。但以鹿角为例,却不是这种情况。假设鹿角相当于青蛙的捕食系统,那么自卫或炫耀就相当于飞虫或小黑点。显而易见,自卫或炫耀不仅异内涵,也不等外延,因为它们在表现模式上完全不同构。只是在人类这一解释者眼里,才难以区分鹿角的适应对象是自卫还是炫耀。
为何会难以区分?佛笃说,那是因为进化论者在此陷入了适应主义的死胡同。所谓适应主义是指,任何一种表现型必定存在某种适应性功能。因此我们才会追问,鹿角的适应性功能是针对自卫还是炫耀。在此,佛笃引入了古尔德的观点。古尔德曾举过这一例子。教堂顶部有一拱肩构造,拱肩的存在其实正是圆顶的一部分,但拱肩又是艺术家大显身手的地方,上面往往装饰有各种图案。若以适应主义的思路来看,就要追问,拱肩为何功能而存在?它是圆顶的一部分,还是为了装饰?显然装饰只是副产品而已。古尔德以此例子表明,生物体的不少功能,有些就是适应现象的副产品。比如人类智力,本是有助于赤手空拳的人类通过发明工具之类更好地生存下来,但在此过程中,它却获得了另外一种功效:思考宇宙的来龙去脉;或者人生的意义之类。后者与人类的生存无关,因而无法用自然选择原理加以解释,当然神创论更乐于从神授角度做出解释。但古尔德提出的却是一种科学解释,因为它引用的是自然的原因,只是与直接的自然选择机制无关。
但佛笃还不满足于此,他要论证的是,进化的动力非自然选择,而是源于生物体的内部结构规定。比如,猪和鸟都生活在蓝天之下,为何猪却没有长出翅膀飞起来?这就是说,它们都面对同样的生存环境或选择压力,却演化出不同的适应对策。究其根本,这与猪和鸟起源于爬行动物的不同谱系有关,也就是说,当初结构上的某个偶然差异,却导致后来的分道扬镳,物种的多样性正由此而来。可见佛笃指出的这一事实没错,用一个专业术语来说,这就是进化的路径依赖现象。但路径依赖与进化动力却是两码事。而佛笃的用意却在于,要回答猪为何无翅,只要考察其身体构造足矣,无须问其适应意义,因此也就无须劳驾自然选择机制。如此说来,佛笃认同的达尔文理论仅是其中的一半:生物的共同由来说。至于另一半,自然选择原理,在佛笃看来,远远谈不上是一种自然法则,而只是一种历史叙事。
说其是历史叙事,而不是科学法则,那是因为科学法则应具有预言功能,而自然选择似乎缺乏这种功能,它只能做事后解释,类似于历史学对历史事件的解释。比如就已经存在的鹿角而言,进化论者解释说是一种炫耀工具,但却无法预言争夺配偶的需要是否一定会导致鹿角的出现,毕竟各种动物早已进化出形形色色的方式用以争夺配偶。那么,自然选择原理是否要被开除出科学的行列呢?
这就必须澄清预言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问题。在科学中,有时预言与解释好比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比如,当初白人首次踏上美洲大陆,导致土著印地安人大量死亡,其中的许多人,不是死于白人的枪炮,而是死于白人带去的种种传染病。③这是因为印地安人没有畜牧业,因而没有机会接触源自于动物身上的种种病菌,他们的身上就不存在相应的抗体,当从白人那儿首次接触这些病菌时,纷纷死亡。这种解释就是基于自然选择原理,即不具抗体的个体被自然选择所淘汰,能生存至今的个体都带有抗体。它同时还具有预言功能,未来若是出现一种新的传染病源,在缺乏有效干预措施的情况下,必将淘汰那些不具抗体的个体。但自然选择确实难以预言具体的细节,比如,在争夺配偶时,是通过鲜艳的羽毛还是婉转的叫鸣声来吸引雌性的注意,对此类现象只能做事后解释。这是因为自然选择的前提取决于偶然不定变异,这就决定了细节的出现是一个无法预言的事件。
然而,引入可预言性作为自然科学的必要条件,恰恰是对科学的某种误解。预言的成立仅仅在经典物理学中,量子力学、统计力学、混沌学都不具有可预言性,亦即偶然并不是源于我们的无知,而可以是事物的本性。若是如此,又怎么能够苛求自然选择原理一定要具有可预言性呢?可见佛笃对自然选择理论的质疑难以有效,既然如此,自然选择理论的科学地位不容轻易剥夺。
三、利己与利他之争
达尔文在另一部巨著《人类的由来》中讨论了人类的起源问题,其中主要涉及到道德的起源问题。道德是一种利它现象,但自然选择强调的却是个体间的竞争,能够胜出的个体必然具有自私性。那么,在达尔文理论的框架内,利己与利他如何得到统一?
要说清其间的关系,首先必须澄清自然选择作用的层次,是基因、个体还是群体。在达尔文时代,基因概念尚未出现,达尔文当然站在个体选择立场上。不过当代两位进化论巨匠道金斯和古尔德却分别站在基因选择和个体选择的立场上,争得不可开交。以道金斯为代表的基因选择说的是,基因之间的竞争决定了优胜劣汰,选择就在基因层面发生。理由是,自然选择作用的对象必须是一种相当稳定的实体,相比于个体,基因的寿命要长得多。成吉思汗征战欧亚,不要说他个人,他所创立的帝国早就分崩离析,但他的基因依然留存于其后人身上。但古尔德却认为,单个的基因难以分出好坏,它们必须相互合作、亦即结合成为个体才有意义,这就是个体选择说的内容。但究其根本,基因选择与个体选择并无实质区别,它们倒是有一个共同的对立面,那就是群体选择。
上世纪60年代,群体选择论曾兴盛一时,因为它似乎为利他现象提供了便捷的答案。比如,个体的衰老就是为下一代的兴起腾出必要的空间,这种牺牲当然有利于整个群体利益。于是,动物之间的互助、甚至包括人类的道德行为似乎都有了合理的解释。但群体选择论恰恰与达尔文理论的核心思想背道而驰。因为达尔文强调的是,自然选择作用于个体而非群体之间的差异。个体只图自身的利益,不会考虑群体的福祉。若说存在群体意义上的适合度,那也只是个体适合度的叠加而已。举个例子,当一头鹿通过迅速奔跑逃脱了熊的追捕时,它经受住了自然选择的考验,当鹿群中更多的鹿都经受住这一考验之后,这群鹿就表现出群体层面上的适应现象。
美国进化论者乔治·威廉斯就是群体选择论的坚定反驳者,其成名作《适应与自然选择》集中表达了他的主要观点。威廉斯的一个中心思想即是,只要可能,就必须立足于更低、也是更简单的层次上来解释现象。比如,狐狸雪夜去鸡窝,肯定会在雪地留下足印,当它明晚再去时,足印有利于它少走弯路。但对留下足印的恰当解释只能是,那是一种偶然结果带来的好处,而非狐狸有意为之。④再以蚯蚓为例,蚯蚓在地里掘食有益于土壤的形成,但对此的解释同样只能是,那只是这种取食活动带来的额外好处,而非蚯蚓有意为之。同理,许多群体利益其实只是个体获取自身利益后的额外结果。正如亚当·斯密所说,面包师为我们提供晚餐只是出于他的私利,而非恩泽于社会的慈善之心。可见集体利益必须以满足个人利益为先,这已成为当今文明社会的共识。
但问题在于,普遍存在的利他行为如何解释?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社会性昆虫,如蜜蜂的行为,不育的工蜂无私地为其姐妹哺育后代,简直就是人类难以企及的道德境界。但若从基因层面来看,这种行为就非常容易解释。由于特殊的生殖模式,工蜂与其姐妹(蜂后)的亲缘系数为3/4,而不是通常的1/2,这就决定了工蜂那种表面上的利他行为,其实有利于自己基因在后代的传播。这就引出了一个概念,亲(缘)选择:针对近亲的利他行为可能有助于间接地传播利他者的基因。当一个群体由近亲个体组成时,基于亲选择机制,个体就会表现出某种利他行为,从而使群体得益。一个极端例子就是个体,组成个体的每个细胞都是由相同的基因组成,它们的亲缘系数为1,这就决定了组成个体的细胞可以为了整体的利益牺牲自己,以达到让生殖细胞能够传宗接代的目的。
在大多数时候,个体利益符合群体利益,此时难以验证上述哪种解释模式更好。但也有时候,两者发生冲突,这就给出了验证可能。比如,处于外围的鱼容易成为捕猎对象,于是,所有的鱼都竭力往中心钻,结果就是鱼群的形成。但不幸的是,当遇到大型捕猎者时,后者往往一口就可以吞下整个鱼群。又如,加拉帕戈斯群岛上有一种莺鸟以仙人掌为食,有个别莺鸟在采食时会折断花柱,以便啄到更多食物,但此种自私行为却有可能让仙人掌绝种,从而毁了群体利益。事实上,这种莺鸟后来果然灭绝了。在上述例子中,群体利益均成为个体利益的牺牲品,可见自然选择并不优先顾及群体利益。
有上述背景知识作为铺垫,我们再来看陈晓平在文中提出的观点。他首先反对的是基因选择,理由如下。首先,个体具有独立生命,而基因却谈不上。比如,一对同卵双胞胎,就基因而言一模一样,他们理该彼此视对方为自己,但事实上从未出现这种情况。同理,父母同其子女的亲缘系数为1/2,同胞手足之间的亲缘系数也为1/2,但常识告诉我们,两种亲情没法相提并论。其次,说基因长寿稳定,那还不如拿原子说事,原子更为长寿稳定。但这一论点显然难以说通,因为基因是最小的遗传单位,而原子不是。最后,进化体现为“物种适合度的不断增加,而不是对已有性状的原原本本的复制。”就最后一点来看,陈晓平的真正立场其实是群体(体现为物种)选择。
以同卵双胞胎或两种不同的亲情为例,基因选择确实不足以完全解释这些现象。由此必须引入更多的相关解释。就以同卵双胞胎来说,完全相同的基因型不足以决定其自我意识,这是因为自我意识的形成还与后天大量的体验活动有关。⑤正是各自不同的体验决定了他们只能是两个完全独立的自我。但附加解释与基因选择决不冲突,尤其在低等动物的情况下,我们更可看出基因选择的强大威力。这就好比伽利略提出的自由落体定律,在现实生活中常常难以真实体现,因为它还有附加条件:在真空之中。但我们并不以此否定自由落体定律的有效性。相反我们承认,不少科学定律仅在理想情况下有效。基因选择原理也是如此,当用于人类这种复杂生物时,就必须添上更多的附加条件。但附加条件再多,根本有效的机制依然是基因选择原理。其实这也早被常识所认可:世上只有妈妈好。母爱的原始基础即为血缘之爱,也就是基因的传宗接代所需。
陈晓平在文中还提出这一事实作为亲选择的反例:配偶双方在亲缘系数上大多远小于它们各自的血缘亲属,但配偶之间的利他倾向一般大于直系以外的血缘亲属。对此的解释是,亲选择仅针对具有近亲关系的个体,至于配偶之间的互助行为,仅是因为它们在抚育后代方面达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对此的验证是,仅在后代必须抚育的情况下,配偶之间才有牢固的联盟;反之,它们就会是“露水夫妻”式的关系。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到来各自飞的情况,在人类生活中比比皆是。总之,利他行为的存在并不必然推出群体选择的有效;相反,基于基因选择,利他行为能够得到合理的辩护。
四、道德的自然史追问
其实达尔文并不以为利己与利他构成一对悖论。达尔文深受他的前辈、苏格兰哲学家休谟的影响。不同于传统观点,休谟认为,道德感深植于情感而非理性之中。这是因为道德离不开行动,而理性只能帮助我们辨别真伪或者说发现事物之间的联系,只有情感才能成为我们行为的动机。归根结底,行为的动机离不开趋乐避苦,快乐或痛苦就是一种情感。但人若只是一味追求趋乐避苦,显然谈不上道德境界。在此重要的是,休谟强调,人还是一种社会性动物,借助合作,人才有可能生存下来。彼此的合作离不开某种纽带,这种纽带就是两性之爱及其由此衍生的对子女的关切之情,这种关切之情甚至还可延伸至旁人,其间起作用的就是同情能力。因而休谟高度评价人的同情能力。显然同情也是一种情感,正是借助于这种情感,人类有了利他行为,这就是道德感的起源。作为一名博物学家,达尔文还就此引入科学论证。达尔文以翔实的资料表明,情感是一种先天性状,甚至动物中也存在情感,养过宠物的人们想必对此不会有异议。如果道德源于情感,这就表明人与动物之间不存在难以跳跃的鸿沟,动物中甚至也有道德的萌芽。这样的观点在当时难免骇人听闻,不过如今已得到实验验证。有实验表明,当研究人员让一头猴子电击另一头猴子,同时给予这种行为以奖赏时,发现该猴子在发现被电击的同伴有痛苦的表情时,却不愿再实施电击行为,哪怕因此而牺牲奖赏。这头猴子表现出来的显然是一种道德行为。
达尔文更深入的工作还表现在,他把此类情感或本能分为两大类:一般本能和社会性本能。前者指向自我利益,表现为食欲、性欲等,目的是保存自己;后者指向群体利益,目的在于合群,或协调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表现为羞愧、慷慨、感恩、内疚等等。更为重要的是,达尔文还指出,这些情感的获得本身就是自然选择的产物。对于群居动物来说,那些不具社会性本能的个体往往会被淘汰,由于它们的不合群,作为“害群之马”,它们自身的适应度就降低了。因而选择的对象依然是指向个体而非群体。道德感的起源即在于社会性本能压倒一般本能。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就会表现出“舍生取义”、“不食嗟来之食”、“坐怀不乱”、“视富贵如浮云”等气节。
可见从休谟、经亚当·斯密直至达尔文,并不视利己与利他为不可调和的冲突,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本是人性之中同时并存的两个方面。在此意义上,一个完全自私的人或一个大公无私的人都难得存在,个体的道德感或多或少存在差异。一个文明社会所要做的,无非就是为社会性本能的胜出尽可能提供适宜的条件。
注释:
①②〔英〕F·达尔文:《达尔文生平》,叶笃庄、叶晓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06、315页。
③〔美〕贾雷德·戴蒙德著:《枪炮、病菌与钢铁》,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8月。
④〔美〕乔治·威廉斯:《适应与自然选择》,陈蓉霞译,上海科技出版社,2001年6月,第10页。
⑤〔美〕达马西奥:《感受发生的一切》,杨韶刚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