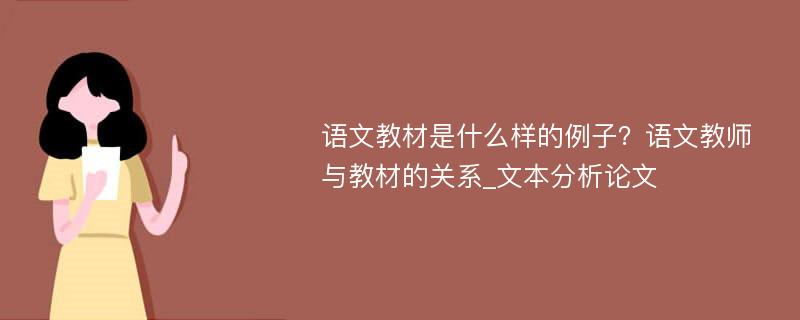
语文教本成为何种例子?——语文教师与教科书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本论文,教科书论文,语文教师论文,例子论文,语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语文教科书的改革是这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重要的一项工作,目前正流通于市场的教科书,不论从选文还是设计,都力图体现新课程的理念,可以说,我们的语文教科书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很多教师在处理教科书时,仍是陈旧的观念,对文本的分析仍是释词—分段—概括段落大意—归纳中心—提示写作特色这种刻板的模式,而且教师本身对文本的解读也很机械。照此,教科书就被看成仅仅是换了几篇文章而已,而其中的新的理念却被覆盖了。其实对教科书的使用,关键在“人”。如果使用教科书的“人”不更换思想,单是教科书在改,其收效是不大的。
笔者在研究中发现:目前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对教科书的使用主要有如下表所示的两种倾向:
教科书使
交往模式
言语行
表达的内容
有效性要求
用的类型 为类型
再现性知
认知式
断言型
陈述内容
真实性
指向性知
表达式
表白型
说话者真诚性
识倾向
的意象
一、再现性知识倾向
有学者在对一所小学的调查中发现:“在语文课堂上,丰宁小学的老师贯彻‘课程内容’的努力首先体现为一种顽强的‘课文至上’的追求。教师们都有一种不言而喻的视课文为神圣的职业意识,她们课堂活动的中心任务就是让学生不留任何缝隙地吃透课文,掌握课文所言所述的每一处细节,所以她们就来来回回地用各种方法重复课文,这一工作占去了她们在课堂上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而她们讲解课文的首要目标则是让学生明白课文到底讲的是什么故事,也就是说让学生掌握课文的情节。”(注:笔者调查、访谈的实录.)这种情形,在我国语文课堂教学中可以说是普遍存在的。教师在教学中要不厌其烦地把课文讲深讲透,不辞劳苦地加课补课,生怕教学内容有所遗漏疏忽。于是语文课堂就成了教师喋喋不休于课文写了什么?是怎样写的?这样写的好处在哪?作者为什么用这个词、这个例子?等等这类抽象的分析,学生也只是为了回答教师的分析提问。教师越是讲得彻底,就越是好老师;学生越是记得一字不差,就越可能成为好学生。对于语文教师来说,教什么和应该教什么,已成定论,关键是如何教的问题,因此总在致力于寻找一种教学方法,使教员因此可以少教,学生可以多学,由此把教师视为一个有知者,学生作为一个无知者,从而体现教师自身的价值。
为了传递教学大纲、课本规定的知识,非常需要时间的保证,因此教师们要极力回避课堂上出现的干扰。从与一些教师的谈话中了解到,现在语文课时是非常紧的。自实行双休制以来,语文是每周四个课时,有的学校加到了每周五个课时,但老师们仍觉得不够用。在笔者的问卷调查中,大部分老师说会考虑到课堂上出现的“干扰”,但同时强调,只要时间允许。学生们也说,当与老师有不同意见时,老师一般要求下课再问。学生会考结束后,笔者想到学校继续听课,老师们善意地建议我:现在听不出什么东西,因为我们正在赶课,下学期再听吧。(注:李书磊著.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63.)
教师的感慨引起笔者深思。在笔者看来,任何文章都应该是带着感情去阅读的,任何文体形式都是一种生命的存在形式、表现形式,不论什么文体形式都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生命的交流,脱离开此,这些文字组合只是一些僵死的符号。因此,不管是教师与文本间的交流,学生与文本间的交流还是师生间的交流,都是一种建构性的情感的交流,都不可能完全再现文本的客观内容。但在现实的教学过程中,这却是大家所追求的。
二、指向性知识倾向
让学生知道什么,即如何真实地再现课文的意义,让学生了解课本、教师所表述的内容,笔者认为这只属于表层知识。如果仅限于达到这一层次,那么,语文教学就变成一种信息学,只管啃咬脱离具体背景的信息。然而对于传递这些信息而言,教师并不比教参讲得更详细。在这种情况下,教学本身容易沦为某种形式的程序操作,也就是说,生活的存在、教师的存在、学生的存在、课本的存在是各自独立的,他们之间不可能发生什么真正的际遇。而指向性知识倾向,正是立足于怎样避免刻板地理解文本,旨在教会学生如何将根据自己的经验及其相关领域的运用,能重构所要理解的文本,这是一种深层理解结构。在这样的理解过程中,重要的不是理解是否与被理解的东西相符,即确定性的获得,而是让学生有能力知道怎样的理解是可能的,以及是否是合理的。学生不是就课文而学习课文,要让学生能把方法、内容和整个课程的结构及其在社会现实中的意义联系起来。正如多尔创设的“舞蹈型课程”,其中的舞步是两个舞伴之间——教师与课本、教师与学生、学生与课本——交互作用的结果。这样,“意义不是从文本中提炼出来,它是我们与文本的对话中创造出来的。”(注:[美]小威廉姆斯E·多尔著,王红宇译.后现代课程观[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149、193.)
但是在现实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时时克制自己,只用一套标准的、已成定论的解读方式,只有让学生记下了这种解读之后,自己才能松口气。学生们也养成了这种规范的思维方式的习惯。上了大学,还是一样的套路来解读文学作品,这样的影响太根深蒂固了。教师们也如此,常年的如此备课,不这样讲还真不知怎么讲了。我们老说语文教育要贯彻人文精神,这不是口号,这是要用心灵去贯通的。如果师生之间、师生与教科书之间真能告别这种僵硬与冷漠,那么教科书中文化传承的表达式的交往模式、表白性的言语行为类型、根据说话者意向的表达内容与真诚的有效性要求也就不再只是一个个希望。正如童庆炳先生所说:“我们现在的孩子们,不会正确地运用自己的笑和自己的哭。为了生活和感受,我们需要美丽的笑和充满美丽的泪。当语文课能让孩子们自然而然地留下泪来的时候,那么语文课也就成功了。”(注:童庆炳.语文与流泪[J].语文教学与通讯,2000,3/4.)
三、有效的对话:师生与教科书融通的关键
教师如何才能处理好与教科书之间的关系呢?笔者认为,有效的对话是师生与教科书融通的关键。20世纪后半叶以来,文化多元化的格局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中国的基础教育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面临着复杂、多元的文化生态环境,这必然会对学校中的语文课程产生影响,用一套标准答案、单一的文化价值观一统学生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我们应该接受的是包容差异、着重建构的多声部对话,而不是一味强调对话的一致性与共通性。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应该区分清楚真正意义上的对话。
霸权支撑下的对话
在平时的教学中,我们习惯于视教科书中包蕴的知识是独立于人之外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去适应它。为了在学校中获得成功,学生们必须成为能接受教师传授知识的人,而不对此表示怀疑。教师也认为教学是把基础知识传给儿童从而让他们能进行“值得做”的活动。于是,教师的问题就转变为如何去设计更有效的方法尽他们所能尽可能多地向学生传递这些知识和技能。当学生排斥学校所传给他们的与自己的世界具有中断性的知识时,学生们始终被视为是低能的或是没有学术水平的。这个观点被巴西的激进的教育家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作为“去人格化”(dehumanizing)与“神秘化”(mystifying)的学习过程来批判。弗莱雷在对教育实践长期的探讨中发现,学校教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讲授”,就是要用教科书中的客观知识去填充学生。学生的主要任务就是接受,并把教师所讲的东西如银行储蓄般“储存”起来,储存越多,意味着越有机会造就学业成功。
在这种填充——储存的过程中,知识被视为私有财产通过教科书经由教师传给学生,这种对教科书的使用方式压抑或者说剥夺了学生以致教师的灵活性与创造性。由此,弗莱雷提出要用“对话式教学”取代这种“讲授式教学”。现在很多语文教育实践在教材使用过程中也在强调着“对话”,但是我们也得思考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对话。大而无当的训导,倒会使我们失去对话的基础。“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成为教育工作者的基本信念,贯穿教育活动的始终。但是,在尊重学生主体——己(老师)所不欲勿施于人——还学生空间这一线索中又暗含着另一文化霸权:“己(老师)所不欲勿施于人”,意味着只有“我”(老师)才有权力判断什么东西是普遍可求的,根本没有想到他人想要的是什么;只有“我”(老师)的心灵才是个有资格的心灵,其他人的心灵则加上括号不需要在场。尽管也会让学生讨论,让学生各抒己见,但教师最后一句话“我来归纳……”又把学生拉人了“正轨”。这当然不是一种有效的对话,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对话呢?
平等的对话
在学校语文中,对教科书的学习是一种特殊的阅读活动,是学生、教师、教材编者、文本作者之间的多重对话,是思维碰撞和心灵交流的动态过程。其中,每一个学生个体与教材作品中的作者进行直接对话应该是中心,其余的几重对话应该是为这个中心服务的。其特征如下:
第一,对话是平等的交流。即对话的双方既不是“主子”的身份也不是“奴才”的身份,而是以合格的“人”的身份来对话。读者与不在场的文本作者是一种平等的身份,学生读者与教师,师生与教材编者之间也是一种平等的身份,谁也不迷信谁,谁也不是先设的阐释标准。而应是通过感性认识、理性思考之后的交流而获得的意义。
第二,对话是带着差异的共同生活。话语有个体差异性,然而,一味让大家陷入各自的差异中,只能成为一个个孤独的个体,其危害与重“一致性”是一样的。有效的对话应基于不仅要知道我不同于你,你不同于我这一事实,更要问问你怎么不同于我?我怎么不同于你?承认不同个人间文化的深刻的互联性,关注着大家如何带着差异共同生活在一起,从而共同丰富着文化的内涵。
第三,对话是爱心的付出。鲁迅曾在二十世纪初期就提出在我们国民性中最缺之“诚”与“爱”。没有“爱”,作品中的意蕴就还原为一个个僵死的语言符号,就不会存在对话。对文本而言,这是一种感情积淀的爆发,应该是一种投入感情的阅读,是一种读者与作者的跨越时空的交流,麻木的心灵是对话的大敌。
叶圣陶先生在论及语文教科书时说:“语文教本只是些例子,从青年现在或将来需要读的同类书中举出来的例子”,其意是说你如果能够了解语文教本里的这些篇章,也就大概能阅读同类的书,不至于摸不着头脑。所以“语文教本不是个终点,从语文教本入手,目的在于读种种的书。”(注: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182-183.)加拿大教育家史密斯曾说:“教学不能仅仅意味着讲,教学应当成为一种订约:教师指出一条路,学生经由此路能够理解并能进入他(她)自己的那个活着的、流动的传统中去。”(注:[加]大卫·杰弗里·史密斯著,郭洋生译.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230.)两位教育家的表述不同,但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主题:理解接受教科书的活动是一个不断创造、意义不断生成的活动。教师不可能穷尽教科书的意义,学生的接受也不是一种复制过程。我们当然不希望我们的学生只是从教师那学到一些“守株待兔”用的知识。我们要通过教科书的学习,培养学生的一种对生活、对人生的感觉,唤醒学生那颗本来纯真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