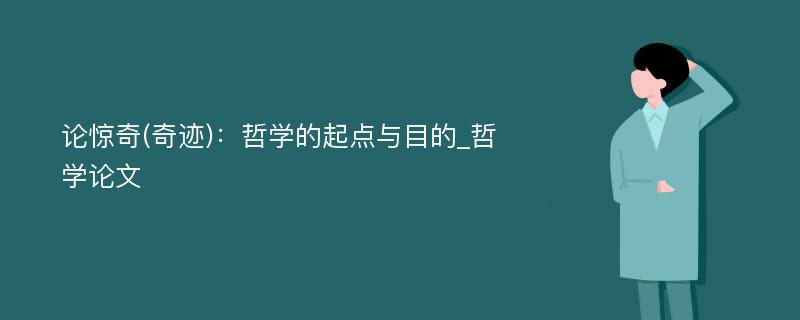
谈惊异(Wonder)——哲学的开端与目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目的论文,惊异论文,开端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西方旧形而上学认为惊异只存在于哲学的开端,哲学靠结束惊异而完成其目的——对事物的本质的认识。本文受海德格尔哲学的启发,认为人不仅在从无自我意识(不分主客)到有自我意识(能区分主客)的“中间状态”中能激起惊异,兴发诗兴,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从主客二分到超主客二分、从有知识到超知识的时刻也会激起惊异,兴发诗兴。本文吸取了尼采、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主张打破西方旧传统,建立以超主客二分的主客融合为最高原则的哲学,把惊异和审美意识看成不仅仅是哲学的开端,而且是贯穿于哲学之始终的目的和任务。哲学本身应该是诗意的创造,哲学和人生本来是美妙的——令人惊异的。
关键词 惊异 哲学的开端 哲学的目的 主客二分 超主客二分海德格尔
知与无知相对。人是怎样由无知到知的?如果处无知而不自知其无知,则不可能兴起求知欲,不可能有对知识的追求。一旦意识到无知,立刻就开始了求知欲。惊异就是对无知的意识,或者说是求知欲的兴起。“对于一个正方形的对角线的不可计量性不知其原故的人,是可惊异的。”〔1〕“一个有惊异感和困惑感的人,会意识到自己无知。 ”〔2〕所以惊异像牛虻一样,有刺激人想摆脱无知而求知的作用。 亚里士多德正是在讨论知识——讨论探究终极原因的知识即哲学时谈到惊异的。惊异是求知的开端,是哲学的开端,——这个断语成了此后哲学工作者所最熟知的成语之一。这句话的原文是这样说的:“人们现在开始并首先在过去开始作哲学探索,乃是通过惊异。”〔3〕我们平常笼统地把亚里士多德这句话理解为“哲学开始于惊异”就完事,而不再追问亚氏这句话为什么只说“现在”与“过去”,而不提“将来”。美国教授、欧洲大陆哲学专家John Sallis深刻地看到了这个问题。〔4〕他在征引了亚里士多德的那句话之后问道:为什么惊异只在知识追求的开始,而“不属于知识追求之所向的将来?”〔5〕原来亚里士多德认为知识追求必然引导到惊问开始时的“反面”〔6〕,即不再惊异、不再无知。 这样,惊异在本质上就与无知联系在一起,“最终,知识与惊异相对立。尽管人是通过惊异才起而追求知识,但这个追求的最终结果却是消解惊异。归根结柢,在知识中将没有惊异的地位,……哲学将会是靠结束惊异而完成其目的”〔7〕。J.Sallis 所看到的问题及其对问题的这一分析,颇富启发意义。
惊异只属于哲学的开端吗?惊异与哲学的展开和目的是对立的吗?这是一个关系到哲学为何物的大问题。
柏拉图把世界分为可理解的世界和可感觉的世界,在他看来,哲学就是对外物的本质的知识性追求,哲学的目的就是“认识理念”。在柏拉图那里,惊异只是由于感性事物中对立面的混合、混杂所引起,或者说,是由于对立面的混合、混杂这样一种感性表象所引起,而在可理解的世界中,对立面则不再是混合、混杂在一起,而是疏理清楚了的,哲学也就在这里展开。〔8〕这也就是说, 哲学的展开和目的不是惊异于感性世界的感性表象,而是在于可理解的世界中关于对立面的疏理。柏拉图在西方哲学史上为把哲学的目的与惊异对立起来的观点开了先河。
自柏拉图以后,西方旧形而上学传统都把超感性的形而上的本体世界当作哲学所追求的最高目的,哲学于是越来越远离了惊异。黑格尔在这方面是一个集大成者。黑格尔说:“希腊精神之被激起了惊异,乃是惊异于自然中自然的东西。希腊精神对这自然的东西并不是漠然把它当作某种存在着的东西就完了,而是把它视为首先与精神相外在的东西,但又深信和预感到这自然的东西中蕴涵着与人类精神相亲近和处于积极关系中的东西。这种惊异和预感在这里是基本的范畴。但希腊人并不停滞在这里,而是把预感所追询的那种内在的东西投射为确定的表象而使之成为意识的对象。……人把自然的东西只看作是引起刺激的东西,只有人由之而出的精神的东西才对人有价值。”〔9〕这里, 黑格尔显然是把惊异理解为只是激起精神的东西的开端,而不是对人真正有价值的、值得追求的目的即精神的东西本身。惊异只是处于意识刚刚从不分主客到能看到自然的东西与精神的东西“相外在”的初醒状态;换言之,惊异意味着刚刚从无自我意识中惊醒,至于真正清醒的状态,即“精神的东西”本身,则不属于惊异。
如果说上面的引文还只是代表黑格尔对古希腊人所说的惊异的理解,那么,下面的一段话就可以直接说明黑格尔自己对惊异的理解和观点。黑格尔在讲到认识过程的初级阶段“直观”(Anschauung)时说:“直观只是知识的开端。亚里士多德就直观的地位说,一切知识开始于惊异(Verwunderung)。在这里,主观理性作为直观具有确定性,当然只是未规定的确定性,在此确定性中,对象首先仍然满载着非理性的形式,因此,主要的事情乃是以惊异和敬畏来刺激此对象。但哲学的思想必须超出惊异的观点之上。”〔10〕黑格尔在这里再明显不过地表达了他自己关于哲学的目的不是惊异而是要超出惊异的观点。在他看来,惊异只属于直观这个初级认识阶段(他干脆把亚里士多德的惊异界定为直观的地位),一旦认识越出了直观的阶段,惊异也就结束。而且黑格尔非常强调认识进展过程中的否定性的作用,认为“推动知识前进的,不是惊异,而是否定性的力量。”〔11〕这就比亚里士多德更进一步把知识、哲学的目的与惊异对立起来了。
黑格尔还扩大了惊异是哲学之开端的含义,认为不仅哲学,而且艺术、宗教,总之,“绝对知识”的三个形式都以惊异为开端,但三者的展开和目的都远离惊异。黑格尔说:“如果就主体的方式来谈论象征型艺术的最初出现,那我们就可以回想起那句旧话,即艺术意识一般和宗教意识——或者勿宁说是二者的统一——以至科学研究都起于惊异,尚未对任何事物发生惊异的人,生活在蒙昧状态中,对任何事物都不发生兴趣,任何事物都不是为他而存在,因为他尚未把他自己从对象及其直接单个存在中区分和解开。但在另一方面,不再有惊异的人,则已把全部的外在性……都看得清楚明白并从而使对象及其具体存在转化为在自身内的精神的自我意识的洞见。与此相反,人只有摆脱了直接的、最初的自然联系和欲望的迫切单纯的实际关系,从而在精神上从自然和他自己的单个存在中撤回并在事物中寻求和看到了普遍的东西、内在的东西和常住的东西,才会发生惊异。”〔12〕黑格尔这段话是在专门分析艺术的最初型式即象征型艺术的起源问题时说的。他认为,象征型艺术或者说整个艺术,起源于惊异,起源于人从不分主客的“蒙昧状态”到能区分主客、能看到外物的对象性和外在性的状态之间。黑格尔强调,惊异只是开端或起源,过此以往,艺术就进到“不再惊异”的阶段,因此,黑格尔认为“象征型的整个领域一般只属于前艺术(Vorkunst)”〔13〕,至于哲学,则不仅超越了艺术,而且超越了宗教。哲学把艺术特别是把作为艺术之开端的惊异远远抛到了他的最高范畴之后。
关于审美意识或诗意的产生,我们平常有一句广泛意义的说法:“人天生都是诗人。”这当然不是说,人从母胎里呱呱落地之时起就是诗人。婴儿在尚无自我意识,尚不能区分主客,尚不能意识到外物时,不可能是诗人。只有在从混沌未分状态到能区分主客的过渡时刻才有惊异、惊醒之感而开始了诗兴。这也就是说,在此时刻之前不可能有诗兴,在此过渡时刻之后,就其处于明白地区分主客的状态这一方面来说,也没有诗兴。黑格尔把这种主客明白二分的态度称为“对于对象性世界的散文式的看法”,“但此种二分总是出现在较晚的阶段,而对真实的东西的始初认识则处于沉浸在自然中的完全无精神性和彻底摆脱自然束缚的精神性之间的中间状态。……总之,正是这种中间状态成为与散文式的理解力相对立的诗和艺术的立场”。〔14〕任何一个人的意识发展过程都必须经历这样一个作为“诗和艺术的立场”的“中间状态”的阶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人天生都是诗人”,或者说,每个人都有诗兴。
但人是否在意识发展到完全明白的主客二分或者说“散文式的看法”之后,就不可能再兴发诗兴呢?不是的。事实上,真正的诗人(不是广泛意义下“人天生都是诗人”的诗人)都是有清楚的自我意识、有自觉、有知识、能明白区分主客的人。但一般人在对世界能够采取明白的主客二分的“散文式的看法”阶段里,往往不再前进而停滞在这个阶段,而真正的诗人则通过教养、修养和陶冶,能超越主客二分的阶段,超越知识,达到高一级的主客浑一,对事物采取“诗意的看法”,就像老子所说的超欲望、超知识的高一级的愚人状态,或“复归于婴儿”的状态,亦即真正的诗人境界。所谓诗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就是这个意思。当然,真正的诗人只能是少数“优选者”,不可能要求人人做到。
海德格尔说:“人诗意地栖居着”,我想这句话不只是指“人天生都是诗人”,而且也指人皆可以经过教养、修养和陶冶而成为真正的诗人或成为真正有诗意的人。
人不仅在从无自我意识到能区分主客这一“中间状态”中能激起惊异,兴发诗兴,而且在从主客二分到超主客二分、从有知识到超知识的时刻,同样也会激起惊异,兴发诗兴。两个阶段的诗兴皆因惊异而引起。如果说前一阶段的惊异能使人自然地见到一个新的视域或新的世界,则后一种惊异可以说是能使人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当然,从广义上说,前一种惊异也可说是创造)。中国美学史上所说的“感兴”,其实就是指诗人的惊异之感。(我之所以把惊异与中国的“感兴”联系起来,是受了叶朗主编的《现代美学体系》一书关于“感兴”的分析的启发,请参看该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9,170,219,221页。)“感者,动人心也。”〔15〕“兴者,有感之辞也。”〔16〕心有所感而抒发于外,就成为艺术,其中也包括诗。儿童即使不经父母教导,也可以在听到音乐时手舞足蹈,这就是一种“感兴”,属于上述前一种惊异;真正的诗人“感时迈以兴思,情怆怆以含伤”〔17〕,这种“感兴”属于上述后一种惊异。这后一种惊异是一种创造性的发现,诗人在这里超越了平常以“散文式的态度”所看待的事物,而在其中发现了一个新世界,好像是第一次见到一样,这就是创造。叶燮说:“凡物之美者,盈天地皆是也,然必待人之神明才慧而见。”〔18〕事物还是原来的事物,但诗人因“感兴”——“惊异”而“见”到其中的“美”,这是诗人之“神明才慧”所创造发现的新奇之处。新奇乃是惊异的结果和产物。
啊!惊异!
有多少美妙的造物在这里!
人类多么美丽!啊!鲜艳的新世界
有这样的人们住在这里!
The Tempest V,i,181—84;译自J.Sallis,Double Truth,第193页
惊异终结之日,也就是新奇结束之时。
西方哲学史自柏拉图以后,特别是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近代哲学史,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把主客二分——主体性当作哲学的最高原则,并从而发展出一套旧形而上学(尽管其中有各式各样的形式,甚至相互反对)。在这种形而上学家看来,个人的意识发展也好,整个人类思想的发展也好,都只不过是从原始的主客不分到主客二分的过程而已,他们似乎不知道有超主客二分的高一级的主客融合。旧形而上学哲学家中有不少人,特别是黑格尔大谈主客的统一,但正如我在很多文章中所论述过的,他们所谈的主客统一都是在以主客二分为最高原则的前提下来谈论的,所谓主客统一只是认识论上的统一,只是通过认识把两个彼此外在的东西(主体与客体)统一在一起,完全不同于超主客二分的主客浑一的“诗意的”境界。这也就是为什么黑格尔把“惊异”和“诗和艺术的立场”只限于从原始的主客不分到主客二分的“中间状态”的原因。惊异终止了,新奇也结束了,世界只是“散文式”的,人们最终能达到的只是一些表达客体之本质的抽象概念,就像黑格尔的由一系列逻辑概念构成的“阴影王国”。哲学成了(除了在开端之外)远离惊异、新奇和诗意的枯燥乏味、苍白无力、脱离现实的代名词。黑格尔虽然承认他的哲学体系的三部分中,以“精神哲学”——关于人的哲学——为最高、最具体的学问,而讲逻辑概念的“逻辑学”是片面的,这是他的哲学的有生气的方面,值得今人大书特书,但他的“精神哲学”中关于“绝对知识”的三种形式(艺术、宗教、哲学)的论述,恰恰是以远离惊异、远离艺术、审美的抽象概念为依归。
黑格尔死后,以主客二分——主体性为最高原则的西方近代哲学基本上终结了,作为概念王国之王的“绝对理念”垮台了,惊异不再只是哲学的开端,而应该成为贯穿哲学之始终的目标和任务。这里的关键在于打破西方哲学史上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以主客二分为最高原则的旧传统,建立以超主客二分的主客融合为最高原则的哲学。尼采,特别是海德格尔,在这方面作了不朽的工作,对破坏旧形而上学,建立融主客为一体的哲学起了划时代的作用。
尼采大力批判了主体、主体性、主客二分和超感性的所谓“真正的世界”。他明白宣布应该“摒弃主体的概念”,“摒弃”“主体——客体”的公式。他斥责柏拉图抬高理念世界、贬低感性世界,是因为“柏拉图在现实面前是懦夫”。他明确主张艺术家比那些旧的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家“更正确”,艺术家“热爱尘世”、“热爱感官”,而旧形而上学者“把感官斥为异端”,他们像基督徒一样“使人变得枯竭、贫乏、苍白”。〔19〕尼采提倡人应该“学习善于忘却,善于无知,就像艺术家那样”〔20〕,这也就是提倡超主客二分、超知识,以达到他的最高境界“酒神状态——一种超越个体、与万物为一的、在更高基础上融主客为一的境界,但这种境界又不是超感觉、超时空的,而是现实的。尼采所贬斥的哲学和哲学家,实指旧传统形而上学和旧形而上学家,他有他自己的哲学,他的哲学可追求的是艺术的境界,诗的境界。这样,在尼采这里,审美意识不再先行于哲学,而是哲学的目的。从此,哲学从“理念世界”、“自在世界”、“绝对理念”之类的“天国”回到了尘世,哲学变得有生气了。不过尼采由于矫枉过正,过份地贬低了主客二分和知识的地位,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尼采是西方哲学史上后主体性——后主客二分哲学中的过激派。
旧形而上学的终结既然把世界还原为唯一的现实世界,惊异也就必然在哲学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海德格尔在这方面作了非常精辟的、正面的论述,这也是他超出尼采的重要论点之一。海德格尔说:“说哲学开始于惊异,意思是:哲学本质上就是某种令人惊异的东西,而且哲学越成为它之所是,它就越是令人惊异。”〔21〕这就明确告诉我们,惊异不只是哲学的开端(且不谈海德格尔把希腊文的开端一词理解为开端的持续),而且哲学本身令人惊异;尤有进者,越是真正的哲学,越令人惊异。海德格尔在《哲学何物?》的讲演中断言:“惊异是存在者的存在在其中敞开和为之而敞开的心境(Stimmung,πáθ·S)”〔22〕。海德格尔认为惊异就是惊异于“人与存在的契合”(Entsprechen ,“适应”,“一致”,“协和”),或者说,人在与存在契合的状态下感到惊异。原来在日常生活中,一般总是采取主客二分的态度看待事物,把自己看作是主,他人他物是客,彼此相对;一旦有了人与存在相契合的感悟,人就聆听到了存在的声音或召唤,因而感到一切都是新奇的,不同于平常所看待的事物,而这所谓新奇的事物实乃事物之本然。所以海德格尔说:“哲学就是与存在者的存在相契合。”〔23〕又说:“诗人就是听到事物之本然的人。”〔24〕海德格尔显然把哲学与诗结合成了一个整体,诗的惊异就是哲学的惊异,都是指人与存在相契合的“心境”或境界。惊异在海德格尔这里完全成了哲学之为哲学的本质。海德格尔哲学的一个重要的有名的观点,大家都知道,就是自柏拉图以来,存在被遗忘了。其实,我们还可以替他补充一句,自柏拉图以来惊异也被遗忘了。海德格尔恢复了存在,恢复了惊异,从而也恢复了哲学的生气和美妙(Wonderful)(即海德格尔所说的“哲学本质上就是某种令人惊异的东西”)。
这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海德格尔认为,惊异不是指在平常的事物之外看到另外一个与之不同的令人惊异的新奇事物,他批评了这种对惊异的看法,他自己的看法是:“在惊异中,最平常的事物本身变成最不平常的”〔25〕。所谓“最平常的”,就是指平常以主客二分态度把事物都看成是与主体对立的单个存在者(beings)。海德格尔认为以此种态度看待事物,存在不可能“敞开”。他的原话:“由于对意识的高扬(在近代形而上学看来,意识的本质便是表象),表象的地位与对象的对立也被高扬了。对于对象的意识被拔得愈高,有此意识的存在者便愈多地被排斥在世界之外。……人不被接纳到敞开之中,人站在世界的对面。”〔26〕反之,在“人与存在契合”的“惊异”中,同样的平常事物就被带进了“存在者的整体”(das Seiende im Ganzen),事物不再像平常所看到的那样,成为被意识人为地分割开来的东西,而显示了“不平常性”,这种“不平常性”就是惊异所发现的。海德格尔进一步指出,正是这种“不平常性”,“敞开”了事物之本然——“敞开”了事物本来之所是。所以只有在超主客二分的“人与存在契合”的“惊异”或“心境”中, 存在才能“敞开”。 〔27〕当代德国海德格尔哲学专家Klaus Held教授说:“惊异使世界变得好像是第一次出现的”,“惊异使人的经验回复到了新生婴儿一样,世界的光亮才刚破烧”。〔28〕Held的比喻和体会很像是老子所说的“欲不学”、“学不学”亦即超知识、超欲望而“复归于婴儿”的思想。要达到这种“惊异”或“心境”的关键在于把平常的主客二分的态度转化和提升为“人与存在相契合”,或者说得简单一点,关键在于超越主客二分,这里的超越不是抛弃,不是超越到感觉世界之外的形而上学的本体世界中去,而是在唯一的可感觉的现实世界之内的超越,是对同一事物的态度的变换。
海德格尔对惊异的看法,和文学家是一致的,只不过是文学家没有作那么多的哲理分析。柯勒律治说:“渥兹渥斯先生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是,给日常事物以新奇的魅力,通过唤起人对习惯的麻木性的注意,引导他去观察眼前世界的美丽和惊人的事物,以激起一种类似超自然的感觉;世界本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可是由于太熟悉和自私的牵挂的翳蔽,我们视若无睹,听若罔闻,虽有心灵,却对它既不感觉,也不理解。”〔29〕文学家柯勒律治的这段话如果用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哲学和语言来概括,那就可以这样说:世界本是一个“人与存在相契合”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事物的意蕴是无穷的,只因人习惯性地以主客对立的态度看待事物,总爱把事物看成是主体私欲的对象,人对这样观察下的事物熟悉到了麻木的程度,以致受其遮蔽,看不到这平常事物中的不平常的魅力,看不到其中的美丽和惊人之处。海德格尔一反西方旧形而上学,把哲学和诗结合在一起,所以他关于惊异是在平常事物本身中发现其不平常性的观点和论述,与诗人、文学家不谋而合。
任何一个哲学家,即使是主张以主客二分——主体性为最高原则的哲学家,其本人实际上也都有自己的“与存在相契合”的“心境”。如果每个哲学家都能像诗人创作诗的作品一样,创作出表现个人独特“心境”(境界)的新颖的、“令人有惊异之感”的哲学作品,那该是一幅多么美妙而令人惊异的景象啊!人类的生命和生活本来是美妙而令人惊异的(Wonderful)。
注释:
〔1〕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1 卷983a12 —13 , 译自JohnSallis,Double Truth,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5,第195页。
〔2〕〔3〕同上,982b12—13,译文同上书,第194页。
〔4〕见J.Sallis,Double Truth,第194页。
〔5〕同上书,第195页。
〔6〕〔7〕《形而上学》,983a12。
〔8〕参看柏拉图:《泰阿泰德》,154b—155d;《理想国》,第7章。
〔9〕《黑格尔著作集》,理论版,Suhrkamp,1970,第13卷,第408页。
〔10〕同上书,第10卷,第255页。
〔11〕J.Sallis,Double Truth,第196页。
〔12〕〔13〕《黑格尔著作集》,Suhrkamp,1970,第13 卷, 第408页。
〔14〕同上书,第13卷,第410页, 参阅朱光潜译黑格尔《美学》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25页。
〔15〕许慎:《说文解字》。
〔16〕挚虞:《文章流别论》。
〔17〕夏侯湛:《秋可哀》。
〔18〕《集唐诗序》。
〔19〕尼采:《悲剧的诞生》,三联书店1986,第331,364 —365,361页。
〔20〕同上,第231页。
〔21〕《海德格尔全集》Frankfurt a.M.Vittorio Klostermann,1975,第45卷,第163页;转译自J.Sallis,Double Truth,第207页。
〔22〕海德格尔:《Was ist Dasdie Philosophie?》Pfullingen,Günther Neske,1956,第26页。
〔23〕同上书,第23页。
〔24〕《海德格尔全集》,第39 卷, 第201 页, 译自“ReadingHeidegger”,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3,第185页。
〔25〕《海德格尔全集》,第45卷,第166页;译自J.Sallis,Double Truth,第208页。
〔26〕《海德格尔诗学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第98页。
〔27〕《海德格尔全集》第45卷,第168—169页。
〔28〕Klaus Held:《基本情绪和海德格尔对当代文化的批判》,载J.Sallis,Reading Heidegger,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第294页。
〔29〕《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第63页。
标签:哲学论文; 柏拉图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尼采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哲学家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