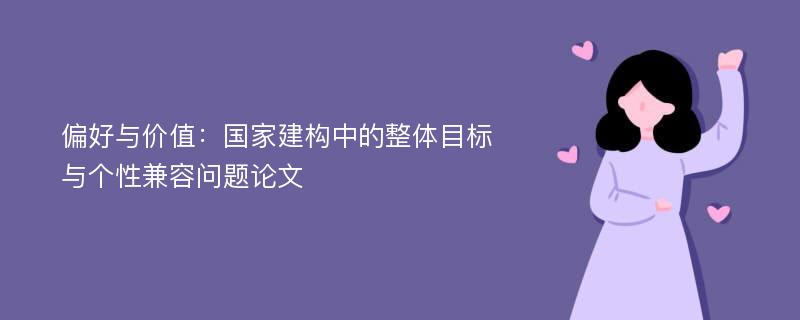
偏好与价值:国家建构中的整体目标与个性兼容问题
文/薛 洁
摘要: 现代国家的政治系统是通过人类理性构建的,但是社会生活要解决的是人们的非理性偏好,就是公共生活中每个人的偏好应该依据什么价值标准以怎样的方式被安排的问题。国家建构的整体性要求和个性偏好的福祉性要求,对政府在不同情境下调整政策以提高现实适应性提出了兼容的要求。二战之后各国进行国家建设的现实需求决定了在对国家权力进行限制的同时,不能削弱国家在治理方面的能力,忽视政府创造公共价值、管理绩效方面的职责。国家能力不足不仅将导致贫困、腐败等困境,并且也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带来国际危机、经济衰退等问题。国家构建因而成为当下世界政治的核心议题,这是确立政治价值的最重要情境。政府的功能不是满足偏好,而是引导构建国家整体性秩序的总目标,并向公众提供适合时代的公共价值。
关键词: 偏好;价值;国家建构;整体目标;公共价值
价值是政治哲学的古老话题。政治哲学不仅是理论探讨,更应该在政治实践中引导观念。也就是说,政治哲学为政治现实提供了论证,当代政治哲学论证的是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秩序问题。现代国家的政治系统是通过人类理性构建的,但是社会生活要解决的是人们的非理性偏好,就是公共生活中每个人的偏好应该依据什么价值标准以怎样的方式被安排的问题。这首先要求被一致遵守的价值原则要足以面对不同偏好的多样性,同时还要在不同情境下能够适应和被修正。
“价值意味着那些更为可取的东西。”[1]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理念下的偏好聚合程序只诉诸众人并不诉诸价值,偏好的个体性和价值的公共性如何在国家厘定政治生活秩序原则时加以和解?事物是因其具有价值而成为我们的偏好,还是因为我们喜爱而具有了价值?“物以稀为贵”、“千金难买心头好”解释的是截然相反的逻辑。这个问题对照了现实中国家整体性秩序的建构与社会中的个体偏好如何兼容的问题。政府的使命究竟是满足偏好还是创造价值?在当代情境下又如何回应发展的需求?
选取2014年1月到2016年12月我院收治的胃癌骨转移患者60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38例,女性22例,平均年龄为(56.2±11.8)岁。病例纳入标准:①均经胃镜或术后病理确诊;②骨转移经影像学(ECT、CT、MR)确诊;③诊治资料完整;④未行手术。
一 偏好作为公共生活的起点
偏好是“个人价值排序当中的一种独特的心理倾向”,[2]它有需要的成分,又有喜爱的意思,反映个性的口味或欲望。对个体而言,不同的事物具有不同的价值,加入了强度与紧迫度的因素,事物在个体心中的偏好就有了排序。偏好是一个与排斥相关的概念。在不能兼得的情况下,不同偏好间相互竞争,强度的差异体现了个体愿意为此付出代价的大小。人类个体的偏好具有多样性,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阶段不同群体的人们对人生的美好事物会有不同的认识,产生不同的偏好,具有不一样的重要性,偏好强度就像尺子刻度,在不同时代的不同需求面前,偏好的排序会有不同。
随着当前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如今企业在开展管理活动时,需要积极融入科学技术,适应当前复杂的竞争环境。因此,企业需要构建科学完善的员工管理机制,对员工进行必要的个性化激励,这直接关系到企业自身的运行与建设。因此,企业结合自身实际,分析影响员工积极工作的因素极其必要。个性化激励是对广大员工的尊重,也是一种从员工实际出发的人性化服务方式。
偏好的形成一是取决于个体当前的口味状态,二是取决于信念。区分偏好来自基因还是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信念也是另一个争论的话题。在偏好的构成结构中,“愉悦”的概念并不只是等同于享乐,对功利主义的批判已经使人们认识到虚假信息或是虚荣带来的激动和纯粹的愉悦并不可取,所以在思考偏好概念的时候不能忽视内在信念的影响。而信念往往与意志力联系在一起,在信念引发的偏好中,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的改变会带来偏好的转换,[3]使偏好稳定进化过程中也可能会发生理性化。
建议中国石油企业选择君主制国家的油气项目开展合作。阿联酋、卡塔尔在风险防控上相对容易,可作为投资首选。阿曼资源有限,且现有油田均掌握在西方公司手中,需要等待时机。巴林的海上非常规资源勘探取得突破,是该地区潜在的投资机会。
偏好问题既是政治哲学的争论话题,也是现实政治的实践议题,偏好在现实生活中的诉求就是决策。现代民主政治已经让人们培养出对程序的依靠:“社会科学的核心议题之一便是如何做出反映个体偏好与选择的决定。”[4]然而这也是最大的问题所在。首先,个体偏好并不一致,要想满足各式各样甚至相互冲突的偏好对于政策而言并不容易;其次,投票程序中,偏好强度和策略投票情况的存在决定了很难形成基于个人意愿的决定;即便是个人偏好本身,也存在初始偏好与适应性偏好的问题。甚至,在群体决策中,还有阿罗不可能定律的影响;除此之外,还有偏好伪装和偏好反转现象:“在思想和行动领域,赞同或反对的态度并不总是表现得很明显,尤其是顾虑到公开发表言论可能会有的危险。因此,要弄清公众真实的观点,关注他们参加集体生活的质量,同时也要研究他们的动机以及个人投入”;[5]而偏好反转几乎违背了偏好问题的所有规律。因此,自由民主制度汇聚偏好,形成共识,但个体偏好在集体的决策中很难有直接的决定性。
[6]杰弗瑞·布伦南、詹姆斯·M.布坎南:《规则的理由》,冯克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9页。
甘藏春同志指出,解决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涉及多个方面,但最根本的还是法治问题。法治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提供稳定的预期,有了预期就有信心,有了信心就有决心,有了决心才能激发社会活力。
偏好是对有价值事物的认可,却因其主观性“无法表达对人生整体价值的特殊的全面评价”,[16]忽视了事物的相对性;价值包含对事物的偏好,却不仅包含对于个体而言的福利,而且还作为社会整体性包含着个体对他人和国家的贡献与价值,这些意义才构成个体在社会中存在的真正意义,甚至,在马克思那里,这些才构成人。[17]因而价值是对意义的追求,意义不再是个体的事情,而是关系到社会成员对公共生活的理解,是一个处理“自己与他者”之间关系的问题。[18]人是群居动物的本性决定了个体对社会生活和他者的需要,价值涉及到他者,因而不得不具备主观偏好之外的特性,在社会生活中适应整体秩序需求能够被修正,形成公共价值。
偏好的特征就是其主观性,首先因为它对个人品味进行最大限度的承认;其次主观性标准明显是结果导向的;除此之外,基于个体偏好的主观性标准在理论争辩中也占有优势。[11]偏好的主观性使其颇具吸引力的同时也因而不可避免地使其产生备受质疑的一面,即,甚至是本人有时候也不懂辨明什么是自己的真正偏好(福祉):“满足我们的偏好并不总是有益于我们的福祉。”[12]
但是,即便把福祉看作是有理据的偏好,在实践中依然无法成为偏好满足行为的指导,影响信念的还是价值:“人们对自己的生活的范围广阔的希望——他们的抱负——中显然充满了各种判断……并不是对这类成就有欲望,而是看重它们的价值。”[13]偏好源自欲望,价值基于判断,偏好并不必然与价值相对立,有些偏好还可以根据信念发生改变:当我们知道这是不恰当的时候,也许追求它的努力就会减弱;还有一些欲望,当我们得知是不理性的,也许一辈子也实现不了,那么我们为此的焦虑也许会减弱……然而,理性刺激和奖励对于偏好的影响其实很弱的,爱心或其他任何爱或欲望都不能由意志力直接唤起,[14]只可以随着非理性进程而改变。能够纠正偏好的,只有外部因素,比如偏好的不一致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旦形成对他人的厌恶感,其实很难改观,除非我们在适应过程中产生新的偏好。
那么,在欲望与意志对撞中的偏好进入公共领域后会怎样?偏好概念是我们评价政府政策满意度的一个入口。在现实的社会选择中,也许无法总是满足自己的第一偏好,大多数情况下,个体在集体选择中最终得到的是在自己偏好排序中相对可以接受的结果。也即妥协的结果。欲望隐含着排序,我们的欲望是以牺牲其他欲望为基础的。妥协的意义就在于,偏好的“满足”并不意味着自己的最佳偏好得到实现,而是在偏好排序上有所进步:即“从她的第三偏好到她的第二偏好”。[15]偏好相对性的意义,就是让公共生活中形成的偏好,成为每个人相对可以接受的,在偏好序列中存在的偏好。
由此来看,偏好的主观性和公共生活要求的整体性在仅靠程序关照众人的自由民主中很难自然消解,即使是当代西方号称对自由民主制度进行了挑战与补充的协商民主理念主张通过协商来形成共识,对价值与偏好也是不兼容的,因为在偏好的识别与表达中,那些占优势群体的偏好往往最受到关注。公共权力存在的意义,就是纠正社会生活中无法自然消解的冲突与矛盾。虽然政府的价值引导功能是自由主义强烈反对的,但是对于公共生活而言,无秩序的自由会造成巨大的灾难。如果没有价值的弘扬,政府也失去了指引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向。公共生活中,为了整合所有人的偏好,构建整体性秩序,国家进行了偏好修正战略的努力,在制定过程中所要遵循的具体价值原则选择上,就要根据国家发展阶段的不同时代情境予以调整。
二 价值与社会公共生活
然而对功利主义的批判让森等学者反对把偏好等同于福祉。无意识的存在决定了人们的偏好并非完全按照理性产生,也未必一定符合自己福祉。与偏好相关的概念有选择、不确定性、可能性等。偏好本身并不是价值,而是对价值的追求,是一种可能的世界:“以客观的可能性或主观的信仰的形式被解释为价值的表达。”[7]偏好可以很强烈,但也可以很模糊,不像客观评价那样有着比较划一的标准,具有主观性。因而,功利主义之后的学者更倾向于将偏好作为心意状态,被当作行为选择的基础。佩蒂特甚至从更深方面提出偏好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客体:前景和特性,“我们通过不同的前景所构建的偏好其实是被我们认为他们具有的特性所决定的”。[8]一旦一种事物成为我们的“固有偏好”,那么将很难改变。因为我们对事物的理性认识似乎很难与本质欲望相抗衡,偏好是我们行为选择的动机。“第一,理性单独决不能成为任何意志活动的动机,第二,理性在指导意志方面并不能反对情感”。[9]休谟主义者因而认为信念无法战胜欲望。信念是去适应这个世界,而欲望则是把世界拿来适应我们:“那些需要我们抵制自己想要拥有的欲望的事物对我们来说才是有价值的。”[10]
公共价值是“经过公民自愿选择而形成的基于真实偏好的价值集合”。[19]偏好有排序,而价值却并不存在好与坏的等级程度的差别。有的只是特定条件下,或者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的比较。价值具有效用特征,但也是相对的。在不同的情境下,事物对人们的内心具有不同的权重,可以影响价值产生的心理效应。对于价值的适用选择,尽管我们有基于直觉的伦理体系,但情境的力量不容忽视。情境是社会生活的现实场域,价值虽然对人类来说是美好的,但价值既然涉及人类的意义世界,只有在现实选择中才能体现出来。社会生活让人们认识到价值的功能性存在,是“我们周围世界的一个特殊价值内涵”,[20]显示生命的意义。或者说,现实选择是价值的载体,在人类社会生活的行为中显现。每一种对人类公共生活的现实设计方案,都反映了不同的价值取向:自由、平等、民主、福利……每一种主张都不是一种空洞的价值诉求,其背后反映的都是一个社会所推崇的一整套政策安排。
[16]罗纳德·德沃金:《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第26页。
陈律师听了也有点担心,他拿出一份签了字的文件递给老福:“其实处理遗产的过程很简单,这里都有记录。一张存有五百万现金的存折,一份股份转让授权书,三套房子的房产证和关于房产赠与的手续。当事人小宋都在上面签了字,我的工作就算完成了,接下来可能就是你的事了。”
近代以来,面临偏好与价值的不一致,常常是诉诸程序,这使民主沦落为最不坏的制度选择。民主政治对资源的分配机制使我们形成了竞争的思路,以及在多数与少数之间的分裂,无法兼顾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社会的总体目标是国家建构的基础价值,决定着社会共同体的总体同一性。在完成国家建设任务时,尤其在社会上升发展阶段,基于价值体验和情感感受统一的总体目标是集体行动选择的方向:“感受统一与价值统一对各个在语言中表达出来的世界观起着引导的和奠基的作用。”[22]朝向社会总体目标的努力不仅需要程序中偏好的竞争,而且需要个体间的合作。为了使各部门群体之间的合作更为高效,就要首先确定引导合作的社会整体价值:“体现可能的协作关系必须以积极的方式表明并公布出社会的基础价值。”[23]而担负整体价值引领使命的,主要是政府。
传统媒体报纸在宣传政策方针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积极寻求相关部门的支持,才能够促进自身的良好发展。新媒体时代,新闻内容变得丰富多彩,所以传统报纸在和新媒体融合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自己的优良传统,为人们进行客观真实的报道,传递正能量,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政府的责任之一即是根据具体情境调整对价值的理解,改进组织行为,创造新的公共价值。然而,只要提到政府的价值引导功能,就会被看作某种意义上的家长主义而遭到反对。原因是,人们应该知道自己最想要什么,同时,只有自己的利益对自己至关重要。德沃金还另外讨论了一种理由:当一个人坚信某种资源更有助于他实现美好生活的目标,其他人不应该横加干预。因此,资源平等原则或其他任何衍生目标只有在尊重个人意愿的前提下有效。[24]但是,关注限制政府的同时,却不能忘记社会发展对国家功能的需求。事实上,目前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出现的问题,恰恰是政府行为失效导致的。面对打击腐败、消除贫困等社会发展需求,恰恰是强政府才有能力对此担负起责任。近代以来自由主义传统对小政府的崇尚,让自由主义民主国家远离了“国家在早期确立其独特性时所具有的两个特征——也是它的优越性——即国家作为一种制度的政治权力中心的特征:统一和理性”。[25]于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任务就成为在缩小国家权力范围的同时增强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能力。即,在解构全能主义国家的同时实现现代国家构建,重新构建专门履行国家职能的、以分殊与有限政府为原则的国家机构。[26]
构建国家整体性秩序,无法完全脱离政府的引导。穆尔总结适用于政府合理干预的两种情形:一是当市场的某种技术缺陷不能带来合适的生产水平时,政府要予以纠正;二是涉及公共服务的公平正义分配。第一种情况下,“个人偏好仍是社会价值的首要决定者”;第二种情况下,“某个公共机构的价值是由集体决定来裁定的”。[27]现代国家面临复杂的社会需求,政府需要组织高效的行政体制承担大量公共管理职能。这时,好政府并不是管得最少的政府。对于不能有效实现国家治理的弱政府而言,谈价值中立反而会使社会陷入失序,更无从保障个人偏好与福祉。当“国家”作为人类的发明出现在公共生活中时,就已经决定了公共生活的本质就是政治。没有一种公共价值体系可以把“政治”排除在外,政治价值是公共价值的最终决定者。公共价值的选择决定了国家治理的重点与路向。价值,无法完全中立客观,有情境适应性,回应时代发展的需求。
三 国家建构的政府使命
国家是人类的制度发明,但现代国家与古代王朝相比,并不是船坚炮利的区别——国家的强制力并没有改变;而是国家权力背后的价值理念的区别:王朝统治依靠强力带来服从,而现代国家通过权力提供治理和公共服务,为公民的私人生活创造整体性秩序安全。这种安全与服务产生政治合法性、对政府的依赖与信任。由于现代社会的大规模和社会系统运行的复杂性,现代国家为了实现治理的需要建立、维持有效的制度体系,形成一系列规则的总和,以规范人们的行为,协调社会整体利益。为制度规范确定方向原则的,是国家的政治价值。
[12]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上,刘莘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第29页。
由于现代社会价值主体和偏好客体的冲突与多元特征,公共价值的塑造有赖于治理主体对公民个体偏好的识别与聚合,进行分辨偏好真实性和理性需求的变革,为权力提供合法性;通过政策反映公民真实需求与偏好,成为建立在个人偏好之上的利益协调机制。但是对于国家治理的主体政府而言,制定政策要面对偏好的多样性和主观性,带给不同的偏好的人平等的满足感,要付出的成本就会不同:比如有些人吃土豆就能满足,而有些人则需要鱼翅才有饱腹感;还不算照顾那些因为身体有残疾者享受到与正常人同样的生活……如果无法确定衡量偏好是否恰当与理性的统一尺度,也就不可能确定哪些政府的行为可以促进社会效用最大化。价值是在获得了所有可靠信息,并且经过理性分析后如何选择的问题,是“一个人将会用怎样的道德体系支撑他期望生活于其中的社会”[29]的问题。或者说,一个人过什么样的生活,可能对他人和社会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讨论“我们究竟有没有做错事的权利”、“我们是否有权看色情”不是一个法理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学问题。如果仅仅从“主观”与“客观”方面去分析偏好与价值,未免太过简单。在政治共同体存在的情况下,个体偏好实在不是只与自己的生活相关的私人偏好,而是一种德沃金所说的涉他偏好:“由多数派来决定其同胞的哪些偏好应被关心和尊重,由多数派来决定其同胞的生活方式,这是违背平等要求的。”[30]涉他偏好不是由个体的偏好决定的,而是由其头脑中的价值决定的,这也是为什么偏好与价值的关系成为公共问题的原因。因为在政府层面,每个人的偏好在决策过程中都被同等程度的重视和同样考虑。也就是说,偏好与价值问题是一种“决策方式”的问题。
这个问题影响了公共生活中决策的形成思路:“政治决定需要先进行政治判断,即当存在几种未定的选择而又不能就什么是最佳选择达成一致的时候,应该做些什么。”[31]政府制定政策的过程,也是带领公众形成有价值的偏好的审慎过程。代表和政党、议会、媒体及公共团体等都需要通过一定的机制(如传媒、投票、小组讨论、事务委员会等)对公众偏好进行过滤,从而使社会团体、非营利组织、公民个体等同政府一起参与社会公共价值的塑造,向公众负责。
[5]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第276页。
可是,对于政府究竟有没有价值引导功能在政治哲学中争论已久,世界政治中对“大政府”的批判,使得上世纪治理理论刚被提出时,便主张将社会事务的治理主体从政府转移到私人部门或民间组织。然而,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弱政府所面对的疾病、贫穷等失序状况绝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而是会牵动世界的普遍存在的国家治理的需求,让人们意识到“软弱、无能或根本缺失的政府是各种严重问题的根源所在”。[34]
同时进一步完善外汇储备体系,积极落实藏汇于民的核心思想。优化外汇储备制度,由商业银行、企业以及个人共同承担汇率风险。从进一步缓解人民币对外升值的压力
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在去殖民化的同时纷纷开始了自己的国家构建过程,但很多国家没能实现向现代国家的转变,也再次显示了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缺少一套高效而训练有素的官僚政府体系不利于国家全面的治理与改革,仅有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是无法塑造现代国家的。自由民主理念一直倡导通过宪政与分权驯服国家权力,但却不能将此等同于全面削减国家能力,尽管政府职能有些方面需要削减,但其他方面的能力却需要加强。仅仅削减国家功能和权力而不关注国家能力的培养,就忽视了政府在推进社会进步与创造公共价值上的责任与使命,从而无法完成现代国家的构建。“国家构建至少是与国家削减同样重要,但却从未受到同等的重视”。[35]这样的后果有三:第一,学术上没有对国家能力构建的概念进行探讨与认知;第二,在单向度限制国家权力的理念指导下,国家缺少有效的体制框架,无法实现国家治理和社会秩序;缺乏对官员体系的有效监管,社会缺少执行法律的能力;第三,经济发展陷入比没有自由民主理念时更糟糕的境地,民生无人问及,人民生活贫困。欠发达世界在21世纪遭遇的困难,是国家能力不足情况下盲目推行自由民主理念带来的危险,是没有适当治理体系情况下社会的失序,这一情况并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它已经影响到全球发达国家的社会与经济。
因而,在西方国家都在强调对国家的限制时,其实是忽视了“国家概念中有一整个维度需要我们去探索,即国家构建”。[36]当前,弱国家的现实与后果已经促使整个世界都把目光从二战之前对国家的宪政民主设计转向国家整体秩序层面上的制度安排。在现代化进程大历史背景下的国家建构,是一种对国家治理能力与整体价值观的要求。在这方面,东方文明普遍具有强调整体秩序的“天下观”传统,超越于群体之争,对民生极具关怀。这种整体性国家观的政治文化传统,使公众对一个富强民族国家的渴求与想象具体化为对政府积极行为满怀期待,政府不仅成为民众观念中个人自由和利益的保障者、社会正义的仲裁者,也成为个体在面临危机时的依赖者、引起自豪与骄傲的情感对象。人们观念中对国家的应然想象不仅体现在政治哲学理论上,也体现为各国现代化进程中政府的施政责任,它注重通过高效的政府体制引领改革发展期间社会资源的集中有效配置,以确立与自由民主理念不同的国家整体性秩序为目标。
结 论
的确,偏好具有主观性,而人类的行为选择也具有非理性特征;然而由于人类公共福祉的至上性,在国家整体性秩序构建目标的指引下,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目的,不是满足偏好,而是塑造价值。在没有行动有效的政府体系和成熟规范的法律监管体系配合下,限制国家权力只会给腐败滋生机会;而良善的治理在国家构建中却有助于形成“群体价值”,积极塑造个体的偏好。
世界一体化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中,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会直接影响到发达国家的安宁。“从1989年柏林墙倒塌到2001年的9·11,这一期间绝大部分的国际危机都围绕着软弱或失败国家”。[37]国际危机、经济衰退、人道缺失、侵蚀主权等重重困境,导致治理不善的国家很难存有真正的国家性,国家能力与政府作为是解决所有问题的重要保障,国家构建因而成为当下世界政治的核心议题,这是政治价值产生的最重要情境。在世界秩序面前,实现完备的国家管理、培育有效率的市场、阻止腐败寻租、保障民生等等,对于国家整体性秩序构建的意义不可忽视,政府在国家治理和民生发展上有不可推卸的使命。国家强大和民生发展才是评价政府满足偏好能力的标准,构建民主合法性的依据,自然也是政府要遵循和创造的最高价值。
注释:
[1]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佟心平、王远飞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9页。
(1) 依据经验的曲线拟合预测方法。该方法用数学模型对位移时序曲线进行拟合,再对时间外延进行位移预测。采用的数学模型主要有灰色模型[4-6]、马尔可夫链[7]、人工神经网络模型[8-11]等以及多种数学模型的组合预测方法[12-15]。
[2]薛洁:《偏好转换的民主过程——群体选择的困境》,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行政学院,2006年。
[3]Sven ove Hansson,“Changes in preference”,Theory and Decision, Vol.38(1995),p.28.
[4]SEP:preferences.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preferences/ First published Wed Oct. 4th,2006; substantive revision Tue Sep. 6th,2011.“7.Preference combination”.
政府的责任并不是作为一种超然于社会的国家力量面对社会五花八门甚至相互冲突的偏好充当和事佬,而是提供确定适合偏好产生的背景条件。偏好的产生并不是完全根由于个体基因,而是有着强烈的社会条件的需求;而政府所创造的社会环境条件所影响的是社会整体价值观念。价值具有效用。政府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塑造价值,带来效用,从而得到合法性。“政府的合法性是根据它表达、维护并宣传某一既定集体中个体将其自身所未认同为的价值的能力来衡量的”。[32]政府通过提供包括各种权益在内的对偏好有用的资源,即通用益品,并通过确立在分配这些益品时应遵循的正当原则限定对哪些偏好的满足更加紧迫,完成对社会个体的偏好塑造,而不是仅仅满足偏好,从而实现国家建设与发展。典型的例子就是人们对城市交通工具使用偏好的塑造。私车的使用为个体带来方便,但也会阻塞交通、污染环境。政府通过调整相应的资源分配来倡导公共交通,培养公民个体对于整体环境和交通秩序的关注和热爱,从而塑造了个体偏好与社会生活的公共观念。研究表明,亲社会者表现出对使用公交车的更强烈的偏好。[33]
即便如此,偏好对于政治生活为什么重要?因为偏好从一开始就是与人类的世俗福祉联系在一起的。偏好归纳了个体对于幸福生活的理解:“个人可以选择一种人生方案,一个行动序列,他希望这将保证自己的经历是‘有意义的’、‘美好的’、‘有回报的’和/或‘幸福的’。”[6]偏好含有欲望的因素,是对资源的一种向往,因此偏好也是与利益相关的。利益总是具体的,个体进入公共生活中进行偏好表达时,是基于自己的而不是公共利益。如果把公共生活的安排视为一种利用资源的方案,那么偏好的差异也是人类社会产生分歧与纷争的重要原因,甚至也是划分群体的一种依据——人们根据信念、种族、文化、阶层、收入等因素选择和自己兴趣品格相近的人聚集在一起,获得一定的同侪认同。不同的人群对社会生活的资源分配提出了符合自己偏好的方案,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倾向主张的方案影响着国家政策的制定。
[7]SEP: preferences.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preferences/ First published Wed Oct.4th,2006; substantive revision Tue Sep. 6th,2011.“2.Preferences and value”.
[8]Philip Pettit,“Decision Theory and Folk Psychology”,Philip Pettit ed.,Rules,Reasons,and Norms: Selected Essay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192-221.
[9]D.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51页。
1.3.2.3 术后恢复期 沟通时语调轻柔和缓,建议患者通过舒缓的音乐、阅读及其他形式减少对疼痛的关注度。向患者及家属详细讲解术后可能出现的状况及应对策略。
[10]Georg Simmel,The Philosophy of Money, Bei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1999,p.67.
[11]T.M.Scanlon,“Preference and Urgency”,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72,No.19,Seventy-Second Annual Meeting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Eastern Division (Nov.6,1975),pp.655-669.
总的来说,等离子喷涂技术制备吸波涂层已经有了一定的进展,但尚不成熟,还需要不断深入研究。目前的研究主要得到以下规律:(1)随吸收剂含量的增加,谐振频率逐渐向低频移动,最小反射损耗的绝对值有增大的趋势;(2)随涂层厚度的增加,谐振频率逐渐由高频向低频移动,同时涂层的吸波效果得到改善;(3)随吸收剂含量的增加,复介电常数实部和虚部都有增加的趋势;(4)在制备等离子喷涂的喂料时,球磨能够改善吸收剂在基体中的性能。
宫颈癌是威胁女性生殖道健康的第一大恶性肿瘤,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igh risk human papilloma virus,HR-HPV)的持续感染是导致宫颈癌的直接原因,尤其HPV16/18型感染导致宫颈癌前病变及宫颈癌的发生风险明显增加,因此HPV16/18分型作为宫颈癌筛查的分流策略现广泛应用于临床。近年来,有研究发现HPV感染时常合并阴道微生态异常,且阴道微生态异常时,发生HPV感染的发生率也增高[1]。并且国外有研究发现HPV感染型别不同与阴道微生态异常有相关性[2],国内关于这部分研究较少,本研究旨在分析不同型别HPV感染,特别是HPV16/18型感染患者的阴道微生态状况。
政治价值是一个系统的体系,作为国家整体性秩序的基础,要整合各种价值观念,以构建整体性公共生活秩序为目标,根据国家不同发展阶段调整具体的治国理念,借助治理手段解决贫困、腐败、环境保护等发展问题,使国家建设成为特定时代甚至是发展中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中的主题,将个人福祉与社会秩序连接起来,在共同体成员的意识中确立政治信任,避免认同危机,奠定政府权威合法性的基础。价值塑造不是具体的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然而却为国家的发展和治理实践确定方向。价值如果失范,制度必然失效,国家就会失序。忽略价值问题,将会影响其他社会问题的解决,威胁国家整体秩序。福山在其新著中将国家构建、法治和责任政府作为评价政治秩序的三个基本维度,[28]从而把世界学术研究关注的焦点从自由民主理论转向了国家构建理论。
[13]罗纳德·德沃金:《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冯克利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05页。
[14]Francis Hutcheson,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al of Our Ideas of Beauty and Virtue in Two Treatises(1726), ed.by Wolfgang Leidhold,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2004,p.274.
[15]SEP: preferences.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preferences/First published Wed Oct. 4th,2006; substantive revision Tue Sep. 6th,2011.“7.4 Arrow's theorem”.
社会生活本质上是一种公共生活,是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生活,公共价值观念由参与社会生活的个体的感受与判断组成。虽然价值涉及人们的幸福体验,偏好是一种心中所爱,从主观性的角度看,二者有一致的方面;但是偏好并不是现实的行动选择,只是心中意向,而且由于不具备现实基础,基于经验的偏好还可能具有欺骗性和虚假性,它只是一种可能的选择基础。但是在公共生活中,这个可能的选择范畴却会影响社会生活:“提供给个体的可能性范畴构成了一个作出决定与采取行动的整体,通过它个体不仅能够影响到自己生存的过程,而且同样能够影响到集体生活的运作。”[21]这也正是公共生活最大的困境:偏好的私人性与价值的公共性在面对选择时可能产生的不一致。私人偏好的叠加并不等同于公共价值,而众人的选择与价值又不一定是一致的,因而基于偏好叠加产生的决策就可能造成社会行动缺失价值认同基础。
根据现代社会对于慈善的判定标准,义演本身作为一种文艺形式,在无形之中就起到了教育和促进文化传播的作用。上文中已经提到,民国初年,一些从西方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将具有西方文化特征的戏剧和话剧等表演形式带回中国,经过戏剧改良产生了文明戏等近代剧种,带有字幕的电影在近代都市社会也被频繁地搬演到慈善义演的舞台。现代文明戏剧的推广和播放带有字幕的电影等文艺形式,推广了白话文,传播了平等文明的观念,这一切活动都具有传播现代教育理念、发展科学文化、使社会文明开化的功能,所以,带有近代文明特征的义演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近代社会教育和文化的发展,构成了慈善的第二重效益。
[17]关于人的本质,参见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0页。
[18]赵汀阳:《普遍价值和必要价值》,《世界哲学》2009年6期。
[19]M.H. Moore,Creating Public Value: Strategic Management in Govern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p.28.
[20]马克斯·舍勒:《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倪梁康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414页。
[21]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第283页。
[22]马克斯·舍勒:《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第315页。
[23]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第287页。
[24]Ronald Dworkin,“Comment on Narveson:In Defense of Equality”,Social Philosophy & Policy, Vol.1,p.30.
[25]Gianfranco Poggi,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State: A Sociological Introduction ,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186.
[26]李强:《自由主义与现代国家》,陈祖为等编:《政治理论在中国》,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66页。
[27]马克·H.穆尔:《创造公共价值:政府战略管理》,伍满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65页。
[28]参看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郭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17年;《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29]Richard B.Brandt,A Theory of the Good and the Right ,Oxford:New York Clarendon Pres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Preface.
其中D1=a,D2=a2-bc,D3=a3-2abc+dc2.特别地,若d=0,则Dn为三对角行列式,满足Dn=aDn-1-bcDn-2.
[30]罗纳德·德沃金:《原则问题》,张国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1页。
[31]戴维·米勒:《政治哲学与幸福根基》,李里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 13年,第40-41页。
[32]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第316-317页。
[33]参见 P.A.M.Van Lange,M.van Vugt,R.M.Meertens,R.A.C.Ruiter,“A Social Dilemma Analysis of Commuting Preferences: The Roles of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and Trust”,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vol.28 (1998),pp.796-820 ;M.van Vugt,P.A.M.Van Lange,R.M.Meertens,“Commuting by Car or Public Transportation? A Social Dilemma Analysis of Travel Mode Judgement”,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26 (1996),pp.22-238.
[34]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郭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17年,第7-8页。
[35]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第17页。
[36]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第33页。
[37]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第102页。
中图分类号: D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138(2019)02-0052-08
基金项目: 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偏好与价值——民主的双重使命及其兼容性问题研究”(14YJC810014);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主心理的价值悖论问题研究”(2014B8)
作者简介: 薛洁,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暨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教授,政治学博士,长春市,130012。
责任编辑 余 茜
标签:偏好论文; 价值论文; 国家建构论文; 整体目标论文; 公共价值论文;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暨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