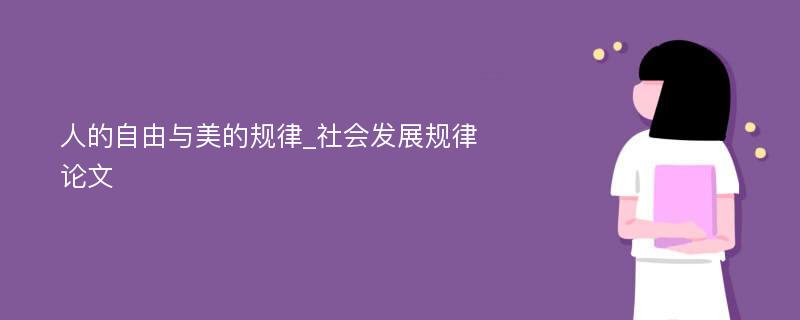
人类自由与“美的规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规律论文,人类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2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0)06-0016-04
“自由”是一个美好的字眼,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之境。“自由”又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人们在广泛的领域里使用它。分析起来,至少有三个层次:日常生活中的自由;政治领域里的自由;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日常生活中的自由是最低层次的自由,是与日常生活规范有关的、一般人能直观地感觉到的一种自由。政治领域的自由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密切相关,但其受关注的程度依赖于同民主政治普及程度有关的民众政治参与意识。哲学上的自由是最高层次的自由,是就人类整体理想而言的一种自由,它贯穿于前两个层次的自由之中,但又不为一般人直观感觉到。本文所要讨论的自由,主要是指哲学意义上的自由。
一人类自由的本质
追求自由是人类的天性。许许多多的思想者从总体上思考人类的自由,试图从终极意义上寻找到人类的绝对自由之境。那么,到底有没有对人类而言的绝对或曰终极意义上的自由?
斯宾诺莎认为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这个观点长久以来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然而,在西方哲学史上,早就有人对这个界说表示不满。康德率先界定知识领域就是必然性的领域,明确划分知识与信仰、必然性与自由,主张在必然性的知识领域之上,还有一个自由的本体界,并把自由从所谓对必然性的认识的老框框中提升到超必然性知识的领域,反对旧形而上学把主体、灵魂与客体、对象混为一谈,揭示主体和灵魂的自我决定的自由本质。由此出发,康德提出“限制知识”的口号,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由不可能在必然性知识领域中得到,只有超出知识领域,才能寻求到自由。康德的这个观点,虽然受到黑格尔等人的批判,但却在西方现代哲学家们那里得到继承、发扬和进一步的完善。
在中国哲学史上,思想家们也非常热衷于探讨自由问题,而且一直都有一种在超知识领域中寻求自由的传统。与康德一样,老子也区分了知识领域和超知识领域,即所谓“为学”与“为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四十八章》)“为学”是对知识的追求,“为道”是对道的体悟,前者属于知识领域的事,后者则属于超知识领域的事。对道的体悟不同于对知识的追求。庄子所说的“心斋”、“坐忘”,主张除去思虑和知识之后,才能达到逍遥自由的体道境界;反之,若沉溺于知识领域,则贵贱、尊卑、成败、大小,判然有别,系之于心,劳其神思,就无法达于“逍遥”之境。儒家也区分知识领域和超知识领域,比如宋儒所讲的“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的区别,即是如此。只不过,他们讲自由,是与道德意识密切相关的。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从心所欲”就是自由,但这种自由是在“不逾矩”即不离开道德上的规矩准则的前提下的自由,是一种相当有限的自由。其后孟子的“浩然之气”,张载的“诚明”,王阳明的“良知”等等,都与自由有关,但又都离不开道德意识,他们实际上是把封建道德准则要么客观化为天命,要么说成人心所固有,从而教人顺之而行,达到不离规范却又不觉得有规范束缚的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这种自由,是戴着镣铐的“自由”舞蹈,远不如道家游于“四海之外”、寝卧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庄子·逍遥游》)那么自由洒脱。
以上所述各种自由理论,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认为在必然性的知识领域中不能得到最高的自由,这种自由一定要到超必然、超知识领域中去寻找。儒家学者和康德都把自由置于道德领域(他们所谓道德的含义是有很大区别的)。康德抽象的道德自由遭到西方现代哲学家们的反对,而儒家的实用伦理道德自由的程度也非常有限。倒是庄子的自由观与西方现代哲学家们十分接近。庄子特别强调“游”在自由境界中的地位,实际上,他的“游”,是所谓“游心”:“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庄子·人世间》)“游心”是一种心灵的游历,是精神摆脱枷锁、获得解放的象征。当他“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庄子·让王》)时,即达到了一种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的最高境界,其实是一种精神的绝对自由境界。西方现代哲学家大多主张自由虽然不在必然性领域中,却也不在另一个抽象的和具有道德意义的世界之中,他们认为自由是对于具有必然性的现实世界的一种态度、心境或“精神状态”,与庄子一样,也是强调一种精神世界的最高自由。当然,他们同时也一再表明,这种自由境界虽是对必然性的超出,但决非脱离具体的现实世界而进入抽象的超感性的世界。
自由是针对人类世界而言的,只有对人类世界才有意义,也只有在人类世界中,自由才成为问题。人类世界是从自然界走出来的,它既超出了自然世界而又未脱离、也永远不可能脱离自然世界;它既指向理想世界而又未达于理想世界(事实上永远不可能完全达到理想世界,因为人类的理想世界也在随着人类世界的发展而变化)。人类的理想世界是最自由的世界,这个世界既根源于现实的必然世界,又不可能存在于必然世界,而是超出了必然世界。这个理想的自由世界只能存在于人类的思维或曰精神领域。人类自由的精神世界与人类的理想相关联,既不能完全脱离必然世界,又必得超出必然世界。因为若全然脱离必然世界,则难免流于绝对空虚;而若不超出必然世界,则又拘于必然性,不能达于自由境界。人类整体的自由精神世界又会随着人类实践和思维能力的发展而变化,它与现实世界始终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有如一颗高悬于人类头顶上方的明星,指引人类向美好的理想世界迈进。
那么,人类如何向自由世界迈进?在这个过程中,要遵循什么样的规律?对这个问题,马克思的一段精辟阐述为我们寻找答案提供了一把“钥匙”。
二“两个尺度”与“美的规律”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1](P53~54)在这段话里,马克思提出了“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以及“美的规律”等重要范畴,牵涉到真、善、美的内涵及其关系。
真、善、美三者各自的含义极其丰富。真,就是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就人类而言,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自然的规律,即人类物质生产和科学研究的自然对象以及人类所处自由环境的本质与发展等客观规律;二是社会历史的规律,即人类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历史发展的规律。善,是指对人类整体来说有利、有益的功利。从哲学意义上看,善与道德应该有所区别。这区别主要体现在它们所揭示的关系上。道德作为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揭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伦理关系;而哲学意义上的善,除了这种关系外,还有一层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只不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尤其是在人类的日常社会生活中,这两个概念却是相通的,道德的就是善的,不道德也就是不善,反之亦然。美,则是指在实践中真、善的生动形象的体现,它是一种以真、善为基础的更高层次和更高境界的东西,具有“润物细无声”式潜移默化的感染作用。三者虽为互有区别的不同范畴,但却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类只有掌握了真,才能获得更多的善;反过来说也一样,人类要想获得善,必以掌握真为前提;又因为人类的任何物质或精神的活动本身总是具体而生动的,故而在这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对真的把握和对善的追求的生动形象的结果就体现为美。因此,真、善、美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具有丰富实在内容的实践问题,它同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任何一个种的尺度”(物的尺度),是指由人以外的客观物质世界所具有的尺度,是由客观事物本身的结构、属性、本质和运动变化规律给人的活动所设定的准则和规范,事实上就是真;人的“内在的尺度”则是由人的需要和“本质力量的性质”所规定的尺度,它是在认识了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性质和特征之后形成,并进而要把自然物改造为合乎人的目的和需要的对象,实际上说的就是哲学意义上的善;这两种尺度统一起来,就形成“美的规律”。在这段话里,马克思所要说明的是人类的生产劳动与动物的活动的根本差别。在比较了这种差别之后,他总结性地认为“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就是说,人的劳动因为遵循了上述两种尺度,具有自由和自觉两大特点,所以是依照美的规律来进行的。因此,存在于两个尺度统一之中的“美的规律”,乃是人类生产劳动所独具的特征。当客观世界及其规律被人类认识和掌握,进而被自觉地运用于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及其创造的结果就是美的。因此,美当中包含了真、善,对美的追求也就隐含了对真、善的追求。人类只有不断地追求真、善、美,使它在人类实践活动中不断地呈现,人类社会才能持续地发展和进步;倘若一个社会忽视或停止了对真、善、美的追求,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减缓甚至停止前进。
从人类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来看,初级阶段的人类社会实践,主要是求“真”和求“善”这两种活动。人类社会发展到了相对来说较为高级的阶段,才出现求美的活动。先秦时期墨子曾说过:“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2](P22)这段话很好地说明了在美的产生过程中使用价值先于审美价值的观点,恰如普列汉诺夫所言:“从历史上说,以有意识的功利观点来看待事物,往往是先于以审美的观点来看待事物的。”[3](P109~110)因为在人类“苦难的童年”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原始初民在自然力的压迫下痛苦地挣扎,一切活动只单纯地为了满足两种本能式的需要,即维持自身生存的求食的需要和维持种族生存的性欲的需要。日本著名汉学家笠原仲二在考察中国人原初的审美意识时,通过大量的材料论述了审美意识是起源于美食和“美色”引起的官能快感[4](P1~15),其见解是独到的。
可见,美是以真、善为前提和基础的;而且,相对于真、善来说,美是一种更高层次、更高境界的东西。人类社会从求真、求善到追求真、善、美初级形态的统一,是一个把“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的渐次升高的过程。无论现实美还是艺术美、物质美还是精神美,总是在求真、求善取得自由从而达到高境界时才会出现。尽管真、善、美互有区别,真的、善的并非都是美的,但美的却必定是真的、善的。美是从真那里开垦出来的,从善那里生长出来的,从美那里我们看到的是真和善的极致!马克思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把“美的规律”看作是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的劳动所独具的特征;高尔基说:“美学就是未来的伦理学”,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指出“若要把感性的人变成理性的人,唯一的途径是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只有审美的趣味才能导致社会的和谐,因为它在个体身上奠定和谐。”
三 “美的规律”:走向自由之路
尽管人类社会是一个由真、善、美和假、恶、丑共同建构起来的既对立又统一的价值系统,但人类一切促进社会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的物质与精神活动,归根结底乃是对假、恶、丑的不断克服以及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
真、善、美三者既相互区别,又密切相联;求真、求善、求美内在地统一于主体的实践活动之中,构成人的活动的完整的有机系统。人们在谈到真、善、美三者的关系时,一般认为它们相互包含、相互渗透,仅此而已。其实,这种说法非常笼统,缺乏细致的思考。真、善、美固然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但它们的关系并不是并列的。求真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客观要求,求善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内在驱力,求美远不止于是人类情感和艺术的需求,而是求真和求善体现出来的必然结果。因为真和善本身是抽象的,美则是具体形象的。由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及其结果永远是具体的,求真和求善的活动必然要显现为生动具体的形象,这显现出来的生动具体的形象就是美。美是真、善的感性显现,是真、善的必然归宿。只要人类追求真和善,其生动形象的结果必然就是美,可以说,美是真、善的“宿命”,真、善“不得不”美。恰如前文所言,美是以真、善为前提和基础的更高层次、更高境界的东西,美当中内含了真和善,对美的追求隐含了对真、善的追求。“美的规律”是人类一切实践活动所要遵循的最高规律。这也是前文所引马克思所说的“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旨意。
在人类意识产生以前,自然界是一个漫无目的的自在世界;人类意识产生以后,理想之花就出现在世界上,人类便开始朝着自由的理想世界迈进。在这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中,求真,即探索世界的客观规律,关系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真理性的认识是人类实践活动成功的保证。求善,即人类在获得了真理性认识之后对功利的追求,是基于人性的内在要求。善和真是相互包含、相互渗透的,善以真为前提,善中必有真;而真又以善为动力,真中隐含着潜在的善。同时,善与“义利”也有复杂的关系。从人类整体和原初的意义上说,善只与利相关,而与义无关。然而,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利”的主体分化了,复杂了,甚至出现了以个人或小集团之“利”损害人类社会整体之利的现象,这时,就需要用“义”来对“利”进行调控。从本质上说,人的一切活动是趋利的,趋利是人类活动的特点,而不是缺点。在一个有生存竞争的社会里,必须承认每一个人都是“自利人”,每个“自利人”在社会中相互竞争,发挥出各自的主观能动性甚至生命的潜能,有利于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利”作为行为动机,本身既不善也不恶,而是中性的,只有当它变成行为之后才会朝善、恶两个方向发展。这就要求某种社会力量来控制“自利人”行为发展的方向。这种社会力量包含很多因素,如法律法规、政策条例等等,但提倡以义制利、义利并重的道德自律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儒家“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舍身而取义”(《孟子·告子上》)的千古训条,虽然在传统社会中为重义轻利的文化取向推波助澜,遭到许多现代人的讥笑,但谁也不能否认这种理论的勇壮精神。尽管提倡儒学的统治者自己未必能依此训行事,但它所铸就的文化精英人格中豪侠慷慨的一面,使他们在一次次民族危难中视死如归,舍弃一切,这不能不令人钦佩,不能说毫无价值。
真和善本身是抽象的,但求真和求善的实践活动及其取得的成果却是生动具体的,这生动具体的形象就是美。美高于真、善,却又内含于真、善之中,是真、善显发出来的形象。从总体上说,真、善、美是紧密相联,互相渗透,不可分割的,但从具体的实践活动来看,美却最生动宜人、更容易把握、更贴近人类的感性生活。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历代有识之士都特别强调美对社会的导引和规范作用。而且,由于美是以生动宜人的形象为特征,“其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5](P54),所以美是让人感到最亲切自然,从而也最有效的一种导引和规范。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就是这个意思。
人类的实践活动总是具体的,具体的实践活动遵循的是具体的“美的规律”,这个隐含了真和善的“美的规律”,是人类向自由的理想世界奋进的路标,或者说就是人类走向自由之路。人类只有顺循此路前进,才能在追求自由的征途中采摘到一簇簇自由的花朵,并不断地向最高的自由境界接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