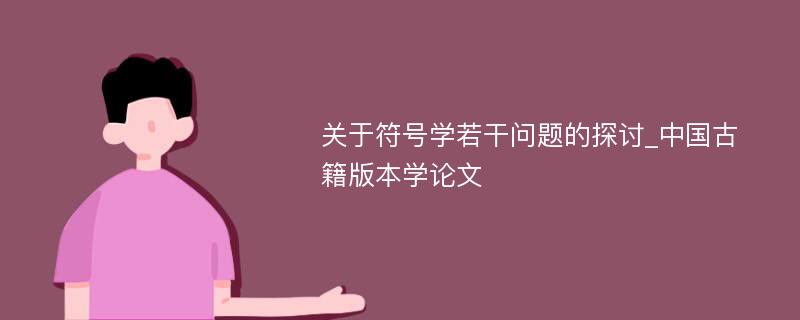
关于版本学若干问题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若干问题论文,版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版本学是研究文献版本源流及其鉴定规律的科学,其范围不能局限于古籍版本,而应是古今中外所有文献的版本。版本学学科体系包括版本学基础理论、版本学史、图书版本源流、文献版本鉴定及版本学分支学科建设。继承和发展传统版本学的方法,重视现代文献版本,加强版本学的实用性,是当前版本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
关键词 版本学 中国古籍版本学 版本鉴定
1 问题提出的背景
本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加强新书版本学研究的呼声越来越高,然而,这只是中国古籍版本学的时间的延伸,于版本学学科建设影响甚微。在基本的概念和认知中,中国古籍版本学等同于版本学已成牢不可破的心理积淀。人们没有认识到应建立一种至少包括中国各时期书籍版本的中国版本学;一些中国古籍版本学论著公然标称为“版本学”,忽略了标题所涵的界定:时代(古籍)、地域(中国)和民族(汉族,很少涉及中国境内的其他民族)。面对如此丰富的古今中外文献及其版本竟把仅属于一个民族历史中一段区间的版本研究不加任何限定地称为“版本学”,不仅大而无当,而且认知失误。
《图书馆学百科全书》有关版本学辞条及其阐释存在诸多问题:1.没有“版本学”辞条:2.“中国古籍版本学”和“校雠学”并列,混淆了学科级别,并在释文中把“中国古籍版本学”转换为“版本学”,混淆了两者的名实。
1991年,姚伯岳油印出版了《图书版本学纲要》,首次把世界版本现象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可惜,该书的论述范围仍然基本上局限于中国书籍版本,尤其是中国古籍版本。
西方版本学约始于18世纪末。版本学一词1763年首先见于法国版本学家德波所著的《版本学说明》一书。1812年,法国佩尼奥在《论版本学》一文中,说版本学是“具有无所不包的内容,既有对大量著作(……)的评论,也有对这些著作的介绍(……),并且包括了目录学的一切方面。”这个定义缺乏版本学的独有内涵,却对西文版本学影响深远。尽管它可以扩展版本学的学科范围,但版本学还必须寻求特有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才能跻身于学科之林。
本文拟探讨版本学的一些基本问题:(1)版本学是一门科学吗?(2)版本学的学科体系是什么?(3)如何加强版本学的实用性?
2 版本学是一门科学吗
多年的研究成果证明,中国古籍版本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然而,这门学科只是版本学的分支学科之一。在学科认知意义上,这个显例可以支持版本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存在。
凡有书籍,就有版本,就有版本学。
2.1 以中国版本学为例
中国古籍版本学建立在对中国古籍制作方式的演变及每种图书版本的演变源流的研究上,研究对象是古籍的各种版本及其鉴定规律,研究内容是:(1)古籍版本学的基本理论;(2)古籍版本学史;(3)古籍制作方式的演变源流;(4)单种(含丛书)图书版本的演变源流;(5)古籍版本鉴定规律。[1]
由于新书版本变化较快,加上对传统版本形式的继承和西文版本形式的借鉴,以及文献类型的多样化所带来的版本变革,使现代文献版本学的内容更为繁富。一方面,机器的进步、材料和技术的一致使现代文献版本的个性趋于淡化;另一方面,文献类型的扩展、文化交流的频繁、出版方式的变革和政治斗争的复杂尖锐给现代文献版本学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中国各少数民族文献也有自己的版本学。由《甘珠尔》和《丹珠尔》两部分组成的藏文《大藏经》,利用雕版印刷术刊印了那塘版、拉萨版、德格版、卓尼版和北京版等。国内外不少学者对其版本进行研究,例如美国比邵夫《甘珠尔及其版本目录》、巴达拉耶夫《论不同版本的甘珠尔》。[2]
2.2 以西方版本学为例
西文目录分为两大类,其一为评论性书目即相当于版本目录。重要的版本目录例如英国的《不列颠博物院藏15世纪印本书目》、《莎士比亚的对开本和四开本:莎士比亚戏剧版本研究》。重要的版本目录学理论著作如美国目录学家F·鲍尔斯著《目录与校勘学》。
西方古籍版本研究。18世纪中叶,欧洲出现了抢购摇蓝版印本的风潮。版本学家为普及古籍鉴定知识,出现了有关摇蓝版的多种参考书,研究内容包括出版商及印刷品目录、技术特征及其鉴定方法(活字字体、出版年、出版地、开本、页码、版本记录等)。这种研究导致人们由最初不分良莠的抢购逐渐注重珍品。
西方同样重视单书版本的研究。古希腊修昔底德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附有作者著作版本目录,并分抄本、全书版本和单卷版本三个系统。抄本附列最重要的7种,“这些抄本中,没有哪一个抄本,在年代上或在质量上都胜过其他抄本的。但有两个系统可以辨别出来。”[3]作者对这两个系统的渊源及优劣作了比较研究。
1981年和1984年,西文国家学者分别在索菲亚和巴黎召开了版本学专题讨论会,这不仅证明了版本学在西方的见重,也说明版本学的存在在西方已成共识。
2.3 版本学是一门科学
古今中外文献都存在版本问题。没有版本的文献是不存在的。各时代、各民族文献的版本、版本原理及其鉴定方法,存有共性和特殊性。这些共性和特殊性的研究,构成版本学的基本内容。写本、抄本、稿本、刻本、活字本,是书籍的基本版本形式。纸张、字体、行款、装帧,是书籍版本的基本构成要素。这些版本形式和构成要素在不同时空的书籍中存有共性和特殊性。那么,对各民族、各时代文献版本的研究,就是版本学。[4]所以,版本学作为建构于古今中外文献版本基础之上的独特学科,是可以成立的。独有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是版本学之成为学科的支点。
由于古代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相对欠缺,文献版本的特殊性多于共性,一如其文化的特殊性多于共性;近世以来,则出现了相反的情形。不过,通观古今中外版本源流及其鉴定方法,在基本方面,无疑是一致的。就版本源流而言,无不与科学、技术和文献的内在发展逻辑相联系,就版本鉴定而言,不外内容和形式两方面。一些具体方面也有一致处。例如西方摇篮版鉴定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一种字体,一个印刷人”,这在中国古籍版本鉴定中同样适用。
3 版本学的学科体系
3.1 版本学基础理论
西方比较流行的版本学定义是:“版本学是研究以书面文字作为社会内部交流工具的科学,涉及到它对社会、文化和经济各方面的影响,因此它包括了与图书有关的一切学科——目录学、图书馆管理、书籍搜集,以及阅读的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5]中国学术界认为,版本学是研究图书版本源流及其鉴定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内容是经过多次传抄或印刷的图书的各种特征,例如年代、版次、印次、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方式、纸张等。东西方不同的版本学定义显露出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学术路径。
应建立一套层次分明的版本学概念体系。其核心(基本)概念有三个:版本学、版本和版本鉴定。版本和版本鉴定包括诸多二级概念。前者是写本、稿本、活字本、刻本、石印本等,后者是形式上的版本鉴定。各种二级概念又包括三级概念。
版本学的功用涉及到它对社会、文化和经济各方面的影响,不应局限于对几个相关学科——校雠学、目录学——的作用上。例如版本学与阅读心理学。版本精良的书籍犹如艺术品,赏心悦目,自会提高读者阅读兴趣和质量。
3.2 版本学史
研究版本学的产生和发展历史,包括历史分期、学科源流、学术流派、人物、著作及现状。版本学史的探讨应在历史、文化的背景下进行,而不纯是技术性的。历史是过程、联系和发展。遗传和变异是版本学史的演变图像。
3.3 图书版本源流
包括图书版本源流和一书版本源流。前者可从整体上认识版本发生发展的规律,后者可探索一书版本流变和文献的、学术的、社会的价值。民族的原典性作品往往是版次及再生版本最多的作品,极富文化内涵。
3.4 文献版本鉴定
是版本学的核心内容之一,版本鉴定的目的是确定版本的真伪、优劣及源流。内容包括(1)一般原理与方法;(2)各种版本的鉴定;(3)伪本的鉴定。
3.5 版本学分支学科建设
这可反映出版本学的丰富内容及其与社会文化经济技术之间的广泛联系。版本学分支学科很多,例如不同民族、时代、地域和制作方式都有专门版本学。比较重要的专科版本学是版本目录学、比较版本学和译书版本学。
比较版本学。是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对不同民族、地域、时期和文化背景下的版本学问题进行的研究,确定其共同点和差异点,揭示客观规律。比较研究需要一定的规范:“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6]
译书版本学。译书包括两种方式:古籍今译和不同语种的翻译。两者都产生新的不同版本。译书版本学具有较多的文化意义,因为从中可以考察文化的继承借鉴关系,显示出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发展、影响以及接受过程、方式和特点。例如,19世纪是中英两国文化交流迅速发展的时期,由双方相互被动转为相互主动,在这种背景下,《红楼梦》开始传入英国,翻译的份量越来越大,直到1973年,企鹅出版社出版大卫·霍克思英译八十回全译本《红楼梦》。《红楼梦》在英国的翻译和出版,正好反映了英国接受介绍中国文化的基本过程。[7]
从上述任何角度考察,中国版本学学科建设都很薄弱。中国古籍版本学的丰硕成果给中国版本学研究提供了某些参考,然而,限于一隅的模式和具体成果很难具有普遍意义。
4 如何加强版本学的实用性
版本学本是致用之学。近世以来,古籍版本学逐渐关注于理论建设,而于实用不免隔离。
4.1 编制版本书目
一些历史久远的出版社,却缺乏回溯性出版物总目录;中国古籍版本研究,也鲜有版本目录的编制。宋代以降,各朝代出版了哪些书?存世多少?存于何处?套印本书籍有多少?一书版本目录,如儒经和二十四史,各书到底有多少种版本?版本目录不仅具有版本学价值,更具有文献学意义,揭示出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的不同层面。中国古代尚有《古今书刻》、《内板经书纪略》的编制。如果历代出版物及其存佚情况不明,那么版本学就没有尽到责任。
西方所编制的大量版本目录表明其版本学颇重实用。例如摇篮版目录,自18世纪末至20世纪,编制不绝如缕,逐渐累积,各具特色,不仅包括存世书目,也可从中检索摇篮版图书印刷商、书名、著有姓名、活字字体乃至收藏处所,为15世纪的文化、经济、技术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收藏家也可据为指南。
4.2 探讨版本学中的特殊性
略有版本鉴定经验的人都知道,版本学基本方法常常受到特殊性的挑战,不了解特殊性无以胜任版本鉴定。例如,经厂本多用绵纸,但并非都用绵纸,此即特殊性。下列因素不合乎常识:伪本、仿古本、创新本、两朝交替之际的版本、书坊分号刻本、日本或朝鲜刻本、影(覆)刻本、原书避讳仍旧的刻本等。版本学家不应予以忽略。这里仅就伪本略加申说。
任何民族的文献都有伪本,伪本无不以赠钱为目的。古代中国书商曾以各种方法作伪,例如书名、著者、卷数、序跋、牌记、藏书印、题跋、纸张等。西文作伪家同样不择手段,其对象无非是手稿和印本书。活字印刷术发明以前,连蜡版、泥版书和抄本也成为作伪的对象。常用的手段是摹写、利用旧书空白扉页和改换装订。撕下古书扉页用以印书显然比中国式的把新书放入米缸使其发黄变皱要费事些。高超的作伪手段甚至可以蒙骗版本鉴定家。社会对古书的需求使作伪者得以售其奸。西方学者为了鉴定真伪,研究了纸张和印刷技术。[8]再高明的作伪家也不可能不留下毛病。可见伪本是一种世界文化现象。在作伪手段上,各民族既有共性,也有特殊性。
4.3 推荐优良版本
近世推荐书目附带版本,似以张之洞《书目答问》为早。该书“略例”称:“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注精校本,事倍功半。”又称:“多传本者举善本,未见善本者举通行本。”即已注意到推荐优良版本。面对古今中外文献,当代版本的选择越发困难。版本学家不仅负有推荐优良版本之责,也担有批判粗劣版本之任,这样才能更多地显示自己存在的价值。换句话说,版本学家应该成为出版界的监督力量,而不是仅仅耽于书斋。
4.4 版本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版本是一种资源。开发版本资源,既有文化、学术价值,也有经济效益。然而长时期形成的重保藏轻开发、重内容轻形式的心理浪费、埋没了版本资源。
4.4.1 旧版本的再生
古籍版本和近现代书籍版本是中国最重要的版本资源,也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这些版本具有版本和学术的双重价值。版本开发不外两种途径:影印和再版。善本书因为具有艺术代表性或历史文物性,不妨覆刻或影印,以满足社会需要。近现代版学术著作在市面已不易见到,不妨新版。台、港地区和日本出版了不少中国古籍和近现代版书籍,行销大陆。大陆出版社尽管是这类书出版的主体,但应当付出更多的努力。
4.4.2 传统版本形式的继承
中国古代出版的书籍,在不同时期、地域、单位都有不同的特色,既丰富了版本文化,给后世留下了极可宝贵的版本遗产,也张扬了版本个性。而这种特色近现代以来几至泯灭,人们再也无法从字体、张纸、行款等方面看出某书属于什么地域或出版社了。装订的单调同样使版本文化黯然失色。这固然是社会、出版界的责任,然而也表明版本学家自立意识和影响力的缺乏。版本是一种文化。版本的单调与丰富、沉闷与活跃,反映出时代的政治和人文空气,反映出时代的欣赏趣味。
传统中国版本形式中有许多值得后人借鉴的内容。以字体为例,古代印本书籍正文的基本字体是楷体,但不同时代、地域、刻书家都有不同的风格,即使在匠体盛行的时代,不同的字体仍然被使用着,清初馆阁体更是风行一时。这些字体所具有的个性特征形成了丰富多彩、赏心悦目的印书字体文化。今天使用最多的仿宋体,其实是所有字体中最呆板、做作的。“毛氏之书走天下”的一个原因,当与刻书者毛晋独创的扁平而厚重的字体不无关系,那种独一无二的字体就是毛氏之书最易为人识别的特征。一个时代、一个出版社是应当有自己字体上的特色的。
历史上不乏由于版本形式的变革而引起出版界革命的例子。英国企鹅出版社,就是由创始人阿兰·莱恩改流行的精装本书籍为平装本书籍从而一举成功的典型。
1455年约翰·谷登堡在德国美因茨将《圣经》首次刊印后,各种新版《圣经》相继问世,仅1777-1977年,在美国就有2573个版本。多样的版本成为人们的收藏对象,各种版本都有人专门收藏。《圣经》一直畅销市场,除了宗教因素外,难道没有版本因素?
继承传统版本遗产,创造有特色的版本形式,发扬光大祖国传统版本文化,注重版本资源的开发利用,应当是版本学界和出版界的重要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