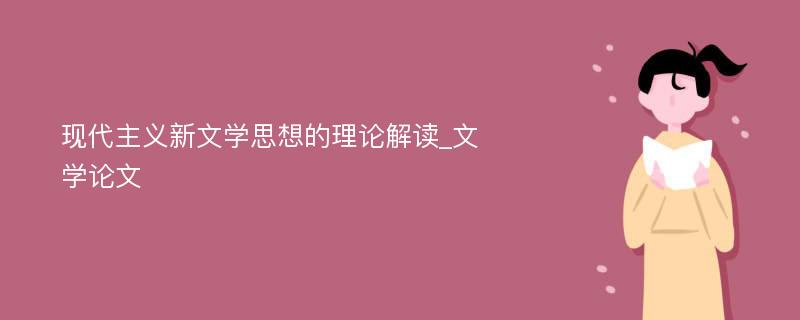
新文学现代主义思想理论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现代主义论文,理论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理论的产生不同于文学创作。或者说,某一个作家、某一部作品都可以相对超越些,可以自由地表现自我的情趣,可以自成一统地创造个性化的艺术。而一种文学理论的形成,则更多地需要依赖历史的积淀和升华,需要依赖客观现实语境的时间和空间的制约。新文学现代主义理论作为特定时期的现时话语,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道靓丽风景线,它自觉而勇敢地充当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先锋性角色,它作为中西文化大交流、大碰撞中的一种初始化形态,尽管还有种种的缺陷、偏颇乃至迷失。但它毕竟是率先代表了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趋势,并某种程度地蕴藉着许多对当下对未来的启示或隐喻。
一
新文学现代主义理论携带着一种先行性的意义。与同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理论相比,它更激进、更大胆、更多一些探索精神。它率先地感知、把握了风靡世界的现代主义思潮,积极地把它移植到中国的现实土壤上,并促使其成功地完成了现代性的转换。这是一种中国文学传统的“西化”过程。西方现代主义的先锋性特质,使其必然要走向世界,造成全球性的冲击波。新文学现代主义思想家对西方的现代派有着特殊的敏感,他们大胆地甚至是无所顾忌地引进那些颇为新鲜的文学思潮和理论著述。这种先行者的努力犹如狂波巨澜,使中国人耳目一新,也强烈地冲击了中国人传统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意识,造成了其思维方式和心理结构的坍塌、革命。同时,这也是一种西方思想的“中化”过程,中国文化固有的强大生命活力也使其必然要以一种开放的胸襟去接纳一切现代性的新知,新文学现代主义思想家就以其丰厚的民族文化底蕴既宽容地接纳了又有机地改造了西方世界的思想理论,从而创造了一种中国特色的现代主义文学理论。
在当时,置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种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及诸种精神焦虑和生存困境中的新文学现代主义思想家们,迫不及待地甚至饥不择食地企望到西方世界那里去寻找精神食粮,他们热切地翻译和介绍各种国外的现代主义文论,其范围之广泛、数量之浩大、内容之驳杂,可谓史无前例,令人瞩目。
广博、迅速,是西方现代主义理论进入中国文坛时的突出特点。中国现代文学史可谓是中西文化的引力与斥力相互摩擦、融会的发展史,几乎所有的新文学刊物都在翻译、介绍西方世界各种流派的思潮理论和文学现象,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正是伴随着这波澜壮阔的西化大潮涌入中国的。据《中国新文学大系》统计,一九二八年——一九三七年间出版的文学类翻译图书一千六百二十余种,其中文艺理论译著有二百多部,瓦雷里的《现代诗论》、《唯美派的文学》等现代主义理论著述便夹杂在其中。例如,孙俍工一九二三年主编的《新文艺评论》一书中,既有提倡写实主义的《文学与人生》,也有《未来派文学之现势》、《达达主义是什么》、《王尔德评传》等现代主义理论文章。郭沫若一九二五年出版的《文艺论集》一书中,既有《文艺之社会的使命》等现实主义文论,又有《批评与梦》、《未来派的诗约及其批评》等现代主义文学思想的阐发。在众多的现代主义思想理论倡导者中间,既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滕固等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同人们,也有人生派的茅盾、王统照等人,甚至还有新文学运动的反对者胡先骕等,他们都以极大的热情充分肯定了现代主义理论学说的独特价值和意义。例如,日本现代理论家厨川白村的精神分析论著《苦闷的象征》一九二四年二月出版,鲁迅的译文就在当年十一月的《晨报副镌》上发表,并同时在北大课堂上进行讲解,其译著单行本也于一九二五年三月由北新书局出版。同时出版的厨川白村的著述还有丰子恺的《苦闷的象征》译本、罗迪先译的《近代文学十讲》、仲云译的《文艺与性欲》、《病的性欲与文学》、樊仲云译的《文艺思潮论》等。他们充分肯定了厨川白村以柏格森哲学的“进行不息的生命力”解释人类生活、以弗洛伊德学说的“生命的根柢”来分析文艺的理论主张,“很有独创力”,“有独到的见地和深切的会心”①。郭沫若更是竭力地推崇这种因生命力受了压抑而产生的苦闷和懊恼乃是“文学的根底”的文学观:“我郭沫若所信奉的文学的定义是:‘文学是苦闷的象征’。”②
循序渐进,为我所用,也是新文学现代主义理论在接受过程中的一种主动姿态。如果说,五四时期的引进和借鉴还处于一种积极探索、普遍尝试的阶段。到了三十年代,新文学现代主义理论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思想的吸收则少了很多牵强、模仿,更多了些成熟、自如。以《现代》杂志为中心的文艺阵地广开言路、博采众家,坚持用大量篇幅多侧面地向国人展示美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英国等诸多国家文学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并在广泛的探索和比较性的选择之后寻找到了一种共识: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历程是历史和文学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诞生了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它表现了“空前的罪恶”,也创造了“空前的贡献”,它是成长中的而不是衰落中的文学,它是“将来的势力的先锋”,是我们“最好的借镜”。他们陆续写下了《刘易士评传》、《戏剧家奥尼尔》、《哀慈拉·邦德及其同人》、《作为短篇小说家的海明威》、《帕索斯的思想与作风》、《福尔克奈——一个新作风的尝试者》等很多文章,认真分析深入研究国外现代主义大师的思想和艺术。如鲁迅说的那样,他们借鉴的前提是“拿来”、“占有”,原则是“自己来拿”,他们立足于本民族的现实基础之上,经过自己“脑髓”的比较选择,既积极地摄取域外的果汁,又在摄取中表现出主动的挑选、扬弃。例如,梁实秋对王尔德唯美主义的介绍不仅是全面系统的,而且融入了自己的思考和批判。他既肯定王尔德是反对现实主义最有力的批评家,又批判了其脱离人生的唯美主义的“想象”:“王尔德所认识的想象是不羁的想象,是放纵的奔驰,没有纪律,没有约束……想象固是重要,想象的质地则尤为重要,真正伟大的作品,不是想入非非胡言乱道,而是稳健的近于常态的人性的。”③ 在这种“自己来拿”的过程中,他们孜孜不倦地坚持以中国文学自己的传统为准绳为坐标,坚持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现代派艺术两者的交融。他们欣赏陶渊明、李白等人的那种儒雅的“古已有之的境界”,也欣赏波特莱尔、瓦雷里等人的那种与“思想的曲线的波纹”相合拍的象征艺术,企盼着东、西方文化两者的充分地贯通、融化,企盼着“象征派的形式”与“古典派的内容”的完美结合。
二
新文学现代主义理论与西方现代派文论相比,还不够经典、不够严密,但是它更开放、更乐观、更具有青春的活力,它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实用理性的基点上,既积极地吸纳着西方现代主义的一切学养,又热情地拥抱着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诸多艺术诗思,从而酿造出了一种丰富多元、兼容并蓄的现代主义理论体系。
新文学现代主义文论虽然没有柏格森生命哲学和弗洛伊德心理学那样强大的理论根基,却也有郭沫若、郁达夫、张竞生、范寿康、吕澂、宗白华、无名氏、徐訏等一大批思想家在论证着生命意识和性心理的课题,并且从不同角度地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生命意识理论体系。在他们的书写中:生命的真实是个体自我,生命的性质是时间“绵延”的直觉体验,生命的主题是痛苦的荒诞的,生命存在的形式表现是非理性的艺术方法。有时,他们从柏格森生命哲学出发,以非理性的生命体验来观照文学创作和审美活动,提出“文学与生命不是判然两物”,文学创作和艺术形式都是生命的“印象”,都是“没有一刻的停滞”的“生命的动流”中的“纯粹的直观”的“一个断片”④。有时,他们接受弗洛伊德“里比多”理论的影响,以“性欲意识的表演”来建构生命意识,主张“利用性欲的精力为一种思想上,艺术上,及行为上的发展。由这个‘性力’的冲动而后所产生的思想,才能精深如柏拉图的哲学,美妙如但丁的诗歌”⑤。强调只有冲破“性力”的压抑使人的本能、情感和意志获得自由发展,才能使文学创造获得“极端”美的形式。到了四十年代,无名氏进一步把这种生命意识的理论思想发展为儒、释、耶三教合一的“新信仰”。他认为,“生命之流有两支:一为音乐舞蹈式的,一为图画式的。前者是上意识的情感活动及飞跃,后者为一种静观,一种流动的理智。没有前者,单有后者,生命未免空虚;有前者而无后者,生命未免盲目混乱。二者只有相辅结合,才能发无穷光辉。前者比较象征西方文化,后者比较象征东方文化。二者相融合。即是东西文化综合的成就。”⑥ 这种从生命本体论出发,以生命的感性活动形式来考察文学和文化现象的生命意识理论,告别了传统的认识论和实践论,进入到了一种生存和存在的非理性思辨领域。
基于非理性的生命意识和心理体验,新文学现代主义理论推崇主观性、内向性的文艺观。他们竭力主张“内心的现实”是惟一的真实,主观自我和心理情绪就是文学表现的目的和内容。他们热烈地倡导自我:“自我就是一切,一切都是自我”……我是惟一的存在者。⑦ 倡导“把内心的要求作为一切文学上创造的原动力”⑧,文学创造的意义和文学表现的形式只在于那种“唯主观”、“唯自我”的“最高真实”。它或者是一种内在心理的“主流的感觉”,如徐訏说,文学作品或理论文本的“主题”“很可能只是一种体验或一种感觉”⑨。它或者是一种现代社会的感性体验或心理情绪,如施蛰存说:“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所谓现代生活,这里面包含各式各样独特的形态:汇集着大船舶的港湾,轰响着噪音的工场,深入地下的矿坑,奏着Jazz乐的舞场,摩天楼的百货店,飞机的空中战,广大的竞马场……”⑩ 由于高度发展的工业化、市场化的“现代生活”和“现代情绪”都是荒谬怪诞、无可理喻的,所以只能用非理性的自觉和感觉才能解释和表现宇宙的奥秘和人生的玄机,文学艺术的宗旨也正在于以隐喻的、潜意识的形式“把刹那底感兴凝定”,从而去显现“启示宇宙与人生底玄机”,使其“永生”。
主观性内向性的思想追求必然导致艺术表现的形式性和抽象性。新文学现代主义理论提出,文学艺术的形式不是真实的,也不仅仅是想象的,它只是一种感觉的形式,一种“感觉的自由”形态,“因为文艺是一种自由发展的东西,一种知觉与灵感所到的艺术表现:不给它感觉的自由便没有它的存在与发展了”(11)。它“摒弃一切客观的写景、叙事,说理以至感伤的情调,而纯粹凭借那构成它底形体的元素——音乐和色彩——产生一种符咒似的暗示力,以唤起我们感官与想象底感应,而超度我们底灵魂到一种神游物表的光明极乐的境域”(12)。它甚至“不是某一个官感的享乐,而是全感官或超感官的东西”(13)。它需要使用象征的方法,使用直觉、感觉、象征、暗示等潜意识形态来象征内心与外物的“呼应或契合”。梁宗岱曾详尽地解释了什么是象征:“所谓象征是藉有形寓无形,藉有限表无限,藉刹那抓住永恒,使我们只在梦中或出神底瞬间瞥见的遥遥的宇宙变成近在咫尺的现实世界……它所赋形的,蕴藏的,不是兴味索然的抽象观念,而是丰富,复杂,深邃,真实的灵境。”(14) 对此,他们还提出了“象征之道”的一系列具体方法:用“大的暗示能”,“暗示出人的内生命的深秘”,暗示出天地万物之间、人与事物之间、人的各种感觉之间存在着的那种神秘、微妙的关系;用“官能感觉”、“印象的写法”,“用有限的律动的字句启示出无限的世界”;用“诗的思维术”、“诗之物理学的总观”等“印象”发出的“称和”、“振漾”以及“运动的律的幻影”来构成象征世界的“运动与心的交响乐”(15);用“音”与“色”的“感觉的交错”的“动律”来组建“纯粹的诗歌”。当然,他们更醉心的还是那种“现实、象征、玄学”三者结合的“新的综合传统”形式,“这个新倾向纯粹出自内发的心理需求,最后必是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现实表现于对于当前世界人生的紧密把握,象征表现于暗示含蓄,玄学则表现于敏感多思、感情、意志的强烈结合及机智的不时流露”(16)。他们解释,这既是以英美新批评理论家瑞恰兹的“最大量意识状态”理论为支柱的又是源于中国现实的现代人生的形式艺术,是“抽象思维与敏锐感觉的浑然不分”,是象征性暗示性的“感觉曲线”,是奇妙的多变的“无形定义圈”。
三
新文学现代主义理论文本是从个性自我出发从现实实践出发的经验式、感悟式的批评。他们大多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体验哲学的艺术思维,多采用综合感悟和具体体验的方式去记录思想、分析作品、评点文坛。
首先,新文学现代主义理论文本的视角是批评性的,不是学理性的。它们很少像西方理论那样致力于探究事物的存在之理和抽象玄理,也就没有西方现代文论那样超验的思辨哲学和学理研究。应该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没有纯粹的专职的理论家,他们常常是政治家、文学家等多种身份的兼容。对于置身于民族危机和生死存亡关头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来说,总是无法摆脱自我身上肩负的那种历史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无法摆脱那种深入骨髓的真实观和悲剧意识。即使是现代主义的思想追求,也大多从民族生存和现实人生出发,针对文坛的具体实际来提出问题、解疑答惑。也大多从个体自我的生存体验和现实感受出发,来介绍作家的生活经历、人生理想、美学追求,并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来论说文学主张和写作方法。例如,每逢社会上出现了一些重大事件、焦点问题,每逢文坛上出现了一些新人、新作品,他们都纷纷写文章表述自己的观点,表现出浓郁的政治功利性、社会实践性和现实指向性。
所以,新文学现代主义理论的文本形式多是一些读后感、随感录、导言、序言、作家作品论、创作经验谈等,没有严密的逻辑系统和学术规范,没有鸿篇巨著的基本原理的繁复阐释或哲理命题的详尽论证。作者大都是源于自己所遇见的印象最深的、感想最多的文学现象来谈论自己的感兴,例如,戴望舒的《望舒诗论》共分为十七条,全文不足一千字。无名氏的《沉思试验》,全书十八万字,纪录他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六年间的一些文学观点,有点像佛家的语录或英美散文的“絮语”随笔。堪称新文学现代主义理论经典的穆木天的《谭诗》、梁宗岱的《诗与真》、戴望舒的《望舒诗论》、李健吾的《咀华集》等著述,其文本形式也都是一些感想和体会,类似有感而发、随想所至的信笔由之,呈现出鲜明的零散性、随意性、偶发性的特点。
其次,新文学现代主义理论文本也是一种印象式、感悟式的批评实践。纵观其诸多的理论著述,都是批评家主体的一种直觉性的感觉体验,都是由“内在的体验力”所搭建的“感情的型”的文本形态。他们强调:“内在的体验力,乃是一切艺术制作的母怀。一切艺术的效应,无非在使我们可以高兴地享受这内在的力量和那活泼性。”(17) 批评家自我“内在的体验力”的高低强弱决定了他们阅读文学作品的接受方式,也决定了他们鉴赏分析文学现象的批评方式。源于这种“内在的体验力”的方式,文学批评的任务和方法都在于“追究自己的感觉”,是“自己印象的分析,自己印象的组合……批评者首要的责任就是考验自己的反应。追究自己的感觉”(18)。这样一来,阅读只是“无定的反应”,批评文字只是“个人印象的最纯粹形式”,批评的最高境界只在于“总是在寻找新的印象”,在于“灵魂在杰作之间的奇遇”。在他们看来,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真实都无非是一种感觉,因为世间的一切都是相对的、纯主观的,人们只能相对地把握客观世界的变动中的一瞬间,这瞬间的真实就是个人主观的感觉和印象。批评家的责任就在于“‘拿他某一特殊时间在人世所受到的印象记在一件艺术作品里面,同时批评,不管武断不武断,它的趋止是什么,所能做的也不外乎把我们对于作品在某一时间的印象凝定下来。’这就是说,批评是一种印象的印象”(19)。
于是,新文学现代主义理论文本的叙事风格多表现为艺术性、情感性的诗思,他们承继了中国文学源远流长的诗化、抒情化的传统,在理论阐述中融入了更多的主观自我的感觉体验,蕴蓄着浓浓的心理脉搏和情感波澜。这里,既有现代主义非理性的直观感觉的投注,又有中国古代文论中以体验为主的“悟”、“参”、“意会”、“心契”、“神与物游”等理念的渗透,他们对现实人生的理解或对文学现象的认知多是源于感觉性的体验、整体性的感悟,不需要遵循一般的从现象到判断、推理的逻辑程序,没有从感性到理性的深化过程,只须精微奥秘、难以言传的直觉,就能达到对事物的形式和本质的完整把握,只须瞬间的妙悟就可参透言外的意旨,只须性灵的“神遇”就会获得“韵外之致”。他们的文笔更多是以散文式或散文诗式的抒情,从容地议论,自如地落笔,洋洋洒洒,神采飞扬。例如,林徽因在谈论什么是诗和怎样写诗时说,写诗是“一串刹那间内心整体闪动的感悟”,“这感悟情趣的闪动——灵感的脚步——来得轻时,好比潺潺清水婉转流畅,自然的洗涤,浸润一切事物的情感,倒影映月,梦残歌罢,美感的旋起一种超实际的权衡轻重,可抒成慷慨缠绵千行的长歌……这感悟情趣的闪动,若激越澎湃来得强时,可以如一片惊涛飞沙……身受者或激昂通达,或禅寂谈远,将不免挣扎于超情感,超意象,乃至超言语,以心传心的创造”(20)。可以说,新文学现代主义理论文本的语言形式大多是这样一些形象性的、抒情性的“心象”表述,它们像抒情的散文或浪漫的诗歌那样洋溢着“文采与意想”的美妙绮丽,浸润着诗的意象、智性和美感,携带着汩汩流淌的情感魅力。
四
与西方现代主义关注人类的生存困境不同,新文学现代主义理论更多地沿袭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性质,“诗言志”、“文以载道”等实用理性和社会功利性无形地制约着他们,使他们要去思考去争取民族和个体的生存权力。对于他们来说,迫在眉睫的问题是个性自我的生存,而不是对存在的思辨。这样一来,主观性与客观性、感性与理性、文学性与政治性等诸多永远无法摆脱的困惑,就构成了新文学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永恒的焦点,或永远阐述不清的尴尬。
追根溯源,国外的那些现代派,真正使之成为现代派的因素就在于其内涵的“现代性”,这就是反对理性,高扬感性。在国外的那些现代派理论中,科学和理性虽然能够帮助人类认识客观世界,但它只能及于物质领域和事物外表,只有依靠非理性的途径才能找到生命的真谛和灵魂的归宿。可是,中国的现实并不具备这样的时空语境。就社会环境来讲,我国二三十年代的社会现实中,政治斗争和阶级矛盾纵横捭阖,没有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所带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文学的主要任务也还是反帝与反封建。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迫切需要的不是内在的精神追求,而是自我的生存权力,是在众多的迷惘与困惑中理出一条救国救民的求生之路。这种渴求理性的现实基础自然不能产生反理性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就思维方式来讲,我国传统的精神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天人合一”、“体用不二”,这既是人生哲学,又是人生方法论。这种物质与精神、本体与功用、理性与感性、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统一也某种程度地影响了新文学现代主义理论不可能走向纯粹的抽象和超验。就哲学理论来讲,我国的传统哲学是人文的,它关注的是人生之道,人性之理,即便是新文学现代主义对西方学说的引进,也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这些理论和思想,而是被糅入了介绍者自己的认识和体验,或者说介绍者仅仅是取其所理解的部分或取其所需要的部分。这就成了中国化的柏格森哲学、弗洛伊德主义。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哲学依据,新文学现代主义文学理论自然不可能高扬起自己的旗帜。就作家队伍来讲,我国的中、小资产阶级很难建立起强悍的自我人格,面对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和急剧殖民地化的严峻现实,他们虽则敏感,但却软弱,虽则孤芳自赏,又缺乏自我实现的勇气和力量。由于自身性格的缺陷,致使新文学的现代派始终没有产生大智大勇的领袖人物。
可以看到,新文学现代主义理论和理论家很少能够独立地傲居文坛,也很少有人能够百折不挠地坚持追求自己的精神目标。在历史的潮汐中,他们或者归入现实主义的洪波巨流,或者遁入浪漫主义的理想天国,或者被政治斗争的漩涡所淹没。没有可以倚靠终身的政治力量,没有独立于世的思想品格,自然不可能超越一切地去思考“我思故我在”的理论。有时,他们自己也往往陷身于自相矛盾的漩涡中无以自拔,他们痴迷着那些刹那间的感官体验和唯美艺术,又不得不以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感去理性地探寻救国救民的生存之路,不得不以文学去承载“国民意识”。有时,他们自己也无法把现代主义思想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截然地划分开来,甚至表现出对现代主义理论常识的混淆迷惘或错误认知。例如,他们在倡导现代主义的时候,竟然认为表象主义是现实主义到浪漫主义的一个过渡阶段:“表象主义是承接写实之后,到新浪漫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不能不先提倡。”(21) 几乎,我们可以在新文学现代主义理论的每一个文本中都能找到这种左右徘徊、上下浮沉的思想心态,这种矛盾错杂、似是而非的理论观点。既然,新文学现代主义理论没有雄厚的“根”,没有坚实的“基”,就必然如浮萍般摇摆不定。
当然,新文学现代主义理论的追求有些太理想化了,也就只能算作是他们的“努力与追求”。如戴望舒所说:“这并非自己自阐已经达到或接近是他底目标——这目标也许将永远缥缈如远峰,不可即如天边灵幻的云。不过单是追求底自身已经具有无上的真谛与无穷的诗趣,而作者也在这里找着无限的欣悦了。”(22) 但是,他们毕竟是在追求的途中不屈地跋涉着,毕竟创造出了一种属于自己的“多元共构互补”的现代主义理论话语,并在寄植的基础上蕴含着先锋性的意义。
注释:
① 鲁迅:《〈苦闷的象征〉引言》,《苦闷的象征》未名社出版,1924年12月。
② 郭沫若:《暗无天日的世界》,《创造周报》第7号,1923年6月23日。
③ 梁实秋:《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文学的纪律》,北京,商务印书馆,1928。
④ 郭沫若:《印象与表现》,《时事新报》副刊《艺术》第33期,1923年10月30日。
⑤ 张竞生:《美的人生观》,《张竞生文集》上卷,第82页,广州,广州出版社,1998。
⑥ 无名氏:《沉思试验之一》,《沉思试验》,上海,上海真善美图书公司,1948。
⑦ 郁达夫:《自我狂者须的儿纳》,《创造周报》第6号,1923年6月16日。
⑧ 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创造周报》第2号,1923年5月。
⑨ 徐訏:《〈风萧萧〉后记》,《风萧萧》,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
⑩ 施蛰存:《又关于本刊的诗》,《现代》杂志第4卷第1期,1933年11月。
(11) 叶公超:《文艺与经验》,《今日评论》,第1卷第1期,北京,1939。
(12) 梁宗岱:《谈诗》,《诗与真二集》,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
(13) 戴望舒:《望舒诗论》,《现代》第2卷第1期,1932年11月。
(14) 梁宗岱:《象征主义》,《诗与真》,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
(15) 穆木天:《谈诗》,《创造月刊》第1卷第1期,1926。
(16) 袁可嘉:《新诗现代化》,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1947年3月30日。
(17) 李长之:《语言之直观与文艺创作》,《时与潮·文艺》第2卷第1期, 1943年9月。
(18) 叶公超:《从印象到评价》,《学文》第1卷第2期,1934年6月。
(19) 李健吾:《自我和风格》,《咀华二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2。
(20) 林徽因:《究竟是怎么回事》,《大公报·文艺副刊》1936年8月30日。
(21) 茅盾:《我们现在可以提倡表象主义的文学么?》,《小说月报》第11卷第2期,1920年2月。
(22) 梁宗岱:《诗与真·序》,《诗与真》,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
标签:文学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现代论文; 艺术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文化论文; 苦闷的象征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文艺论文; 诗与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