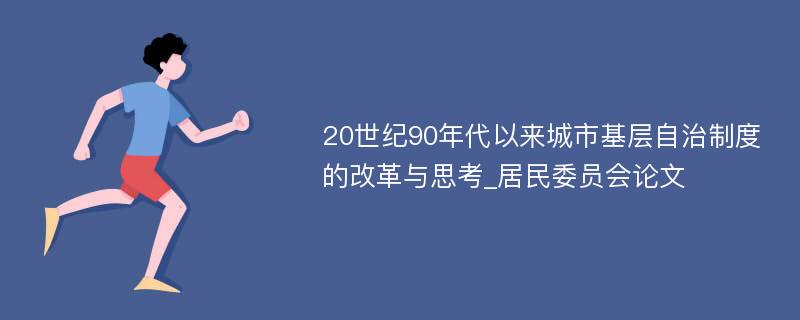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城市基层自治制度的变革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层论文,后期论文,年代论文,制度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城市基层自治制度的变革与创新,是一个逐步摸索、逐渐展开、渐至成熟的过程。以时间划分,这个过程大致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酝酿阶段,90年代前期的产生阶段,以及90年代后期以来的成长阶段;以地域划分,城市基层自治的变革轨迹又可具体还原为沈阳市沈河区、武汉市江汉区、贵阳市小河区、南京市白下区、青岛市市北区、北京市石景山区等地所做的体制创新,凝结成诸如“沈阳模式”、“江汉模式”、“上海模式”、“温州模式”等各具特色的探索形式;以内容划分,则可将此过程分为社区服务阶段和社区建设阶段:在前一个阶段,居委会的组织、经费、人员及功能都得到了强化或改善,但其定位依然是行政性的而非自治性的,它“作为街道办事处下级部门的定位一度得到加强和正规化。协助政府完成城市管理事务使其不堪重负,同时也使其组织与人员进一步行政化”。后一阶段(90年代后期)的主要任务,是由政府主动推动城市基层自治制度的试验性改革,尽管它依然是国家利益和国家意志的体现,却在客观上培育了社会的自主意识和自主力量,居委会作为群众自治组织的地位与功能,到了这个阶段才真正地开始凸现出来,与之相应的制度变革着重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制度空间发生转换:有关社区的任何功能性解释,都不足以完整地揭示其作为自治制度空间所具有的革命性意蕴;实际上,从“单位”向“社区”的空间转换,意味着社会不再按照“单位制”的原则被国家简单地分割和深度吸附。在50年代中叶至80年代初的20余年间,城市居民委员会的组织结构和角色功能虽然屡有变动,但在以“单位制”为核心的计划经济社会管理体制下,其作为“单位制”的附庸补充物的地位却是始终如一的。由于“单位制”的组织形态,是随着党的组织网络向国家和一切社会组织延伸的,因此,它得以顺理成章地外化为城市社会主要的空间表现形式,与之相比,居民委员会则只能作为一种与单位制相配合的辅助性组织设置,存在于“单位”的边缘,拾“单位”难得之遗、补“单位”难得之缺。对于“单位人”,国家可以便利地通过“单位”对其进行整合,对于无“单位”的无组织者,则以街道办事处为核心,通过居民委员会这样一个地域性的“单位”组织,将其整合到国家的普遍意志中。当然,这样一种双重的治理空间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在单位体系以及单位制尚不完善的50年代,人们生活的大部分资源,尤其是政治动员的主要领域实际上集中在街区,因而,当时街区内的国家权力“其实空前强大”。随着社会行政化程度的不断增高,全功能的组织形态使单位成为个人与国家发生联系的接口。显然,单位系统即是主流社会。居民委员会则因其原初的整合对象的不复存在,而日趋转变为在各级“单位”之外实施剩余管理的准行政机构。
计划经济体制的解体与“单位制”整合模式的式微,使中国基层社会原有的“单位”空间形式变得无所依托而且难以维系。以往纵向单一性的社会结构遭到了瓦解,计划经济体制下由各级“单位”、政府组织所承担的大量社会服务、社会管理、社会保障的职能,渐次从国家的权力网络中溢漫出来,这些从企业和政府转移出来的社会管理和服务功能,需要由一个社会结构块面来承接。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实体与国家间的行政依附关系,以及社会成员与单位间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松弛,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也开始从事实上的国家领域。退而居于社会的“日常生活”之中,需要一个同一层面的共同体形式唤起他们的内心情感和归属意识。在此剧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看似已死的传统便以一种新的形式再度复活,人们试图在一个被称做“社区”的新型公共空间里,不仅重温昔日“里弄”——一个建立在邻里基础而非血缘关系上的“熟人社会”——的往日温馨,而且还可以重新找到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单位”——一个“公有”和“共享”的生存共同体——所能给予个人的可靠保障;而社区也在提供共同体式的服务的同时,为重新分化后的社会成员提供了地域和生活方式上的边界意识,这种被西美尔称做“空间的排他性”的地域特性,以及由此特性而唤起的“地域忠诚”,使社区得以成为具有共同体性质的自治空间。社区的这一精神内核,使它日益成为后“单位制”时期市民生活的重要归宿,而市民社会自主性与权利意识的日益增强,又要求与社区唇齿相依的居民委员会摆脱行政附庸的尴尬角色,实现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本性的复归。
2.制度基础趋于下移:单纯依靠政府权威作为城市基层自治的制度基础,是造成自治组织行政化和自治功能“内卷化”的重要原因;90年代后期以来,社区建设的工作目标日益由一种源于政府的外在压力转化为源于社区居民的内在压力,促使居民委员会必须深入动员并切实依靠居民参与,其首要的制度举措便是居委直选。自1999年起,我国便开始着手社区自治的试点。1999年6月,沈阳市沈河区率先进行社区选举改革,采取以户为单位的代表选举方式,相对于长期实行的居民小组代表选举而言,无疑是一场突破。此后,上海、南京、青岛等地陆续进行社区选举的试点,其中,上海和南京开始尝试直接选举,但是效果却不甚理想,暴露出来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社区居民们对于选举没有兴趣,也不积极参加,以致出现了南京白下区在选举中参选的人全部是外来人,选举成了居民们用选举的方法雇用社区居委会成员的尴尬局面”。鉴于此,有人提出将社区选举的试点放到中小城市进行,以期打破大城市社区直选中因选民“政治冷漠”而造成的僵局。广西的居民委员会直接选举,就被认为是为长期困扰中国城市社区的居委会直选难题提供了解决之道,是全国社区自治发展进程中实现的一次重大突破。
目前,尚无足够证据证明广西的社区直选对大城市起到了怎样直接的促动或借鉴作用。毫无疑问,小城市具有一些与生俱来的“直接民主”优势,比如:城市及其社区的面积相对狭小,社会的异质化程度相对较低;相对封闭的地域空间和生活空间,有利于营造相濡以沫的社区认同,而相对简单的生活方式,则使人们有可能将社区选举视为生活中的“大事”,并从中真正地获得愉悦与自我认同。相比之下,大城市则尤如滕尼斯笔下的“社会”,当人们走进社会时,“就如同走进他乡异国”,在这个相互独立的个人“纯粹并存”的陌生世界里,人们丧失了成员间的“默认一致”,只能以原子化的个人利益的“理性协议”作为彼此结合的基础,这样,社会成员尽管可以像在社区里那样,“以和平的方式相互共处地生活和居住在一起,但是,基本上不是结合在一起、而是基本上分离的”。当然,尽管存在着种种不利因素,大城市的社区居委会选举改革依然在尝试和进行着,广州市以2000户左右为标准将城市社区划分为地缘型、单元型、单位型、综合型等四个主要类型,并以新的社区居委会取代原有的居委会。
3.制度结构趋于分离:基层自治组织倾向于建立一个足以涵盖辖区内所有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物业物管部门以及“社区精英”的综合性议事机构,在缺乏国家权力强制性支撑的社区空间,通过程序化的利益博弈协调公共生活中的利益冲突。如果说行政、立法、司法、军事等国家机构及其部门的结构分离,是国家权力自我规范以适当降低其自身强度的结果,那么,城市基层自治制度的结构分离则是在国家权力自我规范的过程中,随着社会权利从国家权力中不断溢出而自我规范,以期适时增强社会权利强度的结果。自治制度变革中的几个区域性典型,均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程度地实现着这种结构分离,例如:沈阳市自1999年上半年起,以微型社区体制改革作为社区建设的切入点,将划分微型法定社区的范围与居委会的换届选举相结合,建立了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协商议事会以及社区(管理)委员会,并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以沈河区为例,全区396个居民委员会以居民认同为出发点,被调整成为164个微型社区,平均每个微型社区拥有居民1200户,然后在此基础上,按照“社区自治、议行分设”的原则,在每个社区组建“一个大会、两个机构”——选举社区居民和社区内的单位代表组成社区成员代表大会,行使社区成员民主自治、民主决策之最高权力;社区成员代表大会推举社区内单位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组成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作为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的常设义务性工作机构,在社区成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民主议事、民主监督之职权;按照每300户配置1人的标准,由社区成员代表大会选举享受政府补贴的居委会成员,并吸收社区民警和物业公司成立社区管理委员会,作为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的办事机构,行使社区管理、服务、教育和约束等职能;建立以社区议事会、管委会为主导,以居民组长和社区成员代表大会代表为主体的社区自治工作网,形成各司其职的管理体系。结构分离既表现为居民委员会的组织结构分离,即由传统的单一结构模式逐渐演化为“议行分立”(议事机构扩展至整个社区)的结构模式;同时,也表现为居民委员会与政府之间传统扈从关系的分离,即由以往的权能一体逐渐演化为权能分立,居委会作为民间自治组织的独立地位日益凸显出来。
城市基层自治领域的各项变革,其最初的驱动力无疑都来源于政府的主观设计和国家权力的积极推动,由此形成的制度变迁逻辑,至少在理论上构成了悖论,即:一项以社会权利为核心的制度变革,其所采取的方式却是国家政权的积极干预和行政权力的强力支撑,而后者的有效性又恰恰来源于它的集中和强制,无限制地渗透在社会领域中必然带来对社会权利的损害。正是这种内在的分裂,导致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基层自治制度改革,尽管颇具创新、成就斐然,却不足十年就显现出了“动力不足”。对于许多地方的基层自治组织来说,变革不过是来自“上面”的又一道行政指令,所须做的只是习惯性地言听计从,至少在形式上满足源于政府的各项考核指标;对于绝大多数社区居民来说,社区只是一个与房产价值、居住条件有一定联系的物质空间,真正的生活空间还是在各人安生立命的单位、在单薄的城市社区无力涵盖的整个城市空间。尤为严重的是,“动力不足”不仅使这场由政府推动的制度变革无力扎根于民间,获取任何一项制度之形成所必需的制度性共识;而且,还有可能因为无力进一步制度化而反过来侵蚀掉业已取得的创新成果。尤其是随着城市基层自治制度的制度功能日益健全,在“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方面,社区公共事务正逐渐涵盖人口与物业管理、社区环境整治、社区生活服务、教体文卫发展、社会福利与安全保障的各个方面,相应的规章制度与考核体制得以建立,居民委员会在各项事务中的核心地位逐渐得到确立,作为新的社会治理空间的社区难免演化为新的权力网络而再度被并为国家的组成部分。
因此,正在进行中的基层自治制度变革,在其“兴也勃焉”的表面繁盛背后,隐藏着一个足以导致其“亡也忽焉”的驱动力问题,而解决这一“动力悖论”的根本途径,则在于促使基层自治制度向更具有政治价值而非仅具有行政功能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基层自治制度变革的根本目的,不应设定在旨在实现某种城市的行政管理功能,而应将它定位于旨在调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条途径。如果说英美国家的地方自治,其主要内涵是通过强化社会权利来抵御国家权力的可能侵蚀,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所谓基层自治,是通过强化国家权力来实现必要的社会权利;那么,90年代后期以来的基层自治制度变革,则理应体现为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沟通”以及以沟通实现的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均衡。在上海南京东路街道社区的制度创新活动中,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面对市场经济社会的资源分化,国家意识到了自身资源的有限性,而在其试图再造社会的最初阶段,国家不可避免陷入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一方面,国家退席旨在为社会力量提供自主的发展空间,使其在国家权力难以触及之处营造有机的社区“共同体”,以此作为国家权力这样一种“机械”凝聚力的基础和补充;另一方面,由于社会自主力量尚未发育成型,国家又必须为之提供身分上介乎“官”与“民”之间的整合因子,以此避免因为国家的突然缺席而造成的失控和分化。在以营造社区共同体为核心内容的基层自治制度变革中,居民委员会正是由于适时扮演了这样一种“双重角色”,而成为社区建设的关键力量。从国家权力的运作方面看,南京东路街道社区的居民委员会依旧承担了大量的“官方”事物,实现其团结居民、教育居民、“上传下达”的传统“行政”职能;而从社会权利的自我发育角度看,居民委员会又因地制宜地借助民间自有的仪式和形式,实现从“官方话语”向“民间话语”的巧妙转换。
社会权利的自主空间,正是在国家权力“在场”的状态下发育成形的,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基层自治制度发展的独特的现实逻辑。曾有学者对此评论道:“不论门由谁来开启,关键的是社区和居委会被推到了前台,它们不再仅仅是国家利益的代言人,而是社区自主整合机制中的主体,这就为相对独立国家的社会开启了大门。”这样的一个开启与培育过程,无疑是城市基层自治制度一切变革与创新——无论成功或是失败——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摘自《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3.352~356
标签:居民委员会论文; 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论文; 社区自治论文; 变革管理论文; 居民自治论文; 社区功能论文; 时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