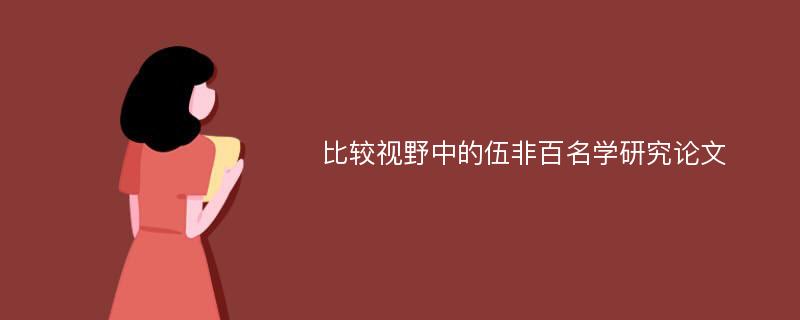
比较视野中的伍非百名学研究
卢 芸 蓉
(南京审计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211815)
摘 要 :伍非百所著《中国古名家言》是名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具有几个显著特色:研究定位上持广义名家观,框架建构具有系统性;研究时机上具有承前启后性;研究方法上具有继承创新性;研究风格上学术性大于政治性。另外,伍非百还为名学研究整理了丰富的资料并提出了很多新颖有说服力的学术观点。据此,伍非百在中国逻辑史及名学研究史上应享有更高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
关键词 :伍非百;名家;学术地位;研究特色
伍非百(1890―1965年)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墨学家和逻辑学家,其在逻辑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在于首次完整地、系统地研究“名家”思想,其专著《中国古名家言》是专门研究名学之作。伍非百持广义名家观,《墨经》也是其名家学说的一部分。伍非百的名家学说研究总体上可以分成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自1914年开始治《墨经》,至1949年《中国古名家言》一书的出版;第二个时期是1949年至其1965年去世。在这期间他不断对《中国古名家言》进行修改,但因种种原因,其修改稿未能定稿出版,直到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才依据其遗稿出版了《中国古名家言》。可以说,伍非百将毕生精力都投入《中国古名家言》一书的创作和修改中。
农业作为我国第一产业,主要是指利用植物的生长发育规律,通过人工培育来获得产品的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建设中占据重要位置。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又可以称之为“农业合作社”,主要是指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农业小生产者联合组成的组织形式,力求维护和改善各自的生产及生活条件,具有服务性、盈利性、民主性以及双层次性等诸多特点,在农业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基于此,本文就农业可持续发展对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要求进行阐述,并提出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对策。
与同时代的名学研究者相比,伍非百的名学研究范围最广、规模最宏大。20世纪初,名学研究处于复苏时期,梁启超、胡适、伍非百等都运用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名学。相比较而言,伍非百在研究范围上比梁启超更
广泛一些。梁启超的名学研究只限于墨家,其名学研究著作主要有《墨子之论理学》和《墨经校释》。胡适的名学研究著作主要有《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墨子小取篇新诂》。胡适的《先秦名学史》被认为对我国逻辑的起源、先秦诸子逻辑理论和逻辑方法的发展做出了大致的、历时的勾画[1]97。也就是说,胡适的名学研究范围虽然广,但是却只是描述了名学的大致轮廓,并没有太多深入的研究。伍非百的研究不仅涉及《墨经》《大小取》《公孙龙子》《邓析子》以及《正名》《齐物论》《尹文子》和其他散见于诸子书中的短章,并且将文本、章句、训诂、义理等融会贯通,使研究更为深入。但较为遗憾的是,现在出版或发表的撰写20世纪中国逻辑史或墨学研究的著作,对伍非百及《中国古名家言》的着墨及评价高度均无法与同时代的其他几位学者相提并论。我们认为,这是有失偏颇的。本文通过进一步研究《中国古名家言》,认为该著应该得到更高的评价。
一、广义名家观与系统性建构
(一)广义名家观
学术界对名学的界定是有争议的,但伍非百持的是“广义名家观”[2]页码,这与伍非百的经历有关。伍非百早年退出军旅后,萌发了文化救国的思想,因此退隐回川,埋头遍读周秦之书,最喜爱的是儒、墨、道三家。而在当时,进步士子一方面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面对中国的现实,倡导以墨家思想启蒙民众。墨家学说中的民主思想是他们首要倡导发扬的,其次则是墨家的无私献身精神。显然伍非百也受到这一思潮影响,他抱着教民救世的美好愿望,首选从《墨经》研读入手,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伍非百历经10年创作出版的《墨辩解故》,使他蜚声学林。此后他又发表一系列研究墨学的文章,如《〈墨辩〉定名答客问》《〈墨辩〉释例》《〈辩经〉原本章句非旁行考》等。这些文章部分被收录在《中国古名家言》一书中,还有一部分被收录在《墨子大全》中,其余则散佚了。这些文章从内容来看,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对墨辩的研究,另一部分则是对墨子的研究。
伍非百的名学研究,既继承了清代学者的“校释”法,同时又引用了“以西释中”法,但更多使用的是“以中释中”法,体现了他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的特点。
(二)系统性建构
从《中国古名家言》来看,伍非百不是简单持广义名家观,而是力图将之构建为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以《辩经》为中心,以《正名》为总结,其他典籍则是围绕《辩经》或从对立角度去驳斥,或从综合的角度对《辩经》的观点加以证明和反驳[2]。这是对“名家”研究的重要突破。
从《墨辩解故》发表到《中国古名家言》出版,伍非百得到同辈或后代学者较高的赞誉,也主要源于其研究成果的系统性。梁启超高度评价:“伍非百著《墨经解故》(即《墨辩解故》,下同),从哲学、科学上树一新观察点,将全部《墨经》视为有系统的组织。”“颇信其为斯学一大创作也。”[5]257汤炳正则认为在近代把全部《墨经》作为“有系统”的整体来进行研究的第一人应是伍非百,而《墨经解故》为第一部书[6]。
没一会,关云飞打电话来督促她和郭启明今天抓紧去交房款。郭启明带着哭腔对她说:“小美,对不起,我真的抢银行了,我要走了!”关小美无论如何不敢相信男友会做出这种事情来。郭启明抽出床板下那把带血的刀说:“真的,你看……”关小美瘫坐在地上。
这种系统性体现在多个方面:
自邓析与子产紧扣名词意义斗法开创名家学派之后,在其他学者眼中名家一直以狡辩者的形象存在,对其评价也多有诋毁之词,因此那些自诩为正统的学者是不屑于研究名学的。名学所研究的内容,对封建君主来说,无定国安邦之用,因此他们不宣扬名学思想;对“学而优则仕”的知识分子来说,无高官厚禄之利,因此他们也没有必要学习名学,且名家思想艰深晦涩,因此对名家的研究一直很少受重视。另外,名学的一些观点被误传而失其真意,如“鸡足三、牛羊足五”之辩,在社会上被道听途说,以致荀子被视为“奇辞怪”,《吕氏春秋》亦视其为“淫辞”。名理学未能自立,也未能成为传统,一些观点因为误传而被折杀。由于以上种种原因,“百家争鸣”之时在学术界一展风骚的名学,自“独尊儒术”到晋代时,已几成“绝学”。
伍非百在解《墨经》中,常结合因明来讨论,并用日常行为的心理来比喻,使释义通俗易懂。如《经上》第74 条“已:成、亡”及相应的《经说》文“已:为衣,成也。治病,亡也”。伍非百解释道:“成,成立也,当因明之‘立’。《经上》‘故,所得有后成也’,下文‘谓也不必成湿,故也必待所为之成也。’与此‘成’字同义。亡,荡除也,今言攻破,当因明之‘破’。凡持论者有以成立自宗为目的者,有以攻破敌论为目的者。有益于己之持论者,则务成之。有损于己之持论者,则务破之。譬如为衣,则欲其成,治病则欲其亡。故曰‘为衣,成也。治病,亡也’。”[3]72对于此条,张惠言的解释是“为衣以成为已,治病以亡为已”,孙诒让解释为“亡,犹言无病也”,梁启超没有解释。相比较而言,伍非百的解释更为详细明白。
在宏观层面上,对名、辞、说、辩四范畴的认识达到同时代学者的新高度。名、辞、说、辩,是古代名辩学上重要的四范畴,《墨经》中的“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其实只指出三个范畴,而到荀子《正名》的“实不喻然后命,命不喻然后期,期不喻然后说,说不喻然后辩”,才提出完整的四范畴。蒙默指出,近代学者对这四个范畴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4]11。蒙默认为梁启超、胡适等虽然认为《小取》是有条理、有格局的文章,但条理如何、格局怎样,并没有明确指出,更没有指出此四范畴是一个“理论体系”。近代学者对此四范畴研究较多,但也只针对此四范畴的认识,却很少有人提及此理论体系的创始人。蒙默认为首先提到此理论体系的是周云之。周云之在其主编的《中国逻辑史》中认为,沈有鼎先生的《墨经的逻辑学》是第一次概括出四范畴理论体系的作品[5]12。但蒙默认为,这个说法有不妥之处。他指出沈有鼎的“三个步骤”说其实只是一个的模糊认识,而此认识,伍非百早已有之。蒙默认为伍非百对此四范畴的认识虽然最终没有达到形成“理论体系”的阶段,但是如果说对此形成的模糊认识,首推还是伍非百先生[4]15。蒙默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伍非百对名、辞、说、辩的认识,也是逐步深化的。在1962年《中国古名家言》一书拟再版的《序录》中,伍非百对此问题的论述已经比较成熟。在此《序录》中,他认为先秦名辩“乃研究‘名’、‘辞’、‘说’、‘辩’四者之原理和应用的,详言之,就是研究‘正名’、‘析辞’、‘立说’、‘明辩’的规律和有关问题”[3]6。这里的论述显然已经有以名、辞、说、辩四级作为名辩学体系的意思了[4]15。伍非百虽然把四者当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来看,可他没有明确指出这是一个“理论体系”,但就是这个“模糊认识”,已然是重要突破,对后人的研究也具有启发作用。
接到任务后,我立即组织了两个层次的起草工作,一个是全市近20个委办局根据十条政策起草各自相关条文和实施意见,另一个是由各委办派出得力骨干参加市里文件起草小组,包括海关组沈耀华、李秀芬,保税区组黄开旭,金融银行组姜建清,证交所组毛应梁、尉文渊,外汇组林月娥,外经贸组陈忠浩,外资组范永进,财税组顾性泉,土地组谭企坤、王安德等人。那两个月里,五加二,白加黑,日夜奋战,除了将80年代经济技术开发区、特区的具体政策条款悉数收集、一网打尽,纳入浦东新区政策外,更主要的是研究特区没有干过的五方面事项。
李老黑干杯后,胳膊伸直,酒杯倒转,杯口斜对着我,让我验杯。李老黑不愧是久经考验的酒场老手,杯中居然滴酒未剩。李老黑的酒杯像探照灯一样在我头顶晃了晃,我知道他这样做不单是让我验杯,更多是包含了催促的意思。
二、研究时机的承前启后
在微观层面上,对一些名辩问题的争论体现了系统性的特征。伍非百以“坚白论”为例,指出综合荀子和庄子的说法,也可以了解“坚白论”的盈宗观点。因为心有征知,能“合异以为同,散同为异”,所以对通过五官所得到的知,能一一为之综合、分析,“或合而为一,或离而为多”,所以万物有奇偶、同异、分合,最终形成概念并命名。“能名而后可因之以记录其旧知,创造其新知,而知识因之以继长增高。”[3]164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墨经》与《公孙龙子》相互为立破,而荀子则是在两者的基础上综合扬弃。此类例子还有很多。也正因为他们对同一问题的讨论,使得他们的内容紧密联系,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名学系统。
1.4 鱼苗培育 刚孵化的鱼苗要首先在60 L的长方形玻璃槽中进行培育。出膜后6~8 h,卵黄吸收完成,幼苗能短暂地无方向地间歇游动,开始投喂活体草履虫;10 d后可以改投全人工制作的蛋白质含量为36%的膨化饲料粉末、轮虫及其他配合饲料,每天3~5次,投喂量以每次10 min内吃完为标准;鱼苗长大到2.5 cm以后移到10 m3的正方形流水池中培育,继续投喂蛋白质含量为36%的饲料粉末。
到了清代,义理、考据之风盛行,研究者将目光投向先秦诸子书,名家也因此再现在人们眼前。五四时期,学者们高呼解放思想,解除儒学枷锁,眼光自然也投向了一直被忽视的“不法先王,不是礼仪”的名学。在西方逻辑学系统地传入中国后,国内学者又发现中国先秦的名学与西方逻辑学在研究内容上极其相似,而西方的逻辑学在科学发展中有着重大作用,认识到这点,中国的名学也被重视起来。至此,“绝学”开始“复苏”。
调查父母进城务工的地点发现,无论在哪里务工,他们与孩子总是聚少离多,许多只能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与孩子短暂团聚。调查还发现,有12.6%的留守儿童不知道父母在哪里务工。分析认为农民在表达感情方面有些羞涩,只是想多赚些钱改善家庭环境,给孩子创造更好的条件,却忽略了与孩子必要的沟通与交流。
纵观这段时期的名家思想研究著作,学界对名家思想越来越关注,其成果也越来越多,但是没有一人如伍非百这样系统、大规模地研究先秦名学。伍非百所著《中国古名家言》,对古代中国的逻辑学说和有关名学学说的不同派系及歧异方向,都一一做了阐明[9]。
在这期间,伍非百除了著成《中国古名家言》,还发表了墨辩系列论文,参与“《墨辩》大讨论”,对名家进行系列考证,对典籍进行整理、辩伪,最终形成系统的名家学说。伍非百在其他学者对名家尚不注重之时,孜孜不倦潜心于名学研究,是名学复苏、起废中兴的一个有力推动者。
伍非百不仅继承了传统名学研究的要义,也与同时代的学者一起,借鉴西方逻辑学与印度因明学说,为名学在新时代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具有启后性。伍非百将西方逻辑学说和印度的因明学说,与《墨经》相互印证,并且用西方的文章结构,按照《墨经》原书的顺序,标成目录,自成统系[8]5。许行成在1923年版的《墨辩解故》一书《序》中认为,《中国古名家言》这本书特别用功之处在于目录与章句,通过目录将一篇零章断句的《墨经》整理成一部有条不紊的《辩学》,也算一项伟大发明[10]4。
清代学者对《墨经》进行了大量整理校读工作。20世纪,将《墨经》当作名学研究的,首推梁启超之《墨子之论理学》,栾调甫曾说梁任公所著《墨子之论理学》乃有辩理之谈[7]。伍非百入手解《墨经》时,《墨经》的研究者寥寥无几。李源澄在《中国古名家言》一书的序中曾说,当时世人皆视《墨经》为天书,当伍非百先生开始研究它时,被世人视为异端[8]3。伍非百在名学尚不流行时,克服上无老师指导,下无同仁讨论的局面,坚持埋头于名学的研究之中,对名学典籍进行了系统而翔实的考证。其后10年之间,名学一变而成显学。十年后书始成,斯学又复沉寂,伍非百始终坚持,外物不能转移其心[8]3。自治《墨经》始,至1932年《中国古名家言》稿成,前后历经20年。一直到1949年,是书才正式出版。
三、研究方法的继承创新
伍非百在校释《墨经》时,一方面采用西方的逻辑学、因明学说来比较说明,另一方面也注意引用先秦诸子之说来相互印证。他主要选取了道家的《齐物论》、儒家的《正名篇》、法家的纵合术、名家的“坚白同异”等观点来印证,并且在此后三年中,先后完成《公孙龙子》《齐物论》《大小取》《形名杂篇》。这些篇籍以《墨经》为正,《公孙龙子》为反,庄周、荀卿为合,在分合訾应之间,把八篇汇集起来,形成《中国古名家言》一书,“由孔子的‘正名’发展到墨子《墨经》,及再由墨家之‘辩’,回到荀子之‘正名’,是一线相承,回环往复的”[3]17。因此蒙默认为《中国古名家言》中虽然八篇各自独立,但是实际上却又是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大致就能够反映出先秦名辩学术发展的轨迹[4]10。至此,伍非百广义名学思想也完整显示出来。
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的体例为校勘、释义、按语。这种“校释”法显然是继承清朝学者的考据之风,因为伍非百自幼读私塾,所以对“校释”法非常熟悉。伍非百在解《墨经》时,还使用了清儒常用的“书证法”。清儒治经,“重取汉代古文经学家的注经方法,即举例为证以解字注音的实证方法”[1]118。伍非百在解“故”时,认为“故”从“古”得义,而“古”指口耳相传之史,后举孔子“信而不作,述而好古”“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以及章实斋“六经皆史也”等例为证。“翻检清代《墨子》诸注,大都采用王引之、孙诒让等人这种穷搜书证以归纳结论的注释方式。”[1]122伍非百治墨以孙诒让的《墨辩间诂》为基础,所以他采用此种方法,应该也是受孙诒让影响。
伍非百对名学的研究主要使用“以中释中”的方法。他始终立足于名家内部的互相訾应、互相对诤,将名家现存典籍看成一个正、反、合的系统,用他们之间的观点互为解释、互相参考。这种方法有助于结合当时社会环境了解名学的本来面貌,也为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逻辑史界的反思提供了研究资料。
当然,伍非百在研究方法上也不排外,伍非百解《墨经》,经常与逻辑学相互比附,并结合生活实例来解释。如《经上》“故:所得而后成也。”伍非百解释:“故、故事也。亦谓之史,引申为‘所以然’,当因明之因、演绎之大前提。”[10]40又如对《经上》:“智,明也。”伍非百解释为:“此智指知识。论辩也,分析也。仅有知觉,不得谓之知识。必须将所知觉者分析清楚,然后谓之知识。譬如雪,仅有冷与白等等感觉,不得谓之知雪。必须有冷不是水,白不是羽,等等分析,然后谓之知雪。”[3]24这种解释结合生活中的实际例子,显得通俗明白。
RF433射频模块选择TI公司的CC1101芯片,具有超低功耗和价格低廉的特点[18],其部分电路原理图如图4所示。
伍非百用西方科学知识来解释《墨经》,并有较前人独到之处。如《经上》“知:闻,说,亲;名,实,合,为”条,孙诒让注:知有此三义;张惠言注:“知有三:闻一,说二,亲三,皆合名实而成于为。”梁启超则详细给出解释,并明确指出这是知识来源的三大途径。伍非百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墨经》中系统的知识论。他认为:材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这是说明“何者为知”这个问题,而“闻、说、亲”回答了“云何有知”这个问题,“名、实、合、为”则回到了“所知谓何”这个问题。三条回答了知识论当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伍非百的这一看法是前人所未见的。
LBL组学员主要以面授课程为主,带教教师对EUS基本结构、操作手法、局部解剖、典型图例等内容进行统筹备课,按照难度循序渐进地设计课程进度,由浅入深地讲解EUS操作手法、EUS下胰腺及胆道正常结构及疾病典型图例(胰腺癌、胰腺囊肿、胰腺囊液腺瘤、胆道疾病等),之后按照学员理解程度继续介绍EUS下治疗步骤。
四、研究风格的学术化
伍非百的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中国古名家言》一书中。该书发表后,伍非百还不断对其进行修改,所以其学术思想一直处于变化中,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其文章中政治色彩的淡化和学术意味的逐渐浓郁。
在1949年版的《中国古名家言》中,处处凸显出伍非百对时事政治的关注,但这种政治色彩在1983年版的《中国古名家言》中就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纯学术的表达。伍非百研究风格的变化与他生活的时代分不开,也反映了他自我突破的能力和勇气。下面以《总序》的叙述为例进行分析。
伍非百在1949年版的《总序》中多处表现出对当时动荡社会的忧虑,字里行间透露出忧国忧民的思想。首先,他交代了走上学术道路的原因是遭世无为、欲隐又未可,本与学术没什么关联。他遍读诸子之书,最终选择了墨家学说作为学术起点。其《墨辩解故》发表后,虽得到众人称赞,但当时学人多蔽于名而不知实,所以他进一步去复古名家言,既为华夏矜世,且能正人心、息邪说。在其《中国古名家言》成稿时,起视边境、寇氛深矣,他遂又骛驰于国计民生有用之学,但辗转20年卒无所成。自觉天地日窄、志事日荒,国家有沦陷之忧。在这种背景下,他以孔子、老子自勉,隐居于四川南充西山,继续著书,身虽隐但仍心系国家[8]11。其次,伍非百发现,在周室衰微、教化不行时,孔子乃作六艺,六艺是百家之通说。而墨子修孔子之术,但弃其礼乐,作《辩经》以立名本,墨学遂微,而形名由此大兴。形名家虽亡,但其所以为名者,因传袭勿替。伍非百还认为,东汉以来重“名节”,魏晋之间重“名法”,晋以来重“名理”,自宋以后,竞言“名教”……莫能外“名”一字。天下之大,万物之多,古往今来学术之众,只有“名”是值得追求的。但现在已经是名不副实,人们处于自欺欺人的状态。结果是国家将亡、种族将尽[8]11。伍非百还认为中国是“名教”之国,这已经是可悲的事了。所以,在这种状态下整理古名家言,是“以名救名”。
1983年版的《总序》中,类似这样忧国忧民的思想,已经全部删改了。第五部分则首先对中国古名家典籍进行界定,确定《墨经》(含《经说》)上下四篇和《大取》《小取》《尹文子》《公孙龙子》《齐物论》《正名》《邓析子》以及在诸子书中的短章单句为现存名家典籍,并且分析了名家典籍散佚的原因以及如何研读名家典籍,然后介绍了各部典籍的大致内容,明确名家典籍有正、反、合之分,而《齐物论》《正名》分别在不同时期成为主流,如《齐物论》后流为魏晋期间的清谈明理,《正名》后流有“正名分”“深察名号”。“其弊极于汉季之标榜‘名节’,魏、晋初之夸饰‘名教’,束缚思想愈甚”[3]17。
从以上两个版本不同之处可见,伍非百在学术生涯早期时刻不忘时事政治,但后期则倾向于纯学术的探讨,文字中剔除了政治成分。这种变化体现在很多地方,反映了伍非百学术上的成熟。
伍非百在名学研究方面所做的贡献,除了上述以外,还包括对名家典籍进行“断章句、详训诂、明大义”等一系列整理工作,特别是对《墨经》的校释,他遵循“旁行”“牒经”“引说就经”等原则,对《墨经》经文次序进行调整,对经文训诂以及对整体章节的划分,使《墨经》进一步条理化,在文本校释上补充并校正了前人的遗漏和误解。
另外,在《中国古名家言》中,伍非百还提出了很多新颖和有说服力的观点。以20世纪20年代关于《墨辩》的大讨论为例,伍非百对同时代学者梁启超、胡适、栾调甫校释的评价[11],就相当有见地。
据此,我们认为虽然《中国古名家言》并非一部完美之作,但考虑到时代等因素,仍不愧为一部名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伍非百在中国逻辑史以及名学研究史上应享有更高的声誉。
参考文献 :
[1]郑杰文.20世纪墨学研究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2]卢芸蓉.伍非百名家思想论略[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121-124.
[3]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1983.
[4]蒙默.中国古名家言之再版代序[M]//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
[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6]汤炳正.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5.
[7]栾调甫.墨子研究论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48.
[8]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M].南充:南充益新书局,1949.
[9]朱前鸿.名家四子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6.
[10]伍非百.墨辩解故[M]//墨子大全:第27 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11]伍非百.评梁、胡、栾《墨辩》校释异同[M]//墨子大全:第27 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274.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the“Mingxue”Study of WU Feibai
LU Yunrong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Abstract : WU Feibai's “The Statement of Chinese Ancient ‘Mingjia’” is a representative book on Mingxue Studies, which has the typical features as follows: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in frame, transition in research time and the researching method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In addition, he also has collected abundant materials and put forward many new and convincing academic viewpoints.Therefore, WU Feibai should enjoy a higher academic status and influen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ogic and the history of “Mingxue”study.
Key words : WU Feibai; “Mingjia”;Academic status; research features
中图分类号 :B22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5261(2019)06-0053-06
收稿日期 :2019-05-04
基金项目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7SJB0353)
作者简介 :卢芸蓉(1974―),女,安徽无为人,讲师,博士。
〔责任编辑 杨宁〕
标签:伍非百论文; 名家论文; 学术地位论文; 研究特色论文; 南京审计大学文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