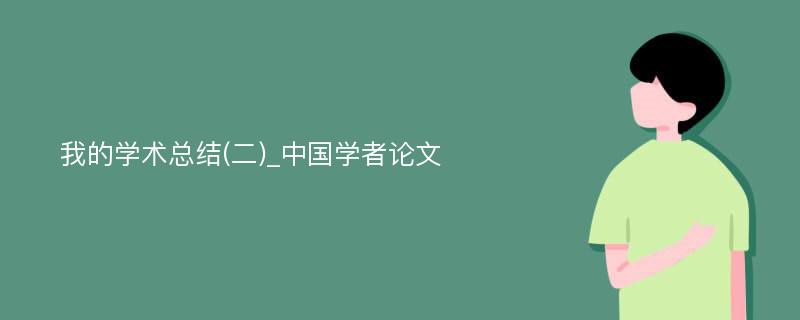
我的学术总结(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二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一、抓住一个问题终生不放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一个学人往往集中一段时间,钻研一个问题,搜集极勤,写作极苦。但是,文章一旦写成,就把注意力转向另外一个题目,已经写成和发表的文章就不再注意,甚至逐渐遗忘了。我自己这个毛病比较少。我往往抓住一个题目,得出了结论,写成了文章,但我并不把它置诸脑后,而是念念不忘。我举几个例子。
我于1947年写过一篇论文《浮屠与佛》,用汉文和英文发表。但是限于当时的条件,其中包括外国研究水平和资料,文中有几个问题勉强得到解决,自己并不满意,耿耿于怀者垂四十余年,一直到1989年,我得到了新材料,又写了一篇《再谈“浮屠”与“佛”》,解决了那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心中极喜。最令我欣慰的是,原来看似极大胆的假设竟然得到了证实,心中颇沾沾自喜,对自己的研究更增强了信心。觉得自己的“假设”确够“大胆”,而“求证”则极为“小心”。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佛典梵语中-am>0和u的几篇文章。1944 年我在德国哥廷根写过一篇论文,谈这个问题,引起了国际上一些学者的注意。有人,比如美国的 F.Edgerton, 在他的巨著《混合梵文文法》中多次提到这个音变现象,最初坚决反对,提出了许多假说,但又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最后,半推半就,被迫承认,却又不干净利落,窘态可掬。因此引起了我对此人的鄙视。回国以后,我连续写了几篇文章,对Edgerton加以反驳,但在我这方面,我始终没有忘记进一步寻找证据,进一步探索。由于资料缺乏,一直到了1990年,上距1944年已经过了四十六年, 我才又写了一篇比较重要的论文《新疆古代民族语言中语尾-am>u的现象》。在这里,我用了大量的新资料,证明了我第一篇论文的结论完全正确,无懈可击。
例子还能举出一些来。但是,我觉得,这两个也就够了。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谈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看到有一些学者,在某一个时期集中精力研究一个问题,成果一出,立即罢手。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学术问题,有时候一时难以下结论,必须锲而不舍,终生以之,才可能得到越来越精确可靠的结论。有时候,甚至全世界都承认其为真理的学说,时过境迁,还有人提出异议。听说,国外已有学者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真理的长河是永远流动不停的。
十二、搜集资料必须有竭泽而渔的气魄
对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来说,资料是最重要的。在旧时代,虽有一些类书之类的书籍,可供搜集资料之用,但作用毕竟有限。一些饱学之士主要靠背诵和记忆。后来有了素引(亦称引得),范围也颇小。到了今天,可以把古书输入电脑,这当然方便多了,但是已经输入电脑的书,为数还不太多,以后会逐渐增加的。到了大批的古书都能输入电脑的时候,搜集资料,竭泽而渔,便易如反掌了。那时候的工作重点便由搜集转为解释,工作也不能说是很轻松的。
我这一生,始终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我搜集资料始终还是靠老办法,笨办法,死办法。只有一次尝试利用电脑,但可以说是毫无所得,大概是那架电脑出了毛病。因此我只能用老办法,一直到我前几年集中精力写《糖史》时,还是靠自己一页一页地搜寻的办法。关于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谈到过,这里不再重复了。
不管用什么办法,搜集资料决不能偷懒,决不能偷工减料,形象的说法就是要有竭泽而渔的魄力。在电脑普遍使用之前,真正做到百分之百的竭泽而渔,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至少也必须做到广征博引,巨细不遗,尽可能地把能搜集到的资料都搜集在一起。科学研究工作没有什么捷径,一靠勤奋,二靠个人的天赋,而前者尤为重要。我个人认为,学者的大忌是仅靠手边一点搜集到的资料,就贸然做出重大的结论。我生平有多次经验,或者毋宁说是教训:我对一个问题做出了结论,甚至颇沾沾自喜,认为是不刊之论。然而,多半是出于偶然的机会,又发现了新资料,证明我原来的结论是不全面的,或者甚至是错误的。因此,我时时提醒自己,千万不要重蹈覆辙。
总之,一句话:搜集资料越多越好。
十三、我的考证
我在上面叙述中,已经谈到了考证,但仍然觉得意犹未足,现在再补充谈一谈“我的考证”。
考证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把它捧到天上去,无此必要;把它贬得一文不值,也并非实事求是的态度。清代的那一些考据大师,穷毕生之力,从事考据,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好多古书,原来我们读不懂,或者自认为读懂而实未懂,通过他们对音训词句的考据,我们能读懂了。这难道说不是极大的贡献吗?即使不是考据专家,凡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学者,有时候会征引一些资料,对这些资料的真伪、迟早都要进行一些必要的考证工作。这些几乎近于常识的事情,不言自喻。因此,我才说,考证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而且考证之学不但中国有,外国也是有的。科学研究工作贵在求真,而考据正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焉能分什么国内国外?
至于考证的工拙精粗,完全决定于你的学术修养和思想方法。少学欠术的人,属于马大哈一类的人,是搞不好考证工作的。死板僵硬、墨守成规、不敢越前人雷池一步的人,也是搞不好考证的。在这里,我又要引用胡适先生的两句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假设,胆越大越好。哥白尼敢于假设地球能转动,胆可谓大矣。然而只凭大胆是不行的,必须还有小心的求证。求证,越小心越好。这里需要的是极广泛搜集资料的能力,穷极毫末分析资料的能力,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然后得出的结论才能比较可靠。这里面还有一个学术道德或学术良心的问题,下一节再谈。
在考证方面,在现代中外学人中,我最佩服的有两位:一位是我在德国的太老师 Heinrich Lüders, 一位是我在中国的老师陈寅恪先生。他们两位确有共同的特点。他们能在一般人都能读到的普通的书中,发现别人看不到的问题,从极平常的一点切入,逐步深入,分析细致入微,如剥春笋,层层剥落,越剥越接近问题的核心,最后画龙点睛,一笔点出关键,也就是结论,简直如“石破天惊适秋雨”,匪夷所思,然而又铁证如山。此时我简直如沙漠得水,酷暑饮冰,凉沁心肺,毛发直竖,不由得你不五体投地。
上述两位先生都不是为考证而考证,他们的考证中都含有“义理”。我在这里使用“义理”二字,不是清人的所谓“义理”,而是通过考证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得出在考证之外的某一种结论。比如 Heinrich Lüders 通过考证得出了,古代印度佛教初起时的印度方言林立, 其中东部有一种古代半摩揭陀语,有一部用这种方言纂成的所谓“原始佛典”(Urkanon),当然不可能是一部完整的大藏经, 颇有点类似中国的《论语》。这本来是常识一类的事实。然而当今反对这个假说的人,一定把 Urkanon 了解为“完整的大藏经”,真正是不可思议。 陈寅恪先生的考证文章,除了准确地考证史实之外,都有近似“义理”的内涵。他特别重视民族与文化的问题。这也是大家所熟悉的。我要郑重声明,我决不是抹煞为考证而考证的功绩。钱大昕考出中国古无轻唇音,并没有什么“义理”在内,但却是不刊之论,这是没有人不承认的。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来,足证为考证而考证也是有其用处的,不可轻视的。
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我的许多考证的文章,却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比如,我考证出汉文的“佛”字是put,but的音译,根据这一个貌似微末的事实,我就提出了佛教如何传入中国的问题,我自认是平生得意之作。
十四、学术良心或学术道德
“学术良心”,好像以前还没有人用过这样一个词儿,我就算是“始作俑者”吧。但是,如果“良心”就是儒家孟子一派所讲的“人之初,性本善”中的“性”的话,我是不相信这样的“良心”的。人和其他生物一样,其“性”就是“食、色,性也”的“性”。其本质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人的一生就是同这种本能作斗争的一生。有的人胜利了,也就是说,既要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他就是一个合格的人。让别人活的程度越高,也就是为别人着想的程度越高,他的“好”或“善”也就越高。“宁要我负天下人,不要天下人负我”,是地道的坏人,可惜的是,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有人要问:既然你不承认人性本善,你这种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十分满意的解释。《三字经》上的两句话“性相近,习相远”中的“习”字似乎能回答这个问题。一个人过了幼稚阶段,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会感到,人类必须互相依存,才都能活下去。如果一个人只想到自己,都绝对地想到自己,那么,社会就难以存在,结果谁也活不下去。
这话说得太远了,还是回头来谈“学术良心”或者学术道德。学术涵盖面极大,文、理、工、农、医,都是学术。人类社会不能无学术,无学术,则人类社会就不能前进,人类福利就不能提高,每个人都是想日子越过越好的。学术的作用就在于能帮助人达到这个目的。大家常说,学术是老老实实的东西,不能搀半点假。通过个人努力或者集体努力,老老实实地做学问,得出的结果必须是实事求是的。这样做,就算是有学术良心。剽窃别人的成果,或者为了沽名钓誉创造新学说或新学派而篡改研究真相,伪造研究数据,这是地地道道的学术骗子。国际上和在我们国内,这样的骗子比比皆是。这样的骗局决不会隐瞒很久的,总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的。许多国家都有这样的先例,真相一旦暴露,不齿于士林,因而自杀者也是有过的。这种学术骗子,自古已有,可怕的是于今为烈。我们学坛和文坛上剽窃大案,时有所闻,我们千万要引为鉴戒。
这样明目张胆的大骗当然是绝不允许的。还有些偷偷摸摸的小骗,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戒心。小骗局花样颇为繁多,举其荦荦大者,有以下诸种: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在公开学术报告中听报告人讲演,平常阅读书刊杂志时读到别人的见解,认为有用或有趣,于是就自己写成文章,不提老师的或者讲演者的以及作者的名字,仿佛他自己就是首创者,用以欺世盗名。这种例子也不是稀见的。至于有人在谈话中告诉了他一个观点,他也据为己有。这都是没有学术良心或者学术道德的行为。
我可以无愧于心地说,上面这些大骗或者小骗,我都从来没有干过,以后也永远不会干。
我在这里补充几点梁启超在他所著的《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到的清代正统派的学风的几个特色:“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这同我在上面讲的学术道德(梁启超的“德”)完全一致。可见清代学者对学术道德之重视程度。
此外,梁启超同上书还举了一点特色:“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可以补充在这里,也可以补充上一节中。
十五、勤奋、天才(才能)与机遇
人类的才能,每个人都有所不同,这是大家都看到的事实,不能不承认的。但是有一种特殊的才能一般人称之为“天才”。有没有“天才”呢?似乎还有点争论,有点看法的不同。“十年浩劫”期间,有一度曾大批“天才”,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我至今不懂。根据我六七十年来的观察和思考,有“天才”是否定不了的,特别在音乐和绘画方面。你能说贝多芬、莫扎特不是音乐天才吗?即使不谈“天才”,只谈才能,人与人之间也是相差十分悬殊的。就拿教梵文来说,在同一个班上,一年教下来,学习好的学生能够教学习差的而有余。有的学生就是一辈子也跳不过梵文这个龙门。这情形我在国内外都见到过。
拿做学问来说,天才与勤奋的关系究竟如何呢?有人说“九十九分勤奋,一分神来(属于天才的范畴)”。我认为,这个百分比应该纠正一下。七八十分的勤奋,二三十分的天才(才能),我觉得更符合实际一点。我丝毫也没有贬低勤奋的意思。无论干哪一行的,没有勤奋,一事无成。我只是感到,如果没有才能而只靠勤奋,一个人发展是有限度的。
现在,我来谈一谈天才、勤奋与机遇的关系问题。我记得六十多年前在清华大学读西洋文学时,读过一首英国诗人 Thomas Gray的诗,题目大概是叫《乡村墓地哀歌(elegy)》,诗的内容, 时隔半个多世纪,全都忘了,只有一句还记得:在墓地埋着可能有莎士比亚。意思是指,有莎士比亚天才的人,老死穷乡僻壤间。换句话说,他没有得到“机遇”,天才白白浪费了。上面讲的有张冠李戴的可能;如果有的话,请大家原谅。
总之,我认为,“机遇”(在一般人嘴里可能叫做“命运”)是无法否认的。一个人一辈子做事、读书,不管是干什么,其中都有“机遇”的成分。我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如果“机遇”不垂青,我至今还恐怕是一个识字不多的贫农,也许早已离开了世界。我不是“王半仙”或“张铁嘴”,我不会算卦、相面,我不想来解释这一个“机遇”问题,那是超出我的能力的事。
十六、满招损,谦受益
这本来是中国一句老话,来源极古,《尚书·大禹谟》中已经有了,以后历代引用不辍,一直到今天,还经常挂在人民嘴上。可见此话道出了一个真理,经过将近三千年的检验,益见其真实可靠。
这话适用于干一切工作的人,做学问何独不然?可是,怎样来解释呢?
根据我自己的思考与分析,满(自满)只有一种:真。假自满者,未之有也。吹牛皮,说大话,那不是自满,而是骗人。谦(谦虚)却有两种,一真一假。假谦虚的例子,真可以说是俯拾即是。故作谦虚状者,比比皆是。中国人的“菲酌”、“拙作”之类的词儿,张嘴即出。什么“指正”、“斧正”、“哂正”之类的送人自己著作的谦词,谁都知道是假的,然而谁也必须这样写。这种谦词已经深入骨髓,不给任何人留下任何印象。日本人赠人礼品,自称“粗品”者,也属于这一类。这种虚伪的谦虚不会使任何人受益。西方人无论如何也是不能理解的。为什么拿“菲酌”而不拿盛宴来宴请客人?为什么拿“粗品”而不拿精品送给别人?对西方人简直是一个谜。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谦虚,做学问更是如此。如果一个学者,不管是年轻的,还是中年的、老年的,觉得自己的学问已经够大了,没有必要再进行学习了,他就不会再有进步。事实上,不管你搞哪一门学问,决不会有搞得完全彻底一点问题也不留的。人即使能活上一千年,也是办不到的。因此,在做学问上谦虚,不但表示这个人有道德,也表示这个人是实事求是的。听说康有为说过,他年届三十,天下学问即已学光。仅此一端,就可以证明,康有为不懂什么叫学问,现在有人尊他为“国学大师”,我认为是可笑的。他至多只能算是一个革新家。
在当今中国的学坛上,自视甚高者,所在皆是;而真正虚怀若谷者,则绝无仅有。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现象。有不少年轻的学者,写过几篇论文,出过几册专著,就傲气凌人。这不利于他们的进步,也不利于中国学术前途的发展。
我自己怎样呢?我总觉得自己不行。我常常讲,我是样样通,样样松。我一生勤奋不辍,天天都在读书写文章,但一遇到一个必须深入、更深入钻研的问题,就觉得自己知识不够,有时候不得不临时抱佛脚。人们都承认,自知之明极难。有时候,我却觉得,自己的“自知之明”过了头,不是虚心,而是心虚了。因此,我从来没有觉得自满过。这当然可以说是一个好现象。但是,我又遇到了极大的矛盾:我觉得真正行的人也如凤毛麟角。我总觉得,好老多学人不够勤奋,天天虚度光阴。我经常处在这种心理矛盾中。别人对我的赞誉,我非常感激。但是,我并没有被这些赞誉冲昏了头脑,我头脑是清楚的。我只劝大家,不要全信那一些对我赞誉的话,特别是那一些顶高得惊人的帽子,我更是受之有愧。
十七、没有新意,不要写文章
在芸芸众生中,在五行八作中,有一种人,就是像我这样的教书匠,或者美其名,称之为“学者”。我们这种人难免不时要舞笔弄墨,写点文章的。根据我的分析,文章约而言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被动写的文章,一是主动写的文章。
所谓“被动写的文章”,在中国历史上流行了一千多年的应试的“八股文”和“试帖诗”,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种文章多半是“代圣人立言”的,或者是“颂圣”的,不许说自己真正想说的话。换句话说,就是必须会说废话。记得鲁迅在什么文章中举了一个废话的例子:“夫天地者乃宇宙之乾坤,吾心者实中怀之在抱。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后面好像还有,我记不清楚了)这是典型的废话,念起来却声调铿锵。“试帖诗”中,也不乏好作品,唐代钱起咏湘灵鼓琴的诗,就曾被朱光潜先生赞美过,而朱先生的赞美又被鲁迅先生讽刺过。到了今天,我们被动写文章的例子并不少见。我们写的废话,说的谎话,吹的大话,这是到处可见的。我觉得,有好多文章是大可以不必写的,有好些书是大可以不必印的。如果少印刷这样的文章,出版这样的书,则必然能够少砍伐些森林,少制造一些纸张,对保护环境、保持生态平衡,会有很大的好处的,对人类生存的前途也会减少危害的。
至于主动写的文章,也不能一概而论,仔细分析起来,也是五花八门的。有的人为了提职,需要提出“著作”,于是就赶紧炮制。有的人为了成名成家,也必须有文章,也努力炮制。对于这样的人,无须深责,这是人之常情。炮制的著作不一定都是“次品”,其中也不乏优秀的东西。像吾辈“爬格子族”的人们,非主动写文章以赚点稿费不行,只靠我们的工资,必将断炊。我辈被“尊”为教授的人,也不例外。
在中国学术界里,主动写文章的学者中,有不少的人学术道德是高尚的。他们专心一志,唯学是务,勤奋思考,多方探求,写出来的文章,尽管有点参差不齐,但是他们都是值得钦佩、值得赞美的,他们是我们中国学术界的脊梁。
真正的学术著作,约略言之,可以分为两大类:单篇的论文与成本的专著。后者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古今中外的许多大部头的专著,像中国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等,都是名垂千古、辉煌璀璨的巨著,是我们国家的瑰宝。这里不再详论。我要比较详细地谈一谈单篇论文的问题。单篇论文的核心是讲自己的看法,自己异于前人的新意,要发前人未发之覆。有这样的文章,学术才能一步步、一代代向前发展。如果写一部专著,其中可能有自己的新意,也可能没有。因为大多数的专著是综合的、全面的叙述,即使不是自己的新意,也必须写进去,否则就不算全面。论文则没有这种负担,它的目的不是全面,而是深入,而是有新意,它与专著的关系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吧。
我在上面几次讲到“新意”,“新意”是从哪里来的呢?有的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出于“灵感”的,比如传说中牛顿因见苹果落地而悟出地心吸力。但我们必须注意,这种灵感不是任何人都能有的。牛顿一定是很早就考虑这类的问题,昼思梦想,一旦遇到相应的时机,豁然顿悟。吾辈平凡的人,天天吃苹果,只觉得它香脆甜美,管它什么劳什子“地心吸力”干嘛呀!在科学技术史上,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来,现在先不去谈它了。
在几十年前极“左”思想肆虐的时候,学术界曾大批“从杂志缝里找文章”的做法,因为这样就不能“代圣人立言”,必须熟读圣书,心中先有一件东西要宣传,这样的文章才合乎程式。有“新意”是触犯天条的。这样的文章一时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这样的文章印了出来,再当作垃圾卖给收破烂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白色垃圾”),除了浪费纸张以外,丝毫无补于学术的进步。我现在立一新义: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到杂志缝里才能找到新意。在大部头的专著中,在字里行间,也能找到新意的,旧日所谓“读书得间”,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因为,一般说来,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往往只谈一个问题,一个新问题,里面是有新意的。你读过以后,受到启发,举一反三,自己也产生了新意,然后写成文章,让别的学人也受到启发,再举一反三。如此往复循环,学术的进步就寓于其中了。
可惜——是我觉得可惜——眼前在国内学术界中,读杂志的风气,颇为不振。不但外国的杂志不读,连中国的杂志也不看。闭门造车,焉得出而合辙?别人的文章不读,别人的观点不知,别人已经发表过的意见不闻不问,只是一味地写开写开。这样怎么能推动学术前进呢?更可怕的是,这个问题几乎没有人提出。有人空喊“同国际学术接轨”。不读外国同行的新杂志和新著作,你能知道“轨”究竟在哪里吗?连“轨”在哪里都不知道,空喊“接轨”,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十八、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
端正对待不同意见(我在这里指的只是学术上不同的意见)的态度,是非常不容易办到的一件事。中国古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可见此事自古已然。
我对于学术上不同的观点,最初也不够冷静。仔细检查自己内心的活动,不冷静的原因决不是什么面子问题,而是觉得别人的思想方法有问题,或者认为别人并不真正全面地实事求是地了解自己的观点,自己心里十分别扭,简直是堵得难受,所以才不能冷静。
最近若干年来,自己在这方面有了进步。首先,我认为,普天之下的芸芸众生,思想方法就是不一样,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这是正常的现象,正如人与人的面孔也不能完完全全一模一样。要求别人的思想方法同自己一样,是一厢情愿,完全不可能的,也是完全不必要的。其次,不管多么离奇的想法,其中也可能有合理之处的。采取其合理之处,扬弃其不合理之处,是唯一正确的办法。至于有人无理攻击,也用不着真正地生气。我有一个怪论:一个人一生不可能没有朋友,也不可能没有非朋友。我在这里不用“敌人”这个词儿,而用“非朋友”,是因为非朋友不一定就是敌人。最后,我还认为,个人的意见不管一时觉得多么正确,其实这还是一个未知数。时过境迁,也许会发现,并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到了此时,必须有勇气公开改正自己的错误意见。梁任公说: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这是光明磊落的真正学者的态度。最近我编《东西文化议论集》时,首先自己亮相,把我对“天人合一”思想的“新解”(请注意“新解”中的“新”字)和盘托出,然后再把反对我的意见的文章,只要能搜集到的,都编入书中,让读者自己去鉴别分析。我对广大的读者是充分相信的,他们能够明辨是非。如果我采用与此相反的方式:打笔墨官司,则对方也必起而应战。最初,双方或者还能克制自己,说话讲礼貌,有分寸。但是笔战越久,理性越少,最后甚至互相谩骂,人身攻击。到了这个地步,谁还能不强词夺理,歪曲事实呢?这样就离开真理越来越远了。中国学术史上这样的例子颇为不少。我前些时候在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上写过一篇短文:《真理越辨越明吗?》。我的结论是:真理越辨(辩)越糊涂。可能有人认为我是在发怪论,我其实是有感而发的。
十九、必须中西兼通,中西结合,地上文献与地下考古资料相结合
这一节其实都是“多余的话”,可以不必写的。可我为什么又写了呢?因为,经过多年的观察,我发现,在中国学者群中,文献与考古相结合多数学者是做到了。但是,中外结合这一点则做得很不够。我在这里不用“中西”,而用“中外”,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并非笔误。
我个人认为,居今之世而言治学问,决不能坐井观天。今天已经不是乾嘉时代了。许多学术发达的外国,科学、技术灿然烂然。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也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我们中国学者,包括专治中国国学的在内,对外国的研究动向和研究成果,决不能视若无睹。那样不利于我们自己学问的进步,也不利于国与国之间的学术文化交流。可是,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国内学术界确有昧于国外学术界情况的现象。年老的不必说,甚至连一些中年或青年学者,也有这种现象。我觉得,这种情况必须尽快改变。否则,有人慨叹中国一些学科在国际上没有声音,这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说汉语的人虽然数目极大,可惜外国人不懂。我们的汉语还没有达到今天英语的水平。你无论怎样“振大汉之天声”,人家只是瞠目摇头。在许多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出席的一些中国学者,往往由于不通外语,首先在大会上不能自己用外语宣读论文,其次在会议间歇时或联欢会上,孑然孤立,窘态可掬。因此,我希望我们年轻的学者,不管你是哪一门、哪一科,尽快掌握外语。只有这样,中国的声音才能传向全球。
二十、研究、创作与翻译并举
这完全是对我自己的总结,因为这样干的人极少。
我这样做,完全是环境造成的。研究学问是我产生兴趣之所在,我的几乎是全部的精力也都用在了这上面。但是,在济南高中读书时期,我受到了胡也频先生和董秋芳(冬芬)先生的影响和鼓励,到了清华大学以后,又受到了叶公超先生、沈从文先生和郑振铎先生的奖励,就写起文章来。我写过一两首诗,现在全已佚失。我不愿意写小说,因为我厌恶虚构的东西。因此,我只写散文,六十多年来没有断过。人都是爱虚荣的,我更不能例外。我写的散文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上述诸先生的垂青,后来又逐渐得到了广大读者的鼓励。我写散文不间断的原因,说穿了,就在这里。有时候,搞那些枯燥死板的学术研究疲倦了,换一张桌子,写点散文,换一换脑筋。就像是磨刀一样,刀磨过之后,重又锋利起来,回头再搞学术研究,重新抖擞,如虎添翼,奇思妙想,纷至沓来,亦人生一乐也。我自知欠一把火,虽然先后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理事、顾问,我从来不敢以作家自居。在我眼中,作家是“神圣”的名称,是我崇拜的对象。我哪里敢鱼目混珠呢?
至于搞翻译工作,那完全是出于无奈。我于1946年从德国回国以后,我在德国已经开了一个好头的研究工作,由于国内资料完全缺乏,被迫改弦更张。当时内心极度痛苦。除了搞行政工作外,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我必须找点工作干,我指的是写作工作。写散文,我没有那么多真情实感要抒发。我主张散文是不能虚构的,不能讲假话的,硬往外挤,卖弄一些花里胡哨的辞藻,我自谓不是办不到,而是耻于那样做。想来想去,眼前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搞翻译。我从德国的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说译起,一直扩大到梵文和巴利文文学作品。最长最重要的一部翻译是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这一部翻译的产生是在我一生最倒霉、精神最痛苦的时候。当时十年浩劫还没有结束,我虽然已经被放回家中,北大的“黑帮大院”已经解散,每一个“罪犯”都回到自己的单位,群众专政,监督劳改。我头上那一摞莫须有的帽子,似有似无,似真似假,还沉甸甸地压在那里。我被命令掏大粪,浇菜园,看楼门,守电话,过着一个“不可接触者”的日子。我枯坐门房中,除了送电话、分发报纸信件以外,实在闲得无聊。心里琢磨着找一件会拖得很长,但又绝对没有什么结果的工作,以消磨时光,于是就想到了长达两万颂的《罗摩衍那》。从文体上来看,这部大史诗不算太难,但是个别地方还是有问题有困难的。在当时,这部书在印度有不同语言的译本,印度以外还没有听到有全译本,连英文也只有一个编译本。我碰到困难,无法解决,只有参考也并不太认真的印地文译本。当时极“左”之风尚未全息,读书重视业务,被认为是“修正主义”。何况我这样一个半犯人的人,焉敢公然在门房中摊开梵文原本,翻译起来,旁若无人。这简直是在太岁头上动土,至少也得挨批斗五次。我哪里有这个勇气!我于是晚上回家,把梵文译为汉文散文,写成小纸条,装在口袋里,白天枯坐门房中,脑袋里不停地思考,把散文改为有韵的诗。我被进一步解放后,又费了一两年的时间,终于把全书的译文整理完。后来时来运转,受到了改革开放之惠,人民文学出版社全文出版,这是我事前绝对没有妄想过的。
我常常想,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如果我自己不跳出来反对那一位臭名昭著的“老佛爷”,如果我没有成为“不可接触者”,则必终日送往迎来,忙于行政工作,《罗摩衍那》是绝对翻译不出来的。有人说:“坏事能变成好事”,信然矣。人事纷纭,因果错综,我真不禁感慨系之了。
“总结”暂时写到这里。有几点需要说明一下:
第一,书名叫《学术回忆录》,是以回忆我这一生六七十年来的学术研究的内容为主轴线来写作的,它不是一般的《回忆录》,连不属于狭义的学术研究范围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都不包括在里面。目的无它,不过求其重点突出、线索分明而已。但是,考虑到文学创作与文学翻译与学术研究工作毕竟是紧密相联的,所以在“总结”的最后又加上了一节。
第二,《学术回忆录》本来打算而且也应该写到1997年的。但是,正如我在上面说到过的那样,我是越老工作干得越多,文章写得也多,头绪纷繁,一时难以搜集齐全,《回忆录》写起来也难,而且交稿有期,完成无日。考虑了好久,终于下定决心,1994年以后的《学术回忆录》以后再写,现在暂时告一段落。
第三,但是,我在这里却遇到了矛盾。按理说,《回忆录》写到哪一年,“总结”也应该做到哪一年。可是,事实上,却难以做到。《回忆录》可以戛然而止,而“总结”则难以办到。许多工作是有连续性的,总结必须总结一个全过程,不能说停就停。因此,同《回忆录》不能同步进行,“总结”一直写到眼前。将来《回忆录》写到1997年时,“总结”不必改动,还会是适合的,有用的。
第四,“总结”的目的是总结经验和教训的。我这一生活得太长,活干得太多,于是经验和教训就内容复杂,头绪纷纭。我虽然绞尽了脑汁,方方面面,都努力去想。但是,我却一点把握也没有,漏掉的东西肯定还会有的。在今后继续写《学术回忆录》的过程中,只要我想到还有什么遗漏,在《回忆录》暂告——只能暂告,我什么时候给生命划句号,只有天知道——结束时,我还会补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