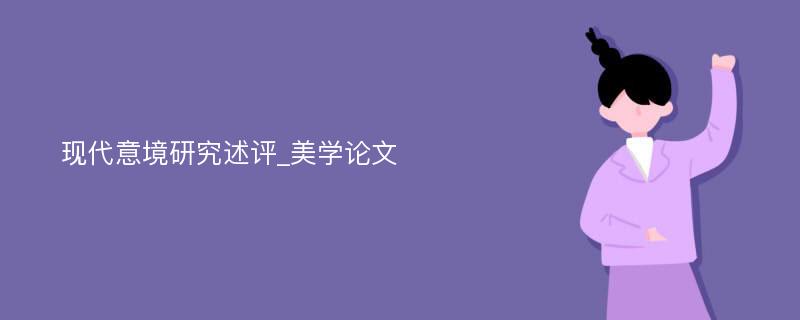
现代意境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意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意境,在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中,是一个最有生命力和最现代化了的重要范畴。因此,在现代的古代文论和美学范畴研究中,对于意境的研究最多、最热烈、也最有成效。本文所指的“现代”,是从1919年至1991年这段时间。在这70多年时间里,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一直处于急风骤雨的变革之中,所以,意境研究的发展既遇到了挑战,也得到了机遇。但是与以往相比,意境研究还是向前大大地发展了,即由十分普遍和深入的理论研究向学科的建构迈进。现从三个方面,述评如下。
Ⅰ、现代意境研究的社会文化背景
现代意境研究,是现代社会科学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而,现代意境研究便与现代社会科学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具体地说,从研究者的观念、研究的方法到研究的规模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现代社会科学文化背景的规定和制约。
1.文艺美学轴心的调节与反调节。
从上古至近古,我国文艺美学的轴心是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于是在这个轴心上便形成了意境范畴和意境理论。然而,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这种情形则不复存在了。首先,连年不断的战争从外部促使文化轴心的转换和文艺美学轴心的调节。从20年代到建国前的30多年中,大小战争连年不断,特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几乎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以各种方式投入战争,当然文化艺术人也不例外。这一时期的文化轴心,便由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转换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审美关系。实质上这是一种战时形态的文化。传统文化人赏花吟月的悠闲心态发生了变化,长期以来占据他们心理世界的风花雪月逐渐被社会人事所替代。如30年代,文艺界人士对“新月派”诗人和林语堂、周作人小品文的吟花玩月的唯美主义倾向的批评,就证明了这一点。其次,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特别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从内部决定了文化轴心的转换和文艺美学轴心的调节。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一个明确的标志。他认为,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以工农兵群众为主体的社会生活,是革命文艺的唯一的源泉,因此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这与在20年代初期,宗白华先生所认为的:“花草的精神,水月的颜色,都是诗意诗境的范本”,因而主张诗人“在自然中活动”[1]是大不一样的。这是传统审美文化轴心向现代转换的根本标志。这时,构成艺术意境的两个方面即“意”与“境”都发生了变化。“意”由诗人之情变为“人民之情”,“境”由风花雪月变为“人民之事”。[2]文艺的情感内涵及其载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近代改良派诗人所向往的“新意境”终于出现了。这种情形在20年代中后期就绽露端倪了。从闻一多先生收编的《现代诗钞》中就可看出,诗境已变化为人或人造物,诸如理发匠、水手、老兵、女人,或者为汽车、火车、大木船、伞、烟囱、刺刀等。现代散文也是如此,即使“写到了风花雪月,也总要点出人与人的关系,或人与社会的关系来,以抒怀抱。”[3]这种情形从延安时期以后,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文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当然,这期间文艺美学轴心的反调节也是存在的,诸如“新月派”的诗歌和林语堂式的小品文等。不过,调节是主流,反调节是支流;调节是现代的开端,而反调节则是传统的延续。
2.外国文艺美学的大量输入和中国现代文艺美学的“西化现象”。
这是促使传统文艺美学轴心转换的另一个原因,也是意境研究所遇到的主要挑战。这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从1919年至1949年为一个时期,共出版西方美学和文艺学译著66部,其中从日语移译24部,从俄语移译18部。[4]这是西方诸国如古希腊、古罗马、德、意、英、法文艺美学的输入期;从1950年至1970年为一个时期,共出版外国文艺学和美学译著63部,其中从苏联移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就有38部。这是以苏联为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影响中国的时期;从1978年至1983年为一个时期,共出版西方文艺学和美学译著37部。这是英美现代美学和西方现代派文艺学的输入期。总之,西方文艺学和美学通过这样三次大规模地输入,加之数量更多的西方文艺作品的输入,都程度不同地影响和同化着中国现代文艺人的观念和思想。从这三个时期所出版的194部国人编著的文艺学和美学论著中,便可以看到这种“西化现象”的广泛存在。在文艺创作方面也是如此。正如梁实秋说的,“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几乎可以说没有人不受“西化”的影响,就连国学渊博的胡适、鲁迅、闻一多和郭沫若等人都是如此。因为,这是时代的潮流。于是,意境在现代文艺作品里由中心跌入边缘,而且逐渐地淡化了、远去了;同样,在中国现代文艺学和美学中,从观点、范畴到理论,也几乎全部是搬用西方的。意境不仅失去了存在的话语环境,也失去了其辉煌的中心话语地位。在这种西化潮流裹挟下的意境研究,也只能是为研究而研究,因为它在重构中国现代文艺学和美学的工作中,已经丧失了所应有的建构能力。
3.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复归。
中国现代文艺学和美学的大量西化,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和美学的丢失。彻底丢失传统,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这是因为,每个中国人的血管里都流淌着传统的血液,每个中国人的心灵里也有着传统文化的深层积淀。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丢失传统等于丢失自己,否定传统就是自我否定。因此,现代中国人每在历史的转型期,都要对传统文化表示怀疑甚至批判,但从不丢弃传统,形势一旦稳定就又要恢复传统,重建传统。“五四”前后、“文革”前后和新时期前后都是如此。否定传统之糟粕,弘扬传统之精华;有勇气批判传统,也有勇气重建传统,这便是现代中国人的特点。所以,70多年来,“全盘西化”的观点一直受到中国人的抵制。这是意境研究在现代得以延续和发展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意境研究在现代虽然遇到了来自西方的三次挑战,但并不是没有机遇。在20—30年代,当西方文化如潮水般涌来之时,仍有人坚持研究意境;在50—60年代,由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对于“民族性”的提倡,使意境研究得到了发展的机遇。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来,随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讨论的深入,随着“传统文化热”的不断升温,随着“民族特色”的讨论和实践,逐步掀起了意境研究的高潮。
总之,现代意境研究就是在以上所述的“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文化背景下开展的。值得指出的是,现代意境研究并不是遗世独立的文化现象,而是紧跟着现代中国文化的步伐前进的。因而现代意境研究不仅有一个纷纭复杂的现代文化背景,而且也深深地打上了现代文化的烙印。比如在下文将要展开的论述中,就会看到80年代以来的方法论热、美学热、文化热、比较文学热等文化现象,对于意境研究的直接影响。因此,只有透过现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来观照现代意境研究,才是全面的、科学的。
Ⅱ、现代意境研究的发展概况
70多年来,现代意境研究沐浴着现代文化的风风雨雨,虽步履艰难,但却一直进行着、发展着。下文将这70多年来的现代意境研究划分为三个时期,并加以述评。
1.第一时期(1919—1950年)。
从1919年至1950年,是现代意境研究的转型时期。所谓“转型”,是指在以“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型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大文化背景下,意境研究的观念、方法和语言操作的转型。但有一个总的特点,就是对“新意境”的理论探求。这个时期的初期由于处在新旧转型的阵痛之中,中、后期又由于战时形态文化的影响,意境研究呈现出戛戛其难的状况。所以,在这个时期共有29人发表意境研究论文30篇,除宗白华先生发表2篇外,每个研究者才发表1篇次,几乎每年还平均发不到1篇。宗白华先生是现代研究意境最早的人,也是这个时期意境研究最有影响的美学家。他在1920年2月发表的《新诗略谈》一文中,将意境看作新诗的本质,要求“新诗的创造”,应“表写天真的诗意与天真的诗境。”这种观点在当时影响很大,如他的朋友康白情先生在同年3月发表的《新诗底我见》一文中,支持这种观点,并在宗先生提出的“情绪的意境”外,又提出“想象的意境”。这就是他著名的“两种意境”说。他认为,“情绪是主观的,而引起或寄托情绪的是客观的”,主客观的统一便是“情绪的意境”;而有些诗则是靠想象去“构成一个新意境,构成一个诗的世界”,这便是“想象的意境”。这两种意境在多数情况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不好分。这是对王国维意境类型说的新发展。到40年代,宗白华先生又发表了《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1943)一文。这篇文章内容丰厚,论述了意境的本质、意义和种类;谈到了意境创造与人格涵养的关系,以及意境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特别是结合佛禅和庄道哲学,论述了中国艺术意境的结构特点,即讲究深度、高度和阔度,尤其是对空灵飘逸的灵境给予更多的关注和论述。这是一篇为现代意境研究奠基的力作,它的影响至今仍然存在着。胡适在1919年10月发表的《谈新诗》和1926年出版的《词选》中,将“新意境”作为一个批评的标尺,成为现代“意境批评”的第一人。朱光潜先生在1934年发表的《诗的隐与显》一文中,提出了“同物之境”和“超物之境”的新看法。值得一提的,还有1934—1935年间钱杏邨、洪为法、许钦文和郁达夫等人对于小品文意境的评论。此外,张其春的《中西意境之巧合》(1937)一文,是最早用中西比较的方法研究意境的。
2.第二时期(1951—1977年)。
从1951年至1977年,是现代意境研究相对停滞的时期。所谓“停滞”,有三层意思:一是在这个时期的初期,有五、六年时间意境研究处于停滞状态。李泽厚先生谈到这种现象时说:“‘意境’是中国美学根据艺术创作的实践所总结地提出的重要范畴,它也仍然是我们今日美学中的基本范畴。可惜对这一问题我们一向就研究得极为不够。这几年来就似乎根本没有看到过研究分析这一问题的任何文章。”[5]二是在这个时期的后期,即从1966年至1977年的12年时间里,由于受“文化大革命”和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的影响,意境研究处于空白状态,在现代意境研究史上形成了严重的“断层现象”。三是在这个时期的26年中,共有47人发表意境研究论文51篇,每位研究者也只是发表1篇次,年平均发表不到两篇。与上一个时期相比,并没有发展多少,几近于停滞状态。当然,这只是一个“量”的分析。从“质”的分析看,也是如此。这一个时期的意境研究质量,与上一个时期相比,在有些地方前进了,在有些方面却倒退了,总的来看处于停滞状态。
和这个时期的社会文化发展相适应,这个时间的意境研究的总特点是,“马列化”与“左倾化”并存。先看“马列化”的意境研究。马列主义哲学是中国社会科学文化的指导思想,自然也是意境研究的指导思想,在这个时期,唯物辩证法也就成为意境研究的主要方法,因此,这个时期的意境研究便具有“马列化”的鲜明的时代特色。李泽厚先生是这个时期较早地发表意境研究论文的美学家,也是“马列化”意境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意境浅谈》(1957)一文,就是运用马列主义唯物反映论观点来研究意境的力作。他认为,意境包括“境”和“意”两个方面,即“生活形象的客观反映方面和艺术家情感理想的主观创造方面”,“‘意境’是在这两方面的有机统一中所反映出来的客观生活的本质的真实。”(引文着重点为原作者所加,下同)。“所谓‘情景的交融’……等等,就都还是为了更深入地本质地反映生活的真实。”他由此出发批评了朱光潜先生,指出其错误在于“否认艺术的意境只能是生活境界的反映”。对于现代意境研究来说,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新的思路。但是,其缺点也是明显的。如果引用他的学生赵士林的话说,就是:“今天看来,他对意境的分析,似还有过分强调‘反映’的痕迹,而对‘表现’的论说似嫌不足。”[6]吴奔星先生的《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境界”论》(1963)一文也是具有代表性的。他运用马列文论的基本原理来评价王国维的境界说。认为,“‘境界’的涵意是和以形象反映现实的艺术规律相通的”;“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谈的是“诗人与现实的关系”;所谓“造境”和“写境”,即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创作方法”。因此,“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可以说初步立足于唯物主义的基地,具有现实主义的倾向。”这些看法虽然显得有些生硬,但却体现了作者运用马列文论的基本原理来研究意境的良苦努力。
再看“左倾化”的意境研究。在这个时期,人们的政治热情极度高昂,特别是在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中,造就了一代人的“大批判情结”式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果导致了左倾思潮在学术界的长期泛滥,也就出现了“左倾化”的意境研究。具体说,就是主要集中在对于王国维“境界说”的批判上。叶秀山在《也谈王国维的“境界”说》(1958)中,追究王国维“境界”说“统一的基础”和“感情的实质”,认为其“理论基础是唯心论的”,其“感情”是“人性论”的,于是进行“彻底批判”。徐翰逢《〈人间词话〉“境界”说的唯心论实质》(1960)认为,王氏的“境界”说,是“蜃楼海市”,是“资产阶级美学观的翻版”。张文勋《从〈人间词话〉看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实质》(1964)一文,给王国维定了三条罪状,即“利用‘境界’说,宣扬艺术至上的唯美主义”;利用“‘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论调,宣扬主观唯心主义”;“用所谓‘赤子之心’,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因此要“加以严肃的批判”。这些文章所表现出的“左倾化”失误,并不仅仅是属于作者个人的,也是属于一个时代的,因为当时很少有人能不这样做。
在这个时期的意境研究中,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指出,就是先后有许多报刊对“意境”展开了集中的讨论。诸如,在50年代的《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里,李泽厚、陈咏、叶秀山和徐翰逢等人发表文章,对意境问题展开了讨论。进入60年代后,报刊上对意境的讨论显得更加热烈。《文汇报》发表了吴彰垒、钱仲联、周振甫、吴调公、叶朗的文章,讨论意境问题;《黑龙江日报》连续发表了问轩的3篇意境论文;《江海学刊》发表了吴调公、吴奔星、端木思敏的意境研究论文;《山花》发表了李德明、陈小平、小高的论文,就“诗的意境与含蓄”问题展开了讨论,等等。
3.第三时期(1978—1991年)。
从1978年至1991年,是现代意境研究的发展时期。进入新时期以来,在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下,我国人民拨乱返正,改革开放,创造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文化发展的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于是,学术文化从政治的战车上被松绑下来,获得了自由发展的独立品格;也恢复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地位,极大地激发了其科学研究的积极性。正是在这样一种祥和、宽松和民主的社会文化气氛中,意境研究获得了空前的全方位的发展。据我的不完全统计,在短短的13年中,研究意境的人约有1091人次,发表论文约有1147篇。就是说,每年平均都有84人投入意境研究,发表论文88篇。这是现代意境研究全方位发展的黄金时期。所谓“全方位发展”的特点是,多元的课题取向,多角度的学科视野,和多方法的研究操作方式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意境史研究。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在现代意境研究中,形成了一个“王国维圈”。只要一提意境,就是王国维的“境界说”;或者一提王国维,就想到意境,似乎意境史是从王国维开始的。这种情形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意境史的研究。进入80年代以来,学界同仁努力从“王国维圈”中走出来,探源寻流,将意境的源头找到王昌龄那儿,找到老庄和《周易》那儿,开始了意境史研究。最早发表的论文是蓝华增的《古代诗论意境说源流刍议》(1982),接着便出现了一大批这样的论著,诸如潘世秀、叶朗、曾祖荫、刘九洲等人的有关论著。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意境的历史轮廓已基本清晰,这是由一组文章的描述所构成的。如胡晓明的《中国前意境思想的逻辑发展》、章楚藩的《“意境”史话》、冯契的《中国近代美学关于意境理论的探讨》、马正平的《五十年来意境研究述评》、张毅的《建国以来“意境”研究述评》和阎采平的《近十年来“意境”研究述要》等等。这一时期,人们还对意境史上的各家学说进行了研究,诸如庄子、刘勰、皎然、权德舆、刘禹锡、司空图、朱熹、严羽、姜夔、谢榛、王夫之、方东树、林纾、闻一多、宗白华、朱光潜、李泽厚、钱钟书等人的意境论,将意境史的研究引向了深入。
b.从不同学科的角度研究意境。这个时期意境研究的学科视野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开阔,有从哲学角度研究意境的,如李林的《诗词意境的哲学思考》;有从美学角度研究意境的,如张少康的《论意境的美学特征》;有从佛学角度研究意境的,如蒋述卓的《佛教境界说与中国艺术意境理论》;有从文化学角度研究意境的,如李悟的《试论意境范畴形成的文化背景》;有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意境的,如陈洪的《意境—艺术中的心理场现象》;还有从教育学角度研究意境的,如滕碧城的《谈诗歌的意境教学》,等等。人们在不同的学科视野里,对意境研究进行了新的开拓。
c.运用不同的方法研究意境。从80年代初期以来掀起的“方法论热”,也波及到了意境研究领域。这是对传统治学方法的改革,同时也是学术观念的深层转换。先是一些青年学者竞相尝试,接着一些中老年学者也都赶了上来,为现代意境研究开了新局。这时期,由于受“比较文学热”的影响,所以用比较方法研究意境的较多,发表论文16篇。或将意境与意象比较,如陈宁的《西方意象与中国意境之比较》;或以中西文化和美学的角度比较,如毛宣国的《“境界说”与中西文化和美学》;或以中外诗歌比较,如吴优生的《中英自然诗的意境结构》;而大多则是将意境与典型比较,如曹顺庆的《意境说与典型论产生原因比较》,周来祥的《东方的艺术意境与西方的艺术典型》等。此外,有用系统论方法的,如鲁文忠的《中国古代意境系统论》,陈良运的《王国维“境界”说之系统观》;有用符号学方法的,如刘庆璋的《文艺“符号”论与“境界”说》;也有用模糊数学方法的,如刘若复的《境界说与模糊性》,等等。这是现代意境研究中的新现象。
d.文学艺术意境研究。近十多年来,文艺界和美学界人士联袂对文艺作品中的意境进行了理论概括和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多,共约有751篇论文。他们结合作品,或赏析,或评论,从微观到宏观,从个别到一般,对文学艺术意境进行了有声有色的研究。在文学意境方面,除了传统的诗、词、散文意境的研究课题外,还深入到小说、报告文学、童话和民间文学等领域。诸如,陈尚仁的《论李士非报告文学的意境创造》,李晓湘的《叶圣陶前期童话意境初探》,刘亚湖的《浅谈民歌的意境美》。在艺术意境方面,除了传统的书、画、音乐、戏曲意境的研究课题外,还涉及到舞蹈、影视、摄影、工艺和园林等领域。诸如,叶林的《舞蹈意境初探》,郭踪的《电影的意境美》,吴正纲的《摄影艺术的意境》,桑任新的《瓷雕的意境·风格·题材》,和金学智的《园林审美意境的整体生成》,等等。这是现代意境研究充分发展的表现。
e.术语新用。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意境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些术语,在近年来的意境批评和研究中重新使用,诸如境、境界、意境、物境、情境、境象、意象、情景、心境、幻境、奇境、象外、诗境、文境、画境等。王昌龄的“三境”说,在古代只有“意境”影响大,其它“二境”连古人都不大挂齿。近年来,人们对于王氏的“三境”说重新观照和研究。如范宁认为,“境界本有三种:物境,情境,意境。意境只是境界的一种而已。”[7]还有王洪的《意境:物境,情境》,陈良运的《论意境的另一种——情境》,也表现出了相类似的思想倾向。彭会资先生主编的《中国文论大辞典》(1990),对历史上的意境研究和术语资料,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整理。其中“构象说”收43个辞条,有6个术语:“情景说”收65个辞条,有10个术语;“境界说”收47个辞条,有24个术语。就是说,共有40个意境术语被现代学者作了重新阐释。
Ⅲ、现代意境研究的学科建构
学科建构,是现代意境研究的最终目标。30年代,老舍先生将意境范畴和司空图、严羽、王夫之等人的意境观点,引入《文学概论讲义》之中。40年代,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专列一章谈“诗的境界”问题。这些是最早将意境研究引向学科建构所作的努力。进入80年代以来,一方面意境研究以突飞猛进之势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一方面意境研究成果及时地建构在各类文艺学和美学著作中,最终形成了意境学科。总体来看,有以下几种情形:(1)意境被建构在当代文艺理论的体系中,如黄世瑜的《文学理论新编》和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程》等;(2)意境被建构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体系中,如陈良运的《中国诗学体系论》和祁志祥的《中国古代文学原理》等;(3)意境被建构在当代美学理论的体系中,如丁枫、张锡坤的《美学导论》和杨辛、甘霖的《美学原理》等;(4)意境被建构在中国古代美学理论的体系中,如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和郁源的《中国古典美学初编》等;(5)意境被建构在部门美学理论的体系中,如肖驰的《中国诗歌美学》、金学智的《中国园林美学》和胡经之的《文艺美学》等。在意境自身的学科建构中,刘九洲的《艺术意境概论》(1987)是第一部意境论专著。它的出现,是现代意境研究的重大收获。它不仅标志着意境学科的形成,也标志着现代意境研究已经进入了“学科建构”的最高阶段。林衡勋的《中国艺术意境论》(1993)和蒲震元的《中国艺术意境论》(1995)的相继出版,就证实了这一点。
以上便是我对现代意境研究的简要述评。现代意境研究的累累硕果,便是我们奉献给新世纪的一份厚重的礼物!完全可以预见,在21世纪,意境研究将会有更大的发展。WW王威轶
注释:
[1]王永生主编:《中国现代文论选》,第一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页。
[2]王永生主编:《中国现代文论选》,第一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0页。
[3]同上,第563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4]以下数据,是我根据蒋红等人编著的《中国现代美学论著译著提要》(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统计的。
[5]李泽厚:《意境浅谈》,《光明日报》1957年6月16日。
[6]赵士林:《当代中国美学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87页。
[7]《文学评论》,1982年第1期。
标签:美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意境论文; 读书论文; 王国维论文; 文艺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