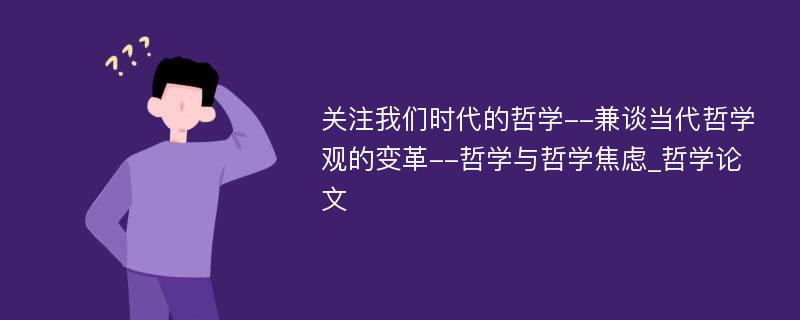
关注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当代哲学观变革笔谈——哲学与哲学观焦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笔谈论文,这个时代论文,焦虑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2)06-0005-22
1
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中是否有可以称为“哲学”(philosophy)的东西,这个问题尽管没 有真正解决,但似乎已经不再引起特别关注了。
中国当代学术思想在形式上是有“哲学”的,因为在学术科目分类中“哲学”已经习 俗性地成为一个独立的名目,有一行人,专事于此。
然而,在内容上,这个与法学、经济学、教育学等比肩而立的“哲学”,实际是什么 ,应该是什么,此类哲学观问题至少在过去50年中一直是中国“哲学”界讨论的热点之 一。从业者为所从之“业”究为何物而辩论,这是一种症状——焦虑:已经开始做事了 ,却时常讨论做的是什么事。大多数学术领域都不发生这类焦虑,似乎只有在中国的(in China)“哲学”才是这样。焦虑缘何而起?焦虑有何后果?本文尝试探讨这两个问题 。
2
焦虑缘何而起?讨论这一点,还须回到早期的那个问题:中国是否曾经有“哲学”?这 个问题曾因胡适、冯友兰分别做“中国哲学史”的撰述而引人瞩目,至今未得解决。这 里不关心如何才能解决它,却要留意何以竟有了这样的问题。
一个人的生活,如果诸事顺遂,在自觉意义上就几乎不出现人生观问题。如果人生出 现了重大的顿挫或转折,人生观问题就不可避免了:我从何处来?要到何处去?怎样走法 ?一种学术思想传统,如果源流不断,学者在其中也就不自问所为何事,而是径直在这 个特定的统绪中试比高下,以求名禄功业。相反,如果学术思想传统断裂,学者的活动 便要指向自身,以重新确定方向和路线。这个时候,旧有的学术范式往往就成了检讨的 对象,进而成为抛弃的对象。但这个过程既不短暂也不愉快。
近代中国的命运也即是传统中国学术的命运,其轨迹发生了重大的捩转。1840年以来 ,特别是1900年以来,随着枪炮战胜了刀矛,西学开始挤压和侵凌中国的传统学术和学 术传统。这种文明间的冲撞局势目前看来是西方占着上风。于是学术范式地弃旧图新也 就在所不免。然而,学术统绪是文明传统的自觉形式之一,要完全干脆地弃旧图新是不 大可能的,尤其是中国的学术思想有悠久深厚的历史,要推倒重来就更加不可能。尽管 鲁迅对中国历史痛下绝词,仅以“吃人”二字概括,这种愤激却也仍是典型中国式的忧 国忧民。较和缓的方式则是以强势文明的学统为指针来重新定位固有文明的学统,使这 种文明及其学统能够有吐故纳新的生长而不至于萎顿消亡。但长痛和短痛一样也是痛, 胡冯二氏的学术努力并不是没有争议的,金岳霖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评论即是典 型。金岳霖十分含蓄地写道:“以欧洲哲学的问题为普遍的哲学问题当然有些武断的地 方,但是这种趋势不容易中止。”[1](P2-3)这里面既有抗议,恐怕也有无奈。在本文 的语境中,金岳霖的评论可以理解为哲学观的焦虑:拿我们自己的学术传统怎么办?易 言之,拿西方的学术传统怎么办?质言之,如何才是哲学?
其实,该个案不过是一个缩影。日后中国假道苏联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并使之在新中 国成立后成为国家社会的哲学旗帜。但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业者,一直挣 扎在中国的实际、苏联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典和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这种 措辞有点怪,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西方的!)之间,游走不定。有时一切以苏联观点为准 ,有时又用马恩的观点批评苏联,有时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哲 学划清界限,有时又大讲起马克思的思想与那些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通与神似来,中 间还总是夹杂着中国社会现实情况的刺激。结果就是我们把很多的时间和优秀的智力投 入到不断地为哲学重新定位方面来,哲学工作几乎就是哲学观(改造)的工作了。若非我 们固有的文明发生了危机,何须理睬什么西方?遑论西方的“哲学”(philosophy)!可是 ,现在的中国人做不成汉唐的中国人,中国人也永不能做成西方人,我们现在只能携着 抛却不净的中国学术传统和新打进的西方“philosophy”一道前行。或许我们可以佯装 不在意中国学术传统的承继,但我们不得不使自己与西方的“philosophy”熟悉起来。 过去100年的“中国哲学”即是例证,如果把其中来自西方的哲学语汇涤除净尽,大概 就没有什么“中国哲学”(Chinese Philosophy或Philosophy in China)了。即使如此 ,百年来的“中国哲学”恐怕也还不是(西方)哲学能够认为同类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 ,哲学观的焦虑可能要长期与我们为伴,也许要到像我们消化了佛教那样消化了“philosophy”时为止。
3
焦虑比麻木要好些,因为在焦虑的过程中,人们若隐若显地发觉问题。但是,哲学观 的焦虑却有一种未必积极的后果,那就是,把哲学的定位工作等同于哲学工作本身,以 为哲学观的问题解决了,哲学问题也就解决了。哲学观焦虑造成的对哲学观的过度关注 和过分期待具有如下四方面的局限性:
第一,“哲学是什么”的问题据说是哲学中最困难的了,可用于难倒哲学家。的确, 它可能是重要的哲学问题,甚至是最重要的哲学问题,但不可能是哲学的所有问题。它 可能潜在地统摄着别的哲学问题,但不可能就是那些哲学问题。几何学的初始概念、推 理规则和公理,可能潜在地决定了一切定理,但它们并不就是那些定理。只有初始概念 、推理规则和公理的几何学称不上真正的几何学,或者说,这样的几何学随便谁都能弄 出半打来。哲学远不如几何学严谨,就更不能靠仅仅确定“哲学是什么”来成就自身了 。
第二,某种哲学观可以用来标注一定的哲学,某种哲学也可以简省地归结为一定的哲 学观,但哲学观不等于哲学,哲学观的研究也不等于哲学本身的研究。如果康德仅仅在 哲学观的意义上提出哲学是批判中的理性重建,黑格尔仅仅在哲学观的意义上提出哲学 是反思中的精神发展,那么,他们在哲学史上就算不上伟大的人物。他们之所以是哲学 史上的伟大人物,因为他们不仅这样对自己的工作做了自我理解,而且还确实创作了伟 大的哲学作品——其哲学观堪称作品的“后记”。后记无论如何高明,都无法等同于正 文,更无法代替正文。近50年的“中国哲学”,哲学观上的论点不可谓不多,但发荣滋 长成熟起来的哲学的确不多,原因就在于从业者多倾向于用很大的概念圈定某种对哲学 的根本看法,长于撰制缺乏正文的“后记”。有些更把“后记”当“前言”写,写完就 不管了,等待别人去进一步耕耘,而别人也有同样的爱好……
第三,在哲学观上发表见解,通常要用含摄面广的大概念。从学理上讲,大概念自然 是需要的。任何一种具有相当成熟性的哲学都不能缺乏最高级的核心概念,而且,通过 精细理解最高级的概念,常可以收到高屋建瓴地规定或把握一种哲学的效果。因此,关 注大概念这件事本身,并不是问题。切实的问题在于,光有大概念,也不就是哲学;只 经营大概念,更谈不上创新哲学。当我们集中精力于大概念的时候,可能会丢失哲学的 真问题。哲学从业者多少都熟悉哲学史,作为一种回顾的方式,哲学史上常会出现某某 论(如唯意志论)、某某学(如现象学)、某某主义(如经验主义),某某派(如智者派)等等 。这是为了历史阐释或总结的方便,它们究竟有多少真实的哲学内涵,往往是不很清楚 的,不过这种不清楚,正是其包容性的优势所在。这是叙述历史难以逃避的策略。但我 们似乎被这种策略迷惑了,我们每每过于挂虑所提观点可能具有的深远历史意义,在观 点的内涵还比较幼稚和贫乏的时候,就急于占用某个大概念,仿佛一旦占有了类似历史 总结中常用的大概念,就真地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就能真地占有历史地位。一旦关注“ 实践”,就很快上升为“实践论”。其实马克思并没有“实践论”,而只有《1844年经 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旦关注“人” ,就很快要上升为“人学”,甚至要把它作为一个学科来看待。其实真正的哲学家,其 实质性的创新努力多不采用这种虽省力却笼统的“哲学观”策略,而是深入到众多有关 问题中去。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并不叫“唯意志论”,而是体现为《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 界》。现象学并不叫“现象学”,而是体现为《逻辑研究》等。经验主义也不叫“经验 主义”,而是体现为《人类理解论》等。
第四,当哲学从业者忙于用大概念给自己戴高帽,也忙于给别人扣高帽时,帽子在己 ,往往掩饰了内容的贫乏,而帽子在人,也省去深入了解细致批评的苦功。结果是本来 可能颇有意义的哲学问题,在这种似高实空的讨论中反倒隐没不彰了。这是很可惋惜的 。中西方异质文明的相遇往往会催生崭新的文明形态,危机有时就是生机,在此过程的 初期,焦虑于哲学观是有根据的,但过分热衷于哲学观的工作却有误哲学本身的工作。 1765年,康德写道:“学问的危机使我产生了最好的希望:长期以来人们所希冀的科学 大革命已经为期不远了。”[2](P18)但是,我们得清楚,此后康德写了三大《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