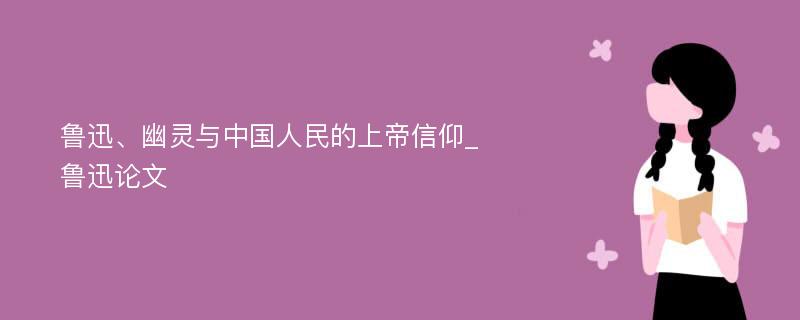
鲁迅与中国人的鬼神信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鬼神论文,中国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一个民族的文明史,不能不研究这一民族宗教观之发端——鬼神观。鲁迅在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探讨中,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批判中,对中国人的鬼神观作了深刻的论述,是他终身所致力于改造国民性的一个重要部分。
1
始于近代的中国神话学、民俗学研究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而是与当时启迪民智、改造国民性的文化运动、政治运动紧密相连,是受西方神话学的影响,伴随着晚清思想革命而生发的。此时神话学、民俗学研究的一个特点是以科学破迷信,是对中国人的鬼神观的批判,对国民性的批判。发表于1903年的蒋观云《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一文,作为中国神话研究的开山之作,首先提出的就是神话对于国民精神的影响:“一国之神话与一国之历史,皆于人心上有莫大之影响。”“神话、历史者,能造成一国之人才。然神话、历史之所由成,即其一国人天才所发显之处。其神话、历史不足以增长人之兴味,鼓动人之志气,则其国人天才之短可知也。”“故欲改进其一国之人心者,必先改进其能教导一国人心之书始。”在此已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问题。近现代思想家、文学家梁启超、鲁迅、周作人、胡适、茅盾、郑振铎等对此都作出了贡献。鲁迅不同于其他文人的地方在于他不仅是借鬼神探索一个民族的灵魂,同时是借鬼神解剖民族的灵魂,借鬼神以批判现实社会的黑暗。
鲁迅是唯物论者,他不信神亦不信鬼,认为鬼神是“境由心造”,人之所为。鲁迅生活于中国近现代文化转型时期,在吴越文化的氛围中,在民俗民风的熏陶下,具有“报仇雪耻”之乡的会稽遗风,形成了鲁迅性格中坚毅的一面;鬼神故事的耳濡目染,又使鲁迅对民间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与爱好。鬼神故事中的优美动人为他所深深喜爱,他不只一次描述的无常、女吊,及《五猖会》中的迎神庙会,《我的第一个师傅》中的出家人生活,都是无以忘怀的童年生活所留下的美好记忆。而《故事新编》中的女娲、禹、羿、眉间尺等不仅代表着鲁迅的审美趋向,也有着深刻的寓意。同时鬼神信仰中的糟粕又是鲁迅所深恶痛绝的,《祝福》中对灵魂有无的发问,《阿Q正传》中对国民性的揭露,《二十四孝图》中对“孝”的质疑,及杂文中随处可见的“鬼”的影相,都代表着鲁迅对中国人鬼神观的批判。
鬼神信仰不仅反映出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同时也是形成一个民族国民性的重要原因。万物有灵、灵魂不灭,是任何一个原始氏族过渡到具有自我意识的“人”的必经的发展阶段。原始时代的人无法解释自然现象,自身现象,对自然界中无以驾驭的东西都认为是神灵的意志,对自身的死亡认为是灵魂的游离与附着。随着人类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科学取代了迷信,原始信仰在西方演化为“神人合一”的宗教,主张的是皈依上帝,尊崇灵魂,鄙视肉体,重彼岸轻此岸的一神论信仰。中国历史几千年的封闭性形成了中国人生活领域和生产方式的同一性,中华文化的“和合”思想一直处于正统地位,在与其他宗教思想的融合中,形成了中国人务实重生的鬼神观念,其鬼神信仰的特点表现为“祖先崇拜”和“泛神论”。
儒家崇尚“天”,主张“天人合一”,所谓“天人合一”即为人与自然的和谐,个体与群体的和谐。中国人以“家”为本位,生活状态上的封闭、保守,传承方式上的重伦理、重血缘形成了鬼神信仰上的祖先崇拜。鲁迅说:“在中国,君临的是‘礼’,不是‘神’”(注:《且介亭杂文二集·陀思妥夫斯基的事》。)。“礼”实际上就是祖先崇拜,“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注:《论语·为政》。)。祖先崇拜强调个人的服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群体与个人的关系中,重宗族而轻个人,个人的一切只有纳入宗族的延续中才有价值。人的生存只是为了光宗耀祖,为了子孙的繁衍,历史上最具畸形的“典妻”习俗,正是为了子嗣,为了子孙的繁衍、延续,可以不受制于封建的三纲五常,伦理道德,此时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生存观上则更重视今生,轻来生,务实求生,“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都是中国人的生之原则。生的渴望是那样的强烈,而死又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幻想着能长生不死,幻想着来世的报应能现世现报。孔子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道教的“求道成仙,长生不老”,都成为中国人生之追求,即信命于天,又渴求着长寿。既然死是不可避免的,就生出种种死后的幻想,在设想着另一个世界的同时,设想着种种长寿的办法,于是鬼神世界有着如此之大的吸引力。
关于死亡的观念反映出一个民族的鬼神信仰,原始民族都相信人死为鬼,其魂不灭,鬼的观念正是由人对死亡的看法而产生的。所不同的是西方宗教认为人死后肉体毁灭,灵魂升入天堂。中国人则认为人死后灵魂回到祖先那里,仍与活人保持着联系,即使死后也在祭祀中与活人连在一起,因此对于死要给予隆重的厚葬,人死后依然要为他造个房子,甚至连鸡鸭鹅狗也要一块带上天。事死如事生,且看丧事中的种种规矩,之隆重,之繁琐,之持久,正是将此作为一种生之延续。“祭祀祖先”,即是相信人死后其魂存在于另一世界中而继续影响于后代,这一世界就是具有血缘关系的宗族体系,同时又恐怕死后成为孤魂野鬼,有了后人的祭祀,灵魂也便得到了安息,有了最后的归宿。“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注:《南腔北调集·家庭为中国之基本》。),“家”如“枷”,困着活人与死人。在批判中国人事死如事生的鬼神观念时,鲁迅指出中国人对于死的态度是随随便便,其原因在于相信人死后可以成鬼,“虽然已不是人,却还不失为鬼,总还不算是一无所有”(注:《且介亭杂文末编·死》。)。在鲁迅的作品中饶有兴味地描写的鬼只有“无常”和“女吊”,“无常”与“女吊”都是民间传说中死后“讨替代”的“勾魂鬼”,“讨替代”是阴间之鬼转世为生的一种手段。鲁迅虽然很喜欢那“鬼而人,理而情”的“无常”鬼,但认为他对于死表现的却是无可奈何,随随便便,这也正是中国人对于死的态度,在这一点上鲁迅更喜欢那带有强烈复仇性的“女吊”鬼,她的“讨替代”,转世为生是为了复仇,唯有“生”才能复仇,而死后的“宽恕”等等都不过是昏话。中国人不能正视死,因而也不能正视生,只能将生与死寄托于鬼神。既然可以长生不死,自然是玩世不恭,随随便便,对于死的随便表现出对于生的随便,昏乱的祖先对于后代,生时便不将他当人,长大后也不会做人,于是一代一代的昏乱下去,由此形成了国民性的自满自足,不求进取,随随便便的苟活。鲁迅执着于生,不畏惧死,以进化的生命观对待人生,批判中国人生死观中的鬼神观念,他说:“我不信人死而魂存,亦无求于后嗣”(注:《书信·310306致李秉中》。),但他也说“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正死掉了”,他将自己的著作喻作“坟”,但却活在了后人的心中。
中国人的鬼神信仰不同于西方民族的鬼神信仰,既没有一个固定尊崇的神祗,却又处处设庙宇拜鬼神,形成了以儒释道“三教合一”为基本特征的“多神信仰”。儒家的鬼神观念是与其“祖先崇拜”相联系的,对鬼神采取的是敬而远之的态度,道教的根源在巫,“巫底思想,即所谓‘万有神教’”(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同时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吸收了儒教、佛教中的鬼神,本身就是多神的组合。佛教是外来宗教,在与道教经历了多次的斗争之后,终于改头换面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待到居士也算佛子的时候,往往戒律荡然,不知道是佛教的弘通,还是佛教的败坏?”(注:《三闲集·在钟楼上》。)因此各种各样的鬼神都同时容纳于中国人的鬼神信仰中,鲁迅将此概括为“无特操”。所谓“无特操”即“没有‘坚信’,狐狐疑疑”“崇孔的名儒,一面拜佛,信甲的战士,明天信丁”(注:《且介亭杂文·运命》。)“既尊孔子,又拜活佛者,”“其实是那一面都不相信的”(注:《且介亭杂文·难行和不信》。)。鲁迅在《吃教》一文中更为形象地揭露了上层名流的这种“三教同源”的“无特操”:“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人总有三种小玩意,一是《论语》和《孝经》,二是老子,三是《维摩诘经》,不但采做谈资,并且常常做一点注解。”这种“三教合一”的“无特操”的鬼神观实际上正是一种自欺欺人。
“无特操”的自欺欺人形成了中国人对鬼神的态度——捧与压,瞒和骗,对凶神采取捧的态度,如火神、瘟神,“凡有被捧者,十之九不是好东西。”捧的目的是为了免灾,对善神则采取压的手法,如对灶神、三尸神。此外还有瞒和骗,如鲁迅在《谈皇帝》中所提到民间对皇帝的瞒,瞒不下去了就用骗,如关羽、岳飞的被杀则被认为,“一是死后使他成神”,“一是前世已造夙因”,“冥冥中自有安排”。(注:《坟·论睁了眼看》。)对待鬼神的捧与压,瞒和骗也正表现出国民性的劣根性,“无特操”使中国人对于鬼神采取为我所用、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于是急来抱佛脚,见佛就磕头,遇庙就烧香,没有了坚信,也就只有盲从。鲁迅赞赏广东人敬鬼时的坚信,虽是迷信,却迷信的认真,这种认真较之“无特操”的迷信更为值得佩服,鲁迅说:“倘若相信鬼还要用钱,我赞成北宋人似的索性将铜钱埋到地里去,现在那么的烧几个纸锭,却已经不但是骗别人,骗自己,而且简直是骗鬼了”(注:《花边文学·〈如此广州〉读后感》。)儒家的务实求生,道教的现世现报使得中国人重现世轻来世,重此岸轻彼岸,既形成了中国人急功近利的鬼神观,也形成了中国人国民性的因循守旧,不思进取,恪守祖训,自大保守,知足常乐,以温饱为生活的最高愿望,满足于“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无特操”的“多神信仰”形成了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鲁迅在揭露“说佛法的和尚,卖仙药的道士,将来都与白骨是‘一丘之貉’”(注:《华盖集·导师》。)的同时发出了:“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玟》《五典》,百宋千年,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注:《华盖集·忽然想到(六)》。)的呐喊。
2
鲁迅在一九一八年八月致许寿裳的一封信中谈到《狂人日记》的创作时曾说:“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鲁迅在这封信中所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是因为当时学界对于改造国民性的研究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中国人的鬼神观对中国人的国民性有着极大的影响,道教的鬼神观又具有突出的代表性。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起源于民间,盛行于民间,在揉合了儒教、佛教的鬼神信仰的同时形成了自己的鬼神世界。它吸收了儒教中重生轻死的生存观,并将其世俗化,如果说儒教的“祖先崇拜”追求的是生与死的连续性,宗族生命的永恒的话,那么道教追求的则是如何长生不死、现世享乐;同时道教又将佛教中的鬼神作为一种现世报应,宣扬不必下地狱,现世的修炼即可成佛,在儒释道中,道教最能迎合中国民众的心理,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因而鲁迅说根柢在道教。同时鲁迅也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学说对中国人的鬼神观及其国民性有着更深层的影响,指出儒教的本质在于“吃人”,在于根深蒂固的传统对国民的制约,而对此的认识在当时尚寥寥。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抨击的是儒家的封建礼教:“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浓缩为“吃人”,这“吃人”的本质是祖先崇拜的伦理道德,是束缚人类心灵的鬼神信仰。鲁迅在批判道教的同时也批判儒教,认为二者对国民性的形成,对国民精神的束缚是相同的。在一九二七年的《小杂感》中鲁迅又说:“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这里所说的不仅是道教,同时也是儒教,二者一是世俗的,一是精神的,其根柢都在巫。
作为原始宗教的发端,各民族文明史中都有作为神人之间联系的“巫”,各类巫术、占星术、方术等等都有其相似的地方,基本上是用于占卜预测,巫是用以沟通神人的关系,是神与人交流的中介。中国巫术的起源也是如此,在《说文》中对巫的解释是:“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人通过巫达到与鬼神的沟通,从而达到成神的目的,于是巫在中国人的鬼神信仰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巫在此后的发展中吸收了民间的鬼神,形成道教的核心,巫风的盛行在于流传于民间的道士和方士思想,道士与方士一个说鬼,一个谈炼金、求仙,道教的鬼神观及画符、求签、扶乩、斋醮等求神的手法极易为下层人民所接受,因而在民间有着广泛的影响。儒家同样也利用巫宣传其鬼神思想,他们所宣扬的礼教、孝道、节烈、三纲五常都是以鬼神为载体;哭竹、卧冰、尝秽、割骨等孝道的感天动地,为历代做人的榜样;寡妇被认为是鬼妻,亡魂跟着,无人敢要,从而成为“节烈”最早的发端,《祝福》中祥林嫂的捐门槛也是她未能“不事二主”的报应;鲁迅所论的“国粹”种种:吃人,劫掠,残杀,人身买卖,生殖器崇拜,灵学,一夫多妻及缠足,拖大辨、吸鸦片无不带有鬼神色彩。当道教的享乐主义与儒家的封建伦理道德相结合时,形成了中国人的鬼神观。鲁迅在一九二五年的一封关于神话的通信中谈到:“自上古至周末之书,其根柢在巫,多含古神话”,“秦汉之书,其根柢亦在巫,但稍变为‘鬼道’,又杂有方士之说”,并认为“中国人至今未脱原始思想,的确尚有新神话发生”(注:《书信·250315致梁绳祎》。)。鲁迅深感中国落后于世界其他进步民族,深感处于二十世纪的中国“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注:《华盖集·忽然想到(四)》。),有着中国人将要被从“世界人”中挤出去的大的忧患,鲁迅此处所说根柢在巫,是指中国人至今未脱离原始思想的鬼神信仰,同样是既包括道教,也包括儒教,是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对中国人鬼神观的批判。
中国人的鬼神信仰形成的国民性之种种正是“古已有之”的祖先崇拜及多神论的“无特操”的延衍。鲁迅在探讨中国国民性的病根时,已经注意到了“心造之境”的鬼神信仰对中国国民性的影响及其阻碍,同时,鲁迅也注意到了传统对于新思潮的抵抗与溶解,他一再提到西方的科学思想一经传入中国往往掺入了鬼神的色彩,“风水,是合于地理学的,门阀,是合于优生学的,炼丹,是合于化学的,放风筝,是合于卫生学的。‘灵乩’是合于‘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注:《花边文学·偶感》。)天文镜本是观天文的,却被嘲讽为不能观天堂地狱,将科学的理论当做神话,以鬼神为道德之根本,于是“连科学也带了妖气”。而火药用来做爆竹,指南针用来看坟山,麻将桌边电灯代替腊烛,无线电中所播的是《玉堂春》《毛毛雨》则更不为奇。鲁迅以科学批判封建迷信,批判中国人的鬼神观,指出要救中国只有一味药,那就是科学,这科学不是带有“妖气”的科学,更不是进入“染缸”的科学,“假如真有这一日,则和尚,道士,巫师,星相家,风水先生……的宝座,就都让给了科学家,我们也不必整年的见神见鬼了。”(注:《且介亭杂文·运命》。)鲁迅早期介绍科学知识,引进西文先进人文思想,以现代科学批判中国人的鬼神观念,这些集中地反映在他的前期杂文中。
鲁迅后期在对国民性、对中国人鬼神观的批判中更为注意“治”与“被治”的关系,“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注:《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统治者的“无特操”——读经,尊孔,拜佛,求仙都是为了维持其统治,并利用鬼神信仰实施其统治,在《新秋杂识(二)》中鲁迅指出统治者对于民间的赶天狗,放焰口,施饿鬼的迷信活动给以自由和权力的目的在于使天下太平,“这是太平的根基”。民间的供奉火神菩萨是为了免去火灾,但并不能避免统治者的杀人放火,“火神菩萨据说原是保佑小民的,至于火灾,却要怪小民自不小心,或是为非作歹,纵火抢掠”(注:《南腔北调集·火》。)。鲁迅视“人间苦”为地狱苦,在人世看到“地狱”,于人身看出“鬼影”,将现实的黑暗喻为“地狱”,并将这“地狱”揭示于国民,他反对将“黄金世界”预约给生活于黑暗中的人民,由此发出了最为深刻的“反狱的绝叫”。
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宗教也同样如此。鲁迅一方面借鬼神反封建,另一方面借鬼神以论时事,揭露中国政治的腐败,指出社会的黑暗对中国人鬼神观的影响:“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注:《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鲁迅一再提到中国就是一个大地狱,“有故鬼,新鬼,游魂,牛首阿旁,畜生,化生,大叫唤,无叫唤,”在这鬼域世界中“像‘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注:《华盖集·“碰壁”之后》。)。在地狱般的生活中,在无望的黑暗里,人民只能将希望寄托于鬼神,寄托于来世的转换,于是鬼神世界向人们展现出无穷的魅力。鬼神的魔力在于它将虚幻的、不可知的事物变为一种精神上可以得到安慰的心灵的寄托,使生活于现实中人的人对未来寄以美好的希望,增强生活的勇气;同时对鬼神的敬畏所产生的种种仪式,不仅表达着人与鬼神的联络,也是人的一种自娱方式,是艰苦环境中人的精神的解脱。在早期的《破恶声论》中鲁迅对此已有论述:“农人耕稼,岁几无休时,递得余闲,则有报赛,举酒自劳,洁牲酬神,精神体质,两愉悦也。”“倘其朴素之民,厥心纯白,则劳作终岁,必求一扬其精神。”在《无常》中鲁迅也指出“敝同乡‘下等人’”由于生活的艰辛,“于是乎势不得不发生对于阴间的神往。”在后期杂文中鲁迅又指出:“在实际上,悲愤者和劳作者,是时时需要休息和高兴的。古埃及的奴隶们,有时也会冷然一笑。”(注:《花边文学·过年》。)鬼神所代表的既是人的希望也是人的无奈,现世生活的黑暗使人们将希望寄托于来世,寄托于幻想中的鬼神世界,希求现世的痛苦能在来世中得到解脱,现世的冤仇能在来世中得到伸报。这不仅是人对自然的无能,也是人对社会的无能。但历史上总还有“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鲁迅称之为“中国的脊梁”,如六朝焚身的和尚,唐朝砍下臂膊布施无赖的和尚,啮雪苦节的苏武,舍身求法的玄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孔明等等,正因为有了这些“‘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即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定要有这样的人,世界才不寂寞。”(注:《而已集·反“漫谈”》。)
3
鲁迅对中国人鬼神观的探讨不仅具有社会文化学的意义,同时又有着神话学、文艺学的意义。我国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在《作为民间文艺学者的鲁迅》一文中总结了鲁迅对中国神话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的贡献,认为鲁迅在中国神话学研究上所作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神话的由来、性质及其与宗教的关系,二、传说与神话的关系,三、诗歌的起源。鲁迅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大多借鉴于西方及日本学者的理论,为我国学术界输入了新鲜血液。
鲁迅在1908年发表的《破恶声论》中对将神话作为迷信来批判的观点提出了异议,认为“夫神话之作,本于古民,睹天物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想出古异,淑诡可观,虽信之失当,而嘲之则大惑也。”同时也指出了神话所具有的娱乐性,神话的艺术魅力对一个民族的精神的影响“盖不知神话,即莫解其艺文,暗艺文者,于内部文明何获焉”,代表了当时神话研究的较高水平。《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汉文学史纲要》是鲁迅对中国文学史的系统的研究,也是鲁迅仅有的几部学术论著,在此鲁迅对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作了极为认真的考证与研究,在总结了日本学者盐谷温对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之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神话的特点在于“神鬼之不别。天神地祗人鬼,古者虽若有辨,而人鬼亦得为神祇。”鲁迅很重视鬼神在中国小说中的演化,认为“六朝人并非有意作小说,因为他们看鬼事和人事,是一样的,统当做事实”。而唐以后的小说虽然仍讲鬼怪,“也不过点缀点缀而已”。鲁迅在此指出了六朝小说与唐小说的不同,同时也涉及到中国人鬼神观的变化,由不自觉到自觉,由信到不信,这种观念上的变化也反映着国民性的变化。在对宋元明清神魔小说的研究中,鲁迅更为注意的是创作者对鬼神的态度,在对《西游记》的评价中鲁迅说:“承恩本善于滑稽,他讲妖怪的喜,怒,哀,乐,都近于人情,所以人都喜欢看!这是他的本领。”“因为《西游记》上所讲的都是妖怪,我们看了,但觉好玩,所谓忘怀得失,独存鉴赏了——这也是他的本领。至于说到这书的宗旨,则有人说是劝学;有人说是谈禅;有人说是讲道;议论很纷纷。但据我看来,实不过出于作者之游戏,只因为他受了三教同源的影响,所以释迦,老君,观音,真性,元神之类,无所不有,使无论什么教徒,皆可随宜附会而已。”对于《聊斋》鲁迅评价其特点是:“描写详细而委曲,用笔变幻而熟达”,“说妖鬼多具人情,通世故”。《西游记》中的三教合一,鬼神人混淆;《聊斋》中的鬼神多带人情味,具有趣味性,都是鲁迅所喜爱并称道的。鲁迅尤为赞赏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鬼,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鲁迅赞扬他“生在乾隆间法纪最严的时代,竟敢借文章以攻击社会上不通的礼法,荒谬的习俗”。鲁迅对神话的研究不仅是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同时也是对中国人的国民性及鬼神观的研究。
鲁迅在梳理中国小说史的过程中,对神话的演变、鬼神的故事做了详尽的考证,从最早的神鬼人相交融到以后的谈鬼神以论苍生,不仅体现出学者的严谨与稹密,同时笔端常带感情,在对吴承恩、蒲松龄、纪昀的评价中体现着鲁迅个人的创作倾向,鲁迅不仅赞扬他们,同时在他的创作中也继承了他们的传统,将这种艺术表现手法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他的杂文几乎篇篇谈鬼神,处处见鬼影。他将对国民性的批判、对绝望的抗争都集中于对“鬼神”的描述中,他的作品不仅是现代史,也是中国人的灵魂史。鲁迅以鬼神论政治,以鬼神反封建,“谈鬼物正像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在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中,展示了活的人间相,或者也可以说是将活的人间相,都看作了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注:《集外集拾遗·〈何典〉题记》。)。他以谈风月、谈鬼神来论时事,虽然他也说“鬼神之事,难言之矣,只得姑且置之弗论”(注:《且介亭杂文末编·女吊》。)。但他在杂文中总是随手拈来中国人所熟悉的鬼神或给以批判,或给以讥讽。“论时事不留面子,贬锢弊常取类型”,鲁迅深黯儒释道,他所取的“类型”也都是儒释道中的鬼神。同时鲁迅对某些鬼神又持有偏爱,他赞扬“以乳为目,以脐为口”“猛志固常在”的刑天;喜爱“活泼而诙谐”“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的无常;更有那具有复仇意味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女吊。对于创世的女娲,射日的羿,治水的禹,复仇的眉间尺等等这些非人间的、中国人所崇拜的神灵给予极高的评价。他的《朝花夕拾》充满着对鬼神的喜爱,《故事新编》中人神混淆,将古代神话人物现代化,以古人古事讽喻今人今世,更有《祝福》《阿Q正传》《白光》中对中国人心目中的鬼神的批判。鲁迅继承了中国古代神话小说的艺术精髓,将其运用于自己的创作中,形成了他独特的艺术特色及以鬼神论时事,以鬼事论人世的审美趋向。
由于鲁迅不是从神话学的角度做纯学术的研究,因而在他的神话论述中除了“述学”之作而外,基本上是即兴的,尤其是对一些神话传说、鬼神故事几乎是随手拈来,并不去做科学上的考证与定义,因此在一些问题上也曾引起过争论,如“新神话”说等。钟敬文先生对此有过评说,他认为鲁迅的小说史研究是“述学”性质的,而在创作中对神话题材的采用则是“即席”的有感而发(注:《作为民间文艺学者的鲁迅》。)。从神话学的角度来看,近现代学者在西方神话学的影响下,以科学的神话人类学分析中国神话,建立起中国神话学的体系,这一神话学的体系与文学的神话研究是两个不同的领域,鲁迅与顾颉刚便是这两个不同领域中的代表。鲁迅与顾颉刚在现代文学史上虽曾有过一度论争,但作为思想家、文学家的鲁迅与作为历史学家的顾颉刚在神话学研究上都有着突出的贡献,作为学者他们同样有着严谨的学风,同样的博大精深,为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学术著作。由于各自的出发点不同,存在着不同的论点也是毫不为奇的,这也丝毫不影响他们各自的学术成就。鲁迅的神话研究是以“立人”为宗旨,以积极入世的精神探讨神话对于国民精神的影响,鲁迅在谈到自己的创作目的时说过,他的小说创作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的,在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更注重的是现实的政治、文化斗争,因而他不可能将“述学”作为终极目的,钻入书斋中皓首穷经,对此鲁迅自己也曾说过:“但我对于此后的方针,实在很有些徘徊不决,那就是:做文章呢,还是教书?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兼做两样的,倘不认真,便两面都油滑浅薄,倘都认真,则一时使热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精神便不胜疲惫”,“我自己想,我如写点东西,也许于中国不无小好处,还写也可惜;但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大概也可以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但我想,或者还不如做些有益的文章,至于研究,则于余暇时做”(注:《两地书·六六》。),这里道出了鲁迅“述学”与创作的矛盾心态,然而鲁迅最终还是选择了创作,这也是由他改造“国民性”的初衷所决定的。因此鲁迅在对神话的研究中,更注重于神话故事中鬼神与人的感情的纠葛、联系,注重神话的文学性、思想性,而不去关注其来源,更不去考证其出处,这也正是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在神话研究上不同于历史学家、民族学家的地方。尽管鲁迅对于神话的研究不是纯学术研究,但他是中国神话学史的开创者、奠基者之一,是早期以人类学观点从文学角度研究神话的代表人物。
大抵中国现代文人都喜欢鬼神,都有着谈鬼说神的情趣,鲁迅如此,顾颉刚也如此。鲁迅在《社戏》中所描述的童年时看目连戏的喜悦心情可说是神话故事对一代文人的熏染与陶醉,使他们一生难以忘怀。顾颉刚也提到他童年时曾有过的这种心境:“我坐在门槛上听他们讲‘山海经’的趣味,到现在还是一种很可眷恋的温馨”(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然而作为历史学家的顾颉刚,有感于中国史书的良莠并生,伪真并存,力求还历史以原来的面貌,他从古代神话传说入手,考证上古历史,辨伪存真,他以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尧、舜、禹等来推断上古时期的真实概貌,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创立了中国神话研究史上著名的“古史辨”学派。在神话研究中他强调的是“史”与“神话”的关系,他认为“神话乃是小说不经之言,须知现在没有神话意味的古史却是从神话的古史中筛滤出来的”(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在对神话传说的研究上顾颉刚更注重故事的起源,并从史书中考证这一神话传说的历史演变过程。如对孟姜女故事的研究,则从《左传》中“杞梁之妻”哭夫考起,考证了几个朝代不同又相同的故事内容,最后成为现在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的史实(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顾颉刚是以“史”作文,而非以“故事”作文,他注重的是“史传”而不是“传说”,对于文学作品的叙述他曾说过:“用了史实的眼光去看,实是无一处不谬;但若用了故事的眼光看时,便无一处不合了”(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基于这种历史学家的特色,顾颉刚在神话研究上所注重的是考证典籍,在他的史学研究中对虚构、夸张、杜撰给予否定;在对神话积极意义的认识上,他所注重的是神话传说中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形态、人文环境及其历史背景。同时顾颉刚也注意到社会意识、政治道德对神话形成的影响,在《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一文中,他所要解决的疑问是“孔子何以成为圣人?”这一问题的提出实际上涉及到了神话的本质问题,即英雄人物是怎样在历史的演变中成为神的,这是任何民族的神话、史诗都涉及到的问题。顾颉刚以“史”的演进考证了孔子由君子神化为圣人的原因,认为孔子的成为圣人是时代的使然。鲁迅说孔子的成为圣人是被统治者捧起来的,顾颉刚的考证其实也证明着孔子由君子而圣人,又由圣人而君子的几起几落是被统治者所利用的过程,二者有相同处,也有相异处。相同处在于他们都认为孔子的成为圣人与统治者的利用有关,不同处在于鲁迅更强
调社会政治斗争,从社会文化学的角度评论孔子,顾颉刚则更偏重于“史”的论证,“史”的演变过程。
史学家执着于历史的真实,真,就要去掉任何伪的装饰涂抹,以显示一个民族的精神内在性,这是史学家的责任。然而在这一去“伪”的过程中,又失去了多少文学的趣味,缺少了多少人间情怀。历史过于严肃,过于古板,但它记录的是民族的真与诚。而文学却带有随意性,鲜活性,它不必去求历史的真,去做古板的考证,它将历史浓缩于人生中,道尽人间喜怒哀乐,给人生以无穷的乐趣,这正是文学的价值与意义。从这一角度来看历史与文学,来看鲁迅与顾颉刚是否会有着另一种意义呢。
标签:鲁迅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中国人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祝福论文; 祖先崇拜论文; 神话论文; 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