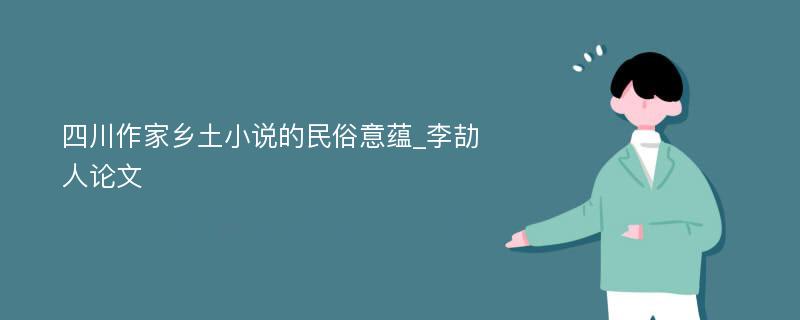
“四川作家群”乡土小说的民俗学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俗学论文,意蕴论文,乡土论文,作家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3)04-0111-07
在20世纪30年代乡土文学中,沙汀、艾芜、李劼人等作家十分注重从四川的乡
风民俗中提炼小说题材和艺术构思,以独特的风格确立了各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 位。就文学研究中的民俗学问题,日本学者井之口章次曾归纳和概括出不同的民俗学取 向,“第一个方向,为了正确理解文学的作品,有必要了解它背后的环境和社会,为此 要借助于民俗学。第二个方向,要了解文学素材向文学作品升华的过程,因为在现实上 ,文学素材往往就是民间传承。第三个方向,再进一步,把文学作品作为民俗资料,也 可称之为文献民俗学的方向。”[1](p.125)三位乡土小说作家的民俗描写同样也呈现出 独特的审美特征。
一
用日本学者的“第一个方向”概括沙汀乡土作品的民俗学意蕴应该说是可取的。1935 年作家奔丧返川收集了不少农村生活素材,触动了他乡土创作的灵感,开始“把笔锋转 到我所熟悉的四川农村社会去了”[2](后记)。沙汀的民俗描写颇为精彩,借助特殊地 域的乡风民俗揭露国民党政府基层的黑幕。《丁跛公》是沙汀第一篇揭露基层官绅腐败 的小说。此后《代理县长》、《在其香居茶馆里》、《龚老法团》、《人物小记》和长 篇《淘金记》、《还乡记》等等都是沿着这一主题和题材开掘的,形成了作家鲜明的艺 术个性。因此,要真正理解沙汀的这些作品,小说中的民俗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
首先,沙汀小说的民俗描写构筑了人物活动和情节发展的人文社会环境,透露出特定 历史时期的风尚,如代表作《在其香居茶馆里》。历史上,四川盆地是最早发现和食用 茶叶的地区。清代顾炎武《日知录》云:“自秦人取蜀以后,始有茗饮之事。”饮茶成 为当地人生活中普遍的习俗。几乎每个乡场都有或大或小的茶馆。“茶馆是三教九流会 面之处,可以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3]像张天翼《清明时节 》把故事放在随缘居茶馆一样,沙汀则通过“在其香居茶馆里”一场“讲茶”,把乡镇 基层“兵役”黑幕暴露得淋漓尽致。按民间“讲茶”习俗,“俗遇不平事,则往茶肆争 论曲直,以凭旁人听断,理曲者则令出茶钱以为罚”(光绪《罗店镇志·风俗》)。四川 有句俗话:“一张桌子四只脚,说得脱来走得脱。”“吃讲茶”含有讲开算数、用茶敬 客的意思。这种颇具人情味的讲茶习俗有利于缓解双方的矛盾和纠纷。小说再现了一场 “讲茶”的全过程,一方面使乡村基层政权的把持者方治国与邢么吵吵间矛盾的来龙去 脉得以交代和展开;另一方面在“无讼”的乡村,“讲茶”也揭示出乡村官绅沆瀣一气 的现实。所以不论是讲茶过程中相互攻击还是讲茶后的彼此勾结,其实质都是鱼肉乡民 的鬼把戏。一场“讲茶”把他们假抗战之名行一己私利之实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
其次,沙汀注重运用民俗事象简洁自然地刻画小说人物形象和性格,有助于反映当时 社会的原生态,如口口声声“小,补之哉”的“龚老法团”和《人物小记》中小高利贷 者“幺鸡”等。特别是刻画“幺鸡”形象,作家选择了日常生活中鉴别钱币这一司空见 惯的细节,而这种甄别真伪的方式体现出人物的精明。沙汀这样写到:
当他收到一块洋钱的时候,他总先用大指头去审查一下花边的匀称,然后拿两个指尖 钳住适中的地方,放近挺直的松须边吹一口,再送往耳朵上去。有时候碰见声誉恶劣的 人,他尽可以再拿到口里去麻烦一下他的牙齿和舌头。至于铜元,不管在这奇怪的省份 里是如何的复杂和作弊,那哑假破滥的识别,他只要在台子上摔几下,在手里过一过,
就明明白白的了。
当然,运用民俗刻画人物性格和表现人物心理最为成功的当然要算沙汀的《淘金记》 。1941年,沙汀在给以群的信中讲述了抗战时期四川绅士们不是为国家效劳,而是挖空 心思淘金牟利,大发国难财的事实。为此创作了这部长篇小说。在川西北的小镇上,哥 老会的舵把子林么长子,乡绅白酱丹为争夺何寡母祖坟地筲箕背上的黄金开采权,上演 了一出勾心斗角的闹剧。从表面上看,矛盾焦点似乎集中在黄金开采权的争夺上。但从 民俗学角度看,民间普遍存在的心意民俗其实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作为术数的一种, 民间把看风水称为堪舆,风水先生叫做“堪舆家”。这一古老职业是专门察看宅基、墓 地的方位、地势、朝向以及与周围环境的配合,以此预测凶吉祸福。何寡母一向认为其 祖坟地就处在“龙脉”上,现在筲箕背的黄金便是证明。正是这块风水宝地,既让女主 人公寝食不安,又给绝望的她以莫大安慰。除了风水之外,民间还特别看重“孝亲敬祖 ”的传统观念。民间认为祖坟是祖先居住的地方,即便“兄弟析饮,亦不远徙,祖宗庐 墓,永以为依”(同治《苏州府志》第3卷)。墓地的选择更说明敬祖对后世的意义。再 说,挖掘祖坟是对祖先大逆不道的行为,更何况容忍别人开挖自家祖坟。因此,不管林 么长子和白酱丹如何软硬兼施,不论儿子“人种”多么令她失望,何寡母始终坚信,只 要守住祖坟这块风水宝地,就意味着她的家族总有时来运转的一天。正是作家对心意民 俗的挖掘和恰当运用,使得何寡母成为心理最为丰富,最具深度的人物形象。
“抗战,在其本质上无疑的是一个民族自身的改造运动”[4](p.63)。沙汀把对民族自 身劣根性的批判深入到人们的习惯思维和日常行为层面,如对乡土世界所遗存的原人心 理进行大胆的揭示。在原始部落征战中,女性往往被视为财富加以掳掠。这种对女性人 格完全漠视的原人心理,在现代男性社会结构中依然存在。女性(特别是有几分姿色的 女性)成了男性地位和身份的象征而受到恶霸官绅的追逐和占有,这种现象四川内地尤 为突出(如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有感于四川农村普遍存在的“霸妻”现象 ,作家创作了《还乡记》。作家借助民俗描写表达对抗战与启蒙关系的思考,同时,作 家还将陋俗与乡土世界兵燹匪祸、苛捐杂税的现状相联系,揭示它们赖以盛行的社会根 源。正如“左联”作家徐懋庸在《神奇的四川》一文中不无讥讽道:“久闻四川是个神 奇的世界,那里的人民过年过得特别快,从同一纪元算起,在同一时期内,别地方的人 们到二十四年,四川人至少已到四十多年了。”“四川各路军的预征粮税,据说在民五 以后,自民五至今,已征到一百余年。这样加速度地下去,说不定在民国一百年之前预 征到一千余年,‘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两句古诗,也可为四川农民咏了。”[5 ](pp.147-148)沙汀小说浓郁的民俗描写,客观上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作品的丰富内涵 ,以及对抗战与启蒙关系的深刻思考。
二
如果说沙汀借助民俗事象表达了对假恶丑的社会现象深刻揭露和批判,那么艾芜则执 著于对民俗生活中真善美的关注和追求。作家对真善美的追求似乎可以追溯到早年所受 到的民间故事的影响。从民俗学视角审视艾芜的“流浪汉小说”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尝试 。鲁思·本尼迪克特说:“我们必须看到,风俗习惯对人的经验和信仰起了决定性的作 用,而它的表现形式又是如此千差万别。……每一个人,从他诞生的那一刻起,他所面 临的风俗便塑造了他的经验和行为。”[6](p.23)社会心理学家也发现,早年的生活和 体验对人的一生都可能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些观点运用到艾芜身上也是比较适合的。民 俗不仅催生了艾芜的流浪行为,而且也影响到作家的精神气质和审美方式。“百善孝为 先”,中国旧时代的家庭教育十分注重伦理道德的正面教化。作家幼年时代,祖母常常 给他讲“二十四孝”中的故事,如“安安送米”等等。但真正对艾芜产生深刻影响的是 AT461型民间故事“魏小儿西天问活佛”。魏小儿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可不知为什么自 己越来越穷。在西天取经的途中他遇到鸦雀、蟒蛇和哑巴少女,他们都求魏小儿询问摆 脱苦难的方法。经过长途跋涉,魏小儿终于取经回来。不但教给鸦雀蟒蛇成凤成龙的方 法,还让哑巴少女开口说话。这个“求活佛型故事”对艾芜有极大的吸引力,激起他无 限的渴望和遐想,在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日后流浪的种子。在《我的幼年时代》一文中 ,艾芜写到:民间故事中的魏小儿,“他小小的年纪,竟能孤独地西行,常常把我幼稚 的想象,带得很远很远”[7]。1925年,艾芜离开家乡,真的开始了童年时期就心驰神 往的“魏小儿式”的流浪生活。先后辗转于云南、缅甸、马来亚和新加坡等地。1932年 ,艾芜根据自己流浪生活的体验,开始创作“流浪汉小说”,后结集为《南行记》。
民间故事所包含的道德伦理教育,某种程度上使得作家能够自觉地用人道主义情怀关 注同情苦难世界中受难的人们。艾芜的《南行记》从一开始就试图把“在现时代大潮冲 击圈外的下层人物,把那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的朦胧反抗的冲动,刻画在创 作里面”[8](p.291)。客观地说,作为“左翼”作家,艾芜不可能不受到左翼文学思潮 的影响。尽管艾芜对那些“被生活抛出去的人们”的同情中包含有“社会分析”所得出 的理性判断,但是他的创作并没有出现左翼作家普遍存在的概念化、公式化的毛病。这 或许是民间故事对艾芜个性气质和审美情绪的影响,或许是流浪生活中奇异的风俗描写 冲淡了“左翼”文学意识形态的底色。在流浪汉小说中,作家用“魏小儿”式的童年视 角传达出对真善美的渴求,“艺术正生根在对生活的肯定和追求当中”[9](p.162)。他 的小说也正如《南行记》序中所说的那样:“打算把我身经的,看见的,听见的,…… 切切实实地写出来。”我们也不妨走进小说家的艺术世界,随同艾芜作一次奇异的“流 浪”,感受西南边陲浓郁的民俗美、人情美和人性美。
怀着对生活真善美的憧憬与追求,西南边陲异域情调的民俗风情让艾芜魂牵梦绕终生 难忘。《南行记》中有旅居云南山寨的奇异风俗(《人生哲学的一课》);也有傣族坝子 上的民居习俗(《我的旅伴》)。有克钦人(景颇族人)奇特的服饰(《山官》);也有荒蛮 边地“杀人祭地”农耕陋习。“每年下种的时候,他们就规定要杀个把外乡人。做啥呢 ……祭祀谷地!听说不如此,便没好收成,这是祖传的章法。”(《森林中》)我们把沙 汀与艾芜笔下的民俗稍加比较就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出于对民俗作历史、道德的 价值判断,沙汀自然要对民俗进行一定程度的变形和重构;而艾芜则注重对民俗进行“ 中性”客观的审美评价,追求民俗生活的真实的图景。艾芜小说的民俗描写无疑具有客 观再现的“逼真”特色。
《南行记》与魏小儿故事明显存在着“同构”现象。AT461型民间故事不仅影响了创作 主体日后的流浪行为,而且也制约了艾芜小说中的人物塑造。作品中的民俗个体大都是 生活的流浪汉。如“赶马人”、“小偷”、“盗马贼”、“抬滑竿的”和“私烟贩子” 等等。而流浪汉们正直善良、乐观通达的人性美、人情美正是艾芜所要挖掘和刻意表现 的。小说的人情美主要表现在西南边陲民俗个体流浪的谋生方式上。客观地说,小说所 描写的这些流浪汉的“职业”并不正当。但艾芜以一种“善”的情感判取替代道德的、 社会的、价值的判断,通过这些不同的生活样式,反映出西南边地另类群体的生活原生 态及其善良的人性。在《山峡中》、《松岭上》和《月夜》等小说中,作家深入到小偷 的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山峡中》小黑牛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那多好呀!……那样的 山地!……还有小牛!”土地对于这些“老实而苦恼的农民”来说是最亲切不过的。但现 实是残酷的:“天底下的人,谁可怜过我们?……个个都对我们捏着拳头哪!要是心肠软 一点,还能活到今天吗?”艾芜在描写他们强硬冷酷的姿态时,仍注重挖掘他们善良的 一面。那个“夜猫子”在“我”书中放了三块银圆后不知去向。从《私烟贩子》老陈身 上分明也能感受到他的坦诚:“我卖鸦片烟就说卖鸦片烟,并没有说我在卖灵芝草!” “我们卖鸦片烟的,都是天字第一号的诚实人!”总之,艾芜在揭示另类的民俗群体时 ,更倾向于展示那种善良诚实的人性和开朗乐观的民间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偷马贼”是《南行记》中一群独特的流浪者,如《森林中》的马头 哥、《山中送客记》中的大老杨等等。特别是《偷马贼》中的老三偷马不成致伤后,非 但不难过,反而感到满足和自豪。只有这样,他才能出名,那些马头哥和店主才会尊敬 他。“偷马贼的招牌,在这边是值钱的”。这种不惜用人格、声誉乃至生命换取生活资 本的“异化”现象,是流浪汉小说中最为突出和醒目的主题。艾芜通过小说主人公揭示 了这种普遍“异化”的根源是乡土社会土地兼并的现状。“我们这辈子人,一落下娘胎 ,就连针尖大的地方都没有……无非是寻裂缝罢了……这就是我老三寻着一条裂缝,钻 进去了。”人性“异化”同样也在“私烟贩子”身上得到体现,如《森林中》、《我的 旅伴》和《私烟贩子》等。即便如此,作家借助民俗事象揭示“偷马贼”、“私烟贩子 ”人性异化同时,念念不忘的还是这些流浪人所葆有的“魏小儿”般善良真诚的美德。
《南行记》充溢着作家艾芜一个流浪汉真切的人道主义情怀。李健吾认为“这种永生 的人类的同情”,是“我们的作家有一个相同的光荣的起点”[10]。长期流浪生活的体 验,使得作家更深切地体会到社会底层人民的苦难和不幸。同时对底层人民所葆有的美 德的揭示,也构成了艾芜人道主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即既有诚实善良的美德又不乏顽强 的生命力。胡三爸自信天无绝人之路,老陈身上“蕴藏着无尽的活力,死的阴影跟他离 得极其遥远”。他们爱憎分明,心地善良。“夜猫子”给“我”留下了三块银圆;《松 岭上》描写了主人公杀了恶霸一家的行为以及开朗乐观但又不乏狡黠的性格。即使他们 仍在从事着“不正当”的营生,但他们还是希望有一个安定正当的职业,像“寸大哥” 那样规规矩矩地做人,重新做一个赶马人。当别人劝他做盗马贼时,他坚决反对:“这 咋好呢?这不是专同你们为难?”在《我的旅伴》中,艾芜情不自禁地这么写到:“我赞 美……那种敢作敢为富有进取的精神,更喜欢……那种心地善良,处处助人为乐的热心 。”
通过对《南行记》的解读可以看出,艾芜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与早年受到民间故事的 熏染分不开,《南行记》中各类流浪个体往往出自作家后来的生活经历和亲身体验。这 是形成最为持久影响的时期,也是最能代表艾芜个人真实或潜在品格的各个方面[11]
(pp.138-139)。难怪许多年以后,艾芜在《想到漂泊》一文中仍然深情地说:“如今
一提到漂泊,却依旧心神向往,觉得那是人生最销魂的事……”
1937年开始,艾芜把一贯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对真善美的追求延伸到故乡广袤的川西平 原上。作家在《春天》改版后记中阐明了自己创作的意图,正是那浓得化不开的乡土情 结,使他常常思念故乡。在艾芜看来,描写故乡生活姑且可以作为乡愁的一种有效的心 理补偿,“于是,便决定把那些在泯江流域的景色人物,移到纸上,也宛如自己真的回 到故乡去一般”。《春天》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小说精品,其艺术成就在于出色地塑造 了三种不同个性的农民典型:憨厚懦弱的邵安娃、敢于反抗,富有同情心的刘老九和“ 阿Q式”的赵长生。在《春天》改版后记中作家特别指出:“赵长生这类农民,在佃农 中,我觉得更占得多些……历史之所以进步得慢,总爱走迂回的道路,赵长生这类人, 我疑心他们是不能不负一部分责任的。”即使在批判赵长生劣根性的同时,艾芜“魏小 儿”式的人道主义情怀仍依稀地流露出来。
艾芜小说符合文学民俗学研究的“第二个方向”。AT461型民间故事不仅催生了作家人 道主义情怀和流浪行为,而且也影响到小说人物的塑造和性格刻画。只有充分考虑到民 俗对作家创作影响的内在机制,也许才能真正领会艾芜流浪汉小说的审美特征。
三
把李劼人的小说作为民俗学资料来看待显然是不过分的。郭沫若在《中国左拉 之待望》中称赞李劼人“大河小说”的风俗描写相当精到:“作者的规模之宏 大已经相当地足以惊人,而各个时代的主流及其递禅,地方上的风土气韵,各个阶层的 人物之生活样式,心理状态,言语口吻,无论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亏他研究得那样 透辟,描写得那样自然”;“至少是‘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11]。这样的评价 精辟地概括了李劼人小说独具的民俗学价值和艺术特色。李劼人创作之 所以取得如此突出的成就,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于作家有着深厚的民俗学功底。1930至 40年代,我国西南地区的民俗学活动十分活跃,不少作家都积极参与了民俗学的搜集和 整理工作。李劼人显然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作家的藏书很大一部分都是有关 地方志、风俗志一类。在从事创作之余,作家还写了《成都历史沿革》、《中国人之饮 食》、《漫淡中国人之衣食住行》(1943年9月发表于成都《风土什志》2卷3号)等民俗 学文章。特别是李劼人花费相当精力完成的《说成都》,在“说大城”、“说 少城”、“说皇城”,“说河流”、“说街道沟渠”等若干方面集民俗风情、地方志于 一体,系统地考论了四川首府成都的历史演变、文化典故和乡风民俗。李劼人 民俗学的深厚学养与他的文学创作可谓珠联璧合,特别是他的代表作《死水微澜》,把 民俗描写与社会心理、时代风貌和人文历史有机结合起来。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他 的小说文本是研究近代四川民俗的最生动的材料。
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经济侵略,西方传教士开始在中国进行 文化侵略,以实现对中国的全面占领和瓜分。“教会与农民真正意义上的冲突实际上是 从风俗之战开始的。”由于两种文化所表现的不同文化心理和文化机制,客观上也就决 定了西方宗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冲突,特别是与中国民间文化冲突。鸦片战争以后,外 国教会在中国开始出现,甚至在广大偏远的乡村都设有教堂。西方传教士排拒中国本土 的人生礼仪、信仰禁忌和岁时节令等民俗文化,并严禁入教的教民参加,取而代之用西 方教会的仪式和活动来规范“教民”的日常行为。“风俗之战的进一步展开是教会对农 村神灵偶像崇拜的破坏与冲击”[12](pp.101-102)。这使得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冲击,乡民的精神结构、文化心理和民俗习惯遭受了极大的挑战。关于“教 会”题材早在20年代乡土作家台静农的《为彼祈求》就有所涉及,浙东乡土作家王任叔 的长篇《莽秀才造反记》也是反映“风俗之战”这一主题的,而四川的“风俗之战”则 表现得尤为突出。李劼人的《死水微澜》通过罗歪嘴和顾天成之间势力的此消 彼长,再现“袍哥”与“教民”的冲突,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四川的社会面貌和时代风 气。
小说一开始描写“袍哥”的不可一世。罗歪嘴是天回镇袍哥势力的代表,他经营鸦片 ,开设赌场,生活糜烂。赌场里“烫毛子”导致罗歪嘴与顾天成的裂隙;特别是“灯市 ”上顾、罗之间的矛盾则进一步公开化,招弟的丢失更加深了顾天成对罗歪嘴的仇恨。 所有这些都为顾天成放弃卖地捐官,以入教的办法对付罗歪嘴作了必要的心理铺垫。小 说中作家对“袍哥”组织构成和运作作了详细介绍;特别是对青阳宫“灯市”的细腻描 写更见李劼人的民俗学功力。
鲁迅在《吃教》中说:“耶稣教传入中国,教徒自以为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却都叫 他们是‘吃教’的。这两个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13](p.245)顾天成之 所以要“吃”洋教,就是携“教”自重并以此来对抗本土的袍哥势力。“吃教”的顾天 成不仅加剧了与袍哥罗歪嘴的厉害冲突,而且也与家族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和抵牾。“家 族之变”所“引起乡村伦理亲属关系的紧张,关键不是信仰的冲突,而是由此带来的习 俗的扞格。”[12](p.105)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中国近代以来不断遭受外族侵略 所烙下的“仇洋”心态。因此,顾氏家族竭力反对顾天成入教。可见,教会和教民的存 在,不仅干扰和破坏了农村社会固有的生活秩序,而且也引起了封建社会家族制度的瓦 解。中国近代史上,由于教会的贪婪,教会对教民活动的限制,加上乡民对洋教想当然 的看法(如挖眼睛做小菜等等),特别是在民众与教会的冲突中,教民依仗洋教势力往往 都以胜利告终。民众与教会的尖锐矛盾,导致晚清大量“教案”的产生。如果没有厚实 的民俗学、地方志的学养,作家是不可能把民众与社会心理如此淋漓尽致地揭示出来。 小说所体现的地方志、风俗志倾向是很自然的。
《死水微澜》中“教民”得势首先表现教民对袍哥势力的胜利。顾天成从罗歪嘴手中 得到垂涎已久的蔡大嫂,就是一个非常形象的诠释。其次,教民得势还体现在对中国传 统家族制度的胜利。作为家族制度象征的族谱中又重新出现了顾天成的名字,顾天成实 际上成了这个家族的无上权威。小说反映出四川乡村在“风俗之战”中传统袍哥势力的 衰落和教民教会势力的强大。顾天成是李劼人精心设计的一个贯穿“大河小说 ”系列中重要的民俗个体。在《暴风雨前》中,顾天成仰仗着“教民”身份,竭力染指 赫又三的乡下祖产和土地;在《大波》中,他则由一个土财主兼教民而摇身一变为新繁 县民团团总;继而又从不可一世的“教民”变为一个哥老会的舵把子。顾天成集粮户、 教民、团总和袍哥舵把子于一身,把势力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就像四川特有的变 脸戏法一样,扮演了一个不甘寂寞的“变色龙”角色,在乡间一潭“死水”中搅动阵阵 微澜。通过顾天成不同角色和活动空间的转换,作家把特定时期四川的社会风貌、风土 人情、人文历史和历史沿革等方面充分地展示了出来。李劼人“大河小说”“ 写出许多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分历史,就是说风俗史。”(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 言)这“不仅成为他的小说的现实主义的重要特色,而且也为‘民俗学’研究提供了极 有价值的史料。”[14](p.148)
用文学民俗学的“三个方向”分别概括沙汀、艾芜和李劼人的乡土创作是可行 的,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这三位作家各自不同的民俗学意蕴。不过话又说回来,对 作品的解读和分析又很难把这几个方面截然分开。他们的民俗描写都不同程度地同故事 的发展,情节的深化,人物性格的塑造,乃至社会心理、时代背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丰富的民俗描写,正如李劼人所说,“我的用意,是想把这东西当成一种生料 ,供献给有心的读者。”[15]在给读者带来异域情调的审美满足时,也能够更好地理解 了作品的时代风貌,更好地领会小说的精神实质。
收稿日期:2003-01-15
标签:李劼人论文; 艾芜论文; 作家论文; 民俗学论文; 文学论文; 春天论文; 乡土小说论文; 袍哥论文; 死水微澜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