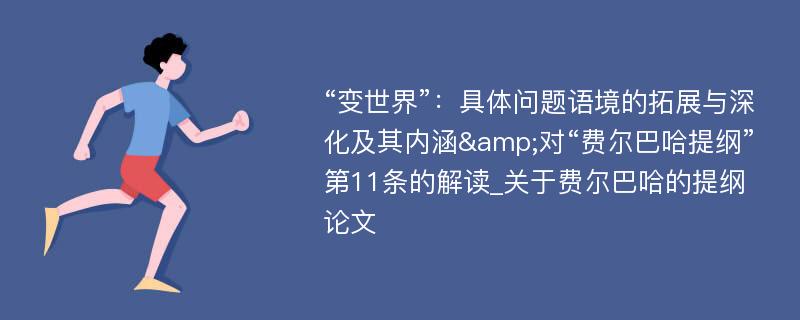
“改变世界”:特定的问题语境及其内涵的拓展与深化——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费尔巴哈论文,语境论文,提纲论文,第十一条论文,内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0)01-0225-05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P57)《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的这最后一条被中国学者极为频繁地引用,“改变世界”也被中国众多学者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全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本质特征。因此,明确“改变世界”的言说语境,判定“改变世界”的具体内涵,对于研究马克思的理论学说,进而对于研究整个马克思主义,都具有某种前提性、根本性的意义。
对《提纲》中的“哲学家们”的具体所指和适用范围,中国学术界颇多争议。有人认为,《提纲》的最后这一条表明了马克思持一种“哲学终结论”的立场[2];有人把其中的“哲学”理解为“包括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在内的所有过去的哲学”①;有人认为“哲学”特指德国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3]。对于“改变世界”的意蕴,学者们的理解更是歧异纷呈。高清海把“改变世界”理解为马克思在哲学思维方式上的变革:旧哲学是从先验的理性原则出发的,所谓“解释世界”,就意味着他们要让现实的世界去屈从理性的抽象原则,“改变世界”则是从现实世界出发,而不是从抽象原则出发[4]。何中华认为,马克思在哲学观上实现了一种“格式塔”转换:由以往那种着眼于对世界的诠释的知识论式的哲学,转变为作为世界本身展现方式的、以“改变世界”为本质特征的哲学[5]。徐长福认为,马克思说出“改变世界”的名句时感悟到了“做”的问题——这一问题,是西方哲学史上明显地忽视了的形上问题[6]。
虽然学者们对“哲学家们”的具体所指分歧甚大,但几乎没有异议的是,可以把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明确地批判过的德国青年黑格尔派划归于“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的“哲学家们”。既然如此,下面就来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马克思认为德国青年黑格尔派“只是”“解释世界”,或者说,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认定德国青年黑格尔派“只是”“解释世界”?
一、德国青年黑格尔派与“改变世界”
对于上述问题,可以找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诸多论述加以阐释,但是,关于这一问题的最为直接与明确的表述则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话:
既然这些青年黑格尔派认为,观念、思想、概念,总之,被他们变为某种独立东西的意识的一切产物,是人们的真正枷锁,就像老年黑格尔派把它们看作是人类社会的真正镣铐一样,那么不言而喻,青年黑格尔派只要同意识的这些幻想进行斗争就行了。既然根据青年黑格尔派的设想,人们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一切举止行为、他们受到的束缚和限制,都是他们意识的产物,那么青年黑格尔派完全合乎逻辑地向人们提出一种道德要求,要用人的、批判的或利己的意识来代替他们现在的意识,从而消除束缚他们的限制。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青年黑格尔派玄想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如果说,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人宣称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那就确切地表达了他们的活动。不过他们忘记了: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1](P65-66)。
联系《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其他相关论述,可以对这段表述作如下的梳理:(1)在对现存世界与思想观念的关系的认识上,德国青年黑格尔派把观念、思想、意识作为现存世界的问题的原因、根源;(2)他们把自己的“批判”指向“词句”,也就是说,把“批判”局限在精神领域;(3)他们的“批判”的开展方式(实现方式)是用词句来反对词句,而且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词句;(4)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词句,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而是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也就是说,“只是”“解释世界”。
那么,与“只是”“解释世界”的德国青年黑格尔派根本不同的“改变世界”该作何理解呢?
早在写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时,马克思就已经明确了自己的“改变世界”的立场:在世俗生活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上,他把宗教的存在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7](P169);在批判的指向上,他给自己提出的方向是“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1](P2);在批判的实现方式上,马克思的说法是“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P10)。后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四条中,马克思在肯定了费尔巴哈所作的工作——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之后,指出了他的局限:没有用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因而未能提出使世俗基础在实践中革命化的任务[1](P55)。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改变世界”的立场有了更为清晰的理论自觉。在意识、观念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物质实践的关系问题上强调,“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P73);他们的历史观“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1](P92)。在批判的指向上,他们强调:“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P75)。在批判的实现方式上,他们强调:“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1](P74)。
通过上述梳理不难看出,马克思以唯物主义地理解社会存在与人们的意识的关系为基础,走向了对现存世界的根本否定。
依据上述对比,可以说,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分歧集中在对现存世界的理解与态度上:首先,马克思“唯物地”“解释”现存世界,认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青年黑格尔派则认为,观念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其次,马克思“唯物地”“理解”对世界的“改变”,致力于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青年黑格尔派则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再者,马克思认为,必须“唯物地”“实现”对世界的“改变”,用物质力量摧毁物质力量;青年黑格尔派却“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词句”,事实上肯定了现存世界本身。
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与“改变世界”
在马克思看来,与德国青年黑格尔派一样,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对现存世界(资本主义社会)持辩护立场,因而也“只是”“解释世界”;不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有其独特的“辩护实现方式”。
1.阶级立场与“改变世界”
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明确了“市民社会”的基础性地位。他认为“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8](P412),因此,马克思在巴黎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9](P50、P51)的。沿着这样的思路前行,他很快发现,国民经济学的理论与“当前的经济事实”明显地发生了矛盾,难以自圆其说[9](P12—14)。透过国民经济学的理论与现实的矛盾,马克思揭示了隐含在国民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中的资产阶级立场:“国民经济学虽然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这一点出发,但是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9](P62)
与国民经济学家们不同,在开始自己的经济学研究之前,马克思就已经自觉地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提出了批判性地认识现存世界的异化劳动学说,揭示了相互联系的四种异化状态: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过程的异化,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9](P52-59)。
2.理论的彻底性与“改变世界”
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在理论上是不彻底的。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却没有说明这个事实,而像神学家一样,把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具有历史形式的事实[9](P50—51)。正如后来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说的,国民经济学家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进行,但并未说明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1](P137—138)。
与国民经济学家把私有财产作为一个无须考察的既定事实不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私有财产归结为异化劳动: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异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事实上,它是异化劳动的结果[9](P61)。把异化劳动作为私有财产的根据,当然有其无法解决的理论困难,但是,重要的并不在于马克思把私有财产归结为什么,而在于马克思认为它需要归结,而不是无须说明的事实(前提)。因此,马克思把私有财产归结为异化劳动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国民经济学把私有财产作为无需考察的前提,从而把资本主义特定的生产方式作为人类生产的一般样式永恒化,把工人的异化处境视为一种永恒的必然性;而马克思的“应该把私有财产本身加以说明”的理论立场,实际上为他以后更加细致、深入地批判政治经济学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研究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来没有提出的问题”——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研究了劳动形成价值的特性,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并确定了价值不外就是这种劳动的凝固。”[10](P21)
3.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与“改变世界”
国民经济学在理论上的不彻底性导致了其对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非历史的态度以及为现存世界作辩护的态度,即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将永恒地存在下去。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经济学家们”的“奇怪的”论证方式进行了剖析:他们认为,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而资本主义制度是天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1](P151)。
与国民经济学不同,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对物质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明确了自己对待现存世界所持的历史的态度: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方式而建立的相应的社会关系,以及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所创造的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都不是永恒的,而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1](P141—142)。
4.思维方式与“改变世界”
国民经济学对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非历史态度是与其抽象地认识问题的思维方式相一致的。被这种思维方式支配了的国民经济学家们热衷于讨论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只看到各个阶段的生产的“共性”,而忘记了其本质的差别。而如果忘记了这种差别,就会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马克思不无讥讽地说,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此[11](P26—29)。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非历史态度与其抽象的思维方式之间的内在关联作了如下剖析:“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12](P98—99)
与“现代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所采用的思维方式是具体的:“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13](P532)针对“现代经济学家”只看到各个阶段的生产的“共性”而忘记其本质差别的倾向,马克思强调,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虽然一切生产阶段所共同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一些抽象要素,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11](P26—29)。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忽略价值形式、货币形式及资本形式的特殊性形成鲜明对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着重分析了价值形式从简单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到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再到一般价值形式,最后到货币形式的历史发展[12](P62—87)。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还明确区分了下述三种“过程”:(1)劳动过程(使用价值生产,有用劳动);(2)价值形成过程(商品生产,有用劳动与创造价值的劳动的统一,使用价值的形成与价值的形成的统一);(3)价值增值过程(资本主义形式的商品生产,有用劳动和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的统一,使用价值的形成、价值的形成与价值增殖的统一)。
5.拜物教与“改变世界”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还把资产阶级经济学称为一种“拜物教”。在商品世界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的形式[12](P89-90),而“经济学家们”却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物所获得的规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属性,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而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一种粗俗的唯物主义,同时也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甚至是一种拜物教[8](P85)。在《资本论》第2卷中,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拜物教“把物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像被打上烙印一样获得的社会的经济的性质,变为一种自然的、由这些物的物质本性产生的性质”[10](P251)。资产阶级经济学所特有的拜物教,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关系物化现象的理论表现。
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深入分析、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拜物教现象。他把拜物教看作是一种历史性的社会现象。首先,在人类产品不表现为商品的地方,也就不会存在商品拜物教,当然也不会有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在封建农奴制社会中,生产关系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劳动的具体形式就是劳动的社会形式,封建主与农奴的关系是非常清楚的,没有披上物的外衣,毫无虚幻之处。农村家长制的生产,在家庭范围内,家庭成员的劳动直接就是社会劳动,家庭所需要的各种产品都是家庭成员的劳动产品,而不作为商品交换,人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很清楚的,没有任何神秘性[12](P94—95)。其次,在古亚细亚等生产方式中,产品转化为商品,从而人作为商品生产者的现象以及货币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只不过处于从属地位。这些社会的生产机体比资产阶级的社会生产机体简单得多,它们或者以个人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为基础,或者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12](P97)。因此,此时商品和货币拜物教作为一种社会现实,并未占据统治地位。再者,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在一切劳动产品(包括劳动力)都成为商品,一切生产者的社会关系都要通过“价值”而表现的时候,拜物教才取得了其在整个社会的支配地位,而且发展到了其高级形态——资本拜物教。最后,当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都极其明白而合理时,比如在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中,就不会再有包括资本拜物教在内的一切拜物教现象[12](P96-97)。
综上所述,“经济学家们”站在作为剥削者的资产阶级一边,把私有财产作为一个无须考察的既定事实,非历史地看待资本主义制度,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自然规律”加以永恒化,采用抽象的思维方式考察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构建了一个具有拜物教性质的经济学体系。这种学说是为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的经济学,同“哲学家们”一样,“经济学家们”也“只是”“解释世界”。马克思则立足于工人阶级的利益,自觉肩负起“把私有财产本身加以说明”的理论使命,历史地看待资本主义制度,采用具体的思维方式,深入分析与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拜物教现象,建构了一种以“改变世界”为宗旨的“批判的”经济学。
三、种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与“改变世界”
如果说马克思的“解释世界”中的“解释”有其特定所指,并非普通意义上的“说明”,那么,“改变世界”中的“改变”也有着非常丰富的具体内涵,而它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做”或“实践”。对此,可以通过马克思的理论与其他种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比较来加以说明。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而扬弃私有财产必须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9](P81)。基于这种自觉,马克思并未一味地谴责资本主义制度,而是首先肯定其历史进步性、必然性与合理性。马克思的这种立场,与封建的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有着明显的区别。
然而,马克思决不是一个历史终结论者,在《共产党宣言》中,他同样指出了资产阶级灭亡的必然性:“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1](P278)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将走向一种自我否定,而这种否定是“内在的否定”。这与那些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生产方式是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8](P412)。因此,共产主义只有在彻底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来实现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明确指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9](P62)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把无产阶级视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1](P278—284),并指出,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1](P307)。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着根本的不同。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改变世界”构想的精髓在于,既不像封建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那样开历史的倒车,也不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那样主张对社会的点滴改良,而是在资本主义的历史成就及其内部矛盾的基础上实现对它的根本否定——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四、几点结论
通过对马克思的理论与德国青年黑格尔派哲学、资产阶级经济学及其他种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其一,马克思“改变世界”的思想与其唯物史观有着密切的联系。马克思对德国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性分析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地理解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的;对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也应着力发掘其“改变世界”的意蕴。也就是说,马克思的主要意图并不在于解释社会意识如何在一定的社会存在的基础上产生,而在于指明社会存在领域的变革相对于社会意识领域的变革的优先地位。
其二,马克思的“改变世界”有其特定的问题语境,因此,《提纲》第十一条中的“解释”、“改变”都有其丰富的具体内涵——前者并非普通意义上的“说明”,后者也不能在一般的“做”或者“实践”的意义上作出过于宽泛的解释。
其三,准确理解马克思“改变世界”的思想,有必要越出哲学的学科边界——“改变世界”不仅意味着一种新的哲学观,而且还内蕴了一种“批判的”经济学和“科学的”社会主义。把“改变世界”理解为马克思在哲学思维方式上的重大变革,当然是必要的,然而,如果“改变世界”在马克思那里只具有哲学观的意蕴的话,那么,马克思顶多只能被称之为古典意义上的哲学家,但不会成为《资本论》的作者,更不会成为把“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作为其“毕生的真正使命”的“革命家”[7](P777)。笔者完全赞同把马克思的哲学理解为一种不同于“理论哲学”的“实践哲学”,但是,当把马克思主义的意义限定为“充当社会的调节性理想而不是建构性理想”[14]时,其“改变世界”的本真精神也就荡然无存。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的中译者就持这种看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Ⅷ页。
标签: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商品拜物教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经济学论文; 德国历史论文; 政治经济学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德意志意识形态论文; 问题意识论文; 哲学的贫困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