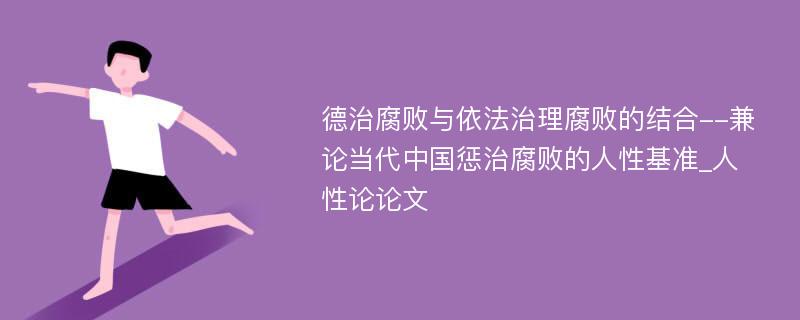
以德治腐与依法治腐的结合——兼论当代中国惩治腐败的人性论基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性论论文,惩治腐败论文,德治论文,基准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73X(2002)04-0014-06
中西不同的人性论设定导致了不同的治政方略和治国路径。一般来说,中国的人性论虽然多种多样,但总体是以性善论为主。西方则是以性恶论为主。性善论往往与德性主义的治政理论相关,性恶论则崇尚法治主义的治政学说。落实到反腐败的问题上,中国的反腐败注重德治教化,西方的反腐败则注重法治惩处。二者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我国新时期的反腐败应当从中西德治主义和法治主义的传统中总结经验教训,力求把道德教育和法治惩处有机地结合起来,坚持治本和治标的辩证统一。
一、中西人性论传统与惩治腐败的策略选择
中国传统人性论思想和德制反腐败思维。中国人对人性的探讨始于先秦时期的孔子。孔子对人性虽未曾明确提出性善性恶的主张,但由于他把人视为有道德的动物,故在基本的价值观念上开创了德性主义人性论的先河。孔子之后,有关人性的思想和主张在诸子百家那里获得较全面的讨论,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人性论争论的高潮,也基本上确定了我国人性论理论的传统。
从孔子的“性相近”出发,孟子倡导性善论。其理论基础就是人的天赋本性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之四“善端”,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此四者是人人都具有的、与生俱来的、内在于己的,因而人性就其本性来说是善良的。人们只要从先天具有善端出发,内求于己,经过不断地扩充、发展,就可以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君子,获得道德上的完善。孟子肯定人性是善的,但并不否定现实生活中人性的恶,认为人性的恶是由于人们放松了对善端的培养扩充而造成的,去恶的路径即是“发明本心”,“反躬内求”,加强自身的修养。一个人如果不能很好地扩充善端,以仁义礼智等道德品质和原则规范控制感官的欲望,“善端”被尽“伐之”,则会私欲膨胀成为恶。从性善论出发,孟子认为人们的犯罪为恶不是人的本性,是可以通过“教之”而使其向善的。但是“徒善不足以为政”,在实行仁政王道的前提下,对于“不仁”的暴君,也是可以“放伐”的。尽管孟子认为法可以并且应当高于君、重于君,但在价值目标和价值层级上却坚定地认为道德高于法制,国家法度的捍卫只能依靠有德的贤臣。孟子的这一思想表明了其德性优先法治和治国必以德性的弘扬为尚的主张。
与孟子不同,荀子提出了性恶论。在荀子看来,人生下来就有好利、好嫉恶、好声色的本性,因而人之性是本恶的(实是趋恶),而为避免“犯分乱理而归于暴”,必须师法之化,施以礼义之道而归于治,亦即化性起伪。荀子的“化性起伪”说并不是要除去人心之好利、好嫉恶、好声色之本性,而是使其在礼义的规导下得到节制,不泛滥。荀子的性恶论,不仅把礼义视为圣人创制的产物,而且把法度也看作是圣人创制的产物。虽然荀子和孟子在人性上所持的立场完全相反,但有一点却是共通的,即二者的目的都是要抑恶扬善。在方法上,孟子的求于内与荀子的求于外存在一定的区别,但都不能完全离开法度的作用。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两人均把圣君贤相式的贤人政治看作是抑恶扬善的根本途径和保障。
与荀子同持性恶论的还有先秦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他从人都有利欲之心,都追求名利立论,认为自利是人的本性,人性普遍是恶的,人与人之间都是一种利害关系。因为人们没有任何向善的可能性,要抑制人的恶性,凭道德教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求诸于重法严刑。法家的隆法而治的主张与儒家的德制主张是相反的治国方式,它为秦代所推崇却被后代崇尚王道的君王所不取。
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存在性善、性恶的人性一元论之外,还有老子的人性自然论、世硕等人的人性善恶混论、告子的性无善恶论,以及董仲舒的人性三品说、李翱的复性说等。其中对历史影响较大的主要是人性有善有恶论和性三品论。政治化的儒家以董仲舒为代表,他的人性论和德主刑辅论在历史上影响十分深远。董仲舒认为,“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既然人有贪仁之性,所以就应当用“德”去启发其善性,用“刑”去威慑其恶性。善恶二性又具体表现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三品。“圣人之性”,不经教化便能“善”;“中民之性”可能接受教化而为善,又可能不受教化而为恶;“斗筲之性”施与教化也很难为善。“中民之性”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人性,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既用德教,扶持其“仁”质而使之为善,又用刑罚以防止和惩戒其“贪”质而使之不为恶。董仲舒的人性论将孟子和荀子、韩非的人性论调和起来,既肯定人性向善的可能性,又承认人性作恶的可能性,但由于总体上倾向于孟子的性善论,故在治国方略和治腐策略上走向了德主刑辅论和大德小刑论。这一思想在历史上也发挥过一定的作用。
综观中国社会的惩腐史,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一般性的认识,中国历史上反腐败对人性预设并不是基于一种非此即彼的单一的人性论基础,而是一种基于人性善恶混论的人性论,表现在反腐败策略的选择上,历朝历代都很少采用单一的徒善与徒法的方式,德法并举是中国历史上反腐败策略的主旋律。但是,这二者的结合并不意味着德、法之间没有轻重缓急之分。儒家基本的倾向是德主刑辅或先德后刑。德化是刑狱的根本,故惩治腐败应当以德为本,以刑为用。
西方人性论思想与法制惩治腐败思维。在西方,对人性问题的探讨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已经开始。苏格拉底提出“道德即知识”、“知识即美德”、“无人有意作恶”的思想,表明了其人性本善的主张。柏拉图认为“善的理念”是一切事物和人性产生的根源,因而人性就其本根和原初性上讲是善的。亚里士多德则指出,善是人类一切活动所追求的目标,而追求善这一目标,就在于人的理性,人能用理性来支配和控制自己的欲望。同时他也认识到人性中存在着趋恶的兽性,对这种兽性的克服,他在《政治学》中主张用法治来解决,并认为“法治应当优先于一人之治”,“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他还对法治做出了自己的界定,认为“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从这里的论述可以发现两点,一是亚里士多德把追求善做为人的目标,二是对于人性特别是政治中的恶主张以法制来抑制或去除。这种对人性的分析和对法治的推崇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
中世纪的欧洲是以神学统治哲学、以神性否定人性为基本特征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和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原罪说代表了这一时期的人性论主流思想。由于人是先天具有原罪的,人生皆恶,那么人的一生就是不断赎罪的过程,以求进入天国。这一时期,政治从属于宗教,国家依托于教会,世俗君主受命于教皇,法律从属于神法,究其实质就是以教会、教皇代表上帝为人间立法。这种对人性恶的绝对化趋向否定了人们正常的生活需求和合理的欲望,造成了对人性的巨大压抑,对人性的极度贬损和对神性的至上性推崇,形成了西欧中世纪时期彻头彻尾的“德”治主义和禁欲主义。因为现实的法和道德律令只是上帝的意旨,是人的道德追求的最高境界。
出于对经院哲学的反叛,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扛起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大旗,反对神性和神道主义。他们高扬现世生活的幸福和价值,把人从天国拉回人间。我们不能否认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者在反叛基督教中的历史意义,但是这种反叛是以走向另一极端为特征的,他们大都把追求现实的物质利益和性欲的满足视为人的本性,而把人的自然本性的实现视为道德,这种自诩为善的人性论在今天看来是一种典型的性恶论。它同样是对人类理性的一种漠视。
进入近代,西方社会关于人性的理论获得空前的发展,出现了各种人性理论假设。如以斯宾诺沙、霍尔巴赫、莫尔等人为代表的自然人性论,以霍布斯、洛克、休谟等人为代表的人性自私论,以莱布尼茨、狄德罗、闵采尔、梅叶等人为代表的理性即人性论,以笛卡尔、康德、摩莱里等人代表的唯理论的人性论,以卢梭等人为代表的天赋人性论,等等。在这几种不同的人性论中,以自然人性论和人性自私论影响最为深远,它们奠定了近代西方性恶论的理论基石。近代西方的这种性恶人性设定是以人都是利己,以追求个人利益的实现为逻辑起点的。这种人性论表现为对任何人的不信任心理。在公共管理领域,人们为了能够抑制某些集团的私欲膨胀而侵犯公共利益,在国家政权组成方面就确立了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组织形式。而对公职人员的行为规范则求助于外在的法制约束。
对现、当代西方影响较大的还有亚当·斯密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这种“理性经济人”一方面肯定人是利己的、自利的,另一方面又肯定人具有同情心、克己、勤劳、节俭等情操,并认为,后者为前者服务。说到底,斯密的人性假设本质上是一种性恶论。
综观西方人性论发展史,确定其为性恶论传统是可以成立的。正如叶传星先生在《论法治的人性基础》一文中指出的,“任何一种社会秩序类型都以对人性的特殊设定和估价为前提,对人性的不同认识和评价直接关系到对人们行为的自律与他律、自由与控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看法,关系到选择什么样的社会调整方式去达到社会秩序”。近现代乃至当代西方政治中的惩治腐败就是以人性恶的设定为基础的,这种性恶设定决定了在惩治腐败的行为模式选择上不可能求之于道德上的教化,而是求之于以法制约,通过法的威慑力量使人们形成一种对法的恐惧心理而不敢去腐败,同时,通过建立严密的法律体系又使人们欲腐而不能。西方国家主要是从这两方面来建立具体的反腐败机制的。
从中西反腐败人性基础的对比分析中,我们可以形成这样一种认识,在中国,性善论的提出虽然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思维,而对人性二元的设定是我国传统惩治腐败中的真实基础。但是这种人性二元的设定又是以人性向善或趋善为主要特征的,因而在具体的反腐败过程中,人们更多地注重道德的教化或对人的伦理、道德的呼唤。虽然德、法并用是我国传统反腐败的实际运行模式,但是以德为本、以法为用、以德制腐的反腐思维一向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在西方,对人性的认识是以恶为主流的,以对人性的不信任为特征,表现在反腐败当中,就是力图以立法来限制权力的滥用,防止人性中恶的因素的膨胀。因而在反腐败的思维上,西方走的是一条以法制腐的思维路径。
二、德治和法治惩治腐败的人性设定分析
按照一般的理解,德治是指以德治国、以德治人。但基于“德”自身的特性——即不依赖于外在强制力——而言,实际上是以德导人、以德范人。由于人们在德性上具有个体差异性和层次性,因而,以德导人的存在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然而德治的实行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施教者自身应该具备较高的道德水准,二是被施教者要有向善的可能性和主动性或有追求德性的需要。在这两个条件中,缺少前者只会导向道德上的伪善;缺少后者,这种对人的道德引导就没有效果。也就是说,实行一般意义上的德治是以人性善为预设前提的。按照同样的理解,法治是指依法治国、依法治人。对此,亚里士多德曾指出了法治必须具备的两个要素,即一是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二是这种法律本身是一种良好的法律。亚里士多德的认识是正确的,尽管其思想并没有在他所处的时代得到实行,甚至到人类文明发展二千多年后的今天,法治在形式上已被许多国家认可为治国方略,但在实质上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施。因为法治除了必须以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为前提外,还跟人们的认识能力和社会所处的其他客观环境有关。民主不真实,则法律得不到“普遍的服从”,就会有个人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情形,就可能会形成专制;同时,民意也得不到真实的反映。此时,法律就会转而成为只对下层普通民众有效,而对统治者失范的专制统治工具。此外,由于特定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条件的制约以及人们认识能力上的有限性,制定良好的法律也非举手之功所能为。根据法本身所固有的特征,即依赖于某种社会强制力——表现为国家、暴力等有形力量——而言,法律和道德是不同的。根据法治本来的意义和它的核心精神,即用法律来制约人在社会交往中的对他人和社会利益中造成侵害的行为或意识而言,法治是以人性是恶或人性趋恶为预设前提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从来是历史的、具体的,因而表现为社会关系的人的本质也是历史的、具体的,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永恒的人性。自从“人猿相揖别”产生人类社会以后,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极端低下,人们的起码需要难以得到满足,为了对抗外族(部落)的入侵和自然界的挑战而保持社会的生存,人们在自己所生活的社会群体内必须形成公正的社会关系,公正地对待每一社会成员。对这种社会关系的调节起初来自人们的自发意识,后来则通过氏族部落首领的德性表现出来。此时,如果我们撇开一些为当时人们所无法克服的困难(如因得不到足够的食物而吃老人)而形成的具有道德意义的问题不说,无论在意识或行为上,人们都表现为善的本性或趋向。
从人类认识到侵犯他族或别的群体能给自己带来利益时,人的本质就发生了变化。当
这种意识进一步外化为人的行为时,人的恶就以完全的形态表现出来。进入阶级社会后,人性中的恶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当然在阶级社会中,人性也并非是性恶一元论,趋善同样是人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恶是人们所厌弃的,善则是人们所愿求的。这样,在现实的社会中,即在性恶的发端至恶性的消隐这一人类历史时期,人性就表现为个人对恶的事实性趋向和对善的价值性趋求的矛盾,以及社会对恶的防范性制裁和善的引导性追求的矛盾。矛盾的解决表明了扬善的可能和惩恶的必要。反映到现实社会的腐败这一具 体领域,就表现为既需要扬善的德治一手又需要惩恶的法治一手。正像现实的人性并非是纯善或纯恶一样,德治和法治也不可能是理论分析上的那种纯之又纯的形态。德治是用较高道德要求来引领和教育社会成员以提高其道德品质的手段和社会状态,法治就是通过不断寻求合理的外在强制来惩恶扬善的手段和社会状态,二者功能和效用相殊,但是追求一种更高的善或最大程度的善却是二者的共同目的。
我们认为,对于惩治公共生活领域中的腐败现象,中国和西方在思维方式上是存在差异的,但这种差异只是侧重点的不同而已,并不是不可通约的。当代西方对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的重视,向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援乞在某种意义上表征了其对传统性恶论的反思,而中国走法治国家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道路则是对腐败周期律的沉痛的自我觉醒。
总之,德治和法治的结合是人类在恶的超越和向善的追寻中合规律性的阶段性存在。唯其如此,人类才能在治疗政治之癌的过程中取得满意的效果。
三、惩治腐败中德治和法治的关系
卓有成效地惩治腐败需要把德治和法治有机地结合起来。事实上德治和法治在治理腐败的斗争中也存在各自的局限和优势,只有把二者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发挥应有的力量。
1.德治和法治的关系是软约束和硬约束,或柔性约束和刚性约束的关系。德治就其实质而言,就是以德导人、以德范人,崇尚的是一种内在的合理性。从性质上讲,道德是一种通过传统习俗、社会舆论和人的内心信念来规约人们行为的规范体系。它通过促进人的道德意识、影响人的道德情感、强化人的道德责任、唤醒人的道德良知而起作用,以人们对某种道德律令或原则的自觉认同而为前提。因此,提升一个人或社会的道德水准必须以说服、教育、激励、引导为手段,而不能简单粗暴地求助于强制的力量压服人们来达到目的。正因为如此,道德对人们行为的规约只能是软性或柔性的,这是德治的通性。由于在不同社会制度条件下,不同的国家和社会所采取的以德制腐、以德导人的“德”所包含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因此,它所能获得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在当今我国反对腐败的斗争中就是要用共产党人和人民公仆应有的德性来教育人们,帮助他们树立和巩固高尚的道德品质,筑起拒腐防变的思想大堤,培养人们的腐败耻辱意识。
法治相对于德治而言则是一种刚性的制约。法治的实质就是依据公正的法律来公正地治理每一个社会成员,它只存在于真正的民主社会。离开这一社会条件,则既不能制定公正的法律,也不能公正地执行法律。由于法律所保护的是社会成员的合理利益和公共利益,在阶级社会还表现为统治阶级的利益,则不可能单纯诉诸软的约束或教育就能了事,还得依靠某种具有强制力的规范来制约侵犯行为,这就赋予了法律的强制力的必要性。因为腐败是一种利用社会赋与的公共权力对公共利益及某些个人合理利益的侵犯,这种侵犯又是以某种公共权力的拥有为基础的,因而对腐败的惩治就更需要强制的力量来予以保证。
从现实的人性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在惩治腐败的斗争中,德治和法治都是必须的,是惩治腐败中两种不同作用方式的社会力量,一种是把人们引向善和光明的拉力,另一种是迫使人们远离腐败漩涡的推力,两种作用方向一致,都向善。
2.德治和法治的关系是理想追求和注重现实的关系。德性的完善是有价值人性的追求目标之一,追求社会人伦的和谐则是人类的永恒使命和目标。人类跟政治中的腐败搏击了几千年,对腐败的控制却依然难见其效,但人们对政治文明理想状态的向往却从未停止过。这两者足以衬托出人们对腐败之害的深恶痛绝。在惩治腐败的过程中,德治的目的就在于追求一种政治活动中的纯洁,并试图以高尚的情操来涤洗人性中一切污浊的违背社会所倡导的道德要求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并经过不断的外界影响来弥合人们道德上的缺陷,以达到一种较完善的人格,最后实现腐败的自动清除。这种不诉求任何外在强制力量而实现的人类对腐败的自我超越是人类自己设计的美好途径和前景,是理想途径和理想状态的二合体。理想只能是对目标的一种预期,它不能决定人们对实现理想的具体手段的现实选择。鉴于德治在惩治腐败中做为手段的理想性性质,我们认为法治在惩治腐败中则是一种注重现实性的手段。一般而言,惩治腐败的法制制定得公正,并得到公正有效执行的国家,其腐败程度相对较轻,这样的国家也就更接近法治的国家。在惩治腐败的斗争中,我们国家对法治的乞援呼声日隆。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针对惩治腐败而提出的“法制是保证”就充分地反映了这一点。然而对问题的解决,需要将理想性和现实性结合在一起,即在惩治腐败中,既要通过德治这种理想性的手段来达到理想状态,又要通过法制的手法来达到现实的目的。
3.德治和法治的关系是治本和治标的关系。德治从本性上来说,就是通过反复的道德范导和榜样的道德力量来纯洁人们的心灵,努力使人们在道德上接近或达到一定社会所要求的道德境界,将外在的道德要求通过受教育者的体认来将这种要求内化为自己内在精神的需要,并外化为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惩治腐败中坚持德治就是使人们形成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自觉的不耻于腐败和不屑于腐败的意识、信念,并在自己的行为中一以贯之。只有当人们在心灵中克服了这种想腐败的意识时,腐败才算得到了最根本、最彻底的治理。尽管在现实社会中这是一项非常困难和艰巨的任务,但唯有如此,才能显示道德的魅力与崇高。法治是一种诉求于外的惩治腐败的手段,其效用机制是通过制定严密的法律制度,公正地执行法律制度,以法制的严惩来强化腐败者对腐败后果的恐惧心理,并通过严密的防范措施来缩减乃至消除产生腐败机会的可能性。但由于这种机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和内心信仰问题,因此,在那些法治无法治理或治理不力的地方,有些人由于道德水平不高和道德品质不好而乘机大搞腐败。世界上还没有也不可能有完善到能规范人的一切行为的法律,故法律只能治标。
分析惩治腐败中的德治和法治的关系,目的在于说明在现实的惩治腐败中,德治和法治都是必要的。在理论上这两者之间也并不是互相背斥的,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法以德导,德以法行。片面强调德治的作用只能滑向道德万能论和泛道德主义。而道德万能论不仅在历史上每每碰壁而且在现实生活中总是行不通。因为道德并不是万能的,它的发展进化需要经济、政治、法律、文艺、宗教等的支持和合作。因此,我们说道德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需要并离不开特有的经济支持、法律保障、政策依托和人文环境。同理,片面强调法治的作用只能导向法律万能论和泛法律主义,而法律万能论历史和现实证明也不过是某些法律爱好者或崇拜者的一种呓言罢了。事实上,法律同政治、经济和道德等因素也是密切相关的。就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而言,两者不仅在起源和发展上具有某些共同点,而且在内容上相互包含,作用上相互凭借。从历史上看,不论哪一个统治阶级,都是一方面借助本阶级的道德来为他们的法律规范及其实施进行辩护,另一方面又借助本阶级的法律来维护和推行他们的道德规范。法律与道德都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建立良好的社会制度的手段,道德“禁于未然之前”,法律“禁于已然之后”,道德可以用来防范尚未发生的违法行为,法律则可以用来制裁已经发生的违法行为。道德范导人心,法律范导人行,二者本质上都是为了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动物。对待法律与道德、法治和德治,重要的是将二者结合起来,使其互相促进。任何厚此薄彼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当代中国,惩治腐败离不开法律和道德两手,为了更好更有力地同腐败现象作斗争,既要坚持德制,又要厉行法制,把德治和法治有机地结合起来。标本兼治,才能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和道德文明。
收稿日期:2002-03-23
标签:人性论论文; 人性论文; 性恶论论文; 儒家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政治论文; 法治国家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法律论文; 孟子论文; 道德论文; 反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