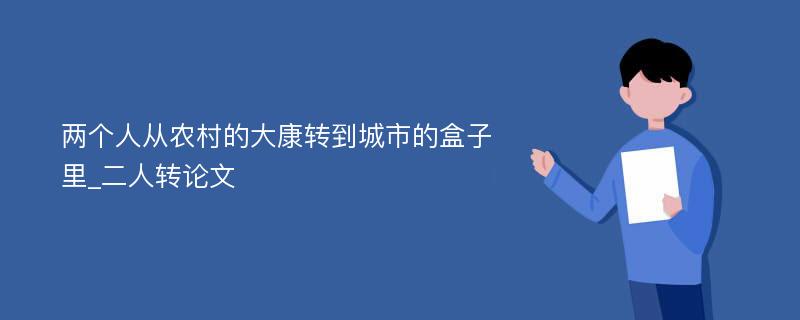
从农村大炕走进城市包厢的二人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人论文,包厢论文,农村论文,城市论文,大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何为“二人转”?
按照美学家王朝闻先生的说法,二人转“她好像一个天真、活泼、淘气、灵巧、泼辣甚至带点野性的姑娘,既很优美,又很自重,也可以说是带刺儿的玫瑰花”。“二人转”从白山黑水的东北土地上热热闹闹地一路走到今天,这种民间艺术形式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东北民间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足见其群 众基础之深厚。尤其是在东北农村,只要唢呐、锣鼓一响,顿时掌声四起,男男女女老 老少少把个临时的舞台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台上台下,一人唱众人和,那种如醉如痴、胜似狂欢的热闹场面,相信每一个初次见识二人转演出的人,都会久久难忘。它那粗 犷、通俗、火爆的表演风格,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性和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感,以及独特的表演程式和舞蹈,正是二人转艺术别具一格的魅力所在。因此,将其誉为“乡土奇葩”毫不为过。
作为东北三省(包括河北、内蒙古部分地区)的土特产,二人转生在民间,长在民间,发展成熟在民间。尽管,关于二人转的归属问题,即它究竟是曲艺、戏曲还是歌舞,至今仍众说纷纭,不过,在广大观众的心目中,似乎更关心的还是它的“好听、好玩、好看”,尤其是它的幽默风趣、直抒胸臆,最为大家激赏。随着时间的推移,二人转的影响和知名度越来越大,早已不再局限于田间地头,仅仅是农民自娱自乐的业余文化消遣,而是过关越岭,开始向大江南北辐射,越来越成为当今文化市场上的佼佼者。
由此,也不断引发出关于二人转的诸多争论,比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二人转是否还是原生态的二人转,东北喜剧小品与二人转,二人转的雅俗之争,二人转与东北文化等。
二人转的今昔
关于二人转的起源和成因,说法不一,二人转艺人自己总结是“大秧歌打底,莲花落镶边”。总而言之,二人转是集东北民间文学、音乐、舞蹈、表演和语言为一身,并开放性地吸纳更多姊妹艺术精华的独特艺术形式,其“唱、做、说、舞、绝”的艺术特质 决定了它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和强烈的艺术吸引力。
可以说,二人转之所以成为独树一帜的民间艺术形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民间”二字,即民间立场与民间情怀。尽管今天的城市观众已很难观赏到原汁原味的二人转表演,不过,从依然活跃在东北农村的民间剧团的演出盛况以及城市舞台上倍受瞩目的演出情形看,多少还是能反窥当初它火爆热闹、俏皮滑稽,特别是与观众紧密结合的艺术特征。二百来年了,二人转始终不曾退出民众的欣赏视野,不由人不叹服它与时俱进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近一两年,二人转频繁进京,或南下巡演,不断引起轰动,在各地的演出市场也常常制造出票房奇迹,例如在上海金茂大厦的演出就曾炒到2000元一张门票,仅从这些表面的受欢迎程度看,是否就能肯定,在终将成熟有序的演出市场中,二人转还能继续一路畅通地“转”下去?我们是不是也该考虑到这种文化消费现象一旦过热,就很容易引起我们的“审美疲劳”,到那时又将怎样面对?二人转的深入生活,贴近群众,注定了它与普通民众之间天生的亲和力,舞台上下的零距离接触使得演出现场始终保持着火爆热烈的气氛。但是,在充分照顾观众情绪的同时,是否也不容回避地存在着过度迎合部分观众的欣赏趣味而使之趋于流俗的现象?这点必须引起我们今天的二人转演员的足够重视,毕竟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还有着审美价值与审美趣味的前提,即便是以丑角取胜的二人转艺术也应遵循长期以来的“笨中求巧,丑中求美”的美学原则,而非一味地为丑而丑,毫无美感。增加技艺上的审美分量和优化、净化演出环境,应是当前的二人转演出必须迫切解决的问题之一。
繁荣背后,也连带着有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东北二 人转,究竟与原生态的二人转相距多远?历经几代艺人的创造和积累,二人转拥有300多 个传统曲目,如《猪八戒拱地》、《包公赔情》、《西厢》等,但时至今日,它们的传 承情况又是否乐观?从农村走进城市的二人转艺术,是否还完整保存着初始的淳朴与乐 观,在与城市观众的相互交流过程中,又发生着怎样的变化?二人转是最善于吸纳和借 鉴姊妹艺术的,草创时期如此,今天更是如此。然而,今日所见的二人转节目,在大量 的“拿来主义”、“为我所用”之后,却忽略了自身的优势,过去素有“九腔十八调, 七十二咳咳”的音乐唱腔以及“四功一绝”的表演手法已难得一见,几乎通篇的说口确 也能博得台下的阵阵爆笑,可笑过之后又能有多少回味呢?
东北小品与二人转
说到二人转的日渐兴旺并为全国观众熟知,就不能不提到东北小品;而说到东北小品,就不能不提到赵本山这个名字。自从1990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以小品《相亲》初次登上央视的屏幕,这个长相难看,经常佝偻着腰、蜷着腿走道儿,头戴一顶皱巴巴帽子的农民“徐老蔫”的形象便开始深入人心,而原本是东北二人转演员的赵本山也藉此一 炮走红,成为今天红极一时、炙手可热的著名笑星。“徐老蔫”之后,从“老乐”、“ 老香水”到后来的“妇女主任”、“村长”、“农民企业家刘老根”,一直到“吃饱了 撑的没事找人陪聊的快乐农民”和“靠卖拐、卖车坑人致富的刁民”,赵本山以其出众 的本色表演在当今的喜剧小品舞台上始终独领风骚,并随之带动了为数不少的东北演员 相继走入了全国观众的视线,成为颇受欢迎的喜剧演员,如潘长江、高秀敏、巩汉林、 范伟、黄晓娟等。
有人说:赵本山的成功本身就是个奇迹。其实,他的成功并非偶然。赵本山扮演过的所有人物形象,无一例外都是土生土长的东北农民,有着乐观憨厚、风趣狡黠的鲜明个性,除去他自身的表演天赋以及对角色的理解和再创造,有一点最关键的因素在于,他所依托的正是身后那片肥沃的黑土地积淀和蕴育出的丰厚营养,最直接的载体便是二人 转。事实上,由崔凯、何庆魁等创作的剧本之所以能为赵本山的表演提供坚实的文本基 础和预期的喜剧效果,同样来源于此。早年从事二人转剧本创作的编剧崔凯就说过,东 北喜剧小品源于东北二人转。与其说是赵本山征服了观众,倒莫如说是东北二人转打开 了局面,从而促成了东北风味的喜剧小品开始全面占领了电视和舞台。
不难看出,在风格独特的诸多东北喜剧小品中,从谋篇布局到刻画人物,从极具生活气息又引人发笑的人物语言到作品整体呈现的喜剧精神,都与二人转有着上承下袭的亲密血缘关系。我们不妨回味一下《相亲》里面徐老蔫一出场就合辙押韵的台词,扯东扯西又句句有包袱的对话,还有载歌载舞的《红高粱模特队》、《过河》等,透过语言层面的精彩,反观作品构思的新巧和表演的程式,最能体现直接借鉴于二人转艺术的特殊魅力,那些通常是白话、俗话、家常话的台词组合,却往往最能勾魂扎心,恰恰是外表的朴素,满含着内里的“俏皮和嘎拗”,令人过耳不忘,由不得你不击节赞赏。
如果说在这些东北风味的喜剧小品中,演员所表现出的非凡的语言功力一半还来自于作者提供的优秀文本的话,那么,直观呈现给观众的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就主要依赖于这些自幼浸染熏陶在二人转艺术中的演员,长期形成的不可多得的艺术悟性和驾轻就熟的表演功力了。正是二人转的丰富营养,提供给了作者和演员取之不尽的艺术灵感, 也奉献给观众无数欢笑的瞬间。因此,所有这些已经成名并且跨入明星级行列的东北籍 演员,常常由衷地感慨二人转艺术对自己的重要意义,相信绝非套话、虚话吧。
二人转名声响了,声誉降了
现如今,说到关于二人转的话题,恐怕最多的就是它的“雅俗之争”。二人转本身是没有颜色的,要说有,那也是大红的扇子、大红的手帕,和扇子手帕下舞动着歌唱着的红男绿女。而自打赵本山提出“绿色二人转”的口号,无形当中将二人转演出市场中存在的隐患揭露无疑。而2004年初央视喜剧小品大奖赛颁奖晚会上出现的赵本山“炮轰央视”事件,更是闹得沸沸扬扬,将这一争论推向了高潮。但是,仅仅靠表面的“绿色”就能改变二人转的现状吗?
以“土色土香,以俗见长”为特征的二人转艺术,历来就是俗文化的代表。而这里的“俗”,应是通俗、民俗的俗,而绝非庸俗、低俗的俗。人们对今天二人转演出(主要 集中在娱乐场所、光盘中)频繁出现的“粉词脏口”的厌恶和否定,其实也不是新鲜事 物。翻阅1959年和1964年由吉林省文化局编印的两本《二人转问题讨论集》,就能发现 ,其中半数以上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净化舞台、严肃台风以及廓清“说口”与“脏口”的 讨论。二人转的说口是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具有憨朴哏俏的健康品质”, 说到底“是对演员素质要求极高的‘脱口秀’”;而后者的油腔滑调、猥形亵态、污言 秽语绝对是应该摒弃的舞台丑恶现象。不能不说,那些为了取悦部分观众,迎合低级趣 味而出现的满台荤话脏口、穷耍恶逗,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二人转艺术的进一步发展,也 反映出今天的一些二人转演员的短视和贫乏。
作为从旧社会繁衍生息流传下来的民间艺术,难免存在一些与今天所要弘扬的时代风貌不甚相符的不和谐音,但为什么半个世纪前就已经讨论过并有过统一认识的问题,时 至今日仍然存在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或许我们更应该将思考的目光投向整个社会背景 和时人的整体心态。在演艺事业日渐步入市场化商业运作模式的今天,对于艺术品味的 追求难道真的不敌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吗?如今,二人转的名声是响了,可声誉却降了, 而一旦被认为缺了那些黄的、粉的、不着调的笑话就不是二人转了,将恶俗肉麻当有趣 ,岂不太辜负了这历经几代艺人艰苦磨砺而成的民间智慧之结晶?
俗与雅,本没有明显的界限之分,越是通俗易懂的越是蕴涵着深刻的思想,大俗即大雅嘛。不过,假若俗得没了谱,失了分寸,难登大雅之堂为人诟病也就在所难免了。
五、二人转与东北文化
关于二人转的研究论著,目前所见的多为对其历史沿革的考证和艺术本体的探讨,另有不少散见于报刊的独立成章的篇目,集中研究的是二人转的艺术特点,颇多真知灼见,但基本侧重于专业角度,其理论建构的影响面明显不足。对于二人转的理论研究,既应结合舞台实践,更应具备相应的理论高度和广度。余秋雨曾有言:“我的《中国戏剧文化史》有缺漏,书中重点介绍的剧目历史上没演过几场,而像二人转这样天天都在生活中演的戏却无法出现在大学的讲台上,无法出现在任何文字本上,这对我们学者而言是个耻辱。”话虽说得有点邪乎,不过倒也确实说明现阶段对于二人转的理论研究,与其火热的演出现状着实不相匹配。前一阵子,偶然读到东北女作家马秋芬的一本书《到东北看二人转》(湖北美术出版社2003年9月版),值得一提。整部作品以“我”的个人经历和观察视角作为贯穿线索,既有主观的回忆录式的叙事,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又有理性的学术分析和客观的新闻纪实。可以说,它既是关于二人转的大文化散文,也是一部以二人转为载体的东北地方文化史。无独有偶,另一位东北女作家素素的文化散文集《独语东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版)中,也曾以相当厚重而感性的文字记述了东北二人转的历史与命运。《移民者的歌谣》,笔端“既包含了对东北地域文化的眷恋和挚爱,又夹裹着某种历史的失意和怅惘,既体现出一种深情的体恤,又折射出某种婉转的对抗。”(洪治纲评语)
同样是用文学的视角,表现民间艺术与民族性格相生相融的际遇,两位女作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了最代表东北地域文化色彩的二人转艺术上,恐怕并非偶然。这是她们对东北文化的诠释和构建,也说明二人转艺术的历史发展和艺术表现形式,确实是研究东北历史、社会和民俗的极为丰富的资源。与此同时,研究东北民间文化对深入理解 当下不断变化中的中国大众价值观和审美口味也显得越发重要。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而 言,对于二人转的深入研究,也是对那些已经或正在发生流变的文化及艺术形式的重视 和关注,其独特的文化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国外学者对我们的秧歌和二人转艺术正在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而它们之所以能够在国际上被欣赏,即“在于它深深植根于东北百姓的精神品质之中,并有着强烈的地域性和世界共通性。它乐曲的‘闹’,舞姿的‘浪’和语言的诙谐不羁,正是真实百姓赋予它朴素的灵性,是在白山黑水、大寒大暑里积淀下的地域魅力。换一个国际的立足点来看,二人转不仅不土俗,它更带有一股民族的生命力和穿透力。”(于渺)
二人转曾是老百姓的书,一部《纲鉴》能从盘古开天辟地起头,一直说唱到改革开放和当下的现实生活,简直就是一本生动的历史教科书。二人转艺人时刻喷涌的激情和即兴的抓哏逗乐,给观众带来的无穷乐趣,更是深深植根于那片盛产大豆、高粱的土壤以及由此孕育出的埋藏在东北人血液里的从容和豁达,泼辣和风趣。二人转艺术的命运和走向,值得我们始终关注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