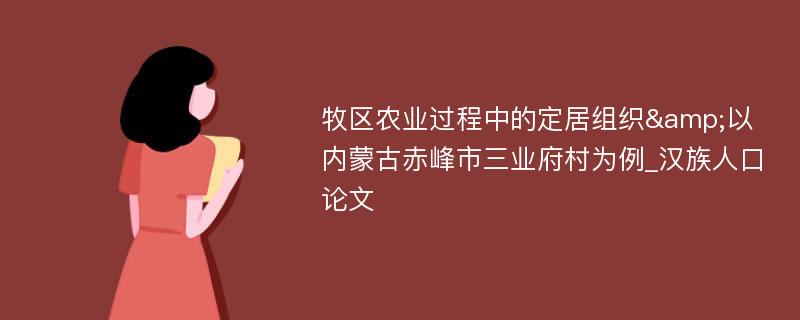
牧区农业化过程中的聚落组织——内蒙古赤峰市三爷府村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赤峰市论文,聚落论文,牧区论文,内蒙古论文,过程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所调查的村落是位于内蒙古赤峰市东北方向100公里的三爷府村,它隶属于翁牛特旗巴嘎塔拉苏木哈日敖包嘎查(汉名:黑塔子嘎查)。这是一个在草原上形成的农业聚落,它的四周是坦荡的荒野,只有村东头有一些略微起伏的土岗,全村主要耕地都集中于此。
三爷府村原来并不是一个农业聚落,而是一个纯牧业聚落。据乡民们说,到本世纪初,三爷府一带还是一片荒凉的草滩。民国初年,翁牛特旗王爷的三公子(姓名待考)领着七八个牧奴到此设立营盘放牧,此为三爷府村成立之始。这几个牧奴中,有一个汉旗牧奴,据说为村中苗姓之祖。直至解放(1947年),村中经济活动仍以牧业为主,蒙汉人口比例为7:1,农业活动微乎其微。
解放以来,情况有了较大的变化。在解放初期的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由于不断有汉族农民的迁入,农田面积有了较大的扩展,草场面积有一定程度的缩减,农业比重逐渐有所上升,但这一期间,牧业仍是三爷府村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从六十年代开始,草原建设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在“以粮为纲”的口号下,草场被大肆围垦,脆弱的草原生态平衡系统被破坏,盐碱化土地大面积出现;同时一些外流人口流到草原,滥挖药材,草场因此被严重破坏,造成草原退化,载畜力降低,严重影响了牧业生产,村民生活非常困难。直到1984年费孝通到黑塔子嘎查调查时,看到的是这样一番景象:“嘎查土地总面积四万亩中,草牧场三万多亩,牧畜五千三百九十头(只),比解放前增加了十倍半。耕地四千多亩,比解放前增加了近十倍。土地总面积是增加不了的,耕地增加则草牧场缩小,牧畜头数增加则每头牧畜的草料供应相应降低,这样就引起严重的草畜矛盾,降低了牧业效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多年强调‘以粮为纲’,大量种植粮食作物,亩产量不到百斤。1972年劳动日值下降到五分。所以从1963年起,一直到1980年,连续吃返销粮,到后来连返销粮也买不起,只能靠国家救济过日子。这种情况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大包干的责任制才得到扭转。”①从费孝通看到的情况,我们可以认定,直到1984年,三爷府一带还可以称得上是半农半牧地区,牧业生产仍占有重要地位。
九年后,当我们再次来到三爷府村的时候,看到的是一番截然不同的情景。在整个村落中,所养的羊只仅百余头,大畜寥寥可数,村民的经济收入全部指望着农业收成和经济作物(主要是葵花籽)。不多的几家专业户也主要靠养鸡的收入。在全村6000亩土地中,1500亩土地由于大面积盐碱化而无法利用;1000亩耕地中,只有640亩可以灌水;荒山草场3000亩,只能打草不能放牧。村民生活相当困难。牧业生产已基本消失,三爷府村已经彻头彻尾地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农业村。
不到50年间,三爷府村从一个纯粹的牧业村落,经过半牧半农、半农半牧,转变为纯粹的农业村落,这种由牧而农的转变过程,必然在村民的社会生活中产生相应的改变,其间的社会结构与组织形式也必然会发生变化。我们现在就来讨论一下这种由牧变农过程中的村落组织的变化。
一、人口及民族构成
三爷府村是蒙汉杂居村。现时的情况是汉族人数远多于蒙族,但解放初期情况并不如此:
表一 三爷府村人口构成变动表
1947年
1989年 1993年
总户数 17
70 70
总人口 93
319271
蒙族户数15
16 18
蒙族人口81
82 50
汉族户数 2
54 52
汉族人口12
237188
蒙汉人口比例7:1 1:31:4
(注:表中1947年和1989年数字出自包智明《变动中的蒙民生活》一文,刊《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1期。)
民族人口构成的变动不仅造成前述的社区经济生产类型的改变,而且在整个社会文化形态上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首先表现在语言的使用上。在三爷府蒙民家庭中,汉语的使用已是一种惯常现象,使用蒙语倒变成一种罕见情况。即使在使用蒙语的家庭中,父子两代人在语言能力上也表现出极不相同的情况。大致说来,40来岁以下的人,使用蒙语的能力越来越弱,而汉语水平越来越高;40岁以上一代人,双语使用都较为普遍,而从使用人数来看,汉语熟练的人不在少数。例如村中主要使用蒙语的家庭是吴国祥家,夫妻两人全系蒙族,交谈时全部采用蒙语;对儿子是蒙汉语兼用,儿子回话全是汉语,蒙语只能听懂不会说了;到孙子辈连蒙语也听不懂了,听说全部是汉语。
与语言情况相似的还表现在习俗上。除了在婚嫁时蒙民还保留拜火习俗外,在节令习俗和婚丧习俗上与汉族几乎没有差别。随着蒙民对喇嘛教信仰的普遍消退,宗教习俗对蒙民影响已经越来越弱。三爷府的蒙民汉民在文化上越来越趋于一致。
正是由于在语言、文化和经济生活上蒙汉民族的联系越来越趋于一致,民族交往越愈频繁,所以在两个民族间的通婚并不存在任何障碍。根据我们在村中调查情况来看,蒙汉通婚的家庭共有12户,占全村总户数的17%。其中汉-蒙通婚的(汉族家庭娶蒙族女子为妻)者6户,占汉族家庭的12%;蒙汉通婚的(蒙族家庭娶汉族女子为妻)也有6户,占蒙族家庭的33%,和1989年相比,蒙汉通婚的比例提高了两个百分点。
但是我们也发现,在1989年和1993年的户数和人口统计资料中,虽然总户数上都为70户,但无论蒙族汉族,人口数均成下降趋势。以1989年为100,1993年蒙族人口下降39%,为50人;减少32人;汉族人口下降15%,为271人,减少48人。人口变动的这种趋向的形成,固然有自然变动(即死亡)和婚迁因素在内,但更多的是机械变动(即迁移),而迁移的原因与经济条件的恶化密切相关。据我们对全村70户家庭的整体调查来看,全村无一户不借粮,无一家不借款,欠款数量少至一二百元,多至上万。连村中首富张孝也有万元以上欠款。入不敷出,收支无法相抵。加之近些年来农村赋税层层加码,农民苦不堪言。正是这种日趋严重的经济形势,造成村民们人心不稳,如,加工厂机械被变卖,房屋被拆;国家打的优质机井废弃不用(只是因为每年要交25元管理费),却家家户户花上1000多元去打小井,饮用含氟量极高的小井水等等。又加上农村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无法应付意外的灾害事故,而且该村又是个典型的近期移民村,各家庭之间缺乏十分密切的血缘和亲缘联系,无法以整体的力量去抵御灾害的侵扰。因此在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面前,整个村落呈现出一种无力的涣散局面。笔者认为,传统的农村社会的整合力量在于亲属组织(宗族和家族)的发达与否,而三爷府村并不发达的血缘——亲缘联系正说明整合力量对农村的社区团结力量的极端重要性。
二、农村牧区亲属组织的比较
在汉族社会这样的农业社会中,不能移动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产出构成农民家庭的主要财产来源。农民依附于土地上而不能随意移动,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农业社会的特点。首先是人与土地的固定联系构成了农业社会中稳定的血缘联系和亲缘联系,由此形成农业社会中十分发达的亲族与亲族组织;第二,由这种固定的血缘——亲缘联系又构成强烈的亲类意识,亲属组织形成一种等级分明,认祖同宗的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排外情绪;第三,认祖同宗的结果产生了对祖先的膜拜和对传统的强烈依恋感。但是,牧区的情况却与农业社会有很大不同。首先牧民所拥有的是可以移动的牧畜。因此牧民的迁移游牧便构成与农民和土地的固定联系的极大不同点,正是从这点上生发出牧区社会的许多特点。我们对牧区社会研究得很少,情况也不太熟悉,但是有些情况却是比较突出的。首先是牧区都是散点放牧,很少出现象农区那样的大聚落,因此牧民的社会联系大多数发生在家庭中;第二,正是由于游牧的特点,牧区社会中宗族组织和亲族组织很不发达,所起的作用也远不如农业社会,社会整合力量往往靠某种宗教的力量或是某些类似行政管理的组织。内蒙古牧区的社会关系我们尚未进行调查,但是我们可以以西藏自治区那曲县牧区情况为例做一介绍。
那曲牧区的藏民社会有八大特征:
(一)家庭类型以核心家庭占优势,扩大家庭则以主干家庭为主,联合家庭很少。因此从家庭规模看,小家庭多,大家庭少。家庭人口多数为4人,户均人口为4.3人。
(二)实行一夫一妻的单偶制,年轻人婚姻自由,很少受到父母的干涉。
(三)离婚自由,婚前及非婚性行为普遍。
(四)私生子多,且不受社会歧视,私生子与其他子女同样享有分配财产的权力。
(五)血缘关系的标志为骨系,其功能是规定通婚和非婚性行为的范围。
(六)家庭财产分配不受性别、年龄的限制。居住形式有从夫居与从妻居。
(七)继嗣制度以双系继嗣为特点。
(八)亲属关系松散且不稳定,宗族、家族对社会的影响力甚微。②
内蒙古牧区的蒙民社会虽然不一定都与西藏牧区的藏民社会完全相同,但是由于游牧和非定居形式是所有牧区生产的典型特征,因此西藏牧区社会与内蒙古牧区社会会有一定的共同性。我们从以上八个特点可以看出,牧区社会区别于农业社会的几个典型特征是:
第一,从家庭规模来看,牧区的家庭规模都不大,这种规模在今西藏和内蒙古牧区都有表现。牧区的家庭规模的大小直接受制于草场载畜力的大小,进而影响到牧民家庭的财产分配。农业社会中家庭规模远较牧区社会为大,家庭类型也多表现为扩大家庭。由于农业社会家庭规模较大,人口众多,因而在农业社会中逐渐产生出一些非农业的手工艺阶层,集市贸易得到形成和发展,因此出现集镇与城市聚落。
第二,牧区由于放牧需要,牧业性聚落规模都很小,各个牧民家庭都是独立自主地从事牧业劳动,因此血缘和亲缘联系并不发达,亲属组织的社会整合作用也并不大。相反,农村聚落规模远较牧区聚落为大,聚落内部人员互相往来频繁,亲缘群体、血缘群体和地缘群体对农民的社会联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由此形成农村复杂的亲属网络,从而控制和规范了农民的社会行为。
第三,由于牧区的亲属组织的社会功能远不如农业社会那般发达,因此就给两性之间的婚姻关系及婚前性关系的自由组合提供了方便。在牧区社会,妇女的地位自由度也较农业社会为大。在农业社会中,随着宗族、亲族和同乡组织的发达,对宗族、家庭的继嗣重要性的强调,性别差异有了极重要的社会功能,女子的自由度越来越受到传统宗法势力的束缚,男女之间不平等地位日益明显。同乡意识则进一步强化了与乡土的联系和感情,因而也就使排外情绪更容易被激化。
总之,从社会整合角度来看,农村社会是一种以明显的分层为标志的有序的等级社会;而牧区,由于其亲属制度不太发达,社会分层也不如农村发达,社会整合度也稍逊于农业社会。
三、三爷府村的亲属组织
从三爷府这个由牧变农的农村聚落来看,它既可能保留一些牧区社会亲属组织的痕迹,也可能随着农业化的进程而逐渐强化具有农业社会的一些特征。
三爷府村是个蒙汉杂居村,汉族大多数是解放以来(1947年)由赤峰南部农业区迁来的,因此三爷府村农业经营活动的发展以及由牧变农的转型与汉族农民迁入数量的增多有着密切联系。而蒙民是三爷府村的本地户,他们由牧转农是被动地与生产活动转型相适应的。在这种生产转型过程中,其原有的聚落组织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逐渐接近于汉族农村社会。
三爷府村的家庭根据户主的民族成份可分为汉民家庭与蒙民家庭。蒙族的姓氏已基本汉化,完全按照汉族命名方式命名,但并不是同一姓氏就是一个宗族,这一点与汉族农村社会有很大的不同。汉族由于大多数是移民,姓氏较杂,也并不是同一姓氏就构成一族,但从人口构成和家庭关系上看,汉族的宗族组织有一定的发展,但还不是那种支配全村的社会势力,因此汉民家庭和蒙民家庭都是以家庭和通婚关系为纽带构成家际社会交往的基础。应该说,汉民家庭组织的形成是农业社会的自然发展,而蒙民家庭组织的形成是在农业化过程中不断地强化通婚和家庭之间联系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在表现上蒙民的家庭联系与汉民的家庭联系略有不同。
在三爷府村70户家庭中,各种姓氏加起来共有20种。其中蒙民主要以金、朱、吴、鲍、孟、李六姓为主,而朱、金两大姓氏是蒙民中的大姓,据说也是最老的本地户,其先祖是随三爷到此设立营盘放牧的牧奴。汉民姓氏相当杂,有张、王、苗、于、孙、范、朱、欧、刘、陈、李、白、祝、金等14姓,在这些姓氏中,孙、张、于、王、刘、苗六姓为汉民中的大姓。
在研究三爷府村民的亲属关系时,首先值得重视的是蒙民家庭的亲属关系,他们的亲属关系的形成也是由牧变农过程中的结果。三爷府村蒙民家庭从代际上来看至多不过四代人,但是由姻亲关系结成的亲族系统却几乎可以把全村的蒙民家庭全部联系在一起,我们试以金姓家庭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在三爷府村,金姓家庭共分为两支互无血缘关系的家庭,这两个家庭又通过朱家结成远亲,因此,金朱两姓家庭构成村中蒙民家庭的主体。
在金姓两支家族中,一支是由11个家庭组成,另一支则是由1个家庭组成。这一户金家支系与另一支与金家有亲缘关系的朱家结成姻亲关系,而朱家又与孟家和吴家也有姻亲关系。这样以朱家为纽带,分别将两支金家、孟家、吴家联成互有姻亲关系的亲属网络,而金家又与鲍家连姻,这样除了李姓蒙族之外,其余所有的蒙民家庭都或近或远地结成了姻亲关系。因此,三爷府村蒙民家庭的亲属网络是以姻亲关系为基础结成的家族组织,其网络的形成原因在于村内的通婚联系。
和蒙民家庭相比,汉民的家庭联系要复杂得多。由于汉族多为移民,移入时间短,所以从代际关系上看多表现为一至两代人,至多为三代。汉族家庭之间的联系表现为两种亲属关系的重合。其一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宗族网络的形成,在三爷府村中有几支较明显的宗族组织系统,如刘姓和陈姓等姓组织起来的与村内其它汉民家庭没有姻亲关系的宗族系统;其二是宗族组织与家族组织相勾联组成的亲属网络系统,宗族关系实际上和家族网络连为一体,难分难解,较为明显的只有苗姓和孙殿成与孙世忠两支孙姓家族。正因为汉民家庭宗族势力并不发达,因此在三爷府村中尚未形成如大多数内地农村那样以“聚族而居”为特点的宗族村落,也没有形成以若干个大姓集团为中心的杂姓村落。三爷府村完全是个多姓村落,没有任何一个姓氏在村中形成颇具影响力的宗族集团,村落社区缺乏凝聚中心,家庭联系松散,社会整合度较差。
三爷府村汉民家庭既然缺乏以宗族为特征的亲属组织,那么能够构成村民家庭关系的另一个最主要的系统则是以姻亲关系为基础的家族组织。由于村中汉民人数较多,姓氏复杂,我们把全村的汉民家庭的亲族关系大致分为一大系与九个小支两个系统。这九个小支分别是祝姓、刘姓三支、李姓、陈姓、范姓和三支王姓(王山、王树、王久海),彼此之间互无通婚关系。
除了祝、刘、李、陈、范诸姓之外,其它汉民诸杂姓构成了一个互有远近亲属关系的大支系,在这个大支系中,可以以关系远近分为两大群体。其中,两支孙姓家族构成一大群体,张、王、于、欧、苗五姓家族构成另一群体,这两个群体又通过孙尚学家将两支孙氏家族和其余汉民诸姓家庭勾连起来。
三爷府村蒙民和汉民家庭关系基本上是以姻亲关系为基础构成的家族网络,宗教网络只是在汉民家庭关系中略有表现,并且也很不发达,远不能和内地汉族农村相比。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蒙汉民族各不相同。对于老地户的蒙民来说,由于三爷府的经济生产活动是由牧业逐渐向农业转变,其适应牧业生产的家庭游牧逐渐转变为固定的土地耕耘,家族间的联系由较松散的组织形式转变为较紧密的家庭关系,并且由于三爷府特殊的环境所造就的文化氛围使三爷府蒙族不愿意与外界操蒙语的蒙族通婚,因此村内通婚较为普遍,这种较密切的地缘——姻亲联系才使得蒙民的家庭联系得以加强。对汉族来说,由于大都是近期移民,姓氏繁多,且无血缘联系。因此就地通婚便构成了汉民家庭亲属网络的最主要途径。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在三爷府村这种复杂的亲属关系网络中,我们找不到一种可以凝聚全体村民力量的社会关系以维持全体居民对整个社区的认同;宗教意识的消退使得宗教力量无法成为社会认同的核心;短暂的迁移历史无法形成具有强烈归属感的血缘群体;原有的牧区因生产方式而形成的松散的亲属关系还在影响着已经农业化的原牧业聚落。因此,联系全村各住户的通婚关系在村民的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村中亲属关系的结成大都是以这种姻亲关系为基础。但是,由于姻亲关系的结成是以经济联系为柱石的,经济形势恶化势必对家庭关系产生严重影响。由此我们可以认定,三爷府村民精神上的无力感正是与整个村落缺乏一种社区整合力量,缺乏一种凝聚核心有关,而这种情况恰恰又是与原有的牧业聚落的社会组织相联系的。
四、邻里与社会网络
在农业社会中,除了亲属组织以外,给予农民社会生活以重大影响的要算是邻里关系了。邻里,按《现代汉语词典》所下的定义是“居住在同一乡里的人”,而邻居,据该字典的解释是“住家接近的人或人家”。邻里关系则是由若干个相邻的邻居组成。帕森斯指出:“生活方式相同的家庭邻接在一起生活比生活方式有较大差别的家庭这样生活在一起可能要舒服得多。因此邻居势必是一致的,而且‘较好的’邻居势必与‘不大合意的’邻居总是隔离的。”③在这里,帕森斯不仅强调了邻居构成的条件,更强调指出居住位置与邻里联系的重要性。因此居住的位置与邻里关系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试以前面所举的小井现象为例来研究村里的邻里关系。
前面说过,1982年,国家鉴于三爷府村水质含氟量较高,便投资打了一口深井,水质较好,用电泵抽水供应各家,每年各户交水电费25元~40元。吃到1990年前后,由于有些用户不交纳水电费,管水员时以断水相威胁。因此自1991年起,各家开始自己打小井吃水。据统计,全村打小井的家共有45户,另有25户没打小井,到邻居处去挑水吃。这样挑水关系就是显示各家关系好坏的标志。据我们分析,从这种挑水关系上大致可以反映出两种类型的家际交往类型:
(一)亲戚型关系:这种类型的打水家庭与有小井的家庭首先有着远近不同的亲戚关系,其次是居住的邻近。这种类型的家庭共有十对。值得注意的是,村内大部分没有小井的蒙民家庭大都去邻近有小井的且有亲戚关系的蒙民家庭打水,这倒不是什么特殊的民族感情所使然,而是因为蒙民家庭居住都比较集中,且大部分家庭都有亲戚关系所促成。
(二)邻居朋友型关系:没有小井的家庭去有小井家打水,绝大多数是本着就近的原则,很少有走远路去挑水的。但是就近并不等于说隔壁。许多家隔壁就有小井,却不常去隔壁家挑水,而常去几步路远的其它家去挑水,究其原因恐怕是多种多样的。逐一分析村内各家各户的诸种社会关系并非本文的任务,不过通过挑水关系我们却可以较清晰地了解村内部分家庭之间的交往联系,从而对村内的社会网络的构成有一概略的了解。
我们先看汉蒙家庭的交往。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三爷府村的蒙民家庭由于语言替换和与汉族的通婚,文化在逐渐趋同,蒙汉关系融洽,这种关系也表现在交往领域。我们从挑水关系可以看出,汉族的王、李、于、白、苗等家庭与蒙族的孟、朱、吴、金等家有着较多的往来,而蒙族的李姓则与汉族的刘家有密切的交往。这种交往的重要一点是基于邻里关系和地理位置的接近,正是由于这一点才使得双方互动频繁。所以巴恩斯说:“每个人好象都同其他一些人发生联系,而这些人有的彼此有联系,有的则没有联系。同样,每个人都有一些朋友,而这些朋友又有他自己的朋友;在某个人的朋友中,有些是相互认识的,有些则不相识。”④因此巴恩斯把这种复杂的朋友关系称为社会网络。在三爷府的村民交往中,不仅汉蒙之间有着这种密切的互动往来,汉民家庭之间同样存在着这种密切的社会联系。根据对村内汉民家庭之间的挑水关系,我们可以看出,陈、张、祝、于、李、白、欧诸姓家庭与王、张、孙、刘、陈、范诸姓家庭有着密切的交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祝、白、刘、李、陈及王树、王山等几户势单力薄的小姓与孙姓家族有着异乎寻常的密切关系,而诸小姓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往来。
这样我们对三爷府汉族村民的社会交往便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在三爷府汉族家庭关系中,除了由孙、张、于、王、苗、欧诸姓组成的一个关系复杂的亲属网络外,还存在着一个由祝、白、刘、陈、李、王诸小姓组织起来的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这个社会网络与孙氏家族有着密切的互动往来,并通过孙氏家族的关系汇入整个村落庞大而又复杂的亲属网络,从而将整个村落联为一体。
从三爷府村的整合组织的情况来看,三爷府村的社会组织有着不同于纯农业社区的村落组织的特征。在农业社区,社区的整合力量是通过某种诸如血缘联系、宗教信仰等稳固的组织为核心形成的。而在三爷府村,我们看到的并不十分紧密的通婚联系与松散的社区互动成为该社区整合中心,这种情况又一次使我们回想起牧区社会的诸种特征,回想起牧民的好客和喜爱交友的社会行为。我们依稀地感到,牧业社会的诸种特征至今仍在影响着已经农业化了的三爷府社会,使三爷府社会的诸种特征仍处在农业社会与牧业社会的交叉路口。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种不太发达的社区整合机制,所以才使得三爷府村的社会状况有着与农业社会不大相同的特点。
五、行政组织功能的消退对社区的影响
以上两节我们讨论的是建立在姻亲关系基础上的亲属组织和建立在地缘关系基础上的邻里组织,这两种组织都是美国社会学家库利所称的“首属群体”。在这种组织中,基本特征表现为密切的情感联系和频繁的互动往来。这节我们将讨论另一种性质截然不同的组织——行政组织系统。
行政组织与首属群体最大不同点在于它的科层结构。上下级关系不是建立在情感联系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服从的基础上。行政组织的运作靠的不是首属群体的互惠合作而是权力。因此这种组织在社会学上习惯地被称为“正式组织”。
应该说,从包产到户制度推行以来,农村行政组织的功能被大大削弱了。本来我们根据别处农村行政组织的状况也认定三爷府村的行政机构已经是一种虚设的行政机构,已经发挥不了多少作用。但在实际调查中我们却发现生产队时代人群之间的互动联系对现实生活的影响。
三爷府在公社化时代属于黑塔子大队第五生产队,这个生产队下又分为三个小组,分别称为北、中、西三组。这种划分一方面根据居住距离的远近,一方面又要考虑到彼此关系。因此组成人员在历史上有一定的变动。
大致说来,西组以居住在村西头的范洪杰、陈树丛、欧生、金宝忠、祝显和、孙继先、朱永深、张忠、张国才、王树、孙殿山、刘栋等户组成,而北组主要包括住在村北的王树、张贵斌、范洪林、欧树军、祝显扬、阿国风、李树林、王福来、陈树立、孙风忠、孙风杰、孙殿成、刘河、刘义、刘江、白显章、王福久、白国军、张吉存、张贵军、陈树林、孙尚学和陈俊。
从北组和西组的人员构成来看,汉族和蒙族的几个小姓家庭都比较集中地住在这两组中,这似乎表明,汉族的祝、白、刘、李、陈、王等小姓和蒙族的李姓是在比较晚近的年代才迁到三爷府村来的。当他们迁来时,现在村落中心已无地盘可供盖房之用,于是他们分别向村中的北头和西头发展,形成今日这种局面。尤其耐人寻味的是与诸小姓有密切往来的孙家也大都在这两个组中,因此社会网络的形成与行政组织的划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和北组、西组不同,中组所处的地理位置是村落的中心,全组共有35户人家。从亲族关系上讲,由于中组各户人家居住和迁移历史较早,彼此早已结成了或近或远的亲属关系,蒙汉通婚也比较常见,因此这个组是三爷府村的中心。
三个生产组的划分原来是为了生产和居住联系的方便而划出来的,但是,随着这种划分的固定化和长期化,村民的社会交往也被划定在一个有限的圈子里。一般说来,各户之间互动联系最多的是本组人家,连挑水一般也不越出本组人家之外。另外,由于中组的人自以本地户自居,而与后来户的北组和西组有隔阂,因此形成了整个村落中的“南北”矛盾。正因为如此,从1992年开始,全村三个组的划分重又取消,改成一个生产队的形式。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三个生产组划分的影响却不会因三个组合并而消失,并将会继续影响着村民的生活和社会往来。
六、结论
在本文中我们以社区整合组织(亲属组织、邻里组织和行政组织)为核心,试图解释在贫困农村都甚为少见的整个社区的不安情绪。在由牧而农的转型过程中,社会的转型也不可避免。但社会转型的过程较经济转型为慢,其表现就是其亲属组织严密化的程度远远达不到农业社区的那种程度,仍表现为较为分散的亲属联系。社会凝聚核心尚未形成,因此社会整合程度较低,这是三爷府村村民精神涣散的最主要的原因。另外,由于以前行政划分所造成的三个生产组之间的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会的整合度。因此,强化行政管理以促进村民之间的团结,增强社会的凝聚力,是克服这种涣散局面的唯一出路。
注释:
①费孝通:《边区开发·赤峰篇》。
②包智明:《藏北牧区亲属结构》,北大社会学所存档。
③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和过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208页。
④巴恩斯:《挪威教区的阶级和委员会》,转引自R.E.安德森、I·卡特:《社会环境中的人类行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8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