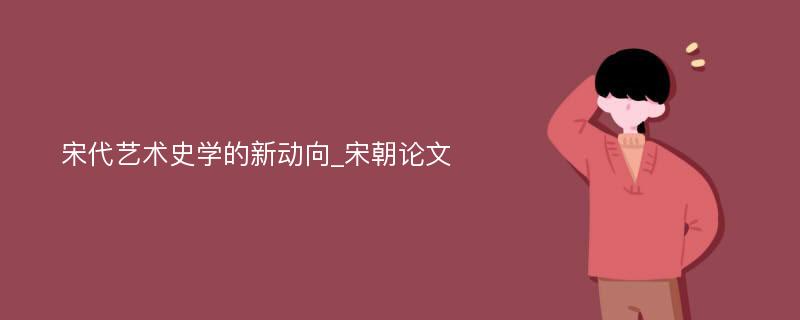
宋代美术史学的新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宋代论文,美术论文,新趋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675(2007)02-0025-08
陈寅恪曾经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中国史学莫盛于两宋。”[1] 美术史学也并不例外。宋代美术史学受当时繁荣的史学背景的影响,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向。
一、官方美术机构的完善对宋代美术史学的直接影响
首先,对宋美术史学产生显见的、直接影响的是宋朝官方美术机构“翰林图画院”的完善和官方绘画教育机构“画学”的建立和发展。
我国早在汉代即在宫廷设有“少府”,另有“画室”、“画工”和“署长”,称画家为“黄门画者”、“尚方画工”。[2] 唐开元初年(713),翰林院添设了“术艺”待诏一职。[3] 唐末,朝廷中已出现授予御用画家以翰林待诏、翰林供奉等职称的做法。
唐末战乱,促使西蜀成为五代绘画艺术的中心。与绘画中心的转移相应,前蜀王建统治时期(907-918年),已在此建立了“内廷图画库”。到了前蜀后主王衍统治时期,画艺更是被朝廷所重视,凡能画之士尽被网罗于宫中。[4] 明德二年(935年),后蜀孟昶创建了西蜀“翰林图画院”,用以容纳御用画家和掌管宫廷绘画事务,并于院中设待诏、祗候等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画院。几年之后,南唐也于保大元年(943年)建立了翰林图画院。
西蜀和南唐画院的建立对绘画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画院的建立,提高了画家的地位,画家的生活有了保障;画院有“每月议疑”的规程,促进了画家间的相互交流。在这样的条件下,画家之间的联系,以及其独立性和创作能力得以加强;画院不但集中而且也培养了一些绘画名手。一些有成就的画家,他们的成就大都直接影响到了北宋的绘画。后来许多画家入宋,成为北宋前期的重要画家。
至迟于太宗雍熙元年(984年),北宋已经设立了翰林图画院。[5]“元丰改制”(1078-1085年),翰林图画院由“院”改名为“局”,与天文、书艺、医官合称“翰林四局”。[6] 进入画院的专职画家由推荐或考试后授职,分为待诏、艺学、祗候、学正四等,未定职称的统称为画学生。这种体制化的行为不仅笼络了绘画人才,而且为绘画的交流和切磋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西蜀、南唐的宫廷画家纷纷进入宋朝画院。一些民间的绘画高手也被选拔进来,这样一来,各个地区、各个阶层的绘画技法在画院中得到融会贯通,并进一步发扬光大起来。
宋代画院规模之大、画师地位之高、院画家成就之显著、院体画之影响深远都远逾于五代的西蜀、南唐。邓椿《画继》卷十有这样的记载:“本朝旧制,凡以艺进者,虽服绯紫,不得佩鱼。政、宣间独许书画院出职人佩鱼,此异数也。又诸待诏每立班,则画院为首,书院次之,如琴院、棋、玉、百工皆在下……又他局工匠,日支钱谓之食钱,惟两局则谓之俸直。勘旁支给,不以众工待也。”这是说徽宗朝优待画师,其实,北宋初年也对入宋画家给过较高待遇,南宋高宗、孝宗时,得“赐金带”的画家,就不下二十余人。
崇宁三年六月(1104年),宋徽宗又于翰林图画院之外别开“画学”,将“画学”纳入神圣庄严的科举制之中。
与画院不同,“画学”是专门的绘画教育机构,纳入国子监教育系统,有完善的教学制度。
《宋史》徽宗本纪称:“画学”置“博士一员”掌其事,米芾、宋迪先后任画学博士。又据《宋会要辑稿》崇儒三大观元年二月十七日条云:“诏书、画学论、学正、学录、学直各置一名。”可知画学博士下另有画学论等四人执教学、管理职。
与以往招募的只有一技之长的画工有别:“画学之业,曰佛道、曰人物、曰山水、曰鸟兽、曰花竹、曰屋木。以《说文》、《尔雅》、《方言》、《释名》教授,《说文》则令习篆字、著音训,余书皆设答问,以所解艺观其能通画意与否。乃分士流、杂流,别其斋以居之。士流兼习一大经或一小经,杂流则诵小经或读律。考画之等,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笔韵高简为工。三舍试补升降以及推恩如前法,惟杂流授官止自三班借职以下三等。”[7] 太学三舍试补、升降及推恩制度是宋代科举制度的补充办法,也被运用到绘画人才的招募上。由于画学的建设,正是“以太学法补四方画工”(俞成《萤窗丛说》),“画工”得以增强文学修养,宋画的文学化遂成时代潮流,邓椿所言“画者,文之极也”实宋代绘画的时代风貌。
此外,翰林图画院作为内廷供奉机构,虽与专门的绘画学校国子监画学性质不同,但究其实际,亦兼具教育之功,北宋后期更与“画学”有密切关系。如《画继》卷十杂说论近云:“又画院听诸生习学”,反映了画院学生习艺学艺的情况。
大观四年(1110年)三月,“画学”并入画院,画院正式代替“画学”,兼任起教育和培养绘画人才的职责。[8]
宋代绘画正是在中央政府的重视和官方美术教育的促进下,在宋“郁郁乎文哉”的文化环境中,取得了其他朝代无可替代的成就。宫廷美术、民间美术、文人美术在此朝分野。世俗美术的发展和宫廷绘画的繁荣,使绘画题材更加广泛,风格多样。山水画进入黄金时期,流派林立,技巧上有不少创新。花鸟画亦迅猛发展,出现了“黄家富贵,徐熙野逸”的迥异风格。人物画也开始朝着新的方面迈进,水墨人物、风俗画、历史故事画都颇为兴盛。
与绘画的繁荣发展相应,美术市场蓬勃发展。当时“画行百姓”众多。一些有名的画工甚至有了“版权”意识:“每作一扇,必画数百本,然后出货,即日流布,实恐他人传模之先也。”(邓椿《画继·卷六人物传写·刘宗道条》)可见书画市场之繁荣。
绘画创作的活跃和绘画收藏鉴赏风气的发展促进了绘画理论的繁荣。由于画师文化修养和地位的全面提高,使宋人得以留下了大量高水平的绘画理论建树。
宋代在绘画理论方面,无论是门类的齐全,体例的完整还是观点的深刻,都堪称是中国古代美术史上的典范。宋代不仅出现了绘画通史性著述诸如郭若虚《图画见闻志》,邓椿《画继》、陈德辉《续画记》,还有地方性画史诸如黄休复《益州名画录》以及评传体断代史诸如刘道醇《圣朝名画评》;甚至还出现了著录性官修画史诸如《宣和画谱》、《秘阁画目》,著录及装裱裁制专著如《思陵书画记》,以及类书《太平广记》、《太平御览》,专门的山水画论诸如郭熙、郭思《林泉高致》、韩拙《山水纯全集》,以及评鉴专著诸如米芾《画史》、李廌《德隅斋画品》、董逌《广川画跋》、张澄《画录广遗》……,此外,在大量的丛辑、诗文、笔记、正史、野史、题跋中,涉及到绘画理论的更是不胜枚举,许多重要的绘画理论观点即散见于文人笔记之中。
宋代绘画著述虽然在数量上无法与明清相提并论,但更具有经典性。宋代美术理论在诸多方面显示出了自己的特点,提出“诗画本一律”命题的是宋代、“逸品”的确立是宋代、文人画理论的形成是宋代、最早的地方美术史的编撰和绘画分科史的出现是宋代、山水画理论的成熟也是宋代……更为重要的是,宋代美术在观念上发生了转捩,从艺术的功能、创作的要求到鉴赏的标准,从历史的评价到现实的导向,宋代与隋唐相比,都有许多不同之处。这一时期绘画理论所提出的一些观点,成为中国古代美术理论的主要内容,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代画院及“画学”的建立和兴盛,为中国古代画学思想走向全面成熟创造了良好的契机,它结束了绘画艺术过去只在民间传承的状况,开创了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先河。由于中央政府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参与,从理论和学术上大大提高了美术创作、研究和教育的水平,促进了大量的美术历史文献的产生,从而不可避免地对当时和此后中国美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复杂的、多方面的历史影响。
二、方志的成熟和其对美术史学的渗透
宋代,走向成熟的方志也开始向美术史学渗透。
方志是地方志书的总称,发轫于春秋战国。最初的方志,无论是体例内容,皆属地理书。魏晋南北朝时期,晋挚虞的《畿服经》增述“先贤旧好”等人物事迹,从而开创了方志记载人物的先例,兼备史、地两性。隋唐两朝,全国出现“盛世修志”的局面,“图经”盛行。所谓“图经”,发轫于东汉;开始多以图为主,表示疆域、山川、土地;经是图的说明,是图的附属物,一般是一图一经的体例。[9] 隋唐时期,“图经”已以经为主,图为辅了。但此时我国第一部官修总志隋代的《区宇图志》仍然“保存着一图一说的图经古制”[9]:“卷有图,别造新样,纸卷长二尺,叙山川则卷首有山川图,叙郡国则卷首有郭邑图,叙城隍则卷首有馆图。”著名的唐代《元和郡县图志》也是“每镇皆图在篇首”[10],仍保留一图一说的体制。
宋是中国方志事业走向成熟的时期。当时国家非常重视地方志的编纂,以至于朝廷于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专门“创置九域图志局,命所在州郡编纂图经”[11]。这是我国设立志局的最早记载。此专门修志机构还设有属员。[12] 北宋时,各名都大县都有志书,全国有600多种,早在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翰林学士李宗谔主纂《祥符州县图经》问世,共1566卷,集历代编修图经之大成,是我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部有统一类例的图志总集。南宋修志一改北宋时奉诏官修的形式,私人修志盛行,不仅名都重邑皆有图志,而且僻陋偏小之邑,亦必有记录。
宋代方志从偏重地理记载转向人物、艺文、政事的记录。唐以前的志书,强调的是“版图地理之为切也”,对于人物和艺文等历史方面的内容,涉及不多。北宋史学家乐史(930—1007)编成举世著称的《太平寰宇记》200卷,增加了人物艺文方面的内容,使地方志体例从地理学中脱离出来,《四库全书总目》说:“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史。”[13]
正是受全国方志事业蓬勃发展的影响和方志本身从偏重地理记载向人物、艺文、政事的记载的转型的影响,我国第一部地区性绘画史籍《益州名画录》诞生了。《益州名画录》作于1105年,距朝廷“九域图志局”的设立(1107年)仅两年,可以想见那时全国的方志事业正如火如荼中。
《益州名画录》又名《成都名画记》,其作者黄休复,字归本,一作端本。北宋初年人。久往成都,通《春秋》学,兼精画学,收藏甚富,景德中著《益州名画录》三卷。《益州名画录》是一部记述唐、五代至宋初以西蜀寺院壁画创作为主要内容的地区性画史。共收自孙位至邱文晓五十八人的小传及其手笔写真外,另附有画无名及无画有名者之记录。此书依靠寻访壁画遗迹来积累编写史籍的资料,故较为翔实可靠,为研究五代西蜀地区及画院的绘画活动,以及对宋初画院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开创地区性绘画史籍的体例。此后,在此书的影响下,后世不断出现地区性绘画史著作,仅成都地区就有如宋代范成大著《成都府古寺名笔记》、元代费著著《蜀名画记》、明代曹学佺著《蜀中名画记》、近人罗元黼编辑《蜀画史稿》(1917年成都存古书局出版)、薛志泽编著《益州书画录》(1945年成都崇礼堂印制)、江梵众、陈蓉峰撰写了《清代蜀中画家传略》(1956年)等,别处尚有如明朝周晖《金陵画品》、茅维《南阳名画表》、徐勃《闽画记》等陆续问世。
方志的成熟,不但直接促进了我国第一部地方性绘画史的诞生,还间接的对我国山水画的创作和理论的成熟产生了某些影响。
中国山水画脱胎于方志中的图经。中国古方志中图经中的图多数都是以山水画形式存在的疆域图,地形图和示意形式的城池图,衙署图等:“直到清代,一般官绘地图还是画着山水和注着四至道里等等。”[9] 至于宋之前《区宇图志》这样的名志,“‘其图上山水城邑题书字极细,并用欧阳肃书,即率更令询之长子,攻于草隶,为时所重。’可见,图上的字是请书法家写,想必图也应是画家所绘。”[9] 正是我国山水画与图经这层渊源关系,使得我国山水画理论从诞生之初,就是在与图经的比较中进行阐述的:“夫言绘画者,竟求容势而已。且古人之作画也,非以按城域,辨方州,标镇阜,划浸流。本乎形者融灵,而动变者心也。”(王微《叙画》)山水画应在人们“披图按牒”时,“效异山海”。当山水画走向百代标程的宋代,人们仍然不忘记将图经作为山水画的参照物:“千里之山,不能尽奇,万里之水,岂能尽秀……一概画之,版图何异。”(郭熙《林泉高致》)正因为有图经这个参照物,才会迫使人们进一步的思考如何创作出有别于图经的山水画,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山水画的艺术自觉。
此外,在隋唐“盛世修志”的局面下“图经”盛行,一图一说的图经古制,引起人们对山水的广泛关注,这无疑促进了山水画的发展。而两宋时期,随着方志的体例逐渐形成,图由主体渐而演变成附庸,图经已经不再是一图一志的古制,山水画从图经中基本转移出来,不再肩负起存照的文献性任务,山水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此时才真正获得普遍的艺术上的独立自由。只有在这种自由的前提下,才可能有马一角、夏半边,以及米芾的米点云山这种艺术游戏的出现,才可能有《林泉高致》、《山水纯全集》这样的系统、完整的山水画论著的出现。
三、笔记体杂史对宋美术史学的贡献
笔记源于先秦。《论语》、《晏子春秋》等被认为是笔记体的早期形态。四库馆臣认为:“杂说之源,出于《论衡》。其说或抒己意,或订俗讹,或述见闻,或综古义。后人沿波,笔记作焉。”[14] 由于笔记体著作的主要特点是形式随意、内容广博,或信笔所记,或聊备遗忘,所以笔记体的著作有许多的异名,如丛谈、笔谈、随笔、札记、丛录、琐谈、见闻录、新语、客话等等。在古代四部图书分类法中,与笔记有关的图籍因其内容不同,分别归于“史部·杂史”、“子部·杂家”或是“子部·小说家”。唐代,修史之风大盛,有些史学家就把一些异闻琐事用笔记形式著录。史学家的这种做法,使得笔记与志怪传奇小说逐渐分头发展。
宋代笔记内容更广泛,志怪成分更少(李肇《唐国史补》中志怪成分尚占10.1%左右,而宋的《归田录》中的志怪成分只占2.6%左右[15]),笔记体全面成熟。
由于宋笔记体走向全面成熟,以及宋文人广泛的参与绘事活动,不但许多重要的绘画理论于文人笔记之中熠熠生辉,许多重要的绘画史料也仅赖此流传。
宋人著名的笔记不胜枚举。正是在不拘类别、有闻即录之间,作者记录所涉上至达官贵人,下及里巷细民,几乎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又因为笔记多为私人撰述,记事少忌讳,其史料价值弥足珍贵。《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总叙》说:“考私家记载,惟宋明二代为多……然虽有疑狱,合众证而质之,必得其情……其有裨于正史者,固均宜择而存之矣。”[16] 王世贞称:“野史……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要了解宋代美术史学的整体情况,宋人笔记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本文重点介绍《梦溪笔谈》和《铁围山丛谈》,以管窥豹。
《梦溪笔谈》是北宋沈括(1031-1095)所著的一部重要笔记。沈括,字存中,武康人。元祐元年,沈括在今江苏镇江修建梦溪园。《梦溪笔谈》因写于润州(今镇江)梦溪而得名。26卷,又《补笔谈》3卷,《续笔谈》1卷。涉及政治、经济、科技、医药、文学、艺术等多种学科。
《梦溪笔谈》卷十七为书画篇,阐述了沈括对书画的评价标准和美学思想,包括中国文人画理论中的“雪中芭蕉”论、“画弦声与画管声”论、“画意不画形”论、“以大观小”的透视规律等等。
从《梦溪笔谈》中可以看出,宋代的画家创作时“理”字当头,不但讲究生活之理,更求画理。如该笔记记载以猫眼及花色鉴别画中花为正午牡丹的故事,正是当时画家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的真实反映。而光凭对生活的观察是不够的,还需加入创作者理性的思考。《梦溪笔谈》中记载,相国寺内高益所作的“众工奏乐”壁画,“人多并拥琵琶者误拨下弦。众管皆发四字,琵琶四字在上弦,此拨乃掩下弦,误也。余以为非误也,盖管以发指为声,琵琶以拨过为声,此拨掩下弦则声在上弦也。益之布置尚能如此,其匠心可知。”
《梦溪笔谈》还提出了“雪中芭蕉”的美学命题,提出了“造理入神”,不以“形器”求“书画之妙”的审美原则,对文人画的形成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理论支持。他的理论与同时代欧阳修、苏轼等的绘画理论是一致的。在当时“一时所尚,专在形似”(邓椿《画继》)的时风下,他们“画意不画形”,追求客观形象之外的意境的审美原则,影响所及,不仅左右了元、明以来的画坛,而且一直延续到现在。
除此之外,沈括还提出了“以大观小”的透视理论,这是中国绘画史上首次用这一理论解释山水画的散点透视问题。宋代李成在画中“仰画飞檐”,沈括嘲笑他是“掀屋角”。沈括说:“李成画山上亭馆及楼塔之类,皆仰画飞檐,其说以谓自下望上,如人平地望塔檐间,见其榱桷。此论非也。大都山水之法,盖以大观小,如人观假山耳。若同真山之法,以下望上,只合见一重山,岂可重重悉见……李君盖不知以大观小之法。其间折高、折远,自有妙理,岂在掀屋角。”
从《梦溪笔谈》中,我们还可以订正美术史料上的一些讹误。如《梦溪笔谈·卷四·辨证二》中记载世人在绘画雕塑时何以多拿韩熙载的形象偷换韩愈的形象。
除了家喻户晓的《梦溪笔谈》外,尚有一些其他的宋人笔记,提供了许多的美术史料,如《铁围山丛谈》、《云麓漫钞》、《容斋随笔》、《皇宋事实类苑》、《声画集》等等。
《铁围山丛谈》是宋代蔡絛所著的一部有名的笔记体史料书籍。其作者蔡絛为蔡京季子。该书给我们展示了相当多鲜为人知的内容,对研究宋代尤其是北宋后期历史有相当价值。四库馆臣评论该书称“其人实不足道,而其书尚有足取者,以其久直中禁,所记徽宗时一切制作始末,究与传闻者不同,故多足以资考证焉”[17]。由于其“久直中禁”,故其所记宋徽宗事乃亲见亲历,成为研究徽宗及徽宗书画的重要史料。《铁围山丛谈》卷一有徽宗师学渊源的详细记载。此外,《铁围山丛谈》还说明了徽宗在位时,为什么各业艺人名声显著,而唯独画家不显的原因:“太上皇(指徽宗)在位,时属升平,手艺人之有称者……此数人者,视前代之伎一皆过之。独丹青以上皇自擅其神逸,故凡名手多入内供奉,代御染写,是以无闻耳”[17]。此外,《铁围山丛谈》还有几则关于书法和文物收藏的内容。如卷四168条提到了徽宗书画藏品;169条《古器说》详细的描述了宫廷令人编撰《考古图》、《宣和博古图》的经过,提到徽宗时重金收集三代礼器,于是天下墓冢破筏殆尽。秦汉间的文物除非特别好的,一概弃而不收,毁坏文物不计其数,至于发冢所毁更无法计算。《铁围山丛谈》书中其他如卷一记九玺之源流,元圭之形制,九鼎之铸造,三馆之建置,卷二记大晟乐之宫律,卷四载米芾《辨颠帖》、宣和书谱画谱之缘起等,都详尽记载了一代之典章文物,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一定程度上可补《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等之缺漏。
其他宋笔记体杂史著作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美术史料,如从赵彦卫的《云麓漫钞》中,我们可以窥见宣和书、画学的审美评判标准;从洪迈的《容斋随笔》中我们可以了解古代颜料都出自何方,使用了什么颜料;从江少虞编撰的《皇宋事实类苑》我们可以窥见北宋初秘阁藏书画的情况;从孙绍远编著的我国最早的一部题画诗总集《声画集》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唐宋绘画的演变,以及唐宋画家活动、创作、交往情况等等,本文不再赘述。
四、美术史学思想的萌芽
虽然唐人张彦远已经开始了对前人美术史著述的批评,然而,他并没有形成自己明确的美术史学思想。
张彦远对于前人的著作,贬损过分,没有给予适当的评价。他说:“后汉孙畅之为《述画记》,隋沙门彦悰,唐御史大夫李嗣真、秘书正字刘整、著作郎顾况,并兼有画评。中书舍人裴孝源有《画录》、窦蒙有《画录拾遗》,率皆浅薄陋略,不越数纸;僧悰之评,最为谬误,传写又复脱错,殊不足看也。”张彦远所举各书,有全部亡佚的;有全书已佚,但在《历代名画记》中尚有部分引用的,如孙畅之、李嗣真、窦蒙等;有原书尚存,并绝大部分被《历代名画记》引用的,如谢赫、姚最、彦悰等。至裴孝源所著,张彦远名曰《画录》,《图画见闻志》则曰《公私画录》,现在所存则为《贞观公私画史》。张彦远又说:“昔裴孝源都不知画,妄定品第,大不足观。”但查现存的《贞观公私画史》只是部分录唐代所藏各种官本,并未加以品第,是否裴氏另有一书,已不可知。张彦远既然批评各家的书“浅薄陋略”,甚至说彦悰的书“最为谬误”,但在《历代名画记》的画家传中,却全部引用了他们的著作,甚至有些传完全是他们的评语,张彦远却一字未加。就是“最为谬误”的彦悰的书,也全部引用。既然说“殊不足看”,而自己又大抄特抄,全部抄入自己的著作里,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张彦远在引用各家文字中偶尔加以批评,如曹不兴、卫协、顾恺之、宗炳、王微、沈粲、丁光、嵇宝钧、王定、康萨陀等传中,间亦提出不同的见解,但在全部引用书目中,其批评所占的分量甚少,可见这些书,并不是“浅薄陋略”到“殊不可看”的地步,也不是“最为谬误”到毫无价值。因此,张彦远虽然已经有了美术史学批评的自觉意识,但是他并没有形成他个人的美术史学思想,这种无的放矢的批评也就显得苍白乏力。
真正的美术史学思想的萌芽,是从宋代开始的。当时宋的美术史学的编著受大的史学环境的影响,在美术史学的著述方法上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向。比如成书于1006年的《益州名画录》,作者在记述画家和作品时,基本不进行艺术分析,而在篇首《目录》中,首先揭出“逸、神、妙、能”四品,并对其各自的特点,用精简的文字加以说明,以作为评定画家艺术成就高下的标准。《四库全书》称“其书叙述颇古雅,而诗文典故所载尤详,非他家画品泛题高下、无所指据者比也。”此外,黄休复是依靠寻访壁画遗迹来积累编写史籍的资料的:“故自李唐乾元初至皇宋乾德岁……取其目所击者五十八人,品以四格,离为三卷,命曰《益州名画录》。”(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序》)因此,书中对这一时期寺院壁画的名目、内容、年代、配列、构图、绘画特点等方面的记载,都是本人亲身采访所得,较为翔实可靠。黄休复的实学精神,比郑樵(1103-1162)提出以实学治史,早100多年。而成书于1071年以后的《图画见闻志》亦在书名上明确了作者的史学立场:“见闻”。尽管如此,作者还是被其后续者邓椿(约1107-1178)[18] 抓住了把柄:“(盖)见者方可下语,闻者岂可轻议?尝考郭若虚《论成都应天孙位》,景朴天王曰:‘二艺争锋,一时壮观。倾城士庶,看之阗噎。’予尝按图熟观其下,则知朴务变怪以效位。正如杜默之诗:‘学卢仝马异也。’若虚未尝入蜀,徒因所闻,妄意比方,岂为欧阳炯所误耶?然有可恕者。尚注辛显之论,谓‘朴不及位远甚’,盖亦以传为疑也。此予所以少立褒贬。”[19]
有鉴于此,邓椿在进行他的《画继》的写作时:“予作此录,独推高、雅二门,余则不苦立褒贬。”邓椿“不苦立褒贬”的史学观,与他的同时代伟大史学家郑樵“不任情褒贬”的史学观有着惊人的一致。在当时宋内忧外患(忧患意识必然会激起一种责任感,表现在历史撰述和史学思想上,则是强调史书的资治作用)以及理学对史学的强力影响下,盛行春秋褒贬笔法(如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和范祖禹的《唐鉴》,都既是史学著作,又是言理的著作,非常重视运用《春秋》书法褒贬史事)。郑樵却反对春秋笔法,视任情褒贬为“欺人之学”。郑樵认为五行灾祥之说不能真正解说历史的发展与变动;同样,史书运用所谓的《春秋》笔法任情褒贬,也是不能如实反映历史的发展与变化的。他斥责前者为“欺天之学”,而斥责后者为“欺人之学”:“凡说《春秋》者,皆谓孔子寓褒贬于一字之间,以阴中时人,使人不可晓解,‘三传’唱之于前,诸儒从之于后,尽推己意而诬以圣人之意,此之谓欺人之学。”[20] 郑樵认为《春秋》只是“纪实事,主在法制,不在褒贬”,他反对史家作史自撰论赞的做法,他说:“纪传之中既载善恶,足为鉴戒,何必于纪传之后,更加褒贬;此乃诸生决科之文,安可施于著述!”[20] 他视这种任情褒贬之文为“决科之文”,而非史家之“著述”。可见,邓椿和郑樵,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他们不妄加褒贬的史学观,对于史学的成熟发展,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而邓椿由于是美术史学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其史学思想的人,在美术史学的发展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标签:宋朝论文; 美术论文; 北宋山水画论文; 宋代绘画论文; 历代名画记论文; 艺术论文; 铁围山丛谈论文; 文化论文; 图画见闻志论文; 春秋论文; 梦溪笔谈论文; 林泉高致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