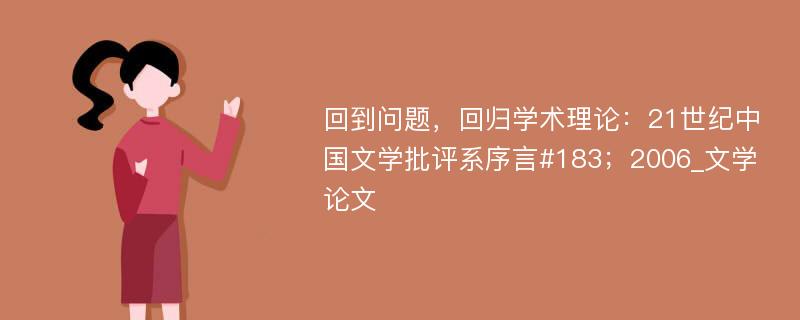
回到问题,回到学理——《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183;二○○六年文学批评》①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学理论文,大系论文,六年论文,二十一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二○○四年文学批评》的序中,我曾经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离当代文学学科化的目标有多远?这自然是一个现在还无法准确回答的问题。在阅读和编选《二○○六年文学批评》时,我回溯了前几年的编选工作,掩卷之余,不免有些兴奋。可以说,今年的批评选是我到目前为止最满意的一个选本。这样说,并非突出我所做的编选工作,而是指二○○六年的当代文学研究是新世纪以来最富成效的一年,它所呈现的状态以及由此预示的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路向,都是值得我们重视和检讨的。
我做出这样的评价,无疑是依据了我对当代文学研究的两个期待,或者说是一种学术理想的选择。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化包含了多方面的因素,但我认为是否能够面对文学研究中的“中国问题”以及如何在学理层面上阐释这些问题是不可缺少的两个“考核”标准。显然,我们不必过多地纠缠“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或者“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在“西学”已经差不多成为我们文学研究的基本的知识背景和方法时,我们的文学研究无论如何也要警惕自己成为西方话语的转述。现在比较紧迫的任务是,批评家或者学者教授需要重视理论阐释“中国问题”的能力。所以,如何贴近中国文化语境,如何贴近文学史,如何贴近文本,如何去伪存真,在发现问题中,提炼出若干关键性的命题并且加以阐释,是当代文学研究近年来的一个趋向。以我自己的阅读来看,学术研究中的“伪问题”实在太多了。“伪问题”的存在和炒作,会制造许多热闹非凡的场景,也会制造出无数学术泡沫。为什么许多论文的意义会稍纵即逝,为什么许多论文在发表之初就失去了学术的意义,为什么许多论文的影响力难以持续?我想,这恐怕与问题的提出和命题的概括不当有关,“伪问题”和“假命题”自然与学术价值无缘。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我想直截了当地说:文学研究和文学写作一样是需要沉潜的。“伪问题”的产生,自然不只是个学术研究的态度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研究者的学术能力问题。如果再作进一步的深究,今天的学术生产方式和学术评价制度也催生了学术泡沫化现象。当我们能够认真面对学术研究中的“中国问题”时,我们究竟有怎样的学理背景又如何在学理层面上阐释问题,就会成为一个“焦点”。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再到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变化,便是学院化学科化。逐渐形成的学术制度未必合理,但其中对文学研究学术化的要求应该不宜否定。我不赞成把学术与思想分开,也不认为一旦学术化就会放弃“问题”与“思想”,相反,我觉得文学研究中的许多问题之所以讲不清讲不透,正是因为缺少了学术的力量,或者学术研究的路径错位。
因此,文学研究的“内部”问题实际上是与学术生态的建设有关。如果从媒介的角度看,当代文学研究是与会议场景、批评杂志和大学的文学教育紧密相连的。我无力对这三个大的环节做出深入的考察,但我可以说些若即若离的话题。在当下的文学研究中,学术会议几乎成为主渠道之一。今天的学人很少不是会议中人,这与当代社会文化结构的新特点有关。学术会议和新闻媒体的结合,一方面扩大了研究的影响力,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常常把文学研究“话题化”、“现象化”和“新闻化”。我也是个不断与会的人,而且通常是一个倾听者。从去年开始,我在思考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学术会议的有效性,即研究的对象是否有效,会议上的讨论是否有效。因为,只有把“有效性”的品格突出出来,才能有效地制止“泡沫化”现象,才能不是制造话题而是讨论话题。大学、杂志社、作家协会之类的组织通常是这些会议的组织者,也承担着有效性的责任。正是怀有这样的想法,我会拒绝一些会议,也会组织一些会议。以我自己的经验看,“会议”作为一种学术生产的方式或者学术研究的场景,正在朝一个有利于良好的学术生态形成的方向转换。收在《二○○六年文学批评》中的不少论文,都是一些会议的学术成果。比如,关于长篇小说文体的讨论,关于贾平凹、莫言的研究等文章,关于媒体与文学教育的文章等。据我所知,关于《秦腔》、《碧奴》、《兄弟》、《笨花》等作品的讨论都有可观的成绩——这一现象传递了当代文学研究学术转向的部分信息。
收在《二○○六年文学批评》一书中的论文,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和特点值得我们关注:
一、关于长篇小说的文体研究。如何看待长篇小说写作,是考察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的一个重要视点这个栏目中的文章,除了张承志、苏童、铁凝的外,基本上是渤海大学会议上的笔谈。当长篇小说成为当下最流行的文体,也成为印刷数量最大的出版物时,它日益暴露出来的问题已经无法回避,几乎可以说我们需要关心长篇小说。其中多数文章又出自作家之手,因此更多地触及到长篇小说写作中的具体问题,更多地表达了小说家自己的甘苦、困惑和期许。由这些基于个别经验的论述,从不同侧面追问了长篇小说写作的普遍性问题。莫言的《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尤其值得一读,这是继当年“保卫先锋”之后的一次“捍卫”。
二、关于作家作品的研究。这部分的工作是当代文学研究的基本层面。本栏目中的论文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文学史的视野,如陈思和的《从鲁迅到巴金:新文学精神的接力与传承——试论巴金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和孙郁的《莫言:与鲁迅相逢的歌者》,都体现了写作者在文学史论述中研究作家作品的学术个性;陈晓明的《本土、文化与阉割美学》,论述了从《废都》到《秦腔》的贾平凹,同时也有批评家自身的反省。二是多元的声音。关于王安忆《遍地枭雄》、余华《兄弟》和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等作品都是引起关注而无定评的作品,本书中的几篇论文,呈现了批评家理解的差异。不少作品的争论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而且逐渐沉淀下来,应该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了。王安忆的文章总是有自己的看法和表述的特点,《城市与小说》亦然。王鸿生的论文是他的系列研究之一,其理论与方法的意义需要我们留意。
三、文学思潮与文学史研究。这部分内容是本书的两个重点。韩少功的讲演录举重若轻,纵横捭阖,其穿透力再次显示了一个思想者的智慧和责任。他的每次发言,都让我们感叹有“想法”的作家太少了。南帆的论文把一个已经存在但始终没有说清楚的问题论述得周详透彻,做了系统的“知识考古”;王光东的论文深化了他在“民间”领域的研究;张清华以“时间修辞”论当代文学的美学演变,其理论品格令人赞赏。关于文学史研究的几篇论文,可以视为本年度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王晓明的论文是他的学术转向文化研究之后的力作,大气而深刻;陈平原在他的文学与大学研究之间找到了一个点,别开生面;郜元宝的论文带来的争议已经超出他所批评的三本文学史之外。这些论文的价值从不同层面显示了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品格。
诗歌研究、文学传媒研究及海外汉学研究的论文虽然没有成为文学批评的主流,但它们同样不可缺少。我在几年的文选中始终保持这几个栏目,是企图重视和强化这样的研究。和八十年代不同,今天我们对海外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接受已经有成熟的学术立场。这次入选的《中国文学(一九四九—一九九九)的英译本出版情况述评》是一篇重要的文献,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当代文学”在“西方”。
回到问题,回到学理——这是我对二○○六年文学批评的印象,也是我对新一年文学批评的期待。
注释:
①《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二○○六年文学批评》,林建法主编,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