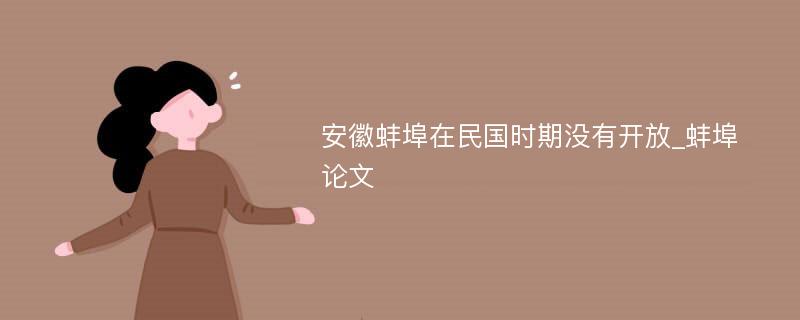
民国时期安徽蚌埠并未开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蚌埠论文,安徽论文,民国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中国的通商口岸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帝国主义国家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而被迫开放的商埠,通常称为“约开口岸”或“约开商埠”,上海、广州、天津、汉口、重庆、芜湖等城市均属于此类。在这些口岸,列强通常设立租界,攫取领事裁判权、土地承租权、行政管理权、关税权、警察权、市政权等特权。另一种为中国政府自行宣布开放的通商口岸,通常称为“自开口岸”或“自开商埠”。由于自开商埠系中国政府主动开设,此类商埠的主权当然完全归诸中国政府。它们概不设立租界,其土地所有权、行政管理权、警察权等统归中国官厅掌握。这一类商埠有吴淞、岳州、南宁、武昌、济南、浦口、郑州、无锡等城市。如果存在民国时期安徽蚌埠开埠史实,那它应当属于第二种类型。
自开商埠始于清末。它本系清政府为了阻止列强的觊觎而主动采取的举措。为了强化自开商埠的管理,清政府出台了一些相关法规,但这些法规均带有地方个案色彩,未具普遍性指导意义。民国肇建后,随着自开商埠的地方愈来愈多,规模愈来愈大,民国北京政府倍感制订统一法规的必要。1915年内务部会同农商部、财政部、税务处等部门共同草拟《自辟商埠开办章程》,修正后经大总统正式公布。依据这一章程,各自开商埠设立商埠局进行管理;划定商埠范围,商埠局测勘商埠四至界址,绘具详细图说,咨明本省最高行政长官派员勘定并报内务部核定;商埠局常年经费由中央承担,但市政建设等事项经费须自行举办税源解决;商埠内可设立海关等机构;本国人与外国人均可居住贸易,但外国人以商埠界内为限,界址以外不得租赁房屋,开设行栈等①。
现在的问题是:民国时期蚌埠到底有没有开埠?关于这一问题,史学界现存两种说法。一种认为,随着1912年津浦铁路全线贯通,蚌埠即已开埠,如《蚌埠市志》一书提出“民国元年,蚌埠开埠”②,此说得到部分学者附和③。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蚌埠开埠于1924年9月,著名经济史专家、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严中乎先生力持此说④。不难看出,前一种观点所提“开埠”的含义系指津浦路通车以后蚌埠开始有了近代商业贸易,并非开设通商口岸之谓。后一种观点中的“开埠”则特指开设与列国通商的口岸。对前一说法,笔者并无异议。后一说法则值得商榷。本文拟就此作一讨论。
关于此说的依据,严先生只是在所列《商埠表》后笼统地指出此表系依照各种有关年鉴、海关报告、经济所所藏档案资料制成,并未开列蚌埠开埠说法的具体资料来源。90年代,《近代史资料》总第85号发表了张洪祥、周德喜两位先生整理的《近代中国自开通商口岸史料》一文,其中一则为《近代中国自开通商口岸一览表》,也强调蚌埠于1924年实行开埠⑤。此表系译自日人英修道于1939年所撰的《中华民国有关列国条约权益》一书。因严中平先生为国内近代经济史研究权威,其说法往往为学界所认同⑥。
笔者认为,这一说法缺乏铁证,不值得采信。
揆诸有关史料,蚌埠确曾于上世纪20年代初谋求开埠。蚌埠原为安徽凤阳县境内濒于淮河的一个市集,清中叶前后一度兴盛,清末遭受战乱破坏,沦为淮河岸边的小渔村⑦。1908年津浦铁路动工兴筑时,仅有一条南北长不足百米的土街,茅屋数十间,人口仅百余人,纯为“一荒凉之乡集耳”⑧。随着津浦铁路1912年底全线通车及1914年前后安徽督军行署等军政机关设于蚌埠,蚌埠自1916年前后开始腾飞,商贸、市面、人口等迅速超越皖北大镇正阳关与临淮关,崛起为皖北第一商贸重镇。1918年,著名地理学专家林传甲曾称蚌埠“俨如一新省会”⑨,上海《申报》也誉之为“小上海”⑩,长沙《大公报》更坦言“蚌埠乃不特为皖省政治之中心,且隐然为北京政治之策源地”(11)。随着蚌埠在军事、政治、地理、商贸等领域上影响力日趋扩大,蚌埠自开商埠的议题开始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从目前史料看,最早提出蚌埠自开商埠的是安徽省议会,时间大约在1921年上半年,据《申报》报道:“蚌埠自开商埠,前经皖省议会议决,俟该埠开凿船塘工程告竣后自开商埠。船塘工程,自上年三月破土开掘,全工至今已得八成余。……本年……秋后工程可望结束。现经实业厅会同蚌埠塘工事务处妥议,将接续自开商埠。”(12)后因军政格局频繁变化,自开商埠一事始终停留在议论阶段。1923年上半年,皖籍国会议员常恒芳等人致书大总统黎元洪,请将蚌埠开为商埠,并恳请特派前安徽都督柏文蔚为督办。内务部等机关审议后即致函安徽省长公署,称“查原函所称各节,自系为发展商务振兴实业起见,惟该处自津浦火车通行后商务已日渐繁盛,究竟现在有无开辟商埠之必要,相应抄录原函咨行贵省长详细查核见复,以凭办理。”(13)安徽军民两署获知后,即咨请内务部将蚌埠请开商埠案提交国务院合议。7月初,国务会议允准蚌埠自开商埠,并于同月2日任命泾县人、在上海经营纱厂的资本家程源铨为蚌埠商埠督办(14)。10月27日,蚌埠闻人唐家骥被大总统任为蚌埠商埠会办(15)。12月12日,督办程源铨自上海来蚌埠就职,即以淮泗道尹办公处为临时局所,着手组织(15)。1924年4月,有关方面公布《蚌埠商埠暂行编制章程》18条,蚌埠商埠局改称蚌埠商埠督办公署,并相继任命各科科长及各股股长,管理机关的组织已基本完善(16)。上述一切似乎昭示蚌埠开埠业已呼之欲出了。
那么,其后数月尤其是1924年9月,蚌埠有没有正式全面开埠呢?答案是否定的。
前已述及,自开商埠属于中央政府行为,牵涉内务部、农商部、财政部、外交部等部门。它的开办,不仅是当地重大政治事件,也是国家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大事务。正因如此,各地自开商埠从筹备、开张至运作等举措,往往成为各主流媒体争相报道的内容。各报刊关于各地所开商埠的报道、通讯俯拾即是,前引蚌埠开埠筹备阶段的诸多报道也足以证明这一点。可是,遍查1924年发行的各主要报刊,均找不到蚌埠正式全面开埠的任何记载。不仅上海《申报》、上海《民国日报》、北京《晨报》、天津《大公报》、天津《益世报》、长沙《大公报》等全国性大报对此毫无记载,而且《东方杂志》、《国闻周报》、《政府公报》等全国性大刊也没有一星半点的反映。1924年8月下旬至9月下旬,各报有关蚌埠的记载非常多,如天津《大公报》,1924年8月27日发表《蚌埠杂讯》,各类新闻有十几条之多;9月2日,又发表了驻蚌记者8月31日所作的《蚌埠军事短简》,所记至为详细。上海《民国日报》这一时期也发表了大量涉及蚌埠的报道,其中该报1924年9月13日发表了驻蚌记者9月11日所作的蚌埠特约通信《蚌埠市况调查》,此新闻稿件较长,对8月下旬以来蚌埠的金融、交通、商业、军事、实业、学务等作了详细报道。如果蚌埠确曾于1924年9月1日开埠,上述新闻应当会有记载。而现在找不到任何佐证,惟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蚌埠并未在1924年正式全面开埠。
另外,划定商埠四至,确定商埠范围,是商埠正式开设的先决条件之一。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正式开埠也就无从谈起,所以1915年《自辟商埠开办章程》第3条规定,商埠局设立后应组织人员测勘四至界址,绘具详细图说,咨明本省最高行政长官派员勘定并报内务部核定。1923年冬蚌埠商埠督、会办就职后,安徽省长公署根据内务部咨文,特此致函蚌埠商埠督、会办,要求勘定埠界,拟订各项章程,以便转报主管部、署(18)。但测勘界址,既需要人手,更需要经费。其时民国北京政府及省政府财政竭蹶,连军费、政费都难以正常发放,欠饷数月甚至半年以上成为司空见惯之现象,根本没有钱拨付商埠公署。商埠公署成立初期,机关内工作人员每月薪水及办公费约支5000元之谱,“均由督、会办挪垫”(19)。由于长期缺乏经费保障,程源铨心灰意冷,不愿问事,随后提出辞呈,商埠的各项事务事实上处于停顿状态,直至1926年4月,王世澄接任蚌埠商埠督办一职,状况才有所改观(20)。王世澄不仅提出了安徽省第一个城市规划——《蚌埠商埠全部计划》,而且派出工作队,测量商埠四至。1926年8月29日中共蚌埠特支曾向中共南京地委报告蚌埠各方面情况,其中提到“现正在计划开辟商埠,已测量妥当”(21),可见蚌埠开埠,划定四至界限,直至1926年下半年才举办妥当。这条档案材料为1924年蚌埠并未开埠提供了铁证。
此外,1926年3月底,蚌埠商埠督办公署呈请内务部、财政部等部门,经内阁会议核定,将原先兴建新船塘而向商户征收的塘工捐改为商埠捐,继续征收,以充商埠公署常年经费。鉴于新船塘早已竣工,许多商户对塘工捐改为商埠捐提出异议。3月30日蚌埠总商会开会,其中部分商户提出“实际各商埠成例,均系由国家承担商埠常年经费,商埠捐必在商埠成立后凡在商埠区域内经营商业者负担”(22)。此则材料表明,蚌埠商埠此时并未成立,所以大家有抗议的理由,这也从侧面佐证了蚌埠1924年并未开埠。
那么,1926年蚌埠商埠划妥四至界限后,有没有正式开埠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
原来,1926年8月,北伐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北伐的对象之一就是控制长江下游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安徽作为孙传芳的势力范围,也深深卷入战争漩涡。社会激烈动荡,正式开埠只能搁置。1927年北伐军占领蚌埠后,由于政权更迭,存在数年之久的蚌埠商埠督办公署无形中取消(23)。而在国民政府时期,随着现代市政的兴起,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均热衷于开设市政机关,对开埠已不再感兴趣。1929年3月,蚌埠市政筹备处成立(24),年余后筹备处被撤销,市政事宜由蚌埠市公安局兼理。此时蚌埠更不可能开埠。1933年底,省政府建设厅长刘贻燕为《一年来之安徽建设》一书作序时指出:“本省市政设施,以经费无着,未能有大兴土木之举,只以安庆为省会所在,芜湖为唯一商埠,其市政之兴废,有关中外观瞻,故各设工务局,择要兴筑。”(25)可见蚌埠这时并非通商口岸意义上的商埠,安徽全境只有芜湖配此称谓。此外1934年出版的《安徽通志稿·外交考》一书,在“外交考·商埠”一目中,也指出:“本省交通之埠三,有已设并开埠者一,芜湖是也。有初允停泊上下客货旋允开埠而迄未开者一,安庆也。有但允停泊上下客货者一,大通是也”(26),对蚌埠根本未提及,说明蚌埠至1934年一直未开埠。数年后,抗日战争爆发,蚌埠沦入敌手,直至1945年8月才获得新生。1945年11月蚌埠市政筹备处再度成立。1947年1月1日,蚌埠正式设市。
综上所述,蚌埠1924年并未开埠,其后亦未曾开埠。总之,民国时期蚌埠开埠之史实并不存在。
①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列强在中国的租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568页;《无锡商埠局暂行章程》,载《安徽公报》第1539期,1923年9月13日出版。
②蚌埠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蚌埠市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③郭学东编著:《蚌埠城市史话》,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④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48页。
⑤《近代史资料》总第8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3页。
⑥杨天宏:《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95页;何一民主编:《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40-1949年)》,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2页。
⑦于万培等修、谢永泰续修:《凤阳县志》,光绪十三年刊本,“卷三·舆地志·市集”。
⑧李品和:《概述》,载《蚌埠市政筹备工作报告》,蚌埠市政筹备处1946年编印。
⑨林传甲:《大中华安徽省地理志》,中华印刷局1919年版,第188页。
⑩《蚌埠大火纪详》,《申报》1919年4月17日。
(11)《蚌埠近讯》,长沙《大公报》1920年3月12日。
(12)《蚌埠自辟商埠之沪闻》,《申报》1921年7月31日。
(13)《皖赣开辟商埠问题近讯》,《申报》1923年6月24日。
(14)《皖省政闻杂志》,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8月17日;《皖闻纪要》,《申报》1923年7月20日。
(15)《大总统令》,《安徽公报》第1578期,1923年11月1日版。
(16)《蚌埠开辟商埠近闻》,天津《大公报》1923年12月30日;《蚌埠商埠局组织近讯》,《申报》1924年2月18日。
(17)《蚌埠开埠积极进行》(4月16日蚌埠通信),《晨报》1924年4月19日;《蚌埠商埠局进行之忙碌》,天津《大公报》1924年3月15日。
(18)《函请拟订各项章程送由省公署转咨核办由》(安徽省长公署公函第687号,中华民国12年11月20日),《安徽公报》第1598期,1923年11月24日。
(19)《蚌埠开埠积极进行》,《晨报》1924年4月19日。
(20)《蚌埠短简》,《申报》1926年4月12日。
(21)《彭芝关于蚌埠政治经济概况的调查报告》(1926年8月29日),载中央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合编:《安徽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1册(1922-1927年),1987年内部发行,第272页。“彭芝”即中共蚌埠特支的谐音代号。
(22)《蚌总商会开会纪》,《申报》1926年4月3日。
(23)1927年12月10日,蚌埠各界举行庆祝讨伐唐生智胜利大会,数十团体到会,未见商埠公署,见《蚌埠庆祝胜利大会》,《申报》1927年12月20日。1928年4月5日,蚌埠举行市民大会,到上百单位,仍未见商埠公署,见《蚌埠昨开市民大会》,《申报》1928年4月7日。
(24)《蚌埠成立市政筹备处》,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3月26日。
(25)刘贻燕:《序》,载《一年来之安徽建设》,安徽省政府建设厅1933年11月编印。
(26)安徽通志馆编纂:《安徽通志稿·外交考》,“商埠”,1934年铅印本。
标签:蚌埠论文; 上海开埠论文; 安徽崛起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蚌埠崛起论文; 开埠论文; 历史论文; 清朝论文; 大公报论文; 申报论文; 民国日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