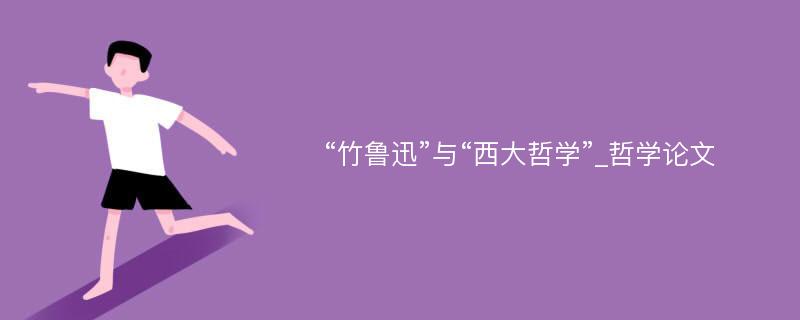
“竹内鲁迅”与“西田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田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0.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7X(2013)03-0125-05
竹内好(1910~1977),作为日本现代杰出的思想家和鲁迅研究学者,他关于鲁迅研究所阐发的思想和研究的方法论,被日本学术界习惯称之为“竹内鲁迅”,其中最能体现“竹内鲁迅”精神的就是1944年出版的《鲁迅》。这部著作在对鲁迅“本源”性的“无”、矛盾性的“混沌”和“挣扎”的“行为”探寻等方面,与“西田哲学”有着深刻的精神联系。竹内好最初提到与“西田哲学”的关系是在1952年再版自注中,他指出:“由西田哲学借来的词汇随处可见,它们是来自当时读书倾向的影响,以今日之见,是思想贫乏的表现。”[1](P134)足见,“竹内鲁迅”深受“西田哲学”的影响。
西田几多郎(1870~1945)被誉为“日本近代最大的哲学家”,其哲学被冠以“西田哲学”。“西田哲学”在当时吸引了众多青年,因为“西田哲学的根本动机,在于探索‘人生的问题’,在于通过这一问题来‘捕捉深邃的生命’”[2](P131)。显然,“西田哲学”与现实人生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的历史矛盾和社会矛盾,与思想极度苦闷的知识阶层产生了强烈共鸣,这正是竹内好接受西田的哲学思想的基础。由此,西田的哲学思想深刻影响了他对鲁迅形象的重塑。
“西田哲学”无疑包含很多丰富而深刻的内容,其中,“直接的最根本的”东西在概念上的表现就是“纯粹经验”、“行为的直观”和“绝对矛盾的自我同一”[2](P133)。可以说,这三者在一定意义上,最为突出地凝括了西田哲学的根干部分或主体部分。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来探讨“竹内鲁迅”与“西田哲学”的精神联系。
一、“本源”与“无”的逻辑
对“本源”或根本问题的追问是竹内好与西田几多郎共同的思想倾向和本质特征。竹内好在谈到他研究鲁迅的目的时说:“我想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为鲁迅定位。我想知道的并不是思想、作品、行动、日常生活、美的价值,而是在本源意义上究竟是什么造就了这多种多样的东西。”[1](P80)西田几多郎在论及自己的哲学研究时指出:“我的目的是,彻底从直接的最根本的立场来观察事物思考事物。对一切事物都把握一个由彼及此的立场。”[2](P133)
在《鲁迅》中,竹内好苦苦追寻的是“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原理”。他指出:“鲁迅的文学,在其根源上是应该被称作‘无’的某种东西”[1][P58],认为鲁迅“本源”的“无”的东西渗透在作品之中。他说,“《野草》各篇极端的独立,但这种独立又反过来以非存在的形式暗示着一个空间的存在。就像一块磁石,集约性地指向一点。这是什么呢?靠语言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勉强而言的话,那么便只能说是‘无’。”[1][P99]
应当说,以追究“本源”为旨趣的思想者,在近代不乏其人,海德格尔等存在主义哲学家自不待言,像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也很有代表性。西田几多郎对于“纯粹经验”的阐发,正是基于这一立场。所谓“纯粹经验”,就是意识现象直接感觉到的经验,实指未加思辨的经验的本来状态。西田几多郎认为,只有“纯粹经验”才是唯一真正的实在。它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是超越个人、超越主客观对立的更为根本的东西,在他看来,“主观与客观不是互相分离而存在的,而是一个实在的相对的两个方面”[3](P59)。然而,这一实在却是不可名状的,不可用概念表述,它的形态“正如我们的心灵被美妙的音乐所吸引,进入物我相忘境地,觉得天地之间只有一片嘹亮的乐声那样,这一刹那便是所谓真正的实在出现了”[3](P45)。这个实在的真景犹如禅师“见道”时的“知与理冥、境与神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之状,实质是一种“物我相忘”的“无”的境界,其中禅的意味非常浓重。“纯粹经验”这个概念是青年时期的西田几多郎在不断“打坐”而获得的“禅”的体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概念是“禅”体验的逻辑表现[2](P168)。也可以说,“西田哲学的出发点是‘禅’,‘禅’是他的人生观,也是他的思想方法论”[4](P330)。而“禅宗”第一要义就是“无”。
西田几多郎崇“无”,以“无”为万物本原[5](P457),而他用“意识现象”和“纯粹经验”表述“实在”,实质是用哲学解释“无”。“无”,构成了西田哲学的逻辑基础。在他那里,贯穿于自然万物和内在意识的统一力本身就是“无”,即“纯粹经验”和唯一的实在。但是,“无”并不等于没有,在西田看来,“无”就是“有”,“有”就是“无”,二者融为一体,相互转化,在对立中包含着统一,西田的“无的逻辑”就是建立在这一“辩证法”的立场之上。在西田的后期著作中,他提出了“场所”的概念。“场所”被他划分为“有的场所”、“相对无的场所”和“绝对无的场所”三个逻辑层次。他对此解释道:“在被限定了的有的场所上可以看见动者,在相对无的场所上可以看见意识作用,在绝对无的场所上可以看见真正自由意志。”[6](P322)在西田看来,“真正的哲学并非存在于意识之中,而是在打破了自我之后才出现的。”[7](P531)他认为,“绝对无的场所”超越了有与无的对立,它是主观与客观、自我与非我得以产生的根本。“西田哲学”这一思想,同样渗透在竹内好的《鲁迅》之中[8](P109)。
竹内好在谈到鲁迅的著名讲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时指出,鲁迅说无力的文学应以“无力”的方式来批判政治,也就是特殊的“沉默”方式,在他看来这种“沉默”就是“批判的态度”。他写道:
说沉默是批判的态度,是说沉默即行动的意思。沉默是行动。作为对行动的批判,其本身就是行动。这是相信不仅语言是实在,没有语言的空间也是实在。使语言变为可能的,同时也会使语言的非存在变为可能。有,如果是实在的话,那么,无也就是实在。无使有成为可能,但在有当中,无自身也成为可能。这就是所谓原初的混沌,是孕育出把‘永远的革命者’藏在影子里的现在的行动者的根源,是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场。[1](P142)
就是说,“无”也是一种实在,实在包含着“无”与“有”。“沉默”,不等于不语,而是不直截了当地进行批判,因此,虽是“无”,也是“有”,于是“无使有成为可能”,所以说,“没有语言的空间也是实在”。另一方面,“使语言变为可能的,同时也会使语言的非存在变为可能”,像《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是一种有声的讲演,呈现的是有的形态,但它采取曲笔,或顾左右而言它,从本质上看,也是一种沉默,所以又是“无”,是用“沉默”进行抵抗、批判,以这种“无”“使语言的非存在变为可能”。而“永远的革命者”就藏在这个“沉默”的所谓“无”的影子里,所以“永远”就是“现在”,是现在的行动者。显然,在这里,“有”是实在,“无”同样也是“实在”,二者互为一体,相互转化,既对立又统一,形成了“所谓原初的混沌”,孕育出“永远革命者”即“文学者鲁迅”,并由此“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显然,在竹内好那里“作为根源的无”便成为了某种动因。就像西田所说的:
如果我们不仅把所谓无当作一个词汇,而且把某种具体意义加在它上面来看,就可以认为它一方面是指缺乏某种性质,另一方面却具有某种积极的性质。因此就物质界会由无生有的观点来说,如果作为意识的事实来看,无也不是真正的无,而可以看作是意识发展上的某一动因。[3](P43)
显然,竹内好把鲁迅的文学,视为“在其根源上是应该被称作‘无’的某种东西”,同样基于这一立场。竹内强调,如果这个“无”不存在,那么,就不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显现,作为显现的鲁迅也就不能不消亡。因此,反过来说,“只要有鲁迅存在,如此假定便是坚不可移的。应该认为,根源上的东西是实际存在着的”[1](P99)。因此,竹内好认为,鲁迅的本质是难以言说和无法命名的“无”,他说:“在本质上,我并不把鲁迅的文学看作功利主义,看作为人生,为民族或是为爱国的。鲁迅是诚实的生活者,热烈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但他并不以此来支撑他的文学,倒是把这些都拔净了以后,才有他的文学。鲁迅的文学,在其根源上是应该被称作‘无’的某种东西。”[1](P58)他把它称之为“文学的正觉”,看作是一种终极性的和非实体性的存在,但现实的鲁迅却由此不断地得以生成。
二、“矛盾的同一的”思想
竹内好在谈到“矛盾的同一的”来源时曾明确指出,“这是从西田哲学中借来的用语,是受当时读书倾向的影响,今天看来既表现了思想的贫乏,又没有西田哲学用语的严密性。”[9]具体说就是借鉴和化用了西田的“绝对矛盾的自我同一”的思想。
“绝对矛盾的自我同一”思想在“西田哲学”中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西田指出,“世界是一即多、多即一的结构。在辩证法的一般者即世界的自我限定中,一通过绝对的自我否定而为多,多通过绝对的自我否定而为一。世界是一与多的绝对矛盾的自我统一。”[10](P185)“竹内鲁迅”就建立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
竹内好用“矛盾的同一的”来界定鲁迅的本质,他说:“鲁迅在本质上是一个矛盾。就像人们说革命家孙文是一个混沌,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家鲁迅也是一个混沌。”而且,“这个混沌,把一个中心形象从中浮托上来,这就是启蒙者鲁迅,和纯真的近似于孩子的相信文学的鲁迅。这是个矛盾统一,二律背反,同时存在。”[1](P14)如同西田几多郎所说的,“在对立的根基上有统一,无限的对立都是从自体的内在性质作为必然结果发展而来的。”[3](P53)这种“矛盾的同一的”特点在鲁迅的文学创作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竹内好指出,鲁迅的小说虽包含有各种不同倾向,但其中至少有一种本质上的对立,可以认为是“异质物质混存一体”。这并不是意味着没有中心,而是说有两个中心。它们既像一个椭圆的中心,又像两条平行线,其两种物力,相互牵引、相互排斥。从大的方面讲,体现为作者和作品的对立,小而言之,体现为《孔乙己》与《药》,《孔乙己》与《端午节》、《药》与《故乡》、《弟兄》与《离婚》等各种各样的对立关系。“这种对立是什么呢?用语言把它们剥离开来表述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城市与农村,追忆与现实,都是其小小的表现;或者也是生与死,绝望与希望吧。……总之,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有两个中心奇妙地联系在一起。”[1](P89)
在对立统一中,竹内好揭示了鲁迅不变的本质。竹内好把没有变化的部分定义为“回心的那种东西”[1](P45),被他视为是鲁迅“文学正觉”的时机和被环绕其中的一生不变的“回心之轴”。于是,伴随鲁迅一生的诸种元素,包括传记、文学作品、论争行为等,不再是各自孤立的独立存在,他想要做的就是“调动这些要素,沿着它们诞生和消失的路向,追踪那个‘回归之轴’的位置”[10](P36)。这个一生不变的“回归之轴”,形成了鲁迅的“矛盾的同一的”本质,构成了作为“文学家”鲁迅的“不变”的内在的必然逻辑。
在哲学意义上,“不变”实质体现了对时间的一种解构。西田几多郎从直接经验的角度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时间涵义,解构了“昨天的意识”和“今天的意识”的独立性,将它们统一起来,把它们看成是“同一意识在连续活动”[3](P55)。他反对对时间的预先设定。在他看来,时间“不过是整顿我们经验的内容的一种形式,因而在时间这种想法产生之前,首先必须使意识内容能够得到结合、统一而成为一体。否则就不能把前后联系起来而在时间性上进行思考。因此不是意识的统一作用受时间的支配,相反是时间通过这个统一作用而成立的。因此可以认为,在意识的根基上,必须具有超越时间之外的不变的某种东西”[3](P55)。从这点来看,在精神的根基上常常有某种不变的东西。“所谓时间的过程就是伴随着这种发展的统一的中心点在变化,而这个中心点始终就是现在。”[3](P56)在这一点上,竹内好与西田几多郎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
竹内好超越于时间之上来认识鲁迅的“不变”,他预设了一个“决定性的时机”,“这是在黑暗里决定了他回心的自我形成作用的反复,就像一根贯穿在他一生当中,使他在不停顿的每次脱皮之后都会回归过来的基轴”[1](P135)。而“本源性”的鲁迅就是不断生成于此,由此,“文学者鲁迅在现时性的意义上诞生了”[1](P107),他同样摆脱了时间的限定。他所说的“现时性”实质就是西田所说的“现在”,即“不变”,也就是坚持认为鲁迅并没有发生变化,当然,他并非无视和否认鲁迅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但是,当他立足于鲁迅终其一生的带有根本性的“回归之轴”时,便作出了上述判断,所以,他说,“我是在不动中看鲁迅的。”[1](P39-40)
竹内好认为,鲁迅作为文学者,具有一种“根本态度”,无论是在与梁启超的关系上,还是在幻灯事件里和“三·一八”事件里,以及其他各种场合,他都固守着这一态度,类似西田几多郎说的“统一力”。西田几多郎说:“这个统一的某种东西,在物体现象上便成为存在于外界的物力,在精神现象上就归于意识的统一力。”西田几多郎认为,“我们能够认识和体会的世界,必须是存在于我们的意识相同的统一力之下的世界。”[3](P57-58)在意识的根基上有着不变的统一力在进行活动,事物是通过统一而成立的,观念和感情也是由于统一的自我的力量才变成具体的实在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精神的根基上经常有不变的某种东西。西田几多郎认为这种不变是遵循了宇宙间有一个一定不变之理,而这“不变之理,是万物的统一力,又是内部的统一力。理不是由物或心所具有的,而是促使物或心成立的。理是独立存在的,不因时间、空间和人而有差别,也不因显灭消长或使用与否而起变化”[3](P56)。
相对西田几多郎从某种“理”之中寻找“统一力”的生成本源,竹内好则把“统一力”归之于鲁迅本身,就是鲁迅自我的不断挣扎与否定,即“回心”。竹内好认为,鲁迅“否定性地形成了他自身”[1](P146)。在谈到论争时,竹内好说:“他是论争者。他通过论争来和异化到自己之外的非我之物进行交锋。这交锋的战场,就是他自我表现的舞台。”首先,“他把那痛苦从自己身上取出,放在对手身上,从而在对这被对象化了的痛苦施加打击”,“可以说,他是在和自己孕育的‘阿Q’搏斗”。因此,从本质上讲,鲁迅的论争体现的就是自我的不断对抗与否定。可以说,“他的与恶的战斗,是与自己的战斗,他是要以毁灭来灭恶”[1](P149)。其次,由此带来的就是把“自己和作品对立起来”,创造出杂感这样独特的文体,而“十余本杂感录,作为其记录,便是不成其为作品的作品”[1](P109)。实质上,论争就是自我对立、自我否定、自我挣扎的过程,也是自我统一的过程。
三、“行为”的意义
竹内好所说的鲁迅由作品向论争的转换,与梁启超等的对立所展开的自我否定或“挣扎”,即“行为”,它所展现的积极的能动性、实践性和创造性,有点类似西田几多郎说的“行为的直观”的内在精神。
西田几多郎在1933~1934年出版了《哲学的根本问题》及其续编。在其中的《辩证法的一般者的世界》一文中,提出了“行为的直观”的概念。所谓“行为的直观”是指,主客体相互限定,相互推动。这里的“行为”含有能动的积极的意义。西田几多郎说:“我们通过行为在外界制作物,制作客观地与我们相对的东西。行为必须是制作。”“我所谓的行为的形象不仅仅是客观的,但又不仅仅是主观的。”这就是说,“行为”一方面是“制作”,具有能动性;另一方面它本身既不单纯属于主观,又不单纯属于客观。我们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客观地改变物、制作物,它是社会的、历史的事件”[11](P338)。而“直观”“就是外现地观察,在与自己绝对相反的他中看见自己”[10](P187)。在西田几多郎看来,它同样具有主体的积极活动,即必须有行动有意义,如他所说“没有无行为的直观”。我们作为行为的自己在主观即客观、客观即主观这个世界中,“是通过见而动,通过动而见”[11](P359)。显然,作为“西田哲学”的一部分,与上述的“纯粹经验”和“绝对矛盾的对立统一”的思想,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行为的直观”被认为“是西田哲学认识论的最高峰”[5](P446),在西田几多郎看来是人把握现实世界的根本方法或唯一逻辑,即把辩证法一般者世界直接化、具体化为行为的直观的世界了。西田几多郎把世界作为历史的世界,并从行为的直观的立场探求它的形成。他把世界的历史运动理解为“由被制作者到制作者”。我们在制作的行为中成为真正的我,在制作物中认识真正的我。只要我们——自己真正是历史的创造性的自己,物就是我,我就是物,我与物是一体。我成为物而动,成为物而见。“我们不是在单纯的意识的自觉中认识自己,而是在历史的身体的创造过程中发现真正的自己。”[10](P189)
联系到竹内好,可以认为,他同样坚持了这一立场,也就是在社会或历史的场域里考察鲁迅,把鲁迅纳入尖锐激烈的思想论争的漩涡中,纳入矛盾对立和自我否定之中,在个体的自我限定和与一般的相互限定中发现鲁迅,也发现自己。竹内好将写小说与写杂感区别开来,认为后者体现了鲁迅的文学态度和行为。他说:“写小说在他那里并不是写杂感的那种行为,写杂感,是得同时把研究文学史的那种强烈的沉潜欲作为支撑之后方可成立的一种行为。”[1](P28)“行为”是竹内好为鲁迅的文学定位时使用的关键词,是与观念在对立的意义上使用的。它是与自我否定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就是“挣扎”,包括从小说到杂感,从创作到论争,从“文学的无力感”到“永远的革命”。自我否定和“挣扎”就是文学的态度和行为,其中体现在文学与政治的对立上。在论及鲁迅和梁启超之间有一种决定性的对立时,竹内好指出,“这种对立可以认为是鲁迅本身矛盾的对象化,因此,与其说是梁启超影响了鲁迅,倒不如说是鲁迅在梁启超身上看到了被对象化了的自己的矛盾。”他将其命名为“政治与文学的对立”,他说:“我以为,鲁迅受梁启超的影响,后来又摆脱它,不是应该解释为他在梁启超身上破却了自己的影子,涤荡了自己吗?”[1](P69)也就是鲁迅自身存在着的矛盾,通过自我否定,将二者对立统一起来。
西田几多郎提出“行动的直觉”正值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传播到日本,他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中得到启发,丰富了他对“行为”的认识。在《善的研究》中,他从心理的、意识的立场,只把“行为”视为有意志或有意识的动作,然而,在接触马克思主义后,吸收了“实践”的思想,“行为”与“直观”相结合在西田的认识论上,使其以往的“直观”具有了能动的作用。“行为”这一实践和能动的思想,同样贯穿在竹内好思想当中,体现在对鲁迅及其“文学”的理解上。
“文学”对于竹内好来说,是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概念,被他注入了实践的、能动的、创造性的精神,而获得了丰富的内涵和全新的意义。“他把‘文学’从一种创作行为推向终极性和本源性存在本身,同时又使这种终极性与本源性在‘文学’的名义下获得现实人生的流动形态。”在竹内好那里,“文学是思想,是行为,是政治,是审美,但它又是远远超过这一切的催生了也废弃了这一切的那个本源性的‘无’,那个不断流动的影子和不断自我更新的空间”[12](P41)。这和他在《鲁迅》中所说的“文学是行动,不是观念”是一样的。他很看重论争,就是因为“论争在本质上是文学的,即不是行为以外的东西”[1](P109)。
综上所述,竹内好的《鲁迅》深受西田几多郎哲学思想的影响,在“西田哲学”导引下从本源的立场上,对鲁迅进行了哲学性的解读,改变了以往对鲁迅的肤浅理解,重新塑造了一个崭新的鲁迅形象,提升了鲁迅研究的学理高度。当然,竹内好这种基于“西田哲学”的对鲁迅的非历史化和非“实体化”处理,也遗留下了一些问题,常遭到后人的质疑和诟病。其实,任何独创性的发现,往往带有一定的片面与不足,但是,这种“片面的深刻”却从一个方面促进了“竹内鲁迅”体系的开放,促使它始终处在不断被否定和被挑战的态势中,“事实上,日本鲁迅研究就是基于自我否定基础之上的‘竹内鲁迅’被反复否定和超越的历史。正是通过自我否定‘竹内鲁迅’这一象征来从中无限地生发新的自我,也就是竹内好所主张的‘在发展中来把握鲁迅’,才使得日本鲁迅研究始终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始终处于鲁迅研究的学术前沿”[13]。
收稿日期:2013-02-22; 修回日期:2013-0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