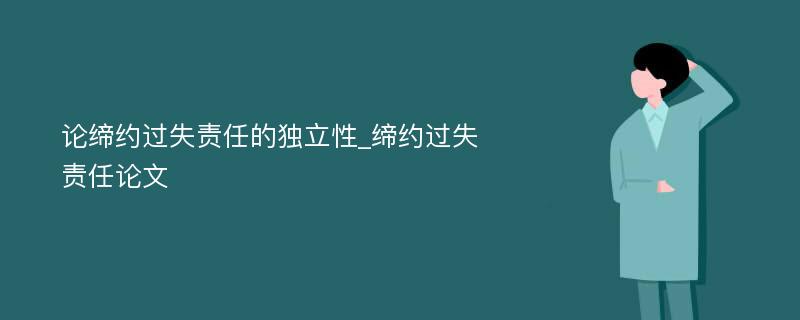
缔约过失责任之独立性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缔约过失论文,独立性论文,责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我国民法上的缔约过失责任是否应为独立的责任类型
我国《合同法》第42条①和第43条②确立了所谓的“缔约过失责任”。据此,缔约过失责任一般被定义为:“在合同缔结过程中,一方当事人违反了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的先契约义务,造成另一方当事人的损害,因此应承担的法律后果。”③当前我国主要的民法和合同法著作几乎都将缔约过失责任作为一种独立的责任类型。④在由王利明教授主持的《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中,缔约过失甚至被从合同法中分离出来而与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悬赏广告一起并列规定为债的发生依据。⑤
作为缔约过失责任之独立性的理论依据,国内学者多从其与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区别入手,在观点上也大同小异,但基本出发点在于:缔约过失责任的基础是依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的先契约义务,此种先契约义务以维护信赖利益为中心。
因此,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的根本区别是:违约责任以有效成立的合同为前提,责任人所违反的是合同义务;而缔约过失责任的当事人之间则不存在有效成立的合同,责任人所违反的先契约义务不是合同义务,而是法定的义务。⑥
另一方面,缔约过失责任与侵权责任的根本区别则体现为:缔约过失责任发生于为缔约而进行接触的当事人之间,双方在以缔约为目的的活动中产生了特定的信赖关系,其内容就是一种依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的先契约义务或信赖义务,比如通知、保护、协助、保密等义务;而侵权责任的发生却不需要当事人之间存在着这样的信赖关系,侵权行为所违反的只是不得侵犯他人的人身和财产的一般义务。从内容上来看,先契约义务所课以的注意要求要高于侵权法上的一般义务。⑦
对于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之间的区分,国内民法学界不存在争议;但是对于缔约过失责任与侵权责任之间的区分,学界则存在着一些零星的异议。持异议的学者一般认为,先契约义务也是法定义务,因此,缔约过失责任只不过是侵权责任的一种形态;⑧从实践来看,“现代侵权行为法也开始承认,在特殊场合,加重行为人的注意义务,缔约过失场合也可构成侵权责任。”⑨比如,消费者在商店购物时滑倒受伤所产生的赔偿诉讼,作为传统上缔约过失责任的一种典型案件,依据我国2004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的规定,则被归入了侵权责任的范畴。此外,针对《合同法》第42条和第43条所规定的恶意磋商、隐瞒重要事实或提供虚假情况,以及泄露或不正当使用商业秘密的行为,即使没有缔约过失理论,我们在司法实践中也完全可以通过侵权法来寻求损害赔偿。因为根据我国的侵权法理论和实践的一般认识,侵权责任的一般依据在于《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的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上述三类行为完全可以包含在其中。因此单凭先契约义务的特殊性并不足以将缔约过失责任从侵权责任中独立出来。
由此可见,在目前国内的民法理论上,所谓缔约过失责任独立性的观点并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既然如此,为什么这种观点仍然能够主导国内的民法学说呢?
究其根源,国内学者对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认识完全来自我国台湾地区和德国的民法理论,⑩而在我国台湾地区和德国,缔约过失责任的独立性是毋庸置疑的,甚至被奉为“法学上之发现”。(11)我国大多数学者所论述的缔约过失责任之独立性的依据也基本上是对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民法理论的简单照搬,比如,缔约过失责任只存在于建立了特定的信赖关系的当事人之间,侵权法无法保护由于缔约过失所导致的特殊损害等。但是,问题在于,这些来自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理论是否完全成立呢?此外,即便这些理论成立,它们能否直接嫁接到我国现有的民法体制中来呢?换句话说,缔约过失责任在我国台湾地区和德国是独立于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之外的责任形态,这是否就意味着它在我国的民法体制下也当然是一种独立的责任形态呢?显然,这是问题的根源,也是上述异议的症结所在。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缔约过失理论在其发源地德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生存土壤”,准确把握缔约过失责任在其本土法学环境中获得独立地位的基本依据,进而结合我国法学理论和实践的环境以及国际上更为广泛之国家的做法,对缔约过失责任的独立性理论作出准确的评判。
二、缔约过失责任之独立性的本土依据:弥补侵权法的局限
缔约过失责任源自德国,国内对其缘起之过程已有详实介绍,本文在此不予涉及。
根据德国的相关民法理论,当事人在进入缔约阶段后即依诚信原则而相互负担一定之义务(包括通知、协助、保护义务等),此即所谓的“先契约义务”。任何一方违反这一义务而致他方身体或所有权受到损害或致他方遭受财产损失的,应当对他方承担赔偿责任,此即“缔约过失责任”。根据这一理论,缔约过失责任所要赔偿的范围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为受害人身体或所有权受到的损害;二为受害人的财产损害。(12)前者主要是指诸如商店这样的服务企业未尽到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而导致顾客受伤或财物损失的情况;后者所谓“财产损害”是指所有权以外的利益损失,也就是德国民法理论上所谓的信赖利益或消极利益的损失,它包括受害人因相信合同的有效成立(但合同最终并未成立,以及被撤销或归于无效)而支出的缔约费用和因此丧失其他缔约机会而蒙受的利益损失。(13)
从《德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来看,缔约过失责任最初并未被作为一般规则得到确认,它仅仅是在民法的学说和判例中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德国民法典》上有关错误的意思表示被撤销后的赔偿(第122条第2项)、无权代理人的赔偿(第179条)、给付自始不能的赔偿(第307条,该条现已被废除)以及违法合同的赔偿(第309条,该条现已被废除)等在解释学上一般被认为是缔约过失责任的具体形式。此外,更多的缔约过失责任形态则是在判例中出现的。(14)
但是,2002年施行的《德国债法现代化法》则对传统民法典的规定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该次修改的重大成果之一就是作为缔约过失责任之理论前提的先契约义务关系在民法典上得到了一般性确认。根据修改后的《德国民法典》第311(2)(3)条之规定,先契约义务被视为一种“准法律行为上的债务关系”,其内容是第241(2)条所规定的基于债的关系而发生的两项义务中的第二项,在《德国民法典》上被表述为“一方对另一方的权利、法益和利益的顾及义务”,即理论上所谓“附随义务”的内容;该种“准法律行为上的债务关系”因下列情形之一而发生:合同磋商的开始,合同的准备(在准备合同时,鉴于可能的法律行为上的关系,一方将影响自己的权利、法益和利益的可能性给予另一方或将自己的法益和利益托付给另一方)或类似的交易上的接触;该种“准法律行为上的债务关系”也可以对不应成为合同当事人的第三人而发生,这类第三人主要包括代理人、投资顾问、管理人和鉴定人等受到当事人特殊信赖而大大影响合同缔结过程的人员。(15)
由于上述先契约义务或准法律行为上的债务并非以合同为依据,所以在德国,对于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的区分争议不大;争议的焦点在于缔约过失责任与侵权责任的区别上:由于二者都属于违反法定义务的责任类型,所以它们之间的界限不像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之间的界限那么明显。在德国的主流学说中,缔约过失责任相对于侵权责任之独立性的理论依据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
1.调整范围上的依据。缔约过失责任与侵权责任乃适用于不同的社会关系领域。王泽鉴先生对德国相关理论作出了如下评介:“侵权行为法仅适用于尚未因频繁社会接触而结合之当事人间所生的摩擦冲突;倘若当事人因其社会接触,自置于一个具体的生活关系中,并负有互相照顾的具体义务时,则法律应使此种生活关系成为法律关系,使当事人互负具体的债务。”(16)也就是说,当事人在为缔结契约而接触磋商之际,已由“一般普通关系”进入“特殊联系关系”,互相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信赖关系”,这种关系以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的通知、协助、保护、忠实等附随义务为内容,其性质及强度上超过一般侵权行为法上的注意义务,而与契约关系较为接近。(17)对此,德国学者梅迪库斯也有类似的表述:“对于当事人而言,开始合同磋商即已经设定增强的注意义务,即已经设定特别结合关系。”(18)王泽鉴先生此处所谓的“具体的生活关系”、“特殊联系关系”或“特殊的信赖关系”就是德国学者梅迪库斯所谓的“特别结合关系”,这正是缔约过失责任适用的领域。在这种“特别结合关系”中,缔约当事人所承担的在性质及强度上超过一般侵权行为法之要求的所谓“增强的注意义务”即为“先契约义务”。
据此可以发现,在被称为德国法学上之一大发现的缔约过失理论中,实际上还潜藏着一个新颖的侵权法理论:侵权法的调整范围限于在损害发生前未发生直接的社会接触的当事人之间的“一般普通关系”,而不包括因当事人之间直接的社会接触而产生的“特别结合关系”。2002年修改后的《德国民法典》第311(2)条将“交易上的接触”作为“准法律行为上的债务关系”发生的依据,显然就是对这一理论的确认。这一理论也明显影响到了我国学者对于缔约过失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理论基础的看法。(19)
2.法律技术上的依据。在德国民法典的体制下,依据侵权法来处理缔约过失纠纷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从目前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所举出的例证来看,这些局限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雇主责任上的局限。根据《德国民法典》第831条的规定,如果雇员在工作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只要能够证明其在选任、监督雇员上已尽到必要之注意义务或即使尽到必要之注意仍不免发生损害的,可以免责。据此,当商店售货员在销售过程中因过失损害客户利益时,店主便可以此为由而不承担赔偿责任。
其次,诉讼时效上的局限。在2002年《德国债法现代化法》施行之前,《德国民法典》上规定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30年(第852条),而适用于侵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则为3年(第195条)。这样一来,依据侵权法来保护缔约过失的受害人,其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要远远短于普通诉讼时效期间。(20)
再次,侵权法在保护范围上的局限。由于《德国民法典》关于侵权行为的保护采取的是一种“相对分散的概括模式”,德国学者称之为“小的一般条款”(21),而非统一抽象的“一般条款模式”,该种保护模式的一大特点就在于谨慎地限制侵权法的保护范围。德国侵权法所规定的一般侵权行为(即过错责任形态)总体上包括三类:权利侵犯型(《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第824条和第825条)、违反保护性法律型(《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2款)和违反善良风俗型(《德国民法典》第826条)。
权利侵犯规则所保护的是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声誉、性权利(22)及其他权利,而缔约过失除了造成受害人身体和所有权的损害外,在多数情况下则造成的是受害人财产利益上的损失(比如支出的费用),而后者并不在以上所列举的权利范围之内。即使是《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所谓的“其他权利”,在德国的理论和实践中也仅仅限于他物权、一般人格权、知识产权、营业权等绝对权利类型;根据德国民法解释学上的一致看法,该款关于“其他权利”的规定并非意味着将一切权利都置于侵权法的保护之下,而恰恰相反,立法者的真实意图是将债权和由侵权带来的一些间接利益的损失(比如,打伤雇工而给雇主带来的停工损失或者给其他雇工带来的工作量的增加,或者打死了某个商店的重要客户而给该商店所带来的潜在营业利益上的损失等)排除于侵权法保护之外。正是基于此,德国民法学者一再强调,侵权法所保护的财产权利并非“总括财产(das Vermogen)”,即一切具有金钱价值的财产利益,而仅仅限于所有权和与所有权类似的绝对权利。(23)这一限定是德国侵权法保护范围之局限性的根源,也是缔约过失责任之独立性的根源所在。
此外,缔约过失在多数场合并非故意,因此不属于《德国民法典》第826条所谓的违反善良风俗;而且,在缔约过失的场合,受害人往往无法找到保护自己利益的具体明确的法律规范,因而也不属于《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2款的范围。所以,德国的侵权法并不足以实现对缔约过失问题的全面规范。
基于此,缔约过失责任规则的提出在德国的法学理论上被看作是对侵权法的不公平和保护范围上的局限性的补充,因而其在德国现代民法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
我国台湾地区侵权法的规定也存在着与德国类似的局限,(24)加之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与德国民法之间的师承关系,德国的缔约过失责任理论在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上基本得到了移植。
首先,就缔约过失责任的保护范围来看,与德国有所不同的是,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学者之间明显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其中,以王泽鉴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主张将缔约过失责任的形态仅仅局限于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责任(即信赖责任),而将缔约过程中的所有权和身体损害排除在外;根据王泽鉴先生的观点,后者在我国台湾地区和其他国家多依侵权法处理。(25)相反,林诚二和邱聪智先生则主张将二者都纳入缔约过失责任的保护范围。(26)
其次,就缔约过失责任的保护模式来看,与《德国民法典》一样,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也经历了一个由具体规定向一般规则转变的过程。在2000年之前,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保持了《德国民法典》的传统做法,即不设一般规则,仅就特殊情况设具体规定。比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规定了意思表示被撤销后的赔偿责任(第91条)、无权代理人的赔偿责任(第110条)、无效法律行为之当事人的赔偿责任(第113条),以及给付自始不能的赔偿责任(第247条)。但是,2000年修订后之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245-1条则增设了一般规则条款:“契约未成立时,当事人为准备或商议订立契约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对于非因过失而信契约能成立致受损害之他方当事人,负赔偿责任:(1)就订约有重要关系之事项,对他方之询问,恶意隐匿或为不实之说明者。(2)知悉或持有他方之秘密,经他方明示应予保密,而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泄漏之者。(3)其它显然违反诚实及信用方法者。前项损害赔偿请求权,因二年间不行使而消灭。”该条款第(3)项之用语明显体现出了立法者对先契约义务和缔约过失责任的一般性确认。(27)
在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上,作为缔约过失责任之独立性的依据,除了与德国侵权法类似的法律技术上的依据外,(28)最主要的论理依据就是所谓的“信赖利益和信赖责任说”,即缔约过失责任所保护的是一方当事人因信赖合同有效成立,但合同最终并未成立,以及被撤销或归于无效时,(29)所遭受的利益损失,包括支出的费用和失去其他缔约机会的利益。这种信赖利益非为侵权法所保护之“权利”的范畴(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84条)。
三、缔约过失责任之独立性的依据在我国侵权法体制下不能成立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发现,缔约过失责任的出现与德国的民法体制,尤其是侵权法的特有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在的问题在于,在我国的侵权法体制下,上述适用于德国或我国台湾地区的有关缔约过失责任之独立性的依据是否还能够成立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一)法律技术层面的国情考察
就法律技术而言,在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侵权法上所存在的不公平和保护范围上的局限性在我国并不存在。
首先,在雇主责任上,《德国民法典》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所规定的雇主免责事由在我国侵权法上不适用。我国《民法通则》第43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2004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进一步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在以上规定中并不存在雇主(包括企业法人)无过错免责的条款。从性质上讲,在我国侵权法体制下,雇主对雇员行为承担的是一种无过错责任:对于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所导致的损害,雇主不得以其在选任、监督雇员上已尽到必要之注意义务或即使尽到必要之注意仍不免发生损害为理由而主张免责。据此,对于店员销售过程中的过失损害问题在我国可以直接适用侵权规则来解决,而无适用缔约过失责任的必要。
其次,由于我国实行统一的诉讼时效制度,诉讼时效期间的长短与责任类型无关:无论是违约责任、侵权责任抑或是缔约过失责任,在诉讼时效期间上并无差异。因此,不存在依据侵权法来保护缔约过失的受害人,其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要远远短于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
再次,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侵权法在保护范围上的局限性在我国也不存在。我国在侵权法的理论和实践中一直采取的是一种较为宽泛的保护模式。除违约责任以外,凡是违反法定义务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侵害他人财产、人身所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都属于侵权责任的范畴;这里的“财产”包括了在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侵权法上不受保护的诸如信赖利益等纯粹的“财产”利益。(30)由于在缔约阶段的先契约义务也属于法定义务的范畴,作为违反这一义务的后果,即所谓的“信赖责任”或“缔约过失责任”,当然应归入侵权责任的范畴。
正因为如此,将缔约过失责任排除于侵权责任类型以外的实践依据在我国是不成立的。
(二)调整范围层面的论理批判
另外一个问题是,缔约过失责任独立性的理论依据,即所谓调整范围上的独特性,在我国是否能够成立呢?
对此,笔者以为,即使在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侵权法理论上,这种将侵权法的调整范围限制于“一般普通关系”的理论也是片面的。依据王泽鉴先生的描述,在损害发生前未发生直接的社会接触的当事人之间的“一般普通关系”由侵权法调整,而因当事人之间直接的社会接触而产生的除契约关系以外的“特别结合关系”则应当比照契约关系予以处理(即所谓的缔约过失责任规则)。但问题在于,这种“特别结合关系”在法律上并非仅仅局限于缔约领域。关于这一点,德国学者豪普特、多尔以及施密第斯也已指出:“纵无缔约行为及契约上之意思,亦得直接由客观的社会关联产生法律关系及债之关系。”(31)比如,发生在亲权或监护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发生在无因管理过程中的管理人与被管理人之间的关系等。因为父母与未成年子女之间或者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早已存在直接而密切的社会接触,他们之间所存在的法律上的利益关系或信任关系也超过“一般普通关系”的程度,而在无因管理过程中,管理人依法须对被管理人的事务尽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这也超越了一般普通关系当事人之间的注意程度。那么,是否在这些领域因为上述义务的违反而导致的损害赔偿后果也应当如缔约过失责任那样独立于侵权法之外呢?除此之外,人际关系中的直接接触也绝非仅仅限于缔约以及上述之亲权、监护和管理他人事务的场合,人们在各种讨论、做节目以及聚会等场合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直接接触,在此过程中当事人相互之间的信赖程度或注意义务也多有不同,那么,是否在这些领域发生的损害赔偿应当根据人们之间所处的“接触关系”的直接程度(或亲密程度)的不同,或者说根据人们之间的信任程度或注意义务的大小,而作出不同类型的划分呢?
显然,目前我们所了解的包括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内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没有采纳这一做法。除了缔约过失责任的争议以外,上述损害赔偿问题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归属于侵权的范畴;即使是在合同磋商或准备过程中发生的过失损害,如果损害的客体是人身或所有权,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包括采纳缔约过失责任理论的国家和地区——仍被归入侵权法的范畴。对此,我国学者王利明教授提出,在合同成立前发生的信赖利益的损害与所有权或身体的损害是不同的,因为前者发生在为缔约而磋商的场合,在此种场合,当事人之间已经发生了“实际的接触(如发生要约或要约邀请)”,产生了“法律上的联系”或“缔约关系”,只有具有了这样的联系,当事人之间才能产生信赖关系,由此产生的责任属于缔约过失责任;而在诸如消费者在商场中被玻璃或悬挂物砸伤或在商场中滑倒摔伤的场合,双方(消费者与商场)并没有发生实际的接触,甚至很难确定受害人具有购货的意思或订约的意图,因此,不存在缔约关系,由此产生的责任不属于缔约过失责任,而属于侵权责任。(32)
笔者以为,王利明教授强调缔约行为的特殊性是有道理的,但就此认为,在合同成立前发生所有权或身体损害的场合当事人之间尚未进入缔约状态(即“实际的接触”或“缔约关系”),显然是对缔约状态或缔约过程的狭隘理解,同时也不符合德国相关传统理论和最新立法的精神。
首先,在合同订立的理论上,商店开门营业的行为就已经构成了对于广大消费者的要约或要约邀请,消费者进入商店后即使没有明确的购买意图,也已经进入到《德国民法典》第311(2)条所谓的“合同的准备”阶段——这就是缔约状态或缔约过程的开始。他们当然有理由相信商场应为他们提供安全的购物环境,而无须等到交易磋商或谈判正式开始后才发生此信赖;如果硬要当事人之间开始了磋商或谈判方才算是有了购货的意思或订约的意图,那么我们又怎么看待某些消费者只问价而不购买或者纯粹凑热闹的磋商行为呢?显然,我们不能够过于苛求缔约行为状态的开始条件。
其次,就在商场所发生的所有权或身体损害而言,也有发生在磋商正式开始以后的。比如,准备购买地毯的顾客在试验地毯的防滑性时摔伤,此时在顾客和商家之间已经开始磋商了。显然,即使我们对缔约行为状态的开始条件作严格的限制,我们也不能一概地说,在合同成立前发生所有权或身体损害的场合,当事人之间没有发生“实际的接触”,没有产生“法律上的联系”或“缔约关系”。
在我国的民法理论和实践中,上述发生在“特别结合关系”领域的损害赔偿,除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责任(信赖责任)存在争议外,一般都被列入侵权法保护的范围。
以上论述起码说明,在实证法的层面上,侵权法所调整或保护的范围除了包括在损害发生前未发生直接的社会接触的当事人之间的“一般普通关系”之外,还包括某些因当事人之间直接的社会接触而产生的“特别结合关系”类型。所以,以侵权法的调整范围仅限于“一般普通关系”为由将缔约过失责任排除于侵权责任类型之外的理论依据是不成立的。
总而言之,无论在法律技术的层面,还是在调整范围的层面,缔约过失责任与侵权法相分离的理论都是德国法学特有的理论和实践的产物,其根源在于德国侵权法保护范围的限定性:由于侵权法保护范围的限定,缔约过失责任无法为侵权法所涵盖,这就为对缔约过失责任适用不同于侵权的诉讼时效和责任条件提供了依据,也促使了在调整范围问题上的新的解释理论的出现。
四、将缔约过失责任作为侵权责任的一种类型是国际上更为普遍的做法
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缔约过失责任及其独立性的理论在除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和理论上是何处境呢?
在英美法系,缔约过失责任的概念是不存在的。根据英美合同法的传统观点,在合同成立以前,处于缔约阶段的当事人之间,除了禁止欺诈和虚假陈述以外,没有任何责任。但是现代英美法已经逐渐超越了这一传统,它们的判例和制定法也确认了处于缔约阶段的当事人之间也存在着除禁止欺诈和虚假陈述以外的其他义务,违反这些义务给对方造成损害的,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对于此类责任的性质,英美法系则没有集中统一的解释,在相关的合同法著作中一般也未有提及。(33)
根据英国合同法专家阿狄亚对于英美法上相关救济手段的介绍,我们发现,在英美法上,缔约阶段的当事人在缔约失败(或谈判破裂)的情况下所要承担的责任包括返还财物、强制履行和损害赔偿。返还财物责任的法律依据来自返还法(也称偿还法),而强制履行则主要针对的是由于缔约一方的陈述使得对方产生了合理的信赖并依此行事的场合,在这种场合,法院可以强制陈述方兑现自己的陈述,而其依据则是英美合同法上传统的“允诺禁止反言”的规则,有时法官也援用“单务合同”规则。至于我们关心的缔约失败后的损害赔偿责任,其法律依据则涉及普通法、衡平法和制定法三个方面。
在普通法上,法院往往直接依据侵权或所谓的“法院制造合同”来追究缔约一方的损害赔偿责任:诸如欺诈、虚假陈述以及过失性的不当表述,在普通法上本身就是侵权行为;(34)而在缔约一方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或诚信义务)从而导致缔约失败的场合,法院则推定缔约当事人之间存在着以这些必要的义务为内容的“默示预备性合同”,以此来强制违反这一义务的缔约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在衡平法上,法院往往也将缔约过错的一方作为侵权人来对待。在阿狄亚所举到的判例中,对在缔约中获取的技术秘密加以保密被认为是一项衡平法上的“默示义务”,而泄密行为则被作为衡平法上的侵权来看待。
有关制定法中所确立的规则也被法院援引来作为追究缔约方损害赔偿责任的依据,比如,有关“反歧视法”的规定被法院作为判决雇主向求职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因为该雇主违背这一规定拒绝雇佣某个求职者;另外,依据有关“公平招标”的欧盟指令,(35)招标人应当根据招标条件公平地对待所有的投标人,因为招标人违背这一规定被错误拒绝的投标人,有权依据该规定要求损害赔偿。当然,从这些法律规定的性质上来分析,背离规定的违法行为应当属于侵权行为的范畴。
总体来看,在德国法系被称之为“缔约过失责任”的法律范畴,在英美法系并没有独立的地位:一方面,英美法系根本没有“缔约过失责任”的概念;另一方面,发生在缔约领域的损害赔偿纠纷,在英美法系乃是侵权法和合同法共同保护的领域,但从英美法律界的倾向来看,侵权法保护则更受青睐,因为所谓的“法院制造合同”被认为是对自由市场理念和合同自由传统原则的过度干涉。(36)
缔约过失责任理论在大陆法系的影响比较广泛。根据有关介绍,(37)采纳德国的缔约过失责任理论的国家和地区主要包括瑞士、奥地利、希腊、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葡萄牙、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等。综观这些继受缔约过失责任理论的国家或地区,直接在立法上将缔约过失责任作为一般性规则加以规定的除了我国台湾地区外,还有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而其他国家或地区则是在学说和判例上将缔约过失责任作为一般性规则,在立法上仅仅针对诸如合同不成立、无效、撤销等特殊情况分别规定相应的赔偿责任。笔者在这里仅对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法国的相关立法和理论进行考察。
希腊1940年的新民法典对缔约过失责任作出了一般性的规定。其第197条规定:“从事缔结契约磋商行为之际,当事人应负遵循依诚实信用及交易惯例所要求的行为义务。”其第198条规定:“于为缔结契约磋商行为之际,因过失致相对人遭受损害时,应负损害赔偿责任,纵契约未能成立亦然,关于此项请求权之时效,准用基于侵权行为请求权时效之规定。”(38)《葡萄牙民法典》第227条作出了类似的规定:“以缔约为目的与对方进行谈判时,必须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准备合同和缔结合同;否则他要对因过错给对方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39)《意大利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也是一般性的,但较之于希腊仍略显“保守”。其第1337条规定:“在谈判和缔结契约的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其第1338条则规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存在契约无效原因的一方,未将该原因通知他方的,应当为此就他方在契约有效期内基于信赖而无过失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显然,希腊、葡萄牙和意大利的民法典的相关规定都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对“先契约义务”的一般性规定;二是对违反先契约义务的“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对于前者,三个国家都予以了全面的肯定(《希腊民法典》第197条、《葡萄牙民法典》第227条、《意大利民法典》第1337条),但对于后者,其立法态度则明显不同:《希腊民法典》第198条和《葡萄牙民法典》第227条的规定是一种宽泛的一般性规则,它将所有违反先契约义务的“缔约过失责任”都涵盖在内;而《意大利民法典》第1338条则仅仅对“缔约过失责任”的一种形态——违背无效事实的通知义务——予以了规定。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在《意大利民法典》中,只存在先契约义务的一般性规则,而无缔约过失责任的一般性规则。
深究其中原因,可以发现,意大利的民法学虽然接受了来自德国的缔约过失责任的概念,但并没有将缔约过失责任作为一种独立的责任类型。在意大利民法学界,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性质存在着“违约责任说”和“侵权责任说”两种观点:前者以先契约义务的相对性为依据,强调该种责任在内容上与合同责任的一致性;(40)后者则以缔约过失责任的“非契约性”或法定性为依据,强调该种责任在来源上的不法行为(即侵权行为)(41)属性。但在意大利的民法理论和实践上,“侵权责任说”乃是主流观点。(42)作为该学说最为权威的代表,意大利最高法院的态度是:缔约过失责任作为一种非契约责任,它在实质上并非来自当事人之间尚未达成的合同或者已经存在的协议,而是来自缔约一方的不法行为,因为该行为导致他方对未来合同的达成产生了信赖。(43)意大利合同法学者玛利亚·迪艾内对于缔约过失责任在意大利民法典上的地位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很明显,如果按照合同责任的理论,似乎意味着现行法典增设了当事人在合同缔结阶段的新的责任类型;然而这是不准确的,因为更准确地说,我们应当看到,随着社会观念的改进,不法行为所包含的范围已经扩张到了违背缔约过程中的正确义务的行为。”(44)
正因为如此,缔约阶段当事人所负有的法定的诚信义务或信赖义务有必要在立法上予以明确,而违反这一义务的后果则属于一般侵权的范畴,除了法律已有明确规定的具体情况外(比如违背无效事实的通知义务(《意大利民法典》第1338条)、无权代理的损害赔偿(《意大利民法典》第1398条)等),可以适用《意大利民法典》第2043条关于“不法行为的损害赔偿”的一般规定。
当然,这只是《意大利民法典》上只设先契约义务的一般性规则,但未设缔约过失责任之一般性规则的一种解释,而并非全部的原因所在。在葡萄牙的判例法上,缔约过失责任也被作为侵权责任来对待,(45)但我们知道它的民法典仍旧设立了缔约过失责任之一般性规则;而当代之德国的理论和司法判例则视缔约过失责任为独立责任类型,但《德国债法现代化法》所确立的最新模式则只设立了先契约义务的一般性规则,而没有设立缔约过失责任的一般性规则;《希腊民法典》虽然对先契约义务和缔约过失责任都作出了一般性规定,其国内的主流观点也倾向于将缔约过失归入合同或准合同(即德国最新模式之“准法律行为”)的类别,(46)但其“准用基于侵权行为请求权时效之规定”的表述也间接说明了缔约过失责任与侵权责任的亲缘性。
法国虽然也引进了缔约过失责任理论,但根据我国学者尹田的介绍,法国传统理论则将合同无效(包括不成立)时当事人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当作侵权责任,认为其应适用《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所规定的过错责任原则。(47)就此分析,法国的情况与意大利是相似的,即一方面承认缔约过失责任理论,而另一方面仍坚持其侵权的属性。这在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教授的著作中也得到了证实。(48)
基于以上比较法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在两大法系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对强化缔约阶段的诚信义务或信赖义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大多数国家还是将其作为传统侵权责任的衍生,并不承认其作为独立责任类型的地位。
五、关于我国《合同法》上缔约过失责任之立法模式的调整建议
从我国《合同法》第42条和第43条的规定来看,我国所确立的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
其一,缔约过失责任在我国《合同法》上是一项一般性规则。
其二,缔约过失责任在我国《合同法》上限于信赖责任。显然,我国《合同法》追随了大多数继受法国家的做法:将缔约过失责任仅仅限于信赖责任(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责任),即因缔约过程中的欺诈、泄密等不诚信的行为所产生的赔偿责任,而将缔约过程中的所有权和身体损害排除在外。在我国的民法理论界,主流观点认为,诸如商店的地毯打滑、电梯安全性上的缺陷或销售人员的过失致使消费者在商店购物过程中受伤或遭受财物损失的情况,完全属于侵权法保护的范围。(49)2004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就明确将此作为服务业的安全保障责任而归入侵权责任的范畴。
由此推理,先契约义务也被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安全保障义务;另一类则是信赖义务。违反前者属于侵权责任,违反后者则属于缔约过失责任(信赖责任)。换句话说,在德国民法理论上作为违反先契约义务之统一后果的缔约过失责任,在我国的一般理论上被肢解为缔约过失责任和侵权责任两个部分。
但问题在于,由于我国民法理论和民事立法对于一般侵权所采取的是宽泛保护的立场,这种“肢解式”的解释理论是多余的:它不仅与我国的现有体制冲突,而且使得现有之责任理论被不合理、不必要地复杂化了,这是科学的理论所不允许的。
通过以上的理论和实务分析,笔者得出的结论是:缔约过失责任的独立性在其起源地得以成立的理由在我国是不成立,也是不必要的;从世界范围来看,将缔约阶段的责任作为侵权责任的一种类型则是更为普遍的做法;从我国民法理论和实践的情况来看,将缔约过失责任归属于一般侵权责任类型也是切实可行的。所以,将缔约过失责任作为独立的责任类型实为我国民法理论上的一个误区。
基于此,笔者主张,我国立法在保留缔约过失责任以明确当事人在缔约阶段的诚信义务的同时,对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应当予以精简。
从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构成来看,它由三个部分组成:先契约义务、缔约过失行为、缔约过失责任。先契约义务是将当事人在缔约阶段的诚信义务法定化的关键,因此必须予以保留;缔约过失行为既然已被定性为一般侵权行为,因此其构成完全可以适用一般侵权行为的条件,对于其具体形式的列举不仅有挂一漏万之虞,而且导致条文臃肿,因此完全可以概括规定的方式予以取代;既然缔约过失行为的两种类型(即违反信赖义务与违反安全保障义务)都属于一般侵权行为的范畴,那么,将缔约过失行为限定在违反信赖义务的范围内已失去了必要;缔约过失责任作为侵权损害赔偿的类型,只须作“准用”侵权法的规定即可,而其所谓信赖利益的损失实为侵权法上的实际损失和预期利益的损失所包含,它们彼此之间的区别应属于法解释理论和司法裁量的范畴。
针对我国《合同法》第42条、第43条之规定以及目前由我国学者主持起草的两部“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的相关规定,(50)笔者认为,它们相对于上述要求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陷:我国《合同法》和王利明先生所主持的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均缺乏对先契约义务的明确统一规定;(51)梁慧星先生所主持的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对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和诉讼时效作出了规定,而这与侵权法和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是重复的;此外,三者都对缔约过失行为的具体形式进行了不必要的列举。
从国际上来看,大凡采用一般规则模式的国家或地区(比如希腊、意大利、葡萄牙,以及德国的最新模式),都强调对先契约义务或信赖义务的规定,而将缔约过失责任作为违反先契约义务或信赖义务的当然结果,因此一般并不对缔约过失行为的具体形式加以列举(我国台湾地区例外)。作为细节上的差别,意大利和德国都只规定先契约义务,而对作为违反后果的缔约过失责任不设统一规定;希腊和葡萄牙则对两者都作出了一般规定。
综合上述分析,笔者以为,希腊民法典和葡萄牙民法典中有关缔约过失责任之立法模式可以作为我们效法的蓝本。据此,缔约过失责任的具体条款应设定为:“在缔结合同的过程中,当事人应负遵循依诚实信用及交易惯例所要求的行为义务。在缔结合同的过程中,当事人一方因过失致使相对人遭受损害时,应负赔偿责任。关于此项责任,准用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定。”相对于我国现行立法和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上述新设计的条款不但内容精简、定性明确,而且更有利于从根本上实现对先契约义务的全面保护。
注释:
①我国《合同法》第42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1)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2)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3)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②我国《合同法》第43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无论合同是否成立,不得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该商业秘密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③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18页。
④同上注,第417~421页;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页以下;参见李永军:《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页以下。
⑤参见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债法总则编·合同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六编第二章“债的发生”第1153条。此外,中国社科院的张广兴研究员也主张将缔约过失单独作为债的发生原因之一,因缔约过失所发生的债也应成为一种法定债。参见张广兴:《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
⑥同前注③,魏振瀛主编书,第420页;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6页。
⑦同上注,魏振瀛主编书,第421页;同上注,崔建远主编书。
⑧学者刘汉霞明确否定缔约过失责任是独立于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之外的责任类型,其主张:“先合同义务在本质上是一种法定义务,根据违反法定义务构成侵权责任的一般理论,缔约上的过失责任只能是侵权责任。”参见张民安主编:《合同法》,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6~67页。
⑨同前注⑥,崔建远主编书。
⑩国内最初能接触到的有关缔约过失责任研究的中文资料都来自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对德国相关学说的评介,主要包括王泽鉴、刘得宽和林诚二等人的著作。就国内的研究而言,除了前注④中提到的一些当前的代表著作外,以国内较早涉及到这一问题的权威民法学理论著作为例,其中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介绍基本上都是以上述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的著作为依据的。参见王家福主编:《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37~39页;王利明:《违约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94页以下;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3~316页。
(11)此语出自德国法学家的一份同名演讲报告,译文载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4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以下。
(12)关于德国民法理论上“财产损害型”缔约过失责任和“所有权和身体损害型”缔约过失责任的区分,参见[德]梅迪库斯:《德国债法总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96~97页。
(13)关于信赖利益或消极利益的概念,参见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页;王泽鉴:《信赖利益之损害赔偿》,载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5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页以下;同上注,梅迪库斯书,第506~507页。
(14)对此可参见前注(12),梅迪库斯书,第92页以下。
(15)参见陈卫佐译注:《德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110页。
(16)王泽鉴:《法学上之发现》,载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4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17)参见王泽鉴:《缔约上之过失》,载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1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6页。
(18)同前注(12),梅迪库斯书,第95页。
(19)同前注③,魏振瀛主编书,第421页;同前注⑤,王利明主编书,第65~66页;同前注⑥,崔建远主编书,第86页。
(20)在《德国债法现代化法》施行以后,德国民法上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缩短为3年,侵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则延长为10年,其效果与修改前恰恰相反。
(21)[德]梅迪库斯:《德国债法分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16页。
(22)《德国民法典》第823条在2002年被修改,其保护范围扩张至一切受“诱使性行为”侵害之利益,从这一意义上讲,该种侵权实属违反善良风俗(《德国民法典》第826条)之具体形态。
(23)同前注(21),梅迪库斯书,第613~672页;[德]福克斯:《侵权行为法》,齐晓琨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
(24)参见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84条(侵权法保护的仅为权利而非财产)、第188条(雇主责任上的局限)的规定;同前注(11),王泽鉴书,第95页。
(25)同前注(17),王泽鉴书,第101页。在继受缔约过失理论之意大利,其民法理论也将缔约过失责任限于信赖利益(消极利益)的损害赔偿。(See Maria Cristina Diener,Ⅱ Contratto in Generale,Giuffrè,Milano,2002,p.145.)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教授也证实,在欧洲各国的理论上,缔约过失的赔偿请求权也通常限于信赖利益的损失。参见[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上卷,张新宝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576页。
(26)参见林诚二:《民法债编总论——体系化解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5页;邱聪智:《新订民法债编通则》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9页。
(27)对此,林诚二先生则有不同看法。同上注,林诚二书,第426页。
(28)同前注(24)。
(29)在德国法系(包括我国台湾地区、意大利)的传统理论中,信赖利益或消极利益一定与法律行为的不成立、无效、撤销相联系。因此,仅对信赖利益进行赔偿的缔约过失责任,在德国、我国台湾地区和意大利,都只适用于合同不成立、无效、撤销的场合,而在合同有效成立时则一般不予认可(虽然在理论上有一定探讨)。同前注(12),梅迪库斯书,第102~104页;同前注(17),王泽鉴书,第98~99页;同前注(25),Maria Cristina Diener书,第145页。
(30)参见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王利明、杨立新编著:《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第6~8页;同前注③,魏振瀛主编书,第675页。
(31)转引自前注(16),王泽鉴书,第11页。
(32)同前注⑤,王利明主编书,第65~66页。
(33)参见[英]P·S·阿狄亚:《合同法导论》,赵旭东等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112页。
(34)同上注,第471页;另参见《美国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第四编“不当表述(Misrepresentation)”的规定。
(35)See Statutory Instrument 1991 Nos.2679,2680; Statutory Instrument 1992 No.3279.
(36)同前注(33),P·S·阿狄亚书,第111~112页。
(37)同前注(17),王泽鉴书,第87页;同前注(25),克雷斯蒂安·冯·巴尔书,第575~581页。
(38)转引自前注(17),王泽鉴书,第102页。
(39)转引自前注(25),克雷斯蒂安·冯·巴尔书,第576页。
(40)二者都以诚实信用为依据。因此,《意大利民法典》第1337条规定的诚信义务被认为是该法第1375条规定的合同诚信的衍生。
(41)在意大利民法理论上,侵权被表述为不法行为(fatti illeciti)。参见《意大利民法典》第2043~2059条。
(42)同前注(25),Maria Cristina Diener书,第139~141页;E.Russo,G.Doria,G.Lener,Istituzioni delle Leggi Civili,Cedam,2005,p.587; Pietro Trimarchi,Istituzioni di Diritto Privato,Giuffrè,Milano,2005,p.270.
(43)同上注,Maria Cristina Diener书,第141页。
(44)同上注。
(45)同前注(25),克雷斯蒂安·冯·巴尔书,第579页。
(46)同上注,第580页。
(47)参见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38页。
(48)同前注(25),克雷斯蒂安·冯·巴尔书,第577页。
(49)同前注⑤,王利明主编书,第65~66页。但梁慧星先生主持的学者建议稿则将其归入缔约过失责任,参见梁慧星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71条。
(50)同前注⑤,王利明主编书,第1182~1183条;同前注(49),梁慧星主编书,第870~873条。
(51)梁慧星先生主持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在第870条规定了先契约义务。同上注,梁慧星主编书,第870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