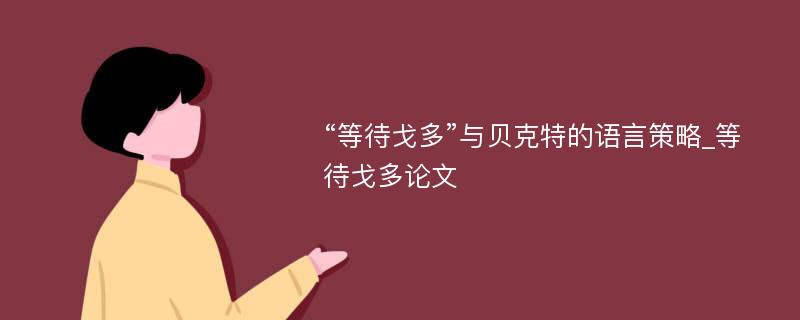
《等待戈多》和贝克特的语言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策略论文,语言论文,贝克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语言:与存在直接对话
荒诞派戏剧作为20世纪世界文坛重要的文学现象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但人们对它的研究却处于困境之中。一方面,它以其一反传统的姿态和狂放不羁的艺术特征,享受了“打破常规”的殊荣,而以后的论者多从“反”处入手对之作褒贬抑扬;另一方面,作为对后现代主义文学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它又在历经怀疑、接受和疯狂的模仿借鉴之后,自身面临着“步入经曲”成为新的传统、新的常规的历史命运。对此,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并设法为研究的深入开拓出新的思维空间。
长期以来,人们对荒诞派戏剧的一般描述都是“它像一个白痴讲的故事,绘声绘色,毫无意义”。①而尤奈斯库的“语言的悲剧”更是一个被用滥了的标签。如果我们以语言作为技巧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也许的确如此;但是,如果我们结合20世纪语言观念的变迁来考察,则又另当别论。语言观在20世纪思想史上产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已成为无可否认的事实,它以原先处于附庸地位的工具论上升到处于中心地位的本体论;在文学中也不仅仅作为文学的基本要素存在,而且还作为艺术领域中最具革命性的力量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威力。19世纪以前,人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成为其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人对语言有着绝对的控制权,“我在说话”表明了人的主体性和中心地位的稳固。而到了20世纪,特别是现代主义后期和后现代主义的时期,人的存在却成了问题。“存在还是不存在?”──这个幽灵困扰着现代作家。“存在──人”的链条的松落使得语言挣脱了人的控制而获得独立,并在存在主义那里取得本体地位。“语言是存在的家”。②语言问题成为存在主义(特别是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本体论的最后立足点。此在存在都最终归于语言,在语言中觅得家园。于是,“语言的命运恰恰基于人与存在的诸关联之上,从而追问存在的问题使最内在地同追问语言问题纠缠在一起。”③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中,我们看到了“存在──语言”的直接对话,人被排挤到语言的后面,因为人只有在语言中才能找到自己存在的理由。于是人与语言的关系颠倒了,成了“话在说我”。这一深刻的变化体现在创作中就是作者语言策略的调整。
《等待戈多》和贝克特的语言策略具有无可替代的代表性。这不仅是因为《等待戈多》是荒诞派戏剧的经典作品,而且还由于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其他荒诞派作家的一致努力和共同特色。所以,从贝克特的语言策略这一角度入手,通过对《等待戈多》的实证分析,我们就能对荒诞派戏剧获得一个全新的认识。
作为剧本的基本话语,题目“等待戈多”告诉了我们关于戏剧的一切。若补足主语的话,那就是“戈戈狄狄等待戈多”。但是贝克特却把这一话语彻底摧毁了,他所用的武器就是“语言策略”。
二、戈多:话语的陷阱
戈多对人们来说是一个永恒的诱惑。从圣昆廷监狱的犯人到学院派的批评家,阐释“何为戈多”一直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各执己见的斯芬克斯之谜。纵观对它的阐释史,我们不能不说所有的探秘者均落入了贝克特设置的话语的陷阱。首先,试图把戈多确定为某一实在之物的企图把《等待戈多》做了庸俗化的处理。比如,因为“戈多(Godort)”与英语“God”相近,而猜其为“上帝、神、造物主”之意,但我们知道贝克特并不相信上帝;认为“戈多”就是波卓,只不过作者没有明说,这多是受了戈戈和狄狄胡言乱语的影响;至于犯人们认为“戈多就是社会”,那也是出于对自身处境的反观;而认为戈多是影射现实生活中的某某人更是无稽之谈。其次,试图把戈多确定为某一隐秘的象征的企图又把《等待戈多》圈定在旧的传统之内。无论认为它象征“死亡”、“希望”还是其它别的什么,都与前者一样,即先有一理论的假设前提:戈多是某一确定的东西,无论是具象还是抽象,无论是实在还是象征。相较而言第三种意见也许更为聪明,认为“戈多就是虚无”、“他是被追求的超验,现世以外的东西”。④但是这种论者的错误比前两者走得更远。他以极简单的方式对戈多作了最彻底的否定,同时也使《等待戈多》全剧失去了其丰富的韵味而变得浅薄。倒是令人束手无策的贝克特的一句戏语给我们提供了打开这个陷阱的秘诀。当有人问他戈多是指什么人时,他说他不知道,“我要是知道,早在戏里说出来了”。这里,贝克特暗示我们不必纠缠于“何为戈多”的问题。因为只要“戈多是”就行了,至于“戈多是什么”则无关紧要。戈多“是”的确定性和“是什么”的不确定性正是戈多本质特性的真实写照。因此,我们对戈多的探讨就有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戈多何为”。
正如基本话语“戈戈狄狄等待戈多”所示,“戈多何为”的问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戈多与戈戈狄狄的关系,一是戈多与等待的关系。
先看戈多和戈戈狄狄的关系。从表象上,戈多的意义既有严肃性的一面,又有非严肃性的一面。戈多为他们提供存在的理由的同时又为他们提供闲谈的话题。第一幕中,戈戈狄狄对“等待戈多”的时间地点的怀疑、对“戈多”的姓名言行的猜测明显带有调侃的色彩。而第二幕中,他们因戈多的即将到来而欢呼雀跃和因为如不履行诺言将受惩罚而黯然神伤,在理由/话题的转换中仿佛透露出戈戈狄狄的灵活自主性。而实质上,戈多对他们享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他既是把戈戈狄狄抛入荒诞世界的罪魁祸首:如果不是他让他们在这儿等他,戈戈狄狄绝不会被困在这里;他不是使戈戈狄狄重新得救的希望之星:他不出现,戈戈狄狄便永远无法认清自己的处境,就永远只能不死不活地等待。同时,戈多的永不出现和戈戈狄狄的永不退场,显示了两者的基本关系特征:不在/在场的二元对立,并显示了“不在(absence)”对“在场(presence)”的绝对权威。尽管全剧中有的只是戈戈狄狄的表演,但是“不在”的话语都显得异常突出,它使得“在场”的话语丧失了解释的权威性,成为被动的接受者。戈多只需托人捎上一句似是而非的口信便会把戈戈狄狄为之付出的全部努力击得粉碎。
这种矛盾也体现在戈多和等待的关系上。从语法分析的角度上讲,“等待”是全句(也是全剧)中唯一的动词(行动)。“戈戈狄狄”是施事主语,“戈多”是受事宾语,因此,“戈戈狄狄等待戈多”就是一个主动语态。从这种字面意义出发,“这部戏剧就是表现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怎样等待戈多”,⑤就成了以往论者研究该剧的思维定势。但正如我们以上分析戈多和戈戈狄狄的关系所示,“戈多”是事实上的主语。它是“等待”的目的、原因,而“等待”却是实现的手段、结果。两者关系是一个内在的被动语态。所以上面的那句话应倒过来说才符合戏剧的实质:“这部戏剧就是表现戈多怎样让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等待。”“等待戈多”的主动和被动关系倒置显示了贝克特的狡黠,从另一角度看,“等待”和“戈多”作为基本话语的组成部分有着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性。“戈多”没有人“等待”,它将成为普通的指称符号;“等待”没有“戈多”作为目的对象,它将失去神秘的诱惑力量。但是,贝克特却偏偏为我们设置了戈多的缺席(永不在场)。这种有意的空缺造成句法上的完整性和意义上的残损性和尖锐对立。并且这种“空缺”是永远无法也不能填补的。“等待戈多”的矛盾性表明:戈多不来,等待才能延续,等待就有价值:戈多来了,就意味着等待的终结。所以,“戈多”的“不来”、“空缺”是全剧的终极真理,是戈多的意义之所在。
戈多以其不在确立他在场的不容怀疑,以其不来显示了他的作用的无比巨大。总之,在贝克特的语言策略中,“戈多”以其空缺而永远居于中心地位。这种“空缺”的无,不是虚无,而是无限。戈多是“不在之在”,“到处都在而无一处在”。⑥
三、失名:对人物的消解
在以往的论者中,分析戈戈狄狄的人物形象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以传统的人物形象的典型性、完整性、生动性来衡量他们,只能让人失望,“这类戏则常常缺乏能够使人辨别的角色,奉献给观众的几乎是动作机械的木偶”。⑦在《等待戈多》中,如果说戈戈狄狄完全像一对连体婴儿,他们不仅个性气质服饰相貌相似,就连境遇也完全一样,他们几次分手,但只是说说而已,走几步还得转回来。在不可理喻的现代荒原上,人只有缩小自己的视野或转向内心才可能获得某种心理平衡。戈戈狄狄若即若离的境遇正是这种荒诞人生的“直喻”。正如狄狄所说,对于这个茫茫苦海,“光一个人,是怎么也受不了的”⑧。另一对人物波卓和幸运儿可以说是他们两人关系的形象说明和有力补充。在前后两幕中,波卓和幸运儿的依附关系虽有所改变,但那根可长可短可松可紧却永不松手的绳子是两人永远无法分离、永恒不变的关系的象征。无论这是把两个人合成一个人还是把一个人分成两个人,其构思绝不在塑造人物,而在揭示人物个性的消失。“非个性化”走出了消解人物的第一步。尽管这种策略并不属于语言方面,但它已经为贝克特实施语言策咯铺平了道路。
首先是使人物的主体性丧失。作为一具有主体性的人,他有思考、判断、选择、行动的自由和能力。但戈戈狄狄不一样。两人的不可分割并不具确立性而具抵消性。在剧中,戈戈狄狄只有一点差异:戈戈只关心他的脚,使劲要把靴子脱下来,而狄狄只关心他的帽子,取下来又戴上。这两个细节象征着戈戈只关心肉体,而狄狄只关心精神。这一差异导致了两人语言上的矛盾。狄狄总是新的话题的挑起者,而戈戈总是用相悖的语言回敬从而抵消话题的意义。如果我们把狄狄作为肯定性因素,把戈戈作为否定性因素的话,那么,“人物一体化”造成的共时并存性使得他们在对待任何问题上都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进而无法思考、判断、选择、行动,只能以不了了之而告终。“只要你(指戈戈)在场,就什么也肯定不了”,就只能听凭戈多的摆布。人的主体性的丧失使人无法弄清自己的处境,更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进而显示出人作为世界的存在物的荒谬性。
其次是使人物的历史性丧失。在传统观念中,“人是时间的动物”是天经地义的。这是因为,人有记忆,能够通过回忆和向往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结起来。但是在戈戈狄狄那儿,记忆力消失了。戈戈是彻底的遗忘,狄狄也仅存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片断。狄狄始终都存在回忆过去的企图,但这种回忆变得异常的艰难。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在剧中贝克特通过不确定的回忆而对人物的历史性的消解的策略也是语言上的。一、非连续性。每当人物真心想回忆时,他的语言便变得断断续续了。“我只要一想起……这么些年来……要不是有我照顾……你会在什么地方……?”这种语言的不连贯反映了思维的干涸枯涩。二、互相抵消。狄狄的肯定性话语与戈戈的否定性话语也抵消了回忆的可靠性。“弗:‘……可是你不答应。你不记得了?’爱:‘是你做的梦’。弗:‘难道你已经忘了?’爱:‘我就是这样的人。要末马上忘掉,要么永远不忘。’”三、自我怀疑。这主要表现在狄狄身上。如“费:‘咱们认识他们,我跟你说吧。你把什么都忘啦。(略停。自言自语)除非不是他俩……’”这样,“他成了一个无法召回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对于失去的家乡的记忆,而同时也缺乏对未来世界的希望。”⑨人物在割断和过去未来的联系之后,永远成为“现时”的人,只有对当时处境作出应急反应的本能。“那种从过去通向未来的连续性的感觉已经崩溃了,新时间体验只集中在现时上,除了现时以外,什么也没有”⑩。于是,人物在舞台上的表演变成了瞬间片断的组合。历史性的丧失使得人被时间撕成粉碎从而失去了完整性。
最后是失名。人物主体性的丧失导致了人物的萎缩,人物历史性的丧失造成了人物的零散化。而这一切发展到极端就是“失名”。在我们既往的观念中,“名”是某一具体的人的指称。人因名而相互区分,“名”是人取得独立性的标志。“名”作为一个确定的能指/所指符号,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等待戈多》中,人物的“名”被贝克特无情地剥去了。等待戈多的人同时具有两个名字:弗拉季米尔/狄狄;爱斯特拉冈/戈戈。但“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仅仅作为贝克特剧本中标志角色的符号而不在人物对白中运用”,“戈戈”和“狄狄”仅仅作为两人单独交谈时的称呼(也许是昵称),而不用在与外人的交谈中。在他们与戈多的联系中,又用了另外一个名字“亚尔伯特”。在他们与波卓的交谈中又用“卡图勒斯”来掩饰其真实姓名。在这里,人物的失名不是没有名字,而是“名”的所指功能的丧失。“名”不再是具有人格特征的人物的指标,而是贝克特标示角色的符号和文字游戏的工具。失名之后,人被彻底消解了。
那么,贝克特这样做的意图何在?他要把我们引向什么地方呢?在人物出场的舞台上,人在被消解之后便不再具有独立的形象意义而成为“影像”,这“影像”的真正主体是人类自身。“全人类就是咱们”,“他就是全人类”。贝克特借助人物告诉我们:剧中的人物是困境中的人类的象征符号。在人物与语言的关系上,人物的消解使得语言的地位更加突出。“‘谁在说话又有什么关系’,有人说道,‘谁在说话有何差别’”(11)。贝克特的这段话被福珂用来说明本文与作者的关系问题,我想同样也可用来说明语言与人物的关系问题。无论话是谁说的,言语都不具有说明指向具体的个人的功能。它仅仅“是自身的表述”,“产生于自身的蜕化”(12)。这也正是与人物的人类性特征相照应的。从中我们看到在后现代主义作品中语言与人物的分离和作者对语言的高度重视。
四、闲谈:把“等待”耗尽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最热衷谈论的是“等待”。因为“戈多”的空缺和“戈戈狄狄”的零散破碎都使人无法把握,剩下的只有“等待”是唯一可以确定的了。并且,“等待”与“戈多、戈戈狄狄”相比,本身还有一个字面意思,只要把它与现实或哲学联系起来,便能引发人无穷的联想和无尽的体验。所以,“等待”的意义不仅是可说的,而且是说不尽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等待”被一致公认为全剧的主题。当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我们通过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无焦透镜却发现了其中的荒谬之处。在对“戈多”这个话语陷阱的设置,对“戈戈狄狄”这两个人物的消解之后,“戈戈狄狄等待戈多”这个基本话语便面临着深刻的危机。但贝克特并没有对它抱着丝毫的同情,反而再接再厉落井下石,向“等待”这个堡垒发动最后的攻击:把“等待”耗尽(burnout)!
其实,在贝克特对“戈多”、“戈戈狄狄”实施空缺、消解策略时,就已经对“等待”做了剥离的处理。首先是语法方面的。“戈多”的永不出场使“等待”成为永远不能完成的现在进行时;“戈戈狄狄”的自我丧失(被消解)使“等待”成为失去主动意味的被动语态。这种变化体现在戏剧中就是小孩所说的“戈多明天准来”的希望与“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的虚妄、狄狄所说的“咱们守了约,有谁能吹这个牛?”的真诚与“千千万万”人也都如此的戏谑同时并存。其次是语境方面的。既然是“等待”,就不可避免地要回答两个问题:“在哪儿等”和“什么时候等”。而在剧中这两个问题是模糊不清的。从戈戈狄狄的交谈中,地点是任意的,“别怕没有空间”;时间也是不定的,更确切地说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时间概念。如果说从语法方面只是把“等待”的意义与其存在方式剥离(而以另一种语法形式替代)的话,那么,从语境方面,“等待”的意义与其存在条件也剥离了。这种“意义受语境限制而语境没有限制”(13)的局面导致了意义的不确定。“等待”便成为一种不受限制的存在。它的直接后果是使“等待”的意义具有了无数可能性,于是观众可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任意阐释。这也就意味着《等待戈多》走回了追求意义的多样性的老路。但是贝克特的目的绝不在于此。他所要做的是反其道而行之:追求一种无意义的意义。贝克特语言策略的后现代性也正是从这儿最终显现出来的。
“等待”在失去一切前提条件之后,只剩下了它本身:一个单词、一个从词源学上讲有“意思”的单词。在《等待戈多》中,“等待”的词性是动词,意思是“不采取行动,直到所期望的人、事物或情况出现”(14)。这个动词表示行为状态。它因为“不采取行动(delayacting(15)──英语解释更准确一些,“等待”有拖廷、推迟、延宕行为的意思,而不仅仅是“不采取行动”),所以没有一个“等待”的动作与之相对应,而必须通过其它意思的一系列动作行为构成一种“等待”的状态。于是,一种矛盾产生了:一方面,“等待”是全剧唯一的活动,它担负着说明全剧意义的重任;而另一方面,“等待”自身也需要说明,否则,将无任何意义。面对着所要达到的目的和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之间的双重隔膜的困境,贝克特选择了更具反讽意味的语言策略:闲谈。
“闲谈”是海德格尔常用的一个术语,用来说明此在存在的方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常有这样的现象,“事情是这样,困为有人说是这样”。(16)这种特点的日常交谈就是闲谈。“闲谈就是在这类鹦鹉学舌、人云亦云中组建起来的”(17)。它是一种“非本真”的存在方式,是一种异化。贝克特所采用的戏剧对白正是这样一种“闲谈”。在《等待戈多》中,闲谈首先是一种无话可说而又不得不说的庸人自扰。交谈本身并不是目的。戈戈狄狄没有一个什么问题需要通过交谈来讨论、协商或解决,所以从根本上讲,他们是无话可说的。但他们又不得不说。困为交谈的目的在于等待。一方面,只有交谈才能消磨时间,暂时忘却百无聊赖的煎熬;一方面,只有交谈才能构成“等待”的状态,证明自己还存在,还在等待。这种矛盾又使得戈戈狄狄只把注意力集中在“闲谈”的形式维持上而对所谈的内容漠不关心。于是,闲谈具有了第二个特点:一种话题频繁转移而又陷于自动交流的语言游戏。话题是构成闲谈的核心要素。没有话题的言语只能算作意识流,连自言自语、内心独白也算不上。所以,寻找话题对戈戈狄狄是至关重要的。但另一方面,戈戈狄狄对任何话题都没有持久的兴趣,也没有深入探讨的能力。他们的谈话并不经过大脑的思维处理,不从逻辑有序着眼而从字词本身出发,随意发挥胡乱堆砌,是一种纯粹的本能反应,一种自动交流。它又反过来使正在谈论的话题有始无终,草草收场、漫无中心、频繁转换。因此,闲谈完全沦为一种语言游戏。我们所听到的是用正常人意识无法把握的天马行空的扯淡。正如维持根斯坦所说,“语言游戏就是说出预料之外的话。我是指,它不基于任何依剧。它是没道理的。它就在那儿──像我们的生活一样”(18)。这种闲谈的随意飘浮游荡的无根性(也即海德格尔所说的“闲谈的无根基状态”(19))只是增加了戏剧的混乱和破碎。
很显然,“闲谈”解除不了“等待”的困境。戈戈狄狄的辞微理拙黔驴技穷与等待的空虚无聊永不休止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戈戈狄狄无法填补“等待”时间的空白;同时,闲谈的荒诞不经语无伦次连自己的存在意义也证明不了。作为一种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目的的手段,“闲谈”成为西绪福斯式的无奈努力。“等待”也在“闲谈”中无可挽回的被耗尽了。“等待”意义的耗尽使“等待”真正成为“某种比愚蠢还要糟糕的东西,一种语言幻觉”(20)。如果真要寻找意义的话,这种无意义的等待正是戏剧所要表达的意义:它是一种无望的救赎,一种不死不活的人类困境的象征。
五、策略:规定将来的创造规则
通过对《等待戈多》中贝克特语言策略的逐层剖析我们已在事实上取得了崭新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从以戏剧为参照研究到将之纳入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的框架之内并借用解构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对其策略的特点进行总结。
马丁·埃斯林对荒诞派戏剧的艺术特征做了权威性的评述,其艺术感受力和理论思辩力均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在他的《荒诞派戏剧》的导论中,他表达出“用荒诞派戏剧本身的规律来说明荒诞派戏剧”(21)的良好愿望。但是因为他对“荒诞派戏剧”极为宽泛的概念界定,无形中冲淡了荒诞派戏剧的鲜明个性(早期的布莱希特也在荒诞派剧作家的名单上)。还因为他习惯性地将荒诞派戏剧与已成传统的现代主义文学相提并论,所以更多地“看到它们属于旧传统的一部分,这一传统虽时时被淹没,但仍然可以一直追溯到古代”(22)。这样,他提供的荒诞派戏剧的标准只能是令人失望的。“埃斯林列出的标准是:‘创造力、引起诗歌意象的复杂性和把这些意象结合在一起并恰当地扮演出来的技巧,更重要的是,‘这些意象所体现的是幻象实在与真实的’也许,我们可以埋怨这种用于评论目的的概念的主观性和模糊性。”(23)欣契利夫的话可谓一语中的。
也许利奥塔德的一番话会给我们以启示:“后现代艺术家或作家往往置身于哲学家的地位:他写出的文本,他创作的作品在原则上并不受制于某些早先确定的创作规则,也不可能根据一种决定性的判断,并通过将普通范畴应用于干那种文本或作品之方式,来对他们进行判断。那些规则和范畴正是艺术品本身所寻求的东西。于是,艺术家和作家便在没有规则的情况下从事创作,以便规定将来的创作规则。(24)因为作家不受制于任何早先确定的规则,所以我们既不可能用传统的规范使之削足适履,也不可能仅仅依据作品来自以为是地为之制订标准,正确的作法是把具体作品放在荒诞派戏剧作品中去考察,把荒诞派戏剧放在整个后现代文化体系中来审视,因为作者的策略不在于当时,而在于将来。荒诞派戏剧自40年代初潮涌动、50年代浪涛汹涌,到60年代消隐沉寂,走过了一个自足的发展过程。历史的定形定位便意味着一个新的规范的诞生。时至90年代,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也趋于积淀之时,这种将来性便成为现时性的东西了。这一理论前提使我们有可能走出从策略剖析到规范总结的第一步。
那么,《等待戈多》和贝克特的语言策略对这种将来的创作规则做出了何种努力呢?即贝克特语言策略的将来性体现在哪儿呢?首先,把《等待戈多》与贝克特的其他剧作联系起来,我们会发现,“统观贝克特剧作的发展始未,他像一直在努力使自己少说一些,少表现一些。……这里贝克特试图点明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找到恰当的词语,找到那最终令人噤口不再作声的词语。(25)贝克特以后剧作中对言词的拒绝正是《等待戈多》中语言对意义的拒绝的逻辑发展。他对“戈戈狄狄等待戈多”这一基本话语的摧毁最终划清了它与传统戏剧的界限。贝克特摒弃了语言对意义的多样、复杂或模糊的追求而通过摧毁意义于无意义中显示意义,是典型的“无”中生“有”。其次,如果把《等待戈多》和贝克特的语言策略与荒诞派戏剧之后的戏剧联系起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一方面贝克特的设置话语陷阱、消解人物、耗尽意义等语言策略都具有普遍性,是几乎有后现代主义作家乐此不疲的艺术共性。另一方面,贝克特这种“无”中生“有”的策略也带着较大的缺陷,并且预示了此后戏剧发展的趋势。世界戏剧经过荒诞派戏剧的冲击救偏,使得“这样的戏剧涉及剩下的少数问题:生、死、隔离和死亡。(26)由此发展下去,“60年代,70年代,以及80年代,我们面临的是现实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完全被打破,看到的是更为抽象的戏剧。”(27)
至此,我们就不难理解《等待戈多》和贝克特的语言策略获得如此巨大声望和成功的原因所在了。而这种策略的研究使我们能够总结出“将来的创作规则”进而更好地把握后现代主义文化和美学特征。这就是在荒诞派戏剧已成历史的今天,重新研究它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注释:
①马克白语。引自《荒诞派戏剧集·序言》,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②海德格尔语。引自《20世纪西方哲学名著导读》144页:“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湖南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③海德格尔语。《形而上学导论》,参见《读书》1987年7期127页。
④⑤罗伯·吉尔曼语。《现代戏剧的形式》,引自《荒诞派戏剧集·序言》。
⑥(16)(17)(19)海德格尔语。《存在与时间》214页、205页、205页、205页。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第1版。
⑦(21)(22)马丁·埃斯林语。《荒诞派之荒诞性》,引自《外国戏剧》1980年1期76页、80页、80页。
⑧贝克特《等待戈多》,《荒诞戏剧集》,本文所引台词均出于此,后不注。
⑨加缪语。《西绪福斯神话》,引自《荒诞派之荒诞性》,76页。
⑩杰姆逊语。《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版207~208页。
(11)贝克特语。引自福柯《什么是作者?》,《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1992年2月第1版287页。
(12)德里达语。引自约翰·W·墨菲《后现代主义对社会科学的意义》,《后现代主义与文化与美学》172页。
(13)乔约森·卡勒语。《解构主义》,《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521页。
(14)《现代汉语小词典》,商务印书馆1980年2月第1版104页。
(15)《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第1314页。
(18)维特根斯坦语。引自卡勒《解构主义》,《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二卷527页。
(20)(23)(26)欣契利夫语。《荒诞派》,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年8 月第1版113页、21~22页、20页。
(24)利奥塔德语。《何谓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52页。
(25)沁费尔德语。《贝克特剧作的艺术特色》,《外国戏剧》1983年1期80页。
(27)磨·鲁宾语。引自《当代世界戏剧面面观──访〈当代世界戏剧百科全书〉主编唐·鲁宾教授》。《文艺报》1994年5月14日第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