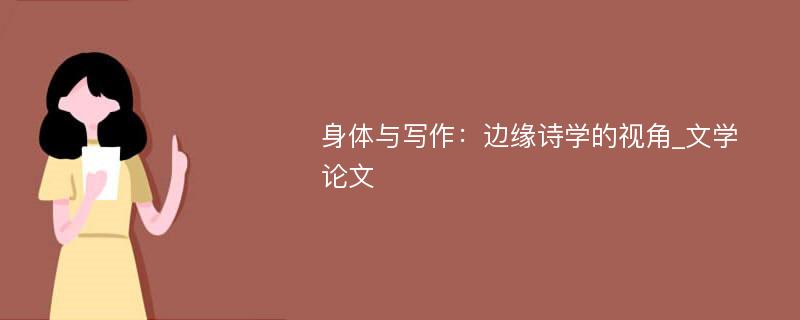
身体与写作——进入边缘诗学的一个视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视点论文,边缘论文,身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293/Z(2004)04-0001-06
一
对写作艺术的关注历来是诗学的基本职能,认为真正的艺术杰作存在着超性别的共同规律,这样的认识迄今仍有影响。不能不承认,在优秀作家的创作经验中具有普遍性的东西。比如创作中那种出神入化的无意识状态,不仅为许多男作家强调,同样也得到女作家们的共鸣。但随着近年来女权运动的崛起,写作的性别意识被提上议程。在很大程度上,如今方兴未艾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便滥觞于文学女性在自身写作活动中性别意识的自觉;正是通过对女性写作特点的深入把握,进一步推进了边缘诗学的建构。
问题来自于伍尔芙对“妇女与小说”的关系所作的这番阐述:“在《米德尔马奇》和《简·爱》中,我们不仅意识到作者的性格,正如我们在狄更斯的作品中意识到他的性格,我们还意识到有一位女性在场——有人在谴责她的性别所带来的不公正待遇,并且为她应有的权利而呼吁。这就在妇女的作品中注入了一种在男性的作品中完全没有的因素。”[1](P54)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后来的“女权主义文学妇女”们的呼应。如著名加拿大女权主义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也以“女人通常不写男人喜欢的那种小说,但是男人是以写女人喜欢的小说而闻名”[2]这一发现,对诗性写作中的性别差异给予了强调。在女权主义批评家看来,对写作活动中一直存在的性别意识的忽略本身,就是对女性群体的一种歧视。法国的埃莱娜·西苏女士说:“大部分男女读者、批评家和作家们是出于无知而不愿承认或者公然否认女性与男性写作之间具有区别的可能性或相关性。”这意味着“迄今为止,写作一直远比人们以为和承认的更为专制地被某种性欲和文化的(因而也是政治的、典型男性的)经济所控制。……整个写作史几乎都同理性的历史混淆不清,它是菲勒斯中心主义传统的历史。”[3](P192-198)
时至今日,对女性写作特点的强调早已成了女权主义批评活动的一种共识。香港的陈顺馨女士通过对女作家凌叔华的短篇小说《酒后》与男作家丁西林改编的独幕剧的比较确认:“性别这个因素在文学创作中是不可忽略的,无论在视角、叙事方式和语言风格方面,都会因女作家和男作家在经验和性别认同上的差异而有不同的表现。”[4](P151)但回过头来看,在相当一段时期里,对女性写作特点的视而不见来自对女性独特创造力的怀疑,而这种怀疑又与女性写作中一度普遍存在着的受男性写作影响,不无关系。伍尔芙曾分析,由于缺乏明晰的历史传统,使得女性在投入到文学写作时常常面临一种十分尴尬的局面:虽然身为女人其实无法从那些伟大的男作家那里得到真正的帮助,但仍会为他们成熟的写作艺术所吸引。“看过女人的作品就觉得男人的文章是如此直截坦白。我们可以看出来思想的独立,体魂的自由,自信的坚强。这些都令人羡慕不已。”[5]虽然伍尔芙对《失乐园》里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男权主义难以忍受,批评作者是“最早的男权主义者”;但也还是情不自禁地赞叹:“弥尔顿以大师的手笔,对诸天使的身形、战争、飞行及住所给予优美的描述,构成了这部作品的主要内容,令人神往。”[6]埃丽卡·琼的自白也是一个突出的案例。这位当代美国女权主义作家在其自传体著作《我挡不住我》里承认:“我想要写一部《战争与和平》,否则,宁可不写。我可不愿写所谓的‘闺秀派作家’之流的作品。我的题材将涵盖战争、斗牛和丛林狩猎等场面。可是到目前为止,我搜罗到的题材不外乎‘琐碎’和‘婆婆妈妈’之类,却达不到任何的‘深度’或‘阳刚味’,令我深深感到挫折和苦恼。”[7](P83)同样还有曾说过“我非常崇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王安忆,由于反感一些女性写作的小格局而虽身为女性但表示“不喜欢被称作女作家”。[8]
诚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观念多少仍可以被看作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范式遗留下来的一种心理阴影。杜拉斯说过:多少世纪以来,女人都是由男人来教育的,男人告诉她们对男人来说她们是低人一等的。针对蒲伯所说的“大多数女人完全没有个性”,杰出的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写道:“我一点也不相信这是妇女与生俱来的,这只是环境对她们的自然结果。”他认为,“假如妇女同男人不住在同一个国家,从未读过他们的作品,妇女就会有自己的文学。”“如果有可能,留给她们的或是很多空闲时间,或是很多精力和思考的自由,去专心致力于艺术或思索,那她们必定比大多数男人有大得多的创造性的活动能力。”[9](P322-326)伍尔芙甚至曾大胆假设:莎士比亚有一位叫“裘底斯”的拥有特殊天才的妹妹,她和他一样渴望着去闯荡世界建功立业,但先是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教育,再是无法像她兄弟那样自由地投身于舞台艺术实践;即使她有勇气拒绝服从传统固执的父母为其作出的婚姻安排只身出走,也会被一位不负责任的男人所骗。最终在严峻冷酷的现实生活里悄悄自杀,就此无声无息地从这个世界消失。所以对于作为男权世界里的弱势群体的女性,文学写作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这种意义凸现于妇女在历史上一直所处的“沉默”状态。一部世界史讲述的从来都是关于男性们的故事,如同伍尔芙所说,关于我们的父辈我们总能知道一些事实,但是关于我们的母亲、祖母、曾祖母们却是一无所知。偶有诸如埃及女皇与武则天等事迹记载,不仅都是男性枭雄们的配角,而且也大多是对女性的一种“妖魔化”:女人是祸水,“能够在历史上留名的女性多是美丽倾国或亡国的女子。”[10]
对女性的这种历史剥夺首先就是对话语权的剥夺。埃德温·阿登纳一言以蔽之:长期以来,妇女构成了一个“被压制了声音的群体”。[11](P173)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伍尔芙曾引用温澈西夫人的诗句指出:“一个尝试写作的女人/被人认为是这么狂妄的东西/以致再没有美德能赎回这个过错。”因为文学写作在实质上是突破沉默的言说和对个体自我的确认,这意味着向男权中心地位的挑战。所以艾德里安娜·里奇指出:“对妇女来说,这种试图了解自己的做法,不单单是为了寻找个性;它是我们拒绝在男性统治的社会里自我毁灭的一部分。”埃莱娜·西苏也写道:“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本文,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她强调,妇女“必须写她自己,因为这是开创一种新的反叛的写作。只有通过写作,通过出自妇女并且面向妇女的写作,通过接受一直由男性崇拜统治的言论的挑战,妇女才能确保自己的地位”,“现在是妇女们用书面语和口头语记载自己的功绩的时候了。”[3](P124,188,195)如此看来,当埃丽卡·琼表示:“我写作的目的就是获得爱和关怀。”“我们写作是为了进入自我,为了盖房子和拥有自己的花园,为了立下声名和历史,并且在人生的旅途上不断创造自己。”[7](P165,223)这并不能仅仅被视作如同男性那样的个体功名欲,还具有一种性别反抗的意味。对于女性,文学写作既是个体的一种安身立命的手段,也是生命中的一种难以承受之轻,是她们书写自身历史的一种方式。
二
爱默生曾经说过:一个诗人的诞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大事。那么似乎也可以说一位女诗人的诞生是自那以后的又一件大事。法国诗人兰波曾经预言:当妇女身上的重重束缚被解除,当她们能自为自主地生活,当男人们允许她们走自己的路时,她也会成为诗人!概括地来看,文学写作中的性别差异主要表现于“为何写”与“写什么”以及“如何写”等三方面。
首先就动机而言,许多知名男性作家表示,小说写作对于他们除了作为一种带有游戏性乐趣的活动与认识方面的好奇心之外,还有着被视为一项事业的考虑与生活的补偿性满足。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尔克斯的这一意识无疑是具有代表性的:“我认为小说是用密码写就的现实,是对世界的猜测。我始终在进行试验,写小说的乐趣就在于此:探索、发现、革新。”他坦承:“我希望达到的目标是发现自己一夜之间毫无思想准备地变成了一个名人,一个人人想见的人,人人想与之讲话的人,人人想与之建立联系的人。”[12]略萨在回答“为什么写作”的问题时也说:“因为不幸福,我才写作。从根本上说,我写作是因为这是一种与不幸作斗争的方式。”[13]而对于女作家们,在其表面的以“职业性考虑”取代“事业化追求”的深层,另有着一种性别文化的意义。王安忆曾经表示,“写作的初衷只是为了找一条出路,或是衣食温饱,或是精神心情,终是出路。”从这听上去似乎很个人化的表达中,能够看到诗性写作与女性性别之间所具有的一种亲和性。就像王安忆所说,首先“文学的初衷其实就是情感的流露,于是,女人与文学在其初衷是天然一致的。”在陈染关于“文学是比较温和的,它是探讨人性问题,这比较适合我”[14](P110)的陈述中,有着同样的性别选择。其次在文体方面,女性在诸如日记与书信等叙事方面所具有的一种相对的性别优势,使她们容易进入到小说文本的建构活动中去。再就是文学写作在方式上对于女性群体显得较为适宜。埃丽卡·琼说得好:“在女性仍被视为第二性的世界,许多女性仍梦想要做个作家,如此可以在家里工作,有自己的工作时间,同时兼顾到育婴的工作。写作看来很适合女性。”[7](P223)
但归根到底,女性写作的社会动力是一个边缘群体的自我表现。就像伍尔芙所说,无论女人们如何为那些由男性所创作的经典文本所吸引,最终仍会失望而归。不仅是因为它们赞扬男性的美德、注重男性的价值、形容男性的世界,还因为这些书里面含有的情感对一个女人是不能了解的。女性写作的意义同样也体现于对自身价值的这种呈现,之所以“一部妇女的书决不会像男人的书那么写法”,就是因为“在生活和艺术之中,女性的价值观念不同于男性的价值观念。当一位妇女着手写一部小说时,她就会发现她始终希望去改变那已经确立的价值观念:赋予对男人说来似乎不屑一顾的事物以严肃性,把他所认为重要的东西看得微不足道。”[1](P57)所以真切地从女性的视野出发,人们将发现存在着一片为女性所独有的艺术表现领域。比如加拿大女作家罗萨林·麦克菲,以一位被诊断患了乳癌的女人的生活变化为题材的小说《毕加索的女人》。不同于一般的绝症,乳癌不仅在于从生理上对生命存在构成巨大危胁,还在于从精神上摧残人的生命意志,使生命主体失去求生的动力。故而在小说里,成为叙述者对自身生活进行自审与调整契机的乳癌,同样也成为作者对所有女性的生命历程作出独特把握的视点。又比如美国作家安娜·昆德伦表现家庭暴力的小说《伤痕累累》和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的名作《紫色》。前一个故事里的女主角弗兰尼实在无法忍受当警察的丈夫的拳脚,而终于带着独生子离家出逃。后者讲述了一个叫“茜莉”的出身于贫苦黑人家庭的小女孩,在遭受了继父的性虐待和被丈夫折磨后最终从同性伴侣中得到一份慰藉的不幸遭遇。在这两个故事里,女人作为“第二性”的痛苦体验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有批评家发现比利时出生的萨滕的日记体散文《过去的痛》里缺少“强大的男性人物”,而萨滕在接受这一批评的同时所指出的“在男人的文学中伟大的女性同样也很罕见”[15],这无疑也是事实。在男作家的笔下不无文学世界里最美丽的女性形象,比如托尔斯泰的安娜、梅里美的嘉尔曼、雨果的艾丝梅拉达、巴尔扎克的鲍赛昂夫人、哈代的苔丝、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以及茨威格的那位“陌生女人”。她们尽管门第有别、年龄不等、种族也有差异,但除了无与伦比的美丽与魅力,以及大都还具有内在的高贵与善良,惟独缺少真正坚强自立让人敬佩的品格。按照通行的文化认同,这种通常以“大丈夫精神”来命名的品格只能是那些卓越男人所特有的品格。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一种性别的自恋法则和接受原理:受无意识的自恋心理驱使的男人总是会在一种性别优越性的支配下,成为作为客体的女人魅力的最佳消费者。但这种消费心理同样也阻止了男人们平视地给予女人以主体位置,那些表现出坚强品质与独特个性的女性形象也只是增加了自身的消费价值,并不具有真正伟大的特点。被批评家认作“纯粹的作家”的玛格丽特·杜拉斯曾经向世人坦白:“我是个彻底的自恋狂。”[16]虽然这听上去似乎有点令人不安,但其实并非如此。从人类学上讲,自恋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文化基因,它是个体自尊自爱自保的生命基础,也是审美与诗性文化赖以滋长的根据地。文明的发展并非是要克服自恋,而是使之门户开放,最终容纳天地宇宙于一体。从而通过自恋而学会珍惜人生、品味生命与存在的意义。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艺术创造就是这种被放大了的自恋的一种符号化表现,这在文学写作活动中尤其鲜明。
所以,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战士保尔到金庸世界里的天下第一英雄萧峰,那些光芒四射英雄伟岸的大丈夫形象通常总是在男性作家笔下诞生。同样道理,只有在文学女性的作品里,才有可能出现那种真正能够平视男性英杰并与之相媲美的女性形象。玛丽·沃德对《简·爱》的分析颇为精辟:尽管这部小说的结构是老一套的,情节的安排上不够艺术性,总的布局也显得平庸,观念不够深刻;“但这本书却是新颖独到的”:通过女主人公简的形象的成功塑造,表现出了女性的生命力,一种“个性——坚强、自由、激越的个性——乃是这部书中唯一的但足够的魅力。”[17]无可置疑,对女性生命力的这种漠视正是父权专制文化的基本特征。穆勒早就指出,当人们为那些气壮山河的男人们所折服时,常常忽略了一件事实:那就是在这些大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位了不起的母亲。温柔与文雅是女性身上常见的两大美德,“这两种道德影响的结合便产生了侠义精神”,这是女性文化“影响人类道德修养之顶点”。所以“如果妇女仍处于从属地位,侠义标准行将消失”,[9](P336)反之,女性一旦走出男权文化造成的自虐心理,终止对男子汉神话的迷恋,便常常会热衷于展示其对“小男人”的种种发现。
三
问题不在于对女性的赞美和对男性的批评。在男性作家笔下也会出现伟大的女性形象,比如高尔基的“母亲”;也不乏受批判的男性形象,比如雨果《巴黎圣母院》的主教弗洛诺、莎土比亚《奥瑟罗》里的亚古、哈代《苔丝》里的让天真美丽的苔丝因爱丧命的富家公子。无须赘言,这种赞颂是彻底的,批判也是深刻的。但在男性作家以母性化来对女性作出赞颂时,其实已经将女性拔高为不具自我意识的“超人”,使之成为男性的一种精神慰藉;并以此对那些拥有主体意识的女性,以女妖的命名进行排斥。所以埃丽卡·琼写道:“母性仿佛一个陷阱,无论对我母亲、祖母和历史的女性而言都是如此。”[7](P275)日本的水田宗子女士更是强调:无论是将女性升华为母性来歌颂还是将之描述成妖魔来贬低,都是对女性形象的神话化。当代女权主义批评所要做的是,认清这种以母性/妖女模式展开的女性神话是一个阴谋,“把女性神话化是向往专制主义重要的一环”,其中的“母性神话是近代人超越个体向往专制主义的根本意志的产物。”[18]或许此盲有些过重,但认为在男性作家对母亲型女性的这种赞美中存在着对女性主体意识的某种遮蔽,这并不过分。因为将女性神话化也就是将女性非人格化,尤其是当女性魅力被视作妖女习气来疏远,作为生命个体的女性的自我意识也随之被抑制。此外,上述这些男性作家对丑恶男性形象的塑造并不是对男性生命作出自审,而是对普遍人性中的缺陷的揭露和对不合理的社会体制的批判。以此看来,通过女性意识的审视来丰富诗性文化对人类生命世界的表现,使原本极不平衡的艺术建构得以全方位的展示,这是女性写作带来的最大收益;通过自身的生命体验写出一直被男性文化所抑制的女性的勃勃生机,这是女性写作所无可替代的艺术使命。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理论提出,话语的真理性不仅在于它说什么,而且还在于它怎么说。陈顺馨以其对当代中国“十七年文学”的研究表明,女性叙事话语虽然在内容和主题方面与男性无大差异,对主流意识形态也是认同的,然而在“怎么说”这个方面仍显出了有别于男性话语的某些特质。这个发现颇能给人以启迪。比如茹志娟和赵树理都曾写过有关妇女解放的作品,但采取的视点不同:茹志娟喜好以“内视点”的方法叙述故事,使得她所描写的女性人物能给人一种感同身受的效果;而赵树理则习惯于“外视点”展开情节,偶尔进入人物的内部意识也会表现出某些障碍。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女性的写作实践能“自然而然”地拥有这份差异。正如陈顺馨通过对杨沫与孙犁的比较所作的“跨性别叙述”的分析:杨沫在《青春之歌》里有意无意地采取了男性化的叙述,不仅常从男性人物的角度审视女主人公,而且着眼于林道静如何在代表党的男人们的帮助下成为一名“战士”的历程。与此不同,孙犁则更多地表现出了一种接近于女性的叙述方式,注重于对人物的内心情感的把握与理解。[4](P75)这就像一些女权主义批评家所一再指出的:“女人写作”并不等于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写作”,事实上许多文学女性的创作恰恰体现了男性的立场。所以,即使是那些看似从女性的自我体验出发,通过“颠倒位置”的方式将女性的性意识置于中心的文本,同样也难以避免落入传统的男权观念的陷阱。
女性写作所面临的这种自我异化,首先来自于与审美接受与市场需求方面迄今仍然存在联系的性别制约。艾德里安娜·里奇曾指出:尽管弗吉尼亚·伍尔笑是在对一群女观众演说,但她清醒地意识到,她还被男人们偷听。这让她多少得有所顾忌,因为对于广大的文化消费者,男性的影响不可低估。在某种意义上,那些“无名”的普通消费者“天然”地是男性文化的盟友。这种市场心理无疑会通过对出版者施加压力和对文学女性提供诱惑,而使女性作家自觉不自觉地削弱自主意识来迎合这种格局。此外,女性写作的异化也来自于语言规则。西苏说得好:我们应该把文化置于它的语词中,正如文化把我们纳入它的语词和语音中一样。这就意味着“我们自降生人世便进入语言,语言对我们说话、施展它的规则,甚至说出一句话的瞬间,我们都逃不脱某种男性欲望的控制。”[19]男性文化的控制首先就表现于他对语言交往规范的控制上。艾德里安娜·里奇便承认:“我知道我的风格首先是由男诗人形成的。”[3](P129)所以,女性写作的确立,有赖于文学女性对现行写作体制的“叛逆”,在此,写作主体对自身体验的分析梳理仍是主要的资源。因而对于一些文学女性提出的“身体写作”的主张,需要认真对待。
杜拉斯说过:“作家的身体也参与他们的写作。”[20](P75)埃莱娜·西苏也提出:“通过写她自己,妇女将返回到自己的身体。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只有到那时,潜意识的巨大源泉才会喷涌。”她建议女性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来为自己开辟出一条通往写作之路,“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因为“男人们受诱惑去追求世俗功名,妇女们则只有身体,她们是身体,因而更多的写作。”她表示“我从未敢在小说中创造一个真正的男性形象,为什么?因为我以躯体写作。我是女人,而男人是男人,我对他的快乐一无所知。我无法去写一个没有身体、没有快感的男人。”[3](P192-204)陈染同样表示:“我还是一直很认可人的生物基础。”[14](P86)对于这些来自优秀的文学女性的经验之谈,我们不能以生理本质主义来看待。事实上,虽然女人写作未必就是真正体现自立自足的女性意识的女性写作,但无疑是实现女性写作所不可缺少的前提。对于人的生命构成,自然与社会间存在一种张力关系:一方面人的自然性通过文化性方能得以呈现,另一方面它也对人的社会性形成制约,人类文化的发展同样也得以自然条件为前提。所以,即使是提出了“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这一思想的波伏娃,同样也在结束其《第二性》时对性别构成的这种生理基础给予了强调:“男女之间永远存在某些差别,她同她自己的身体、同男性的身体、同孩子的关系,将永远不会和男性同他自己的身体、同女性的身体、同孩子的关系完全一样。”一种真正属于女性自身经验的表现,归根到底在于自立精神。正如琼所说:真正的女性立场并不意味着与男性对立,更不是对男性的仇恨,而是终止对男性的迎合与屈服,实现同男性的平等相处。所以,女性写作不可能也没必要回避对女性内在性意识与爱欲需求的表现,关键在于能否以一种平等、坦然的心态深入到女性真实的内在生命。
所以,实践身体写作并不仅仅只是对女人的性需求进行淋漓尽致的展示,它意味着以感同身受的方式对人的生命感觉作全方位的提取与把握。杜拉斯说过:“我有许多思想,我要把它炫示于外,小说有时就是证明。”但不同于男性作家们通常表现出的对所谓“大题材”的偏好,杜拉斯的女性视野让她选择那些细小的事物和微不足道的景象,就像她在一首诗里所说:“好好看看雨和生命/看看暴风雨、寒冷、虚空、失去的猫、这朵花和你。”因为归根到底,文学写作的意义不在于传达符号化的“思想”,而是捕捉身体性的“感受”。这就需要创作主体的生命投入,用杜拉斯的话说,“这种自身向作品转移的过程,就是写作本身。”[21]因而可以这么认为:正是通过女性写作的自觉,人们对诗性创作与生命的关系有了较以前更为深入的认识,也对其表现方式有了更加丰富的把握。杜拉斯有一个十分精辟的见解:男人可以建筑许多房屋,但不能创造一个家。女人就是家,她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由女人创造出来供人安居其中的家,这就是乌托邦的所在。[20](P48-58)以女性所具有的那份温柔写出一种独特的温馨,无疑是女性写作所具有的诗性优势。
卡露尔·斯皮查克和凯瑟琳·卡特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当一个女子说,“今天天气不错,你说是不是?”她会被认为是缺乏权威感,因而她的能力就要打折扣;但当一个男子说这同样一句话时,他就被看成一位开放性的和蔼的谈话对象,因而他的交流能力就被拔高了。[11](P162)对这样的性别歧视实行颠覆的最好方法,是让作品自身来言说。比如丹麦女作家凯伦·布里克森的名著《走出非洲》,在这部以散文体方式写成的具有纪实性的叙述文学里,同样有着以奇特壮观的大非洲景象为背景的远途打猎狮子、坐飞机在高空翱翔、参加土著居民的歌舞表演等传奇生活场景。但作者的女性立场使她的叙述重点着眼于以农场生活为中心的个人体验:“在黄昏的寂静里,我们的生命仿佛随着时钟的滴嗒声一点一滴地流逝。”作者让我们在她的回顾里走近索马里的妇女和老人,草原上的蜥蜴与萤火虫、猴子与鹦鹉,以及吉库尤大酋长和来来往往的各路客人,还有在家里帮工与她一起渡过了非洲生涯的当地的厨师、小随从等。通过这些,作者不仅真切地写出了非洲,让我们感受到了那变幻的云朵下面的乞力马扎罗山周边绵延起伏的黛色峰峦;而且也表达出了她对土地、自然、人类的热爱,和对友谊与爱情、事业与工作等的独特理解,是对生命的深思。如同作者在书中所说:身处非洲草原你会觉得“草是我,空气和隐约的远山是我,疲惫的牛群也是我。”[22]布里克森的文学实践表明,对人类命运与存在意义的思考不仅可以像托尔斯泰那样借助于重大的战争时空展开,同样也能够依托于平常的和平环境进行。所以,随着女性写作走向成熟,作为一种诗性品格的伟大并不会消失,而只是其内涵变得更加深厚而丰富。
标签:文学论文; 女性写作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小说论文; 性别文化论文; 杜拉斯论文; 读书论文; 作家论文; 母亲论文; 女性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