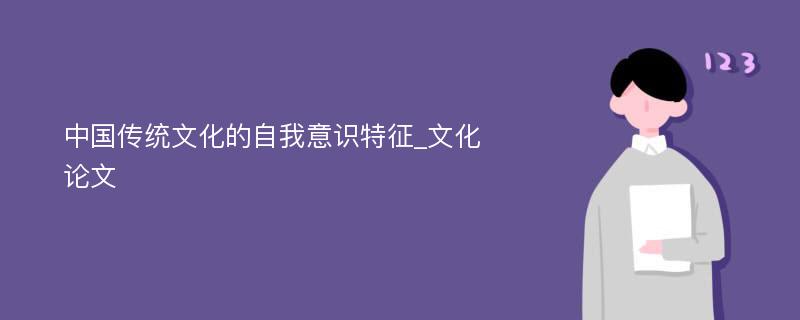
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意识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文化论文,自我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透过儒道禅三角结构,我们可以体味到中国文化中自我意识的独特魅力。
⒈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超强的自我中心倾向。在西方古代文化中,弥散着强烈的自卑意识。这种自卑意识的根源在于神人分离、神人对立。在上帝面前,人总是感到自我的渺小和有罪;把自我置于上帝无所不在的监视之中;总是期望诚心诚意的忏悔可以求得上帝的谅解。中国传统文化则是神人一体,神性和人性相通,甚至就是人性之中。孟子讲“善端”,禅宗讲佛性,都不在彼岸而在此岸。不仅如此,神常常就是人。皇帝曰:“真命天子”,英雄圣人死了都升为星宿,光照人间。天存在的目的再明白不过,是为了人的。
西方那种科学和宗教、心灵和肉体、自然和人生并存的二元论,对中国人来说是不可理喻的。在中国人看来,人就是凝天杰地灵之所在,肉为心生,地为人生,天佑人生。真正的人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在人之外,没有更优越的存在。神不过是完人,天道不过是人道,如果人是卑污的,天道绝不会是崇高的,。而在古人看来,天道堕落是不可思议的。这种事情只发生过一次,就是共工的反叛,最终天还是被女娲补上了。
⒉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不是“小我”,而是“大我”。在西方古代文化中,“我”就是个人之我,就是区别人与自然之我。这种自我意识就是分化神人、天人、个人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则相反,是一种反分化的直觉的整体意识。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人的最高理想。北宋哲学家程颐说:“道未始有天人之别,但在天则为天道,在人则为人道。”①张岱年先生指出:“天人既无二,于是亦不必分别我与非我。我与非我原是一体,不必也不应将我与非我分开。于是内外之对立消弭,而人与自然,融为一片。”②
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什么独立的东西。没有天国地狱,没有内心外物。按照董仲舒的说法,天地万物都是与人相应的存在。西方人从自然中看到的是与人毫不相干的自然规律。为达此目的,他们千方百计发展逻辑推理、实验手段,以排除人为干扰。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思义的。虽说天行有常,然超人之常对中国人来说是索然无味的。上升到哲学意识,这无非是说,凡非我之存在,均属天意义之存在。
中国传统文化中鲜有“个人”的概念。杨朱为我,一毛不拔,被后人骂了又骂。于是,人人都相竞拔毛,以利天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即家,家即国。成人的标准是安家立业,成圣人的标准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通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个人和社会扯不断理不清地纠缠在一起,恰如俗语说“牵一发而动全身”。个人是整体的零件,这种意识是根深蒂固的。所以中国人鲜有李尔王追问“我是谁”劲头。“我是谁”对中国是不言而喻的,我是老人或儿子,我是天子或臣子,只要看到别人,立刻就知道自己。中国有句古话:“知足者常乐”,个人的自我总是自满自足,不证自明的。
⒊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不是理智的,而是实践的。在西方人看来,哲学就是爱智慧,即使基督教主张信仰主义,经院哲学家们仍用理智和逻辑的方法千方百计为上帝的存在寻找证明。西方人追求自我,首要的目标是求真。中国人一向不愿为此费力。理智的作用是区分事物,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反对的东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超越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道家强调坐忘,佛家主张顿悟,儒家坚持知行合一,没有一个以理智为宗旨。只有春秋战国时出现过讲究逻辑的名家,也是昙花一现而已。
坐忘、顿悟、知行合一,都强调的是一种行为体验。中国人从不为知而知,求知必有所得。孟子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③研究学问的目的地在于得道,得道便得精神自由。所以,中国人追求的自我不是认知,而是一种境界。
中国古人达到自由境界的方式,并不是掌握自然规律,获得行动自由,而是一种道德反省,即传统意义上的实践。道德反省的实践是一种自我完善的活动。它追求一种最高境界,但不是通过理智去认识,而是通过生活实际去身体力行,最终了悟到这种最高境界的存在。坐忘、顿悟、知行合一,都是通过生活实际达到道德完善的过程。对中国人来说,自我的实现不是真理问题,而是道德问题,是真善合一问题。
中国古代文化素有深厚的伦理实用主义倾向。对不可实践之物,要么根本不加思索,要么敬而远之,这一点使中国人缺乏认真的宗教态度。对于单纯的信仰问题,中国人很少出现宗教激情与狂热,除非信仰涉及政治或伦理问题。比如,近代西方传教士来华,未成为政治问题之前,民间官方,均听之任之;一旦成为政治问题,才举国讨伐。特别是民间,一般都是“临急抱佛脚”、“心到佛知,上供人吃”,对西方人来说,几乎近于对神的戏弄。人们一般并不区别不同宗教,既拜佛又信道,同时还可以去教堂凑凑热闹。
对于自我的丰富和发展,标准完全是政治伦理的、功利的。在中国人看来,没有比道德价值更高的价值。中国人的自我多是道德自我,即人格理想和良心。皇帝贵为天子,但史家有权褒贬,其标准就是有德或无道。中国人正统观念极强,但种族主义情绪却极淡。中国人关心的是“道统”的延续,至于王朝血统是出自贵族还是市井无赖,甚至是汉族还是异族,人们并不过份挑剔。扫荡南宋、南明残余,乃至镇压辛亥革命的主力,并不是“鞑虏”,而是地道的汉族军人。康熙派兵攻占台湾,消灭的本是中国当时最后一个汉族政权,但史家均称之为康熙天下一统的赫赫战功。郑成功的抗清复明收复台湾是统一祖国,他的孙子为保卫台湾与清军对抗就变成了分裂祖国的不义之举。西方文化在中国一直不走运,其根本原因是中国人受其物质文明诱惑的同时,意识到它与中国的“道统”格格不入。所以,人们对西方文化的对抗情绪是根深蒂固的。
⒋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不是变易的,而是永远的。西方人的自我意识是通过自我分析和自我批判,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发展变化,自卑后又自尊,迷信后又反省,从存在到认识,从心理到实践,神性、人性、自然性三者之间,分子又合,合了又分。法国现代著名作家罗曼·罗兰把法兰西精神概括为“欣悦的灵魂”,即一种既不安又激动不断更新的精神,是十分透澈和准确的。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不是分析的和批判的,而是对自我本质的直观把握,因而不是循序渐进的,而是反复体验的。
无论儒家、道家还是禅宗,无论是先秦诸子还是宋明理学,基本精神都是一以贯之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我始终被看成是宇宙的一个部分或阶段,有待于提升到与宇宙一体的高度。所以,中国人的自我既不自卑也不膨胀,始终提倡一种刚柔并用、自强不息的精神。同时,自我的起点和归宿都是自明的,源出于天道,复归于天道,并不为自我争个性和独立性。中国人的宗教态度不虔诚,但也绝不象普罗米修斯那样,敢于公然宣传藐视宙斯。“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不过是诗人的抒怀。在中国人心中,“造反”、“反叛”都是恶的,刑天共工都是对反叛者的惩戒。当然,中国历史上不乏成功的反叛者,但没有一个宣称自己反天道而行自由。恰恰相反,都编一些神话证明自己受命于天,替天行道。中国文化追求的整合不是分化,是和谐不是反抗。
这一点决定中国人远比西方人更为透澈地洞悉自我的归宿。中国人并不坚守自我,而是不断追求超越自我,通过反复的体验,确证自己与天道的同一。中国人已经意识到自我拓展并不是自我存在的目的,转而追求自我确证。儒家主有为,道家主无为,有为也罢,无为也罢,二者目标是一致的,或替天行道,或复归于道。绝不奢求天道以外的自由。在这方面禅宗是最透澈的。相传禅宗六祖慧能作偈云,
“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生生死死,争争斗斗,到头来终免不了万物归一。中国文化中充满了过眼烟云,挥手即逝的伤感,因为人们知道“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反反复复,不过是不断印证自己与天道的距离。
如果把人类自我意识比作山,那么西方文化是盘山而上,激动不安,大汗淋漓;中国文化则攀崖直上,没有台阶,没有论证,没有分析,内心平和地稳坐在每一条盘山道上。当西方人被上帝压得喘不过气来,中国人正安然坦诚,与天道对话;当西方人为发现自我欣喜若狂时,中国人仍安然坦诚,化解自我;当西方人翻然醒悟,自我反省和批判,中国人还是不卑不亢,徜祥于天地之间。戴维·科尔比感叹道:“对于依靠崇信理智威力为生的科学家来说,这个故事的结局就像一场恶梦。他攀越过由愚昧无知构成的一些高山,他就要征服最高峰了;但当他爬上最后的山岩时,欢迎他的却是一群已在岩上坐了若干世纪的神学家。”④西方文化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中国人老早就提出来了”,这并不为夸张。人与自然之间应建立协调关系,自我发展应有节制,不应限于理性,肯定非理性活动的意义,在儒道禅三家中都能找到相应的命题。这一特点体现了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独特价值。中国文化有着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独特视角。
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把文化理解为分化,从整体中发现对立,然后强化对立、明了对立双方的特点。在西方文化史上,二元论不断重复出现,十分类似交响乐的主题曲。古代有亚里士多德质料和形式的二元论,中世纪有阿威罗伊的知识和信仰二元论,近代有康德现象和物自体二元论。对立面的统一对西方人来说,几乎是可望不可及的。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把文化理解为整合,从对立中发现整体、强化整体,明了事物的起始和归宿。在中国文化史上,二元论是罕见的,神人一体、天人一体,能统一的都统一。二元对峙不可逾越,对中国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相比之下,西方文化是侧重发展的文化,注重的是文化变化的实际过程,不断涌现出新观念,但常常不知其所归。从怀疑主义到不可知论,从不可知论到科学主义,对文化的归宿,西方人总是徨惑不已。中国文化是侧重追溯和总结,注重的是人之初和人之所归。庄子感叹道:“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荣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⑤西方人流连于不知其所归的状态,而中国人最怕的就是知其所归。在中国,皇帝为自己造陵墓,老人为自己备棺材。中国人对死是坦然的,认为人固有一死,但要死得其所。中国人的凝重、坦然、通达的性格,就是这种注意总结的文化烙印。
⒌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意识的缺陷。如上特点使中国文化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但作为自我意识,也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文化局限。
(1)整合而不分化,导致文化不发展。文化的特点之一是主题重复和不断自我确证。和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更接近人类的文化主题,神人合一、天地合一、心物合一,是文化追求的终极境界,西方文化分分合合,无非在接近这一主题。中国人在一开始就达到了终点。然而,文化的主题重复是在不断确证中提升,西方文化虽历经曲折,常常陷入多面性,但却不断自我更新。中国文化却在文化主题中坐观西方文化发展至少千年以上,最终成为落伍者,在物质文化上未达到近代科学水平,在精神文化上未产生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普遍真理。落伍的文化的根源在于不重分化,不能不断提出新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的风格不注重开拓新问题,而注重对老问题的再理解,从孔子到五四运动,儒家思想的基本范畴没有重大改变。
对同一问题的重复解释,最终会导致问题本身的常识化。一种问题一旦常识化,就与日常经验融为一体,失去了学术研究的创造性价值。比如,经过数千年教化熏陶,“天理良心”、“动中有静”、“有生必有死”、“名实相符”、“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已成为妇孺皆知的常识。仅仅肯定动中有静,错误难免,方生方死,并不能提高自我意识的水平。这种文化不仅不会发展而且会日益经验化,失去理论探索的意义。
美国现代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说:“除去新涉及的耗费和其他起抑制作用的因素外,中国倒退的关键纯粹是信奉孔子学说的官吏们的保守性,……在这种复辟气氛下,所有重要官吏便都关心维护和恢复过去”。⑥中国文化的确在西方文化所攀登的岩顶坐了若干世纪。它一直坐在那里静观西方文化在盘山道上爬来爬去,这种爬来爬去并不是重复循环,而是在不断前进中发展。文化发展的源泉在于分化,这是中国文化用长期停滞换取的代价。
(2)神人一体,理想境界貌似现实,却没有可实现性,结果导致名实矛盾。神人一体,使中国人以现实的态度对待理想境界,不把人生的归宿推给来世。然而,这种理想境界本身却缺乏可实现性。圣人是人不是神,但却是完人。人作为一种未规定性,根本没有成为完人的可能性。“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中国人深知这一点,所以也未把圣人当成人。圣人、至人、佛始终是可望不可及的目标。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在实践上则是虚幻的。
所以,中国人不得不养成一种伦理实用主义态度,即说归说,做归做;在可实现的问题上,认认真真地知行合一;对不可实现的问题,则束之高阁,作为装饰、纹花。比如,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用死来验明证身,既痛快淋漓,又一劳永逸。死是人生一切矛盾的解决,也是生的凝固,这恰恰符合成为圣人的要求。“盖棺论定”,“为死者讳”,是中国人的自我评价传统。死人不会改弦易辙,不会犯错误,可以保存一个完整形象。死亡就是不存在,对一个不再存在的人的任何赞美都查无实据,心诚则灵。因此,宣扬死人是维护圣人形象的最实用的选择。在以死确证自我方面,中国人是认认真真地知行合一。
然而,对于“浩然之气”、“万物与我为一”这种阳春白雪,中国人只好束之高阁。孟子讲“侧隐之心”,不忍看杀牛,但并不因此不吃牛肉。朱熹讲“存天理,灭人欲”,却“大儒争闲气”,让妓女吃板子。清军入关,儒生们为“尊王攘夷”奋起抗战。一理清朝恢复科举,儒生们大多甘心做雉发蓄辫的孔子门徒。
这种伦理实用主义态度养成一种善于变通的文化性格,即对文化精髓进行名不符实的修正、歪曲。明明知道文化精髓难以实现,又不肯公开改变,另寻出路,于是在保留名份的前提下各取所需。一个秀才的寡母与河对岸的和尚私通,秀才苦于母亲夜渡艰辛,亲修小桥于河上。待母亲死后,秀才杀死和尚。人问何故,秀才答曰:修小桥为母行孝,杀和尚替父报仇。岳飞不敢违抗昏君之命,撤兵丧生,谓之忠,若他效法赵匡胤黄袍加身,夺下天下,也绝不会被视为“犯上作乱”。对于天道,人们未曾斗胆修改,但对历史,人们素来持“成者王侯败者贼”、“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以成败论英雄的观点。再暴戾、再荒淫的统治者,只要夺取天下,稳固统治,人们都心甘情愿地接受。这样,实质上把有道与无道等同于有权或无权,把“天不变、道亦不变”偷换成以吏为师,学在官府。
这种善于变通,名不符实的文化性格,所鼓励的只能是文化精萃有名无实。一方面:名实脱节,势必导致浅层文化和文化弊端大泛滥。文化理想被束之高阁;在实践上造成虚假的自我,或堕入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的形式主义,或蜕变为欺世盗名的文化骗术。另一方面,名实脱节,严重地束缚着文化发展。在文化变迁中,人们竭力保留的往往并不是真正的文化精萃,恰恰是文化糟粕,因为文化精萃只剩下空名,已没有实际内容。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在与英法帝国主义政府外交谈判时,对丧权割地赔款并不分寸必争,却对是否允许外国使团驻节北京晋见皇帝一步不让,千方百计所要保存的是面子。而蜕变成空名的文化精萃,却成为文化发展的桎梏。要变,却要千方百计保留名分。对新文化,取舍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名分。在鸦片战争之后,许多中国人明明吃了西方技术文明的大亏,却仍然坚持认为技术是匠人的雕虫小技,为徒有虚名的礼仪之邦而夜郎自大,其根本原因就是依照士农工商的等级名分,技术是下九流的东西。
(3)天人一体,天高人低,人的自我缺乏独立性。中国人的自我作为大我,有强调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相统一的优越性。但是,自我只有获得相对的独立地位,才能显示出自我与外物的根本区别,才能更新发展。中国人的传统自我始终与天地社会处于绵延、粘连的状态。中国人对自我的追求,不是自我的独立性,而是自我的化解。
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意识只是自我的原始状态,天地、心物、人我浑为一体,还有待于上升到成熟阶段。自我意识不成熟的标志就在于不分化。有分化的整合与无分化的整合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别。有分化的整合是辩证的自我意识,无分化的整合是直观的自我意识。
由于缺乏分化,直观的自我意识只能达到一种缺乏真理的道德自我。道德和真理不同,是约定俗成,沿袭传统的。一种道德可以是有权威的,但未必是合理的。传统在形成之初,往往都是客观规律的反映,是合理的,但如果传统不随社会更新,就将丧失其合理性,保持道德自我合理性的唯一办法,就是按照真理的发展调整道德自我。近代西方文化强调个性自我,有其近代科学的基础。经验科学有两个基本原则:在经验事实面前人人平等,真理是独立思考大胆创新的产物。由于古代中国缺乏系统的科学理论,其自我意识只能停留在封建宗法桎梏的束缚之中。
整合而不分化,有名而无实,有自我而不成熟,是中国传统文化弊端所在,障碍了自我意识的发展。就抽象的、终极的意义看,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意识博大精深,综合达观,优越于陷入自我对立、自我分离之中的西方文化。尽管现代工业化使西方文化独占鳌头,却始终无法取代中国文化的位置。就具体的、现实的意义看,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意识是非发展的、非现代意义的,需要经过加工改造,才能在现代实现其独特价值。
注释:
①《二程全书·语录》。
②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2年,序论,第7页。
③《孟子·离屡》。
④戴维·科尔比《简明现代思潮词典》,重庆出版社1987年,第23页。
⑤《庄子·齐物论》。
⑥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