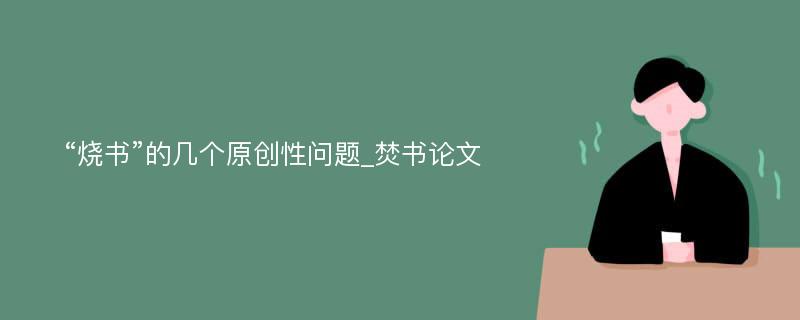
《焚书》原本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贽是我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大家,是近百年来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人物,其《焚书》是公认的研究李贽的最重要的材料。然目前我们所见的《焚书》都是在万历年间惨遭禁毁之后重新编刊的,且都刊印于李贽身后多年。因此,《焚书》的原貌究竟如何?现存的《焚书》是否都是李贽的作品?这应该是研究李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可是自从十九世纪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先驱者吉田松阴开始重视李贽,逐步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研究李贽的热潮以来,虽有个别学者如胡适曾明确怀疑过《焚书》的可靠性(注:胡适《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今所传《忠义水浒传》,大概出于李贽死后。因为他爱批点杂书,故坊贾翻刻《水浒传》,也就借重这一位身死牢狱而名誉更大的名人。日本冈岛璞翻刻的《忠义水浒传》,有李贽的《读忠义水浒传序》一篇。此序虽收在《焚书》及《李氏文集》,但《焚书》与《李氏文集》皆是李贽死后的辑本,不足为据。”见《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37页。),但后来者鲜有认真地关心过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以致目前有的所谓校本也于此不置一词,在广大读者乃至一些学者的心目中,早不辨《焚书》的原貌如何了。今笔者不揣愚陋,提几个问题供同好讨论。
《焚书》原本当为几卷?
目前所存多种明刊《焚书》,及最为通行的中华书局1960年排印本与1974年修订本的基本格局大致相同,都为六卷:卷一“书答”,卷二“书答”,卷三“杂述”,卷四“杂述”,卷五“读史”,卷六“四言长篇”等。但考察李贽自己当年所言及有关记载,原本当为两卷。
下面,不妨将李贽自己谈及《焚书》的文字摘录于下:
一、《焚书》卷一《答焦漪园》:“……更有一种,专与朋辈往来谈佛乘者,名曰《李氏焚书》,大抵多因缘语、忿激语,不比寻常套语。恐览者或生怪憾,故名曰《焚书》,言其当焚而弃之也。见在者百有余纸,陆续则不可知,今姑未暇录上。”
二、《焚书》卷二《与河南吴中丞书》:“……兹因晋老经过之便,谨付《焚书》四册,盖新刻也,稍能发人道心,故附请教。”
三、《续焚书》卷一《与汪鼎甫》:“发去《焚书》二本,付陈子刻。恐场事毕,有好汉要看我《说书》以作圣贤者,未可知也。如无人刻,便是无人要为圣贤,不刻亦罢,不要强刻。若《焚书》自是人人同好,速刻之!但须十分对过,不差落乃好,慎勿草草。”
以上三则材料可说明两个问题:
一、从内容看,原刻《焚书》是“专与朋辈往来谈佛乘者”,亦即《焚书自序》说的“答知己书问”,其中主要部分可能就如袁中道所说的是“与耿公辩论之语……遂裒之为《焚书》”(《李温陵传》)。换句话说,《焚书》的原刊只是“书答”,别无他文,而现存《焚书》的“书答”即为两卷。
二、从篇幅看,原刻《焚书》曾将稿本订成“二本” “百有余纸”,刻本装成“四册”。百余纸的篇幅分成两卷四册,也合当时出版物的一般装帧情况。
今考察目前国内外所存明刊《焚书》的实际情况来看,均叶九行、行二十字,虽这六卷书的装订并不相同,但均可证明两卷“书答”即“百余纸”,且也可装订成四册。其具体情况如下:
一、四册装本,卷一为60叶,卷二为59叶,共119叶,即与“百余纸”的说法相合。两卷合订成一册。
二、五册装、六册装本,卷一标66叶,由于第52叶的叶码刻成“五二之五八”,虚标了6叶,故实际上也是60叶,装订成一册;卷二亦标为66叶,由于第11叶刻成“十一之十八”,虚标了7叶,故实际上也是59叶,亦装订成一册。两卷“书答”亦共119叶,但装订成二册。
三、十册装本,其叶码标号,同五册装本与六册装本,二卷均虚标为66叶,但实际也共119叶。不同的是,它将二卷分装成四册,第一册是卷一的第1叶至第31叶,第二册是卷一的第32叶至第66叶;第三册是卷二的第1叶至第39叶,第四册是卷二的第40叶至第66叶。
由此可见,两卷“书答”确为百余纸,刻本可装订成四册(十册装本即是),抄本或成二本,与李贽自己所言完全符合。
不过,他在《续焚书》卷一《与焦弱侯》也说过“《焚书》五册”的话,但这是指他后来抄写的一种稿本。在这封信中,他接着说:“幸细披阅,仍附友山还我!盖念我老人抄写之难,纸笔之难,观看之难,念此三难,是以须记心复付友山还我也;且无别本矣。”因此,《焚书》的刻本还当是四册二卷百余纸。
除了李贽自己所言之外,又有旁证两则可明《焚书》初刊是两卷:
一、与李贽同时代的同乡何乔远(万历十四年进士)的《闽书·方外志》下卷录沈铁《李卓吾传》云:“所著有《藏书》四十卷,《说书》、《焚书》各二卷,《初潭》四卷,而佛经诸书不与焉。”
二、日本吉田松阴《己未存稿》“与士毅书”则云: “向目肖海(士屋)借示李氏《焚书》,卓吾居士一世之奇男子,其言往往与仆之心合,反覆甚喜。”后于“寄书”则中又云:“李氏二册返璧,此书甚可宝贵。”这里所说的“二册”虽不等于“二卷”,但绝不可能是六卷本,一般说来,还当是两卷本。
总之,李贽《焚书》的原刻当为二卷四册百余纸,仅为“书答”,今通行的六卷本中的后四卷,均为后人所增编。换言之,四百年来所谓的《焚书》,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焚书》。
《焚书自序》是否是伪作?
我于国内外翻过多种明刊《焚书》,一般都无序言,仅见一种明刊,扉页题书名曰《卓吾先生李氏焚书》,后有《首序》一篇,署“会稽陈证圣书”。其序曰:
李卓吾先生以儒术起家二千石;有理学名,然多涉释氏,制行瑰异,措论玄冥,世亦病之,因是祸构,遗稿数十万言,悉焰祖龙。吴人士镌其余而隘之制,议,者曰……。梓成,吴人士征予序,因题数字于弁。
这篇序言比较老实的是,交代了此本是劫后重刊。它于“数十万言”灰烬之后“镌其余”,说明了这是重编。重编的原则是否尊重原刊,它没有说,甚至通篇没有提到过“焚书”两字,因此可以理解为重编进了原《焚书》之外的东西。这篇序言故作狡狯的是,编刊者可能是用了化名。所谓“吴人士”者,可能即是吴地人士之谓也。当时吴郡人士刻印李氏书籍最有热情。用化名是为了避禁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焚书》劫后重编初刊时,可以有、甚至必须有这样的一篇序言,但也必然有聪明的书商觉得这样的序言未若有李贽的《自序》更有销售的宣传力,于是有李贽《自序》以及有其好友焦竑序的本子应运而生了。今查晚明“吴郡赵邦贤刻”《李温陵集》及“姑孰陈文梓”《李氏文集》,卷首分别有一篇《李温陵自序》或《李卓吾自序》。两文内容相同,也与现今通行本《焚书》卷首的《焚书自序》相同。陈刊《李氏文集》是赵刻《李温陵集》的删节本。《李温陵集》二十卷与《焚书》六卷的内容有很多出入,且是后人顾大韶所编。这篇序文既然是后人所编《李温陵集》的《自序》,怎么又拿来作为内容不同的《焚书》的《自序》呢?这是可疑点之一。
再观通行的所谓《焚书自序》开头的一段行文,实从《焚书》卷一《答焦漪园》改头换面而来。《答焦漪园》云:
承谕,《李氏藏书》谨抄录一通,专人呈览。年来有书三种,惟此一种系千百年是非,人更八百,简帙亦繁,计不止二千叶矣。更有一种,专与朋辈往来谈佛者,名曰《李氏焚书》,大抵多因缘语、忿激语,不比寻常套语。恐览者或生怪憾,故名曰《焚书》,言其当焚而弃之也。风在者百有余纸,陆续则不可知,今姑未暇录上。又一种则因学士等不明题中大旨,乘便写数句贻之,积久成帙,名曰《李氏说书》,中间亦甚可观。如得数年未死,将《语》、《孟》逐节发明,亦快人也。
《焚书自序》则云:
自有书四种:一曰《藏书》,上下数千年是非,未易肉眼视也,故欲藏之,言当藏于山中以待后世子云也。一曰《焚书》,则答知己书问,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我矣,故当焚之,言当焚而弃之,不可留也。《焚书》之后,又有别录,名为《老苦》,虽同是焚书,而另为卷目,则欲焚者焚此矣。独《说书》四十四篇,真为可喜,发圣言之精蕴,阐日用之平常,可使读者一过目便知入圣之无难,出世之非假也。
两文行文的逻辑完全相同。不同的是:
一、《焚书自序》将《焚书》的社会作用提得更高,更尖锐,甚至预示着以后“必欲杀我”的结局,从根本上有异于李贽自己的理解而完全暴露了后来者所写的口气。
二、将书“三种”增为“四种”,即加进了一种《老苦》。究竟有没有《老苦》这部书?似乎也有点疑问。这是因为:第一,李贽从来没有明确说有《老苦》一书。不但这篇《答焦漪园》中说“年来有书三种”时没有《老苦》,而且他在《续焚书》卷一《与方伯雨》中谈及自己著作时也没有它;第二,同时代的好友谈及他的著作时亦都不及此,如袁中道《李温陵传》曰:
公素不爱著书。初与耿公辩论之语,多为掌记者所录,遂裒之为《焚书》。后以时义诠圣贤深旨,为《说书》。最后理其先所诠次之史,焦公等刻之于南京,是为《藏书》。
焦竑《李氏藏书序》亦曰:
余知先生之书当必传,……书三种:一《藏书》,一《焚书》,一《说书》。汪可受《卓吾老子墓碑》亦曰:
老子好读书,多所著述,有《焚书》、《藏书》、《说书》之属行于世。
汤显祖《李氏全书总序》亦曰:
世假李氏书夥甚,真出其手者,雅推《藏书》、《焚书》、《说书》。
三、至今未见有《老苦》的传本,亦未见有严肃文字的正式著录。
但是,之所以有《老苦》一书的说法并非纯是空穴来风。袁宏道于万历十八年(1590)写的《得李宏甫书》诗中曾有一句话:“迹岂《焚书》白,病因‘老苦’侵。”至万历四十年(1612),袁中道写《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见《珂雪斋集》文集卷九,同卷《妙高山法寺碑》亦有类同的文字)回忆其兄宏道当年之事又曰:
戊子(1588),举于乡……。明年,上春宫……。一一提唱,聊示鞭影,命名曰《金屑》。时闻龙湖李子冥会教外之旨,走西陵质之。李子大相契合,赠以诗,中有云:“诵君《金屑》句,执鞭亦忻慕,早得从君言,不当有老苦。”盖龙湖以老年无朋,作书曰“老苦”故也。仍为之序以传,留三月余,殷殷不舍,送之武昌而别。
这里的“仍为之序以传”,指的是李贽为袁宏道的《金屑》作序,是明确的。问题是“作书曰:‘老苦’”作何解?假如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写了一本书曰《老苦》”,再与袁宏道《得李宏甫书》中两句对仗的诗联系起来的话,就可肯定李贽确有《老苦》一书。这就使目前一般的标点本往往在这里打上了书名号,《焚书自序》的伪作者显然也是这样理解而增加了一书之作。
但是,袁中道说的“作书曰‘老苦’”句是否可以有另外的理解呢?
假如将“作书曰‘老苦’”理解成“写了一篇文章曰《老苦》”呢?这样不就可以将李贽自己所言及时人著录,与袁氏兄弟所言统一起来了吗!因为就李贽及时人著录而言,《老苦》不是“书”,所以理所当然地不及此;而袁氏兄弟主要意在说李贽有这样一篇作品,就提到了它,两者就没有矛盾,但可证明所谓《焚书自序》是错误地理解了袁氏兄弟的话而妄增了一篇书名。
另外,袁中道的“作书”句,是否可以理解成仅仅书写了“老苦”这两字以抒怀呢?笔者认为这一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这是因为,李贽本来就是擅长书法,何乔远《李贽传》(《闽书方外专》下卷)称其“尤善大书,笔力神劲,铁腕万钧,求之不易得”。书字抒志,也是情理中事。袁宏道从李贽那里得书回来后曾说:“幸床头有《焚书》一部,愁可以破颜,病可以健脾,昏可以醒眼,甚得力。”他也只欣赏“一部”《焚书》,而从未明确谈到有什么《老苦》一书,所以究竟有没有《老苦》一书是值得怀疑的。所谓《老苦》一书,多数是由作《焚书自序》者误解了袁中道所言而杜撰出来的。这也就不难理解《焚书自序》在说到本来就没有的《老苦》时,只能用隐隐约约的文字,模模糊糊地混了过去。
《焚书自序》中还有一个漏洞是“然余年六十四岁矣,……故刻之”一句至关重要的话。这句话,使绝大多数的研究者都轻易地将《焚书》的初刊年代定于万历十八年(1590)。惟见1933年日本铃木虎雄所作的《李卓吾年谱》(朱维之译)有异说。他可能因未见此《焚书自序》,故也未受其惑,考订《焚书》初刊于万历二十年六十六岁。其根据即从李贽《与河南吴中丞书》出。铃木引录李贽之文时,略作了注解(见括号中语),曰:
迩居武昌,甚得刘晋老之力。昨冬获读《与晋老书》(吴与刘之书),欲仆速离武昌,甚感远地拳拳至意。兹因晋老经过之便(此云刘于今夏赴保定之巡抚任,途次河南),谨付《焚书》四册,盖新刻也(《焚书》为此时所刻,亦可知)。稍能发人道心,故附请教。
刘晋老,即刘东星,字子明,号晋川,故称为刘晋老。铃木接着上文又引李贽《寓武昌郡寄真定刘晋川先生》诗八首及《明史》卷二二三刘东星传,以印证刘于“万历二十年(五月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李贽请吴中丞捎“新刻”之《焚书》,当在此时。本来,李贽于万历十八年因《焚书》手稿的流传(袁中郎初得之《焚书》也当为抄本),而使耿定向认为是“闻谤”而大为恼火。万历十九年,蔡弘毅即著《焚书辩》,诬陷李贽,当事者竟要驱逐李贽,一时间他受到极大的压力。正在这时,李贽受到了身任湖广左布政使刘东星的庇护。因此,若《焚书》刻于万历十八年,李贽早该在万历十九年两人相识相知时就相赠了,没有必要待刘东星远离去保定后,再将“新刻”之《焚书》托人捎去。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新刻”两字,可以理解为“新近刚刻印”,也可以理解为“重新刊刻”。在这篇《与河南吴中丞书》中的“新刻”两字,联系上下文字及语气,显然当属前者。“盖新刻也”,即全书新近刚刚刻成,而决没有重新刊刻的意思。因为下一句“稍能发人道心”,显然是对全书的总体评价,而没有丝毫与前刻(假如有前刻的话)相比的意思。前文已述,李贽与刘东星于万历十九年已相识相知,假如《焚书》前已刊刻,一般早会相赠。即使未曾相赠,刘东星也必然会知其内容,现在若送以重刻本的话,必然会谈及与前刻不同的所在,而这里一无所言,故可断定此“新刻”,即初刻也。《焚书》既然新刻于万历二十年李贽六十六岁时,那么说六十四岁刻《焚书》的《自序》显然是胡说了。
这里还要作补充说明的是,前文引录的《与汪鼎甫》中所说的“发去《焚书》二本,付陈子刻”,并不是在万历二十年,而是在万历二十八年李贽随刘东星在山东济宁时。此事在《续焚书》卷一《与方伯雨》中也谈及:“雪松昨过此,已付《焚书》、《说书》二种去,可如法抄校付陈家梓行。如不愿,勿强之。”结合《与汪鼎甫》中说起同时送去的《说书》“不刻亦罢,不要强刻”云云,看来这次重刊比较勉强,最后未必如愿。不久,李贽即被害书毁,也就彻底搁浅了。因此,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焚书》在李贽生前经过多次刊刻,也是经不起推敲的。看来,在李贽生前,《焚书》只是在万历二十年刊刻一次而已,其他均为抄本流传。
最后,如《焚书自序》末所署“卓吾老子题手湖上之聚佛楼”之“聚佛楼”亦甚可疑,因李贽于龙湖,所居芝佛院或维摩院,未见有载“聚佛楼”者。笔者孤陋寡闻,或许真有其“聚佛楼”乎?或者芝佛院或维摩院中有一“聚佛楼”乎?抑或压根儿就没有什么“聚佛楼”,所谓“聚佛楼”者,完全是作《焚书自序》者凭空想象出来的?
《焚书》后四卷是否掺假?
万历四十六年(1618),亦即李贽身后十七年,张鼐为刊印《续焚书》而作《读卓吾老子书述》时说:“卓吾死而其书重,卓吾之书重而真书、赝书并传于天下。”李贽的门人、整理出版者汪本钶对当时伪书的大行说得更明白:“嗟乎,人谁不死,独不得死所耳!一死而书益传,名益重。……至于今十有七年,昔之疑以释,忌以平,怒以消。疑不惟释且信,忌不惟平且喜,怒不惟消且德矣。海以内无不读先生之书者,无不欲尽先生之书而读之者,读之不已或并其伪者而亦读矣。夫伪为先生者,套先生之口气,冒先生之批评,欲以欺人知而不能欺不可欺之人,世不乏识者,固自能辨之。第浸至今日,坊间一切戏剧淫谑,刻本批点,动曰卓吾先生,耳食辈翕然艳之,其为世道人心之害不浅,先生之灵必有余恫矣。”(《续刻李氏书序》)再具体一点,仅就小说戏曲的评点本而言,正如当时钱希言在《戏瑕》中所说的那样:“数年前,温陵事败,当路命毁其籍,吴中锓《藏书》板并废,近年始复大行。于是有李宏父批点《水浒传》、《三国志》、《西游记》、《红拂》、《明珠》、《玉合》数种传奇及《皇明英烈传》,并出叶(按:指叶昼)笔,何关于李?”既然伪托李氏之书一时风行于世,后来者在收集、编集李贽的遗作时,是否能逐篇辨明,非真不录呢?我看在崇李与趋利之心同时驱动之下,在当时出版李著“赶浪潮”的情势中,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而且,当第一套六卷本《焚书》问世之后,后来的商贾往往是照本翻刻,哪里会去管它孰真孰伪?这样,《焚书》的辨伪工作、特别是后四卷的辨伪工作显然是十分艰巨的,而这恰恰是研究李贽的第一步。这里,我作为提出问题,举三例来略作说明。
首先,后四卷中的第一篇,亦即卷三《杂述》中的第一篇《卓吾论略》就可以讨论。此文开头第一句即云:“孔若谷曰:吾犹及见卓吾居士,能论其大略云。”接下去就从“居士别号”说起,一直说到“五载春官”之时,全文都是站在孔若谷的角度上用第三人称写的。当然,此文的具体内容应该是由李贽提供的,但其作者应该是孔若谷:它是有关李贽的重要的传记材料,但不能混同于“卓吾自述”。而且,在包括“吴人士”刊本在内的多种明刊本中,这一篇与极个别篇章与众不同,另有零星旁批,这也是一种非常特殊而令人怀疑的现象。或许有人会说,“孔若谷”者乃“乌有先生”、“亡是公”之流,是李贽虚构的一个人物。这当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此名似乎不类虚构,因此还是有怀疑的余地的。
再看名声很大而被胡适怀疑过的《忠义水浒传序》,见于《焚书》卷三《杂述》;同时也见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刊的容与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与万历四十二年(1614)刊的袁无涯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全书》。后两种《水浒》的所谓李卓吾的批点,目前一般学者都认定是假的或掺假的,是由叶昼、冯梦龙辈所伪造掺假。若从刊行的时间来看,多数是后两种伪托的《水浒》出版于前,而六卷本的《焚书》重编于后。这样就有一个问题,即这篇《忠义水浒传序》究竟是先由叶昼伪造,后由“吴人士”辈编入《焚书》,还是确是李贽先作,再由叶昼等拿来装点门面?我们知道,李贽确实批点过《水浒传》、《西厢记》与《琵琶记》。他在《续焚书》卷一的《与焦弱侯》中说过:“《水浒传》批点得甚快活人,《西厢》、《琵琶》涂抹改窜得更妙。”袁中道在《游居柿录》中也说过他在武昌亲见李贽在“逐字批点”《水浒传》,他又对钱希言说过李贽批点过《北西厢》(见《戏瑕》卷三)。但从未有人说过李贽为一本《忠义水浒传》写过序。且从李贽同时批点的《北西厢》、《琵琶记》来看,均未见有序。就是今存叶昼伪托的、且与《忠义水浒传》同是容与堂刊的《李卓吾先生批评北西厢记》与《李卓吾先生批评琵琶记》也都没有李序。此也可旁证李贽当时只是批点,未曾作序。这些都不能不使人怀疑这篇《忠义水浒传序》有可能是别人伪作的。
与上相关的还有几篇论及《西厢记》、《琵琶记》、《红拂记》、《玉合记》、《幽闺记》等戏曲小说的文章,即《焚书》卷三中的《杂述》与卷四最后的《玉合》等四篇。其中《红拂》一则文字,作为“李贽”的自序也见于叶昼伪批的容与堂刊《李卓吾先生批评红拂记》,其他均未见于容与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评”的曲本。这些文章与上《忠义水浒传序》一样,不能不使人疑窦丛生。张大复《梅花草堂集》卷一《第一不可说》文说:“李卓吾《焚书》载昆仑、琵琶是天下第一等奇事;又载若无母书(按:见《焚书》卷四《读若无母寄书》)是天下第一等文章;却又着‘卓吾子曰’,便觉气韵索然,议论酸腐。此老胸中垒块,下笔无状,其种种可喜可愕之谈载在他书者,且与天壤俱敝矣!”他的这种感觉,也是值得玩味的。
以上只是提出问题,并非就是断定《忠义水浒传序》等即是伪文。《焚书》后四卷中究竟有没有掺入伪文?哪几篇是伪文?还是要细细斟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