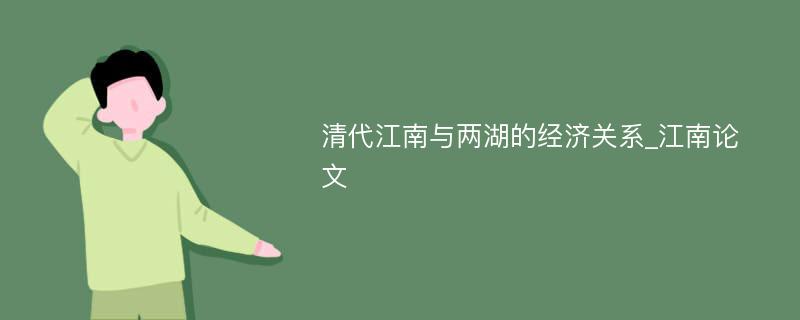
清代江南与两湖地区的经济联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湖论文,江南论文,清代论文,地区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2)01-0013-05
明代,随着江西地区移民的大量涌入,垸田的开垦,各种水利设施的兴建以及优良稻种的引进和改良,两湖地区得到进一步的开发,以稻米为主产的农作物产量提高,至清代更是出现了双季稻的推广。明弘治时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注:关于“江南地区”的界定,本文主要指明清八府一州之地,包括今南京、镇江、常州、苏州、太仓、上海(松江)、嘉兴、湖州和杭州。因为这一范围的江南地区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其内部是一个自然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域,还同属于太湖水系,各地相互发生紧密的联系,且经济水平相近。参见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到万历年间,更有“(湖广)鱼粟之利遍天下”之说(注:张瀚:《松窗梦语》卷4《商贾纪》。)。清代康熙中期至乾隆后期的十八世纪是“湖广熟,天下足”一语流传的主体时期,也是两湖地区粮食外运的鼎盛时期,这期间,两湖每年约有400-1000万石大米输出,约占当时稻米总产的8.1%-16.8%,平均稻谷商品率在12.5%左右(注: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5页。)。就明清两代两湖地区米粮外运的特点比较而言,清代两湖地区的米粮外运,已不再仅仅是偶尔为之,或是各区域间粮食丰歉余缺的相互调剂,而是一种比较稳定的、经常性的粮食流通,它更多的是源于明代开始的、各地农产品的商品化而带来的、省际之间大规模的商品粮流通。
由于地理位置的便利,两湖米粮输出所及范围很广,除与之相邻的贵州、广西、广东、江西、安徽、河南、陕西、四川等八省外,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更是两湖米谷的重要的输入地。本文意在探讨清代江南与两湖地区市场的互动关系,及其对两地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
清代两湖地区的稻米产区虽然很广,但大量的余粮输出则主要以洞庭湖平原、江汉平原和湘江中下游地区为主。“湖广素称沃壤,故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谚,以今日言之,殊不尽然。湖北一省,宜昌、施南、郧阳,多处万山之中;荆州尚需从武(昌)汉(阳)搬济兵米;德安、襄阳、安陆,其地多种豆麦,稻田亦少;武昌所属,半在山中,惟汉、黄两郡,尚属产米。湖南亦惟长沙、宝庆、岳州、澧州、衡州、常德等府系广产之乡,其中亦复多寡不等;余郡远隔山溪,难以转运”(注:朱伦瀚:《截留漕粮以充积贮札子》,《清经世文编》卷39,户政14,仓储上。)。其中,尤以湖南米占多数。清代湖南的稻谷单产、总产都要高于湖北(注: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页。)。康熙年间,湖南所产之米,“运下江浙者居多”,因“江浙买米商贩多在汉口购买,而直抵湖南者无几,是湖北转运江浙之米,即系湖南运下汉口之米”(注:赵申乔:《自治官书》卷6《折奏湖南运米买卖人姓名数目稿》,引自蒋建平《清代前期米谷贸易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雍正间,“自湖北以至江南一带,俱仰赖湖南之米”(注: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魏廷珍奏,《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第2册。);乾隆时,“湖南官仓,不但备本省之荒欠,兼备邻省之荒欠。所云邻省,上如粤东、粤西,下如湖北、江西、江南、江浙,倘有荒欠,皆取资于湖南所贮之额”(注: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卷38。蒋建平前引书,第53页。)。仅官仓所拨即有如此重要之地位,加之商人贩运,其数量将更是可观。
在江南与长江中上游两湖、四川地区的商品贸易中,米粮输入占据相当成份。入清以后,“苏松户口繁多,民间食米多取给于外贩”(注:《清世宗实录》卷51。)。从方志及大量的清代奏折记载来看,江南地区的米粮输入主要仰赖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安徽、江西、两湖及四川地区,其中尤以两湖地区为多。康熙时“江浙百姓咸赖湖广米粟”(注:宣统《黄安乡土志·实业》。)。雍正时,湖广粮食供应区域更加扩大,不仅凶年供应江浙之食,“号丰年必仰给湖广”,而且,大多湖广之米,聚集苏郡的枫桥,再由此转销上海、福建(注:道光《蒲坼县志·风俗》。)。雍正元年十月二十四日,都察院左佥都御史陈允恭奏道:“(浙江需米)小商由江南贩运于浙,巨商由上江(今安徽)、湖广、江西贩运于苏州。”(注:《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第2册。)苏州的枫桥成为当时江南地区最大的米粮转运中心。如前陈允恭所奏,浙江“边山际海,产米有限”,“即在平日乏米者,大半仰藉于杭州之墅河,而墅河之商贩,运于苏州之枫桥,枫桥所贮之米,皆由湖广、江西、上江运漕巨商载运而来,并非苏州土产。”雍正帝也深知这一点,于其登基元年上谕内阁时曾提及:“浙江及江南苏松等府,地窄人稠,即丰收之年,亦皆仰食于湖广、江西等处。”雍正五年,署理湖广总督傅敏则奏称:“大江以南,皆系财赋重地,独至米谷,则江浙等省每赖湖广接济。”(注:雍正五年三月,《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第9册。)与此同时,江南松江府、太仓州、海门厅、通州(今江苏南通地区)等产棉区,“种花者多而种稻者少,每年口食全赖客商贩运”,政府也“准其招商赴上江(今安徽等地)有漕聚米之区,采买运济”,而且采买数量有日增之势。以崇明县为例,乾隆二十年前,“核计崇商买米之数不过二十余万石,近则递年加增,已买至三十余万石”(注:高晋:《请海疆禾棉兼种疏》,《清经世文编》卷37,户政十二,农政中。)。到清后期,崇明县“民间食米,皆仰给于上江”(注:光绪《崇明县志》卷6。)。
从李煦奏折中可以看出,清代江南地区与两湖地区的经济联系日趋紧密,上游地区输入江南地区米粮的多寡,直接影响着江南地区的米价波动。康熙四十六年十二月“太仓一念和尚聚众起事折”:“……至于苏松米价腾贵,一两六七钱一石,一因本地歉收,二因湖广客米到少,三因贪利之徒贩米出洋。”(注:《李煦奏折》第42页。)康熙五十一年八月初八日“苏扬米价并进晴雨册折”:“苏州、扬州,因湖广客米到得甚多,所以米价仍贱,上号不出八钱,次号不出七钱。至于雨水调匀,田禾渐渐结谷,九月内定得丰收。”(注:《李煦奏折》第122页。)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六日“苏州米价并进晴雨册折”:“窃苏州八月初旬,湖广、江西客米未到,米价一时偶贵,后即陆续运至,价值复平,上号卖一两一钱,次号卖九钱五分。今秋苏州丰收,约有九分年景,雨水亦复调匀,民情喜悦。”(注:《李煦奏折》第203页。)
雍正元年秋,苏州地区干旱,“沿河田亩可望有收,高阜田禾大半枯槁”,而塘河水道日浅,“湖广、江西客米大船难到”,引起苏州米价不稳(注:《苏州织造胡凤辇奏报八月少雨米价渐昂折》,雍正元年九月初三日,《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第1册。)。乾隆时,“浙西一带地方所产之米,不足供本地食米之半,全藉江西、湖广客贩米船,由苏州一路接济”(注:《清高宗实录》卷314。)。乾隆十三年四月三十日,升任浙江巡抚的顾琮复奏浙省米贵缘由:“杭、嘉、湖三府,树桑之地独多,金、衢、严、宁、绍、台六府,山田相半,温、处二府,山多田少,向资江、楚转输,近岁江、楚价昂,商贾至者无几”,故而米价上涨(注:《清高宗实录》卷313。)。江西、湖北地区的米价上涨或粮船来迟,都会直接影响到江南地区的米价及米粮供应,“来船稍阻,入市稍稀,则人情惶惶,米价顿长数倍”(注:《清高宗实录》卷314。),江南地区对江西、两湖米粮依赖的程度于此也可见一斑,以至“无论丰欠,江广安徽之客米业售者,岁不下数百万石”(注:包世臣:《安吴四种》卷26。)。江南米粮对外来粮食的这种依赖一直延续到清后期,“江苏省各府县产米不敷民食,向赖湖广等省商贾贩运”(注:《清穆宗实录》卷57。)。民国《六合县志》亦载,“雍正志云,邑产良谷,岁供苏浙籴买,而土人亦多赴江西湘楚一带贩卖,乾嘉以后,则多贩运至浙江海宁之长安镇,光绪间乃改趋无锡、上海”(注:民国《六合县志》卷14《实业》。)。
可以说,清代,只要两湖地区不发生大的灾荒,均能充分供应江南地区的米粮,保证该地区粮价的稳定。康熙间,“江浙楚省,地处天南,灾情流行,亦所时有。然米价不至腾涌,贫民不至失所。彼固恃有巨商大贾,通行舟楫,千艘万舳,装载发贩,挹彼注兹,周流无滞,故得价值平坦。不惟兴利,兼可救荒”(注: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90页。)。雍正间湖广总督迈柱奏报:“现今雨旸调顺,即菜、豆之类均获丰收,早禾茂盛,晚禾青葱。虽江浙贩米甚多,而二麦登场,米价仍然平减。”(注:雍正十二年五月十五日,《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第26册。)各类运粮船往返航行于长江之上,甚为繁荣。“诸商人闻江北旱蝗相继,争籴米而东,舳舻首尾相衔,蔽江而下,汉江之间,米价日增,而江南依然如故,利之所在人争趋之”(注: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
就两湖地区的米粮集散地而言,湖南主要有湘潭、衡阳、长水、常德、岳阳等城,湖北则主要以汉口为中心。汉口也是当时长江中上游地区最大的米市,雍正间,“烟火百万户,绵亘数十里,其间巨商大贾以及担夫贩竖,无不毕集”。乾隆时“户口二十余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人类不一,日消米谷,不下数千。所幸地当孔道,云、贵、川、陕、粤西、湖南,处处相通,本省湖河,帆樯相属,粮食之行,不舍昼夜。是以朝籴夕炊,无致坐困”(注:晏斯盛:《请设商社疏》,《清经世文编》卷40,户政十五,仓储下。)。同时,汉口也是内地货物之一大集散市场,各种生业,无不可行。俗称“八大行”者为其中最盛之商业,为:盐行约10家、米粮行20家、杂粮行20家、棉花行10家,油行10余家,茶行10余家,药材行20余家,广福杂货行30余家,年交易额达9670-10070万两。其中米粮行和杂粮行的年交易额达3600万两左右,占总交易额的35.75%-37.23%,油行交易额约2400万两,占总交易额的23.83%-24.82%,粮油两项即占交易总额的60%左右。棉花行交易额800万两左右,占总交易额的7.9%-8.3%。粮、棉、油三项交易几近占总交易额的70%(注:据吴量恺《清代经济史研究》数据统计,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汉口的繁荣与其数量庞大的粮食运转业的发展密不可分。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湖出境的大米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长江上游的四川。清代,随着成都平原的开发,川米产量大增,甚至超过了两湖、江西等地,有“江浙之米历来仰给于湖广,湖广之米又仰给于四川”之说。如前朱伦瀚奏疏所言,由于大量米粮流出省外,带来了湖北地区粮价的上涨,必须仰仗川米的接济平抑物价。“武流一带,有待川米来而后减价之语”(注:朱伦瀚:《截留漕粮以充积贮札子》,《清经世文编》卷39,户政14,仓储上。),这说明在乾隆时川米入境已很普遍。另外,从乾隆帝多次指令沿江地方官,不得截留运载川米商船的谕旨中也可看出。乾隆三十九年上谕:“江南向每仰给川楚之米,今岁亦间有偏灾,更不能不待上游之接济。……楚米既不能贩运出境,若复将川米截住,不令估船运载,顺流而下,则江南何所取资?”因此,乾隆帝传谕:“如川省米船到楚,听其或在该省发卖,或运赴江南通行贩售,总听商便,勿稍抑遏。”(注:嘉庆《四川通志》卷首。)乾隆五十年九月十二日谕军机大臣等:“据舒常奏:‘楚省商贩米船过境,已有一千三百余只,从江西贩去米谷,约有数十万石。嗣商贩陆续采买,官为照料,更可迅速,无价昂之弊’等语。湖北灾区,急需客米接济,前已节次降旨,令江西、湖南、四川各督抚帮同料理,遇有湖北商贩到境,毋稍留难阻滞;并出示晓谕各该省民人,毋得居奇。又因安徽、江苏、浙江等省,必须川米接济,其商民贩运者,必经由湖北,该省毋得中途拦截。似此通盘筹画,方于各省民食有裨。今江西省商贩赴楚,已有一千三百余只,米谷约有数十万石,嗣后陆续采买,官为照料,更可迅速运往。本日又据李世杰奏,将常平仓谷碾出三十万石应粜,是商贩运楚米石日渐充裕,民间可无虞艰食。其有运往安徽、江苏、浙江粜卖商船,该省断不可于中途遏籴,务俾商贩流通,灾歉之区,均资接济。”(注:《清高宗实录》卷1238。)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初九日,又下谕:“……江浙等省全赖川米接济,若将川省、湖广船只尽行封雇,则商贩无船装载,川米即不能转运,各省米价必致腾贵,于民食大有关系。该督何见不及此。著保宁务须设法妥办,止须陆续拨运,期于要需无误。”(注:《清高宗实录》卷1286。)
据奏报,乾隆三十二年十月,汉口到过四川、湖南米52000石,十二月汉口到过四川、湖南米72200石;乾隆三十三年正月汉口到过客米90900石,其中四川、湖南米45900石,六月汉口到过四川、湖南米69000石,十月到过四川、湖南米69000石;乾隆四十三年六月到过汉口川米29900石,闰六月又到川米10900石;乾隆四十四年二月汉口到过江西、湖南米12500石(注:《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另见龚胜生前引书,第262页。)。由上列数字可以看出,每年汉口至少消费川米、湘米约70余万石,其中川米达50余万石。若论川米运抵汉口转贩他处的,其数量显然要多得多。
长江中上游地区输入江南地区商品粮的多少,国内外学者多有研究。全汉昇根据雍正十二年五月十五日“江浙官籴商贩,陆续搬运四百余万(石)之多”和七月初八日“江浙商贩已运米五百余万石”的材料,推算雍正十二年一年中,自湖广运往江浙的食米,约为1000万石左右。装载这1000万石的湖广米船,由汉口出发,沿江而下,大部分运往苏州出卖(注:全汉昇:《清朝中叶苏州的米粮贸易》,《中国经济史论丛》第2册,第573页。)。吴承明先生估计,清前期江南地区每年从长江中上游的江西、湖广、四川输入的稻米约为1500万石(注: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王业键研究指出,在18世纪后期,流入江南地区的各类粮食总计约有3000-3500万石左右,其中通过海路和大运河运入江南的关东及华北的大豆、豆类制品、谷类粮食和水果每年亦约有1500万石,每年沿长江贩运到江南地区的大米大概为1500-2000万石,占流入江南地区粮食市场商品粮总数的一半以上(注:史志宏:《王业键〈1638-1935年间江南米价变动趋势〉述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可以说长江中上游地区输入的米粮对清代江南地区粮食市场的繁荣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二
随着长江中上游地区米粮的大量输入,江南丝棉纺织品农户的粮食来源有了保证,促进了江南地区丝棉纺织业和其它手工业多种经营的发展,江南地区大量的丝棉纺织品也因此而源源不断地输往全国各地。江南地区购买米粮的大量资金主要来源于丝棉纺织品的贸易所得。湖南长沙、善化有许多江浙商人,乾隆时,长沙“南客苏杭,其货绫罗古玩之属”(注:乾隆《长沙府志》卷14《风俗》。)。善化有三个江苏商人会馆,即苏州会馆,在十铺福胜街,康熙间苏州商人建;江南会馆,在十铺太平街,江浙商人建;上元会馆,在十三铺县围后,南京商人建(注:光绪《善化县志》卷30《会馆》。)。湖南常德府,“境内不种桑,……不工纺织、锦绮之属,取之江浙远方”(注:嘉庆《常德府志》卷18。)。湖南保庆府邵阳县,“杭绸、宁缎、湖绉,今市肆所售者,皆江苏、浙江产也”(注: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4页。)。商人们将江南的棉布运往各地出卖,再贩来湖广、江西的稻米。嘉庆十五年,湖广商人邬大志、熊正达等人自称,“向或自船自本贩米苏卖,或揽写客载运货来苏,是米济民食,……苏省之流通,全赖楚省之运转”(注:《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243页。)。雍正时,“江、广米商稔知江宁有布可易,故岁岁载米依期而至”(注:晏斯盛:《上制府论布商易米书》,《清经世文编》卷47,户政二二,漕运中)。
江南丝绸更是湖北市场上的抢手货,“新杭市接王江泾,新杭人家稀入城;有时千匹万匹练,却上江船汉口行”(注:陈毓乾:《新杭竹枝词》,转引自陈学文《嘉兴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第79页。)。清代,江南地区棉织品销售市场虽然在长江中上游地区有所缩小,但汉口市场上诸种高级棉织品如毛蓝、京青、洋青、黑青、假高丽布等多来自苏州和松江地区;丝织品种如贡缎、广缎、洋缎、羽毛缎、羽绉、哗叽、宁绸、宫绸、纺绸、庄绫、汴绫、湖绉、茧绸、帕头等等,多来自江浙的南京、苏杭、湖州等地(注: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食货志》。)。乾嘉年间,汉口镇内的江南及宁波邦约60-70家,交易货物以棉花、海产物、米、帽子、绸缎为主,年交易额约3000-3500万两,占总交易额(14950-16000万两)的21.88%-23.41%,与在汉口的潮帮、广东帮及香港帮(年交易额为3500万两)并驾齐驱(注:据吴量恺前引书第90页统计。)。江南商品在两湖地区市场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江南与两湖地区的经济交流中,清代两湖地区纺织业的兴起与发展,对江南棉布传统市场的影响值得关注。随着植棉业和纺织技术的日益普及,清代两湖地区的棉纺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在湖北形成了汉阳、德安、荆州等主要产布区,湖南则有耒阳、巴陵、祁阳等产布区。
湖南衡州府耒阳布销郴、桂、粤西地区,据县志载:女“勤纺织,工缝纫,操作不辍,无论贫富,大都类然。……惟北乡为最。其布通行郴、桂、粤西间,为利甚溥,足以济半年食用”(注:光绪《耒阳县志》卷74《风俗》。)。湖南巴陵布则销广西,巴陵布质较粗糙,称都布。“吴客在长沙、湘潭、益阳者,来鹿角市之。……岁会钱可二十万缗”(注:吴敏树:《巴陵土产说》,《样湖文集》。)。鹿角在巴陵南洞庭湖畔,吴客所贩似沿湘江运广西。当有40-50万匹(注: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祁阳县文明市因其地“西通粤、走黔蜀”,成为当时布匹流通转运的中心,并远销广东、云南地区,“染采其所织布,通市于粤滇”(注:民国《祁县志》卷10,货物卷引旧志。)。
湖北汉阳府汉阳布销秦、晋、滇、黔一带:汉阳县附郭,“街居妇女多事剪绣,乡农之家勤于纺织。每入夜登机,旦即成布”(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130,《汉阳府风俗考》。)。乾嘉年间,南乡产扣布,“(农)家春作外,以此资生。妇女老幼机声轧轧,人日可得一匹,长一丈五六尺。乡逐什一者,盈千累万,买至汉口,加染造,以应秦晋滇黔远贾之贸。”同治时,南乡农村棉纺织业仍很兴旺,“其布则曰扣布,南乡治此尤勤。妇女老幼自春作外,昼则鸣机,夜则篝灯纺绩,彻夕不休,比巷相闻。人日得布一匹。远者秦晋滇黔贾人争市焉”(注: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1-162页。)。
汉阳府汊川布销襄樊、楚南、秦晋滇黔等地。“当农事甫毕,男妇老幼共相操作,或篝灯纺绩,日夕不休;或机声轧轧,比屋相闻。故业此恒劳。”所产大布、小布,销路很广。“近而襄樊、楚南,远而秦晋滇黔,咸来争市焉”(注:光绪《汉川县志》卷6《物产》。)。
德安府安陆县所产棉布,称“为大市,细薄如绸”,另有“椿布,西贾所收也,至呼为边布”,“民恃此为生”(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168《德安府物产考》引康熙府志。)。销“行西北路,万里而遥”(注: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3页。)。梭布则聚于应城,运到汉口,“行东南诸省”(注: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3页。)。
云梦布则经晋商贩运北方,凡西客来楚货布,必经云城捆载出疆,……故西商于云立店号数十处”,以应购运之需(注:道光《云梦县志》卷1《风俗》。)。云梦县自身就是湖北布销往塞北的集散地。“大约湖北产布区,行销西北者以云梦为集中地,捆载北去;行销西南者以汉阳为中心,溯江而上”(注: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湖北监利布销西南地区,乾隆时,“棉布出监利车湾者最佳”,“行销外省”,而主要销西南,“蜀客贳布者相接踵”(注:光绪《荆州府志》卷6《物产》引乾隆旧志。)。后扩大销区,“西走蜀黔,南走百粤,厥利甚饶”(注:同治《监利县志》卷8《风土》。)。
沙市布经四川销云南地区:“广布产于湖北沙市”,“由荆州贩至四川叙州府,由叙州府贩至(云南)昭通,再由昭通府以关驮运从可渡入境”(注:民国《宣威州乡土格致》第27课,“广布”。)。云南宝威所需的“广布多产于湖北沙市”,“每月约百卷,值银二十六两,平均每年运入二千四百卷,值银五万二千两”(注:光绪《宣威州志·乡土格致》。)。同时,四川阆中县还用丝交换湖北棉布,“昔商业之大者,无过于转运丝布,收本地丝载至湖北沙市、汉口变卖,随即买布以归”(注:民国《阆中县志》卷17《实业志·商业》。)。
其他地区如蕲水县、孝感县、黄州府的广济县、罗田县、荆州府的石首等地清代均生产棉布,并销往外省区。此外,江西省的清江县所产布也很有名。据县志载,“女红以纺织为事。轧轧之声,日夜不少息。有娣姒(即妯娌)轮纺彻夜者。布既易成,且以警夜。”其县所属“永泰市在城东南十五里,……地出棉布,衣被楚、黔、闽、粤”(注:同治《清江县志》卷2《市镇》。)。
四川潼川府中江布也远贩滇黔地区,道光《中江县新志·风俗志》:“邑出布、帽、鞋、袜、篾扇等货,……皆赖女工,余或纺棉绩麻。”“物产志”载:“棉布,邑境悉产木棉,下村尤盛。妇女又能纺,故纺者恒多。其佳者皆曰卓布,皆能行远。商贩至滇黔,为大装货。”(注: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0页。)
从上述资料来看,清代两湖等地棉布的行销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其精者皆远行滇、黔、秦、蜀、晋诸省”。吴、皖等地居民,也很珍视湖北所产的“府布”(注:民国《湖北通志·物产》。)。大体来说,两湖棉布主要销向是西北秦晋、西南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及东部闽西、赣南地区。这一销售格局与当时全国棉布生产的总体格局不无关联。清代全国各地的棉纺业,北方有华北冀鲁豫产布区,东部有江南地区这一传统的全国性产布中心,南方广东地区也有较发达的棉纺织业,这一生产格局也决定了两湖等地的棉布销售大体局限于湘、鄂、川、滇、黔等中部、西南部地区,“南达南岭,北抵中原,西不过川滇,东不过武夷、富春”(注:刘秀生:《清代中期湘鄂赣棉布产销与全国棉布市场格局》,载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
两湖棉纺织业的兴起与发展对江南地区棉纺业的影响则是,直接扼制了江南棉布在中西部市场的销售空间。笔者曾撰文指出,虽然从明代开始,江南地区就成为全国主要的棉纺织品生产基地,但始终缺少先进的生产技术的发展为后盾,其自身缺乏为其产品开拓市场的能力,在生产效率上并无太大的优势可言,再加上长途贩运的费用,其产品在同外省区产品的竞争中,并无绝对的取胜把握。因此,清代江南棉布在远距离区域市场的销售额急剧下跌。在全国其他地区棉纺业相继兴起的情况下,江南棉布难以继续保持其空间范围的市场优势(注:张海英:《明清江南地区棉布市场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1期。)。清代,华北等棉纺业的兴起已使江南棉布失去了大部分的北方市场,而两湖地区棉纺业的发展则使江南棉布在中部、西南地区的市场上受到排斥,使得清后期江南棉布的销售范围主要限于其内部周围地区、东南沿海及便宜的水运所及的地区(如运河南段沿岸等地)。
不过,就笔者所翻阅的两湖及四川、江西等地各府县方志的物产记载中,清初康熙及至乾隆时期的物产类棉布,多属提及,详细记载较少。表明清初时该地棉纺业已出现,但大量转销外省区的记载不多见。棉布大量外销他省区的记载大多为道光以后的方志,更多的是同光年间的记载。这说明清代江南以外地区棉纺织业的发展及至排挤江南棉纺品的销售市场还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
三
在两湖地区输往江南的商品中,除大宗的粮食外,还有大量的木竹。清代江南作为全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不仅其丝棉纺织业独树一帜,而且其造船业、造纸业、刻书及木器家具等也堪称一流。同时大量市镇的兴起而带动的建筑行业的大规模发展、以及绵长的海岸线上海塘的修筑等等,形成了一个需要量相当可观的木竹市场,而江南地区内部所产木竹远远不能供其所需,每年都要从福建、贵州、江西及至长江中上游地区输入大量的木竹(注:参见李伯重《明清时期江南的木材问题》,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第85-87页。范金民在其书中对江南修筑沿海堤塘所需的木材消费予以关注,这在以往的研究中尚不多见。)。据石莹研究指出,清代的汉口是西南、中南地区木竹汇聚的最大集散中转市场,而江南市场则是汉口市场上集散转运的大量木竹的最重要的销售场所,每年都有大量的木竹自汉口市场运往江南地区。以至长江上的税收大户九江关,其关税以“木税及船料为大宗”。乾隆后期,其每年所征的60余万税银中,木竹、盐船两项即“居其过半”,以至该关关督竟以木竹多到和少到作为关税增减之理由上报朝廷,可见木竹税收在其关税收入中的地位,从中也反映了从此处过关的木竹流量之大(注:石莹:《清代汉口的木竹市场及其规模分析》(未刊稿):许檀:《清代前期的九江关及其商品流通》,《历史档案》1999年第1期。)。
清代江南与两湖地区的经济交流中,商品种类也绝非仅限于丝棉织品、粮食及木竹等项,从乾隆时期清政府所颁布的准允漕船所携带的江南及两湖等地土宜明细栏中可以看出,允其所带物品种类繁多。如乾隆四年规定的江南各省土宜中,除布匹和绸缎外,各类纸张36种,苏木、肥皂、扇子、锡箔箱、漆、草席等杂货34种,橘饼、蜜果、烟、皮蛋、火腿、柴菜、闽姜、乌梅等食品31种,伞、笔帽、木屐、小镜架等竹木器等16种,其他如柏油、桐油及香油等油类、糖类、药材类、酒类、磁器、铁器等类物品将近50种;两湖地区的土宜也涉及杂货、食品、药材、铁器、纸张等70余种(注:据吴琦《漕运与中国社会》资料统计,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172页。)。官方控制严密的漕船尚允带种类如此繁多的农副手工产品,民间贸易的商品流通的种类与数量当比这要丰富得多。
清代江南与两湖等地大规模的粮食、丝棉织品及木竹等大宗商品的商品流通,反映了同时期全国性商品市场网络体系的发展与成熟,其对两地的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就江南地区而言,大量商品粮的输入,保证了江南丝棉经济作物种植区农民的日常生活及粮食的各类生产资料性消费,促进了江南丝棉纺织业和其它手工业多种经营的发展;与此同时,它也丰富活跃了江南地区的粮食市场。必须看到,沿江而下的大量商品粮,并非全部由江南地区内部消费,还有相当部分藉此中转沿运河北上山东、直隶地区,或南运福建等地(注:张海英:《清代江南地区的粮食市场及其商品粮流向》,《历史教学问题》1999年第6期。)。粮食市场的活跃推动了江南与闽粤、华北等其他地区的经济交流,加强了国内市场的联系,促进了各不同经济区区域性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对两湖地区来说,大量商品粮的输出,也同样刺激了该地区粮食种植业的发展,使其成为清代全国最大的稻米产区。清代,由于地利的优势,两湖地区米价较其他省份低,从而形成了米价的空间梯度差;另一方面,清代两湖米价始终保持上涨趋势,形成了米价时间梯度差(注: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6页。)。应该说,米价长期维持高价位趋势,为地域生产专门化和传统农业向商品农业转化提供了重要条件。如果米价长期下跌,谷贱伤农,农民就可能不会以谷为命脉,两湖也就不可能一直成为清代全国重要的商品稻米产区。正是因为米价的长期上涨,使两湖与江浙等省的粮食流通得以维持和加强。江南地区作为两湖地区商品粮的长期固定的消费大户,其市场流入量占两湖粮食外流总量的四分之三有余(注:吴琦:《清代湖广粮食流向及其社会功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2期。),这对促进两湖地区以稻米为主的商品农业得到进一步发展,使其成为清代全国最大的商品粮输出基地,功不可没。
另一方面,两湖地区棉纺业的兴起,虽对江南棉布市场有所冲击,但对两湖地区而言,它反映了该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也使得该地区的总体经济势力随之提高。这对江南经济而言,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个机遇。随着清代全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提高,江南与各地区的经济联系将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