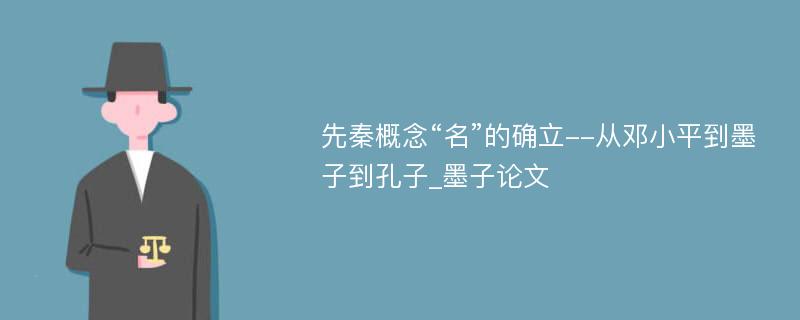
先秦概念之“名”的确立——由邓析经孔子至墨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墨子论文,孔子论文,先秦论文,概念论文,邓析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名”作为一个范畴(无论是哲学的还是逻辑学的),在我国思想史上差不多是最早被提出来的,与之相对的范畴则是“刑(形)”或“实”。孔子有一套“正名”理论,老子讲“无名”,荀子提出“约定俗成”的命名原则,诸子都曾讨论过“形名”或“名实”问题,都有各自的名实观,而名实之争则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延续到近代。
金岳霖先生在《知识论》中曾提出关于概念的双重作用的理论,冯契先生在其《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中加以发展。冯契先生说:
概念的摹写和规范作用是不可分割的。摹写就是把所与符号化,安排在意念图案之中,在这样摹写的同时也就是用概念对所与作了规范;规范就是用概念作接受方式来应付所与,在这样规范的同时,也就是对所与作了摹写。只有正确地摹写,才能有效地规范,只有在规范现实的过程中才能进一步更正确地摹写。(注:《冯契文集·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3页。)冯契先生关于概念的双重作用的理论对于中国逻辑史的研究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本文将以此为指导,侧重研究作为概念的“名”由邓析经孔子到墨子的逻辑发展。
一、邓析的“刑名之辩”:概念之名的发端
邓析是班固所列名家第一人。由于今本《邓析子》的真伪尚无定论(注:《汉书·艺文志》记有《邓析子》两篇。今本《邓析子》有《无厚》、《转辞》两篇,但其真伪有争议。唐人李善注《文选》引用今本《邓析子》十余条,可见他并不视之伪书。本文对今本《邓析子》的真伪问题存而不论。),我们对邓析的研究将首先借助《吕氏春秋》等书的记载。邓析在政治上是激进派,站在子产、驷颛等执政权臣的对立面。子产“铸刑书”,邓析则教人学诉讼。《吕氏春秋·离谓》中记载:
(邓析)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裤。民之献衣襦裤而学讼者,不可胜数。
郑国多相县以书者。子产令无县书,邓析致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令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矣。刑书铸就,人们有法可依,遇有案件(“狱”),自然希望在专业人员的帮助、指导下进行诉讼。对法律条文的研究使邓析能够得衣、得襦裤,这又反过来刺激他深入研究法律条文中的“名”。“县”(“悬”的通假字)、“致”、“倚”这些名的含义(可理解为概念的内涵)与所指(可理解为概念的外延)各不相同,邓析注意到了这些,采取了合法(至少是不违法)的方式来表达政见。百姓本可以用“县书”的方式来参政议政,而子产下令禁止,邓析就改用“致书”(让人把表达政见的书信送去);“县书”虽在禁止的范畴之内,而“致书”却不同于“县书”,子产就是满心的不高兴,也无可奈何,因为这并不违法。当子产下令禁止“致书”,邓析又改用“倚书”的方式,仍不违法,子产也只能是“欲加之罪而无辞”。邓析就是在与统治者的合法智斗中,通过对法律条文的表达的准确性思考,开始了他的“刑名之辩”,启历史之先河。当然,还很难说邓析所使用的这些“名”就是概念,它们主要还只是表达对象的语词,但既然要表达对象,就不免有概念成分。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与子产展开“刑名之辩”的过程中,邓析较多注意的是名对现实的规范作用,既然子产禁止的是“县书”,“致书”则不在“县书”之名规范的范围之内,邓析用“致书”的方式来参政议政,也就不违反子产的规定。
《吕氏春秋·离谓》也曾对邓析提出批评,
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对邓析的两可之说的批评源于这样一件事,
洧水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请赎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人必莫之卖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邓析。邓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后人也多有视此为诡辩者。实际上邓析对矛盾双方均应以“安之”,恰恰是因为一方“莫之卖”、一方“无所更买”;“安之”虽同,所以“安之”则不同,这是对矛盾事物的辩证的思维,不违反逻辑规律。我们退一步看——视之为诡辩,人们对此的难于理解而又努力去理解,正好促使人们对思维自身加以研究,这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对逻辑理论的诞生起刺激作用。
从今本《邓析子》的材料来看,在“名”与“实”的关系问题上,邓析主张“循名责实”、“按实定名”,
循名责实,实之极也;按实定名,名之极也。参以相平,转而相成,故得形之名。(《邓析子·转辞》)“责”在古汉语中有“索取”之意,可引申为“要求”,因此“循名责实”之“名”体现了概念对现实的规范作用;“按实定名”的“名”当为新名,由实(思维对象)来确定,体现了概念对现实的摹写作用。不仅如此,名与实还应“参以相平,转而相成”,“参”在这里是“检验”的意思,经过实的检验的名才能成为平常之名,才能使名实相怨得以平息。由对现实的摹写而形成的名在规范现实的过程中又加以充实和完善;概念对现实的摹写与规范的双重作用相辅相成,在不断的摹写、规范的辗转过程中,公认的名才能得以形成。
不错,邓析“循名责实”、“按实定名”的思想中确实已经包含了把“名”作为概念加以考察的最初探索。如果我们对邓析在《转辞》中所讲的那段话理解得不错的话,那么邓析的概念理论实在是比较全面的,他既注意到了概念之名的规范作用,也注意到了概念之名的摹写作用。比邓析稍晚的孔子,不过是提出了“正名”,比邓析晚了近三百年的韩非才有“循名而责实”(《韩非子·定法》)的明确提法,而这两个人也不过是仅仅沿袭了邓析概念理论中“循名责实”这一个方面,而对邓析的“按实定名”这一思想则有所忽视,更不要说继承“参以相平,转而相成”这一理论贡献了。但这种全面性是以牺牲深刻性为代价的,即邓析对概念作用的每个方面的分析都不够深入。这一工作后来由孔子和墨子完成:孔子侧重考察了概念之名的规范作用,墨子考察了概念之名的摹写作用,使这一问题的“两翼”得以展开。
总之,邓析的“两可之说”和“刑名之辩”对中国逻辑思想的产生做出了贡献。虽然邓析并没有提出“名”这一范畴,但邓析所发起的“刑名之辩”毕竟已经注意到了“刑”与“名”的对应关系,而先秦的哲人由邓析对政策、法规的思考而引发的“刑名之辩”为起点,进而探究“形”(具体事物的形状,由“刑”到“形”本身就反映了理论的发展)与“名”的关系;以“形名之辩”为中介,注意到具体事物不仅有“形”的性质,还有其它的性质;再由此而引申到对所有思维对象与名的关系之探讨,即对“名实”关系的全面讨论。在这个意义上说,研究中国的“名”的发展,不能忽略了邓析。
二、孔子的“正名”:对概念的规范作用的考察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当时阶级矛盾尖锐、封建等级混乱、周礼破坏殆尽。孔子认为社会的混乱局面完全是由名实相违造成的,因而提出了为政必先“正名”的治国方针。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论语·子路》)孔子在这里明确提出了“名”的范畴,并把它放在“言”、“事”、“礼乐”、“刑罚”、“民”这样一个概念序列中加以考察,这在中国逻辑史上是有重要贡献的。
孔子之“名”首先是一个政治、伦理范畴,因为孔子的正名原则是正名以正实,即用原有的、存在于周礼中的名去规范现有的实,其目的在于实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名分等级制度。在孔子的概念序列之中,我们可以容易地推演出“名之正”既是“礼乐兴”的必要条件,也是“刑罚中”的必要条件,而“礼乐”是只适用于社会上层的规范,“刑罚”则是适用于社会下层的规范,这就是所谓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礼记·曲礼》)。
当然,我们强调这一点——孔子之“名”首先是一个政治伦理的范畴,但也不能忽略孔子之“名”中包含了概念因素。“名”这个字在孔子之前就已有之,甲骨文、金文、秦篆中的“名”字写法不尽相同,但都由“夕”和“口”两部分组成。有论者云:“在较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夕’的造字本意,是借用月牙的形状,表示黑夜,‘口’则是摹写人的口部形状。‘夕’和‘口’会合而为‘名’,表示在黑夜里,用眼睛看不清东西,需要用口说出名称、语词来区分和说明事物。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说:‘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命。’清段玉裁注说:‘故从夕口会意。’就表示了这种看法。从‘名’这个字的形成过程及其结构,就透露出名(语词、名称)的指谓功能与交际功能。”(注:《中国逻辑史·先秦卷》,李匡武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8页。)“名”作为语词(或名称),是思维的物质外壳,也是交际的工具。“名”的交际功能的实现是不能脱离其指谓功能的。语词中的实词都有语义成分,这就是借助语词这一语言形式所表达的概念这一思维形式。这可以初步说明孔子之“名”中是包含概念成分的。
另外,孔子是在中国历史上较早对人的思维能力加以注意并初步探索人类思维现象的一位学者。“在殷商甲骨文和稍后的青铜器铭文(金文)中,尚未出现表示思考、思虑、思维意义的‘思’字,而在《论语》一书,竟有24次出现具有上述意义的‘思’字。”(注:《中国逻辑史·先秦卷》,李匡武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孔子对人类所特有的思维能力的反思,进一步说明孔子之“名”可以、而且应当含有概念的成分。
通过“正名”达到“正实”,以实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这样一个伦理目的,这就是要用名来匡定实,要实来符合名的要求,名是第一位的,实是第二位的。这里应当引起注意的是,孔子之“名”是周礼中早就规定好了的道德规范,是静态的;而实却是礼崩乐坏,是动态的。以旧名去规范新实,固然反映了概念的明确性方面的要求,但随着认识对象(实)的发展和名的主体——人——的认识能力的提高,名的含义与所指也应该有所变化。就“名”之中所包含的概念成分而言,表达概念的语词(即作为语言形式的“名”)可以不变,但反映在作为概念之“名”中的思维对象及其属性却会变化(增加或减少,改正或深入)。孔子过于强调作为概念之“名”的确定性要求,不顾动态的现实,一味地用静态的名去正实,使名成了静止的,因此走向形而上学。
孔子在中国逻辑史上最主要的贡献是提出了含有概念因素的“名”这一范畴。虽然孔子把“名”置于一个概念序列之中,但他关于“名”的理论是不系统的,而且具有片面性。说它不系统,主要是因为孔子尚未涉及名的产生、分类等问题;说它具有片面性,是因为孔子虽论及名的作用,但只强调了(甚至是过分强调了)作为概念之名对现实的规范作用。
此外,“在孔子这里,与‘名’相对的‘实’的范畴,还没有提出来,孔丘还没有对名、实关系作出理论上的概括。”(注:《中国逻辑史·先秦卷》,李匡武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46页。)名与实是一对范畴,只有名实对举才能使关于名的理论系统、完善。当然,我们也不能苛求孔子,作为中国逻辑史上概念理论的发展,提出“名”这一范畴无疑是基础的、重要的一环,在此基础上其后学才能进一步发展,提出“实”这一范畴,构成中国逻辑史上概念理论发展的下一环。孔子在中国逻辑史上完成的任务,“主要在于提出问题,而不在于对问题的解决。”(注:《中国逻辑史·先秦卷》,李匡武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0页。)而只有提出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三、墨子的“举实加名”:对概念的摹写作用的考察
墨子虽“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但后来在“政治上‘背周道’,思想上‘非儒’”。(注:《名学与辩学》,崔清田主编,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73页。 )可以说墨子对孔子的概念理论采取的是一种扬弃的科学态度,既有批判又有继承,在批判、继承中有所发展。
方今之时,复国之民始生,未有正长之时,盖其语曰,天下之人异议。是以一个一议,十人十议,百人百议。其人数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故相交非也。(《墨子·尚同中》)众人众议的结果是:
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是以天下乱焉。(《墨子·尚同中》)
今此何为人上而不能治其下,为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则是上下相贱也。何故以然?则义不同也。(《墨子·尚同下》)通过墨子的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与孔子相似,墨子也把天下之乱归咎于名实之乱;所不同的是,孔子抱怨变化了的实(虽然孔子未曾提出这一范畴)与名不符,而墨子则更强调名的含义缺乏约定性。当然,墨子所谓“义不同”之“义”,并不是指“语义”之“义”,而是指“道义”之“义”,而天下之乱是由于对“义”这个具体的名的含义(即“道义”之“义”的语义)的不同认识造成的。在这里,墨子把孔子的抽象的正名理论应用于具体的社会现象分析,足见其对孔子的继承。不仅如此,与孔子“正名以正政”一样,墨子所主张的“尚同”也是为天下之治服务的。
墨子对孔子名学思想有所继承的基础上,更多的是批判。墨子从驳斥儒家之所谓“仁”入手,批判了孔子“正名以正政”这一思想所表现出来的本末倒置的名实关系。
子墨子曰:“今瞽者曰:‘钜者白也,黔者黑也。’虽明目者无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虽禹汤无以易之。兼仁与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墨子·贵义》)墨子从名实关系的角度指出:对于“黑白”之名,瞽者与明目者都可以区分;对于“仁”与“不仁”之名,“天下之君子”与禹汤也可以有相同的认识。然而,若使黑色之物与白色之物混在一起,瞽者就无法区分;若仁与不仁的行为混在一起,让“天下之君子”选择或判定时,他们也会茫然无措。对于“黑”与“白”、“仁”与“不仁”这些概念的区分,不应当“以其名”,而应“以其取”。从名实关系上讲,就是应当首先取其实,然后才能定其名,即“取实予名”。当然,墨子在这里还没有提出“实”这一范畴,更没有明确提出“取实予名”的理论,只是注意到了实是第一位的,为他提出“实”的范畴作了必要的准备。还应当注意到,“以其取”之“取”有“选择”、“选取”之意,这是需要实际操作的,因此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在墨子区分名的标准中,是含有实践意味的。只是我们不能把这种实践意味看得过高,墨子还完全没有在理论上探讨实践范畴。
在此基础上,墨子提出了“实”这一范畴,
子墨子曰:“是与天下之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亡为仪者也。”(《墨子·明鬼下》)
今天下之所同义者,圣王之法也。今天下诸侯将犹多皆免(免,疑衍,从俞樾说)攻伐并兼,则是有誉义之名而不察其实也。此譬犹盲者之与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墨子·非攻下》)在《墨子》中,“实”字多出现在“众之耳目之实”这一类的语句中,象《非攻下》这样名实对举的地方并不多。与孔子不同,在《非攻下》中墨子把诸侯行“攻伐并兼”之实却拥有“誉义之名”这种名实相乱的现象归咎于“不察其实”,即名没能更好地反映实,这就与孔子仅仅注意名对现实的规范作用不尽一致,墨子首先注意的是名对实的摹写的功能,在“察其实”的基础上才能区分不同的名。
还应该注意到,在《非攻下》中墨子不仅提出了“实”这一范畴,也提到了“物”——“此譬犹盲者之与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这里的“物”即客观对象,是与作为思维对象的“实”相统一的,也具有了客观性。如金岳霖所言,“所与就是外物或外物的一部分。所与有两方面的位置,它是内容,同时也是对象;就内容说,它是呈现,就对象说,它是具有对象性的外物或外物底一部分。”(注:《知识论》,金岳霖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30页。 )此所谓“外物”就是墨子所说的“物”,而就对象而言的“所与”则相当于墨子的“实”,因此,从“所与就是外物或外物的一部分”即可证明物与实的统一。“名”作为对“实”或“物”的摹写,就是思维主体对“所与”的“所授”。“所授”过程中自然离不开约定俗成,约定俗成固然具有主观性,但一经约定,“所授”也具有客观性(此即概念之名的确定性),人们只能按照约定来使用,不能随意更改。
墨子对许多名都加以明确规定,如在《非攻下》中区分了“攻”与“诛”,只有“攻伐无罪之国”或“大为不义攻国”才是“攻”,而“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都不能称之为“攻”,而是“诛”。再如,
兼者,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乱小家,强不劫弱,众不暴寡,诈不谋愚,贵不傲贱。……别者,处大国则攻小国,强劫弱,众暴寡,诈谋愚,贵傲贱。(《墨子·天志中》)在明确区分了“兼”与“别”的基础上,墨子提及“分名”问题,
分名乎天下,恶人而贼人者,兼与?别与?即必曰别也。……分名乎天下爱人而利人者,别与?兼与?即必曰兼也。(《墨子·兼爱下》)
墨子的“分名”还只是对具体的某个(或某些)名的区分,是基于他“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尚同中》)的目的,虽然其区分标准与作为概念之名的抽象特征(内涵或外延)无关,但这在逻辑上的意义在于为其“举名”提供基础。对于行“兼”之实者,“举天下之美名加之,谓之圣王”(《墨子·天志上》);对于行“别”之实者,“举天下之恶名加之,谓之暴王”(《墨子·天志上》)。墨子在这里所讲的“举名加实”,还只是以具体的名(如“圣王”、“暴王”)加于具体的实,尚未从具体中抽象出明确、系统的理论。
在对同一实加以称谓时,可以用不同的名(至少作为语言形式的“名”是可以有所不同的),这取决于称谓者的视角。如被称为“兼”、“别”的对象(即实),当称谓者带有审美意向加以称谓时,就用“美”、“恶”之名,当称谓者带有评价意向加以称谓时,又会用“圣王”、“暴王”之名。墨子固然没有把这个问题上升到如此的哲学高度,但他由此而注意到了同实异名和同名异实的问题。同名异实如:
子墨子曰:“方今之时以正长,则本与古者异矣。譬之若有苗之以五刑然。昔者圣王制为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乱天下。”(《墨子·尚同中》)“五刑”之名虽同,“五刑”之实却异,古圣王之五刑用以“治天下”,而有苗之五刑却只能“乱天下”。
由以上这些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墨子关于“名”的思想是很丰富的,也有许多新思想,涉及了多方面的问题,如名的约定性、“察实”的正名方法、名的区分、名实之间复杂的对应关系等。但我们也应注意到,墨子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多为具体的,其概念理论还处于萌芽阶段,尚未上升到抽象的系统理论。墨子对这些具体问题的讨论,为公孙龙提出初步系统的概念理论作了必要的准备。墨子对举名(名是某一具体的名)加实的分析,为后期墨家抽象出“以名举实”的理论作了准备;墨子对名(具体的,如“义”)的约定性分析,也为荀子关于名的“约定俗成”(《荀子·正名》)这一抽象理论作了准备。
同孔子一样,墨子关于名的思想也还仅仅是为政治、伦理服务的工具,还没有成为纯粹的认识工具,因而也还没成为独立的、专门的知识。在这一相同点的基础上,更主要的是墨子批判了孔子“正名以正政”这一颠倒名实主从关系、只是强调概念对现实的规范作用的理论。墨子注意到对不同的名的区分不能“以其名”,而应“以其取”,强调了概念对现实的摹写作用。但墨子对孔子的批判、对孔子“正名”理论的发展有矫枉过正的嫌疑:通观《墨子》一书(不包括《墨经》六篇),墨子非常强调概念对现实的摹写作用,而对概念对现实的规范作用强调得不够。
总之,墨子在中国逻辑史上概念理论发展方面的主要贡献在于名实对举,把名纳入名、实这一对范畴体系之中。这构成了中国概念理论发展的重要的一环,只有在名、实的比较中,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名;只有在较丰富的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才能概括出抽象的理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墨子初步奠定了中国的概念理论的基础。
来稿日期:1999年6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