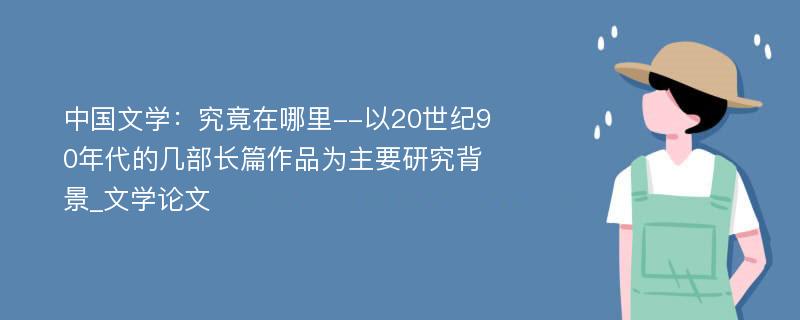
中国文学:究竟在何处定位——以九十年代的几部长篇为主要考察背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篇论文,几部论文,中国文学论文,背景论文,在何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八十年代中期,拉美文学的引进,在中国文坛带来了“爆炸”式的震荡效果,不但诱导了各路好手的群起效尤,而且使“诺贝尔奖”成为热门话题并急速膨胀成一个“情结”,刺激得不少作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频频跷首眺望万里之遥的斯德哥尔摩。这其实反映了 当时文坛的浮躁、盲目和不成熟。进入九十年代,情况大为不同。一批作家开始沉静潜心,真刀实枪地埋头苦干了。他们的自信,不仅来自自身实力的提高,还更来自文学的“双向开放”,或者说由被动接受域外文学的单向“输入”,开始转入主动出击和本土文学的有限“输出”。部分作家的频频出访和作品被反复评介,甚至打入“诺贝尔奖”的评奖外围,以至于在诺贝尔颁奖讲坛上为人注意(如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在获奖演说中提及莫言[1])……这一切都为当代中国文学赢得了声誉并逐渐为世界文坛所关注。与此同时,他们也开阔了视野,扩张了胸襟,无形中增强了面向世界的勇气与信心,清醒地意识到,必须拿出“拳头产品”才能与世界文学对话。于是乎,我们先后读到了刘承志的“生命之书”《心灵史》,陈忠实的“可作枕头安眠”之书《白鹿原》,贾平凹的“唯一可安妥灵魂”之书《废都》,莫言的“献给母亲与大地”之书《丰乳肥臀》,韩少功的长篇处女之作《马桥词典》……
指出上述作家创作包含或潜藏了“走向世界”的动机,决非空穴来风。比如一位研究者就详细分析了贾平凹创作转向的动因:“不少论家指望他重返商州现实,但是在贾平凹的心里,自《浮躁》走出国门之后,特别是美国学者葛浩文翻译上的繁难及平凹访问美国之后,他深深体味到风情醇厚的商州故事与现代意识充塞头脑的美国读者在沟通上存在巨大障碍,这障碍极大地弱化了贾平凹作品的艺术光线,为此,平凹曾著文吐露苦衷,并意欲将创作转向,从城市生活寻求切入点……抒写当代城市人的生活,对于东西方读者而言,沟通上较之商州故事更为方便……这便是《废都》、《白夜》创制之初的心理动因。”[2]为了“沟通”,考虑表现内容(题材)固然是一个方面,但表现形式的选择问题必然也将结伴而来。选择何种艺术样式或风格更易于被世界(美国?)所接受所认可,是西方化的?拉美化的?还是中国化的?或者是兼容并包,择优杂取?在创作之初,作家们的脑子里必定会有一个写作参照系,一个美学目标,一个艺术定位。不同的眼光导致不同的选择,于是乎,我们看到的作品也呈现出迥然各异的艺术风貌:《心灵史》显然深受回民哲合忍耶教派秘籍《热什哈尔》之影响,它是史学、神学、哲学和散文与诗的综合,它远离“纯文学”,但又具有纯文学所罕见的凝重的神秘之感,酷厉的牺牲之美;《白鹿原》在传统写法的基础上汲取“外国良规,加以发挥”,表现出一种开放的现实主义品格;《废都》则完全回到明清小说的叙述方略和语言,散发着些许现代“古董”的意味;《丰乳肥臀》基本上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如《百年孤独》等)为借鉴,以奇异、诡谲、变形、荒诞为特色;《马桥词典》则以现代语言哲学和域外小说形式来审视和表达本土文化,突出了形式意识和理性精神……
本文无意也无力对上述诸作进行全面的分析与评估,甚至仅对“艺术定位”这一点也不能多作比较。我只想简单列举其中两个比较极端的例子,点明其艺术定位有欠妥恰,进而阐明我的主张。在我看来,《废都》太“旧”或太“土”,《丰乳肥臀》则太“新”或太“洋”。以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观点看,前者对传统的艺术“审美图式”不仅未作拓开与推进,反而是一种收缩与倒退;后者则过于超前与“越位”,至少对中国绝大多数读者来说走得太远,致使其中许多宝贵素材和珍贵感情都为“形式”所弱化、所遮蔽,既造成了接受障碍,也消解了艺术力量。尤为令我遗憾的是,我认为在这几人当中,莫言的艺术定位最具弹性和选择性,从写实到写意,从传统到新潮,他都应裕自如并有过上乘表演,可这一回他却依然认准了“魔幻”。他的这种定位自有他的理由和深思熟虑之处,但从客观效果看,这是一次艺术定位的失误。究竟如何定位才算正确,谁也无法具体回答。我的笼统看法是,只有立足本土,创化传统,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征服中国读者;而只有首先征服了中国,然后才可能征服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的那句名言仍然没有过时,即“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
下面,就我的“定位”理由,分四个层面扼要陈述如次。
第一,走向世界不是走向西方。我们承认,现代以来尤其是二十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艺运动取得了很大成就,对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其一,西方的文学自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哲学背景和社会基础,他国不可能照搬;其二,西方的文学也是他们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成果,有的还可能是一种“弯路”的畸形产物(如后现代主义),他国不必要照搬;其三,西方化并不等于世界化,西方文学也仅仅是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济与科技的先进也并不等于文学的先进。任何民族和国家的文学要取得世界性的认同都不能靠紧跟谁或摹仿谁,只有立足本土,以富于民族特色的艺术创造去参与世界的对话,才可能对世界文化有所贡献。仍以与我们“国情”相近的拉美文学为例,在长达150年的文学实践中,他们走过了追随法国古典主义、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的曲折道路,一直到本世纪40年代才产生“背叛情绪”,坚决地实行大地文学、乡土文学、土著文学的口号,扎扎实实地转入本土创作,回到印第安文化和美洲文化的传统,使域外经验和现代意识在传统这棵古树上开出奇葩,这才有了60年代的“爆炸文学”。再以与我们文化相亲的日本文学为例,在经济法制和意识形态全盘西化的进程中,他们始终未放弃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大江健三郎“感谢尼尔斯和他的朋友大雁,”是“因为这只大雁使我重新发现了《源氏物语》”。[3]而且川端康成也认为“自己植根于东方古典世界的禅的思想和审美情趣之中”,“却并不等于西方所说的虚无主义”。[4]结果是,他们都获得了世界性的承认。
第二,中华文化不必妄自菲薄。恰恰相反,它作为人类四大古老文明的硕果仅存者,之所以能维系中华民族数千年不坠,不仅证明它具有一般传统文化的超稳定性,还说明它具有超越一般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的巨大活力。同时我还始终顽固地坚持认为,就知性的、分析的理性思维而言,我们也许弱于西人;但就感性的、整体的审美把握和艺术思维来看,我们却比他们更优,也即是说,中国的东方式的审美思维是更加接近艺术本质的。最近,画家石虎先生更对汉文化沿坡讨源,提出了“字思维论”,已经引起中国诗界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郑敏先生据此追溯到80年前(1908)美国语言学家范尼诺萨对汉语作为诗歌媒体的一篇赞美文章,其中早就阐述了汉语的象形文字所传达的动感,所包含的具体图画和多词类功能;因其非抽象性,包涵有浓厚的感性直观素材而更能表达诗的本质,认为“汉语文字由于其记载了人的思维心态的过程而开创了语言哲学的新篇章”,并对此东方哲思的特点惊叹不已。郑敏先生进而发挥道。“舍自己文化的本源去模仿他文化,岂非自甘沦为他文化的影子与附庸。”“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无知,对他者的文化传统虽同样无知,却盲目崇仰其新潮是造成当前我们文化危机的原因之一。”“其实任何新潮都有其传统基础,任何创新都来自对传统的深邃的理解,最伟大的创新者必是最深刻的继承者……割断当前与传统,只能搅起一时的新鲜感,绝不能产生经典之作。文化传统之可贵正在于此。”[5]
范尼诺萨作为“他者”却如此理解和推崇汉字文化,确令我辈羞愧;但另有一批具有文化上的双重或多重背景的中国文人最终对于传统文化的彻底皈依,是否又会让我们感到困惑呢?——本世纪上半叶,陈寅恪、辜鸿铭、钱钟书等一批大师少年出洋,游学多国十余年,在深谙异域文化和精通数门乃至十数门外语返国之后,却一头扎进了传统文化之中,有的人甚至还拒绝白话文和简化字,坚持使用文言文和繁体字写作,并且依然达到了学术高峰,这究竟作何解释?与此相近的例子还可举出台湾作家余光中、白先勇等人,他们在本世纪中叶也曾先后留学英美,也曾迷恋过艾略特和罗伯格里耶,但当他们回到台湾之后,也是一头扎进了传统文化之中,余光中还专门为此撰文:自称是文化上的“回头浪子”,而且他们也都成了台湾文学复兴的领军人物。这又究竟作何解释?难道仅仅是说明了他们的“好古”或守旧?或者是说明了中华文化强固的惰性和强大的惯性?难道不可能或更可能同时也说明了这正是他们“入乎其里,出乎其外”之后一种深刻选择的结果,由此而恰恰证明了中华文化的博大深邃和魅力无穷呢?
情形恰如郑敏先生所指出的,我们目前最需要的,首先是对中华文化传统深刻的学习、认识、理解和继承,(尤其是一批青年作家对于古典文学的“补课”),而不是妄自菲薄和自卑自弃。
第三,世界文学不能缺少中国。两千年的中国文学史因诞生了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等一批文学巨人,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精华,已然成为了人类文明宝库中的瑰宝。而中华文化对东方的覆盖性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没有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世界也将是一个跛子。而且按照新儒学的观点,儒教文明还将为后工业社会的人类提供一剂拯救的良药。此说自然有待实践检验,但中国文学和文化已越来越为世界所重视却是有目共睹的。虽然由于西方某些人士的偏见以及汉“美文不可译”(张承志语)等诸多原因,西方世界不少人对中国文学和文化还处于少知甚至无知的状态,这一点最近被季羡林先生的“失语新说”一语中的:“专就西方文学而论。西方文论家是有‘话语’的,没有‘失语’;但一读到中国文学,我认为,患‘失语症’的不是我们中国文论,而正是西方文化。”[6]但毕竟不乏有识之士开始了筚路蓝缕的工作。前文提及的范尼诺萨是一例,晚近又有美国青年学者金介甫专程来华深入调查考证,撰写了洋洋三十五万字的第一部出自西方学者之手的《沈从文传》,而且对沈推崇备至,认为“沈的杰作可以同契诃夫的名著媲美,“《边城》像《追忆似水年华》那样扎实”。并且预言,历史“总有一天会对沈从文作出公正评价:把沈从文、福楼拜、斯特恩、普鲁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7]此外,拉美文学大师纷纷看好中国,几年前,马尔克斯和略萨都相继自费来华考察访问,目的无非是想亲自感受领略一下中国文化的神秘魅力。而至于博尔赫斯,简直就算得上一个中国文化通了,他对周易和老庄都有相当精湛的研究。谁能说,在他们的“文学爆炸”当中就没有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滋养与影响呢?
第四,传统文化不能固步自封。前述两点极言中华文化之精深之伟大,决非鼓励夜朗自大,提倡一成不变,实在是出于一种补偏救弊之用心。我们强调立足本土,回到传统的同时,也强调传统需要出新,需要创化,需要开放;向世界开放,向时代开放,向现实生活开放。摹仿洋人没有出路,摹仿古人也没有出息。因为毕竟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前进,世界在变小。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稳定性中都在不断滋生出新的变性与活性,都不可避免地要和异质文化进行愈来愈广泛的交流与溶合,从而催发出新质和新机。我们应该拿出泱泱文化古国的气度,大胆地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坚信“吃了羊肉决不会变成羊”,而只会变得更加强健有力。“五四”时期,茅盾说鲁迅的小说一篇一个形式,而鲁迅则自己的创作也是“仰仗了百余篇外国小说的阅读”。钱钟书的《围城》则——是他在英法文学中长期徜徉之后直接汇入20世纪世界小说大潮中所溅起的浪花,它是中国传统开放的结果,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但归根到底,它还是一部反映中国知识分子众生相的、飘逸着中国风神的杰出的中国小说,它首先是中国的,然后才是世界的。我们今天所要做的,就是继续站在人类文化的最新高度,广迎八面来风,博采四方精华,更新观念,创化传统,以富于民族特色的新文学参与国际性的现代文化建设进程。
事实上,近年来的中国文学界也在实践中逐渐地从借鉴、摹仿乃至照搬域外文学的浓重阴影中挣脱出来了。从韩少功“寻根”,重视“寻找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到张承志坚定地表示:“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深深感到,中文的美是不可抗拒的……不管中文的美是否能让世界感受,只要我们有能力继续创造用中文写作的美文,厚重的中国文明就永远可能不被消灭。”[8]从王蒙、李国文、刘心武诸君对《红楼梦》等古典名著的兴趣与日俱增以及对其美学价值的重新认识与评估,到一批中青年理论批评家对新潮热的反省以及对国内创作实践的认真扎实的爬梳与清理,等等,都是中国文学界日见成熟的表征,是他们运用从本土从自身生长出来的智慧和从传统中创造性转化出来的话语系统走向世界大文化建设的开始。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都为中国作家寻求与世界接轨的“艺术定位”展开了背景,提供了前提,暗示了方向。这就是希望之所在。
注释:
[1][4]大江健三郎:《我在暧昧的日本》,《性的人》第299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
[2]孙见喜:《猜想:一个苍老的顽童》,《小说评论》96/3。
[3]大江健三郎《答谢辞》,《性的人》第307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
[5]参见郑敏:《一场关系到21世纪中华文化发展的讨论如何评价汉语汉字的价值》,《诗探索》96/4。
[6]季羡林:《门外中外文论絮语》,《文学评论》96/6。
[7]金介甫:《沈从文传》第2—3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8]见《张承志警告中国作家》,《无援的思想》第106页,华艺出版社1995年。
标签: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定位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九十年代论文; 贾平凹论文; 郑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