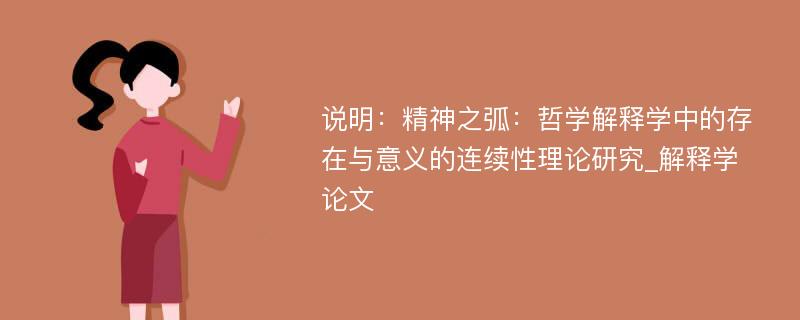
解释:精神之弧——哲学解释学关于存在与意义的连续性理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释学论文,连续性论文,理论研究论文,在与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解释,本是传统释义学的基本概念,它描述的是对经典文本的正确理解和释义现象。但在现象学的改造中,解释成了描述人类探寻存在的基本事件,并且,是作为存在和存在意义的连续性得以揭示的事件而被讨论的。
关于存在及其意义是否具有连续性的问题,是存在论不能回避的问题。以往的哲学对此有两种回答:其一是经验论,它立足于“变”,认为一切存在都是偶然的、个别的、具体的,不存在什么超验的统一性;其一是形而上学,它立足于“一”,于是,一切存在都是在空间、时间中延展的整体。如果经验论的说法成立,那么,存在就成了一个个孤立的现象,果如此,存在何以自明其真实性,存在意义何以证明自身的可靠性?反之,如果形而上学的说法成立,那么,存在及其意义的连续性过程岂不是先在的,岂不是等于说一切都是宿命,果如此人类的一切努力岂不枉然徒劳?看来,这的确是一个哲学难题。黑格尔用辩证法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他把绝对精神作为纯粹思维范畴,从而把“变”和“一”统一在一种三一式发展过程之中,但由于他的绝对精神并不只是纯粹思维范畴,而同时也是实体,于是,他建立的“有—无—变”的辩证统一过程,仍是一种先验的、先在的链条,它成了历史决定论的理论根据。历史存在被这种理论解释成统一的、宿命式的貌似辩证的连续过程。
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对此的解决是:把存在当作纯粹的思维范畴,把此在当作敞开存在本身的先决条件,如此,则变化中的现象存在就有了重要意义,同时,最重要的突破在于,历史此在敞开其真实性和意义的可靠性,是在与作为思维范畴的存在进行的解释中实现的,就是说,统一性并非黑格尔式的一种需要用现象填充其间的套子,而是在历史此在的现实性中被解释所发现、被延续的东西。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更明确地把这种思路表述为对话,存在的统一性是在历史此在与先验的传统的对话中得以显现的,存在及存在的意义是在偏离传统的向度中延续、返回传统的。反过来说,先验的东西不是存在的既定的路标,而是给存在的勘探提供认证的必要参照,是历史此在通达存在、获得存在意义的对话伙伴,其生命所在,也是在与此在的对话中才能实现。于是,对话与解释的概念就由传统释义学上升为敞开存在、理解存在意义的基本途径、基本方法。既然我们不能漠视存在,既然我们已知存在是无限的,既然我们不能回避存在的意义问题,那么,我们必须敢于在林中路上前行,在解释中通达存在。这就是现象学的存在论和哲学解释学的意义理论的题旨。
一、实存的时间性与历史性
与萨特的虚无化理论不同,海德格尔阐述人的实际存在达到本真状态时,并不是一片纯粹的黑暗,并不是一片缺乏意义的慌诞。此在的本真状态,意味着此在对自己的存在已有所领会,这正是此在达到本真状态的标志。那么,当我们身处本真状态的此在境地时,发生了什么本质性的事件呢?在海德格尔晦涩的话语中,我们看到,此在(Dasein)意味着空间和时间中的位置已是实存的。“只有在‘此’之中,也就是说,唯当作为‘此’之在而展开了空间性的存在者存在,‘这里’和‘那里’才是可能的。这个存在者在它最本已的存在中承担着非封闭状态的性质:‘此’这个词意指着这种本质性的展开状态。”(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87年版,第163页。)显然,这里所说的“空间性的存在者存在”,是指人在现实世界、生活世界之中的亲历,亲历即空间的占位。然而,这种位置还不等于本真的状态,从存在论的逻辑上说,它只是一个重要的起点。在这个起点上,非封闭的展开状态同时还指敞开存在,即对存在的真实与意义的澄明的拥有。反之,则是荒诞。于是,我们看到,此在的“此”,不意味着时间性的占位。就是说,此在,须在一种时间线索中才是可能的,“此”(Da)即时间的显现。此在即在实存中展现存在的时间性。于是,海德格尔说:“此在源始的存在论上的生存状态的根据乃是时间性。”(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87年版,第282页。)
为什么说时间的显现,时间的展现?难道时间不是客观的,不是自在的吗?原来,海德格尔所说的时间,并非指物理自然世界的存在方式,而是指人生存于其中的生活世界的存在的一种结构方式。其间的区别是:意义。自然世界的时间,是显现物质运动过程的方式,它本身是无所谓意义的;而生活世界的时间却是人的生存意义的存在的过程性结构。由这个区别,时间维度有着不同的特征,前者表现为无始无终的运动中的量度,而后者则表现为有始有终的统一的量度,即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维度是统一的连续链。这种时间观,自然并非海德格尔初创。不过在海德格尔以其独特的见解阐发新的时间观以前,以统一的意义作为时间内涵的形而上学曾严重地遮蔽着对存在以及历史的理解。统一的三维时间链,把历史构造成一种有始有终的完整过程:或把历史构造成从创世到末日审判的完整过程,或把历史构造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一个轮回过程,或把历史构造成沿着既定规律不断推进的进步过程,总之,一切都已先在地预成了。那么,人的历史活动、历史实践还有什么意义呢?按照其逻辑,历史活动只不过是把它再实存地扮演一遍,还能是什么呢?在这种时间链中,我们自以为已被编入历史的长河之中,已被置于宇宙间漫漫的意义绵延的一个瞬间里;在这种时间链中,一切存在者都被贴上标签,有意义与无意义早已有前定,人只有定在,而没有此在。因此,在这种时间链中,人的能动性必然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再现:一种是自以为历史性关键时刻已“到时”,天已降大任于斯人,于是,此时不干,更待何时?于是,定然以主观凌侵客观存在,干出些“改造世界”“创造历史”的事来;另一种则表现为消极无为的等待,因为,此时在既定的时间链中意味着尚未“到时”,于是,在百无聊赖中的等待就成了一种常态,这时,人们只感觉时间空着,于是,用一种消遣跳到另一种消遣,用一种抓紧时间的方式,去代替另一种抓紧时间的方式,用一种“打发时间”的方式去代替另一种“打发时间”的方式。这两种表现方式根出一源,都是把存在及其意义凝固化,教条化、僵死化,于是,时间就被封闭在一种永恒宿命的序列中。时间因此成了既定的绝对实体存在的结构。
时间被封闭,意义被凝冻,意味着人们对存在已坠入虚假意识,意味着人的存在的颓落、沉沦。一旦存在的本无特性以它无可抗拒的力量在人们正视现实、正视存在的目光中显露,这种时间的链条就会断裂。另外,存在的本无特性也必然会在颓落、沉沦中的人们的灾难性打击中显露,此时,人们顿觉坠入虚无的深渊,意义的可靠性,时间的永恒性都立刻崩溃,由此,绝望与恐惧弥散开来。
但是,毕竟人的生存不会只是颓落、沉沦,具有本真状态的此在于虚无的夜幕中必然不是无所作为的。所以在此在筹划自己的存在之时,也就是在存在的因缘整体中发现自己的可能性的时刻,进而也就是把此种可能性向着曾在,即过去勾连、发掘的时刻,于是在可能性将在通达曾在之际,就开通了一条由将在到现在,再到曾在的时间链,存在及其意义的敞开、澄明,就是这条时间链给出的果实。这种时间链的真实性何在?它与以往的时间观有何不同呢?
第一、此在是显现时间的基础。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中,此在具有本体论的优先地位,这意谓着此在是敞开存在的唯一现场,在存在的连续性状态中亦是如此。这一见解改变了时间的封闭性观念,还存在及其意义以变动不居的本来面目。此在正是开放的存在及其意义的起点,时间正是这种开放的存在及其意义的结构形式。
第二、时间链由于此在的开启,呈现为一种向无限延伸的向度,而不再是由实存填充起来的一种既定的绵延。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非封闭的存在”概念所昭示的新时间观。与封闭的存在相一致的是封闭的时间,而与非封闭的存在相一致的则是开放的时间,封闭的时间给出的存在意义当然是先在的,凝固的;开放的时间给出的存在意义则是永远向前推进的,开放的时间犹如一道不断前移的地平线。
第三、曾在、现在、将在这三种时间的样式,并不是从后向前推进的,而是从将在向现在进而向曾在回溯的。海德格尔的这一看法是异乎寻常的。他说:“此在本真地从将来而是曾在。先行达乎最极端的最本己的可能性就是有所领会地回到最本己的曾在来。只有当此在是将来的,它才本真地是曾在。曾在以某种方式源自将来。”(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87年版,第368页。)这样的向度,的确令人费解,时间从将来开端,岂不是说时间是倒流的吗?对于自然时间来说的确可以如此责难,不过,从时间作为存在意义的结构来看,它却是真实的。如果我们承认存在是开放的,如果我们承认时间是由此在所开启的,那么,最后展露的是将来,将来即生存论上的能在,也就是可能性,可能性便是意义的曙光。于是,将来的显露,就必然向曾在回朔,使这能在的新曙光在尘封的以往抓出自己的曾在。所以海德格尔把时间的展露称作“绽出”,而不是流出。将在、曾在、现在一同绽出。存在的意义正是在这种绽出中澄明敞开的。
将来回朔到曾在,构成时间的三个刻度,这一合乎逻辑的进展,在存在论上意味着什么呢?在我看来,它意味着存在及其意义的确认。此在所把握的能在,虽是意义的初始,但是,如果不能通达曾在,就还不能自明为意义。因为,在时间链上,曾在意味着根据,意味着时间的连续,意味着意义的历史性质的获得。这一点,在海德格尔自己的表述中是模糊的,而我认为这恰好是存在论的一个重要环节。正是在这个环节上,才产生了解释。
曾在是什么?为什么不说“过去”,而说“曾在”?其中深义在于:曾在并非过去的全部遗产,而是在这遗产中重新辨认出的东西,正是在这种重新辩认中,存在及其意义才进入了澄明。“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注:同上,第184页。)这个前提,就是既往的遗产。遗产中有什么?对此,此在的不同状态有不同的向度;非本真状态的此在沉沦于既定的未来的等待之中,对于过去,对于历史,要么转眼即忘,要么自以为了然在胸,自以为自己就已是历史性的,只是时机未到。实则在这种自以为是的了然中,历史及其遗产已凝固化为几条遗训,实际的历史早已湮没在遗忘的尘灰之中了;本真的此在则不会忘却过去,而是一再地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既往,因为记忆的机能正是由筹划的可能性唤醒的。“人们对有些事物有记忆,而对另一些事物则没有记忆,而且,人们象从记忆中忘却一些东西一样,在记忆中保存了另一些东西。”(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示》,上海译文92版,第19页。)记忆使曾在从过去中突现出来,从而使将在清晰明朗起来,并且返回自己的根柢之中。记忆使本真状态的此在具有了历史性。
海德格尔的以本真状态的此在为基点的时间观,使哲学思考存在及其意义的思路大为改观。其贡献所在就是终止了形而上学的封闭统一的存在论和意义论,揭开了存在的无限延伸以及意义的无限生成的真相。“此在根本上由以出发去未经言明地领会与解释存在这样的东西的就是时间。”(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87版,第23页。)时间被视为一切存在的领会与解释的地平线。这一新的时间观,就奠定了哲学解释学作为人文领域把握存在及其意义的基本方法论的地位。
二、解释与循环
哲学意义上的“解释”概念,既然处理的是与思维相同一的存在的连续性问题,那么,解释便上升为生活世界里把握存在及其意义的普遍方法。实现由基本存在论向人文历史领域里推进的是伽达默尔。
伽达默尔把海德格的由时间性展开的解释现象,还原到经验层面上。既然此在是时间性、历史性的唯一的开启者,那么,历史存在的拓展、历史意义的确认,就必以历史活动中的此在为起点。这个见解对直到本世纪仍占有统治地位的历史主义,无疑是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反叛。
历史主义无论是作为理论的形态,还是作为朴素的形态,都是指这样一种历史观:历史是实在的,客观的,历史的发展是按照自身的自在自为的规律行进的,那么,对历史的真理性认识与把握,就是指人的意识最大限度地同一于这种历史存在本身,只要人们拥有正确的认识历史的方法——象自然科学那的精密的方法——最终地、彻底地揭开历史之迷、把握历史真理则是可能的。伽达默尔认为,这是“历史客观主义”的天真幼稚。对历史的认识根本不可能达到最终的客观性,“一种真正的历史思维必须同时想到它自己的历史性。只有这样,它才不会追求某个历史对象(历史对象乃是我们不断研究的对象)的幽灵,……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92版,第19页。)这个看法似乎使人茫然,但它却是一种明智而可信的新世界观、新历史观。它揭开了一种真相:认识历史和世界,把握历史真理和世界的意义,绝不应是一种无历史的、真空中的认识主体对那历史之迷的寻求,而是历史实践中的此在,带着被历史给予的历史性对历史实在进行的理解。历史实在本质上也并不是一个被我们的超历史的目光,即解除了历史性负担的纯粹客观的目光所打量的对象,如此打量中的对象就不是历史意识认识、研究、理解的对象。这样形态的存在物当然也并非乌有,但谁要是把它当成历史对象,那它实际上就已不是在认识历史存在,而是在认识物理存在物。认识历史、理解历史当指认识、理解我们的历史性融入其中并与历史实在达成统一的存在方式。这样说,是不是说认识即是自我认识呢?这不是又回到黑格尔了吗?其实不然。黑格尔的自我认识,主体是绝对精神,而哲学解释学所说的理解历史,其主体则是历史此在;黑格尔的自我认识,给了的结果是封闭的绝对存在,而伽达默尔的理解历史给出的则是由历史此在向前延伸、勘探到的存在。也就是伽达默尔所说的“效果历史”。“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注:同上,第385页。)这种新的历史观在人文历史领域具有普遍的效用:既我们的存在是历史性的,那么我们的任何精神活动也就都是效果历史的一个事件,换言之,也都是一个理解与解释的事件。
理解与解释在何种条件下才能展开?在历史此在的解释学处境之中。
解释学处境的展现有赖于“效果历史意识”这个基础。何谓效果历史意识?伽达默尔曾这样界说:“在我所使用的效果历史意识这个概念中,合理地存在着某种两重性,这种两重性在于:它一方面用来指在历史进程中获得并被历史所规定的意识,另一方面又用来指对这种获得和规定本身的意识。”(注:同上,第11页。)这首先是说,我们的存在是有历史性的,这么说,并非在重复“我们是历史的存在物”这样一个黑格尔式的说法,在黑格尔的话语中,历史存在物是被绝对存在规定好了的,也即定在。而效果历史意识则表明,我们是历史过程之中生成的一个存在者,在这个存在者身上,既携带着开放的历史实在给予的东西,又携带着我们所属的历史传统给予我们的东西,于是我们的历史性属于历史存在。不过,我们的历史性是一个需要获得确认的东西。它决不是那种在我们的自我意识中自明的东西,而可以说是在我们的自我意识的掩盖下尚不明朗的朦胧地带。如果不是如此,理解就无从缘起。其次,效果历史意识是对自己的历史性进行反思的意识,如果没有这种反思,则至少表明此在历史性尚不自觉。因之也就尚无理解与解释现象发生。
反思自己的历史性与理解历史属于同一个事件。它必然展开在一个解释学处境之中。正是基于这种地位,“解释”被视为精神现象的普遍事件。解释学处境的特征是怎样的?,按伽达默尔的解说,“处境这一概念的特征恰恰正在于,我们不是处在这处境的对面,因而也就无法获得关于它的对象性的认识。我们处在这种处境之中,我们总是发现自己已处在这样一个处境之中,对这个处境的澄明是一项永远无法彻底完成的任务。”“但之所以无法完成,并不是因为反思具有缺陷,而是因为我们是作为历史性的存在,这种无法完成性是由历史存在的本质所决定的。”“所谓历史性地存在,这就是说,永远不能在自身的知识中达到领悟。”(注:见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92版,第387页,此处引文用倪梁康译文,见倪著《现象学及其效应》,第287页。)这意味着什么呢?其一,解释不是对历史实在的一种彻底的、终结性的把握,因为你的成见就在其中,其二,解释也不是自我认识,因为,历史性存在乃是与历史实在交织在一起的存在方式与意义。在此种处境中,就意味着任何解释都是相对的,都不是绝对客观的。
在此种处境中,解释必先在解释物(文本)面前展开自己的“视域”,这就是说,处境中人,就带着处境规定给他的限制性眼界,“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这个区域囊括和包容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见到的一切。”(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92版,第388页。)视域,就是著名的地平线概念。反思自己所处的历史性存在,必先拥有自己的地平线。
那么,解释是否意味着在这地平线上去明察呢?显然不可这样理解。解释不是宣判,而是展开为一个过程:当解释的地平线出现之时,就会在视域的边缘上出现一些既熟悉,又陌生的地带,那是什么?那就是文本展现的视域与解释者的视域相融合的部分。文本的视域(假定它是一个可解释的文本的话)总是一个或正面,或反面地与解释者的视域相对应、对立而又有相融部分的视域,在文本的表面物之后总是呈现着被传统处理过的、关于历史真实的从来如此的见解,同时又必然地呈现着被解释打开了的边界。于是,解释就是解释者的视域与文本的视域相互辨认、相互指证、相互认可与确认的过程。由于历史此在的前见,解释者的视域与文本的视域之间,“历史意识进行的每一次与传统的交往,自身都会经历到文本与当下之间的张力关系。”(注:见伽达默尔《真理与方示》,上海译文92版,第393页,此处引文用倪著第278页。)这种张力其实是一种积极有效的关系,没有这种张力,才真正是我们的视域不具备历史性的标志。但解释就不是一味地对立,它就会在中间地带出现一种融合。即“视域的融合”。解释学的真正位置就在于这中间地带内。(注:见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92版,第379页。)
视域融合作为一个过程,它的出现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种循环论证;当下的视域的未经确证的意向须在文本视域的辩认、确证中才是可能的;而文本视域的未经言明的开放的背景的显现又有待于当下的视域的明朗,于是这个矛盾的解决有赖于循环。当下的地平线与文本的地平线就是在这种不断往复的循环中获得了视域的融合。从而使历史存在及其意义的理解向无限推进一步。由此,循环论证就是解释学关于意义的连续性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则。
循环论证在旧的释义学和传统的逻辑学都是一种必须排除的情况,它是指:要想说明局部必先说明整体,要想说明整体必先说明局部。如此一来,释义就会陷入荒谬。海德格尔曾纠正了这种见解,在他为解释学奠基时,就已把循环论证视为有效原则。他指出:“在这一循环中看到恶性循环,找寻避免它的门径,或即使只把它当作无可避免的不完善性‘接受’下来,这都是对领会的彻头彻尾的误解。”“循环中包藏着最源始的认识的一种积极的可能性。”(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87版,第187页。)因为解释学是把解释看作向无限开放的存在延伸的工作,而不是像旧释义学那样,把释义看作向意义封闭的文本中求准确的努力。那么,层次的不同决定着功能的区别。既然我们否认历史存在中有什么绝对存在,一切都在变化之中,那么,封闭的意义,在精神探寻中就是一种错误的期待。历史存在及其意义永远不会有一个无可置疑的最终成果静静地等在那里,等待人们不加循环地去采摘。反之,要想理解历史,就必须要正视这个循环,正确地加入这个循环。
循环论证、视域融合、效果历史意识就一道构成了哲学解释学关于意义连续性的基本理论。一切历史的理解活动都无非是在效果历史意识的作用下,由循环论证的方式对历史真理的拓展和延伸,存在与真理就是在这种拓展和延伸中向前推进,探入无限。它告诉我们,意义的连续性进展从轨迹上看,乃是一条弧线。意义的敞开,精神的发展是一条弧线,而不是一条直线,这个描述是明快而又令人深思的。它昭示着一种现代的存在观和意义观。这个描述是明快而又令人深思的。它昭示着一种现代的存在观和意义观。在这里,让我们再一次品未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的书前题诗吧:
如果你只是接住自己抛出的东西,
这算不上什么,不过是雕虫小技;——
只有当你一把接住
永恒之神
以精确计算的摆动,以神奇的拱桥形弧线
朝着你抛来的东西,
这才算得上一种本领,——
但不是你的本领,而是某个世界的力量。
三、哲学解释学的有效性及其边界
意义的连续性,无疑是二十世纪人类思想的重大课题。当人们以反形而上学为旗帜,一次又一次地在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生命领域大规模发起大解放时,却一次又一次地面临意义的断崖,当人们把现世的享受当作生存的意义,并以前所未有的能力创造着前所未有的物欲的时候,却时时觉得自己已迷失在无意义的荒原,这种境遇反映着一个悖论:形而上学既要不得又缺不得,有了形而上学就有了意义连续统一的前提,但也就有了使意义凝固的封条,而抛弃形而上学固然杜绝了任何产生教条及封闭意义的可能,但也就根绝了意义追问的可能,难道可以设想没有关于终极价值的设定,却能使人们找到意义的事吗?看来,形而上学应当废止,但形而上的欲望却是永远不应、也不可能废除的,因为这种根本性的欲望乃是意义之源。由海德格尔从现象学方法中生发出来的存在论以及随后形成的哲学解释学,从本质上看,是以反形而上学的方式“重构形而上学”的努力。(注:保罗·利科《解释学与人文科学》,河北人民87版,第88页。)或许,应该说哲学解释学的出现才是二十世纪人类思想一个“秘而不宣的期待。”
哲学解释学是否不辱使命地满足了这一期待呢?在我看来,还只是半部辉煌、半篇文章——
首先,必须承认,哲学解释学的努力推进了正确运作、有效满足形而上的欲望的进程,使现代哲学的意义论建立在一个较为明智的方法论基础上。
其一、它确认了此在的优先地位,确认了从现象出发的原则,更重要的是,它确认了现象与此在乃是形而上的存在意义的基础,而不是被理性主义所鄙弃的无真实可言的假象,也不是旧唯物主义所钟情的客观本体;也就是说,本真状态的此在与现象,既不因分有彼岸之光而有意义,也不因其实存而自明为意义,现象之为现象、此在之为此在已既是第一性的、实存的、未被规定的“存在者”,同时它又是带着“历史前见”的、带着“纯粹意向”的关联物,正是这种两重性,使此在与现象成了解释的起点,成了意义生成的起点。
其二、它确立了广义的文本在意义生成中的重要地位,这就把意义的视域以及意义的探寻放置在一个确凿的、实际的、可观察的背景之上,意义实质上是效果历史意识的“水中月”,“镜中花”,是特定文化系统和文化语境中生成的,脱离这种语境的意义言说只能是伪造。在意义生成的诸种条件之中,文本是一个沟通此岸与彼岸、未知与已知、经验与超验、现实与传统的中介,正是这个中介的开放性,使关于意义的言说既与传统相连续,又使传统向未知延伸,也正是这个中介,关于意义的话语同传统的话语系统保持在一种景深之中。这一意见对于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反思文化传统、建设文化传统,无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三、意义的生成只能是此在与文本的对话与解释,是开放的存在与经典文本——艺术、游戏、节日、庆典、习俗、交往方式、惯例在对话中解释传统、延续传统、发展传统的本质性事件。这个思路的有效性,至少是将意义的创造归位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上,它将能起到扼止主观主义、避免主体性过度溢出的作用。
其四、以对话为逻辑原则的解释,就使意义的追问不再以绝对客体为本体,不再以绝对知识为其目的,真理性的意见也不再具有那种夸张的绝对正确性,意义也不再是那种凌驾于历史存在之上的“绝对”。如此就既免除了把相对意义、相对真理僭越为绝对意义、绝对真理的激进,使思想的冲刺多一份审慎,同时也就使思想多了一份尊严;另一方面,这种意义论的逻辑又保留了终极意义的形而上的永恒位格,使之成为永无终结的引力之源,而不被实体化、人为化、教条化。应该说,这是对形而上学的真正克服,同时又是对形而上的欲望的最有效保存。
其次,哲学解释学能否为自己终结性地解开人类存在及意义之谜的努力而高奏凯歌?我以为不能。当哲学解释学把存在及其意义的谜团机智地处理为解释时,其细密的梳理和严格的逻辑所建立的全部理论大厦,却立足于在一个并非无可置疑的基石上,这就是:此在。
当人们把此在视为通向存在的起点时,当此在的解释学角色——观者成为意义的逻辑前提时,我们为这种把存在与意义之思的视野推进到无限开放的现象世界的构想而欢呼,但是当人们从这里出发去寻找意义时,就在这个原点上必然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此在是一个面目不清的角色,与此同位的观者是一个面目不清的角色,经验世界里,谁是合格的此在?谁是真正的观者?谁的此在、谁的此时具有敞开存在昭示意义的权力?谁的此在是恰好把握到历史存在变化的“在者”?是所有的“此在”,还是特定的“此在”有此权能?与此相应,是否所有的观者的“前见”都无差别地拥有解释权?如果是这样,是否所有的解释,即见仁见智的解释都无差别地合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谁的“前见”将具有更多的合理性?又怎样判定谁的“前见”以及解释更为合理?如果判定的尺度取决于对话中达到的视界的融合说出的东西,那么,你怎能说谁的前见能带来对话,谁的前见不能带来对话,对同一个文本的不同话语有无正误之分、真伪之分,如果有,裁决的权威是谁:如果把裁决权交还给文本,岂不是又回到了旧解释学中,如果不能由文本裁决,又该由谁来裁决呢?我以为,这些疑问归根到底都来自一个问题:此在的本真状态与非本真状态的界线在哪里?本真状态的此在何以证明自身?显然,这个被哲学解释学轻轻避开而实际上不可能避开的悬案,正是哲学解释学的“阿喀琉斯之踵”。
此在的非本真状态到本真状态的过渡,与经验此岸与超验彼岸的鸿沟及其过渡属同一个命题的不同层次,哲学解释学把寻找意义的人们带到了现实世界的时候,尽管它已立足于存在思维的最直接统一的状态——此在,然而此在之为此在,仍是一个不能自明的起点,仍是一个必须用另一套方法才能进行廓清的疑团,不然,整套的哲学解释学将难有真正的效力,甚至会在破除思想的极权主义时,放任思想的无中心状态。这给现代哲学思考留下了前沿性课题。看来哲学解释学理论效力也有着自己的边界。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正确地理解,建设性地运用其理论原则,避免又一轮的理论迷信,是十分必要的。
标签:解释学论文; 存在与时间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真理与方法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伽达默尔论文; 存在论论文; 哲学家论文; 现象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