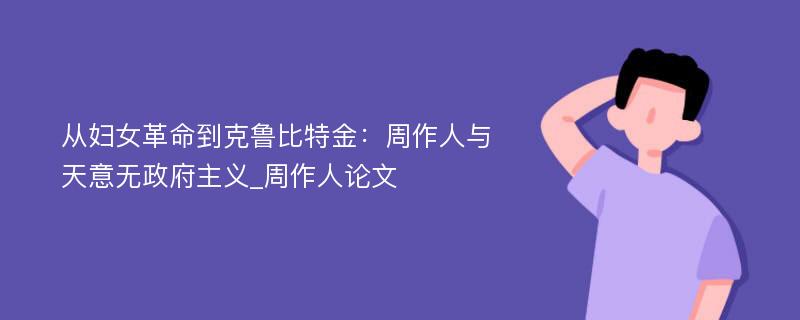
从女子革命到克鲁泡特金——《天义》时期的周作人与无政府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克鲁论文,无政府主义论文,时期论文,女子论文,周作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广泛传播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无政府主义对中国近现代思想的发生、形成、演变均有着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五四”前后,无政府主义思想更一度成为社会改造思想的主流。包括蔡元培、陈独秀、鲁迅等在内的一大批启蒙知识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这股思潮的熏染。其中周作人鼓吹的“新村”运动,更带有明确的无政府主义色彩,并成为启蒙思想界流行一时的话题。但是,对这一问题研究界显然还缺乏足够的关注。因此,本文追根溯源,试图通过梳理早期周作人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种种关系,发掘五四时期周作人新村理论的思想背景,为重新解读新文化运动前后周作人的思想变动,提供一个新的逻辑起点。
一 与《天义》的文字因缘
周作人最初接触无政府主义的时间可以追溯至留日时期。1906年夏秋之间,周作人和回乡的鲁迅一同赴日,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这一时期,以幸德秋水、堺利彦、大杉荣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作为日本社会党中“软”、“硬”两派中的“硬派”,占据了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主导地位。这些日本社会主义者与中国革命派知识分子交往密切,在留东学界极有影响。在日本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推动下,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于1907年初现历史舞台。是年6月10日,刘师培、何震夫妇于东京创办刊物《天义》,鼓吹无政府主义,以言论偏激大胆著称。同月中旬,刘师培、张继等于东京创办“社会主义讲习会”,7月31日举行第一次集会,“会员到者九十余人”[1]。同年6月22日,另一份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在巴黎创刊,以吴稚晖、李石曾、褚民谊为骨干的编撰阵容亦可谓活力十足。一时间,无政府主义思潮弥漫于革命派知识分子阵营。
留东学界激烈的思想氛围,无疑对青年周作人有所触动。周氏兄弟都成为《天义》的读者,周作人还接触到了《新世纪》,且对吴稚晖的文章印象尤深。[2](P677)对于激进思想的兴趣很快体现于周作人的文学活动。他翻译了斯谛普尼亚克的短篇小说《一文钱》,载《民报》第二十一号。在周作人看业,这位民粹派革命者的作品是一篇“宣传小说”,流露出俄罗斯革命者特有的乌托邦色彩。[3](P168)周作人对作者的亡命生涯颇为熟悉(注:他在《读书杂拾》中介绍斯谛普尼亚克“与克洛颇特庚同为却轲夫斯重兀(Chaikovski)党人,运动农工至为有力。后逃亡英国,著书布其国中惨状,中有《地下之俄罗斯》一书,文情皆胜,最有名,露政府厉禁”,这些材料显然是从克鲁泡特金的《一个革命者的自叙》中得来的。),称斯氏为“虚无论派之社会改革家,于官僚僧侣,至为疾恶,篇中所述,虽多诙谐,而诚实者太半,特稍张大而已”[4](P538)。此后周作人又在文章中多次提到斯谛普尼亚克,对这位革命者兼作家始终保持着关注。(注:例如1909年,周作人将《一文钱》收入《域外小说集》第二集;1917年又将《一文钱》发表于《叒社丛刊》;1926年,他在《奴隶的语言》一文中又提到了斯谛普尼亚克。)然而,对民粹主义者的偏爱只不过是周作人思想逐渐倾向于激进的一个讯号,真正使他对无政府主义萌发理论感兴趣的,则是《天义》对传统两性伦理的批判。
《天义》最初是何震所主持“女子复权会”的机关刊物。它标举“女界革命”,首先是与何震的个人兴趣有关,而后更是成为《天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一个特征。何震曾就读于上海爱国女校,深受蔡元培、蒋智由、林懈等人“男女平等、女权革命”主张的熏染,赴日之后接受了无政府主义,言辞更激烈。借助于无政府主义的批判理论体系,何震首先指出了中国女性悲剧命运的政治、文化背景:专制统治者“以一男配无量之女”,“实男界之娼妓”,“其凌虐女子之罪,上通于天”[5];儒家学说亦为男权统治服务,“苟有利于男子,不惜曲辞附会以济其私。其始也,立夫为妻纲之说,一若天之生人,厚于男而薄于女。欲伸男子之权,则以女子为附属于男,又虑女子不甘附属也,则倡服从之说,并责女子以从一而终”。文章痛陈:“吾女子之死于其中者,遂不知凡几。故儒家之学术,均杀人之学术也!”[6]其中隐含了对传统儒学异常决绝的背叛。其次,无政府主义作为社会革命理论,也使何震可以对女性问题的社会根源进行深入分析。她颇有预见地指出,封建传统是女性大敌,资本主义也并非理想世界。虽然西方女性地位有所改善,如实行一夫一妻制、婚姻自主、男女同受教育等,但仍然受经济因素的强烈制约:“名曰结婚自由,然欧美男女之结婚,岂尽由两性之爱恋哉!或男子以多财相耀而诱女子,或女子挟家资之富而引男子爱慕之心,或富者恃其财力而强娶民女,此为力所缚者也。”所以女性并没有真正摆脱枷锁,“若如今日欧美之制,势必女子有自由之名而无自由之实,有平等之名而无平等之实。”[7]在何震看来,女性要获得解放,必须将男女革命、家庭革命与社会革命同时进行,甚至可以性别、家庭革命为社会革命的突破口。“汉一”就在《毁家论》中指出:“盖家也者,为万恶之首。自有家而后人各自私,自有家而女子日受男子羁縻,自有家而后无益有损之琐事因是丛生”,“欲开社会革命之幕者,必自破家始矣”[8]。《天义报启》也认为:“世界固有之阶级,以男女阶级最严”,“故欲破社会固有之阶级,必自破男女阶级始[9]。”
《天义》把改变女性地位作为社会革命的契机,从而将女权革命提到相当的高度,这与周作人对女性问题的重视正相契合。清末民初,革命思想界出现了大量对于“新女性”的想像和叙述,正如刘纳先生所说:“男性不再赏玩女性的幽怨,却期待女性的奋起。……这一时期的男性知识分子破天荒地试图以男性为标尺改造女性,以期让女性与男子担负起同样的‘国民’的责任。”[10](P88)传统文人模仿女子口吻的创作方式仍然流行,但作品已注入了崭新的社会内容,因而不再一味轻薄。周作人的“戏拟”之作便处处透露出对女性的全新要求。从1904年开始,他以“吴萍云”、“萍云”、“病云”等笔名在《女子世界》发表文章多篇。在《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一文中,他批评中国传统女子“情如小鸟,弱不禁风,多病多愁,工啼善怨”,是“只供男子之玩弄,为生殖之器具也者”,又说“然此乃19世纪之女子,而非20世纪之女子也!”而要成为“20世纪之女子”,就应该“易陌头杨柳,梦里刀环之感情,而尝弹雨枪林,胡地玄冰之滋味”,使自己成为“不尚妍丽而尚豪侠,不忧粗豪而忧文弱”的新女性”[11](P271)。在《〈造人术〉跋语》中,周作人更是赋予女性以再造中国的历史重任:“世界之女子,负国民母人之格,为祖国诞育强壮之男儿,其权直足与天地参,是造物之真主也。”“吾国二万万之女子,二万万之新造物主也。文明种子,于是乎萌芽;祖国人才于是乎发育。”[11](P273)依此思路,他改译了《天方夜谭》中的《阿里巴巴和四十个强盗》,题为《侠女奴》,连载于《女子世界》。可能是担心读者过于关注离奇的情节而忽略译者的本意,周作人托名“会稽碧螺女士”一吐心曲:“行踪隐约似神龙,红线而今已绝踪。多少神州冠带客,负恩愧此女英雄。”[12](P322)后来在出版单行本时,周作人更是借《绪言》明白道出自己推重一介“女奴”的真正用意:“沉沉奴隶海,乃有此奇物,亟从欧文移译之,以告世之奴骨天成者。”[11](P522)译者不惜拔高原作以激发民气的良苦用心表露无遗。此后发表的《女猎人》、《好花枝》、《女娲传》等篇也都寄托了类似的深意。
由于东渡之前周作人已对女子问题颇为热衷,因此,他向“女子复权会”主办的《天义》频频投稿也就不值得奇怪。(注:他以“独应”笔名在《天义》上发表诗文《妇女选举权问题》、《绝诗三首(刺女界也)》、《读书杂拾》、《中国人之爱国》、《见店头监狱书所感》、《防淫奇策》以及《论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之别》等等。历史学者杨天石先生还认为周作人与吴弱男以“雠”的笔名合译了马拉叠斯丹(E.Malotosta)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之工人问答》(载《天义》第16至19卷合刊),见《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3),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4页。但我面询杨先生,却没有得到能够支持此说的直接证据。由于此文为白话译文,而周作人早期罕有白话作品,因此南开大学张铁荣先生也不认为此文为周作人所译,所以此处只能存疑。)可是略加比较即可发现,《天义》时期的周作人更加注意将女性解放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政治意识显著增强,这显然与日本当时的社会革命思潮有关。在《妇女选举权问题》中,周作人详细介绍了英国妇女杂志中关于女性与选举权的各种观点,明确支持女子获得平等选举权,同时指出留学女界现状勘忧:“顾比者女子所学,仍以物质为宗,冤哉!(留学生矣多营营于铁道工艺,嗟夫!是攘攘者,皆杀吾族精神之虫害也夫!)”他反对女性留学偏重于器物技术层面的倾向,主张通过女性自我精神的觉醒与张扬,摆脱精神枷锁、获得平等权利。尽管周作人的认识较之在国内时已有所进步,但《天义》的编者(可能是何震)却认为还不够激进:“既争参政之权,即系承认有国家有政府也。故本社之旨,在于灭绝人治,弭消男子之特权,使男女归于平等,不仅以妇人参政为目的也。”[11](P284)显然,周作人虽认识到女性问题本质上属于社会问题,但他选择通过代议政治实现男女平权的思路,较之何震“灭绝人治”式的女权革命观更为保守。然而,四个月之后发表的《防淫奇策》,就表明周作人向无政府主义有所靠拢。他在文中指明,所谓“淫盗”的产生,原因在于人的本性屡被扼杀、不能张扬,遂向“恶”发展。其根源在于“以人人私有其女子并私有其财产也”,“岂知以女子财产为私有者,已犯天下之首恶”,因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同样是“淫恶”的渊蔽:“其男女结婚离婚虽克自由,然亦仅有其名耳。实则男女婚姻,受宗教法律及伪道德之裁制者,不知凡几。或两情相悦,以门第财产之差别,不克遽遂其情,是则今日之婚姻,均非感情上之婚姻也。既非出于自由恋爱,则男女之大欲不克遂,淫恶之生,乃事所必然。”[11](P5)周作人将女性问题的根源归结为财产私有制度,其实已否定了自己此前在代议政制下“争取选举权”的改良主义观点,其结论必然指向完全推翻现在的私产制度,这与何震的主张已相当接近。值得一提的是,周作人在其后漫长的文字生涯中,始终坚持这样的女子革命观,再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由女子选举权而至发现女性问题的社会根源,周作人实则已对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改造理论有所触及。当然,“国家的独立始终是中国革命的首要主题”[13](P309)。这就决定了民族主义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总体思想背景,周作人也不例外。但无政府主义的介入,却使周作人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强烈诉求中,仍能保持对于狭隘国家主义的警惕。他在《中国人之爱国》一文中嘲讽那些放言爱国的“中国志士”:“夫其标义甚高,设词甚美,敷陈所至,议论风生,纵横浩瀚,如河汉之不可及也”,然而“一经俗说,便生曲解,谬种流传,利害倒置,祸胡胜言”。所以要想使中国不亡,“其惟君辈之勿言爱国始矣。”因为“通言爱国,皆爱政府耳”,无异于替腐朽政权苟延残喘。在他看来,真正的爱国应该发自于真挚的乡土感情,如莱蒙托夫,“顾其有情,在于草原浩荡,时见野花,农家朴素,颇近太古”;而不应“盲从野爱,以血剑之数,为祖国光荣,如所谓‘兽性之爱国者’也”,不可“以凶暴为雄,以自夸美”,更不能自甘为奴,从暴君驱驰,而言忠爱。所以,他强调:“凡是爱国,国民之云,以正义言,不关政府。”周作人将“爱国”归结为朴素的、天然的乡土情感,与盘踞在同胞之上的统治者无关,何况清廷这样的“异族”政府。在他看来,满清政府是根本不足与之合作的,那些“国民拒款会”、“女子保存国权会”,“其谬比于吴紫英创办之国民捐。若辈蠢蠢,所为支离,莫可究诘,徒增悯叹”[14](P4-5)。文中周作人多次否定政府,反对借国家主义的名义为清廷苟延残喘,与《天义》的无政府主义论调颇为接近。但周作人笔下的“政府”又是有明确的现实所指的。换言之,无政府主义对“国家”的抽象批判在作者的借用中被不动声色地转换为“反满”,从而以潜台词的方式强化了其中的现实意义。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表述方式并非出于周作人对无政府主义的有意误读。相反,它倒是这一时期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经常使用的、源自民族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双重身份的一种特殊修辞方式。
1907年12月,刘师培夫妇秘密回国,向两江总督端方自首,充当暗探。次年二月,两人回到东京,继续编辑《天义》,不久另出《衡报》,继续宣传无政府主义。此时由于种种原因,刘师培夫妇与章太炎、陶成章等发生冲突,关系破裂。1908年11月,刘师培夫妇回国,不久即因出卖张恭而败露劣迹,刘师培遂公开入端方幕,为其考订金石,兼任两江师范学堂教习。[15](P164-173)在民族革命者的眼中,刘师培夫妇既然可以由一个极端革命派转变为叛徒,那么他们所鼓吹的无政府主义恐怕就和他们的人格一样难以信任。与此同时,也可以注意到周作人对无政府主义的态度迅速冷却,他的文章中很难再找到激烈的词句,或者即与此事有关。事实上,也许正是周作人对刘师培人品的鄙视,使他多年后仍然说:“当时也曾遇到《天义》时代的刘申叔先生,但我一毫都不受到他的感化,在他的《国粹学报》时代一样。”[16](P368)我们知道,对于一个《天义》的忠实读者和撰稿人而言,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周作人像钱玄同一样参加过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活动,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周作人与刘师培的文字之交不仅止于《天义》。据周作人回忆,由于友人孙竹丹的介绍,“我们为《河南》写文章,……编辑人为刘申叔,刘名光汉,系江苏人,与河南无关,不过因其学问闻名。且其时亦搞革命,故请其担任编辑”[17]。周作人的文章能够频频见于《河南》,与刘师培担任《河南》的实际主编恐怕也不无关系。(注:在《河南》上,周作人相继发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第4、5期)、译作《庄中》、《寂寞》(第8期)以及《哀弦篇》(第9期)等重要文章。)较之周作人在《天义》上的篇什,这些文字多谈文学,政治气味更为寡淡,也与《河南》较为隐晦的整体风格协调一致。其原因即在于刘师培虽为无政府主义者,但也是国粹派的主将,通过《河南》宣传无政府主义,正如周作人所说:“似乎也不可能,而且无此必要吧。大约只是写他那‘国粹学报’派烦冗的考据文章。”[3](P255)
二 与克鲁泡特金的相遇
同样是向刘师培编辑的刊物投稿,场合不同,所投稿件的政治色彩便有浓淡之分,这显示出周作人颇善揣摩编辑心理的一面。而在《天义》发表的文章中,周作人多次提到了克鲁泡特金,便更体现出他对时代风气的敏感。
巴枯宁去世之后,克氏的无政府共产主义逐渐成为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主流。周作人留日时期,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正受到克氏理论的影响。1905年2月,幸德秋水被捕入狱。他在狱中“被克鲁泡特金的著作所强烈地吸引住”,从而表现出向无政府主义转变的趋向[18](P77)。此时克氏的《互助论》、《面包与自由》等经典著作也相继译为日文。与之相应,《天义》上对克氏学说介绍也最多。所以,周作人对克氏产生兴趣,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与时人一样,周作人首先也是被克氏的冒险生涯与革命精神所吸引。他回忆道:“克鲁泡特金的著作我也读过《面包的获得》等,又从《在英法狱中》一书内译出一篇《西伯利亚纪行》,登在《民报》第二十四期上……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别的两种,即《一个革命者的自叙》与《俄国文学的理想与事实》。”[16](P3-4)《一个革命者的自叙》,又名《一个革命者的回忆》、《我的自传》。书中克氏以优美的文笔记叙了自己前半生的生活,介绍了俄国、西欧民粹派及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活动,是克氏作品中最富于文学性的一部,[19](P509)也最能表现他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自我牺牲精神。大杉荣曾说:“我们要真知道克鲁泡特金,与其读他底《面包与自由》或《互助论》,不如先读他底《自传》。”[20](P505)对这样一部既有文学色彩又富革命精神的作品,周作人印象颇深:“这是一部很好的书,我还是民国以前读的,现在原书已久已遗失了,但有好些地方还记得。[16](P3-4)。1907年,在鲁迅的建议下,他选取《自叙》中的一节加以改写,以《论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之别》为题发表于《天义》,[16](P229)意在廓清林纾之流对于“虚无主义”的错误认识。文中指出“虚无论者”语出屠格涅夫小说《父与子》,后广为流行, “论者用为自号,而政府则以统指叛人”。于是不明真相者遂将种种暗杀、暴力活动皆归罪于虚无党人,“致混虚无主义于恐怖手段(Terrorism)”。然而“此大误也,是无异以哲学问题混入政治,如斯多噶宗派(Staicism)之与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相去不知凡几矣”。他强调,虚无主义“纯为求诚之学,根于唯物论宗,为哲学之一支,去伪振敝,其效至溥”,不但并非林纾等人以为的“剧盗术”,反是医治“虚伪凉薄”之国民性的一剂良药[14](P46-48)。一年之后,在畅论文学之际,周作人仍念念不忘向读者重申虚无主义的真精神:“有译《双孝子噀血酬恩记》者,以无君党人溷于虚无论者,情实既迕,言议尤惛。夫虚无之论,本于哲学唯物一派,正中国所谓求诚之学。其与政海波澜初无系涉,今妄为周纳而任情斥詈之,纵有益于一人,奈诚妄之道何哉!”[2](P28)周作人指出虚无主义并非仅有暴力的一面,而是确有其哲学基础,力求使读者对无政府主义的兴趣从行动转移至理论层面,在当时思想界实属难能可贵。延至五四时期,周作人对虚无主义的评价仍以克氏说法为依据。[21](P69-70)此外,克氏另一部自传性的作品《在英法狱中》对周作人也影响颇深。在《读书杂拾》、《西伯利亚纪行》中,他对西伯利亚流放苦境以及斯谛普尼亚克生平的介绍皆源于此书,并称赞克氏“俄国民生彻底之变革”的革命主张为“仁人之言”[4](P533-534)。他还在《见店头监狱书所感》中详细介绍了克氏对监狱制度的观点,批评了留学生界热衷狱政之学的庸俗风气:“特狱之为物不祥,仁人所不乐言,更何必需之有?”[14](P51)把一位外国人反复称为“仁人”,这对于孤傲如“鹤”[3](P268-269)的周作人来说并不多见,足见他对克鲁泡特金的推崇。
周作人对《俄国文学的理想与事实》的喜爱,则体现了克氏对周作人影响的另一面——文学批评。此书原名《俄国文学的理想与现实》(《Ideas and Realities in Russian Literature》),由克氏在美国的八次讲演汇编而成,初版于1905年。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几乎同时出版了韩侍桁和郭安仁(丽尼)的两个译本,均名为《俄国文学史》。虽然翻译成书的时间较晚,但这本书其实很早就对中国文学批评界产生影响,成为中国文学界认识俄国文学的重要参考。1921年,沈泽民节译了此书的一部分,以《俄国的批评文学》为名刊于《小说月报》号外;沈雁冰的《近代俄国文学三十人合传》也部分借用了此书的一些论断;此外,郑振铎的《俄国文学史略》也参考了克氏的观点。但最早接触此书的,恐怕还要属周作人。[16](P4-5)他回忆道:
《俄国文学》所给我的影响大略与勃阑兑斯的《俄国印象记》相同,因为二者讲文学都看重社会,教我们看文章与思想并重,这种先入之见一直到后来很占势力。我还不忘记怎样的佩服莱耳芒多夫(Mikhail Lermontov),以不能见他的《木齐剂》(Mtsyri)一诗为恨,同时对于普式庚(B.Pushkin)很感到不满意。普式庚被称为俄国的摆伦,但他没有摆伦那样的对于自由的祈求与对于伪善的憎恶。克鲁泡特金说:
“到了晚年他就不能再与那些读者们接近,他们以为在尼古拉一世的军队压服波兰以后去颂扬俄国的武力,不是诗人所应做的。”勃阑兑斯也说:
“普式庚少年时的对于自由的信仰,到了中年时代,却投降于兽性的爱国主义了。”他又引普式庚在1831年所作《给谤毁俄国的人们》一诗为例,即是为辩护俄国用武力压服波兰的独立运动而作。昨今时价不同,普式庚的名声很大了,究竟如何我辈外行无从得知,但多少总是先入为主,觉得上述二人的话仍有些可信耳。[16](P4-5)
在前面提到的《中国人之爱国》一文中,周作人对“兽性的爱国”的批判,显然就来源于克鲁泡特金与勃兰兑斯等人对普希金狭隘民族主义的否定。五四时期,周作人对克氏文学论说的运用更为娴熟。他曾借用克鲁泡特金对《死魂灵》中契珂夫形象的分析来说明阿Q的典型性,[16](P131)还在《诗的效用》一文中以克氏的道德观来讨论诗怎样“感人向善”:“这善字似乎还有可商的余地,因为他的概念也是游移惝恍,没有标准……倘若指那不分利己利人,于个体种族都是幸福的,如克鲁泡特金所说的道德,当然是很对的了,但是‘全而善美’的生活范围很广,除了真正的不道德文学之外,一切的文艺作品差不多都在这范围里边,因为据克鲁泡特金的说法,只有资本主义迷信等等几件妨害人的生活的东西是恶,所以凡不是咏叹这些恶的文艺便都不是恶的花。”[22](P18)还是在这篇文章中,周作人又以克氏对文艺价值标准的认识来反驳托尔斯泰民粹主义艺术论:“托尔斯泰论艺术的价值,是以能懂的人的多少为标准,克鲁泡特金对于他的主张,加以批评道,‘各种艺术都有一种特用的表现法,这便是将作者的感情感染与别人的方法,所以要想懂得他,须有相当的一番训练。即使是最简单的艺术品,要正当地理解他,也非经过若干习练不可。托尔斯泰把这事忽略了,似乎不很妥当,他的普遍理解的标准也不免有点牵强了。’这一节话很有道理。”[3](P19)可见,从留日时代到五四前后,作为文学观念的重要源泉,克氏对周作人的影响从未中断。
除了自传与文学之外,周作人对克氏的介绍似乎较少涉及其社会政治思想。然而,这并不表示周作人对克氏政治理论的冷漠。事实上,周作人对于克氏的《互助论》、《面包与自由》等经典著作亦相当熟稔。它们所产生的影响,只是在进入新村时期之后才得以逐渐显现,而且很可能比周作人自己所意识到的要深入许多。周作人对克氏思想的持续关注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周作人所推为“仁人”的克鲁泡特金,也正是日本“白桦派”提出新村主张的重要理论资源。如果没有早年对无政府主义的接触以及对克氏思想的认同,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对新村的热衷就将会失去它的逻辑起点,从而变得难以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