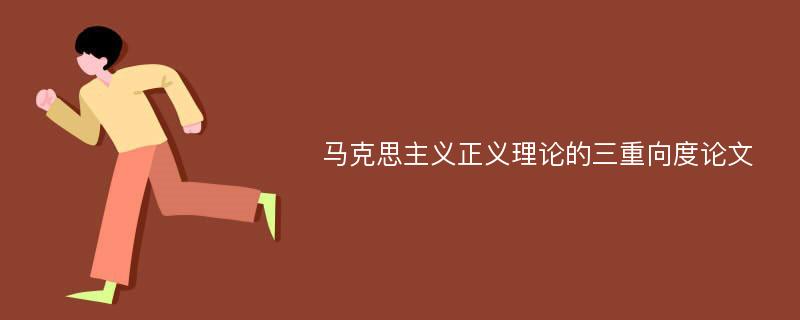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三重向度*
张晓萌
[摘要] 在政治哲学史中,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否存在正义理论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构成其合理性始终是争论不休的学术焦点。无论是伍德从法权意义上重新审视马克思的正义主张,还是柯亨从自我所有权角度捍卫马克思的正义立场,都从侧面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实现了科学与价值的辩证统一,消除了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将二者对立的理论张力,致力于寻求对社会存在的内部矛盾和历史规律的更深层次的理解,而非在历史生成之外构建绝对真理和规范性原则。把握其价值取向和内在理论向度成为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研究的题中之义,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包含三重向度,即历史发展运动中的正义向度、社会生产领域中的正义向度以及社会结构和制度变革的正义向度。
[关键词] 正义;历史唯物主义;生产正义;制度正义
正义体现着人类对美好社会的理想诉求,又是反映和评价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准。自古至今,人类从未停止过对正义的追寻,因为人类始终致力于自身的发展完善和对理想社会的崇高追求,并且这种追求日趋自觉与深刻。无论是古希腊哲学传统将正义理解为美德与等级秩序,还是近代西方思想家从抽象人性论出发寻求永恒正义原则,都呈现出对正义的抽象化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继承了西方哲学传统,更重要的是完成了对其批判与超越,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揭示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表达了对人自身全面而自由发展与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追求。历史唯物主义的叙事话语在承载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的同时,也为探讨马克思的正义理论留下了理论难题,即马克思从未试图探讨正义的规范性原则,也没有尝试建构系统的正义学说。如此,马克思主义是否存在正义理论?在何种意义上构成其合理性?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与解读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议。如何批判性地分析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面临的诘难,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资源进行系统梳理并予以辨析,俨然成为当今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题中之义。
一、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合法性论争
对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阐释,首先涉及的问题是对其“合法性”的回答。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历史难题,即马克思对待“正义”的理论态度究竟如何。马克思不仅没有在文本中系统地对正义及其相关概念予以解读,还在批评拉萨尔等人时明确地对“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进行公开谴责。那么,马克思究竟批判的对象是资产阶级关于正义和权利这一类抽象的、空洞的道德说教,还是如一些学者所言马克思从根本上反对平等、权利的观念,并且拒斥正义原则和基于此而产生的分配?
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究竟是否给正义预留了合法的位置?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以下两种基本观点。一方面,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中存在正义缺席说。以艾伦·伍德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马克思没有以不正义之名谴责资本主义,因为正义并非某种道德概念或原则,正义与否的标准仅仅取决于社会关系和分配制度与生产方式之间的相适应性。另一方面,以G.A.柯亨为代表的思想家认为马克思思想中隐含着正义的理念。柯亨在《自由、正义与资本主义》中指出:“正义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中占据着核心的地位。马克思主义者做出的特殊判断表明了正义的存在,而且他们做出那些判断时所带有的强烈情感也表明了正义的存在。由于缺乏对自身本质的意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常常错误地描述了自身,而且马克思主义对正义观念的蔑视充分证明了这种自我理解的缺乏。”[注] G.A.柯亨:《马克思与诺齐克之间:G.A.柯亨文选》,44-4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在针对手机浏览器开发的过程中,凸显出一些问题,如采用不同方式接入网络的安全问题并未考虑,手机端浏览器对脚本支持(复杂数据格式验证)的不完善,各手机操作系统平台浏览器对页面的解析能力等还需要进一步测试。这些问题需要在以后的工作中去进一步的探索并完善。
艾伦·伍德将正义理解为一种“法权(judical)概念”或“法定(Legal)概念”,即从法权意义上审视法律、制度和权利等问题。在伍德看来,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源自他拒绝这种法权的社会概念,并且坚决反对将正义在意识形态上神圣化。究其原因,这种理论姿态取决于马克思对法权意义上的正义在社会生活中功能的理解,在马克思看来,作为法权概念的正义是基于某种特定生产方式而生成的次生的、依赖性的产物,不足以作为衡量社会的根本标准。国家在根本上受物质生产的决定和支配,与其相适应的正义观念作为一个与法和权利相关的“法权概念”属于上层建筑,其评价标准归根到底受到生产方式的支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家出资购买劳动力商品,如果劳动力商品得不到充分使用,工人没有进行无偿劳动,那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会存在。因此,既然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劳资关系来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劳资双方的交易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言是充分的、适合的,那么这种劳资关系就是正义的。在伍德看来,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的真正基础存在于他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起源、组织功能和未来命运的综合考察中。然而,这种考察方式和理论阐述并非从道德的维度上展开,马克思也从未试图在规范性的维度上对正义进行系统讨论,因此,马克思从未以正义的名义谴责资本主义。
在这一富有争议的理论阐释中,伍德将马克思主义从抽象思辨的、包含先验道德假设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中剥离出来,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以往一切旧哲学尤其是抽象的、思辨的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和超越。在这个意义上,伍德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出了系统辩护。但是,与此同时,他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惜彻底摒弃可能对此造成困扰的正义的道德立场,即彻底否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价值维度,将马克思主义仅仅视为一种基于经验和事实的实证科学,而非关于价值判断和评价的规范理论。究其实质,伍德的观点依然不能摆脱西方哲学长期形成的主体与客体、事实与价值、科学与人文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克服这一传统从而实现了哲学的革命。
自休谟以来的近代政治哲学通常依据道德来阐发正义,即正义意味着同情、关爱以及人道主义等;时至亚当·斯密,正义被理解为既是道德层面的,也是经济层面的,劳动是财富源泉的思想成为其正义观的基石;马克思则批判性地继承并超越了前人,认为正义不再是一个能够通过道德论证而予以确证的概念。经过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洗礼,马克思开始转向探索关切人的历史现实和感性的人的实践活动的历史唯物主义道路。
正义是历史的产物,也在历史中被塑造与规定。在马克思那里,正义这一价值范畴来源于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运动和社会实践。不同于传统西方哲学局限于政治生活内部的视角,仅仅围绕权利谈权利,围绕正义论正义,马克思坚持从社会历史的真实运动和客观进程出发,主张对正义和权利的理解和评价必须坚持历史标准。关于权利、分配的正义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制约,割裂人类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抛开人类社会的现实实践谈论正义,极易使正义沦为一种抽象的原则。
两组术前NIHS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14 d的NIHSS评分均较术前显著降低,但观察组比对照组改善更明显(P<0.05)。见表3。
针对水池水深1.0 m、2.0 m、2.5 m等运行工况,量测了4~5#、5~6#隔板之间的水池内表层流速分布。流速测量中对测点坐标的控制方法如下:以4#横向长隔板前端与池室左侧边墙的交点为0点坐标,向下游方向为Y轴正方向,垂直于边墙向右侧为X轴正方向。图4为根据试验绘制的水池表层流速矢量图和流速云图。
上海地方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走在全国前列,利用要素市场齐全的优势,上海坚持公众公司导向,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目前,整体和核心业务资产上市的国企已占上海竞争类国企总数的2/3。
二、历史发展运动中的正义向度
柯亨则是从“自我所有权”的规范性命题出发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非正当性。在回应罗伯特·诺齐克提出的理论难题“张伯伦论证”时,柯亨发现之所以自由至上主义理论能够对马克思主义造成深层次的挑战,恰恰在于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共享了“自我所有”这个前提。对马克思而言,“自我所有权”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是自身能力的正当所有者,这意味着一个人在如何运用自己的能力(如劳动能力)上具有至高无上的决定权,而不是在他人的命令下从事强制性的活动(如生产劳动)。“只有工人本人,而不是其他人,才有权利决定如何运用自己的劳动时间……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本家剥削了工人——就依靠着这样一个命题:人们是自己能力的正当所有者……那么,就无法避免对像自我所有原则这样的内容予以肯定。”[注] G.A.Cohen.“Marxism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or Why Nozick Exercises Some Marxists More Than He does Any Egalitarian Liberal”.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 Supplementary,16,pp.366-369.因此,当马克思主义者谴责资本家侵占或盗取工人的劳动时间时,这实质上是在强调劳动者对自身的劳动能力和如何支配劳动时间拥有完全的决定权。另一方面,资本家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迫使工人为其劳动并合法地占有工人创造出的剩余价值,因而是非正义的。柯亨从生产资料的自我所有原则向获取正义原则做历史追溯后指出,这种资本主义的占有并非天然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而是经历了从“无主”到“有主”的转变过程。在洛克式的所有权逻辑主导下,资本家将原先人们所共同享有权利的、公有的或无主的生产资料变为私人财产,将自身的劳动加之其上并留下“足够的、同样好的东西”给其他人时,实现了该占有的正当性。进而,资本主义对生产资料的获取为占有者带来了与此相关及由此生成的一切优势,“一个公正的占有者除了占有资源,无需对它作任何努力,就能把私有化所产生的生产提高的一切好处收入囊中”。[注] G.A.柯亨:《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96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这种所谓的正当性在为资本家带来累加优势的同时,却制度性地造成了劳动者最终无权获得“足够的、同样好的东西”的历史境遇。
因此,当马克思批判资本家对工人进行剥削时,是在双重意义上批判资本主义的非正义性:一方面是在谴责资本家按照洛克式的所有权逻辑获得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凭借此“先天”优势构建起对工人不公的资本主义生产,以资产阶级“获取正义”和“程序正义”取代了实质性的正义;另一方面是在批判资本家剥夺了工人的劳动时间和劳动能力,而这本应是工人正当拥有的力量,而资本家通过“交易正义”这一形式上的平等,实质上掩盖了工人的所有权被剥夺的事实。基于所有权的分析,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是非正义的这一观点便有了充分的支持性论据。应当肯定柯亨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辩护所做出的努力,其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正义学说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不得不强调的是,“自我所有权”同样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将马克思主义正义观建立在“自我所有权”基础上的做法,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在建构政治哲学时的差异化理论路径。对此,柯亨在后期的思想中不断呈现并展开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立场,即消除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所共享的自我所有原则。
恩格斯指出:“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4-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将工人的“活劳动”转化为“死劳动”,并将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与资本的增值紧密捆绑在一起。马克思在讨论“资本”时,始终要求追溯资本生成和增值的历史进程与运动方式,即资本的历史性生成;同时也要求将资本置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制度中加以认识,揭示具体物的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关系,即资本及其关系的运动。资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财富或者资产的概念,也并非仅仅作为物质实体被认知,而是具有价值增值的经济层面与制度构建的政治层面双重含义。一方面,资本在经济和生产上呈现出将追求财富积累和利润增长合理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其在制度层面将以财产为基础形成的所有权制度及其正义性合法化。在此,资本不再是关于财富、货币的静态的或是被动的概念,而成为一种主动性的语义构建与权力,形成对具体现实的抽象的统治力量。因此,马克思在发现了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和剩余价值的秘密基础上,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在遵循所谓“等价交换”的平等原则背后是抬高物的价值并贬低人的价值,在形式公平的背后是包含强制性因素的劳资矛盾,从而将资本主义自由、平等的虚假面目揭示出来。
其次,马克思持有面向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价值指向的正义立场。马克思认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人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社会历史是基于人的本质、立足于人类实践得以展开的历史,历史唯物主义通过揭示人类历史客观规律和社会发展趋势,指出人通过对历史规律的把握和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具有了由现实到理想、由实然到应然飞跃的历史可能性。马克思反对设定一种高悬的、永恒的价值,认为任何价值都只能在人的历史性活动中寻找意义、获得解释。资产阶级宣扬的自由与平等并以此为基础建构的永恒正义,无非是为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的产物,其抽象论证正义和权利的方式外在于历史的真实进程,不能真正推动历史的进步和人的发展。马克思在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基于人、面向人而展开的价值体系,指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内在于客观历史进程和人类社会发展趋势之中,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关系的价值诉求将会历史地得以实现。由此,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在人类社会发展趋势中实现了对“突然”与“应然”的统一,将作为客观趋势的“人的发展”与作为价值规范的“人的发展”辩证统一起来。
在马克思看来,历史表现为人的实践活动的具体展开,而人的最本质的实践活动是生产活动。人的生产总是需要借助一定的社会生产形式,并且要关注产品如何流通与分配,这就涉及人的义务与权利、贡献与收益、财富与分配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均是内置于生产方式本身而进行的讨论。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内讨论程序正义、交易正义或分配正义等问题,需要深入到生产关系的实质和生产的普遍规律中加以理解。我们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认同马克思拒斥法权意义上的正义阐释,而坚持一种立足于社会生产关系建构起来的实质正义。
因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既不是一些反对者所指责的那样是缺乏价值指向的“经济决定论”或“机械决定论”,也不是基于经验性研究而展开的实证科学,更不是以先验价值或道德假设作为判断标准的人本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超越了西方传统哲学价值规范与科学实证相互对立的“二元论”解释模式,基于人的生存境遇并始终面向人的真正解放,寻求对社会存在的内部矛盾和发展规律的更深层次的理解,在历史的延展中将价值与科学、应然与实然、理想与现实统一起来。因此,作为科学性与价值性辩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必然包含正义性维度。
三、社会生产领域中的正义向度
在饲养管理中,应按照猪的不同生长阶段,选择优质全价饲料,合理供应饲料喂量,给猪提供生长发育所必要的营养物质,确保蛋白质、能量、矿物质、维生素满足生猪生长、生产需要,严禁使用发霉、变质饲料和假冒、劣质、违禁兽药及添加剂,同时保证饮水质量安全。坚持每天及时清理猪舍卫生,保证猪舍干燥清洁,将粪便在指定地点堆积发酵或沼气处理,使病原菌没有滋生场所。控制好猪舍内小气候,如温度、湿度、密度、清洁度,并合理分群,搞好调教管理,以提高生猪福利待遇,为猪的生产和生长创造最佳环境。
艾伦·伍德与柯亨对马克思主义与正义的双重回应,共同塑造了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当代哲学话语,这一学理分歧在日后引发了更为持久深入的马克思主义与正义之争。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究竟持有何种正义立场,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回应上述争议。
首先,马克思反对抽象的、形式化的正义阐释,主张将正义纳入历史的范畴中加以考察。如果说马克思的确在文本中直接抨击过“正义”,那么重点在于马克思是在何种意义上理解正义。马克思并没有从抽象价值层面抑或立足于道德应然的立场谈论正义,因为离开物质生活关系和具体历史而进行的讨论脱离了社会现实,只会形成抽象的形式正义。凯·尼尔森曾指出:“卡尔·马克思——和绝大多数追随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一切道德说教。马克思主义者们站在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对立面来寻求将社会主义置于一个科学的立足点上,强调对科学但却不道德的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重要性。”[注] 凯·尼尔森:《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观念:道德、意识形态与历史唯物主义》,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马克思认为,对正义的理解不应该外在于人类社会形态,而是内在于社会形态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中。在这里,显然马克思反对形式化的、脱离社会历史的抽象正义观,正义只能被理解为历史的和具体的。
由于正义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关系中具有不同的实现程度和评价标准,所以评价正义应当立足于历史性的社会生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说什么天然正义,这是毫无意义的。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3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这些语义上的直白表达也被伍德等学者作为直接依据用于阐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正义的接纳。其实并非如此,正义和权利总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应该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人类不可能超出历史条件提出特定的任务。这就是为何马克思所提出的“与生产方式相一致”体现的阶段性正义,如果将古代奴隶社会视为正义的原则置于资本主义社会,就会变为非正义的。马克思并不是要承认资本主义生产的正义性,这恰恰是被批驳的对象,他要强调的实质上是社会生产及其正义的历史性。
在1923年南华足球队访问澳洲时,当地报纸曾评论说:“这17名球员所组成的球队,不只是有使者的责任,而是代表世界上最古老的中国与地球上最新领土的澳洲之间,建立起来的深厚的友谊和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16]”所以无论是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中美乒乓外交,还是20世纪末发生在美国与古巴之间的棒球交往,都说明了现代社会条件下体育在改善国家关系和推动国际进步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和巨大影响力,因此应注意发挥和加强体育在对外关系上的作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主动进行的体育对外交往活动,就是在用特殊的肢体语言向世界宣讲中国故事。
在马克思看来,“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极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观念上的权利来满足,绝大部分却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实现”。[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正是在此意义上,生产正义一方面要求保障工人获得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并公平地获得自我实现手段的权利;另一方面要求保障工人公平地参与企业生产经营与社会决策的权利。然而,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决定了它无法在社会生产领域实现正义,其财富分配无法保障多数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而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社会正义,是一种贯穿生产领域和分配领域的根本性变革,只有生产资料真正归社会共同所有,而非资产阶级等少数人所有,才能真正建立基于实质正义原则的社会,真正保障大多数人能够享有实质性的公平正义和权利。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具有立足于社会生产的正义向度,而非抽象的、空洞的、形式化的资产阶级法权教条。
四、社会结构和制度变革的正义向度
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包含了对人的权利和社会正义制度的实质性考察。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关于权利的合法规定与权利的实际享有之间存在巨大的“裂痕”。虽然资本主义法律在形式上确立了所有人自由、平等的权利原则,但实际上,不同社会阶层在实际享有这些权利时存在机会、能力、程度等方面的不平等。18世纪至19世纪的资本主义历史表明,只有资产阶级在事实上享有这些权利,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事实性压迫及由此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异化,则表明生产资料私有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无法解决的弊端,即日益扩大的社会生产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根本矛盾。资产阶级虽然宣称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产阶级权利的永恒性和普遍性,但这种社会结构和制度使得无产阶级根本没有条件和能力享有这些权利,因而资产阶级所谓的正义对广大无产阶级来说只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
细读马克思的文本,可以发现马克思其实并不反对人的权利主张,他真正反对的是资产阶级辩护士“关于‘正义’的空话”[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3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以及论证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合法化、永恒化的方式。资产阶级曾经在历史上起过革命性的作用,它斩断了同封建特权的一切联系,并且以自由、平等为武器,旨在消灭一切旧的特权阶级。然而究其实质,资产阶级无法摆脱维护自身阶级利益的封闭立场,因而无法代表人类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和正义之道。资产阶级欲盖弥彰地辩解,“在阶级社会中一切阶级都可以享有这些权利”,但事实上只有在无阶级的社会中所有人才能享有这些权利。[注] R.G.佩弗:《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348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因为无产阶级没有私有财产需要保护,他们在解放自身的同时也实现了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摧毁了为少数人代言的那套保护私有财产的资本主义制度。因而,无产阶级运动的任务不仅在于消灭一切“阶级特权”,关键在于“消灭阶级差别本身”[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在此意义上,无产阶级的制度变革运动和要求更接近一种实质性的公平与正义。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因此,马克思极力反对并试图打碎资产阶级费尽心思所营造的关于权利和正义的意识形态幻象,使无产阶级尽早觉悟,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有清醒认识并联合起来进行抗争。
马克思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关于权利和正义的抽象说教,本身并不是指向正义概念本身,而是将斗争的矛头彻底指向私有财产制度以及由此造成的结构性社会压迫以及阶级特权,即导致权利、财富、机会、收入等方面的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正义和法律所规定的权利、自由等价值,本质上是相应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所决定的次生规范。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彻底变革导致社会不公平的根源,即彻底变革私有财产制,才能实现真正符合整个人类根本利益和价值诉求的正义的社会。
通过上述论述和分析,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包含丰富的正义思想,其理论向度在历史发展运动、社会生产领域、社会结构和制度变革中不断得以展开。对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讨论应当深入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语境和历史进程中去,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在何种意义上是可能的,以及依据何种范式将其正义理论充实到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马克思强调在分析历史发展客观进程的基础上寻求社会权利与正义、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以及人类的最终解放。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在历史生成之外构建绝对真理和规范性原则,而是真正超越了传统西方哲学植根于科学与价值二元张力的解释模式,从本质上寻求对社会存在的内部矛盾和客观规律的更深层次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体现了科学性和价值性的辩证统一。其中,价值性的维度突出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理想和利益诉求,历史性的维度强调了历史进程对正义的阶级性、时代性、区域性的客观约束,两个维度辩证地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对于集现实性与理想性、科学性和价值性于一体的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应该成为我们重视并付诸努力的时代课题。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Justice Theory of Marxism
ZHANG Xiaome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whether there is justice theory of Marxism and in what sense constitutes its rationality has always been a controversial academic debate.While Allen Wood re-examines Marx’s justice proposition in the judicial sense, Cohen defends Marx’s justice position from the angle of self-ownership, both of whom reveal that Marxist justice theory surpasses the 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 paradigm of modern west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which emphasizes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value.Justice Theory of Marxism is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science and value, eliminating the theoretical tension between them, and striving to seek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and historical laws of society, rather than building absolute truth and normative principles outside the generation of history.To grasp its value orientation and internal theoretical dimension has become the theme of Marxist justice research.Specifically, Marxist justice theory includes three dimensions: justice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movement, justice in the field of social production, and justice in the revolu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
Key words : justic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roduction justice; institutional justice
*本文为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中的‘马克思与青年’专题研究”(19GJJB03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晓萌: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872)
(责任编辑 李 理)
标签:正义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生产正义论文; 制度正义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