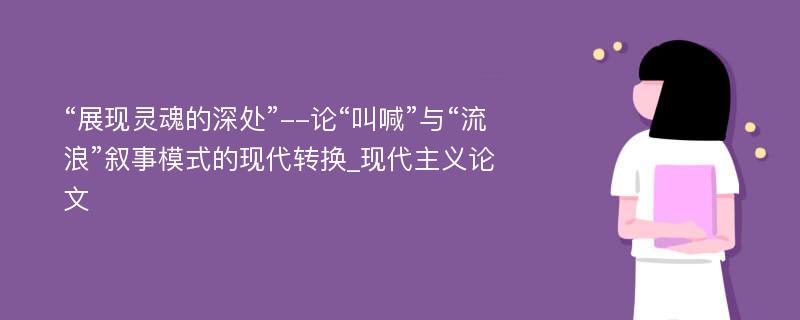
“显示灵魂的深者”——试论《呐喊》、《彷徨》叙事方式的现代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彷徨论文,试论论文,灵魂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小说的现代性是基于传统的养育和对传统的反叛的。这一反叛因于20世纪人对自身和世界的存在的意识的复杂性。小说艺术面对这一存在的复杂性的呈现,也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反应,这一反应至少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一、叙事方式的转换:小说观念与技巧的革新;二、对人的灵魂本体的深广开掘,无边拓进:现代小说的存在深度;三、叙事风格的多重变幻(反讽或神话、神学叙事的风格等):在叙事方式与复杂的存在之间对小说形式整一性的现代寻求。本文首先从第一个方面来考察在20世纪的小说视野中,中国现代小说的杰出代表——《呐喊》、《彷徨》的现代性。
一、 由“讲述”到“显示”:现代小说叙事方式的转换倾向
在生活中,我们除了通过内心信号了解自己外很难了解其他人,而且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自己的了解也是相当偏颇的。然而文学,却以其奇特的方式直接地和专断地告诉我们各种思想动机,而不是被迫依赖于那些我们对自己生活中无法回避的人们所作的可疑的推论。每当作家深入情节表面底下,去求得确实可信的人物思想情感画面,把所谓真实生活中没人能知道的东西讲述给我们时,人为性就会清楚地出现。布斯(注:布斯(Wayne C.Booth,1912—),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 当代颇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其《小说修辞学》(1961)为西方现代小说理论名著,被称为“20世纪小说美学的里程碑”。)将小说这一“奇特的方式”称为早期故事中专断的“讲述”。(注:参阅华明等译《小说修辞学》第1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早期小说的这种专断的讲述,在中国传统小说和西方19世纪小说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古典小说中,叙事基本上由讲故事的人逐事铺陈,独自维护整个叙事的情节完整和叙事的理念或情感核心,读者只是作舒适平易的领受。在西方几乎也同样如此,在从奥斯汀、狄更斯、萨克雷到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经典中,我们都能看到:作者与叙述者相隔不远,他们都有着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对于任何事件、场景都有着随意进入的特权,可以出入任何人物的内心,经常以充满感情的语句向读者作直接的情感沟通和道德吁求。“讲述”的方式几乎成了小说历史中的一种叙事成规。
然而,小说本体的存在,事实上是一种反对话语。在与社会和法定文化的关系中,小说一直取反对立场。对于公认的价值体系与认识方式,小说由于其向精神深处的无限深入、拓展与追求,无疑是揭开蒙蔽的很好的彰显方式。通过描写那些在公认的价值体系中没有一席之地的人与环境,小说使这一价值体系受到潜在怀疑。通过肯定自己“不在文学领域之内,而在非文学话语的‘现实’世界之中的地位”——小说的“现实主义”由此而来——小说揭示了无情的事实与传统的认识方式之间的差距。(注:[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4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讲述”的叙事方式一旦由19世纪的经典成为一种成规,在小说的历程中,在小说的真实深处,必然要遭到另一种话语的反对。
关于这股反对话语我们比较熟悉的言词有“作者的退隐”、“隐含的叙述者”、“不可靠的叙述者”等。它的事实存在是,在众多现代作家的作品里面,作者自我隐退,放弃了直接介入的特权,退到了小说舞台的侧翼,让他的人物在文本中去决定自己的命运。从福楼拜以来,许多作家和批评家都确信,“客观的”或“非人格化的”或“戏剧式的”叙述方式自然要高于任何允许作家或他的可靠叙述人直接出现的方法。小说叙事方式的这一现代转向及其各种复杂问题,已被归纳为艺术的“显示”和非艺术的“讲述”的区别。(注:《小说修辞学》,10页。)讲述一个故事的老套数应抛进历史的垃圾箱,诚如斯地泽尔所说:“在世纪之交,普鲁斯特、乔伊斯的小说之后,出现了新时代的黎明。”(注:《小说修辞学》,2页。) 而约瑟夫·沃伦比奇干脆说:“我喜欢把‘讲述’的小说家(像萨克雷、巴尔扎克那样)和那些‘显示’的小说家(像亨利·詹姆斯那样)区别开来。”(注:《小说修辞学》,1页。) 将“讲述”与“显示”视作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泾渭分明的标志,20世纪小说理论家们如是宣布尽管显得匆忙甚至有些偏颇,但这一事实的潜在真相却是无可否认的,——现代小说出现了悖离作者在作品中直接控制读者反应的历史转变,越来越普遍地采用了显示即自然而然地客观地展现人物活动和事件经过。(注:《小说修辞学》,10、3页。)这一“自然而然地客观地”可用法国新小说派的罗伯格里耶的一段话来补充:
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是谁在描述这客观世界?这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叙述者又是谁?他同时出现在一切地方,同时看到事物的正反两面,同时掌握着人的面部表情和他内心意识的变化,他既了解一切事件的现在,又知道过去和未来。这只能是上帝。
只有上帝可以自认为是客观的。至于在我们的作品中,相反,只是“一个人”,是这个人在看、在感觉、在想象,而且是一个置身于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之中的人,他受着感情欲望支配,一个和你们、和我一样的人。书本只是在叙述他的有限的、不确定的经验。这儿,就是这样一位当代的人在作自己的叙述者。(注:崔道怡、朱伟等编:《“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下册),522~523页,工人出版社,1987。)
“一位当代的人在作自己的叙述者”,关于这一叙事方式的历史转变的心理与时代背景我只能简而言之。19世纪对于欧洲那些小说家来说,无疑是个自信的时代,小说家们自信人与人之间具有一种稳固的关系,享有一个共同的现实,所以他们能够从容不迫地坚持用一种假定的文学形式进行抒情或道德言说。然而20世纪初,随着弗雷泽、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和荣格这些令人悲喜交加的伟大人物的出现,人在对宗教原始根源、生命本能、无意识的力量的探索中对自身的理解开始发生变化,19世纪那种人与人之间的稳固关系、共有现实开始遭到怀疑,与之相对的是个人经验、现实的无限复杂性凸现出来。所以彼得·福克纳说:“现代主义是艺术摆脱19世纪诸种假定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注:彼得·福克纳:《现代主义》,付礼军译,5页,昆仑出版社,1993。)、“关于复杂性的意识将成为现代主义作家的基本认识”(注:彼得·福克纳:《现代主义》,付礼军译,26页,昆仑出版社,1993。)。
面对日益凸现在人类面前的无限复杂的现实,20世纪这些现代小说家们对现实事件的随意偶然性的依赖远较以前的现实主义作品为盛,以自我的专断的“讲述”干预现实与读者的做法开始大大收敛,对于现实世界呈现给他们的材料他们也不做多少理性主义的处理,也并不打算给那些刺激内心的外在事件的残酷延伸以一个完满的结局。(注:彼得·福克纳:《现代主义》,付礼军译,29~29页,昆仑出版社,1993。)
二、鲁迅小说叙事中的中西遇合
如果说欧洲小说的艺术形式(形式即完成了的内容)的革新来自于詹姆斯、沃尔夫、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罗伯-格里耶、萨洛特这些20世纪的小说天才,那么在东方,中国的传统小说真正的反对话语则首先来自于几乎与沃尔夫、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卡夫卡同时的鲁迅。最起码有两个方面他们对现代小说历程的贡献是相似的:一、各自以其独特的风格带来了小说的叙事方式的现代转向。基本上倾向于与早期小说专断的“讲述”相区别的“显示”,显示主观心灵或一个人心灵中的事物与时间流程;二、小说叙事的“显示”倾向反映了这些中西方的小说天才在20世纪复杂的存在境遇里“人”的遇合。这个时代的伟大作家都意识到了现实社会的复杂性,价值的混乱,困境的逼压,并在他们的作品中具体展现了对生活的复杂、深切而广阔的理解,1965年罗伯-格里耶那段“一位当代的人在作自己的叙述者”与鲁迅1925年的这番话是有相通之处的,且后者几乎是前者的前因:
我是否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无数个“讲述”的声音被镌刻为丰厚的“显示”。20世纪的小说读者将要作怎样的艰难的领受?
三、作为“显示”的文本(注:文本——作家笔下的作品,在未经读者接受之前,只是一种有潜在意义的作品(文本),它还不是现实的作品,文本只有经过读者的接受,才能变成有生命活力的现实的作品(本文),《狂人日记》等鲁迅小说在“文本”状态中是一种较为客观的“显示”,而在“本文”状态中却有着丰厚的“讲述”,此“讲述”正是我们所要聆听的。)——《狂人日记》
我们一直很奇怪为何在一个时代转折关头,作为“以小说参与历史发展的宣言”而存在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篇之作(注: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15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狂人日记》有着它那非常奇特的叙事方式,它为何没有世纪之初启蒙主义者那种悲情激昂、愤激民生、慷慨陈词式的呼吁诉求,几千年来在故事中间游走的那个万能叙述者为何几乎消失不见,仅冷漠、戏谑地闪现在文章开头的短短题记里?这个人似乎只是随意发现另一个人的日记,翻阅之后又随意地拿给我们看,至于他自己,对日记则连书名也懒得去改。一切的情形是这样的:叙述者突然进入了一个人的内心(日记应视为人的心灵的文字记录),然后默默地一页一页地将这个人的内心显示给读者,似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一切就是那个叙述者自己的声音。这难道就是先驱者的宣言?它为何外表如此沉默?
如果仅仅将《狂人日记》视作一篇揭露和控诉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的战斗檄文和宣言书的话,我们就无法圆释鲁迅为何选择这样一个叙事方式倾向于“显示”的文本。我以为,这一文本的成因与鲁迅对当时现实的无限复杂的认识及对自身灵魂的认识有关。
《狂人日记》的明显的和最重要的主题意识当然是对五千年“吃人”的封建主义的批判和要冲破这间“铁屋子”的呐喊和抗争。然而,作者的这一核心声音却同时遭到另一些声音的逆向牵引。其一就是,启蒙者的声音与蒙昧的民众之间有没有一个19世纪小说家之于读者的那种自信的假定的共同经验、共享现实的基本听力场?如果缺乏这一现实,启蒙者的言说在民众没有听觉的境况里岂不就是可笑?奥斯汀、司各特、萨克雷这些维多利亚小说家信心十足地对读者直接地抒情、呐喊“咱们中间有谁在这个世界上感到幸福呢?咱们又有谁实现了愿望?”这一习惯,对于现代读者却是矫揉造作得令人难受!(注:彼得·福克纳:《现代主义》,付礼军译,6~7页,昆仑出版社,1993。)这一现实之于萨克雷这样处心积虑于心灵呼喊的小说家是多么尴尬而残酷!20世纪初的鲁迅有没有遭遇这一与接受者缺乏共同现实的空空呐喊的尴尬与残酷?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回的苦楚,你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呐喊·自序》)
在这里的心理与语气里,鲁迅对民众的不信任是明显的,他所勉强信任的也只是少数,“不幸的少数者”;他所说的“希望”似乎与己无关,是身外之物;他之所以大声呐喊、写文章似乎也只是经不起钱玄同的劝告,姑且做一做而已!“我知道自己实在不是作家,现在的乱嚷,是想闹出几个新的作家来,——我想中国总该有天才,被社会挤到在底下,——破坏中国的寂寞。”(1919年4月16日给傅斯年的信)
探究鲁迅当年复杂的思想状况,我们就会知道:此时鲁迅和在东京策划《新生》的时候已大不相同,也和绍兴光复后率领学生上街游行的时候迥然相异。当年那种真理在手、理想必胜的自信,慷慨激昂志在天下“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雄心已为十年诸多失败感的人生所淹没,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面前,自信的言说与行为让位于铁屋子“万难破毁”的绝望和对于这绝望不甘沉沦的抗争。王晓明先生分析鲁迅写“呐喊”小说时的心理障碍时这样说:“一方面,他必须加入陈独秀们的思路合唱,必须装得和他们一样满怀信心,以为用这些外来的思想就一定能改造中国;可另一方面,他心里又并没有这样的信心,他相信的东西甚至和它相反。”(注: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51~5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他早已过了信仰纯一的年龄,思想上只会越来越复杂,现在却在扮演一个信仰坚定的角色,除了戴面具,他还有什么别的法子?”(注: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5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王晓明先生以“戴着面具的呐喊”为题来叙述鲁迅刚刚开始的小说人生,未免让很多人一时难以接受,但这多少反映了一个事实:无限复杂的现实给鲁迅的思想带来了某种愈来愈复杂的意识,在这样的时刻,若要鲁迅对于蒙昧的民众——读者作直接了当的道德陈述已是不可能,——真理已在心头摇摇欲坠,还凭什么作早期故事中那专断的讲述?让小说干脆违心地成为革命文艺的赤裸裸的宣传也一样不可能,文艺“我以为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挂招牌”,“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而已集·文艺与革命》)。必须找到一种叙事方式,既能承载反封建的呐喊之音,又能有力地排空那不断侵蚀、干扰呐喊之音的虚无、绝望的心灵秘响——简洁明了地让一个叙述者翻阅那个“狂人”的日记显示这个人的内心无疑是一种很好的方式。那两册日记事实上既是独自发声呐喊、反抗的他物,又涵盖了鲁迅那不愿过多袒露的真实心灵,“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详尽,大约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坟·写在<坟>后面》)。
更为严重的是,抑在鲁迅呐喊之喉的还不止是他对于现实的沉重的复杂性意识,在“显示”的文本里明亮的抗争呼声中,还有着无法藏匿的鲁迅自身魂灵的阴影:
我未必无意之中,也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
……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一个为民生奋力呐喊的启蒙先驱,在着力揭露和批判黑暗事物的罪恶这时,却敏锐地感到自己血液中的不纯不洁!我未必就不是吃人者!“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但我现在发见了,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而已集·答有恒先生》)吃人与救人,竟同时生于一个人的内心,两个如此背谬的矛盾形式能在哪一个真理上统一起来?莫非我们真的是亚当的子孙,“造成这惩罚的不是我自己,而是‘盘据在我身内的罪’?”
四、“显示”文本的一种意义
关于鲁迅在这里的负罪与忏悔意识,已有论者作过深刻的阐述。吴俊先生在其《鲁迅个性心理研究》一书中一再强调:《狂人日记》是一部“原罪的忏悔和绝望”之作,是作者对于自身历史和自身命运的自觉诘难和深刻绝望。(注:吴俊:《鲁迅个性心理研究》,22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在这里,我们所要惊讶的是,在我们面前翻开的两册日记残篇13则,事实上竟有如此复杂的未翻开的潜在话语(在鲁迅研究的历程中,将会有着更加丰富的心灵的探索):悲怆的呐喊与虚无的心灵,要推翻历史而自己却在历史之中,拯救民众的命运却发现自己也在沉沦之中……众音交织竟成等待爆发的沉默。由众多复杂的意识(现实的与自身的)所孕成的真实讲述成为文本的暗流,在文字在阅读层面之下汹涌回流。在“显示”的文本内,事实上是现代小说中人真实灵魂的“潜流与漩涡”(王晓明语)。以一个“显示”的文本,客观地自然而然地陈述“一个人”在特定时间里的所看、所感、所想象,这一叙事方式,显然要较那种专断地全知全能地讲述真实、可信,同时这一叙事方式也便于现代人对于自身困境的某种言说适当地隐藏。而对于那些同样能感受到人类困境的杰出心灵来说,通过那些意义丰厚的言(言词)、象(意象、语境)、议(叙述者心情的不自觉流露),这种隐藏事实上是一种彰显。正是在这里,“显示”的文本之于现代小说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凸现出来。
自从人类的共同经验、共享一个现实的神话被打破以来,人们感到,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再也不适宜表达具有极大的复杂性的个人经验或人类经验。于是,现代主义在各类艺术中的共同特征就是在表达方法上进行的种种试验。人们认为传统艺术对经验作了过于简单的描述。在现代文学中,传统的叙述结构已经衰落,取而代之的将是所谓的“空间形式”(注:彼得·福克纳:《现代主义》,付礼军译,30页,昆仑出版社,1993。),即一部作品的整体统一性表现在“内心关联的完整图式”或“内在关联的原则”之中。艾略特的《荒原》、庞德的《诗章》、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普鲁斯特的作品都给我们做了很好的典范:读者不是被要求去追寻一个故事,而是被要求去发现一个人性、存在中的“图式”(Pattern)。 但人们仍普遍感到:现代主义作品由于努力表达一种更复杂的关于现实的感受而未能获得整体的和谐。在现代主义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中,这个问题被不断地也确实非常恰当地提出来。毕竟,“时代之缺乏统一性……决非是艺术应该……普遍缺乏统一性的理由”(注:彼得·福克纳:《现代主义》,付礼军译,30~31页,昆仑出版社,1993。)。这就意味着,在现代小说中,某种可能使用的能获得整体和谐而又不同于传统叙述方法的方法亟需我们去探寻。这样,“显示”的文本由于其承载的多种复杂意识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使现代小说达到整体和谐的重要意义。另外,在“显示”的文本中,读者通过用心“观看”,也许会发现某种人性、存在的图式,将获得一种生存的澄明。《狂人日记》中就有着一种反抗者尴尬而绝望的心理图式:反抗者同时又是受罚者。施罚的还不仅是外在力量,更是来自自身血液中!“狂人”的结局是“赴某地候补矣”,抗争的喧哗与骚动最终归为“狂人”远去的音尘。反抗与受罚是鲁迅小说中的一个普遍的“图式”,在后来的论述中,我们要详说。
五、《孔乙己》、 《药》的叙事方式及“显示”文本的三个视角
《呐喊》中的第二篇《孔乙己》无疑也是中国现代短篇小说中的精品。这个短篇,结构是精致而完美的。《狂人日记》所显示的是一个人的内心势态,叙述者来到人物狂人(“我”)的内心之中。而《孔乙己》的叙述者则站到了人物的身外,他仅仅是一个酒店里跑来跑去的小伙计,一切人世悲欢在酒店内外上演,这个小伙计似乎只是一个缺乏能力的世相“显示”者,他也只是站在柜台边上不经意地窥到了一个人物的完整命运,他对这个人的结局的表述也显得含糊不清。与《狂人日记》一样,《孔乙己》除了一个批判“吃人”的封建礼教的主题之外,另一个潜在的主题也隐约可见,孔乙己并非一开始就是个灵魂萎顿借酒聊生的儒生,他也曾是个反抗者!是个自命清高、孤傲俗世之人。他身材高大,总要穿上那身长衫,品行很好(酒钱从不拖欠)。关键的是,他简直有点恃才放旷:他替人家抄书以餬口,这是谋生的要事,但竟然不到几日,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稍有理智的人恐怕不会这样。他的“坏脾气”恐怕主要不是“好喝懒做”,而是骨子里对丁举人之流的反抗情绪。在一个民不聊生的年代里,一个穷人想到偷书多少是件高尚的事:对坚持不吐俗语的孔乙己,他偷书恐怕不是为了换酒喝。在《孔乙己》中,仍有这样一个反抗与受罚的沉重主题,但奇怪的是,这个小伙计如此平静,几乎很少有同情的或悲悯的判断——即使在孔乙己这个昔日高大的书生最后几乎以双手爬在地上行走的结局面前。几乎一切都是显示没有作者明确判定、抒情的讲述。这个小伙计所表现出的“中立性”、“公正性”甚至“冷漠性”是令人惊讶的,他仅仅充当了一个旁观者、一个叙述代言人,他是整个人物命运的戏剧化的叙述者,他站在舞台的边缘,努力控制着巨大波澜的心控制着他那可能悲凉愤激的判断,正是通过控制叙述者的内心观察、道德判断,《孔乙己》作为一个“显示”的文本,却讲述出鲁迅深沉而复杂的时代悲音。
鲁迅小说中的所谓“讲述”,事实上是寄托在小说中那个叙述者、隐含作者身上。在《狂人日记》中,这个隐含作者呆在一个人的心里。在《孔乙己》中,这个隐含作者则走出了人物内心,站在故事的边缘(仍在故事之中)。而在第三篇《药》中,叙述者则彻底来到了故事之外,但他不是像乔伊斯所说的“在小说世界之外修剪指甲的神”,而是在那个“乌口街口”的乌蓝的夜空中的显示世态者,缓缓地呈现着人物、事物的客观流程,人物的思想动态、面目神情也只是叙述者“一个人”的可能推断。可以说《药》仍然是以“显示”倾向为特征的小说文本。
六、“显示”的深处乃现代灵魂的潜在讲述
叙事方式由传统的“讲述”向“显示”的转换,是《呐喊》、《彷徨》作为中国现代小说之代表,具有在世界文学视野里同步的现代性的一个方面。《呐喊》的头三篇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经典,不仅有它们思想、精神意义上的原因,还有叙事方式上的有力辅佐。更重要的是,这三篇里叙述者三种不同的“显示”视角,几乎可延伸至整个《呐喊》、《彷徨》。即便是鲁迅自己,对它们也是很满意的,“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名作《伤逝》副题是“涓生的手记”,是直接显示一个人的心灵。《头发的故事》通篇是N君的喋喋不休。 它们类似《狂人日记》。名作《在酒楼上》、《孤独者》则是叙述者“我”将那些孤独、失败的心灵主体拉近“我”的面前直接显示命运与心声(由心灵主体展示其命运与内心),它们与《故乡》等叙述者居于故事之中的篇目可以类似于《孔乙己》。而《阿Q 正传》这样的叙述者流离在外的小说则类似于《药》,它们的叙事方式显得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但倾向于“显示”。而在那些文本的缝隙中,在作者心情不堪抑压的地方,讲述的声音仍在汩汩外溢。——“显示”的文本的现代性不是现代灵魂的声音、形象的消失,而是更深更复杂的潜在。我们所更要做的是:潜入“显示”的层面,让那深处的“讲述”之音再度浮出。
(注:“以完全的写实主义在人中间发见人。……我但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即我是将人的灵魂的深,显示于人的。”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则手记。鲁迅曾盛赞他说:“显示灵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作心理学家;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作者……灵魂的深处并不平安,敢于正视的本就不多,更何况写出?因此有些柔软无力的读者,便往往将他只看作‘残酷的天才’……在甚深的灵魂中,无所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但将这灵魂显示于人的,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集外集·〈穷人〉小引》)“显示灵魂的深者”,细读鲁迅及鲁迅小说,亦如是。)
标签:现代主义论文; 狂人日记论文; 鲁迅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彷徨论文; 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现代小说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读书论文; 孔乙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