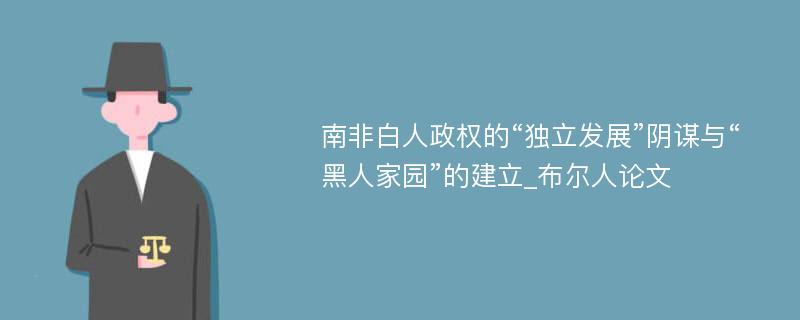
南非白人政权的“分别发展”图谋和“黑人家园”的设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非论文,图谋论文,白人论文,黑人论文,政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47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8)06-0061-09
20世纪的到来不仅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新世纪的开始,也标志着南非白人剥夺黑人土地的历史从两个半世纪的“豪夺”跨入了“巧取”阶段。如果说南非联邦的成立实现了“合”——两个白人民族之间的联合,那么它同时也开始了“分”——白人民族与广大黑人、有色人和亚洲人的“分离发展”或叫做“分别发展”。此后,南非几乎就是沿着这条分别发展的道路走完了整个20世纪的历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历史发展中,掠夺者都认为需要通过他们自己硬性规定的法律,来赋予他们凭借暴力得到的原始权利以某种社会稳定性。”[1](p.451)1910年南非联邦成立后,即着手制定“分别发展”的计划,从1913年的“土著土地法”,到50年代的“班图斯坦”政策,到60年代正式建立“黑人家园”,种族主义政权一步一步地将黑人“逐出南非”,将自己两个半世纪以来的掠夺成果进一步合法化和永久化。
一、“分别发展”的动因
阿非利卡人所以选择“分别发展”的道路,是因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南非的经济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矿业革命、英布战争和南非联邦的成立彻底改变了南非历史的发展方向。
金刚石和黄金从总体上改变了南非的经济结构。首先,随着布尔人在日益加强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不由自主地转向工矿业和服务业,他们也开始像英国人那样,从竭泽而渔式的、无序的、直接的、赤裸裸的暴力掠夺南非人的土地、天然资源和农牧产品为主,改为在此基础上借助司法和行政手段有序地掠夺非洲人的劳动力,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其次,黑人民族的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同样受到新兴的工矿业的冲击,尽管被剥夺了大部分生活资源,但他们凭借着勤劳和智慧,对市场经济的反应比一些布尔人还快,在英布战争前,黑人的商品经济已足以与布尔人相竞争,尽管还受到诸多限制。结果阿非利卡人嫉恨而又惊恐地发现似乎在一夜之间南非白色的地图上出现了许多非洲人自营农场的“黑点”。这意味着他们“在战场上得到的成果有可能在市场上丢掉”。[2](p.127)他们要竭尽全力保住已经到手的不义果实。
历时三年的英布战争对此后阿非利卡人的掠夺方式也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英布双方为这场白人之间自相残杀的战争都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①尤其是布尔人,但他们失败的结果却是获得了整个南非。战争的结束标志着两个白人民族不再为争夺南非的土地资源而厮杀,因为在此之前,阿非利卡人只拥有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的政权,而现在他们则拥有了全部南非的土地支配权。促使这场战争以如此戏剧性收场的直接因素是双方都无力再打下去,而最深层的原因却是因为两败俱伤的结局更突显了黑人人口在数量上的优势,特别是布尔人,更感到了陷入黑色的汪洋大海的危险。长期的野蛮征服和屠杀,并没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南非的人口对比。②正如他们担心的那样,一些非洲人利用两个白人民族自相残杀之机,夺回了几十年来被布尔人强占的土地,另有一些非洲人拒绝为布尔人地主服役。
南非联邦的成立是南非历史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南非联邦实质上是两派欧洲人为了更加牢靠地剥削非洲人民而成立的联盟”。[3]尽管对黑人人口数字怀着莫名的恐惧,但如今阿非利卡人不必再担心虽不属于同一民族但却属于同一肤色(种族)的英国人的压迫,他们完全可以放手地全力对付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黑人民族。既然整个南非都已归白人国家所有,而且国家的任何资源都可以任由统治者支配,像以前从开普出发一路抢劫剿杀土著民族直到林波波河的做法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不符合新的历史条件下白人的根本利益。正如有的学者所形象地指出的那样:尽管阿非利卡人的农牧业在经济中仍占有一定的比重,但对南非这个“黄金之国”来说,它的真正财富已经不是“黄色的,而是黑色的”。[4](p.28)因此,南非联邦成立后,布尔人用以掠夺非洲人的武器,不再是他们传统的牛车和枪炮,而是国家机构的强制力,是更系统、更广泛地“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4](p.28)采取法律和行政手段,更加残酷和有效地奴役和掠夺南非全体黑人。
一方面是贫穷的阿非利卡人流落街头,无所事事;另一方面,在经济结构变迁和阶级分化过程中富裕起来的阿非利卡人在进行资本主义农场经营时又严重缺乏劳动力,尤其是在英布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期;主要由英裔和外国资本家经营的矿场更因在英布战争期间黑人劳动力大量逃走而产量剧减,而恢复和扩大金矿生产的关键就是要有足够的劳动力。尽管原本铁板一块的阿非利卡人之间也出现了分化,因为英布战争而使有些人无家可归,一些人成为“拜旺纳”(bywoner),还有一些人成为“白旺纳”(bewoner),③更有高达20-30万的“贫穷白人”流落街头,但由于背负着“肤色优越”的十字架,他们显然不可能成为可靠的劳动力源泉,像正常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经历过的那样。因此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阿非利卡人农场主和以英裔白人为主的矿业资本家在硝烟刚刚散尽的统一的南非大地上又展开了对黑人劳动力的激烈争夺。尽管保留地的土地数量有限,人均不足3摩尔根,④大部分黑人青壮年男子需要外出做工才能勉强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在客观上造成了南非黑人无产阶级化的部分现实和广阔前景,但传统的土地公有制和牢固的血缘纽带仍然约束着村社内部的贫富分化和土地兼并行为,遏制了外出的黑人劳工与土地彻底分离的过程。特别是在英布战争后,劳动力供应的趋势对白人更加不利。
从黑人情况看,一方面,一些黑人凭借良好的悟性和勤奋劳动,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财富,然后便开始购买土地,特别是在德拉肯斯堡山麓和德兰士瓦西部地区,黑人纷纷购买布尔人在英布战争中丢弃的地产,独立进行商业化经营。南非土著事务委员会在1903年提出的一份报告中说,“土著开始购买约翰内斯堡附近的土地,以生产供应兰德矿区的食物”。[5](p.890)在1913年土著土地法颁布以前,非洲人以集体或个人名义先后在保留地以外购置了100多万摩尔根(约合100万公顷)的土地。1904年,德兰士瓦大约有13万黑人耕种的是自己的土地,1912年这样的土地共有112.5万英亩,[6](pp.127-129)约有12.3万名黑人住在私有土地上。[7](p.39)在1913年前,散布在欧洲人土地上的“黑点”已达114个。不知不觉之中,一个不依赖白人农场和矿山而独立经营的、比较稳定的非洲自耕农阶层,悄然出现在南非土地上,其中有些人正在朝着资本主义富农的方向发展,并很快在经营水平上超过了那些“高贵的”穷困潦倒的白人。另一方面,大批缺乏可耕地的黑人农牧民移居到白人农场主的地产上,成为“垦户”或分成制“拜旺纳”,或成为“擅自占地者”(Squatter)——在1913年以前,住在未被欧洲人实际占据的土地上的黑人约有32万。[8](p.359)“垦户”和分成制“拜旺纳”租用白人农场主的一部分土地,向主人交纳货币或实物地租。尽管地租苛重,但在分成制条件下,黑人佃农仍有一定的积极性,通过增加对生产的投入,在交纳完地租后他们的实际收入一般都要超过白人农场中黑人帮工的工资,比起封建农奴关系更重的工役佃农和直接到矿场做工的黑人,他们的生活更显得“自由”和“舒适”。所以,无地的黑人和从保留地出来的黑人大多选择去当垦户或对分制佃农,而不愿去做工役制佃农或到矿场做流动劳工。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对分制日益盛行,分成制佃农的人数猛增。这对急需劳动力的金矿产业极为不利,而金矿业正逐渐成为南非经济的支柱产业。当时矿场劳动力缺口达129364人。[9](p.621)大部分金矿由于劳动力紧缺而实际上处于停工状态。由于矿场的工资比战前还低,其他待遇和井下安全也比战前更差,返回矿下做工的黑人很少。在英布战争刚刚结束至南非联邦成立前的过渡时期,英国人主要是通过输入契约劳工特别是华工来解救燃眉之急。从1904年5月到1906年底,运抵南非的华工达63000-64000人左右,[10](pp.114-115)正是他们的劳动血汗使得南非的黄金产量迅速回升。矿业的恢复为英布战争后一度陷入窘境的南非“贫穷白人”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因而可以说,大批华工的到来实际上加强了阿非利卡人的经济地位,因为华人纯粹是苦力,只许承担非熟练劳动,不得担任诸如司机、机修工、管子工、电工、店员、会计员、工程师、医生等技术工种。[11](p.108)在实际工作中,每增加10名华工便可增加一名白人技工。德兰士瓦金矿业总会主席不得不承认华工的贡献:“中国工人对过去两年来工业的扩展有很大贡献,通过工业的扩展,千万人有了职业和收入,假如没有中国工人的输入,这些人在德兰士瓦是没有地位的。”[12]然而正如殖民初期运来奴隶一样,使用契约华工也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要一劳永逸地解决劳动力供应问题,仍有赖于当地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黑人民族。
无论南非的经济结构发生怎样的变化,对黑人土地的剥夺,是在其他领域里对黑人进行直接或间接剥夺的基础。南非联邦成立后,对黑人土地的剥夺仍在继续,在不放弃暴力的同时,主要是通过种族隔离手段,通过扩大保留地制度和实行班图斯坦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巧妙而又最大限度地实现对黑人土地和劳动力的剥夺和榨取。
二、“分别发展”的基础:《土著土地法》与“保留地”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经过深思熟虑,阿非利卡人上台伊始,就颁布了1913年的《土著土地法》。负责起草该法的是土著事务部长赫尔佐格,他主张立即采取断然措施,终止白人雇主和黑人佃农之间的对分制关系,结束黑人土地和白人土地棋盘交错的状态,认为禁止黑人购买白人土地的唯一办法就是采取种族隔离政策,实行“分别发展”,以“使整个南非不致成为土著所占据因此由土著所管理的国家”。[13](p.351)土著必须在政府划定的区域,即保留地内建立自己的家园,继续保存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同时,他们有义务为白人农场和矿井提供必需的劳动力。赫尔佐格提出建议说:“请不要把整个联邦都拿走。把它分开吧。一部分给班图人,让他们在那里按照自己的本性自行发展吧!”[4](p.37)白人议员几乎异口同声地表示:“法令应该规定欧洲人和土著两个种族基本必须分别居住于各自的地区。”[7](pp.41-42)
1913年11月27日,南非国民议会正式通过了《土著土地法》(The Native Land Act No.27 of 1913)。它明确规定:划定非洲人保留地的范围,禁止非洲人购买、租佃或占有保留地以外的任何欧洲人土地;禁止继续采用货币地租和分成制地租;在欧洲人农场上使用土地只许采用工役地租的形式,佃农每年必须为农场主服徭役90天以上;禁止非洲人在欧洲人占有的土地上进行任何独立的经济活动。
《土著土地法》一经公布,布尔人农场主立即掀起了大规模驱赶黑人垦户的浪潮。非国大秘书长普拉彻(Sol Plaatje)描述了非洲人的境况:“1913年1月20日,星期五,南非土著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实际上不是个奴隶,而是自己出生地上的贱民(pariah)。”[14](p.82)如此,随着金矿开采而逐渐崛起的黑非洲最早一批自耕农和佃农阶层,刚刚诞生不久就被《土著土地法》所赋予白人的种族主义经济特权扼杀在摇篮之中。可以说,1913年的土地法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peasants)和现代意义上的农民(farmers)的分水岭。⑤本来经过长期分化自然产生的新式农民阶层(farmer class)由于其进行生产活动的最主要因素——对土地的自由支配权被剥夺,而又重新回到了旧式农民阶层(subsistence peasants)状态,甚至地位还不如以前。结果是南非通往美国式资本主义小农经济的道路被堵住了,挡路的是种族主义的藩篱。
1913年的《土著土地法》使两个多世纪以来白人强占黑人土地的结果合法化,巩固了白人非法所得的成果。这部土地法严格限制了黑人土地所有权的地域范围,从法权上把南非的国土按照肤色界线划分成了两个部分,为后来全面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奠定了基础。南非第一届白人政府的核心人物史末资将军在一次演说中说:“在我们的土地所有制和管理形式中,我们的政策包括种族隔离……所以归根结底,在南非你将看到有广大的地区是由黑人耕作并由黑人管理,而在这个国家的其余地区则是由白人管理他们自己。”[7](p.30)[13](p.344)这种种族隔离政策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种族隔离政策的不同之处是,它一开始就深入到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范畴内,具有很大的韧性,不从制度和政权上变更就无法铲除。
《土著土地法》实施的基础是土著保留地(Reserve)。“打一开始,南非白人就抱定了这样的意念:黑人应当有他们自己的,但是将被迅速减少的领土,以适应白人的需要。当然,被禁锢在保留地的黑人,不能对白人的资源存非分之想,而且不应当构成对白人安全的某种威胁。因此,保留地的存在,纯粹是白人利益的一种直接表现”。[15](p.19)最早的保留地是英国传教士为布道和商业目的而设立的,称为教会保留地。由官方划定的保留地是英国驻纳塔尔土著事务秘书谢普斯通(Theophilus Shepstone)设立的,此后便在整个殖民地推广开来。1841年纳塔利亚共和国人民议会作出决定:“为了(布尔)共同体的安全起见,完全有必要将仍在我们中间生活的卡弗尔人安置到边远的地方”,“必须强行押送到指定的地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5](p.593)不管是英国人或是布尔人,设立保留地的直接目的都是为了获得非洲人的劳动力供应。布尔人坦白地承认,建立保留地是由于居民不能获得劳动力。[14](p.75)
1913年以前土著保留地的面积如下表(1摩尔根≈2英亩):[16](p.74)
省 面积(摩尔根) 在整个地区中的百分比
开普
71155618.47
那塔尔 2897120
22.83
德兰士瓦
10775133.22
奥兰治自由邦 742900.48
联邦 111644847.13
1913年《土著土地法》颁布后,在一些地区未能得到贯彻执行,仍有858000公顷的土地由非洲人所有,它们大都是黑人通过各种途径从白人农场主或政府那里购买来的,零星地夹在白人的大片地产之间。如何结束非洲人经济生活的“自成一统”,是白人处心积虑要解决的问题。
1927年赫尔佐格又提出了“土地法令”(The Land Bill of 1927),即1913年土著土地法修正案(The Native Lands Act,1913,Amendment Bill)。1913年土地法建议在保留地之外确立黑人可单独从政府或欧洲人那里购买土地的区域,也就是说,要另外划出一部分土地供黑人购买,但这一部分土地的面积到底应该有多大,当时并没有确定。1927年,赫尔佐格提议划出一个让渡区域(released areas),在那里黑人和白人都可以竞争购买土地。只是规定白人在区内不得购买周围全部被黑人土地围住的土地,反之亦然。这样的地区占了保留地之外联邦土地的大约8%(根据1913年土地法)。除了以族体为单位,法案还禁止各种“土著人协会”购买土地,如工商业联盟。如果欧洲人要卖掉在“让渡区域”内购买的土地,黑人可以购买与“让渡区域”外亩数相等的土地,如果它与黑人土地相邻。黑人和白人土地之间必须筑有篱笆。[16](p.140)
这一对白人作出了巨大让步的主张甚至得到了黑人的赞同,尽管黑人处于明显的劣势,他们认为黑人和白人竞争购买土地的建议还是公平的。然而白人农场主认为1927年土地法由于实行起来过于复杂,结果其中的大部分内容被白人议会所拒绝。他们所接受的只是其第19条的规定,即在法令正式实施前,白人农场主要容留和使用非洲“垦户”(squatters)或分成制佃农,必须领取许可证,但得到许可证的条件是使用劳役佃户,并且要交纳3英镑费用,如果欧洲人实际占用该土地;如果未实际占用,费用为5英镑。[16](p.141)这是强化1913年土地法的规定。少数农场主为了补偿领取许可证的费用,趁机同佃农或“垦户”签约,将他们变成仆役(servants),长年留在主人那里劳动。有些农场主不愿交纳费用,便通知佃农或垦户要么变为仆役,要么离开农场。这一部分黑人由于在人口过多的城市或保留地已经无法找到容身之地,被迫变为欧洲地主的仆役,即长期劳役佃户。当时就有人质疑说:这样的话,佃户“将没有合同的自由,所谓的仆役将与奴隶毫无区别……这比废除奴隶贸易前南非土著的条件有任何改善吗?”[16](p.146)尽管法令中并未暗含这些黑人可能被买卖的内容,他们却可以被主人从一个农场转到另一个农场,“这将是强迫劳动的最高形式”。[17](p.147)
1927年赫尔佐格还促使议会通过了“土著管理法”(The Native Administration Act No.38 of 1927).规定设立一个“土著委员会”,授权该委员会处理有关保留地的一切问题,并考虑将一些行政权授予保留地的酋长。1927土著管理法的目标是确保黑人社会文明的解体,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教会土著(为白人)工作”。[16](p.11)1936年,在政府授意下,一些酋长组成了“土著代表委员会”,作为政府在种族问题上立法的咨询机构。从这些机构的设立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班图斯坦制度的一点雏形。
1936年4月,阿非利卡政府又通过了《班图人托管与土地法》(The Bantu Trust and Land Act No.18 of 1936)。这一法律是对1913年土地法“分别发展”方案的进一步完善和补充。根据这一法律,政府将在5年内收购价值一千万英镑的土地以扩大黑人保留地的面积,解决黑人购买土地的问题。这部分“让渡”出来的土地实际上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黑人“自由”购买,另外相当大一部分由新成立的“南非土著托管局”(The South African Native Trust)出钱从白人农场主那里收购,然后用来“安置黑人,拓殖这部分土地,促进保留地的农业,从总体上提高黑人的物质条件、道德和社会福利水平”。[18](p.40)在托管局的农场上,黑人实际上成为土著事务部的佃农,每人耕种的土地不超过5摩尔根,这对于维持生存来说极其艰难。欧洲人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拒绝让出哪怕是一英亩的土地来增加土著的居住面积,他们坚信,为土著附加任何土地份额都将对他们的劳动力市场构成威胁。[19](p.107)南非的经济生活依赖于一个庞大的劳动力储备的存在,而“黑人作为独立的农业耕作者(拥有土地)不能实现这个功能”。[18](p.41)黑人保留地的总面积最终只增加到154000平方公里,仅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2.4%,尽管南非黑人的人口增加了数倍,保留地的面积却一直没有再增加,而为了换取这不到13%的土地面积,黑人付出了巨大的政治代价,原先仅有的一点选举权也被剥夺殆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非利卡政府对黑人的控制稍微有所松动,黑人民族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卓越的经营能力“向白人地区发展”,原来的“黑点”不仅没有彻底消灭,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还有向城市——阿非利卡人生活的中心区蔓延的趋势。战争结束后,阿非利卡人又重新感受到了国内日益增长的“黑色危险”。当时席卷非洲大陆的黑人民族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风暴也使阿非利卡人受到极大的震动。1948年,在新一届政府选举中,极右派国民党人马兰上台执政,从此开始了南非种族隔离从政策向制度的根本转变。
三、“分别发展”的最高阶段:“黑人家园”的设立
在极右国民党人上台以前,尽管已经采取了不少从地域上分离白人和黑人的措施,但都不是以各个民族单位为基础。伴随着种族隔离理论的出台,政府的立法步骤也接踵而至,并且一步比一步加强和严厉,阿非利卡人开始以民族为单位把各个黑人族群隔离开来,过去的黑人保留地变成了“班图斯坦”,即所谓的“黑人家园”。这是继1936年剥夺了所有南非黑人的选举权后进一步剥夺所有南非黑人的公民权,从而剥夺他们所有资源的举动。
1951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了“班图权力法”(The Bantu Authorities Act of 1951)。根据这项法律,撤销了1936年的“土著代表委员会”,建立部落、地方和地区三级“立法会议”。立法会议的主席皆由酋长担任,由白人政府支给他们薪金。1954年,由政府任命的以汤姆林森为首的“南非联邦班图人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委员会”提出了一份调查报告,它首倡将当时所有三百多块黑人保留地合并为8个班图斯坦,实行分别发展,由白人作为班图居民的监护人履行他们的职责。这份报告被誉为班图斯坦制度的“圣经”。根据报告的建议,阿非利卡政府于1959年通过了“促进班图自治法”(The Promotion of Bantu Self-Government Act of 1959),规定在不同民族的基础上建立8个由白人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班图自治区”,⑥把原来的“地方立法会议”改为班图人“议会”,设立“班图人自治政府”,通过将古老的社会机构现代化来强化传统酋长的权力。这样,获得了自治的班图人民族单位就不再称为“保留地”,而叫做“班图斯坦”(Bantoustans,即“班图人的家园”)了。1959年3月,原来由科萨人居住的几块保留地被归拢到一起,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特兰斯凯“地方立法会议”。1963年,阿非利卡政府通过了“特兰斯凯宪法”,第二年,在特兰斯凯成立了黑人“议会”和“政府”,第一个“南非共和国范围内的自治地”,即第一个班图斯坦就这样建立起来了。从1968年到1975年,阿非利卡人又相继炮制了9个班图斯坦。
20世纪60年代正是非洲大陆非殖民主义化的高潮阶段,受其他非洲国家黑人民族运动的影响,南非黑人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下加紧了反对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斗争。为了“顺应”形势,堵塞社会舆论谴责的口实,1961年维沃尔德总理表示:“迫于南非所受到的外部压力,政府应当把班图斯坦的政治演变一直引导到最后的独立。”他进一步解释说:“这种使南非变成好多个国家的支离破碎的局面,如果力所能及的话,我们显然是宁愿予以避免的。但为了白人在这个归他们所有的国家里换取他们所要求的自由和权利,(允许黑人独立),这是唯一的办法。”[20](pp.74-75)1970年,南非政府通过了“班图斯坦国籍权利法”,规定所有黑人必须取得他所属的班图斯坦的国籍。1976年10月,特兰斯凯,这个最早建立、面积最大的班图斯坦宣布“独立”。按照南非政府的设想,其他9个班图斯坦最终都要脱离南非而“独立”,成为名副其实的“黑人家园”(Homelands)。
“黑人家园”的民族与面积:(单位:平方英里。1平方英里=2.59平方公里)[21](p.2)
“家园”名称主要民族 面积
特兰斯凯科萨人 14178
西斯凯 科萨人
3547
夸祖卢(或译克瓦祖鲁) 祖鲁人 12141
莱博瓦 佩迪人/南恩德贝莱人 8549
文达文达人
2333
加赞库卢尚加/聪加人 2576
博普塔茨瓦纳茨瓦纳人14494
巴苏陀·夸夸南苏陀人 144
斯威士 斯威士人 818
南恩德贝莱 南恩德贝莱人
从最初的保留地和特居地到最终的班图斯坦和黑人家园,这中间隐藏着白人政府的一个极其险恶的用心,即强制非洲人画地为牢,把占南非总人口76%以上的黑人严格地圈在不到13%的南非国土上,从根本上剥夺他们对整个南非所享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保留地内的南非黑人还是南非的国民,而到了班图斯坦和黑人家园,南非黑人却成了“南非的外国人”。在世界近现代史上还从没有哪一个国家政府宣布境内的绝大多数国民为外国人的先例,而阿非利卡人政府却公然做出了这样的“创举”,把300多块面积狭小、互不连结、资源贫乏、贫困不堪的非洲人保留地归并成10个左右“自治”或“独立”的民族单位,使占南非76%以上的黑人变成“外国人”,从而将黑人过去创造的全部财富堂而皇之地攫取到白人自己的手里,继续无休止地榨取他们的廉价劳动力,并使南非的土地问题永久性地极端恶化。对此,就连被迫“独立”的黑人家园的领导人也看得明白,在特兰斯凯宣布独立前夕,6位班图斯坦政府的首席部长发表了一份共同声明:“我们拒绝放弃我们生来作为南非人的权利。我们将要求分享主要是由我们创造的经济财富。”[21](p.75)非国大也指出,把班图人分离出来并剥夺他们在国内其他土地上的基本机会和权利,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非洲人是本土的居民,对全国各地的发展做出了充分的贡献,他们对整个南非作为他们的家乡拥有不容争辩的权利。[13](p.356)
事实上,黑人家园独立的过程也就是黑人丧失最后一点独立生存权利的过程。尽管经过1913年和1936年土地法的剥夺,由于黑人的抵抗,在半个世纪的时间内,阿非利卡人并未能完全将黑人“垦户”即所谓的“擅自占地者”逐出白人尚未垦殖的土地,而令白人恐惧的“黑点”也没有完全消灭,到1976年,仅克瓦祖鲁地区就有144个“黑点”。在确立班图斯坦制度的过程中,阿非利卡人有意加强了对这两部分黑人土地的最后一轮剥夺。1950年政府颁布了“集团住区法”,1957年通过该法的修正案,都曾强迫黑人迁离,但收效并没有预期大。1959年“班图自治法”出笼,政府一再提出“归并方案”,要求对土地占有状况进行调整。这表面上看来是为黑人家园的完整着想,因为各个班图斯坦地域狭小,大都由数块乃至数十块互不相连的飞地组成,这本来是白人长期以来蚕食和侵吞黑人土地的结果。博普塔茨瓦纳“总统”曼戈佩在“独立仪式”上曾抱怨说:“我‘国’领土七零八落,完全缺乏可信性,会使全世界认为南非的意图是十分可疑的”,同时这也是“令人不安的怨恨的源泉”。[22]现在,白人政府提出归并土地,并不是要实现黑人家园的“领土完整”,而是别有用心,即彻底消灭“黑点”,将“擅自占地者”驱逐到黑人家园。在1960至1970年十年间,656000名“擅自占地者”和10000名“黑点”上的黑人农民被没收了土地,驱赶出白人地区。70年代以后,归并规模越来越大,仅1973年“归并方案”涉及的黑人人口就达100多万。1973年班图事务部又提出了“重新定居计划”,涉及的黑人总数达400万人以上。成千上万的黑人家庭被迫迁离故土,搬进黑人家园,他们中的许多人是“黑点”上的居民或“垦户”,还有一些人居住在本来就属于自己的私有土地上。
事实上,黑人家园从来就没有固定不变的“国土”,一切都服从于白人政府的需要。70年代初,在莱布瓦(Lebowa)和博普塔茨瓦纳(Bophutatswana)两个黑人家园发现了富矿,其开采权落到了阿非利卡人手里。1975年白人政府又从克瓦祖鲁黑人家园的滨海地区割走了一块世界罕见的钛矿地带。1978年,南非政府又以安全为由,索回了文达一块长60公里、宽10公里的边境地区。由此可见,炮制黑人家园的过程就是继续剥夺非洲人地上和地下资源的过程。尤为荒谬的是,被阿非利卡人宣布为第十个黑人家园的南恩得贝莱,当时竟然寸土皆无。
把上千万黑人驱赶进黑人家园,一方面是要夺走他们的资源,另一方面,对这些资源的开发还有赖于失去土地而无以生存的黑人劳动力。这是制造黑人家园所产生的一箭双雕的效果。南非经济在20世纪50-70年代种族隔离制度最为严酷的时期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发展,创造经济奇迹,除了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外,最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黑人家园的实施造成数以百万计的廉价劳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白人农场机械化的加强使农业部门与工矿业部门争夺劳动力的现象成为历史。根据1980年12月第2089号政府通知(Government Notice 2089 of September 1980),南非正式废除了阿非利卡人农场主偏爱的佃农制度。这些“释放”出来的黑人被迫回到家园,加入失业劳工的队伍,等待他们的就是和自己的同胞竞争获取城市和工矿业中心提供的微薄的工资。南非矿业劳工组织总经理就此解释说:“我们的情况一直是这样:我们需要农民作为劳工,我们的工资不足以满足一个工人及其家庭的需要,除非以其家园内一小块土地的收入作为补充。例如,来自约翰内斯堡的一个有家口的男子,不可能依靠我们发给的工资糊口。”[18](pp.57-58)在先后成立的十个黑人家园中,半数或绝大多数的人口都直接住在白人地区,向白人农场主和矿业资本家出卖劳动力;住在黑人家园的黑人,大部分青壮年男子也不得不到白人资本家开办的“边境工业”区做工。颇具代表性的是面积仅457平方公里的黑人家园——南苏陀·夸夸(Qwaqwa),在法律规定持有该“国”国籍的黑人人口中,只有25000人居住在本土,其他1200000人都住在白人地区为资本家做工。[4](p.63)在家园之外的整个白人地区,大约有三分之二的黑人在城市和矿区直接为白人资本家从事工矿业生产,或作为他们的家庭奴仆;另外三分之一在白人大农场上做农业工人。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没有班图族工人,南非的农场和企业就会在五分钟内陷于停顿。”[23](p.27)黑人家园存在的唯一和最大的功能就是可以在那里再生产没有公民权的劳动力,而白人资本家完全可以以低于劳动力成本的低廉价格在榨取完他们的潜力后把他们打发回家园。一位班图人牧师说:“你们(欧洲工厂企业主)需要我们的劳动,但是,一旦我们为你们不需要时,你们就把我们送走,尽可能离你们远些,而且一直到我们的劳动又为你们所需要以前,你们再也不想看见我们,我们就象马一样,在工作以后被关进马厩中去。”[24](pp.768-769)在六、七十年代,大约有400000黑人被认为已经失去了“生产能力”,结果像垃圾一样被扔进了黑人家园。[25]正如沃斯特公开宣称的那样:“问题的关键是我们需要他们,因为他们是给我们干活的……但是为了使他们给我们干活,就永远不应当给予他们索取政治权利的合法资格。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不管是否已经让他们在这里长住。”[15](p.19)关于这一点,史末资政府早在1922年就有明确说明:“白人建立和专有的城市,黑人只有在他们准备为白人服务的情况下才能被允许留在那里,而在完成任务后就应该让他们离开。”[4](p.223)马兰也承认:“我们全部的经济结构主要是依靠土著劳动”。[26](p.140)1970年土著事务部长博塔重申:“不管是在哪些方面,任何社会平等,都是与白人地区的黑人毫不相干的:他们在那里没有发言权,他们既没有产业所有权,也不能从同样的职业中得到好处。”[4](p.224)他们所能做的,就是长期做白人的流动劳工。正是贫穷的、仅占南非全国土地面积12.4%的“黑人家园”源源不断地向发达的“白人家园”输送肉体能源,才使南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保持着非人道的经济繁荣。用布罗代尔的话说:“若不借助别人卖身的劳动,它大概压根儿就生长不成。”[27](p.62)
通过独到的精心设计,南非白人政权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部分实现了“分别发展”的目标,即南非白人经济的现代化。但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这条按照种族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铺就的路径不依白人意志为转移地指向了死胡同。到20世纪80年代,“分别发展”实际上已经完全停滞,南非白人一度引以为自豪的经济繁荣转变成了负增长,白人的政治统治也面临着黑人反抗的巨大冲击,阿非利卡人政府在国际上更陷入空前的孤立。万般无奈之下,南非历史上最后一位白人总统德刻勒克鼓足勇气,释放了黑人领袖曼德拉,通过公正的选举,曼德拉成为新南非的领路人。令人钦佩的是,曼德拉及其继承者姆贝基还原了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不是以种族,而是以民主为手段为南非的全面现代化开辟新的路径,尽管目前困难重重,但没有分别的发展无疑会前途光明。
收稿日期:2008-05-04
注释:
①关于在这场战争中英布双方投入的兵力和伤亡人数,各种史书统计不一。有的估计英国人阵亡数高达21000多人(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8,p.631.);威勒登认为,布尔人及其奴仆共有26万人被关进集小营,其中12万人为布尔人老弱妇孺。参见D.L.Weidler,A History of Africa:South of the Sahara,New York,1962,p.302.
②据1904年的人口统计数字,南非的欧洲人口为1116806,仅占总人口的21.6%,而非洲人口,包括黑人和有色人,占了当年人口总数的78.4%。参见Union of South Africa,Office of Census and Statistics,Census of the European or White Races of the Union of South Africa,1918,Part I-Population,Cape Town,1919,U.G.50-1919,S.P.10A,p.2; p.18.In D.Hobart Houghton and Jenifer Dagut,Source Material on the South Africa Economy-1860-1970,Oxford Uni.Press,1973,Vol.2,pp.203-204.
③Bywoners和Bewoners为当时的术语,都是“居住者”(residents)之意,更确切地说,是“寄居者”。两者的区别是:当Bywoners是地主自己的儿子——无论已婚与否,或是自己的女婿时,就变成了Bewoners。也就是说,Bewoners和其寄居的农场主之间有父子或姻亲关系,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但作为独立的农牧民拥有自己的畜群。参见Timothy J.Keegan,Rural Transformations in Industrializing South Africa,Ravan Press,1986,p.21;pp.226-227,notefoot 5.Bewoners在国内尚未见有合适的译名,笔者姑且将之译为“白旺纳”。
④根据1911年的普查,南非境内黑人农业人口为3880514人,保留地面积只有11164484摩尔根,人均占地在3摩尔根以下。参见Buell,The Native Problem in Africa,Vol.1,New York,1928,pp.74-75.
⑤关于“农民”一词的定义,一般认为peasant的最主要特征是其经营活动受到外力(外在的强制力)的制约,商品化程度阙如或很低;而farmer更具近现代意义,自由度比较大,商品化程度高。参见C.Bundy,The Rise and Fall of South African Peasantry,California,1979,pp.4-13.清华大学历史系的秦晖认为农民(peasant)是以农业文明时代人的依附性为本质的共同体成员,而farmer是“种田人”,作为一种自由公民的职业,它完全可以存在于市民社会。参见秦晖:《农民问题:什么“农民”?什么“问题”?》,《方法》,1998年第8期。
⑥这8个黑人民族单位为Lebowa(北苏陀人)、QwaQwa(南苏陀人)、Bophuthatswana(茨瓦纳人)、KwaZulu(祖鲁人)、KaNgwane(斯威士人)、Gazankulu(聪加人)、Venda(文达人)、Transkei和Ciskei(科萨人)后来又增加了South Ndebele(夸恩得贝莱人)作为黑人民族居住单位。
